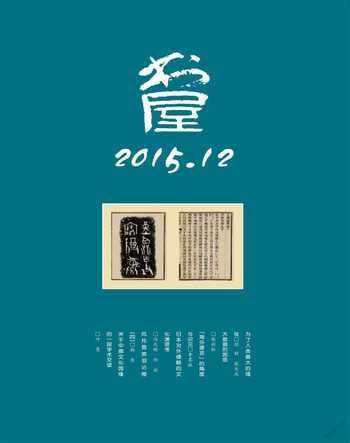黄绍湘:天不容伪
《书屋》杂志在2007年第二期发表了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刘绪贻的《我研究美国史的经历》一文(以下简称为《经历》)。刘绪贻在文中一开始就写道:“我发表过研究美国史甘苦的文章。承蒙《书屋》编辑部的信任,让我再系统地谈谈我研究美国史的经历。我觉得《书屋》编辑部的这种意图必有其理由,所以乐于遵命。”刘绪贻在该文中总结了他的经历,强调他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为了突显这一点,他全面反驳了上级对他的批评,更不惜以不实之词,对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研究美国史的黄绍湘教授进行人身攻击。由于刘绪贻的文章流传甚广、影响深远,致使黄绍湘蒙受了不公正的名誉损害。
按照刘绪贻在其《经历》一文中所述:“当时我研究美国史,经常感到一种‘紧跟’的负担。美国史中哪些部分可以研究,哪些部分不可以研究;美国历史发展进程遵循什么规律;美国历史上人物和事件应如何评价等等,都是要有指示,尤其是最高指示作根据的。违反或背离这种根据,不独研究成果不能问世,而且会招引批判甚至祸灾……还得经常打听关于美国的事务最近有什么最高指示,发了什么最新文件,以便找来阅读,作为紧跟的根据,否则寸步难行。”由此可见,刘绪贻自己当时是以跟风的办法来进行他的美国史研究的。
刘绪贻在建国初期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宣誓要为了共产主义的事业而奋斗终生,但是这却并不一定成为他的真正信仰。改革开放以来的宽松政治气氛,才使得刘绪贻能够畅所欲言。2011年5月,在腾讯《大师》第三十六期上,刘绪贻与沈洪联名发表题为《刘绪贻:一个自由主义者的生活态度》长文,其中刘绪贻明确描述了他目前所真正信仰的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像瑞典那样的社会民主主义:“我当时考虑到,二战以后,法西斯主义完蛋了,到了九十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也完了。还有一种是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他还存在。还有一种就是民族社会主义,这四种。这几种当中,从我的想法,我感觉到将来整个人类的前途,主要是向社会民主主义发展,就按照瑞典这个道路前进。我就希望大家能够看了这个书(按:该书即为刘绪贻在香港出版的《箫声剑影:刘绪贻口述自传》)以后,就觉得将来这个社会应该向这个道路走,只有这个才有前途,我写这个书主要的目的就是在这儿。”
在该文中,刘绪贻还进一步表述他的真实观点:“中国人他所想的宇宙,都是他空想出来的,而美国人他是从一点一滴研究,这样慢慢积累起来的,所以美国他有科学。”又说:“因为我做学问,我是不在乎毛泽东怎么想,马克思怎么想,我怎么想就怎么想。”
再回顾一下刘绪贻在《经历》一文中是如何评价自己的工作的:“(一)我和同僚、研究生一起冲破了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个禁区。(二)我成功地为罗斯福‘新政’翻了案。(三)我提出了两个新概念。(四)我提出了两条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规律。(五)我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原理和列宁关于垄断资本主义亦即帝国主义的理论。”
刘绪贻“冲破了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个禁区”的说法,十分含混笼统,缺乏事实根据;他也没有认识到,在美国乃至全世界罗斯福“新政”都从未曾有过什么定案,那么他又从何来翻案呢?至于他的第三、四、五条,也只是他的一家之言。
刘绪贻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发表的涉及马列主义的文章,很快就受到了国外的注意。1983年,刘绪贻接到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邀请,准备1984年6月去意大利的贝拉焦参加一个名为“外国人心目中的美国史”国际学术会议,并写了一篇准备提交会议的论文《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史与马列主义》。
黄绍湘敏锐地察觉到了刘绪贻的新观点,而且果敢地在当时“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思潮下,先后发表了三篇文章,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来指导美国史研究,并对刘绪贻关于罗斯福“新政”的观点进行了未指名的学术批评。刘绪贻随即以“与黄绍湘同志商榷”为副标题,做了反批评。然后,黄绍湘再以“答刘绪贻同志”为副标题,深入展开争鸣。
之后,刘绪贻没有再发表文章,这场正常的学术争论似乎也就到此罢休。但是,2001年刘绪贻在他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美国史论丛》中,附了一个据称是1999年写的后记,解释:“此文发表后,黄绍湘教授曾在《世界历史》1985年第八期上发表文章进行答辩。我本来准备写文章争鸣,但后来听从了朋友们善意劝告:是非曲直,让读者去评论。于是,我就未再为此专门写文章。”刘绪贻愿意保留自己的观点、不想进一步争鸣,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他在该书的序中却又提出:“要为罗斯福‘新政’翻案就很可能受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者的攻击,因而具有一定的风险。后来我的确一再遇到这种风险。”刘还称“频遭阻抑,屡挨闷棍”,看来他是把这场正常的学术争论称之为“阻抑”、“闷棍”了。刘绪贻不继续与持有不同观点的人展开争鸣,却给对方扣上一顶“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者”的帽子,这种做法实在令人无法认同,难怪他在后来要发表针对黄绍湘的不实之词,也就不再遵循学术争论的正途了。
2012年8月23日,《南方人物周刊》的记者专函向刘绪贻《经历》一文中的以下文字求证:“……此文发表后,引起较广泛共鸣,有些出版物全文转载。但是,由于此文对于‘新政’的看法,和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长黄绍湘教授美国史著作中对于‘新政’的看法很不相同,她就写了《开创美国史研究的新局面》和《开创我国美国史研究新局面的浅见》两文,不点名地对我的观点进行批驳。1985年,《世界历史》又先后发表了我和黄先生争鸣文章。本来,学术争鸣应该是很正常的事情,对发展学术有好处。但是,可能由于支持我的观点的人较多,黄先生就不再遵循学术争论的正途,却写信给她的朋友、当时中央政治局宋平常委告了我的状,说我把中国美国史研究会领导得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宋平同志将此告状信批转给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处理,胡又将信批转给该院所属世界历史研究所,也就是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挂靠单位。该所虽然并不支持黄先生告状信(尽管黄是该所研究人员),但它顶不住那么大政治压力,只好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秘书处转到南开大学去了事。”
黄绍湘的家人根据事实,当即回函反驳了刘绪贻针对黄绍湘的写信告状、迫使美国史研究会秘书处迁址的不实之词。《南方人物周刊》在2013年3月11日,发表了题为《刘绪贻 百岁老人看中国》。该文依然提到了黄绍湘教授的名字及她与刘绪贻之间存在的学术争论,但是已经摒弃了刘绪贻上述不实之词。谣言止于智者。
然而,经过我们的调查,发现包括“百度·百科”、“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网站”等几十家网站和书刊,全都未加核实地转载了刘绪贻《经历》的全文、或者摘登了包括上述不实之词的文字。针对黄绍湘的不实之词,就此不胫而走,在美国史学界和网络上广泛流传。甚至于在《百度·百科》词条“刘绪贻”中,“与黄绍湘论战”被列为刘绪贻人生的四大经历之一,而且是解放以后的唯一经历。
那么,事实真相又是如何呢?
首先,当时宋平同志是中央组织部长,并不分管人文科学、教育、意识形态等问题。根据我们了解的事实真相,黄绍湘作为宋平的同学,虽曾与他通过信,但是完全没有涉及刘绪贻及美国史研究会的问题,更无告状之事。
至于刘绪贻认为可能由于支持他的观点的人较多,黄绍湘就会去“告状”,这实在是违反历史事实的一种主观臆想。黄绍湘在学生时代就为了抗日救国成为“一二·九”运动骨干,由清华大学全体学生选举为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代表,后来加入了共产党(那时刘绪贻也在清华大学);她由党组织资助赴美留学时又积极参加美国共产党中国局领导的进步活动(那时刘绪贻也在美国);解放前她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白色恐怖下积极从事共产党领导的地下工作(那时刘绪贻也在国统区)。北京师范大学张宏毅教授在1996年评论和介绍黄绍湘的专文中特别肯定:五十年代抗美援朝时期,“一边倒”之风刮得正烈,黄绍湘在1951年公开发表文章《评〈美帝破坏条约的历史上的罪证〉》,反对随意摭取历史史例,作为揭露美国的“历史罪证”。黄绍湘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历史上的一切制度、现象、政治人物、个别问题都由当时当地的历史条件所规定,我们着手分析时,必须依据当时当地的具体历史条件,去评定它们(或他们),不然,就会陷入简化主义或公式主义的错误,就是非历史观点的方法。”她在文章的末尾总结性地指出:“我们研究历史,尤其研究其他国家的历史,要站稳科学的历史的立场,绝不可以牵强附会,曲解历史,因为任何外国史的研究,在国内还是崭新的园地,我们对于任何专题的研究,如果不用冷静的头脑,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处理,就会发生严重的偏差,引起学术界的混乱现象的。”
黄绍湘从青年时代就信仰马克思主义,并以此作为研究美国史的指南,在不同历史时期,她始终不跟风,她也从不畏惧属于少数派而去与当时所谓的多数派直面抗争。黄绍湘早已将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她还有何惧?她又何需去“告状”?当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甚嚣尘上之时,她接连发表数篇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招致某些人的忌恨,个别人甚至在背后辱骂她为“马克思主义的僵尸”,她听到后只是付诸一笑,不予理睬。这样铮铮铁骨的共产党员,岂能是某些人(即使也有共产党员的称号)所可以吓倒的?因为属于少数而去“告状”之类的话,栽在黄绍湘的身上,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刘绪贻理应尊重客观史料。那就让我们回顾一下有关美国史研究会秘书处迁出武汉大学的史料吧:
1990年3月9日,刘绪贻在给北京师范大学黄安年教授的信中谈到:“从心理上说,我对研究会有感情,秘书处留在武大我或许感到安慰。但是,我只是研究会五个顾问之一,我只愿意就如何加强研究会的工作提出建议,我不能、也不会干预你们理事会的任何决策。下届理事会为了加强研究会的工作,决定把秘书处放在哪个学校,我都没有意见。超过以上范围的话,就不是我说的。”
时隔十七年之久,在2007年初,刘绪贻在他的《经历》一文中,却对此公开发表了与他在1990年3月9日所说的完全不同的说法,即那些针对黄绍湘的不实之词。
那么,刘绪贻的“超过以上范围的话,就不是我说的”话,又是从何而来的呢?请读者参考我们查到的以下旁证线索:2015年3月19日,黄安年教授发表文章写道:“由于众所周知的非学术因素,1989年后秘书处被迫由武汉大学迁往南开大学。……对于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秘书处由武汉大学迁往南开大学的细节,相信在刘先生自述(下卷)中会有他自己的回忆。就我所知,由于有关人士对于研究会学术自主和学术问题不同见解的非学术性的粗暴干预,迫使秘书处改址,使学术问题政治化,这既非广大会员的愿望,也实际上造成了对刘先生和武汉大学美国史研究室集体的感情伤害。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主管单位即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的相关负责人曾暗示我:他们深感沉重压力,如果研究会秘书处不迁往南开,那么中国美国史研究会能否存在都会成为问题。我感到在当时特殊的政治气氛下,非学术因素的思考一时让我们难以清醒、自主和抗命。”按照黄安年的文章,“有关人士”不仅“迫使秘书处改址”,并且威胁到“中国美国史研究会能否存在”。不知黄安年所指的“有关人士”为何许人也?对黄安年做暗示的“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主管单位即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的相关负责人”,又是谁呢?黄安年对这些问题应该有所回答。
经由刘绪贻等人之口,那些针对黄绍湘的不实之词以讹传讹,损害了黄绍湘的名誉,已是不争之事实。我们出面要求刘绪贻和黄安年这两位资深历史学家,对其进行史料的求证工作,这应当是合情合理的吧?在他们还没有对此作出反应之前,请允许我们提供一些“秘书处迁址”的相关事实吧:
我们在网上查到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大事记(1978—2009)》,系美国史研究会秘书处文,发表于《美国史研究通讯》2009年第一期;学术交流网/美国史研究会/2009年12月27日发布。该大事记中写道:“1986年,8月2至9日,我会在兰州召开第五届年会,此次会议选举产生第四届理事会,由十九名理事组成。理事长为张友伦,副理事长为顾学稼、齐文颖、李世洞,李世洞兼任秘书长,并聘请宦乡等五人为顾问。”“1990年,……根据新理事会的决定,研究会秘书处由武汉大学迁至南开大学。”“秘书处地址:武汉大学1979—1990,南开大学1990—2002,厦门大学2002—至今。”
从以上史料记载,我们认为:南开大学知名美国史专家张友伦教授,1986—1996年任美国史研究会第四、五、六届理事长,南开大学在世界历史研究分工中侧重北美、美国史,这才是美国史研究会秘书处从武汉大学迁到南开大学的真正原因;况且秘书处迁移,是由第五届新理事会决定,这与刘绪贻等人的所谓“世界历史所顶不住压力”的说法,出入太大,实在令人惊诧。
我们还特别以电子信件的方式,就此事向一位当时的副理事长求证,他的回答跟我们分析的一样,根本否定有什么“压力”:“……关于刘绪贻所说美国历史研究会由武汉大学迁往天津一事,我认为刘的看法是不对的,想系他的猜测。因为世界史所管不了那么宽,也不会去管。因为研究会之类的组织并非官方的,而是民间的。武汉离开北京较远,人手也不多,而天津南开的美国研究人员要多些,办事的人手当然也多一些。所以就由南开的人来办事,实际上所办的事,就是发发通知,联系一下各地的同行而已。其他什么都没有,也没有人想争这么个差使。办事机构设在某地,绝不意味着该地就是中心。刘可能是多疑了。他以前常说,什么什么人不让他发展马列。他说这个话,就说明他的疑心病有点多……”由此可见,向当时决定“秘书处迁址”的理事会成员求证,并不是一件难事。
在此还需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刘绪贻在他的《经历》一文中,用了约百分之二十一的篇幅,谈到他研究美国史遇到的主要阻力,这就是“‘左’倾教条主义的势力仍然雄厚”,其中,刘绪贻以三百六十五字针对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黄绍湘,一千六百零四字针对他当时的上级。让人深思的是,某些人在网站上却偏偏瞄准了刘绪贻用字最少的“阻力”黄绍湘,大加宣扬一些不实之词,这是因为黄绍湘的数篇关于“罗斯福新政”的文章,史实详尽、论点清楚,是某些人无法公开、正面驳倒的。他们只能匿名于网上反复转载刘绪贻的不实之词,把一场公开的学术争论,发展为混淆是非的人身攻击。历时八年之久,如此兴师动众,谁能相信这是一个偶发事件呢?
人没有什么事不能做出来,只是天不容许人作伪。
(此文中所有引用的资料,均有确切出处。因篇幅所限,无法在此刊出。有兴趣的读者,请发电邮给huangshaoxiangworkshop@gmail.com,索取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