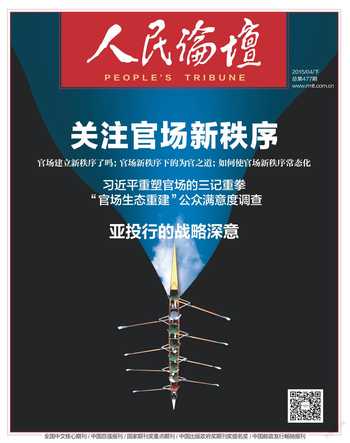官场秩序的运行逻辑与变革轨迹
宇文利

【摘要】在当代中国,伴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和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官场秩序的变革已经势在必行。构建一种服务于现代政治运行体系、致力于党和国家改革发展进步目标的新型官场秩序,不仅关系到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也关系到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顺利发展。构建现代官场新秩序亟待扭转官员的思想认识、整肃官场不良习气,重建以民为本、施政为民的根本利益标准,秉持群而不党、廉政高效的政治行为原则,坚守有为无私、行而不殆的实践道德操守。
【关键词】 官场秩序 政治生態 运行逻辑 【中图分类号】D602 【文献标识码】A
官场是古今中外所有国家管理体系和政党政治中普遍存在的官员个体生存、职业活动和社会交往的空间和场域。在古代的官场中,官员和公职公务人员之间大都存在着经济依赖、政治关系和交往互动,因而相互之间也呈现出盘根错节的人身隶属和政治依附关系。自从现代文官制度在西方出现并在世界各国普及以来,官场的他律性、自治性、自为性等现代性特征日益显露,并不断得到孕育和发展。在当代中国,伴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和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官场秩序的变革已经势在必行。构建一种服务于现代政治运行体系、致力于党和国家改革发展进步目标的新型官场秩序,不仅关系到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也关系到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顺利发展;不仅关系到中国政治建设和党的建设的成效,也关系到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和持续繁荣。
官场秩序最能够体现出时代政治的本质与特色,在特定政治框架下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持久性
官场是通俗性的民间话语,在日常使用时往往会包含贬义,它原意指的是官吏阶层的生态及其活动的范围。实际上,从古到今,无论中外,在政党和国家的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中,政治运行、党派活动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营建与官员的存在、发展和作为紧密关联的风气、氛围、规则和生态,这就是所谓的“官场”。任何“官场”都包含并依靠既定的工作程序和行为规则来维持其常规运转,这种程序和规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官场秩序”。在表面形态上,官场秩序是官员基于一定的关系规则和行为规范、出于对政治或社会目标的遵循而采取的有序的政治行为与活动状态。但实际上,官场秩序却是特定社会政治生态的直接反映,是政治行为人在特定的政治制度环境和政治文化环境中所采取的适应性行为的统一外化和整体表达。具体而言,官场秩序由较长时期内官场运行的基本社会规则、工作规范和交往准则所建构并维系,体现的是官员在以领导、管理和行政为主体的社会活动中所遵守的关系模式、行为结构、工作状况和活动状态。从本源上看,官场秩序是在特定的政治制度、行政文化、管理机制与特定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环境和状态相互作用下产生的,具有明显的政治属性、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也最能够体现出时代政治的本质与特色。
官场是变动不居的,但在特定政治框架下形成的官场秩序却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持久性。这种稳定性和持久性与社会政治环境、结构及其变革有密切联系。当社会发展处于平稳期,社会的政治环境相对封闭、政治结构相对固定之时,官场秩序就相对固化,不易发生变革。此时,官员和政治行为人即便部分地发生变化,也不大容易撼动原有的官场秩序。在早期西方文明国家和中国古代社会中,奴隶制和封建制王朝中的官场是由存在严重人身依附关系和政治隶属关系的官吏们所组成的,官宦之间的相依、相护和相卫成为当时官场秩序的官场法则,久而久之也就形成了由内在利益关系盘根错节地笼络在一起的庞大的官僚阶级和官僚集团。不过,官场秩序在本质上毕竟反映特定时代的生产关系或交往关系,它具有时代性,也并非铁板一块。在社会转型和政治改革中,当体制变革特别是文官体制变革发生时,即便是浸洇浓厚官场习俗和行政文化的旧秩序也能够被剔除,并为新的行政秩序和官吏活动规则所取代。从历史上看,彻底的社会政治变革一般都能够大尺度地触动官僚利益关系和政治活动结构,因而它也就成了改变或创新官场秩序的重要抓手。
官场秩序的主体要素、规则要素、目标要素和时空要素
官场是一个颇具复杂性的官吏生活、工作和活动的场域,其风气、氛围、规则和秩序的形成都不是在短期内完成的。官场秩序所呈现出来的良莠优劣有多重诱因,大多与其建构要素有密切关系。一般说来,官场秩序的建构要素包括四个方面:
其一是主体要素。主体要素是建构官场秩序的基本要素。官场秩序反映的是官员和公务人员活动的基本生态与状况,是一种基于特定主体及其活动的程序性或次序性的存在。官场是由人组成的,官场秩序就是人的秩序,没有人的秩序也就无所谓官场秩序。同时,官场秩序也是社会秩序之一,没有了社会,自然也就没有了官场和官场秩序。当然,在官场中,人和社会是有机统一的,这里的人并不是普遍意义上的所有人,也不是只具备自然属性、履行自然行为的自然人,而是参与特定政治运行并隶属于特定政治活动结构的社会人。从微观和具体的角度看,官场秩序的主体就是各级官吏和公职公务人员,是执行党和国家所规定的各项任务的政治人实体。他们构成了官场秩序的主体要素,既是官场秩序的“剧中人”,也是官场秩序的主要“剧作者”。
其二是规则要素。规则是秩序的基础和保障,任何秩序都要依靠规则来捍卫、保持和发展,任何有秩序的活动也必须要遵守规则。社会秩序需要社会规则,官场秩序需要官场规则。官场的规则要素是官场秩序的内在支撑,是官场之所以造成秩序和遵守秩序的基本价值砝码。换言之,规则要素是建构官场秩序的保障性要素。在官场秩序中,各级各类官员和公职公务人员所遵守的规则不仅有约束性的政治规则、法律规则和道德规则,也有保障性的职业制度和工作行为规范。这些规则体现在为官施政的方方面面。总的来说,构成官场秩序的规则要素众多,其中既有成文的政策规则、体制规则和制度规则,也有不成文的文化的、道德的和习俗的规范等。但不管是成文的制度性规则还是不成文的习惯性规则,都对官场秩序的维持发挥着重要影响,也对其发展和创新起着重要作用。
其三是目标要素。官场中的存在、发展和行动都需要目标,目标要素是建构官场秩序的核心要素。众所周知,目标是所有组织化活动和群体行为的宗旨,自然也是政治活动和官员行为所奉行和遵守的要旨,特定的官场活动和行为总脱离不开既定的目标。在官场中活动的个体,往往会有自己的行为目的和实践目标,但这种行为目的和实践目标是否符合官场规则并能否融入官场秩序,往往要由构成官场秩序的规则来裁定。在多数情况下,个体化的目的和目标之间所存在的冲突需要按照既定的秩序规则来调整。不过,从整体上看,目标是制约某种理想化的官场秩序能否达到和实现的关键因素,也是使官场秩序得以变革和调整的缘由。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官场生态中,目标要素往往体現该官场生态的内在价值追求,预示着官场秩序的质量和层次。
其四是时空要素。时间和空间是人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由人构成的任何场域的测量指标,在官场中也不例外。时空要素是建构官场秩序的基础要素,也是特定官场秩序的见证。毋庸置疑,官员和公职公务人员的所有行政行为与政治活动都离不开既定的时间和空间,都必须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存在与展开。时间和空间的存在及交叉,为特定场域和范围内展开的政治活动与行政作为提供了可以把握的条件,为官场秩序的建构提供了时空坐标。因此,所谓官场秩序都注定是在特定时空环境中的状况和形态。当时过境迁时,既有的官场秩序就可能发生改变。构建新的官场秩序,意味着在某一特定空间内的官场生态将会呈现出新陈代谢,将由新型的秩序结构取代旧有的秩序,创造新的秩序状况和形态。
官场秩序的运行逻辑:权力聚散、智识兴废、利益得失
要素只是提供了构成官场秩序的基本要件,要素间的内在衔接、相互作用、关联互动与有机组构才是创造官场新秩序的关键。要素间的结合与互动总要遵循一定的逻辑关系,该逻辑也就是官场秩序的运行逻辑。各个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内的官场秩序都有其特殊的运行逻辑,有基本的官场作为的支点和目标。但是,从普遍意义上说,所有官场秩序都会在保持稳定和均衡的原则下按照利益最大化、价值最宜化和绩效最优化的基本逻辑来运行。概括而言,在官场秩序中发挥主导作用的运行逻辑有:
其一,权力聚散。官场也是权力场,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所谓“权力”,按照美国政治学者罗伯特·达尔的解释,就是“处于社会关系之中的行动者排除抗拒其意志的可能性”。官场秩序在其最直接、最简洁的层次上是由权力的配置及其实施来构设的。在一定的国家体系和政治结构中,当权力特别是政治权力集中于某些单独的个体或集团时,围绕其所形成的官场秩序就内在地受到权力变化的影响。伴随着权力的聚拢或散失,掌握权力的主体所构成的官场秩序也会发生变化。因此,权力聚散是官场秩序中最为直观的“琴键”,也是构建官场新秩序时不可绕过的逻辑观察点。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因为国家体制和政治体制的不同,不同国家的官场秩序具有不同的权力主体,也就存在着带有不同价值指向的秩序构建方式。
其二,智识兴废。构成并影响官场秩序的另外一个重要逻辑范畴是智识。在现代社会中,要在政治活动和施政行为中做出既合乎律则又合乎目的的决策,必须依靠智识来发挥作用,并且这种由智识因素而引发的决策是独特的和不可替代的。一个良好有效的政治决策或施政决定,必定包含着科学合理的智识因素,也必定是智识有效运演的结果。由此,在官场秩序及其建构中,智识兴废是其中隐而不秘、牵而能发的运行逻辑。当然,官场并非学术界,它不以生产和评价智识为标的,但由于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活动和行政行为都大体上以科学化和理性化为基点,因此,构建官场秩序同样会受到智识逻辑的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受智识兴废的牵引、控制和支配。
其三,利益得失。“熙熙攘攘,利来利往”。利益是人类政治活动所追寻的核心价值之一,利益范畴也是政治运行中内在的实践范畴之一。既然政治活动离不开利益,官场秩序同样也就难以逃开利益得失的束缚。在多数情况下,官场秩序的重构都包含着利益的巩固、组合或再生。由于利益主体的差别性、利益来源的多样性和利益分配的复杂性,在一定的政治生态和官场中,因为利益得失而造成的官场秩序的变革就显得颇为频繁和复杂。因为利益反映了人们内在的、深层次的生存需求和实现需求,具有超越权力形式和智识价值的特性,因此,不管怎样衡量和判断,利益逻辑都可以说是支配官场秩序变革的根本逻辑。这样看来,重构官场新秩序必须重视利益关系的变化和利益逻辑的实现。
构建官场新秩序,需重建以民为本、施政为民的根本利益标准
在当代中国,构建官场新秩序既是深化改革的要求,也是全面改革的必然结果。从中国现在所面临的世情和国情及其所处的社情、党情和民情出发,构建现代官场新秩序亟待扭转官员的思想认识、整肃官场不良习气,重建以民为本、施政为民的根本利益标准,秉持群而不党、廉政高效的政治行为原则,坚守有为无私、行而不殆的实践道德操守。
首先,以民为本、施政为民的价值标准是构建官场新秩序中具有贯通性的逻辑主线。毋庸讳言,利益是古往今来所有的政治活动和行政作为永远难以剥离且永久捍卫的目标,但是为什么人的利益而奋斗、服务什么人的根本利益却是揭示政治活动和政党本质的关键,也是区分不同政党和官场性质的标准。中国共产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政治结构和文官体制的根本价值追求就在于坚持“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在于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待当作官场作为的重要奋斗目标。照此来看,要构建现代性的官场新秩序,毫无疑问应该摒弃在陈旧官场文化和腐朽官场习气的前提下进一步夯实并始终坚守人民利益至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原则。
其次,群而不党、清正廉洁的政治行为原则是构建官场新秩序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逻辑起点。纵观中国政治政党与社会发展史可见,在封建官场文化的熏染下,不少朝代在建政之初所营建的清明官场最终都陷入了腐朽落败的泥淖之中。旧时官场秩序的紊乱固然与腐朽的政治制度和官僚体制有关,但也与官员们的不端政治行为和行政伦理有密切关系。作为现代社会的政治管理者,官员和公职公务人员理应牢记并笃行“为政以德”的良训,一方面秉持“周而不比、群而不党”的政治纪律,不搞小圈子,不造小地盘,戒除山头主义和帮派思想;另一方面也要坚持清正廉洁的政治行为原则,“老老实实做人、干干净净干事、清清白白当官”。唯如此,才有可能建立起风清气正的官场新秩序。
最后,夙夜在公、勤而不殆的实践道德操守是构建官场新秩序中发挥支撑作用的逻辑支点。官场秩序靠官员的道德操守和实践伦理支撑。中国古训说:“在其位,谋其政。”身在官场,就应该明白为官做事的责任和使命,应该明白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当官只是获得了为人民群众谋福利、替人民群众行使权力的条件,而并非获得了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的特权,更不可依权弄势欺压百姓。在官场伦理所要求的廉政之外,官员和公职公务人员还必须有勤政之德,有夙夜在公、勤而不殆的道德操守,有恪尽职守、劳而不辍的实践意志,切实戒除慵懒怠惰,摒弃滞政殆政之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要有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想干事、肯干事、能干事、干成事,为工作尽心尽力、尽职尽责、忘我奉献,真正做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
(作者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参考文献】
①(美)罗伯特·达尔:《权力》,《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英文版,1976年。
责编/高骊 美编/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