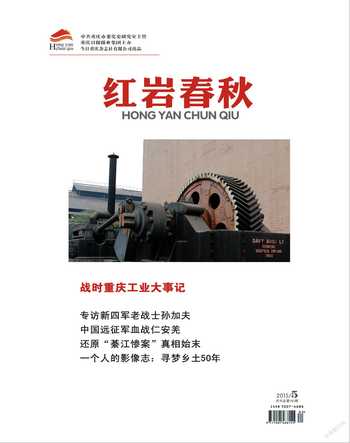一个人的影像志:寻梦乡土50年
马拉




打开摄影家李代才这本200多页600多幅黑白图片的个人摄影集《大足影迹》,翻到第11页的《古戏台前农贸市场(雍溪2005年)》,我立马叫了起来:“小时候,我在这里看过戏!”大足雍溪古镇是我妈妈的老家。小时候,妈妈送我到镇上跟外公外婆生活过几年。老街老桥、小河小船、古庙戏台,组成了我最美好的童年乐园。七八年前,听说这个戏楼要拆,我和报社的同事鞠二哥还赶回去作过报道,也算为抢救戏楼出了一点儿力。
这几年,妈妈探亲回来说,戏楼没拆,但河边开了一个化工厂,高烟囱那个烟子哟,麻雀飞过去,都要遭熏下来,好多人因此生病。妈妈记忆中的故乡,已经完全变了样。
当那种曾经滋养我们长大成人的乡土之美面临沦陷之时,李代才的这部影集正是沦陷前夜对乡土之美的最后一瞥。他用相机抢救了我们的村庄,黑白影调,淡然如月光,就像1964年唱响全国的歌剧《刘胡兰》中所唱的那样:“借月光再看看我的家乡。”
相馆
1962年,李代才花了80多元买了一部目测焦距的上海牌201折叠式相机,在老家龙水镇街上租了一间门面,办了一个照相馆。这一年,他才19岁。他说:“我从小喜欢美术,在龙水中学读书时,参加过课余美术小组,报考过四川美术学院附中,但美术老师把报名时间记错了,就没考成,后来又想去报考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但把北电摄影系的招生简章找来一看,人家报名资格仅限北京、上海,更考不成了。”家境贫寒,高中才读了一年半,17岁的李代才就休学回家摆了个画炭精像的画摊,当时一幅炭精像5元钱,价格算是高的,但业务不好,后来李代才干脆就开相馆了。
李代才一个人经营的相馆成了当地的时尚中心。3天赶一场,十乡八里的乡亲们都涌来照相。学生娃娃来照耳朵必须露出来的登记照,大姑娘小媳妇来照耳朵可以藏在黑发后面的“妖精”照,大胖娃娃又哭又笑的满月照,男男女女喜气洋洋的结婚照,都从李代才手上过。最大的业务是毕业照,龙水只有一个中学,每年学生毕业,李代才扛起机器就去了。
照相、洗印、放大、裁切,都是李代才一个人干。“当时胶卷用的是上海牌、天津牌、公元120牌,4.5×6的可以拍16张,6×6的可以拍12张。当时一寸的照片,一底两张,2角8分钱,加洗一张,8分钱。”也没有彩照,照片着色的业务很受欢迎,“着色分水彩和油彩,油彩主要用于12寸的大照片,水彩主要用于小照片。油彩和水彩都是特制的透明颜料,用棉球棒小心翼翼地涂在照片上。现在,这种颜料可能买都买不到了。”
当时的照相机还是一种奢侈品,大多只有政府、公安和宣传部门配有。县里有照相机的人家,可能在派出所都有记录。因为有些人觉得照相机可能是特务和间谍的工具,所以照相馆当时也被划入特种行业管理。
一年多过去,李代才的照相馆变成了供销社龙水照相美工店,上面还给他派来3个人,仍然由他负责。这时店里的相机也换成了上海生产的木架6寸外拍相机。除了商业照片,他开始把镜头对准相馆外面的风土人情,拍了很多纪实照片。1980年,他还拍出了改变自己命运的艺术片《水库之晨》,发表在1981年第8期的《大众摄影》上,在当时的永川地区(1983年以前,永川地区下辖8个县,即永川县、江津县、合川县、铜梁县、璧山县、大足县、荣昌县、潼南县——编者注)的摄影界引起轰动,因为这是全地区在国家级摄影刊物上发表的第一幅照片。
闻讯的永川地区防疫站宣传股想挖李代才去当专职摄影,大足县(今重庆市大足区)近水楼台先得月,立马调李代才到县文化馆工作,成为专职的摄影干部。当时县上没有新闻单位,李代才就成了县里面唯一的御用摄影师,这时他手里的家伙已经换成了上海牌双镜头相机。
李代才当年考北京电影学院无望,但他注定和这个学院有缘。有一年,著名摄影家、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吴印咸到大足北山参观,李代才陪同。“他问我们,现在国内摄影书出得太少,你们好不好买?我就说不好买,你那本《摄影用光》,我都是借来手抄的。县上陪同的领导就说,你去拿来吴老看看,我拿来吴老一看,很感慨,还在书上签名留念。他说,抄书好苦,以后我出了书,寄给你就是,你不用抄了。后来,书好买了,我也用不着吴老寄了。”
后来,李代才任大足图片社经理,写信请吴印咸题写招牌,吴印咸欣然答应。“据我所知,这可能是吴老唯一一次为全国县级图片社题写招牌。这跟当初我手抄他近8万字的书有关系,我就是这样自学出来的。”
石刻
我在影集里还发现了一位老朋友:大足石刻博物馆老馆长郭湘颖。照片上他和北京来的大画家梅绍武站在“北山石刻”简介下面,郭馆长看上去还是小伙子模样。“那是1979年,老郭当时好像还是一个管理员”。早在1976年,李代才就开始拍摄大足石刻了,“当时我还在龙水照相馆,石刻博物馆的人请我去拍一点石刻的资料,我就去了,向他们学了很多东西。”他把自己拍的一张大足北山圆觉洞六臂观音照片,寄给成都一个朋友作纪念。这张神奇的照片通过这位朋友传到了上海滩,一个编剧看到了,由此写了一个纪录片脚本投给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这个电影厂以前拍过《敦煌》,万万没想到在重庆的一个山湾里,还有能与敦煌壁画媲美的精美造像,电影厂的一个摄制组马上开到大足拍了《大足石刻》纪录片。李代才全程陪同,还向摄影师李文秀学了一些绝招。李文秀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拍过当时非常火的《针刺麻醉》《汽垫船》《日全蚀》《台风》等片。李代才从电影动态摇臂拍摄中得到启发,就用带脚架的120相机来复制电影的全景拍摄法,利用接片方式,拍摄了一幅宝顶大佛湾石刻全景,在没有大画幅相机的当时,拍出了大画幅的效果,“以前从未有人这样拍过大佛湾。以后也难了,因为现在大佛湾里面树木长高了,丛林茂密,遮挡太多,再去拍,一个镜头根本拿不下来。”
《大足石刻》全国公映时,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送给大足县一个拷贝,李代才坐在大足唯一的电影院里看了,心情非常激动,“1945年,杨家骆、马衡、顾颉刚等13位专家学者组成的大足石刻考察团,来大足可能拍过资料电影片,但上海科教片厂是新中国成立后拍的第一部关于大足石刻的完整的纪录片。”
2001年,李代才的《大足石刻精品》专题摄影集出版,获得中国摄影出版社2001-2002优秀图书奖,封面图片选的就是他当年拍的那张大足北山圆觉洞的六臂观音。
乡情
“谨以此书献给家乡父老乡亲”,这是李代才《大足影迹》扉页上的献辞。这本影集里最早的图片是1962年拍于龙水的《七部脚踏水车引水灌溉》,从那以后的50年间,在李代才的乡土摄影之路上,每一张标题后面标有时间和乡名的图片,都是一篇篇他写给故乡的农事诗和民俗志。
我们看见乡亲们用手提式插秧机、脱粒机、水田拖拉机、脚踏水车、电动抽水机在田间劳作,他们坐着独轮车、骡马车、白木船、摩的、板板车、人力三轮、拖拉机穿行在路上和河里;玉龙的媳妇在河边洗衣,登云的姑娘在院坝里用没有自来水的洗衣机;雍溪包皮蛋、中敖蒸泡粑、珠溪的米花糖、龙水的平桥黄馒头和担担面、三驱的油炸粑、万古的石磨豆花……都是乡情。
还有用小船接送学生上学的女教师吴国贵,用耳朵可以认字的唐雨小兄弟;1979年干旱断流,龙水七孔桥下河床干涸;6月盛夏,龙水街边12条大汉打着光巴胴(即赤裸着上身)围炉吃火锅,他们锻造的刀具,刚好打凿北山和宝项山的石头。
乡亲们有时也被叫去开会,1976年9月18日,在龙岗会场举行毛主席追悼会,标语上写着毛主席的名字。10月24日,还是同一个会场,召开粉碎“四人帮”大会,标语上除了毛主席的名字,还写着华主席的名字。
乡土生活中,这些大会都是刮过河面的大风,散会以后,乡亲们的日子,仍像濑溪河与雍溪一样静静流淌,他们仍然淡定而低调地包皮蛋、点豆花、吆鸭子、烫火锅。正如李代才在北京的女儿李红菲所写的那样:“谢谢父亲!透过《大足影迹》画册,我和故土时刻相连,我和父老乡亲血脉相连,既有温情的回忆,更有无限的憧憬,我的乡愁是父亲的一幅幅照片。”
2015年1月24日,现居成都的李代才,回家乡捐赠《大足影迹》1000册。72岁的李代才表示:“1000册画册价值10万元,对企业、商家或单位来说,也许微不足道,但对一个退休摄影工作者来说,不是小数目。自己之所以省吃俭用捐赠这批画册,就是为了报答故乡的养育之恩,也希望更多的人以各种方式回报家乡。”
(作者单位:重庆晨报。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责任编辑:邓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