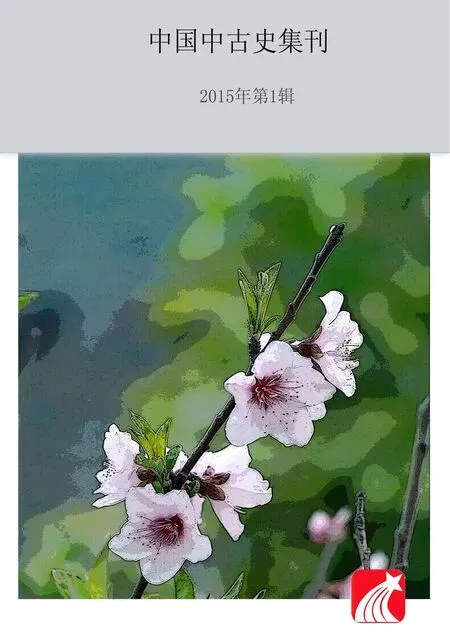墓葬中的窣堵波
——再论武惠妃石椁上的勇士神兽图
王庆卫(西安碑林博物馆)
墓葬中的窣堵波
——再论武惠妃石椁上的勇士神兽图
王庆卫(西安碑林博物馆)
陕西历史博物馆2010年入藏的唐敬陵武惠妃(贞顺皇后)彩绘石椁以其宏大的规模再现了盛唐文化的风采和广纳百川的唐帝国特征,很快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和讨论。[1]葛承雍:《唐贞顺皇后(武惠妃)石椁浮雕线刻画中的西方艺术》,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05—323页;李杰:《勒石与勾描—唐代石椁人物线刻的绘画风格学研究》,西安美术学院博士论文,2011年;葛承雍:《再论唐武惠妃石椁线刻画中的希腊化艺术》,《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4期;程旭、师小群:《唐贞顺皇后敬陵石椁》,《文物》2012年第5期;葛承雍:《唐代宫廷女性画像与外来艺术手法—以新见唐武惠妃石椁女性线刻画为典型》,《故宫博物院院刊》2012年第4期;杨远超:《武惠妃石椁外壁屏风式花鸟画艺术特征初探》,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程旭:《唐武惠妃石椁纹饰初探》,《考古与文物》2012年第3期;田小娟:《武惠妃石椁线刻女性服饰与装束考》,《文博》 2013年第3期;杨瑾:《唐武惠妃墓石椁纹饰中的外来元素初探》,《四川文物》2013年第3期。武惠妃石椁内外都雕刻着精美的图案,内壁以传统的仕女图像为主,外壁以卷草为基础穿插有人物和动物形象。内壁的图案在唐代的遗存或遗物中多有发现,外壁的图案则十分少见,尤其引起大家争论的主要是其中的四幅勇士神兽图,本文在分析外壁图案整体内涵的基础上,认为这四幅图像可能是犍陀罗佛教艺术中的护法者赫拉克勒斯和狮子形象的变体,而整个石椁外壁图案则是组成了一幅佛教的涅槃之地—窣堵波的墓葬化表现,故此本文提出我们的另一种解读意见,以为学界之参考。
一
武惠妃石椁造型精美,青石质,高约2.45米,宽约2.58米,长约3.99米,面阔三间进深二间,由盖顶、椁板、立柱、基座共31块石材组成,庑殿形顶,外壁整体纹饰使用对称布局,以神话人物和花鸟画面为主,绕以各种花草纹、动物纹、云纹等,各种艺术形象常常都是成组出现;内壁以仕女画面为主,边框饰花卉纹。
石椁外壁图案所反映出的宗教内涵和意义,葛承雍先生认为武惠妃石椁围绕着冥界主题没有采用佛教、道教或是儒家的生死关怀,而是取材希腊罗马神话源泉的原型构图蓝本,引入了新的西方神灵世界;[1]葛承雍:《唐贞顺皇后(武惠妃)石椁浮雕线刻画中的西方艺术》,第305—323页;葛承雍:《再论唐武惠妃石椁线刻画中的希腊化艺术》,《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4期。程旭先生主张唐玄宗用皇后的礼仪埋葬武惠妃时,通过带有佛教色彩的盛大乐舞场景抚慰自己的这位宠妃,使其死后能够享受没有痛苦和烦恼的极乐世界,石椁外壁图案散发着浓厚的佛教意味,但同时还包含着其他的思想与信仰;[2]程旭:《唐武惠妃石椁纹饰初探》,《考古与文物》2012年第3期。杨瑾先生认为武惠妃石椁外壁的图案许多都具有祆教艺术色彩,程序化地表现或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普遍思想和追求。[3]杨瑾:《唐武惠妃墓石椁纹饰中的外来元素初探》,《四川文物》2013年第3期。从几位先生的观点中我们深受启发,本文倾向于石椁外壁的图案整体表达的都是佛教的内涵,其中不乏中原文化的元素,不过很可能已经佛教化或者被佛教艺术所借用了。对于外壁图案中的佛教色彩,程旭先生已经对其中的伎乐图像、飞天供奉和迦陵频伽论述颇多,笔者就其中还未讨论或可以增益的部分做进一步的分析。
第一组:鸿雁形象。在石椁外壁的不同部位雕刻的鸿雁形象有十三只之多,有的展翅飞翔,有的口衔璎珞颈系绶带,有的立于牡丹花上,有的作回首状,还有的鸿雁成对出现,姿态变化万千各具特色。雁的形象在唐代是常见的祥瑞图案,在石椁中出现如此多的鸿雁形象,不仅仅是为了表现一般的思想和信仰,应该有着独特的宗教意义。
唐代有些舍利容器上出现了鸿雁纹饰,如陕西周至仙游寺法王塔天宫出土的银棺上装饰一对鸿雁,法门寺塔基地宫出土的六臂观音金函盖刹部位也装饰有鸿雁。鸿雁是世俗纹样中吉祥的象征,含有祈求夫妇和谐、生活美满之意,常见于唐代铜镜、金银器等日用器物,将这些纹样装饰在舍利容器之上,这反映的不仅是文化融合的问题,更是供养者对美好生活期盼心情的一种折射。[1]冉万里:《中国古代舍利瘗埋制度研究》,文物出版社2013年版,第158页。除此之外,雁在佛教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更是佛教文化的一个重要代表符号。
《大唐西域记》卷9《雁窣堵波》:“昔此伽蓝,习玩小乘。小乘渐教也,故开三净之食。而此伽蓝遵而不坠。其后三净,求不时获。有比丘经行,忽见群雁飞翔,戏言曰:‘今日众僧中食不充,摩诃萨埵宜知是时。’言声未绝,一雁退飞,当其僧前,投身自殒。比丘见己,具白众僧,闻者悲感,咸相谓曰:‘如来设法,导诱随机,我等守愚,遵行渐敎。大乘者,正理也,宜改先执,务从圣旨。此雁垂诫,诚为明导,宜旌厚德,传记终古。’于是建窣堵波,式昭遗烈,以彼死雁,瘗其下焉。”[1]《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70—771页。
飞雁自殒而给众僧带来佛法感悟,这是雁在佛教中可以作为供养物出现的一个例证。佛陀三十二相中手指缦连如雁,“尔时雁王者,我身是也”[2]《法句譬喻经·忿怒品第二十五》,《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四卷,第596页。,故佛陀可称之为雁王,而佛堂在佛典中经常被称为雁堂或雁宇。《大方便佛报恩经》中有五百飞雁化身为五百罗汉的故事,另外还有五百飞雁闻佛法然后得以升天的传奇记载,这些都是佛教寓教化于故事之中,通过故事向人们说教传法的重要手段。在佛教当中,雁有时候不仅仅可以用来指代佛陀本人,更是与佛教的弘法息息相关。
隋释智 《摩诃止观》:“所言慧眼见者,其名乃同实是圆教十住之位。三观现前入三谛理,名之为住,呼住为慧眼耳。故法华云:愿得如世尊慧眼第一净,如斯慧眼分见未了。故言如夜见色空中鹅雁,非二乘慧眼得如此名,故法华中譬如有人穿凿高原唯见干土,施功不已转见湿土,遂渐至泥后则得水。”[3]《摩诃止观》卷3上,《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四十六卷,第25页。
上文雁和鹅并称,两者之间有着一定的类似或关联性。[4]孙英刚先生指出:汉文典籍中的鹅与雁在梵文中经常是同一个词表示的,汉文中的差别经常是翻译原因造成的。在中土佛教文献中屡见飞雁,这是不是遗留有早期佛教中天鹅事迹的影响?在迦腻色迦圣骨盒盖侧面装饰着飞翔的天鹅,一般认为鹅在这里表示着引导灵魂飞升的含义,武惠妃石椁中出现的众多雁是否也有着类似的含义,或者说中土佛教中飞雁是否有贵霜王朝鹅的象征性,这都是需要进一步关注的地方。
今天西安的大雁塔,坐落于唐代的大慈恩寺内,对于大雁塔名称的由来虽然还没有比较完善的答案[1]阎文儒:《西安大雁塔考》,《史学月刊》1981年第2期;王泽民、巨亚丽、王磊:《西安大雁塔名称溯源—兼论九百年来的一个误解》,《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4期;申秦雁:《西安大雁塔名称溯源补正》,《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2期。,但是从其命名可以看出雁在佛教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敦煌莫高窟第158窟涅槃佛佛枕上面雕刻有联珠纹衔绶带大雁的纹样,涅槃情境下出现的雁纹与武惠妃石椁上出现的雁纹似乎都有着和死亡相关联的寓意,而这也为理解雁在佛教中的内涵进一步提供了线索。
第二组:狮子形象。在石椁外壁出现了十多幅狮子的形象,根据画面可分为三类:类一,是单独一体的狮子,这种形象出现最多,造型多头顶双角,和别的动物或植物图案构成完整画面;类二,是骑狮图,这种图像共有三幅,狮子肩生长翼回首瞠目怒视骑者;类三,是还有一幅狮子追扑噬羊的画面。石椁外壁狮子的造型富于变化,多是保持着狮首,身体已经瑞兽化了。
佛教中经常以狮子象征佛陀,佛陀一般被称为狮子王。在佛陀的本传故事流传中,狮子在其世系、修行、弘法等层面均有着极为重要的象征意义,如“佛上身如狮子相”、“佛之说法犹如狮子吼”等。在南北朝的造像中佛和狮子经常一起出现,狮子充当着佛法的护卫者形象,之外也作为衬托佛陀力量的动物而出现。[2]关于狮子在中古陵墓礼仪空间中的使用,可参见李星明:《护法与镇墓:唐陵礼仪空间中的石狮》,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主编:《佛教史研究的方法与前景》,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8—35页。《大般涅槃经》中把狮子的品行和德行与佛陀联系了起来,尤其是大乘佛教更是将狮子吼附会为佛陀天生的能力,而且狮子吼被指示为佛陀弘法更是普遍的认识。在武惠妃石椁上面出现如此多数量的狮子形象,不能不让我们对整个石椁的艺术选择有所重视。
《新唐书》卷76《后妃上》:“玄宗贞顺皇后武氏,恒安王攸止女,幼入宫。帝即位,寝得幸。时王皇后废,故进册惠妃,其礼秩比皇后。……生子必秀嶷,凡二王、一主,皆不育。及生寿王,帝命宁王养外邸。又生盛王、咸宜太华二公主。后李林甫以寿王母爱,希妃意陷太子、鄂光二王,皆废死。会妃薨,年四十余,赠皇后及谥,葬敬陵。”[1]《新唐书》卷76《后妃上》。
武惠妃虽然得享荣华富贵,却命途多舛,儿女多生变故,加之武氏家族的尚佛传统,一般认为武惠妃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2]武惠妃作为武则天的亲族,在其成长的过程中受到了武则天思想信仰的很大影响,关于武氏家族的佛教信仰学者论述颇多,最有代表性的论著可参见陈寅恪:《武曌与佛教》,《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53—174页;《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金明馆丛稿初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66—295页。对佛陀与狮子之间的关系是否接受或认同,了解这些比喻及其在佛教艺术中的表现,是区分佛教徒和非佛教徒的重要指标之一,佛陀与狮子的比喻和象征的主体意识存在于佛教徒的意识之中,这也是信徒们从中汲取信仰力量的一种重要方式。[3]陈怀宇:《动物与中古政治宗教秩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56页。在武惠妃石椁中出现大量的狮子纹饰,正可以说明武惠妃石椁在营造时对本人信仰的重视,同时似乎也暗示着希望利用狮子形象的威猛来庇佑武惠妃的灵魂。
在敦煌绘画中有通过狮子攻击水牛来描绘佛陀弟子舍利弗战胜外道牢度叉的故事,石椁中刻画的狮子扑盘羊的图案,是否也蕴含着佛陀摧毁外道的意义呢?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这种推测,但是从中国僧人对狮虎的认识和解释,以及以猛虎取代狮子的例子来看,这种改变图像中的某些因素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第三组:童子形象。石椁上童子众多,整个周边不同位置共有七八种不同的造型(图一),而且均为两两出现左右对称。其中最多的一类是莲花童子形象,这类童子或坐或立,有的手持莲叶,有的手捧果盘,不过多与莲花一起出现,似与佛教典籍中的莲花童子有关;还有一类童子形象是手捧果盘,伸腿骑在大雁身上,大雁呈展翅高飞之状。
石椁上的童子图案,葛承雍先生认为是希腊罗马题材中的小爱神,他们常常成为家庭幸福生活的引导者,也是新生精灵的精神象征。[1]葛承雍:《再论唐武惠妃石椁线刻画中的希腊化艺术》,《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4期。对于石椁中大量的童子形象,笔者更倾向认为这是受犍陀罗佛教美术波及所致,虽然犍陀罗艺术中的童子形象深受希腊罗马题材中的爱神影响,但所表示的含义已经和希腊艺术有所不同。
犍陀罗艺术中的植物、动物和童子形象,似乎有意强调动植物的繁荣和生命的复苏。在犍陀罗美术中,扛花环的童子是极具代表性的题材,迦腻色迦舍利容器的中间部位就有童子扛花环的形象。扛花环的童子在古罗马时期一般用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战胜的画面,一个是葬礼的画面,后者所象征的是死者在另一个世界的荣光,大量用于石棺浮雕中。犍陀罗佛教美术中扛花环的童子图,一般被雕刻在窣堵波上面,这种做法就是将佛陀的永恒世界(窣堵波)以乐园来加以修饰,穿插童子形象从而成为丰饶乐园和再生的最好象征。[2]〔日〕宫治昭著,李萍译:《犍陀罗美术寻踪》,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47页。
在武惠妃石椁外壁的童子形象多与莲花一起出现,有的童子还盘坐于莲花花瓣中央,莲花在佛教中有着特别的意义,莲花化生与犍陀罗艺术中扛花环的童子的寓意如出一辙,都可以表达转生的主题。在犍陀罗佛教美术中,不仅有扛花环的童子形象,还有表现裸体童子各种姿态的画面,对比石椁中各种童子形象,就会发现石椁的构图和犍陀罗的雕刻方法十分类似,不过进行了中国化的改造。在佛教美术中大量出现表现生命力的童子形象,无疑蕴含着亡者对再生的向往,这也与黄泉下的美术所要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
经过前文的讨论,笔者以为石椁外壁的图案虽然有些雕刻还不能一一和佛教中的具体形象作对比分析,但整体意蕴表现的是与佛教相关联的构图思想。
二
石椁上的四幅勇士神兽图分别两两对称分布在石椁大门两侧的窗棂之下(图二),编号1、2的处于左边窗棂下,3、4的处于右边窗棂下。编号1的图案中人物造型留有胡须,额头戴日月冠饰带,全身穿紧身衣服,双手拽着狮形神兽,身体紧绷;编号2的图案中人物腰部束紧而下肢细长,头戴长条饰带,颈戴数圈有吊坠的项圈,腰系革带,脚蹬波浪纹软尖鞋,双手紧绷神兽缰绳;编号3的图案中人物秃顶,卷发后梳下披,下巴胡须稀疏,颈戴三环项圈,一手拽绳,一手拉绳缠指下末尾,瑞兽狮首虎身,鬃毛后卷;编号4的图案中人物全脸髯须,脚穿尖顶鞋,头顶环形饰带,双手拉紧缰绳拽着狮形神兽。
对于这四幅雕刻,葛承雍先生认为表现出的是中外文化交流元素中的希腊化艺术[1]葛承雍:《唐贞顺皇后(武惠妃)石椁浮雕线刻画中的西方艺术》,第305—323页;葛承雍:《再论唐武惠妃石椁线刻画中的希腊化艺术》,《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4期。,程旭和杨瑾两位先生则认为属于传统观念中的胡人训狮图案。[2]程旭:《唐武惠妃石椁纹饰初探》,《考古与文物》2012年第3期;杨瑾:《唐武惠妃墓石椁纹饰中的外来元素初探》,《四川文物》2013年第3期。武惠妃石椁外壁的图案整体风格属于佛教色彩,处于显要部位的勇士神兽图也应该是属于佛教蕴涵的图像,笔者以为这四幅图表现的可能是力士狮子的含义。
《洛阳伽蓝记》卷1《城内·永宁寺》载:“(永宁寺)南门楼三重,通三阁道,去地二十丈,形制似今端门。图以云气,画彩仙灵,列钱青璅,赫奕华丽。拱门有四力士、四师子,饰以金银,加之珠玉,庄严焕炳,世所未闻。”[1]《洛阳伽蓝记校释》,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6—8页。
永宁寺早在北魏迁洛初期已在孝文帝关于都城建设的构想之中,直到孝明帝熙平年间始由胡太后付诸实现。永宁寺的建成,开创了有关寺院建筑、雕塑等方面的新格局,永宁寺作为北魏国寺,建成之后对后来的佛教艺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孕育着隋唐时期的萌芽。[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魏洛阳永宁寺(1979—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3—155页。永宁寺南门是整个寺院的轴心之处,作为拱卫南门的雕塑原则一定有着严格的佛教意义,拱卫南门的四力士和四狮子形象,用金银、珠玉装饰,庄严肃穆。
古代的门户具有分界和通贯的双重作用,是空间控制与社会控制的重要设施,所谓“门户之政”有着实际的意义。[3]刘增贵:《门户与中国古代社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97年第68本第4分册。在墓葬美术中棺椁上雕刻的门窗有着独特的地位和象征性,这种宗教学上的意义和永宁寺南门的寓意十分接近,这四幅图案雕刻在石椁门的两侧,这和永宁寺南门的情况基本一致,根据类比原则把两者进行比较是比较合理的。由于文献记载不清晰,无法确知永宁寺力士狮子的具体情况,不过四个人物、四只动物的组合两者是一致的,那么通过从表现内涵上来进行比较,武惠妃石椁上的四幅勇士神兽图案是否和这种力士狮子图有关联呢?
勇士神兽图的雕刻特点,葛承雍先生已经有了非常详细的论述,对于他提出的希腊化特点我们表示赞同,不过笔者以为这种希腊化并不是直接产生的影响,而是经过犍陀罗佛教艺术的改造后对中土的影响所形成的。
在希腊神话中,最著名的勇士就是赫拉克勒斯(Heracles),他是希腊神话中的著名英雄,他先后完成了十二项危险的任务,后来成为奥林光辉中的大力神。在赫拉克勒斯的任务当中,完成的第一项就是要杀死内梅亚森林中危害平民生命的一头雄狮,这头雄狮是一个巨大而可怕的怪兽,赫拉克勒斯经过与雄狮搏斗用自己的木棒打昏了雄狮,然后用双手将它扼杀。从希腊神话可以看出赫拉克勒斯和狮子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在许多希腊雕刻中和狮子一起出现的人物指的都是赫拉克勒斯。
犍陀罗艺术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和女神在当地的文化与宗教信仰下,自然地与佛教的精神相交融所产生的。犍陀罗艺术中各类佛教神祇的造像,绝大部分借用了希腊罗马古代众神的外形,金刚力士就普遍借用了古代希腊罗马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的外形,希腊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就是在贵霜时期进入了犍陀罗地区。将赫拉克勒斯形象铸在钱币上为希腊诸王所通用,赫拉克勒斯形象在贵霜王朝的银币上已有出现,近代在犍陀罗地区发现了大量背后有赫拉克勒斯形象的钱币,钱币的正面是当代国王的头像,背面是赫拉克勒斯手持木棒和狮子皮的立像,将希腊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用在钱币上,有护卫国王和捍卫国家利益的用意,也显示出赫拉克勒斯的重要地位。[1]霍旭初:《龟兹金刚力士图像研究》,《敦煌研究》2005年第3期。赫拉克勒斯在犍陀罗佛教美术中一出现,就和佛陀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往往是作为护法者的形象出现的,这和赫拉克勒斯护卫王权的观念是同出一辙的。
巴基斯坦的安丹赫里出土有一件浮雕,在佛左侧的部位站立着裸体的赫拉克勒斯,左肩扛着大木棒,右臂搭着狮子皮。收藏在英国大英博物馆有一件大约为公元2—3世纪的石雕残件,佛陀左下方是一金刚力士,金刚力士披着狮子皮,头上戴狮头,右手紧握金刚杵,左手按在长剑柄上,这是将希腊赫拉克勒斯外形用于佛教金刚力士的一件极为典型的艺术作品。在佛教艺术发展过程中,赫拉克勒斯造型不断发生变化,大约在公元2—3世纪出现了头带狮头皮冠、手持金刚杵的造型,这种造型被固定下来之后,逐渐就从犍陀罗普遍流行并开始向西域以至更东的地方传播。
在中原佛教艺术中发现的天王像或力士像,是多种外来文化和中国本土文化不断融合与互动的结果,这些外来文化包括印度、犍陀罗、伊朗,间接包括古希腊罗马。[1]李凇:《长安艺术与宗教文明》,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36页。在力士像中,赫拉克勒斯的造型影响最为明显,可以说是从犍陀罗一路东行来到了中原大地,在这一路上不断适应新的变化,加入新的艺术元素,不过作为护法者的主要身份却一直保留着。巴楚托库孜萨拉依佛寺出土的金刚力士雕塑、高昌古城发现的力士图像壁画,都是赫拉克勒斯形象不断东行变化之后的产物。
通过上文分析,我们倾向于认为武惠妃石椁上的勇士神兽图是赫拉克勒斯和狮子造型的变体。在唐代塔基地宫或天宫中,狮子、天王以及金刚力士像是一种重要的供养品,如法门寺塔基地宫阿育王石塔一侧出土有2件彩绘石狮;陕西临潼庆山寺塔基地宫出土有三彩护法狮子;法门寺塔基地宫中室和后室石门两侧有天王像。另外多有雕刻在石门上和甬道两侧的天王、力士等护法者的形象。
一般发现的力士多和佛陀一起出现,和狮子组合出现的比较少,但在犍陀罗佛教美术中这种构图的造像已经出现,赫拉克勒斯与狮子的图像至少有两种表现方式,一种是搏斗的场面,一种是和平的形式。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公元1—2世纪赫拉克勒斯和狮子图像的浮雕(图三),这件浮雕出自犍陀罗地区,浮雕中的赫拉克勒斯全身赤裸,头上系着希腊英雄化的头饰,左臂上搭着狮皮,右手拿着一件大木棒,目光炯炯有神注视着左侧的狮子,狮子右前爪向前伸出,尾巴向上舞动充满了动感。浮雕以赫拉克勒斯为主体,狮子处于从属地位,不过两者之间并不是希腊瓶画中常出现的搏斗场景,而是看起来比较和平的画面,这种场景的出现可能和赫拉克勒斯与狮子同属于佛陀的护法者有密切的关联。
赫拉克勒斯和狮子的图像是犍陀罗艺术中很特别的一种,犍陀罗艺术随着佛教东传越过葱岭,这种图案应该也随着僧侣或商队传入了中原。北魏的力士多是手持金刚杵的形象特征,在永宁寺南门处出现的四力士四狮子的配合是否和大都会博物馆所藏的赫拉克勒斯与狮子图有内在的关联,或者说这种赫拉克勒斯和狮子图的佛教寓意影响了永宁寺南门处的力士狮子的组合选择,这些都需要引起我们特别的关注。
尼雅遗址的东汉墓曾经出土过一件夹缬蓝印花棉布,在上端残破处有佛脚、狮尾和蹄形痕迹,左下角有一个半身菩萨像裸体露胸,颈与擎上满配璎珞,头后有背光,手捧一个喇叭口形的容器(图四)[1]李遇春:《新疆民丰县北大沙漠中古遗址墓葬区东汉合葬墓清理简报》,《文物》1960年第6期。。从残存的人脚趾和狮尾看,这幅画的主体画面表现的是赫拉克勒斯斗狮子的图像。[1]林梅村:《汉代西域艺术中的希腊化因素》,郑培凯主编:《九州学林》第1卷第2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5页。
西安碑林藏《石台孝经》台基共分三层,最上面一层的东侧面刻有两幅人物狮子图,构图造型突出了狮子的比例,狮子栩栩如生刻画逼真,两幅图左右对称,内侧为狮子,外侧为人物,左边的人物左手拽着缰绳,右手举着前端弯曲如环状的棍形物(图五);右边的人物形象上部有所剥阞,不过仍可以看出双手紧拽缰绳(图六)。同武惠妃石椁上的图案相比,两者构图非常相似,都突出了狮子的比例,不过《石台孝经》中的狮子写实性比较强,手举棍状物的人物头戴幞头帽,面部圆润,穿着宽大的汉服,看起来已经是中原人物形象了;右边的人物和武惠妃石椁图案中编号4的画面极其类似,穿着紧身衣服小腿曲线夸张,头上赤裸,侧脸高鼻深目,完全是西方人的造型,《石台孝经》和武惠妃石椁的这两幅图案可能有着共同的来源。《石台孝经》的年代为天宝四年,比武惠妃石椁晚七八年左右,可以认为《石台孝经》上线刻的人物狮子图也应是力士狮子的含义,右边的一幅还保留着犍陀罗的艺术痕迹,而左边的人物造型已经完全中国化了。在武惠妃石椁立柱上还有三幅胡人御兽图,其中一幅人物的手持之物和图六人物手持的棍状物基本一样,这两幅图之间应该有着一定的关联,对于这三幅胡人御兽图的内涵我们倾向于认为是和佛教的供养有关,但对于如何具体解读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证。《石台孝经》作为玄宗自己的一座纪念碑,表达着至高的皇权和威望,在基座上面雕刻力士狮子图的目的和犍陀罗地区在金币上刻画赫拉克勒斯的目的是一致的。古代西域是狮崇拜的流行区,从印度到波斯,狮子被赋予了神秘的色彩享誉僧俗两界,成为神力和王权的象征。[1]蔡鸿生:《狮在华夏》,《中外交流史事考述》,大象出版社2007年版,第173页。力士狮子图有着两方面的内涵,对于佛教来说是护法者,对于世俗社会来讲则是王权的守卫者,这在《石台孝经》和武惠妃石椁中分别表达着不同的思想和意识倾向。
从考古发现来看,东汉末中国与犍陀罗的文化艺术交流并没有因为东汉王朝对西域失去控制而削弱,相反犍陀罗语还成了洛阳和犍陀罗之间的国际通用语,并在西域塔里木盆地的许多绿洲国家成了官方语言。[2]林梅村:《松漠之间:考古新发现所见中外文化交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46—69页。不过犍陀罗对中国的影响主要在佛教艺术方面,米兰佛寺的壁画、克孜尔石窟的壁画、楼兰遗址的葡萄纹佛门以及于阗和喀什绿洲流行的艺术品许多都是按照犍陀罗的艺术原则创作的。从尼雅遗址的棉布画面到武惠妃石椁上的力士狮子图,从东汉到盛唐,都可见犍陀罗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武惠妃石椁勇士神兽图的母题可能是赫拉克勒斯和狮子的图像,一方面他们的造型距离原始的希腊形象越来越远,不仔细分析的话甚至难以找到两者间的承袭关系,但是他们象征性的角色—勇士和护卫者的身份一直不曾改变。希腊赫拉克勒斯的造型特色似乎越往东,丢失、增添和改变的情形就越多,由西域进入中国河西地区,不再全然裸体,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东方化的造型,不过他手中的大木棒和狮皮或隐或现,顽强地保留在中古艺术中。[3]邢义田:《赫拉克利斯在东方—其形象在古代中亚、印度与中国造型艺术中的流播与变形》,《画为心声:画像石、画像砖与壁画》,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58—513页。石椁上的四幅力士狮子图中,力士形象中隆起的额头、下垂的卷发、卷曲的胡须和宽阔的胸部都充满了希腊化色彩,但均不是常见的裸体形象,而有着酷似胡人的着装,不过身侧的狮子和浓密的大胡子似乎都预示着赫拉克勒斯的身份和来历。
力士,乃护法之神;狮子,守护伽蓝者也。以四狮子作为装饰很容易使人想起阿育王石柱的四狮柱头造型,北魏皇兴造像背后所雕刻的四大护法天人和西安碑林藏景俊石函四侧所刻画的护法天人形象,武惠妃石椁中力士狮子图的佛教内涵可以确认,它们之间应该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和影响。
三
武惠妃石椁外壁椁板画面20幅,各画面构图不同,内容丰富。石椁外壁主题为花鸟图像,牡丹、莲花、团花、石榴、葡萄等组成繁复华丽的卷草纹饰,各种鸟类和动物穿插其中;立柱画面20幅,以缠枝卷草、海石榴、牡丹、葡萄、西番莲纹饰为主,穿插异兽、天马、狮子、鸿雁、鸳鸯、伎乐、童子等各种形象。这些形象中除了佛教寓意的图案,还有着中亚或者粟特特色的艺术,亦有中原本土“多子”心愿的表达,组成了一幅立体化的图像情景。
植物纹饰的大量使用,是这个时期艺术风尚的一个潮流,在石椁外壁雕刻的各种植物纹,简单的线条却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气息,表达着时代的审美趋向和人们的欣赏与喜爱,暗示着四季的变化。人们习惯将人间的事物和品质与对自然界的描述相类比,这种类比和暗喻中最多的就是四季花鸟纹饰。为死者和生者所采用的动物和植物纹饰都是模仿宇宙的计划的一部分,并由此创造出与宇宙相一致的吉祥空间,人们认为图像创造了吉祥图景,而不仅仅是描摹原物,是宇宙观的力量的又一例证。[1]〔英〕杰西卡·罗森著,邓菲、黄洋、吴晓筠等译:《作为艺术、装饰与图案之源的宇宙观体系》,《祖先与永恒:杰西卡·罗森中国考古艺术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307—343页。生与死是统一的连续体,墓葬不仅仅呈现了死后世界,也表现出对日常生活的解释和说明。
花草纹饰是春夏来临的标志,古人通过强调春夏之际来确保墓主人享受到这些美景。植物图案是构成丰饶乐园最重要的因素,同时还往往和女性联系在一起,在武惠妃石椁中大量采用植物纹饰,除了对于生命的信仰之外,也许和她的身份有着一定的关联。
已经有学者对唐代墓葬中的佛教因素进行了考察[1]张建林:《唐代丧葬习俗中佛教因素的考古学考察》,西北大学考古学系主编:《西部考古》(第一辑),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462—470页;李星明:《隋唐墓葬艺术中的佛教文化因素》,巫鸿、郑岩主编:《古代墓葬美术研究》(第一辑),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第245—269页。,武惠妃石椁外壁的纹饰整体构成了一幅佛教的圣地,动植物纹饰萦绕的画面,正把石椁营造成了一个墓葬中的窣堵波。窣堵波象征着佛教的最高境界—涅槃,那是一个美丽而富饶的世界。在佛教文献中,很多时候雁的出现都是和表现佛教天国的美好联系在一起的,在《南本涅槃经》和《长阿含经》中,雁和鸳鸯以及各种异类奇鸟相合而鸣,共同营造出了一个美好的佛国净土,而这正和石椁外壁图案所要表达出的窣堵波内涵是相通的。在武惠妃石椁外壁雕刻有多幅类似屏风画的图案,下方是一只鸟类,上方是植物纹饰,这种构图方式在新疆阿斯塔那唐代墓葬中亦有发现,对于这种图案是否具有佛教意蕴还需进一步分析,不过表现的都是对于死后美好世界的向往与诉求。
在印度早期的窣堵波周围,用浮雕表现了充满茂盛生命力的动植物,供奉舍利的窣堵波成为人们的礼拜对象。作为释迦坟墓的窣堵波,不会再有轮回转世,它所表现的是绝对永恒的寂灭世界,于是作为涅槃的象征而成为佛教徒崇拜的对象。作为佛教徒所崇拜的窣堵波其实并不仅仅是释迦个人的墓葬,更在于释迦所达到的涅槃境界,是佛教徒希望达到的一种理想境界。在印度佛教艺术中,桑奇三塔有着重要的地位,形状酷似半球形;[1]关于桑奇三塔的详细介绍,参见扬之水:《桑奇三塔:西天佛国的世俗情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在拉合尔博物馆收藏有一件石质窣堵波(图七),形状与一般的窣堵波相同[2]〔巴基斯坦〕穆罕默德·瓦利乌拉·汗著,陆水林译:《犍陀罗:来自巴基斯坦的佛教文明》,五洲传播出版社2009年版,第195页。,这种用半球形状来表示佛教理想境界的涅槃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门、窗棂似乎都在暗示着在画面深处还有另外一个空间,从而把石椁内外不同的世界有机地联合起来。一般认为门窗是建立生与死的连接和转换,淡化生死的对立,分别在藏与露的矛盾中妥协融合,在观感上使得内外成为一个三维的空间。门窗这类建筑元素刻画在墓室或棺椁上面,是为了将其转化为一种完整的“建筑”,而这种建筑在亡者的世界里有着独特的意义和象征性,实质上是将生者世界的建筑构件符号重新包装赋予新的内涵,从而成为为亡者所用的一种独特的“语言”。[3]郑岩:《逝者的面具:汉唐墓葬艺术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78—419页。门与窗在墓葬中可能意味着通过这个孔道进入另一个世界,同时这些孔道类的装饰经常也预示着亡者升仙的通道。武惠妃石椁用种种艺术象征与元素来呈现佛国净土,门和窗户显示的正是佛国的入口,亡者灵魂的目的地是奔赴往生的净土,而动物和各种植物纹饰则加强了各种符号的祥瑞和神圣含义,可以说,武惠妃石椁所要表达的是将石椁幻化成一座墓葬中的涅槃之地—窣堵波,从而达到信徒生命信仰的理想境界。
犍陀罗涅槃图中一定有执金刚神作为护卫者出现,这种雕刻在犍陀罗发现很多。执金刚神在犍陀罗的佛传故事雕刻中有着多种多样的造型,在佛教文献中几乎不涉及执金刚神,但在犍陀罗的佛教艺术中执金刚神却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1]〔日〕宫治昭著,李萍译:《犍陀罗美术寻踪》,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171页。执金刚神和力士的概念经常混淆,作用也十分类似,在武惠妃石椁门两侧雕刻力士狮子图,正和佛陀涅槃中的纹饰图案相一致。
石椁外壁图案的犍陀罗色彩十分强烈,这种再三强调与古印度的密切关系,其意图很明确,来自佛教发源地的西方的艺术形象应该受到格外的尊崇,这样就会显示出石椁窣堵波化的正统性和权威性[2]〔日〕肥田路美:《南北朝时期至唐代瑞像造型的特征及意义》,中央文史研究院、敦煌研究院、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主编:《庆贺饶宗颐先生95华诞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68页。,或者可以说是体现出了中国佛徒所设想出的“西方印度佛国”的记忆。这种用神圣空间感所表达的窣堵波通过中国化的表现形式与主题,来表明这是一种真正承袭印度正统佛教特征的保证。
窣堵波具有生与死的双重特征,它所表现的涅槃世界和彼岸世界是互为表里的两个层面,这样的艺术形式产生在犍陀罗地区,给后来的佛教艺术带来很大影响。在犍陀罗艺术中,窣堵波雕刻的纹饰以动植物为主,充满着与生命的丰饶乐园相关的表现,窣堵波虽然代表死的坟墓,但它却超越了生死轮回世界,这样“死”的窣堵波就可以被当作体现轮回根源的“生”的场所。[3]〔日〕宫治昭著,李萍、张清涛译:《涅槃和弥勒的图像学—从印度到中亚》,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15—60页。在窣堵波中,佛教的涅槃、生命的再生、丰饶的乐园三者是互相映衬的,武惠妃石椁外壁的纹饰雕刻就是围绕着这三方面展开的。
墓葬中的图像背后都潜藏着更深一层的象征意义,即与墓主死后命运和归宿息息相关的丧葬信仰。高丽长川1号壁画墓反映了一套相对完整的设计思想,特别是它以绘于重要视觉位置的佛教图像,将坟墓与天堂联系了起来,从中可以了解佛教究竟在哪一层面与世俗的墓葬发生了关联,而墓葬中的佛像图像又可以多大程度上反映时人的宗教信仰。另外从墓葬的特殊性和图像的复杂性能够知道,佛教图像在墓葬中的意义取决于图像所在的整体语境,而且还要考虑到墓主所处的时间、地域、社会文化背景、身份及其思想等诸方面的差异。[1]李清泉:《墓葬中的佛像—长川1号壁画墓释读》,巫鸿主编:《汉唐之间的视觉文化与物质文化》,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497页。武惠妃石椁中雕刻的佛教纹饰,许多都保留着犍陀罗艺术的痕迹,虽然中国人对于源自希腊的古老艺术不是很熟悉,但与她有关的象征图像和本土传统艺术结合在了一起,虽然经过了变化,但许多重要的象征符号还是被保留了下来。若干源于希腊罗马风格的样式和装饰主题在传播到近东时已经经过了艺术的改造,其结果是在传入中国以前与原型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卡雷茨基:《中古时期中国装饰艺术中的阿娜希塔女神及其有关象征图样和纹样》,巫鸿主编:《汉唐之间文化艺术的互动与交融》,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341—371页。,在武惠妃石椁门两侧雕刻的力士狮子的图案也是这种文化传播中的典型个案之一。
结语
武惠妃石椁上力士狮子图的母题可能是来自赫拉克勒斯和狮子的故事,在东传的过程中其形象不断发生着变化,但是作为护卫者的身份一直没有改变。石椁外壁雕刻大量带有佛教色彩的动植物纹饰,让整个石椁成了墓葬中的窣堵波,早期佛教艺术中对亡者的终极关怀在盛唐皇妃的墓葬中出现,也证明了佛教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力也许比我们所要了解的还要深刻。石椁内外壁的图像表达着不同的生死信仰,把佛教的乐土、天界和幸福家园结合起来,希望武惠妃可以在死后得到真正的涅槃,从而进入到另一个生者祝愿的彼岸的终极世界。

图一 武惠妃石椁外壁童子形象,程旭:《唐武惠妃石椁纹饰初探》

图二 武惠妃石椁勇士神兽图

图三 赫拉克勒斯与狮子,浮雕,现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图四 尼雅遗址东汉墓出土的棉布残片

图五 《石台孝经》台基上层东侧人物狮子图(左),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

图六 《石台孝经》台基上层东侧人物狮子图(右),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

图七 石质窣堵波,现藏于拉合尔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