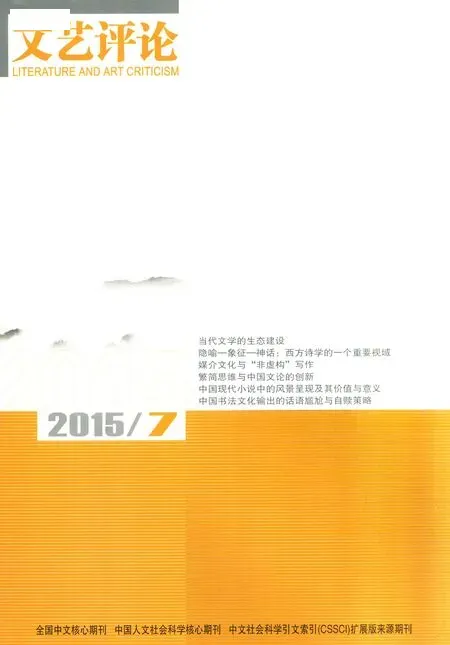尊重文学多样性及其自身规律
——当前中国文学的生态学思考
○孙德喜
尊重文学多样性及其自身规律
——当前中国文学的生态学思考
○孙德喜
从1949年至今,我们的当代文学走过了六十多年的路程,其间令人感慨和深思的东西很多。其中,萦绕在人们脑际的一个问题始终存在着,那就是我们的文学艺术的运行总是不那么令人满意。对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换一种思维方式,借鉴生态学理论来思考我们的文学现象,或许可以从中得到某些启发。
对于文学艺术,我们的期待常常是过去多年提出的口号“百花齐放”。这个口号很好,非常符合我们的愿望。但是仔细推敲一下,我们的具体操作实际上比较难办。首先,哪些作家作品算是“花”,哪些作家作品不仅不能算是“花”,而且还可能是草,甚至是有毒之物?如何确定衡量的标尺?其次,最关键的问题是,判断一个作家或者一部作品是“花”还是“草”,究竟由谁来认定?如果有权认定作家作品优劣的人在判断上失误了怎么办?再次,即使被判定为“草”的那些作品,是否就没有生存的权利?
其实,这种类似的问题在生态学上也存在。一方面,我们在要求保护生态平衡的时候,突出强调的是物种多样性;另一方面,地球上确有许多有害物种,破坏或者威胁人类的生存和社会的发展。在面对这个问题时,人们有不同的意见。一种观点是以人类为中心来思考问题,要求对于物种存在的态度应以人类自身的利益为依据。如果某些物种危害到人类的生存或者其他物种的生存就必须予以限制或者根除。这种意见可能受到一些人的质疑,并被称为“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还可能受到尖锐的批评:“它只承认人类的内在价值,而大自然丧失了内在价值,仅成了满足人类理性探究欲望和物质消费欲望的对象。正是这种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使得现代人甚至把人口的过度繁殖也视为文明的一种重要成果,完全不顾人与大自然的生态平衡。而更为可怕的是现代文明的世俗化方向,即充分肯定了人的欲望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把世俗物质欲望的满足视为人生的核心要义。”①另一方面意见就是尊重和爱护一切生命,“强调世界上万事万物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以一种整体性观点来观照世界……”②这两种颇具代表性的观点其实都存在一定的偏差。就前者而言,人类的贪婪和物质欲望的极度膨胀确实应该引起我们高度警惕,但是它所强调的以人类根本利益为中心的生态观应该得到肯定。人类的根本利益必须成为生态平衡和保护的出发点。因为,环境保护与维护生态平衡,只是针对人类而言的,其他生物都是在人类的训导下才能有所作为。如果没有人类的存在,那么所谓的生态平衡不仅得不到维护,而且失去了意义,因为其它生物是否意识或者感受到生态平衡的问题都很难说。其次,提出生态平衡问题的是人类,而不是其它生物,而人类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的目的就是为了人类的健康、更好地生存和社会的发展进步。
就后者来看,在理论上,我们应该尊重每一种生命,而且各种生物相互依赖而存在,生命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众生平等。著名作家韩少功就曾为某些生物被限制或消灭而鸣不平:“我还会想起很多我伤害过的生命,包括一只老鼠,一条蛀虫,一只蚊子。它们就没有活下去的权利么?如果人类有权吞食其他动物和植物,为什么它们就命中注定地没有?是谁粗暴而横蛮地制定了这种不平等规则,然后还要把它们毫不过分的需求描写成一种阴险、恶毒、卑劣的行径然后说得人们心惊肉跳?为了自己的生存,为了自己一种富足、舒适、安全的生存,我与我的同类一直像冷血暴君,用毒药或者利器消灭它们,并且用谎言使自己心安理得。”③这个观点最大的问题是,只看到各种生物之间存在相互依赖,形成整体性的一面,而没有看到相互争斗和绞杀的一面,有些生物可能直接威胁和危害人类,有些生物可能危害其它生物的生长,成为其它生物的杀手,威胁生态平衡,必须予以限制或根除。比如蚊子、臭虫、老鼠、罂粟等等直接危害人类的健康,蝗虫、一枝黄花等动植物直接侵犯其他植物生长的空间,掠夺其他植物的营养,还有许多害虫威胁着农作物的生长,造成农作物减产甚至绝收,对于这些生物,我们虽然不必完全铲除,但是必须严格限制,否则必将对人类危害无穷。人类固然需要尊重其它生命,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生物的生存本来就自然地形成食物链,如果没有食物链,不用说人类,世界上绝大多数生物都将灭亡。或许有一天,人类通过改造基因,变有害生物为有益生物,但是改造后的生物会不会因为变异而产生新的危害呢?这个谁都难以预料。
通过对生态学理论的探讨,我们在当代文学运行遇到的问题并试图予以解决时可以得到某些启迪。一方面,我们需要物种多样性,需要尊重生命;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对有害生物予以铲除或者限制,其实这也是对其他生命及其生存权的尊重。从文学方面来看,文学也需要多样性,只有不同形态的创作才能形成竞争,形成生机勃勃的局面,而且我们应该尊重作家创作的权利。作家既有权进行从内容到形式的创新和探索,又有权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作家有创作的自由。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确实有些作家受各种因素的影响,生产出危害人类精神健康的作品,比如有的作品鼓吹暴力、煽动仇恨,有的作品可能涉嫌侮辱和诽谤他人,严重侵犯他人的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现在的问题是,对于危害人类精神健康和社会发展进步的文学作品,我们如何确定?如何解决?过去,对于文学作品是否有害常常是由权力来认定,并且通过批判和封杀(打入冷宫)的方式来解决。现在仍然有不少人希望有关部门出来管一管。但是,这样解决问题的方式带来了非常严重的两个后果:一是由权力认定一个作家一部作品是否危害人类精神健康,可能被权力所利用,为权力自身的利益服务;二是权力认定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太大,极易造成文字狱。尤其是在权力不受制约的情况下,权力扩张,造成的危害更严重。20世纪50年代以来,这样的历史教训太多了。李建彤写作《刘志丹》本来是为了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结果却是,《刘志丹》不仅不能公开出版与读者见面,而且还受到了严厉的批判政治迫害。这是典型的权力将权力斗争引到了文学领域的事例,权力为了维护其自身的利益而肆意地伤害文学。从20世纪50年代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开始,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胡风文艺思想、被打成“右派”的作家及其作品、延安整风运动中挨整的作家、直到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等先后受到权力的整肃和批判。这些受到否定并被禁锢的作家作品并不是所谓的“毒草”,也不存在被指控的罪名,根本没有危害到人类的精神健康,但是它们遭到了厄运,这是权力根据斗争需要所为。而权力在批判作家作品时具有很大的主观臆断性,将批判文学作品、批斗作家纳入到其斗争的战略部署之中。由此可见,单纯地让某一部门或者机构去管文学,让他们拥有对于作家与文学作品生杀予夺大权,就可能再次出现文学史上这样的灾难。从生态学角度来看,对于有害生物的确定如果缺乏科学依据,结果不仅不能维护生态平衡,而且严重地破坏了生态平衡。“大跃进”时期,全民发动,消灭麻雀,由于缺乏科学知识,结果错把益鸟当害鸟。这样的教训是很深刻的。因而,我们的文学生态出现了严重的问题,真正那些危害人类心理,戕害人性和良知,鼓吹暴力与仇恨的文学作品由于意识形态的偏差和权力的喜好进而充斥文坛,这就导致了当代文学的严重危机,很少有作家作品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
从生态学理论来看,我们必须尊重生命,每一种生命都有其存在和生存的权利。在文学领域也是如此,每个作家都拥有天赋的言论自由的权利,每部文学作品都有其存在的权利,或者说他们的“生命权”应该受到保护,而且这在我们国家的最高法律——宪法中得到明确的保障。问题是我们现在虽然制定了某些具体保障作家和作品的权利法律(比如著作权法),但是还很不够。因为著作权法所保护的是作家的知识产权,而知识产权之外的权利并没有明确的保障,而这些权利需要制定新闻出版法来加以规范。在保护生态方面,我们制定了《野生动物保护法》《野生植物保护条例》《草原法》《森林法》等法律法规。同理,只有制定了《新闻出版法》,作家的言论自由的权利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任何部门、机构、团体和个人都不能以任何借口剥夺作家写作的权利,不能剥夺作品的发表、出版和传播的权利。即使某个作家犯了法,只要在法院判决中明确规定被剥夺政治权利之外,他的作品依然拥有发表、出版和传播的权利。现代文学史上的周作人在日本侵占华北期间投靠侵略者,后来被判犯有汉奸罪,但是他在五四时期所写的大量的散文作品仍然可以重新出版,与读者见面。因此,某部作品或者某个作家哪怕令某些人厌恶或者反对,也不能被扣上什么帽子而遭到封杀与禁锢。
与此同时,我们可能遇到这样的问题,某些文学作品就像有害生物一样,可能危害他人,或者引诱犯罪,或者危害心理健康,或者威胁他人的安全,或者侮辱诽谤他人,造成他人名誉受损,损害他人利益,给他人精神造成损失和伤害,这就需要像对待有害生物一样,予以铲除或者限制。如何确定某部文学作品危害他人与社会呢?当然,不能由权力来确定,应该由法律来确定。我们的法律在保护作家与作品权利的同时也在保护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为社会的和谐与健康发展护航,因此有必要对于有害作品及其作者给予法律制裁。因此,某部作品及其作者如果形成对他人的伤害,就应该由受害人向法院提出诉讼,法院受理后根据控告人提出的证据与理由,确定该作品对他人伤害的程度,再依据法律相关条款作出判决,要求其作者、出版者与传播者销毁有害作品并向受害者赔偿与道歉。如果某部文学作品危害的不是某些个人,而是整个社会,比如鼓吹暴力,煽动仇恨,制造社会族群的分裂与对抗,那就由公诉人提出起诉,法院在确定合法证据的基础上根据法律作出判决。在法院审理文学作品是否有害的过程中,应该给予该作品的作者与出版、传播者以辩护的权利。这样,既可以避免产生冤假错案,又不会出现文字狱。至于一部作品不受部分人的欢迎,那只是部分人的事情,这些人可以不予理睬与阅读不喜欢的作品,也可以通过文学批评表示反对意见。每一个读者都有根据自己的阅读感受表达肯定或者否定的权利,而作品的原创者同样拥有说明、辩护与反批评的权利。正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喜欢某些动植物,可以主动接近;如果我们不喜欢某些动物或者感觉到某些动物可能威胁我们的安全,我们可以尽量避开,甚至拒绝其靠近。但是,我们没有权利给任何一个厌恶的作家作品贴上某个标签并将其逐出文学的殿堂。
我们面对着许多物种的灭绝或者濒临灭绝而深感忧虑,接着我们可能要采取一定的措施来保护这些濒临灭绝的生物;可是在对待文学问题时,我们怀着的却是另一种担忧,那就是在当前出版业非常发达与互联网十分普及的情况下各种文学作品扑面而来,令我们目不暇接,给人以泛滥的感觉,于是要求把文学作品的出现“管”起来,不能让那些低俗的,色情的,恐怖的、怪异的作品泛滥,不能让我们的文坛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这样,我们就可能在看似正当的呼吁和要求之下,将某些作品视为劣质的或者不健康的,进而将其扼杀。
其实,在生物界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有些动植物可能被作为名贵品种而备受人们的青睐,受到宠爱而重点豢养或栽培,而另外一些动植物则可能不那么美观,不能被利用而不受重视和欢迎,如果在某些情况下影响到人们的生活,就会有人要求将其铲除或者杀掉。但是,如果我们掌握了一定的生态知识理论,以生态整体观来看待动植物,我们就可能不会粗暴地对待自己不喜欢与厌恶的动植物。在整体生态观那里,“1、一切生命形式都是互相依赖的;2、生态系统稳定性取决于它的多样性和复杂性;3、所有资源都是有限的,所有生命系统的生长也是有限的”④。这就是说,世界上的生物或者说各种生命形式相互联系,彼此相依相存,不是分开割裂的,大家共同组成一个生态圈,都是地球大家庭中的一员,共同维护地球上的生态系统。从生态学的这一观念出发,人们可以看到文学世界也应该如此。这就是说,文学世界应该由各种形态的文学样式构成一个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不同形态的文学相互依赖。一方面,各种形态的文学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和价值。那些被奉为经典的文学作品固然得到精英们的推崇而受到追捧,但是那些通俗的、流行的文学作品也有存在的必要,因为不同的读者对文学作品的需求肯定有别,而且同一个读者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环境下对于文学作品的需求也有差别。就是精英与学者也不一定整天都在阅读屈原、《红楼梦》、鲁迅、沈从文、托尔斯泰、卡夫卡,有时他们也可能放下身段去读一读“三言二拍”、古龙、琼瑶与村上春树。那些经典之作给人们带来思想的启发与精神营养、情感的熏陶与心灵的震撼,而非经典之作却可以给人们以精神的娱乐和放松,调节人们的心理情绪。这就像生物一样,有的可以制作成精美的食物,有的可以供人观赏,有的可以与人相伴,有的可以作为人的某种工具而驱使……各种生物相对于人类而言各有其价值。就是撇开人类来说,各种生物需要其食物营养,由此组成了食物链。离开了食物链,许多生物就无法生存下去。更何况还有不少生物在相互激烈的竞争中保持其某些特长与技艺。如果某种生物的天敌消失了,那么这种生物的某些功能也就会很快退化或者消失。就文学史来看,高雅与通俗从来就不是泾渭分明的,从来就不是相互隔绝或者互相对立的。先秦时的《诗经》既有“雅”与“颂”比较高雅的作品,又有非常通俗的“风”,它们在孔子这里受到了同等对待。在明清时期,小说被认为是通俗文学形式,常常受到歧视,但是不少明清小说中的诗词歌赋就非常典雅,可谓“俗中有雅”。此外,许多经典作家都会从通俗文学或者民间文学那里寻找精神资源与艺术资源。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文学形态的多样性时代也是文学竞争的时代,作家如果要在这个时代拥有自己的立足之地,在激烈的竞争中产生危机意识,这就促使其不断强化自己的竞争力。
在互联网时代到来之前,文学作品的发表与出版主要是由期刊图书编辑把关,那些质量低劣的作品就会被拒之门外,与此同时,那些思想和情感不合主流意识形态的作品也可能遭到拒斥。这样状况,到了互联网时代有了很大的改变,一部作品不管质量如何,只要作者满意就可以将其贴到网上。因此,互联网上张贴的文学作品不仅数量惊人,而且质量得不到保证,形成汹涌的文学泡沫。而这些文学泡沫极有可能将精品淹没。这同样引起不少人士的忧虑。其实这样的忧虑多少有些杞人忧天。本来,文学的发表根本就没有编辑,也没人把关。古代文学作品的“发表”,有的是民间吟唱流传,有的题在墙壁上,有的应和酬唱,有的自己编订,有的赠送友人,同样存在着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问题,但是那些质量低劣的必然为历史所淘汰,而那些精品虽然一时可能被埋没,但是终将被挖掘出来。到了20世纪,出版业出现,编辑在文学作品的发表上确实严格把关,但是由于国家意识形态的强大作用,编辑所把的重点并非艺术质量之关,更多的是意识形态之关。所以,有时候,图书期刊上发表的也有不少文学垃圾,同时确有不少文学精品不能发表。“大跃进”时期出版的许多民歌集,其中绝大部分作品质量低劣;1949年以来的地下文学(或称“潜在写作”)就有不少堪称经典的作品却不能在文坛上亮相,不能与读者见面,其中最突出的就有北岛、多多、食指、舒婷等人的朦胧诗。即使在平时,文学作品的发表与出版同样有可能淹没精品而出现文学垃圾。这主要是文学编辑的文学修养与出版商为市场利润所左右的缘故。因此,我们不能将文学把关的重任托付给文学编辑。
从生态学来看,任何生物都有其存在的权利与价值,文学作品也是这样。同时,我们必须看到,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各种生物在大自然面前还会面临着被淘汰的危险,不少物种进化了,适应了自然环境而生存下来,更有不少物种不能适应自然环境的变化而从地球上消失。这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以生态学眼光来看文学,同样如此。文学作品虽然质量上参差不齐,优劣同在,但是如果能够为读者所接受,那就有其一定的生命力。如果某部文学作品质量实在低劣,味同嚼蜡,让人不堪卒读,那么很自然地被历史淘汰,而这样的文学作品必然没有生命力。而那些思想深刻,艺术精湛的优秀的文学作品一旦被人发现就会受到欢迎,赢得广大读者,被人一代又一代地阅读和接受,自然就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因此,面对着互联网时代文学的纷繁复杂现状,我们应该有足够的耐心,不是寄希望于某个部门或者某一类人,而是让时间来检验。自然界的优胜劣汰规则在文学领域也是适用的,因此,不应强加人为人力,更不应让权力介入。
生态学理论给我们的启发可以归结为:尊重和理解文学的多样性和文学自身的规律。如果文学出现了问题,危害到人类的精神健康,侵犯他人权益,那就应该通过法律程序来解决。在这方面,与生态学关系密切的道家文化也有相似的表述:“顺其自然”,“无为而治”。习惯于权力的介入实际上是对丛林法则的认同。当人类进入现代文明社会,那种以强力欺凌弱小生物的丛林法则就应该被抛弃。只有如此,才能排除对待文学的主观性、随意性和强暴性,才能拆除了文化专制主义强加在作家头上的枷锁,给文学设置的牢笼,让文学在自由的土地上成长。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
①②汪树东《生态意识与中国当代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第13页。
③孔见《韩少功评传》[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209页。
④余谋昌《生态哲学》[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