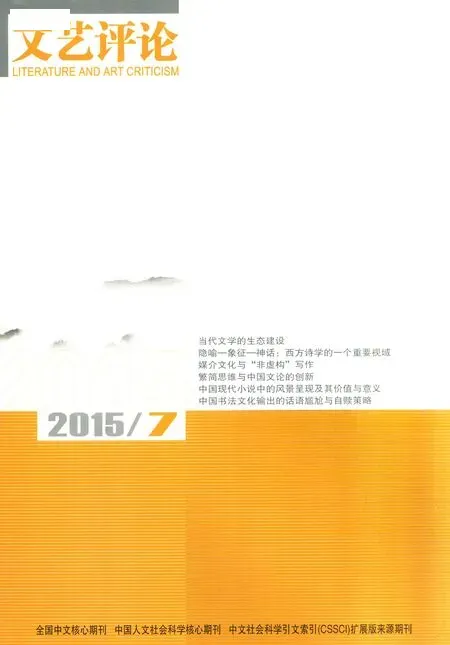媒介文化与“非虚构”写作
○刘 浏 丁晓原
从写作文本与其所书写的对象世界的关系观照,文体大体上可分为虚构文体和非虚构文体。非虚构文体不是横空出世的文体类型,它是经历漫长的社会变革与书写文化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非虚构”是对20世纪虚构文学的反拨,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报告文学热,还是20世纪90年代新写实主义小说等都昭示着传统文学的精神回归。进入21世纪,“非虚构”写作特别活跃,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非虚构作品,促发了非虚构热潮。《人民文学》的“非虚构”栏目和“人民大地”“非虚构”写作计划等,对非虚构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与此同时,也引发了研究者对非虚构文体的更多关注,有关“非虚构”的争议颇为热闹。
“非虚构”写作不仅是一种建立在文本内容真实基础上的书写方式和文体类型,也指称着以一切的传播手法表达非虚构书写意义的表现方式和传播模式。它不仅囊括了新闻、报告文学、纪实小说、传记、日记文学等几类非虚构文学体,具有“纪实”+“文学”的表现张力,同时,在文学生态环境的变化发展过程中,“非虚构”写作与传播媒介融会贯通、相互影响,尤其是在媒介融合时代,“非虚构”写作表现出更多的可能、绽放了无穷的魅力。
一、“非虚构”写作的媒介转向
随着传媒技术的发展,非虚构所处的媒介环境也发生了改变。技术支持是非虚构文本媒介发展的决定因素。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卫星电视、有线电视、网络媒体、手机媒体等媒介新技术在我国全面推广和普及。互联网将全世界240多个国家和地区联结成网,不受时间、空间限制,人们能够通过文字、图片、声音、影像等形式迅速、海量、互动交流。新媒介技术的产生和普及,社会主导媒介的更迭,会对社会的媒介环境乃至整个社会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波兹曼指出,“技术变化不是附加的;它是生态学的。一种新媒介不是增加了什么,而是改变了一切”①。父辈文化中非虚构的“文本-人”传播关系变为了“文本-空间-人”的传播。同时,本来只能被动接受文本信息的读者,可以采用图、声、影等各种手段方式了解非虚构,还可以利用新媒介技术进行分享和推广,这即是新的因素被导入进旧的环境时形成的一种新的环境。新媒介被广泛使用使得非虚构传播空间——由非虚构文本而派生出的非虚构传播场域——由现实拓宽到虚拟世界。《相爱十年》是由慕容雪村所著《天堂向左,深圳往右》改编而成的都市青春偶像励志片。《天堂向左,深圳往右》的故事开始于2002年,亿万富翁肖然因酒后开车死在凌晨的深圳。那时他正处于事业的巅峰,声名远震,富比王侯。对于他的死亡,人们有多种看法,有的说是谋杀,有的说是意外,知情者却一口咬定他是自杀。接着,故事回溯到1992年,肖然和女朋友韩灵、刘元、陈启明这一群本是意气风发踌躇满志的年轻人,带着各自的理想从全国各地来到了深圳,创业、打拼、生存,在冷酷现实前头重脚轻地行走着。当图书被搬上银幕,传播场域的改变要求传播文本内容的变化。书中的韩灵和肖然不会让你心之向往,肖然在书中更世俗,对韩灵不那么温柔体贴,当然也没邓超那么帅;韩灵在书中懂得应酬,懂得暧昧,崇尚金钱不会让人心生怜惜。“电视剧更多的是刻画爱情,原著更多的是在深圳这个大背景下人性的变化”,“我是看完电视剧觉得有遗憾再去翻书的”,“这是慕容雪村的风格”,“插一句,那个刘元的演员是不是还演过一个啥性无能的角色?看着不大爽”……这是随机地进入《相爱十年》的网络论坛里网友们的留言讨论。可以试想,如果没有被拍成电视剧或是没有网络论坛这样的传媒工具,《天堂向左,深圳往右》仍只是一本深刻反映时代变革、广受读者亲睐的文学作品。而如今,它的传播影响力大大波及至更广更深,在网络上引起广泛热烈的讨论。人们依据自身的体验和感悟在网络空间直抒胸臆,在文本以外甚至影视作品以外又制造了一个传播空间。这是仅在印刷媒介时代不可能存在的。
报告文学作品影视化也是“非虚构”写作意义延伸的典型,以张胜友在这方面的探索和实践为最。与同时代的报告文学作家不同,张胜友对于报告文学坚守而不固守。作为改革作家,他勇于改革报告文学传统的表达方式,于传统纸媒介质报告文学之外,卓有成效地开创了影视报告文学,成为这一新类型创作的最重要的代表性作家。他先后创作了《十年潮》《历史的抉择——邓小平南巡》《让浦东告诉你世界》《闽商》《风从大海来》等多部电影、电视政论片,获得了艺术成就最高肯定。影视报告文学是文字语言与图像语言的合体,它有更加丰富的组聚合关系,能呈现出更生动多样的语言效果。影视报告文学文本以文字语言的形式存在,有自身的组合系列和聚合系列,而影视报告文学的另一个并列元素是图像语言,它也有一套组合系列和聚合系列。对于影视报告文学来说它的内部有四套语言系列,每两套系列之间的互相组合都能生成一种意义,这使得影视报告文学指说内容更加立体、鲜活和透明。影视图像由每一个单位时间的画面串联起来,文字与画面依靠声音融合。画面时而波澜壮阔、时而幽静婉约,声音时而激情澎湃、时而清新甜美,根据表现需求的不同,影视报告文学将画面和声音进行重组和搭配,有时画面定格配合缓缓的人声讲述,有时画面不停切换而音乐声戛然而止,从而营造出一番更高境界的和谐。这种和谐就是通常所说的意指,即“传播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分别指向形式和内容,两者的结合构成意指,从而与现实事象发生联结”②。以《风帆起珠江——献给改革开放30周年》为例,第一篇章“万古江河”开篇,也是一个很巧妙的意旨形成范例。“这是美国人从太空拍摄的珠江三角洲的照片。一张拍摄于今天,另一张则拍摄于三十年前”,伴随着解说词,画面上出现了两张对应的照片——一张呈现的图景标志着这片土地过去的荒凉,而另一张照片里出现了各式密密麻麻的建筑,展现了如今这块土地的繁荣昌盛。试想,如果没有声音语言,整个关于历史与现在的对比都不能让人理解;如果没有图像的配合展示,这个对比又只能是观念上的想象,无法达到具象的落实。只有当所有符号发挥最大效用时,意指意义才能最优达成。如上述所言,张胜友的影视报告文学作品体现出能指和所指的高度融合,为意指的表现提供了有利“环境”,这就是为什么他的作品内容特别饱满和精彩的原因。
如果说影视报告文学是“非虚构”写作在新的媒介环境下的创新,那么作为本来就是以电子媒介为载体的纪录片十足在近几年迎来了“第二春”。我们可以将纪录片等非虚构形式看成是一种语言表达,是包含文字语言、声音语言、图像语言在内的复杂的语言形式。纪录片的文字语言,主要指的是纪录片解说词。解说词最早出现在纪录片作品里是1927年约翰·格里尔逊创作的《漂网渔船》,从此“解说加画面”模式流行于世。理性客观的解说词可以起到补充信息、设置悬念、推进情节等作用。纪录片的主要目的是反映人类生活的复杂性和多义性,而不是以意义标准将其简单化,就像中国电视片研究会会长陈汉元说的:“纪录片的使命就是忠实于记录事件发展过程,我们不要干预这个过程,因为过程就是历史,如果干预了、使他的走向变了.那么你可能歪曲了这段,你在捏造变更历史的真相。”③所以,纪录片最基础、也是最核心的工作则是用图像呈现故事。每一条纪录片背后都累积着成数倍时间量的声像、文字素材,这些素材就是独立的、无规则的言语,传播者通过编辑、制作的复杂加工,将言语转化成纪录片语言。
“纪”与“录”两字体现了纪录片的主要构成,分别是以解说词为主的文字语言以及以同期声、音乐、图像等代表的电子媒介语言。以下就以《舌尖上的中国》(以下简称《舌尖》)为例解析纪录片语言。“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富戏剧性的自然景观,高原,山林,湖泊,海岸线。这种地理跨度有助于物种的形成和保存,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这样多潜在的食物原材料。为了得到这份自然的馈赠,人们采集,捡拾,挖掘,捕捞。穿越四季,本集将展现美味背后人和自然的故事。”——这句话是《舌尖》第一季第一集的开篇语。一语中的,为整部纪录片奠定了明朗的基调。在《自然的馈赠》中,选取了松茸、笋、诺邓盐、藕等四样最具代表大自然送给人间的食材作为纪录对象。数十分钟的纪录片里,随着解说词的指引,我们从香格里拉的原始森林,穿越到浙江的毛竹林,再到云南大理北部山区,乃至湖北的嘉鱼县。只有一千字的解说词,却向我们叙述了四个美食场景:藏民丹增卓玛和妈妈凌晨3点就出发,步行30公里,小心翼翼采集松茸;与笋常年打交道的老包只需要看一下竹梢的叶子颜色就能知道笋的准确位置;云南山里人老黄和儿子熬盐制作火腿;“从老家安徽赶到有藕的地方”的安徽人——圣武和茂荣是兄弟俩等故事。
《舌尖》的解说词断句很短,几乎不使用形容词。尽管在第二季时,用语方面有意偏向文学的诗意,但仍然坚守精炼、简明的风格。“不管是否情愿,生活总在催促我们迈步向前,人们整装,启程,跋涉,落脚,停在哪里,哪里就会燃起灶火。从个体生命的迁徙,到食材的交流运输,从烹调方法的改变,到人生命运的流转,人和食物的匆匆脚步,从来不曾停歇。”这是《脚步》的开篇词。“脚步”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每一种食物的获取都要经过漫长“跋涉”。就像这一集中的主人公之一白马,他“选了一根藤条,使自己与大树相连,从现在起,这根藤条关系性命,看起来进展不错,一个小时后,白马爬了很高,但还有更高的距离要爬。父亲放心不下,匆匆赶来,白马不敢用双手砍树,速度明显慢了下来。现在,他准备摆脱藤条,40米高,并且没有任何保护,这是一次危险的行走,野蜂并不怕人,白马从长辈那里学会了点燃烟雾,迫使蜜蜂放弃抵抗,砍开蜜蜂藏身的树洞,就可以得到最甜美的蜂蜜”。又如为了获得蜂蜜需要经过上万公里的艰苦守候的养蜂人谭光树夫妇——“油菜花刚刚开花,谭光树已经准备启程,老谭是职业养蜂人,二十多年来,依靠这份工作,他养育了一双儿女。每年清明,他都要和妻子吴俊英,踏上追逐花期的旅程,一昼夜,蜂箱已在500公里外的秦岭。花的味道决定了蜂蜜的味道,地区不同,味道也完全不同,这正是蜂蜜作为美食的神奇之处。秦岭出产中国最顶级的槐花蜜,但老谭心里一点也不轻松,毕竟,养蜂是靠天吃饭的行当。四月中旬,天气突变,大风伴随降雨,花期提早结束,没有人知道,糟糕的天气会持续多久。二十多年前,老谭对未婚妻许诺,要带她从事一项甜蜜的事业。交通不便的年代,人们远行时,会携带能长期保存的食物,他们被统称为路菜,路菜不只用来果腹,更是主人习惯的家乡味道。看似寂寞的路途,因为四川女人的存在,而变得生趣盎然。妻子甚至会用简单的工具制作出豆花,这是川渝一带最简单最开胃的美食。通过加热,卤水使蛋白质分子连接成网状结构,豆花实际上就是大豆蛋白质重新组合的凝胶,挤出水分,力度的变化决定豆花的口感,简陋的帐篷里,一幕奇观开始呈现。现在是佐料时间,提神的香菜,清凉的薄荷,酥脆的油炸花生,还有酸辣清冽的泡菜,所有的一切,足以令人忘记远行的疲惫。丰盛的一餐,标志着另一段旅程的开启,全部家当,重量超过10吨,天黑前必须全部装车。因为工作,每个养蜂人每年外出长达11个月,父母的奔波,给两个读书的孩子提供了安稳的生活。二十多年,风雨劳顿,之所以不觉得孤单,除了坚忍的丈夫,勤劳的妻子,相濡以沫的还有一路陪伴的家乡味道”。许多人说,看了之后热泪盈眶。情感的迸发来自文本的叙事触发。《舌尖》采用的两条叙事线索,一条是美食线索,一条是与美食有关的人文线索。一个个小故事就像是一颗颗美丽动人的珍珠,被串联在美食线上,两者相互依托、相互映衬。讲述每一个故事时,都是铺成后戛然而止。故意留下伏笔,让观众为每个片段的主人公揪着一颗心。直到解说词结尾——“甘肃山丹牧场,老谭夫妇准备向下一站出发,又是一次千里跋涉;宁夏固原,回乡的麦客们,开始收割自家的麦子;东海,夫妻船承载着对收获的盼望,再次起锚。这是巨变的中国,人和食物,比任何时候走得更快,无论他们的脚步怎样匆忙,不管聚散和悲欢,来得多么不由自主,总有一种味道,以其独有的方式,每天三次,在舌尖上提醒着我们,认清明天的去向,不忘昨日的来处”——给出一个大团圆的美好结局。
纪录片的故事不是说出来的,而是用画面语言讲出来的。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探讨图像话语一般包含有三个层次的讯息:“语言学的讯息、被编码的图像讯息和非编码的图像讯息。其中被编码的图像讯息对应于直接意指形象,而非编码的图像讯息对应于含蓄意指形象。”④在纪录片中,被编码的图像是具体的食材、人物;非编码的图像讯息则是食物与人物之间的联系。
在《舌尖》的摄制中,特写、超常规视角和快速镜头被常常使用。在《转化的灵感》中,介绍了豆腐的制作过程。图像语言的表现,分别是原料大豆、豆浆、石膏的特写镜头,接着是胡学兵用石膏水点豆浆的长镜头,再来是胶凝后的豆腐特写。原本需要很长时间的制作豆腐过程被浓缩进几个图像里,原本需要花上数百字叙述的内容数十秒钟的镜头就已做到。更重要的是,与文字语言相比,图像更加形象、直接。从大豆到豆腐的过程,几乎不需要解说词的赘述,观众只用看其画面就能一目了然。除了特写和长镜头外,《舌尖》的剪接也为纪录片增色。“纪录片虽是摄影机对现实影像的一种纪录,但是纪录片的本质并不仅仅停留在此,剪辑才是凸现一一落实纪录片创作之大义精髓。”⑤《舌尖》的剪接率非常高,对一些必要的长镜头多采用交叉剪辑,将持续性的镜头拆分拼接,把长镜头拆分成很小的片段,使冗长枯燥的长镜头变得短小跳跃,画面的视觉效果立马增强。比如《家常》中介绍“新婚的女儿回门,娘家会制作枣花馍。馍的数量和花样,代表了对女儿的疼爱程度,没有一个母亲会怠慢”,竟然由27个分镜头组成。包括揉面,捏各种各样的形状,用筷子、剪刀等工具塑形,放入枣子、制作者特写等。图像语言的优势还体现在意义渲染上。“在蛋白质的提供上。大豆食品是唯一能够媲美肉类的植物性食材。对于素食者来说,这相当完美。中国的豆腐在‘清寡’中,暗含了某种精神层面的气质。古人称赞豆腐有‘和德’。吃豆腐的人能安于清贫,而做豆腐的人也懂得‘顺其自然’”,在讲述中国传统食物——豆腐时,画面配合一块块洁白无瑕的实物,素净的形象引发观者的联想。又如,《相逢》对火锅的拍摄——混合着花椒、辣椒的火红底料,黄喉、毛肚、鸭肠、胗花、耗儿鱼、午餐肉等食材,滚沸的锅、汆烫、蘸碟……好一幅琳琅满目、热火朝天的景象。正如“火锅,最集中地体现了中国人对于热闹对于团圆的向往”所言,山城里灯火阑珊,遍布一间间挂着红灯笼的火锅餐厅,吃火锅的人们各个酣畅淋漓,满足无限。
纪录片的渲染还体现在声音语言的运用上。音乐、音效的配合,不仅加强了画面的张力和表现力,更对纪录片整体叙事抒情增添了艺术感染力。在纪录片中,音乐和画面的紧密结合就会产生单独二者所不能产生的意境,赋予了它们新的生命。刀与砧板接触时的“咚咚”响、鳜鱼下锅煎炸时的“吱吱”声、打鸡蛋时筷子与瓷碗间“叮咚”作响、千岛湖中大鱼在水里的“噗通噗通”翻腾……无不形象又生动地刻画着食材的优良、制作的精细。这些响声,不单单是烹饪美食的声音,它们更见证着人与整个自然之间的互动。《舌尖》的声音语言中,当属配乐留给人们最深的印象。有一首反复播放的音乐,可以被认为是《舌尖》的主题曲。它是由中国民乐演奏和西洋交响乐协奏等版本,配合叙事基调,被多次插入纪录片中。极具中国味儿的民乐版本,曲调轻快、悠扬,常用于介绍传统美食的制作过程;西洋乐版本,则气势恢宏,被运用于开篇或是结尾等处,给人一种磅礴、震撼、升华之感。
无论是新闻、报告文学这样的书写文本,还是影视报告文学、纪录片这类的多媒体声像文本,“非虚构”写作都是种再现。只是书写文本用的是文字语言,而纪录片用的是多维语言。语言方式只是“非虚构”写作组织结构,其背后深层次的审美意义同样值得关注。纪录片通过其画面、叙事、构图、解说词和音乐等方面传递它的美感,传递其对审美价值取向的追求。大美始于大爱。食材、美食、地理、风物不止于舌尖,终究归于家和爱。无论生活多么不易,我们总是记得家乡的味道和爸妈的味道,一个味道一旦和记忆里的某个特殊时刻相结合,那么美食就不单单只是美食了,它已成为心灵里最珍贵的东西,一辈子都难以忘怀。时光走过,味道永恒。《舌尖》正是利用观众的视觉、听觉体验,触动嗅觉、味觉感官,激发脑的回忆、心的感动。正如《家常》里所纪:“家,生命开始的地方,人的一生走在回家的路上。在同一屋檐下,他们生火、做饭,用食物凝聚家庭,慰藉家人。平淡无奇的锅碗瓢盆里,盛满了中国式的人生,更折射出中国式伦理。人们成长、相爱、别离、团聚。家常美味,也是人生百味。”
二、非虚构与全媒体新文化
无论是纪录片还是影视政论片,从表现形式上来看都是非虚构文本与媒介融合后的产物,是技术进步的结果。但若把它们的诞生与发展放入整个社会进程中审视,它们既是文化流变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全媒体新文化变革的主要因素。当文学被无数次地宣告死亡之后,2003年美国批评家希利斯·米勒在他带来的作品《论文学》中对文学的命运作了如下表达:“文学的终结就在眼前,文学的时代几近尾声。该是时候了。这就是说,该是不同媒介的不同纪元了。文学尽管在趋近它的终点,但它绵延不绝且无处不在。它将于历史和技术的巨变中幸存下来。文学是任何时间、地点之任何人类文化的标志。今日所有关于‘文学’的严肃思考都必须以此相互矛盾的两个假定为基点。”一方面,“某些经典的人类精神活动范式的存在根基显现出被动摇的迹象。在这种冲击下,千百年来一直被作为人类精神家园守望者和美的创造者的文学活动不能幸免于难”⑦,媒介不仅冲破了当代文学的外部环境,而且也进入文学生成机制内部,对包括作家队伍、文学结构、文学主题、创作方式、传播介质、传播方式、影响范围、文本型态、受众结构、接收方式和接受心理等文学活动的全过程都产生了深度影响。但另一方面,如果没有机械复制技术的发明,影视政论片可能还只是极少部分人知道的文本外化的传播种类。积极地看,媒介融合并不是取代纸质媒介,它只是一种“非虚构”写作本事迁移方式,也是生产经典的另一种可能。“本事”是中国古典文化与传统诗学所固有的一个本土性概念。“所谓本事迁移,指的就是特定原发性事件被其他文本所引用、转换、扩充、改编、续写、改写、重写、戏仿等。在这里,本事迁移并非本事的照搬,也非阐释本事原型中为人所共知的主题或思想,而是在处理、改造本事材料的基础上,利用本事原型所提供的相关材料与想象空间,来进行新的艺术世界的建构,来揭示本事或过往‘本事改写’中所未曾发现的本事意蕴与意向,进而使‘本事的再生产’具有当下性。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本事迁移’实质上是创作主体基于艺术想象的建构机制及其能力而对原态性本事所作出的重构”⑧。正如影视政论片之于报告文学,通过媒介化的本事迁移,“非虚构”写作可以重新塑造经典。可以看出,尽管媒介文化有很多诟病,但是必须正视,它确实推动了“非虚构”写作的发展。
媒介化是当下文化的表征之一,它指向消费社会中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是一个生态系统的存在,社会生态决定文化生态,文化生态决定文学生态。让·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一书开篇写道:“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富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恰当地说,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商品)的包围……我们生活在物的时代:我是说,我们根据他们的节奏和不断替代的现实而生活着,在以往所有文明中,能够在一代一代人之后存在下来的是物,是经久不衰的工具或建筑物,而今天,看到物的产生、完善和消亡的却是我们自己。”⑨消费社会这样一个被商品所包围并以商品的大规模消费为特征的社会不仅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还改变了我们的社会关系和文化生活方式。我们必须要意识到“人们需要商品,是为了使文化的各个范畴得以显现并且稳定下来”⑩,曾经作为表达自我工具的“非虚构”写作,已经成为联结社会群体关系的坚固纽带。包括作者与读者、读者与读者关系在内的传播者、受众等群体关系,正是通过诸如纪录片、影视政论片等大众传播商品维系。正如鲍德里亚所言,“电视带来的‘信息’,并非它传送的画面,而是它造成的新的关系和感知模式,家庭和集团传统结构的改变。谈得更远一些,在电视和当代大众传媒的情形中,被接受、吸收、‘消费’的,与其说是某个场景,不如说是所有场景的潜在性”⑪。
这与法国著名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所说的文学场的作用不谋而合。“文学场或艺术场是能够引起或规定最不计利害的‘利益’的矛盾世界,在这些世界的逻辑中寻找艺术品存在的历史性和超历史性,就是把这部作品当成一个被他者纠缠和调控的有意图的符号,作品也是他者的征兆。这就是假设从中表现出一种表达的冲动,而场的社会必要性所规定的形式,趋向于使这种表达冲动难以辨认。抛开为追求纯粹的形式而超脱纯粹的利益这一点,是理解这些社会空间的逻辑必须付出的代价,社会空间通过它们运行的历史法则的社会炼金术,最终从特定情感与利益通常残酷的对抗中,抽取普遍性的升华了的本质;而且它提供了一种更真实的最终更有保证的观念,因为这是一种不那么超凡入圣的观念,这来自人类成果的最高征服。”⑫布尔迪厄将文学场视为社会生活的一种表现,是充分地融会了社会生活的各种需要的一个场所,并且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需要又可以影响与制约着文学的形成并转化成文学观念。全媒体时代中,“非虚构”写作的直接动力是文化的市场化以及大众文化的繁荣。场域改变导致了文化资本重新分配,使得大众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政治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双双边缘化。
依据布尔迪厄的理论推断,“非虚构”写作与大众媒介的联姻使得非虚构文学场发生变化。这个变化来自与媒介技术的介入、大众文化各因素的促成;同时,新生成的非虚构文学场也反作用于“非虚构”写作及大众传播受众的社会生活。大众媒介就是将以语言为主的信息符号转化为可感知的文学形式,进而将包含信息思维和文化符码传递给接受主体,并被其理解和认同的物态化。非虚构文体媒介化后,信息生成的最终指向接受主体。各种被媒介化后的信息和观念只有被接受主体所接纳或识别使得接受者与“非虚构”写作达成信息共鸣,才能使新的非虚构文学场发挥最佳效果。否则,则需要找出场里各元素中哪个环节影响了效用发挥。有人会以大众媒介复制方式太过多元而造成大众产生真实与仿真的模糊感来抨击媒介文化的弊端。在他们看来,电子媒介的出现,打破了信息传播的静态性和符号单一性,以声像传播为主的电子媒介直接诉诸人的视听感官,以完全富有生活气息的具象性符码来传达信息。摄影、电影、电视、VCD、广告、仿真雕塑等种种形式的图像产品迅速流行,虚拟的幻觉形象越来越在我们的生活方式中起主导作用。各种视像符号包围着我们,体现了一种欲望和离奇的幻想,视觉传媒拼贴、组接着各种视觉影像,组成了比现实更现实的一种“仿像”。极强的影像表现力最终将媒介制造的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混同为一,不但塑造了大批沉迷于形象魅力的消费者,而且也为商品附加了无尽的象征意义。依托电子媒介进行商业信息和广告的传播,它所带来的不仅是即时的形象享受和消费刺激,受众对媒介的记忆依赖性使得这种符号具有更多的潜在消费价值。传统的意象为主的文化正在被仿像为主的文化所冲击和消解。那么,小说等文学形式在文化市场一枝独秀的“霸权”就是理所应当?文学就应该固守原态,任凭时代进步、社会发展却原地踏步、不进则退吗?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带着它的意识形态一起走进现代社会的。虽然我们可以批判包括网络在内的现代电子传媒是虚拟的“电子幻觉世界”,以“天涯若比邻”的虚假方式遮蔽了人与人之间更加冷漠的关系。但在整个被媒介裹挟的世界里,电子幻觉世界提供的自我满足和幻觉实现,是传统平面传媒难以抗衡的。它在通过开放、平等、自由的写作、浏览的同时,也在无意中结束了传统文学的历史和观念。因此,现代传媒的发展和多元文化、特别是与科技手段相关的消费文化的兴起,是抵抗以印刷为中心的“个人价值主义的技术”⑬,向非虚构新文化转变的动力和象征。
非虚构的全媒体新文化特征包含后现代性。“我们可以回顾一下现代主义文化艺术的特征:充满精英意识的高雅文化,仅仅为少数人欣赏的文化,表现自我个性的审美文化,甚至‘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化观念,等等。显然,这一切都是后现代主义艺术家所要批判和超越的东西。因此,我们大概不难由此推论,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是反美学、反解释、反文化和反艺术的,但是它反对的是哪一层次上的文化呢?这也许恰恰是我们容易忽视的:它反对的正是具有崇高特征和精英意识的现代主义美学,抵制的是具有现代主义中心意识的解释,抗拒的是为高雅文学的艺术,总之,后现代主义文化艺术与现代主义的高雅文化艺术不可同日而语。它既在某些方面继承了现代主义的部分审美原则,又在更多的方面对之进行批判和消解”⑭——这是学者王宁对后现代主义反叛性的理解。媒介融合后的非虚构表达不仅是视觉性、消费性,是祛精英化的。自此,普通大众就不需要花费很多时间阅读厚厚的长篇文学名著,只需在自己家的电视或是个人电脑里花上一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欣赏到一部纪录片或是影视非虚构作品所提供的审美愉悦。抑或,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们也可以改变了研究方法,走出书斋、打开多媒体,观赏和研究更容易激发审美情趣的声像作品。在后现代社会里,打破常规、开拓创新成为主要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方式。如今,媒介话语对非虚构“商品”有增值意义,使得非虚构文化逐渐倚重视觉、依赖技术和消费,完成了从现代性向后现代的过度,但这并不是终点。非虚构文化向图像转化不会对包括“非虚构”写作在内的文学艺术发展的终点有明确指向性。说到底,它只能表示一段时间内文学的存在状态,这个状态恰好为人们提供了更多关于文学的思考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