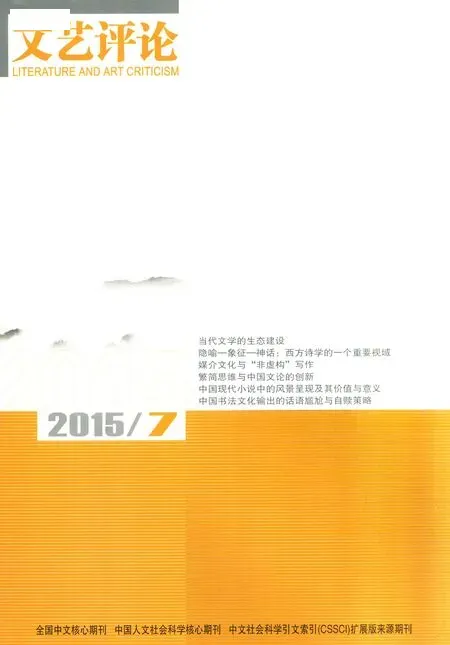中国现代小说中的风景呈现及其价值判断
○王卫平 陈广通
中国现代小说中的风景呈现及其价值判断
○王卫平 陈广通
风景描绘是小说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小说史而言,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小说,却从一开始就自然而然地将风景看作是自己血肉之躯的一部分。虽然开始时它并没有特别明确的风景意识,但,将风景写进小说,却在古代小说家们那里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①。
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过程中从来就不缺乏风景描绘的传统。如果稍加留意,就会很轻易地发现中国古代文学对于风景的言说几乎可以构成一部文学风景发展史了。从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开始,风景就已经在文学创作中占了相当重要的地位。随着魏晋南北朝之际文学艺术自觉时代的到来,山水诗中的风景描写也取得了独立意义。景物本身就是诗歌创作的目的,不再承担审美之外的任何功用。到了初唐以后,文学作品中的风景在普遍意义上真正与思想、意志、情绪融为一体,同时又保持自己的独立审美价值,盛唐达到鼎盛。到宋代仍没衰落,散文方面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明清两代诗文中的风景运用比之前代虽无特出之处,但也不乏精彩。就小说而言,中国古代的风景描写也仍有传统,虽然少见作家们有明确的理论倡导,但在作品中对于风景的描绘也从没中断过。特别是到了《红楼梦》出现,风景在小说中的描写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红楼梦》中虽然少有大段大段的景物描画,但只是在关键处看似随意的那么轻点几笔,境界就已然全出。“五四”前后,经过对于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对于外来方法的借鉴,中国现代小说中的风景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态势。本文要讨论的正是中国现代小说中风景描画的繁荣及其意义与价值,并尝试指出它所存在的缺失。
一
中国现代小说对于风景的描绘是精彩纷呈的,我们在这里把它按风格分门别类加以论述。
1.破败、凋落的风景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小说流派应该算是早期乡土小说。也是这个流派开始了中国新文学对于风景的透视与把握。这个流派对于中国现代小说发展的第一个贡献是“第一次提供了中国农村宗法形态和半殖民地形态的宽广而真实的图画。初期乡土小说相当真切地反映了辛亥前后到北伐战争时期中国农村的现实生活,表现了农村在长期封建统治下形成的惊人的闭塞、落后、野蛮、破败,表现了家民在土豪压迫、军阀混战、帝国主义势力逐步渗入下极其悲惨的处境”②。与此内容相适应,早期乡土小说作家所描写的风景也多是破败、凋落,气氛是阴冷的,色彩是暗淡的。研究者多把鲁迅划为早期乡土派的,但他的创作具有多方面的开拓性,乡土小说的创作道路也正是由他开创。鲁迅《故乡》的开头部分为我们描画出了一番晦暗阴冷,满眼望去尽是苍凉的景象,一切都是死气沉沉,“没有一丝活气”。而劲风悲响,奏出一个没落时代的哀歌。早期乡土小说中也有一些明丽的画面,不过那也只是作为人物悲惨处境的一种反衬。台静农就经常使用“以乐景写哀”的方法。③《拜堂》写的是主人公与寡嫂成亲的故事,拜堂成亲本来是一个喜庆场面,可是其中所揭示的中国农民背负肩扛的传统观念的因袭重担是多么沉重。人们有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有对人性天性欲求的合理要求。问题是在那样一个黑暗腐朽、专制封建的年代,他们对于新生活的追求似乎都成了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情。在实施的时候他们心理承受着巨大压力,以至于心惊胆战,“做贼心虚”。
她们三个一起在这黑的路上缓缓走着了,灯笼残烛的微光,更加黯弱。柳条迎着夜风摇摆,荻柴沙沙地响,好像幽灵出现在黑夜中的一种阴森的可怕,顿时使这三个女人不禁地感觉着恐怖的侵袭。汪大嫂更是胆小,几乎全身战栗得要叫起来了。
《拜堂》中这段风景描写,无疑对于揭示人物的心理起到了重大作用。像《红灯》《新坟》用的也都是“以乐景写哀”的手法。
在小说中同样多写农村凋敝、破败风景的是20世纪30年代以茅盾为首的“社会剖析派”。这个流派以科学的世界观为指导,极力辨析近现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同时希图以他们宏大规模的文学创作来概括现代中国社会的全貌。他们与早期乡土小说一样也描绘农村的破败,这里的风景也同样不是美丽的。如茅盾的“农村三部曲”和《霜叶红似二月花》等作品中都有这种描绘。这个流派的作家善于以客观冷静的“再现”方式来勾画农村残破的风景。吴组缃《樊家铺》的开头就是一段纯粹的乡村景象介绍,一段白描,就是把这个村子的外在形貌用笔勾勒。那“乱石砌成的大路”、裂了缝的土墙、屋梁、顶棚给读者的仍然是一片衰败、残破的画面。从这样的画面中我们可以想象到村人的贫穷,以及他们生活的窘迫状态。
2.淡然恬静的风景
同样写乡土小说的现代作家是废名,但他的“乡土”与前面所述的早期乡土小说是有所不同的。废名给“乡土”增添了另一种意义,研究者们把它叫做“乡土田园小说”。顾名思义,废名是通过“田园”把“乡土”提到了不同于“土滋味”、“泥气息”的中国古代士大夫的审美趣味上。我们可以在他的作品中领略到陶诗风范与唐人风致,他有意识地以诗入小说,把小说当绝句来写,那么他的作品中就自然少不了风景的点缀。常常在不经意间,或是直接引用,或是反用其意,在叙述的间隙就把诗带进了字里行间。最常见的还是这种小境界的创造:
傍晚,河的对岸以及宽阔的桥柱上,可以看出三五成群的少年,有刚从教师的羁绊下逃脱的,有赶早做完了工作修饰得胜过一切念书相公的。桥下满是偷闲出来洗衣的妇人,有带孩子的,让他们坐在沙滩上;有的还很是年青。一呼一笑,忽上忽下,仿佛是夕阳快要不见了,林鸟更是歌啭得热闹。
这是《浣衣母》中的“风景”,颇具陶诗风范。陶诗风范则主要表现为通过风景透露出的道家宁静淡泊的人生态度。废名小说中的风景并没有浓重的色彩,就那么自然随意,似乎是一阵微微的清风,又像是一抹薄薄的流云。正是在这清风流云上面表现了作家的淡然清澈。
与废名风格相似的风景勾画高手是沈从文。沈被夏志清称赞为“中国现代文学中最伟大的印象主义者”④,这话是不错的。《静》中,岳岷登楼远望那段描写确实美妙无穷。《边城》更是达到了人事风景的浑然一体,开头的那段风景描写是沈从文的经典之笔,常常被众多论者所引用,而且不管是论沈从文思想的还是论沈从文艺术的都可以信手拈来。正是这样的水光山色哺育了翠翠这样天真诚挚、柔美多情的少女。而且细心体会过的作者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如果把《边城》中的风景从作品中剥离出去,整个故事就将变得了无生趣。
3.浓酽滞重的风景
滞重浓酽的风格在“革命小说”的风景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与废名、沈从文为代表的轻柔淡然风格恰成对比。它对于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有多大贡献我们暂且不论,这里我们要讨论的仍然是它的风景。“革命小说”,要表现的自然是革命斗争,革命斗争必然残酷、惨烈,必然充满了血与火,所以“革命小说”也就少不了狂暴、呼喊、怒吼,其中的风景也就必然风起云涌、巨浪滔天。难得的是作家们也多少能做到风景与人物心情和故事情节的统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感觉到风起云涌、巨浪滔天所唤起的力感,有时还真的让人产生了“内摹仿”的冲动。洪灵菲《流亡》中,写沈之菲到香港后来到海滨时的那一段风景描写就与主人公内心的壮烈激情配合得相得益彰。海上的斜阳、浪花在一个满怀革命理想、积极乐观、有必胜信念的革命者看来无疑是壮丽的、宏伟的、博大的,这些壮观的景色就如他坚定的心一样坚不可摧。静得牢不可破,动得无坚不摧。浓酽则表现为“革命风景”喷薄出的鲜红与灰黄颜色,鲜红是革命热血的奔流,灰黄是人民苦难的象征。
还有一种和“革命风景”同样沉重浓郁的,但更多表现个人压抑的风景展现。作家郁达夫,他的作品多抒写动荡时代中个人的主观情绪,表现在时代潮流冲击下的青年人内心的苦闷、彷徨、忧郁和哀伤。所以作品中的风景也让人感到灰暗、阴冷、压抑、局促。《沉沦》里的主人公热爱国家、向往自由、追求个性解放,却为社会抛弃。只身来到异国他乡,他所处环境下的风景不管是室外还是室内,都是一味的空旷,人处其中只感孤单无助。更有一些“沉沉的黑影”如鬼如魅,加重了他内心的恐惧。《春风沉醉的晚上》《青烟》里也是哀怨、悲愁的调子,风景也多灰暗、阴沉,满蕴着由经济生活的困窘与精神世界的饱受压抑而带来的凄恻与悲凉。与郁达夫这种格调相仿的女作家庐隐,她也注重哀婉凄切的环境气氛的烘托。比如她的代表作《海滨故人》。
4.浮华绮艳的风景
这种风格的风景来自于现代小说史上最具现代色彩的流派——新感觉派的组接。这个流派的代表人物有施蜇存、刘呐鸥和穆时英。后两位多写繁华都市纸醉金迷的快节奏生活以及在这种生活表面覆盖下现代资本主义殖民地众生的变态与淫糜。“中国新感觉派创作的第一个显著特色是在快速的节奏中表现大都市的生活,尤其表现半殖民地都市的畸形和病态方面。”⑤这就使刘、穆的“都市风景线”充斥了浮华、绮艳与变态的繁杂。穆时英《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中那段描写街面景色变化的文字五光十色、华彩缤纷、光影交错,让人目眩神迷。病态社会里这种资本主义畸形发达的文明带给我们的也正是这种烂肉桃花一样的体验。刘呐鸥《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中赛马开始前那段环境,描写的本来是“晴朗的午后”,却充满了“赌心狂热的人们”,这是否可以理解为末落时代的垂死挣扎呢?“光闪闪的汗珠”蒸腾出的是一股腐烂、陈朽的“尘埃、嘴沫、暗泪和马粪的臭气”。
施蜇存更进一步,他深入到了人的心理风景。《梅雨之夕》里那位带了雨具的男子送没带雨具的女子回家,一路的内心风景何等微妙。也可说是波澜起伏、曲折幽微了。而这所有一切都发生在那霏霏淫雨里。《春阳》则是一位丧偶少妇的悲情心理。然而,心理必然来自于现实,必是社会现实才让她有了如此的命运,才让她如此纠结,为了保住所得的遗产,她也只能这么单身活着。可她也有人类原始的情欲,这个该如何满足?这无疑昭示了她的悲剧所在。而她的悲情心理是通过“满街满屋的暖太阳”烘托出来的。毫无疑问,新感觉派在发现了都市风景错乱的同时,也给健康的现代文学风景增添了一抹有些病态的情绪。从艺术角度来看,这也是一种丰富与补充。
二
风景之所以在现代小说中表现得精彩纷呈,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如前所述从中国文学诞生的那天起,风景就已成为文学作品中极其重要的元素(虽然理论上的阐释者并不多)。它有时被用来营造气氛,有时被当作人物性格的反衬,有时作为一种象征,还可以用以构造意境……总之从古代至现代,风景在文学中从来就没缺席过,它已经绵延了几千年,形成了传统,而传统的血脉是不可能被割断的。“五四”先驱者们破旧立新的态度异常坚定、绝决,可也并不是如后来“寻根文学”者所言的完全割断了“传统的脐带”。先驱者们的义无返顾也只是有意为之的一种策略与姿态,他们是为了尽快建立起新文学的秩序,立稳脚跟,与世界对话。态度是决断的,但提倡新文学者也是实在无法割舍传统文学的千年积淀。鲁迅的诗歌多为旧体,有的作品中渗透了儒家孝道思想,也有的作品与佛学思想不无关系。郭沫若发出时代需求的呼喊,可也是无法丢弃心中古典文学的浸染。他的《凤凰涅槃》就有对于“天人合一”境界的陶醉,他本人也曾承认陶渊明、王维对他的影响。既然传统无法割断,那么文学中的风景也当然步入了现代,并接受着现代技巧的改造与重铸。比如传统的道家“天人合一”思想、“物我两忘”境界,前者如前面讲到的郭沫若,后者以废名为例。废名是现代作家中的写景高手,他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说自己是有意把小说当成绝句来写的。而引入作品中的诗句,或是化用的诗句,又以风景诗为多。他有本事做到不露痕迹、自然而然。使景中有情、情中有景,常常是叙述过程中仿佛不经意间就来那么一句半句,或是那么随意的一句写景妙语。初一读到有点意外,回首咀嚼就情趣顿生了。
“五四”以后,外国文学的大量译介,也是风景在现代小说中繁盛的一个原因。被介绍进中国的大都是有着世界级影响力的作家,其中不乏写景的大手笔: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川端康成……他们的创作无疑使中国作家对于风景在小说创作中的意义有了新的不同以往的理解。比如风景在叙事节奏、小说结构等方面的作用是之前的中国作家很少思考的。外国此类小说的阅读无疑给作家开了眼界,提供了新的借鉴。与此同时,外国各种文学思潮也大量涌入,其中最具影响力的莫过于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在最初传入时,人们并没有重视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明确分野,但它们都强调加强实地描写,加强细节、局部的真实以取得“可信”的效果。浪漫主义则凌空高蹈,并不在意细枝末节的相像,只求内心情感的畅达抒发。这样就使风景的描写也呈现出了不同的风貌。前者细而精,后者粗而略,具体表现各有特色。同时泛神论、卢梭返归自然等哲学思想的传入也给小说中的风景运用造成颇大的影响。泛神论认为神存在于自然万物中,“我”也是自然的一部分,神即万物,那么“我”亦即神。这就要求把个人融入自然,拥抱宇宙,放眼众生。是一种对于自然的崇拜,也是一种敬畏。这种思想在当代世界是不可多得的。
同时,中国现代小说中风景描写的繁荣也与作家个人的人生经历、审美主张、创作追求有关。以京派为例。这一派小说家大都生长于农村,日后通过各种努力在城市中觅得了自己的位置,然而他们无法忘怀故乡的人事。是故乡的那片土地滋养了他们,使他们在童年时期已经开始产生了对于世界、人生、艺术观念的萌芽。小孩子喜欢与大自然亲近,风景自然也就给了他们最初的生活体验,或纯净或朴厚,都在他们的生活道路上印下深深的痕迹。当他们日后从事创作时会回想起曾经让他们心潮澎湃或恬淡宁静的风景,并把他们对于世态、历史的看法融入风景的描绘中。最典型的是沈从文,湘西山水自然优美,他在《从文自传》里就写到自己童年时期对于大自然的热爱。常常是和小伙伴们一起逃学,到附近山上河里游玩嬉戏,他们上山爬树、下河泅泳、捉鸟摸鱼……宁可被罚挨打,也还是初衷不改。于是大自然像长养翠翠一样长养着他,他也日甚一日从自然环境中学到了从学校里所学不到的丰富知识,渐渐地感知体悟,竟把整个生命都融了进去。于是当顽童沈岳焕成为作家沈从文时,这种深切的生命体验也就自然发展成为他一贯的美学趣味与艺术追求。
三
朱光潜在《文艺心理学》中把美分为两类:刚性美与柔性美。中国古代叫做“阴柔”与“阳刚”,康德称作“雄伟”与“秀美”。大体而言,美分为这两类是具有很大包容性的,风景也无非就这两种,或是这两种风格的综合。“古道西风”属于前者,“小桥流水”属于后者。我们写风景也无非是造这两种境界,或两者兼而有之。⑥可是美的创造的原则是“适宜”,处理任何事物都有个“度”的问题,我们不能“过”,也不能“不及”。莱辛论述《拉奥孔》是论者们经常会举的一个例子:拉奥孔被巨蟒缠身,那是非常痛苦的事情,但是雕塑家并没有让拉奥孔开口大叫,而只是让他垂头叹息。如果开口大叫,那就必然把痛苦表现到了极点,而在最高处是没有下落的余地的。我们的想象也随之停止,就失去了意味。中国现代作家描写风景时却常常在“度”这个问题上处理不当,把握不好“雄伟”到何处止,“秀美”到哪里停。“雄伟”的形象是指在“物理”和“精神”两方面足够大的形象,它带有“阻拒”性,初看使人惊惧。而这只是瞬间,接下来通过主体心灵的领悟是会发生转变的,主体会在忘我的境界中与物合一的。⑦但有的作家正是一味寻求在这个“巨大”上用力,似乎越“巨大”越好,结果却适得其反,形象过于“巨大”超过了正常人的心理承受限度是会让人“恐怖”的。这样,主体心灵就被从审美静观的状态里拉回了实际生活的运作机制中,失去了审美体验所需的“心理距离”。最后“美”也就沦为了“丑”,创作失败。现代小说中不乏这样的例子。如革命文学兴起之初,它会不厌其烦地给我们捧来一把血、一把泪、一个破裂的头颅、一具残缺的尸体,似乎只要有这些东西就会组成一幅动人的图景。如今我们再回头看看那些作品有几部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呢?沈从文当时就说:要血和泪吗?对不起,这个我不能给你。我们不能不说当时的沈从文是清醒的。“秀美”的事物多小巧、精致、轻柔、绵软,它可让人愉悦,引人怜惜、诱人爱慕。但是,如果处理不当或过火就会显出矫揉造作,有刻意为文的痕迹,更有甚者还可能让人产生哗众取宠的感觉。河边的洗衣少女,头发上斜插一支红花,临水自照,我们会感觉秀丽可爱——那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相反,如果把这位少女换成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那不就很滑稽了吗?“五四”以来有不少这类作品,特别是鸳鸯蝴蝶派之类的那些才子佳人小说。可是,这个小说流派的存活时间并不短,究其原因(包括上述的“革命文学”)应该是与社会环境和时代风潮有关。
现代小说中风景描绘的另一个缺点是浮泛的问题。不论《诗经》《古诗十九首》,还是唐诗宋词元曲,它们莫不把写景作为艺术表现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能把景、事、人和谐地统一到一起,我们读起来并没有游离之感。而现代文学中有不少作品文字并不粗俗,却总有些让人感觉虚假、繁缛,问题出在哪里呢?一言以蔽之:人景分离。优秀的作品总是将景物描绘与人物行动、情绪流动相结合,突出的是人物的细微动作所引发的风姿摇曳,并不是为了写景而写景,而是做到了“物、情、意”的三位一体。反观那些失败的作品,却只将传统中用滥了的套语强加附会,这样看上去很美,仔细体会却了无滋味。
事实上这也涉及到了风景在小说与在诗词中的不同作用和意义的问题。在古代诗词中,风景大都是作为诗人情志的载体或是映射而存在的。风景的描摹过程事实上也是情感流泄的过程,诗人们把情与景统一到一起造成一个有广泛延展性与纵深感的审美空间,达到的不止是“情景交融”,这种意境甚至会上升到哲理体悟与思索的高度。有时读者会很轻易地发现在古代最优秀的写景诗中“物、情、意”是三位一体的,如果把景作为一个独立的元素从整首诗中抽离出去,那么这首诗也就一无所有了,景也失去了它作为整个诗境有机体组成部分的特定意义。就像黑格尔所说:砍下的手已经不是手了。而在作为叙事文学的小说中,风景的意义却并不被认为如此重大(至少现代作家是很少有人谈论到风景之于小说的意义的)。小说中的风景一般是被作为整个情节或者人物的陪衬而存在,或者烘托气氛、或者反衬性格,如果将风景抽出,故事的完整性并不受到质的破坏。即使像《边城》那样浑然天成的作品,如果没有风景,它的事件也仍可完整,只不过整个艺术效果与作者的美学精神将大打折扣而已。这正是现代作家的短板,他们没有把风景在文学中的意义提升到应有的高度。丁帆教授说:“在中国人的‘风景’观念中,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是两种不同的理念与模式,在中国人的审美世界里,‘风景’就是自然风光之谓,至多是王维式的‘画中有诗,诗中有画’的‘道法自然’意境。”⑧此说诚然,但笔者还是微有异议。我们看看中国古代诗中的一流作品,那里的风景显然没有仅仅停留在“画中有诗,诗中有画”的层次上。比如柳宗元的《江雪》,谁能说它没有人文意义?更不用说苏轼《题西林壁》这种明而显之的妙理小诗,它已经有了相对、转化等哲学思辨意义涵盖于其中。而且“道法自然”难道不是一种哲学思想?中国小说中的风景有没有这种哲学意义上的提升呢?古代小说里当然少见。唐传奇、宋元话本里的风景描写绝少仅见,到了明清章回小说,风景描写有所发展,但也很少有能激起读者哲思体悟的。在西学东渐与有意无意之间对于传统转化的过程中,现代中国小说的风景描写显然也顺应潮流有了巨大进步。但“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即使将‘风景’和人文内涵相呼应,也仅仅是在文学为政治服务的狭隘层面进行勾连而已,而非与大文化以及整个民族文化记忆相契合,更谈不上在‘人’的哲学层面作深入思考了。从这个角度来说,‘五四’启蒙者们没有深刻地认识到‘风景’在文化和文学中更深远宏大的人文意义。”⑨这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不过,也不能一概而论,沈从文就“在其景物描写之中更多地是注入了老庄哲学的意蕴”⑩。鲁迅也“注意到了‘风景’在小说中所起着的重要作用,即便是‘安特莱夫式的阴冷’,也是透着一份哲学深度的表达,这才是鲁迅小说与众多乡土题材作家的殊异之处——不忽视‘风景’在整个作品中所起的对人物、情节和主题的定调作用”⑪。
关于风景在小说写作中的意义,曹文轩在他的《小说门》中从引入与过渡、调节节奏、营造气氛、烘托与反衬、静呈奥义、孕育美感、风格与流派的生成这七个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述,⑫此不赘述,在这里我们要重点考察的是引风景入小说这一行为本身对于作家以及中国小说发展的意义。对于某些作家来说,风景使他们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标志与印记,不仅仅是风格上的,有时候风景甚至可能会是作品生命系统完整呈现的必备要素。以沈从文为例,在他的小说中风景绝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诚如上文所述,如果把《边城》中的“风景”抽离出去,故事的完整性当然不会受到大的损害。问题在于,如果没有了风景,那么整部作品所表现出的作家的情感与哲学体悟也将了无存在。因为在《边城》中,风景本身即是一种“结构”。它不是作为“背景”而存在,而是用一种弥散的方式渗透在作品的字里行间,渗透在人物的生命中。中国现代小说中的风景描绘是对中国古代风景入小说的继承和发展,风景的描绘在中国小说中从来就没有中断过,现代作家们把风景作为小说组成部分实属自然而然。他们的成就在于,把之前人们认为是陪衬性的风景发展成了必不可少的结构性风景。尤其是鲁迅、废名、沈从文等人,他们使人们意识到了风景在小说中的独特地位与价值。当代经济高速发展,林泉山水已被破坏殆尽,钢筋水泥筑起另一道风景。然而那已不是自然,我们离自然已越来越远。文学中的风景也就随之失去了一大片领地,现在的我们很少感受到田野上清新的风,天空上悠悠的云。曹文轩时时哀叹“现代小说却已不再注目风景——最经典的小说使我们再也看不到一点风景。”⑬在当代文学中,风景是缺失的。回头看看先驱者们走过的路,他们各自独树一帜,或精雕细刻、或自然天成。单从技巧上讲,就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更重要的是他们那种委怀自然的胸襟,对于我们今天的创作实在是一种启示。
生态文学批评者认为“人类的生活家园是自然生态环境,而人的精神家园也应从自然生态中寻找。”⑭当代也有不少作家已经意识到人类生命与自然的关系,可是文学中的风景似乎仍没得到应有的重视。我们不能把风景等同于自然,但是风景是自然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亲近自然、热爱生命需从“风景”开始。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①⑫⑬曹文轩《小说门》[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2年版,第275页,第297-325,第338页。
②③⑤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68页,第66页,第140页。
④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7页。
⑥⑦朱光潜《文艺心理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12页,第220-222页。
⑧⑨⑪丁帆《新世纪中国文学应该如何表现“风景”》[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第18页,第18页,第20页。
⑩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2页。
⑭张艳梅等《生态批评》[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