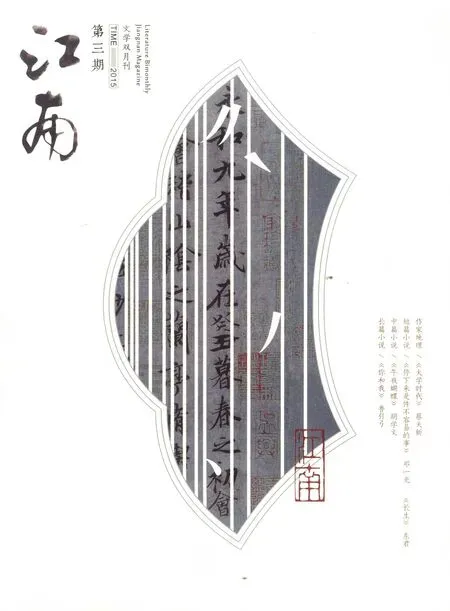长 生
□东 君

有一阵子,我喜欢去河边走走、坐坐。河流的悠长与时间的闲散,在悄然散落的阳光里,仿佛有着对应的关系。散着手走路,看着自己的影子缓缓移动的样子,这一天也就在不知不觉中拉长了。无聊的时候,我会随手拍几株树或一些野花野草什么的,发到微信群里。于是,就有人说我是个闲人。闲人,没有大事可干,通常会把时间消磨在手机游戏上、女人身上或是几件可有可无的物事上。可我就是喜欢闲逛。
我在一家不大不小的公司上班,曾经给几位不大不小的部门经理开过车,两年后我换了岗位,不必再驾车四处奔波了。我买了一辆电动摩托车,每天打卡上班,过着两点一线的单调生活。年初体检时,我发现自己的脂肪肝超标了,卵磷脂小体也在逐步减少,诸如此类的小毛病一点点出来了,医生说,这都是久坐的缘故。于是我弃车徒步,每天沿着河堤走半个多小时的路到公司,虽然多绕了点路,但也值得,这样既有助于锻炼身体,又可以调整生活状态(有时候我还可以在散步途中发现一些鲜为人知的乐趣)。我的生活节奏就这样慢下来了。
这阵子,我常常看到一个老人划着一艘小船(当地人称之为河鳗溜)往返于河面。他不钓鱼,不摆渡,也不做航运赚水脚钱,就是在河里划过来划过去。我一度以为他是这里的河长,后来发现不是。这年头,河面舟楫早已零落,我所能见到的船也大都是马达轰鸣的机动船,手划船是极为罕见的。因此,当它出现在铺散着大片阳光的河面,不免显得有几分突兀。有时一只白鹭飞下,落在船头,跟他对视着,没有一点惊惧的样子。船在动,那是一种静止的移动。我没有比它走得快一些,也没有更慢一些。只不过,我是用双腿散步,船是用双桨散步。那一刻,我感觉自己的双腿跟船桨之间似乎真的有了某种呼应。
阳光温暖如手,漫不经心地抚摸着流水和两岸的石头。我的目光被那艘小木船牵引着,有了一种连自己也说不清楚的寂寞之感。不多久,小木船竟缓缓向我这边偏斜过来。水鸟腾地一下从船头飞起,一带远山在云下浮动着。听得竹篙触石的声音,我便下了一级踏埠,用探询的口吻问道,老人家,能借你的船坐一程?
你要坐我的船去哪里?
我犹豫了一下,听到自己漫不经心地答道,去南边。我所说的“南边”是在小镇的另一边,我回答那句话的时候,正好有一阵南风朝我吹过来。
我上了船,左右摇晃了一下,迅即稳住。船上光洁无垢,中舱铺着一张龙须草席,因此我便脱了鞋子,放在一块垫布上,那里还摆有一双布鞋,沾染了泥迹和苔藓的颜色。我把一张钞票递给老人,他却把票子对折一下,放回我口袋。老人说,我是闲来无事,划船玩玩的,你也不必付钱的。这不,我也碰到过像你这样的年轻人,觉着好奇,就过来坐我的船。我想到哪里,他们就跟着我到哪里。他们坐车是有目的地的,坐船就不同了,可以随我东飘西荡的,说话也一样,天南地北,胡说一通。随即,老人弯下腰来,打开船上一个樟木箱的盖子,掏出一包蚕豆和一瓶酒,问我,自家烧的米酒,能喝上一点?我说,我已经戒酒了。他又从樟木箱里掏出保温瓶和茶叶罐子说,如果你没什么要紧事,就坐我的慢船,陪我聊聊天,喝喝茶吧。他给我倒了一杯茶,然后回到船尾,一边划船,一边跟我闲聊,好像我们已经认识好多年了。这大概就像人们所说的,初见有如重逢吧。
老人说,前阵子他常常看见我在岸边低头赶路,这阵子却不晓得我为何散起步来了。我告诉他,我原来上班都是从这边路过,现在对手头这份工作已经腻烦,不想上班了。老人听了也没深问,只是说今天天气如何如何好,那些闷在屋子里的人不出来走走是很可惜的。我跟老人尚不熟悉,当然没有必要告诉他我想辞职的原因。事实上,我也谈不上有什么苦衷,只是不想老呆一个小地方。生活越来越单调乏味,跑出去的愿望也就日甚一日。至于去哪儿,我还没打定主意。
沉默有顷,老人突然像想起什么似的,跟我作了自我介绍:我叫长生,是这个镇上土生土长的,土得不能再土了,不会坐车,至今还没出过远门呢。
不知道为何,我与长生聊天时,语速也慢了下来。我想我的语速已接近于流水的速度、船行驶的速度。从河中央看两岸风景,跟站在岸的这一边看那一边,毕竟是不一样的。那一刻,水在流动,船在流动,目光在流动,思绪也在流动。在流动中忘掉了水程的远近。船过十间桥,长生指着岸上的一排高楼说,这镇上五百年以上的物什还剩三样,你可晓得?我摇摇头说,我从来没听长辈说过。长生说,这三样物什现在可以看到两样,喏,就是那座桥边的大榕树和树下的一块石刻照屏。还有一样?我问。长生指着岸边的服装贸易市场说,从那里过去,有一座胡宅大屋,正屋头门台外有一个道坦,现在已经变成市民活动中心,那里有一棵大榕树,树下有一口五百年古井,那口古井原本是地主伯胡醒石祖上留下的。胡醒石是谁?没等我发问,他已经说开了。提起老古早的事,他的目光就跟流水间的落叶似的,一下子就漂远了。
长生的父亲是一个残疾人,双脚不能走路,就以桨代脚,在水上做起家来。那艘船是一种叫作“河鳗溜”的内河货客船改造而成的,炊膳设在后舱,父子俩平常就睡中舱,中舱立棚,可以推拉。家是不系之舟,但他们飘来荡去,不出塘河一带。塘河以北是一条横亘着的大江,江水无常,他们不敢过江去讨饭吃;内陆河不免恶风浪,却是可以测知、躲避的,父子俩托命于水,倒也无妄无灾。长生的父亲每经过一座村庄,就开始敲梆;见岸边有人拿东西出来,便伸出一根挂着布袋的竹竿。施舍的东西要么是一捧米,要么是一些剩菜冷饭。长生的父亲收回布袋之后,都要双膝跪地,唱几句利市歌。有时候,长生的父亲还会向岸上的人家要一点米糠或麸皮,往后看见鸭子游近了,就给它们撒一把。塘河一带的人大都认得长生父子,说起来,也常常会为他们的身世感叹几句。尽管如此,岸上的人也没有进过敲梆船,而船上的人也没有上得岸来。唯一坐过敲梆船的人,大概只有地主伯胡醒石了。
那年夏天的午后,胡老爷穿一件无袖的绸衫,摇着一柄带坠子的折扇,慢悠悠地走过来,猫着腰钻进船篷,坐定,抛下一枚银元,说,走。长生的父亲问,去哪里?胡老爷说,风从哪个方向吹过来,你就往哪边走。长生的父亲明白,胡老爷要他划“倒风船”。长生的父亲划动木桨时,胡老爷便迎风坐着。未几,胡老爷从布袋里掏出一包蒜香豌豆、半壶黄酒,一壶茶,摆在桌子上。胡老爷从摊开压平的纸蓬包里撮了几颗花生米,递给长生。长生瞥了一眼父亲,见父亲摇摇头,他也跟着摇摇头。胡老爷问,你多大了?长生说,九岁。又问,没上过学堂吧?长生点了点头。船划到柳荫间,一阵河风吹来,胡老爷连连赞叹:好风,好风。长生笑了一下,赶紧捂住嘴。长生一直在船上住着,从来不觉着风有多好。胡老爷饮下一浅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颇有些借风下酒的意思,喝得兴起时,便拈着胡子,嘴里念念有词。长生不明白他在念什么,但觉着好听。本城的人都知道,胡老爷早年在日本留过学,回国后跟几位乡绅合办了一座学堂,还捐了一百亩地做学田。胡老爷常做一些怜贫恤孤的善事,跟下等人也没摆过什么架子。那年头,富人家坐花船“荡湖”是常有的事,但胡老爷偏偏喜欢坐长生父亲的敲梆船,也不拘远近,在河上度过一个美好的下午,就照例抛下一枚银元。
斗地主、分田地那年,胡老爷首当其冲,人被抓去,书被烧掉,书房前的两株白玉兰和金桂被伐倒做了柴禾。胡老爷在批斗会上虽然把所有的罪行都归到自己名下,但四个儿子还是脱不掉干系,幸得镇上贤人二三替胡家说了几句公道话,他们才免于陪斗。镇上的人把胡老爷批斗了一阵子后,实在玩不出花样了,就拉到野外枪毙。长生说,胡老爷是他这一辈子见过的最有风度的一位大先生。临刑那天,他跟父亲一起划着船去西郊外的河滩边观看。胡老爷被人押送着缓步过来,他穿一身羽纱长衫,把头梳理得一丝不乱,一副要出远门的样子。行刑的时候,胡老爷向行刑者和那些踮着脚看热闹的人鞠了一躬,然后转身,向天地鞠了一躬。一声枪响,几只野鸭子便扑棱棱飞了起来。胡老爷死后,没人给他收尸,让寒雨浇淋。长生的父亲说,胡老爷是个好人,但好人没好报。长生的父亲把船划到河心时,又掉过头来。长生说,他父亲这辈子从没上过岸,但为了胡老爷,他破了一次例。长生的父亲在岸边挖了一个坑,把胡老爷草草掩埋了。
长生说,他爹替胡老爷殓尸,从来没有告诉任何人,但胡老爷的后人终究还是知道了。
胡老爷有四个儿子。长子伯远曾留学日本,学的是造船技术,回国后曾在上海一家造船厂当技师。土改后,胡伯远受牵连,到乡下放鸭;之后又进了一家乡镇造船厂当技师。他会拉大提琴,也会拉大锯。但长生从来没听他拉过什么大提琴,只是听他说过:会拉大提琴的人,拉起大锯来,声音要比别人悠扬。
胡老爷的次子仲远是个好玩之人,平素喜欢种花、养狗、熬鹰、遛鸟,土改后莫名其妙地做起了兽医,之后又因为莫名其妙地治好了镇长老爹的疑难杂症,就变成了可以挂牌接诊的名医。
胡老爷的三子叔远是个乏善可陈的败家子(富人家通常都会出这类败家子),早年混迹市井染上了赌瘾,一发不可收。赢了钱,他便穿上破衣裳,为什么?怕人家借钱;输了钱,他便穿上早年的一身西装,又为什么?好去借钱。
胡老爷的喜子(本地话里“四”与“死”谐音,“四”字也就念成“喜”了)胡季远是个名气不薄的书画家,自号柿叶山房主人,在山里买了一块地,可居可游,屋后种了几株柿树,柿子熟了,分赠邻里或朋友,自己不怎么爱吃,但玩经霜的柿叶。怎么个玩法?就是在残叶上写写画画,然后随风抛撒到山谷里去。后来也不知为何,他竟连画笔也扔掉了,甘愿去做油漆匠。
这四人,后来跟长生都结下了不解之缘。
长生在十二岁之前一直跟随父亲,过着浮家泛宅的生活。十二岁那年,父亲突然病倒了。长生把船划到十二间桥,朝桥堍喊了几声“胡医师”。一个白脸长身的人就从一家药铺走出来。胡医师就是胡老爷的二公子仲远。
胡医师带来了一个大柑,递给长生的父亲说,吃一个吧,是“重五柑”,润润喉。长生的父亲说自己什么都吃不下,也不想吃。他把大柑递到长生手中说,“重五柑”胜羚羊呢,你到一边吃去吧。长生收下了柑,舍不得吃,捧在手里,被阳光照着,呈金黄色,仿佛带有一丝暖意。胡医师给长生的父亲检查身体时,脸色有些凝重。他写了一张纸条,嘱长生去卫生院取一种药物。
长生回来后,胡医师没跟他说起父亲的病情,却问道,长生,往后你想学门谋生的手艺?没等长生回答,他又接着说,我哥哥进了一家造船厂,手下正缺人,你如果愿意,我可以介绍你做他学徒,好歹也可以混碗饭吃,总比现在跟着你父亲过乞讨的日子强吧。
长生看了看胡医师,又看了看父亲。父亲点了点头。
胡医师说,长生你收拾一下行李,现在我就带你去造船厂。
长生说,阿爹病倒了,没人照顾,我怎么可以在这个时候出走呢?
胡医师说,没事的,你爹这几天就把船泊在这里的小河湾,我有空过来照顾一下他。
长生的父亲也接过话说,我只是得了风寒,将息几天就好了,不碍事的。
长生上岸时,双脚竟有些发飘。胡医师笑着说,长生,你的双腿直不起来么?长生敲了敲自己的膝盖,腿就直了些,可他一走动,腿就松垮了,双膝向外,形成了罗圈腿,这样一高一低地走着,足底便像是装了弹簧。他明白,长生的双腿原本可以伸直的,但因为长时间曲膝坐在船上,双腿就走样了。长生穿过一条布满凹痕的青石板路时,有几个小孩子跟在他后面,模仿他外八字脚走路的样子。胡医师回过头来,张开双手,像赶鸭子似的驱散了这群孩子。
到了造船厂,长生见到一个面目与胡医师酷似的人,他就是胡医师的长兄胡伯远,人称胡大先生。胡大先生听完胡医师的介绍,轻轻地“哦”了一声,摘下鼻梁上的玳瑁眼镜,把长生上下打量了一番。
胡医师走后,胡大先生把他带到作坊,劈头就问,造船很苦,你吃得了苦?
我不怕苦,长生说,我有的是一身力气。
胡大先生说,你说自己力气大,好吧,你可以去挑粪壅田了。
这么一说,长生就懵住了。
胡大先生说,造一艘船,固然是体力活,但也要用脑子。胡大先生这样说着,便用手在长生的脑袋上轻轻地拍了一下。
我可以收你做学徒,但有个规矩,得先给你说清楚了。
什么规矩?
你得给我准备好两样礼物。
胡师傅,你也晓得,我们家实在是没什么值钱的物什拿得出手。
虽然你两手空空,但你身上兴许有的。
长生把口袋朝外翻过来说,如果有,我一定会双手奉上的。
我说的两样礼物是摸不着的。
那是什么?
是谦卑和勤快。
师傅说的是这个呀,我有的,我有的。
胡大先生没有再说什么,当晚就让长生留下来,还给他添置了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品。
长生在造船厂做学徒,每月食宿免费,逢年过节还能拿一点酬劳。若逢初二、十六,造船厂的老大照例要请大家吃一顿红烧肉。长生长这么大还没吃过红烧肉,先咬一小口,便有油汁从舌间溢出,满嘴生香;他把嘴角舔干净后,才下第二口、第三口……胡大先生说,他近来患了胆囊炎,不吃油腻,因此就把自己那块红烧肉搛到长生碗里,但长生只是闻着肉香,舍不得吃。匆匆扒完了一大碗饭,他就偷偷用油纸包好红烧肉,打算带回船给父亲享用。
没承想,他刚踏上船板,船舱里面就响起了剧烈的咳嗽声,然后他就听到父亲声嘶力竭地喊着,不要靠近,不要靠近。长生跪在外面,一动不动。这时候,河面陡生凉风,船上的炉灶扬起一小束黄尘,布幔抖动了一下,父亲伸出一只枯枝般的手臂说,他的病已经没有好转的迹象,现在什么东西都吃不下了,只求一死。但他也有一个愿望,死后如果没有棺材殓尸,就把这艘破船当作他的棺材,放到海里去,让风浪吞没。
长生旋即登岸,三拐两拐找到了胡医师。从胡医师口中得知,他父亲得的是肺结核,会传染的。胡医师和父亲事先商量好了,让长生去学手艺,就是为了免于传染。父亲的病情传开后,周边那些公婆船上的船户就恶声恶气地驱逐他离开,大概也是怕被传染。
不到一周,父亲就断气了。长生依照他的遗愿,把他的尸体跟那艘小木船捆绑在一起,送出风急浪高的海口,然后就坐上了胡大先生的舢板船。转眼间,他就看见父亲的小木船一点点小下去,直至被一个浪头抹平。
站在一边的胡大先生双手合什,拜了三拜,接着又抬头望天,长叹一声道,其生也若浮,其死也若休,这样的归宿也未尝不好。
长生不懂这话的意思,但似乎又明白了点什么。
在长生眼里,胡大先生跟胡老爷一样,也是个有学问、有情味的人。
有一天,胡大先生要坐船去龙泉看树。同行者有造船厂的几个老师傅和学徒,长生也在其中。龙泉在西北方向,地势偏高,若是沿瓯江走,就得赶早潮时分,顺流而上。他们坐的是一种瓯江上常见的舴艋舟,船艏与船艉呈月牙形,人坐在船篷里面,也不感觉江流湍急。胡大先生坐在船尾,跟大伙讲述自己当年坐瓯江交通船去龙泉做洋布生意的经历。到了温溪,正是中午时分。大伙肚子饿了,开始升火烧饭。船锚定之后,胡大先生从溪流里捕了几条鱼,从岸边摘了一些野菜,就在船上的江灶舱上做起了菜。饭饱,继续行船。
一路上山环水绕,每每遇见怡人景色,胡大先生就让船工停棹,饱览一番。一位老师傅说,我们这哪儿是去看树?分明是游山玩水嘛。另一个师傅也说,一堆石头,一滩子水,有什么看头的?胡大先生说,走山路不看水,走水路不看山,怎么说得过去?你们看树不看山水,又怎么能了解木头的妙用?胡大先生说起话来,总是藏着什么叫人半懂不懂的深意。途中有市墟,也要停船,大伙上岸闲逛一圈。因为身上没带几个钱,他们也只是走马观花而已。胡大先生不然,他看什么东西似乎都能看出门道来。他从市头走到市梢,心静步缓,仿佛游山。同行者都没心思陪他逛街,跑到一座祠堂后面看草台班戏子去了。唯独长生背着一个布袋,同书童似的跟在胡大先生身后。东转西转,胡大先生转到了附近的林场,见到了一位跟他合伙做过洋布生意的老友。聊到太阳西斜时分,主人置酒留饭,胡大先生却借口有事,匆匆走掉了。经过半山腰的一户村庄,只见家家户户都种着瓜果。胡大先生没有伸手去摘树上的果子,但看到地上的果子会弯腰去捡,用手擦拭一下,放进长生背后的布袋里。这一路过来,胡大先生还认得许多野菜,叫得出名目。看到没有篱笆环护的野菜,他便弯下腰来摘了几株,还跟长生讲解如何用油盐调食。他们到了船上,太阳正好落山了。那一顿晚餐有菜有鱼有瓜果,二荤三素,居然不费一毛钱。
大伙把肚角撑饱,牙缝塞满,就散坐在滩头聊女人。长生年纪最小,锅碗瓢盆就归他清洗。胡大先生回到船上,从布袋里掏出一根烟杆,拍拍船舷,一边装上烟叶,一边带着惋惜的口吻说,今天我瞄中了几块上等的龙泉杉,只可惜手头没钱。这样说着,他又点燃烟,望着不远处寂寥的灯火说,我有钱的话,就买两立方的龙泉杉,造一只舴艋舟,空闲的时候就划着船去没有人的地方吹吹风。
长生听了,心里默想,自己往后若是有了一艘船,也会跟胡大先生一样的。
船划到龙泉境内,他们就沿着深僻的山路,走进了一片杂木林,胡大先生又向大伙讲解每一种树的特征与用途。有时候,胡大先生还讲几个有趣的地方掌故。这一路上,胡大先生每经过一处树林都要驻足片刻。看到桐树结籽,他就让大家采集一些散落地上的桐籽。桐籽做什么?捣成桐油。看到几根桷木,他也随手捡来,说这桷木做刮板最合适不过了。经过一户编织草席的人家,胡大先生又停了下来,向主人讨要了一麻袋草席的下脚料。
龙泉之行,大伙都说玩得很尽兴。归途中,长生在心里合计了一下,这一趟坐水路去龙泉看树,除了租船费用,其他吃住的费用一概省掉了。带回来的桷木、桐籽、草席的下脚料,也都是不花一分钱的。胡大先生对什么事看似不着意,实则处处留心。
闲时,胡大先生近乎散漫地做起两件事来。
一是搜集一些别人弃而不用的木头。这些木头解好之后,就放自家瓦背,教风吹日晒,这叫“漂木板”。夏季台风过后,暴雨连旬,他看见有一块木板从上流冲下来,就用长竹篙捋了过来,一看,水杉棺材板,木质极其好,舍不得丢,就用锯子解了,放在瓦背,也不讲究什么忌讳。有一回,长生在胡大先生家蹭饭,无意间看到了从龙泉带回来的几根桷木做成的刮板,它们像腊肉似的挂在镬灶间里离灶孔最近的地方,作甚?就是让烟火熏。好的刮板,要熏个两年左右。胡大先生手上用的刮板都是熏过两年后呈暗黑色的。
除此之外,有空的时候胡大先生就带长生等四名学徒去罱河泥。胡大先生打桨,四人持竹竿挖河泥。装了半船河泥,胡先生就歇手,从不多取。河泥一时间也没有派上什么用场,就倒进造船厂边上的一个河泥坑里。长生对胡大先生说,这些河泥要是卖给柑农,还可以换来几升米呢。胡大先生摇摇头说,不卖。那么,长生问,你让我罱河泥究竟有什么用意?胡大先生说,我想让你们每人都感受一下自己造的河泥船是不是受用。
隔了一阵子,长生才明白,胡大先生罱河泥是另有一番用意的。
胡大先生造的木船,要比寻常人讲究一点,不但讲究造型,还讲究外观装饰——除了船帮两侧髹漆,在船艉还要画上一组戏曲人物什么的。造船厂没有人会干这活儿,请的是外面的师傅,也就是胡大先生的三弟胡季远。如前所述,他原本是个画家,经过一番思想改造,竟当起了油漆匠。不过,一般的油漆匠在当地只能称为“油匠老司”,而胡季远与别人不一样,他除了油漆,会画各种物事,人们称他油匠先生。塘河一带,职业后面凡是带“先生”二字的,都格外受人敬重,比如:道士先生、唱词先生、教书先生等等。胡季远给造船厂画画,不收一分钱。每回画毕,胡大先生都会送他一船河泥(胡季远家有一片柑园,八九月间藏好的河泥晒干了,肥性好,可以赶在冬季撒到柑园里更新旧土)。河泥的用处就在这里了。油匠先生胡季远得了空闲,就来造船厂画船艉,而长生总是蹲在一旁默默看着。胡季远问,要学这门手艺么?长生点了点头。胡季远说,那好,以后给我斟酒的活儿就交给你了。胡季远这人饭前没有酒润润舌头,就连提画笔的力气都没有了;有了酒呢,容易贪杯,而且多饮必醉,醉了同样是连画笔都提不起来,通常是躺在船舱里呼呼大睡,仿佛去了一回醉乡。长生见过此状,以后就学聪明了,给胡季远打来的黄酒仅半壶,不够,再打半壶。胡季远喝了一斤黄酒,止于微醺,这时节画画的兴头最高,教长生画画也最用心。长生学了一年多,居然也能画上几笔了。胡季远看了,有时点头,有时则摇头。点头,是夸他有了长进;摇头,是说他没念过书,再怎么用功,将来充其量也只是个画匠。长生也自觉在画画方面天分不高,以后也就老老实实造他的船了。
头几年,胡大先生造好船之后,长生都要上来坐一下;而后几年,长生造好了船之后,胡大先生也都上来坐一下。胡大先生说,树离开土就死了,变成木头,可木头变成船,遇上了水,又会活过来。你造的木船好不好,就看它放在水里活不活。
有一天清早,新船上水,胡大先生抱膝坐在船头,望着清寂的河面,突然跟长生重提旧事。胡大先生说,很早很早以前,我还住在一座临河的大宅院里,一大早听到敲梆声,心头就有一种异样的被清水洗过的感觉。我晓得是敲梆船出来讨饭吃了,其中想必也有你父亲的船,可我从来没有施舍过一碗饭,也没拿正眼瞧过。直到有一天,家父提起了你父亲——
长生点点头说,胡老爷坐过我们的船,我这一辈子都记得。
胡大先生问,你可晓得我爹为什么愿意坐你爹的船?
长生不语,胡大先生便接着说,因为你爹的船跟别的船不一样,它虽然陈旧,但船板干干净净的,用我爹当年的话来说,就像切豆腐的那块板。
长生说,我爹说过,人可以很穷,但不能因为穷就把自己弄得脏兮兮的。
胡大先生说,你爹的心地也是干净的啊。
那时候,长生觉得,胡大先生也是干净的,天空与河流也都是干净的。
然而,“文革”来了,人心也变得不干不净了。因为外边每天闹革命,造船厂被迫停产。油匠先生胡季远自此以后没再来造船厂,再后来听说出了事——据说是有一回,他读完一部佛经,忽来兴致,按照从右至左的书写习惯写了“放下”二字,贴在墙上,结果被人误读成“下放”。革委会的人说,既然他要“下放”,就把他下放到黑龙江绥芬河那边的农场去。从此杳无音讯。胡大先生也大感不妙,对妻子说,这阵子风声吃紧,我得外出避一避。其时正是九月,庭院里开满了菊花。妻子问,要多久?胡大先生说,看形势,少说也得一年。妻子指着菊花说,明年菊花再盛开的时候你要记着回来看看我们。胡大先生点点头说,好。次年秋,菊花开了,又败了,胡大先生仍未见回来。再过一年,油菜花开了,正在收油菜花籽的长生看到胡大先生回来了,那时候才晓得,胡大先生已经疯掉了。
胡大先生晚年就住在自己造的一艘舴艋舟上。船泊在离村子有点远的小岛附近,那里潴水颇宽,没有人烟。他到底靠什么生活,没有人知道。长生驾着小船去找他时,他不想见。后来一听到什么打桨的声音,他的木桨便同鸟翅似的,张开来,向清冷的地方划去。有一天,人们发现这艘船连同胡大先生突然消失了。村上的人说,胡大先生造的船变成了宇宙飞船,飞到外星球去了。
“文革”结束后,镇上的造船厂开始恢复生产,但收到的订单以铁壳河轮与农用水泥船居多。但凡有木船生意,就由长生接过来做。此后十几年来,长生造木船的数量越来越少。无论怎么说,有船可做,手艺也就不会荒疏掉。长生的儿子转眼间也长大了,进了造船厂,不过,年轻人毕竟脑子活泛,也舍得出力气,什么种类的船生意好他就跟师傅学什么。
有一天,长生正在侍弄菜园时,儿子跑过来说,家里来了一位上海老板。长生有些疑怪,赶紧拾掇农具,回到家里,一看才知道这位“上海老板”不是别人,正是胡老爷的三公子、胡大先生的三弟胡叔远。见他西装革履、一身光鲜,长生就估摸着这老赌棍准是又输了钱,如果他开口借钱,长生就不知道怎么应对了。胡季远跟长生绕圈子说了一大通怀念故旧的客套话之后,就把此行的意图挑明了:这些年,他跟几个上海人合伙在浦东办起了一座造船厂,目下正在搜罗各种人才,他早前听长兄介绍过长生,因此就慕名而来,聘请他担任技师。长生问,你造的是什么船?胡季远说,什么船都造,木船、水泥船、铁壳船,十吨的、五十吨的、上百吨的,只要有订单,我们都造。长生说,我年纪也不小了,人又老拙,不想再跑出去折腾了。胡季远说,我知道你心里想说什么,现在的胡季远已经不是从前的浪荡子了。这样说着,他举起一根残缺的食指说,多年前,我戒了赌,断指明志。长生“啊”了一声,久久没说话。胡季远瞥了一眼门外道坦上反扣着的一艘木船说,刚才我见你儿子给船缝填灰时手脚麻利得很,如果你们愿意,就跟我一道去上海闯荡一番吧。长生沉默有顷说,这阵子造船厂生意清淡了,我儿子就老老实实呆在家里,随我学做木船了。不过,我知道这小子野心大得很,一心要干大事,不如随你去外边打拼一番吧。
长生不晓得自己为什么会那么爽快地答应胡叔远的的要求。待胡叔远走上村口一条大马路,长生依旧驻足树下遥遥目送,那一刻,他越发觉得这胡叔远的背影跟胡大先生极像。当晚,他还梦见了胡大先生,穿宽衣大袖,着布鞋,月亮走,他也走……
儿子走出去了,长生明白,年轻人注定是属于外面那个世界的。儿子在信中告诉长生,他在上海见识了大船之后,才知道家乡的“河鳗溜”有多小。短短几年间,儿子就从一名普通技工变成了部门经理;再过十多年,他就接替胡叔远的位置,做起了造船厂的老板。儿子是越来越有出息了,但父子俩见面晤谈的时间却越来越少了。二十年后,儿子的造船厂变成了一家大型集团公司,长生跟他一年间也难得见上一两次面。
长生问儿子,人忙一辈子为的是什么?
儿子说,为的是有一天去美国的夏威夷买一栋大房子,每天可以躺在海滩边晒晒太阳。
长生又问,夏威夷的阳光跟这里的阳光有什么区别?
儿子说,太阳只有一个,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夏威夷的阳光。
果然,儿子不仅在京广沪买了别墅,还在夏威夷买了房子。有一回,儿子订好了机票,准备接他去夏威夷住上一阵子(那里的房子空着也是空着)。长生说,不去,不去。
终究是没有成行。
长生是个闲不住的人,晚年虽然家境富足,但他每天不做点什么心里头就不踏实。除了在老家后院里种点菜,他还在三里外的一亩小岛屿上辟了一座柑园,雇人一起打理。长生说,小时候,胡医师曾馈赠他一个“重五柑”,他一直视若恩物。现如今,他每年都要提一篮柑去看望瘫痪在床的胡医师。
依旧划船,去柑园,或是访友。他这辈子什么地方也没去,就是喜欢在这条河流上划过来划过去。人与船,分享着流水的寂寞。
阳光照在长生身上,也照在我身上。那时我居然觉得,一个人呆在一个熟悉的地方晒晒太阳也是一件挺好的事。偶尔也能看见有人摇船过来,但都是水泥船。我问长生,你造过水泥船?长生说,我这辈子造过各种各样的木船,却没造过水泥船。水泥这东西造船,尽管经久耐用,看上去却很粗陋。长生停顿片刻,把桨打出一个漂亮的水花说,木船跟鱼一样,只有放在水里才是活的。
这条长河是南北走向,船穿过小镇,屋舍渐疏,间杂几座廊亭庙宇。越往南走,水域越发宽阔,星罗棋布的小岛上是一片又一片绿桔黄柑。长生说,这片土地如果不种柑桔的话,也许有一天会生出钢筋和水泥。
再往南走,就是另一座县城了。这一路过来,共有二十多座桥,不过,现在已经没有几座像样的石桥了,多的是混凝土桥。长生说,那边过去半里许,有好几条巷子都是以桥命名的,这是因为它的前身都是水巷,后来河流变成马路,桥也就废了,只留个桥名作巷名了。
长生没有再荡桨前行,而是把船划进了一条小河湾,那里有一座榕荫覆蔽的小岛。喏,这就是我家的柑园了,长生指着前方说,这些老树结出的柑特别甜,再过两个月就可以把船划过来摘柑了。长生这样说着就坐下来,点燃一支烟,默默地吸着。吸完了之后,他又开始划船,两把石林木做的木桨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
我平躺下来,隔着船板,能听到汩汩水声,仿佛在诉说着这条长河的身世。太阳慢慢西斜,船在阳光和阴影间缓缓穿行,我消受着整个下午的散漫。忽然想起,前阵子有位叫八爪的网友曾约我坐船去前头那座小镇的杨府庙看地方戏,吃地道的鱼丸面,我应承下来了,却一直抽不出时间。这些日得了空,却找不着八爪了。如果这回坐船过去,戏是看不到了,或许还能在杨府庙旁的老字号店里热热地吃上一碗鱼丸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