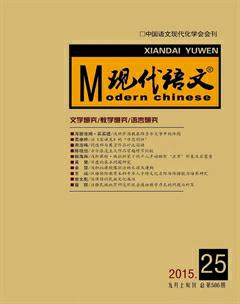描述与探寻
摘 要:巴金的《第四病室》和契诃夫的《第六病室》都是以“病室生活”反映黑暗现实的作品,它们分别揭露了在国民党及沙俄的罪恶统治下,广大人民于夹缝中艰难生存的悲惨境地。但对比而言,前者更倾向于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全景式描述,后者则更侧重于对其精神状态的思考和探寻。本文将分别从影响中的差异、文本体现、原因分析这三个方面,探讨两个文本在主题倾向上的差异。
关键词:差异 现代主义 对比 作家风格 民族性格
一、影响中的差异
巴金早年的作品具有强烈的主观性、抒情性,感情奔流激越,多热情奔放的抒情咏叹,诗意化色彩浓烈。而在40年代中期,巴金迎来了创作的又一高峰期,在这一时期,他的创作风格却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他开始写没有英雄色彩的小人小事,写社会重压下人们司空见惯的‘委顿生命,写‘血和痰,调子也变得悲哀,忧郁。”[1]从《还魂草》开始,到《火》三部曲《憩园》《第四病室》《寒夜》,巴金早期对旧社会充满激进色彩的控诉和抨击渐渐转向了对深刻冷静的对人生世相的揭示。这不仅有抗战初期激奋乐观的民族心理沉静后,作家随着时代心理变化而发生的风格变化,也是巴金本人在40年代对契诃夫的热爱和借鉴所致。其中《第四病室》可谓是受其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奥尔德里奇曾把“影响”界定为“一个作者作品中的某种东西,假若他没有读过前一位作者的作品,这种东西就不可能存在。”[2]我认为这种定义用在巴金对契诃夫风格的接受上,是极为准确的。
自福柯《规训与惩罚》中提出“社会是大病房”的观点以来,“社会——病房”成为很多哲学家、文学家的思想共识。契诃夫在1890年前往库页岛进行长达3个月的考察后,写下了极具象征性的《第六病室》。而巴金写于抗战胜利前的《第四病室》可谓与《第六病室》直接呼应,都是对借病房生活的描写揭示本国人民在黑暗现实下的悲惨境遇,两部小说从书名、情节开展的主题方面都极其相似。但相似的同时,《第四病室》和《第六病室》在很多方面都有着明显的不同点,就主题而言,虽都为借“病室”批判社会,但两位作家的切入点和倾向性也存在不小的差异。
《第四病室》可以说是一部详细的“病房照”。通过病人陆怀民日记中细致入微的描述,我们几乎可以清清楚楚地知道病房内的方方面面:住院环境的恶劣、病人的形象与性格、医护人员的行事风格以及病房内痛苦、挣扎与死亡的再现体验。可以这么说,巴金在《第四病室》里更侧重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全景式叙述,而这种叙述又主要集中在其肉体与情感所受的苦痛和折磨上。
相比较而言,《第六病室》则更像是医生和精神病人一对一对话时的“剪影”。和契诃夫的其他许多作品一样,小说中没有众多的人物和复杂紧张的情节,它以医生安德烈和精神病人伊凡的争论和人生走向为主要情节,展现了一个荒谬、无聊的病态社会对人灵魂的污染和扭曲。在其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契诃夫对人类精神状态的探索和其人生态度的转变。
综上,笔者将两文主题上的差异概括为对生存状态的描述和对精神状态的探寻。下面我们将从文本出发,探讨这种差异性在文本中的具体体现。
二、文本体现: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碰撞
总的来说,文本中艺术形式的选择体现着两位作家各自写作风格的转变,这种转变不仅体现在文本的艺术形式上,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主题倾向性的产生。从这个层面来说,两文中的艺术形式和主题倾向可谓互为因果。
巴金的创作由早期浓烈的主观性、抒情性转向后期冷静忧郁的叙述,所以《第四病室》虽以病人的日记作为切入点,采用第一人称限制性叙事,但在艺术风格上仍归于现实主义。而《第六病室》则不同,契诃夫在许多文学评论家心目中是绝对正统的现实主义作家,“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是他著名的现实主义宣言,但我们发现,在契诃夫的许多作品中也依稀体现了现代主义、象征主义的某些观念和形态的萌芽。《第六病室》在我看来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现实主义的手法使得巴金在创作《第四病室》时更倾向于全景式的叙述和揭露,而现代主义的影响却使得契诃夫更加注重对世界的荒谬性、人的孤独、虚无与异化的探寻。在文本中,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情节、人物:全景式叙述与印象性捕捉
《第四病室》的主体是病人陆怀民在住院期间的十篇日记。日记中记载着他从住院到手术、出院的一系列见闻,基本上坚持着传统小说以情节为中心的故事设计与安排。而在《第六病室》中,虽是第三人称叙事,但作者行文时却着意弱化文本对人物、情节、环境的客观描写,而更侧重于对其进行“印象性”的捕捉。
这是前者主人公第一次踏入“第四病室”时对病房内部环境的描述:
床头靠着墙,左面挨近第六号病床,右边靠近第四号,不过中间各有一条过道,各隔着一个小小的方木柜,那是靠着床头白粉墙安放的。左边柜上放着两个吐痰的被子和两把茶壶,显然是给我们两个人分用的,第六床的柜子被铁架占去了。方柜下面有门,里面分两格,全空着,可以存放我带来的衣物。床下有一个方凳,凳上放着一把起了一点儿锈的便壶。
在这段描述中我们看到,全段没有出现任何一个有关主人公感情或印象的形容词汇,这都是客观到不能再客观的叙述,不带一丝感情色彩。而我们再看看《第六病室》中有关病室外部环境的段落:
医院的院子里有一所小屋,四周生着密密麻麻的牛蒡、荨麻和野生的大麻。这所小屋的房顶生了锈,烟囱半歪半斜,门前的台阶已经朽坏,长满杂草,墙上的灰泥只留下些斑驳的残迹。小屋的正面对着医院,背面朝着田野,中间由一道安着钉子的灰色院墙隔开。那些尖端朝上的钉子、院墙、小屋本身都带着阴郁的、罪孽深重的特殊模样,那是只有我们的医院和监狱的房屋才会有的。
这种“客观”与“印象”的差别作用到读者的阅读感受上,便使得在读者的脑海中,前者倾向于一幅素描的病室结构图,而后者更像一幅灰色的、阴郁的印象画。契诃夫在必不可少的环境描述的基础上,以“牛蒡、荨麻、大麻”这些充满象征性的对象和“锈、朽坏、杂草、灰泥、斑驳”等印象性叙述让我们感受到了一阵阴冷的寒意和一片压抑的氛围,最后更是以“抑郁、罪孽深重”两词直接对病室周边的氛围定了调子。这种阴冷的感觉贯穿整个文本,它不仅是在描写病房环境的阴郁,也是也描摹当时社会中人心灵的孤独、迷失与扭曲。
而在人物形象与性格的刻画方面,两个文本也呈现出同样的差异。在《第四病室》中,所有的人物形象几乎都是靠对话、动作来展开的,如第二床老人的任性荒唐、第六床的正义感与爱抱怨、第八九床的缺乏同情心等等,他们都是相对全面却浅层的描写。而《第六病室》对除了安德烈和伊凡之外的人物,都是运用简短直接、却具有象征性的手法进行勾勒。其中最触目惊心的就是伊凡右边的“邻居”:
满身肥肉,胖得几乎滚圆,面容呆板,毫无表情。他是个不动的、贪吃的、不爱干净的动物,早已丧失思想和感觉的能力,他那儿经常冒出一股令人窒息的、刺鼻的臭气……可怕的倒是这个没有知觉的动物挨了打却毫无反应,既不发出任何声音,也不做出任何动作,连眼睛也毫无表情,而只是身子稍微摇晃几下,好像一个沉重的大圆桶。
这个农民的形象是有着强烈的象征意味的。他代表着在契诃夫观念中最底层、同时也是最无可救药的精神状态,他不仅身体不动,连精神、感知上都极端停滞、迟钝。在后来安德烈与伊凡的争论中,伊凡反驳安德烈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认为如同安德烈那样生活,最后就只能弄成这个农民的样子。
从以上两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巴金侧重于在情节的有序展开中进行客观全面的叙述和描摹,而契诃夫则着意于捕捉最具有象征意味的客体、细节,对其进行印象性描绘,他的兴趣不在于客体与事件本身,而在于它们呈现在观察者想象中的状态,强调主体的心理感受。如同托尔斯泰所称赞的一般:“不加任何选择地、信手拈来什么油彩就在那里涂抹,好像涂上的这些油彩相互之间也没有任何联系。但是倘若你离开一段距离后再看,一个完整的全面的印象就产生了。”[3]这种艺术手法的差异源于作家关注点的不同,也使得两个文本在主题倾向上产生了差异:一个倾向于客观叙述,一个侧重于主观探寻。
(二)对比:传统式揭露与非理性的荒诞意识
《第四病室》和《第六病室》两个文本中都存在着对比现象。但我认为,前者的对比多体现在对金钱基础上社会世相的传统式揭露,而后者的对比则体现在精神境界和人生处境的巨大反差上,有着强烈的戏剧化倾向和非理性荒诞意识。
在“第四病室”中,反差最为明显的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护工对不同病人的态度,二是病人的心地差异。护工态度的差别主要体现在对第八九床的客气、周到和对第六床、第十一床的漠视、折磨上。护工老郑处在社会底层,却能在小便盆、大便盆的处理方式上对没有钱的病人进行肉体上的摧残。而最令人寒心的是十一床痛苦地死去,却还因没有钱挨了老郑狠狠的一巴掌。这种差异的原因其实就在于第九床充满厌恶口吻的那句话:
“这种人只晓得要钱!你有钱给他,你就是他的祖宗!你没有钱就是他的孙子!”
而另一方面,第八九床也极其缺乏同情心,和老郑一样以别人的痛苦为乐,如第八床对别人吊盐水受苦时的幸灾乐祸,第九床在十一床临死时的兴奋、以及几床人在别人开刀需要休养时大声说笑话、唱淫曲等等的行为。如果说老郑是在生活的压力中扭曲成“见钱眼开”的性格,那么这些病人就纯粹是没有良知的恶趣味了。他们不关心战争的局势、以他人的病痛为乐,与第五六床(第五床即主人公陆怀民)尚未泯灭的良知与正义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主人公时常看不惯开口让护工帮忙,而第六床也总是对这种行为表示愤慨。但换个角度来说,主人公自己对第六床的病痛和死前的哀求也无甚在意,第六床也每次只是口头说说而已,所以笔者认为,在这个病室中并没有精神境界的强烈反差,有的只是“世态炎凉”的体现。
但《第六病室》中的对比则有着全然不同的含义了。精神病人伊凡与看守者尼基达构成强烈的对比,医生安德烈则存在一个于两者间过渡的过程,而其精神境界的提高与生活处境的跌落又构成了第二个荒诞的对比。
伊凡·德米特利奇出身贵族,他善于体贴、乐于助人,有着较高的学识和素养。他本是一个有理性、有见解、爱思考的知识分子,但却因为生活在那愚昧、沉迷又荒诞的社会中,精神长期忧郁苦闷,最终因被害妄想而被关进了精神病院。他是被社会逼疯的,可是他的精神境界可谓是书中最高的,故而在被关进病室后还能吸引安德烈来时时和他聊天,最后甚至感染安德烈渐渐认同他的思维方式。与伊凡形成对比的是看守者尼基达,他是“头脑简单、讲求实际、肯卖力气、愚钝呆板的人”,而就是这样的人,本身处在社会底层,却拥有了行使上层统治阶层职能的权利,残忍地摧残伊凡以及后来的安德烈。愚蠢的疯子主宰着清醒者的命运,这样充满荒诞意味的对比实在让人心惊胆寒。
而安德烈的转变也是文中极为重要的对比之一。他在刚刚当上医生时,虽然看不惯医院乃至整个小镇的环境,却觉得自己无能为力,一味冷漠、避世、混世,差不多算是被这个他所蔑视的环境同化了,可在这个阶段中,他衣食无忧,社会地位不低,尼基达也对他十分恭敬有礼。但当他与伊凡接触,开始对自身和社会有了渐渐清醒的认识后,却渐渐为社会所不容,不仅被同事诬陷得病而丢了工作,还被关进病室,遭受尼基达的拳打脚踢,最后悲凉地死去。
在这样的对比中我们不难看出,巴金侧重于描述、揭露黑暗社会中在“金钱本位”观念下的处境凄惨的平庸人物,而契诃夫则着力于在对比中进行对人类精神状态的不懈探索,并通过精神境界与生活处境的荒诞反差进一步控诉荒诞、黑暗的社会对人类心灵的异化和扭曲。
(三)痛苦:肉体情感折磨与精神迷失
如上文所说,“第四病室”中的病人更多受到肉体和情感的折磨。肉体的痛苦体现在没钱买药、护工漠视、以及一些医生的冷漠与不负责任上,而情感的折磨则多体现于其他病人的嘲笑捉弄以及孤身在外没有亲人朋友的孤独上。这种孤独是情感上的孤独,而《第六病室》中的孤独则是精神上的孤独和迷失。
对于巴金在《第四病室》中用尽笔墨、极力描述的恶劣的生存环境方面,契诃夫只是寥寥几笔便带过了:
早晨,病人们都去凑着一个大木桶洗脸,用长袍的底襟擦干,这以后他们用锡杯子喝茶,茶是尼基达从主楼取来的,每人只准喝一杯,中午他们吃酸白菜汤和麦粥,傍晚吃午饭剩下的麦粥,算是晚饭。
而文中更多的,是对其精神状态的痛惜与惋惜:
空闲的时候他们就躺着,睡觉,瞧着窗外,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每天都是这样。(病人)
他往往突然站住,瞧着他的同伴,据此可以看出,他想说些很重要的话,然而分明考虑到谁也不会听他讲话,理解他的话,就不耐烦地摇着头,继续走来走去……他那些疯话是难以写在纸上的。他谈到人的卑鄙,谈到践踏真理的暴力,谈到将来人世间会有的美好生活,谈到窗上的铁格子,这使他随时想起强暴者的麻木和残忍。(伊凡·德米特利奇)
“第六病室”里的其他病人都是不会思考的生物,所以身处这个病室,喜欢思考、充满理想思维的伊凡根本找不到可以说话的人。他们都是“疯子”,这无可厚非。但在伊凡没有被关进病室前,状况仍是令人悲哀的雷同:
在这个城里生活沉闷而乏味,社会上的人缺乏高尚的趣味,过着黯淡无光、毫无意义的生活,用暴力、粗鄙的淫乱、伪善使这种生活增添一些变化。
他和安德烈一般,觉得自己与周围的生活格格不入,心灵感到极度空虚。可最终把他逼疯的,是“谁也不能保险不讨饭也不坐牢”的敷衍黑暗的社会制度,安德烈的悲剧却真正是由自己的精神改变所造成的。文中有近乎半数的篇幅是伊凡和安德烈之间的对话。安德烈觉得“智慧是快乐唯一可能的源泉,可是在我们四周却看不见,也听不见智慧”,他在这样的环境中渐渐被同化,开始心灰意冷,觉得生活与工作都没有太大意思,只追求所谓“内心的安宁与满足”。“二十年来我在全城只找到一个有头脑的人,而他却是个疯子。”
这种令人窒息的社会氛围造成知识分子精神的普遍沉沦,他们“因‘失去自我而悲哀,因‘寻找自我而痛苦”[4]。于是那么多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就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一步步变得冷漠、麻木、浑浑噩噩。安德烈在精神上渐渐找回了自我,可最终走向了“死亡”的结局。这可能说明,在这部作品成稿之时,契诃夫还未真正找到他们(包括作者本人)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的出路,他的探寻还只停留在伊凡的这段话里:
“我只知道上帝是用热血和神经把我创造出来的……如果是有生命的,就必然对一切刺激有反应……受到痛苦,我就用喊叫和泪水来回答;见到卑劣,我就用愤怒来回答;对于肮脏,我就用厌恶来回答。依我看来,实际上这才叫生活……机体越高级,就越敏感,对现实的反应也越有力……”
契诃夫在《第六病室》中对人类精神状态的探寻止于应“有反应”一点,但对于“如何反应”却没有明晰的答案,所以安德烈最终死在了病室,伊凡仍旧在病室中苦苦挣扎。但是无论如何,这是一次有意义的探寻,是契诃夫当时对社会的关注与思考在写作方面的体现,也是现代主义心理与形态在其作品中萌芽的体现。
三、原因分析
通过以上的文本分析,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第四病室》和《第六病室》一个运用现实主义的笔法对国民党统治下平庸人物的悲惨生活进行了全景式叙事,一个则结合了现代主义、印象主义、象征主义手法对荒诞社会中知识分子的精神虚无和异化做了批判和探寻。这两部相似的作品在主题倾向上产生这样的差异,首先是出于作家风格的差异。
在前文中我们说到,巴金在40年代开始有意识地改变了自己以前那种激情澎湃的“诗化”写作,转为冷静而朴素的平凡叙事。在笔者看来,这可能存在着以下三个原因:1.对抗战长期性以及现实社会复杂性的认识。“作家们随着时代心理的变化而转为沉郁苦闷。”[5]2.与俄国文化的共鸣。巴金在40年代成为契诃夫作品的热心读者,开始着重吸收并自觉借鉴19世纪俄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3.生活阅历的积累。“随着年龄的增长,巴金的心境日趋平和,同时对于早年革命热诚以及乌托邦式的理想(即认为只要改变中国政治和社会制度,人民就会得到幸福)不再存天真的想法。”[6]总的来说,在抗战后期,随着巴金在艺术探索上的日臻成熟,他越来越摆脱早期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色彩,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严峻的现实主义。而他一贯所推崇的美学理想——无技巧的艺术——与此相结合,则更推动了巴金转向“现实主义写作”。当然,这并不代表巴金完全放弃了对作品的主观情绪的倾注,在《第四病室》中,我们仍能时时刻刻感受到作者情绪在主人公陆怀民以及女医生杨木华身上的体现,只是这种情感已由早期的“喷涌式”转向了内敛、不动声色,这更使得他此时的作品在现实性描写下依旧保留有人道主义的感染力。
而契诃夫的创作可谓是俄国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现象。“契诃夫是擅长采用多种多样的、往往能在不知不觉中起影响作用的写法的,在有些地方他是印象主义者,在另外一些地方他是象征主义者,需要时,他又是现实主义者,有时甚至差不多成为自然主义者,”[7]多元性和复杂性大概也是由三个原因所致:1.童年经验的影响。从牛津大学教授罗纳尔多·亨利对契诃夫的研究可以看出,“契诃夫几乎从童年时代起,就对乐观主义的世界观产生了不信任感,就有了把生活视为永无止境的、不可逃避的、失望的生活感受。”[8]童年的缺失和痛苦使得作者着意于在作品中描绘“死亡感受”,而这种破灭和虚无的感受恰巧与20世纪的文学新思潮特点不谋而合。2.充满危机与矛盾的时代下的“世纪末情绪”影响。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是欧洲文化普遍存在危机的时代,整个社会被怀疑、悲观和失望的情绪所笼罩,陷入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作者因童年经验的影响,较之其他俄国作者,最早开始发现并探索人类的生存处境和精神状态。3.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契诃夫处于两种“主义”的过渡时代,一种是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为代表的已经很成熟的现实主义写作,而另一种则是20世纪现代主义、印象主义、象征主义等的先后涌现。于是“处在世纪之交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契诃夫在继承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优良传统的同时,在很多方面又突破了现实主义的藩篱,表现出新的创作理念和艺术品质。”[9]综上所述,就不难理解《第六病室》在艺术风格上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了。
最后,笔者对于主题倾向的差异还有另一种尚不很成熟的猜想,即民族性格的影响。中华民族的祖先因地处黄河流域,“千里平衍、无冈峦崎岖起伏……气候四时寒燠俱备,然规则甚正,无急剧之变化”,[10]在这样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平原文化使得中国自古以来存在着“生存第一的文化价值观”与“客体本位观”,这点在人民身上大概表现在苟且偷安的生活准则与身不由己的生活感受,而这种民族性格对于文学作品的创作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影响,它不仅体现在现代文学极力表现的“批判国民性弱点”的主题上,其实也体现在作家的创作过程和写作风格当中。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是相对稳定的,而俄国的民族性格里却存在典型的矛盾性,就笔者查阅到的资料来看,俄国自古因地域环境、战争历史和宗教背景的原因,其民族性格中既有着和中华民族相似的“奴性”和“保守性”,但同时又隐藏着强烈的反叛精神,同时,亚洲游牧民族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还使得俄国人存在着对“精神游牧”的向往,即对精神真理和自由的不明确的追寻。
笔者认为,这种民族性格的差异在《第四病室》和《第六病室》中,就隐藏在作者对于“病室处境”出路的探寻上。不难看出,“第四病室”里的“光明”是女医生杨木华大夫,她有着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人道主义精神,对病人怀有一颗善良而火热的心,而她也清醒地痛苦着,因为在这样的社会,再怎么善于行医治病也救不了人,因为都敌不过钱。杨大夫是作品中闪烁的一道亮光,寄寓着巴金的美好感情和愿望,可是由此也不难看出,作家在进行出路探索时,更多地是把希望寄托在外界上,即少数“清醒者”的引导上,故而最后的结局里仍希望通过杨大夫还活着的猜测使读者心中抱有最后的一丝温暖和希望。而在“第六病室”中,我们看到更多的则是主人公自己对于人生、痛苦、死亡的不懈思索和探寻,虽然不够坚持,中途也走了弯路,但在这一点上还是表现出了更强的主动性。
描述与探寻、人道主义与荒诞意识、被动适应与主动性生存,这就是我对两部作品主题倾向差异的看法。
注释:
[1]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5页。
[2][美]乌尔利希·韦斯坦因:《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页。
[3]朱逸森译,帕别尔内:《契诃夫怎样创作》,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页。
[4]马卫红:《现代主义语境下的契诃夫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页。
[5]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45页。
[6]陈思和,李辉:《巴金研究论稿》,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4页。
[7]史敏徒译,[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第一卷),中国电影出版社,1985年版,第261页。
[8]马卫红:《现代主义语境下的契诃夫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3页。
[9]马卫红:《现代主义语境下的契诃夫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19页。
[10]梁启超:《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49-350页。
参考文献:
[1]许力.契诃夫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研究[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11.
[2]王薇.抗战后期巴金小说与俄国文化[D].重庆:重庆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黄慧辰 湖北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430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