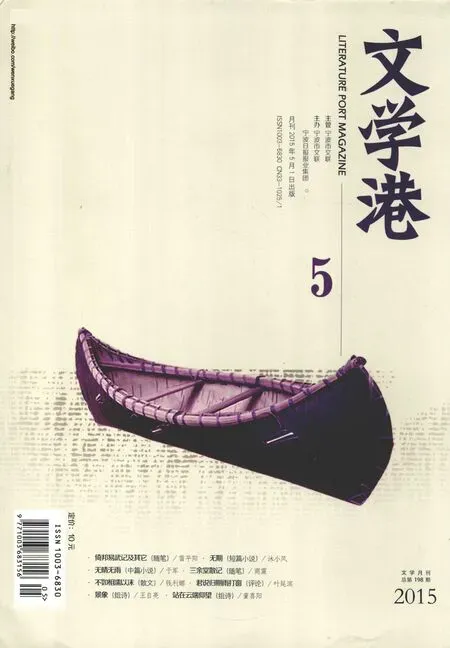柿林村记
胡廷武
柿林村记
胡廷武
2014年11月我在宁波时,曾有柿林村之游。柿林村位于四明山腹地,离宁波市区六十公里,而离余姚城五十公里,有公交车可以直达,沿途路况很好。
我们头天到余姚办事,第二天一早从余姚出发,出城不久,汽车就走上了四明山区的盘山公路。四明山区山势雄伟,林荫茂密,大部分在国家划定的森林保护区范围之内。时令已是深秋,一些树正在落叶,一些树则常青,偶尔闪现的一树树红叶十分耀眼。我是一个来自山国的人,对这种景致不甚敏感,但是很快我就被路边的竹林吸引住了。这些竹林不是一片一片的,而是郁郁葱葱地铺满整座、整座的山冈,而且山冈与山冈之间也没有空隙,像大海起伏不断的波涛一样连接在一起。竹林我过去在云南、四川和其他地方都见过,但是像从余姚去往柿林村的路上这样,几十里不间断的似乎少见,我觉得称它们为竹海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因为离公路很近,我看见竹林中有时隐时现的小路,非常想下去游玩一下,用手机拍几张照片,但是我看全车其他人都没有这个意思,就没有提出来。集体出游得处处考虑同行的人,不能随心所欲地独自行动,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但集体出游也有它的好处,就是一路上可以互相交流、说说笑笑,不知不觉间就到了目的地。经当地朋友指点,我们从移动着的车窗里就看到了柿林村,它像一小片灰白色的云彩,飘落在一处绿色的山冈上,四周全是重重叠叠的青山,黛色或赤色的山岩,目光所及之处,再无人间烟火气。据说柿林村的人家都姓沈,他们的祖先可以上溯到周代王室,他们也是宋代《梦溪笔谈》作者沈括的后代,有显赫的祖宗;村庄的开创者沈太隆,则是沈氏宗族的第45代祖。沈太隆是元末明初的人,由于厌倦尘世的扰攘,带着妻儿到四明山中来结庐隐居。他曾经有诗记载这件事说:“洞天福地甚奇哉,不染人间半点埃,相士择宜居此地,岭头惟有白云来。”从诗中可以知道,太隆先生曾经在四明山中辗转跋涉了许多地方,最后才在相士的帮助下,选定了这里作为隐居之所。当时他所建的不过是两间茅屋而已,不期子孙一居就是六百多年,形成了现在两百多户人家,七百来人的柿林村。柿林村又曾称为峙岭和仕林;叫峙岭是因为村后有两岭对峙,而叫仕林乃是因为村子里曾经人才辈出。峙岭的说法,有民国年间编撰的《峙岭沈氏宗谱》佐证,而仕林的说法似乎不见于文献,我疑心是出自后人的杜撰。近世更名为柿林,则是因为当地多柿子树的缘故。
柿林村的村民大多从事于柿子、茶叶、竹笋、花卉的种植,其中柿子种植有两百多亩,每年的收入达几十万元,是全体村民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之一。这里的柿子叫吊红柿子,比普通柿子个儿小,而颜色鲜明沉着,正是所谓中国红。走近村口的时候,我就看到村前村后,村子周围,甚至村子中间,到处是柿子树。树上火红的柿子,像点点星光,在村子上空、在没有阳光的天幕上闪烁。同行者中有当地的作家,他们指给我看村前村后那些成林成片的柿子树,并说我们来晚了一点,要不这些树上的柿子成熟而还没有采摘、或是刚刚开始采摘的时候,才是最热闹、最壮观的时节。那时候满山柿子如火如荼,村子里家家户户宾客盈门,都是来买柿子的。村子上面公路上的汽车排成串,人们一边把装框或装箱的吊红柿子往车上搬,一边又忙着摘树上的柿子。柿林村摘柿子的方法是,人爬到树上,用一根竹竿去摘;竹竿尖上剖成杯状,柿子一离树即掉进“杯”里,然后放进预先挂在粗丫枝上的木桶或竹筐里;木桶或竹筐装满了,用绳子吊下树来。整个过程小心翼翼,所以他们出售的柿子,往往是完美无损的。
现在树上的柿子既然已经不多,所以来大量运送柿子的汽车也就没有了,我们只看见村口的台阶边上,有两三个摆小摊的老年妇女,她们把柿子、栗子还有新鲜蔬菜,放在簸箕或提篮里出售,她们的商品,最显眼的还是柿子。几位老妪坐在那里一边做针线活一边聊着闲天,看着我们这些外地人从她们旁边的台阶上走下去,她们并不着意兜售自己的商品。我觉得这不是集市,这只是乡村悠闲生活的一个场景,而这种情景我们实在是久违了。
我们走进村子,见村子里的道路很窄,大都是碎石或者鹅卵石铺成,刚好够两个人并排走过,大概是因为走的人少吧,碎石缝隙里沉积着淡绿色的苔晕。村子里的房子大体是青瓦石墙,砌墙壁的石头以褐红色或深褐色的居多,杂以土黄色、灰色或白色。奇特的是,这些砌墙的石头并不方正,而是奇形怪状的,难得工匠们可以把它们稳当地砌上去,而且向外的一面,又基本上是平整的。有的墙面以好几种颜色的石头组成,像一幅幅现代派画家的作品。在狭窄的、深深的小巷里,有的路段两边都是高墙,深色的墙面上,不时地出现一二盏红色的灯笼,有人告诉我说,那是为夜晚的行人照路的。漫步在这样幽深、寂静的小巷,恍若行走在已经过去了上百年的时光里。在一个小巷口上,见有一户人家在自家的门里摆了一个小摊,卖时鲜果品,其中有吊红柿子,还有很大的榛子,守摊的是一位中年妇女。两个姑娘见柿子很新鲜,问多少钱一斤,那中年妇女说:“现在村子里的吊红柿子快要落潮了,好的要12元、10元一斤,我这个比别人家差一点,你们就给8元一斤吧!”从来卖东西,我只见过把自己的产品往好里说的,说自己的比别人差一点的,我还从未见过。《镜花缘》中写到过一个君子国,那里买卖东西,买的人夸卖方的东西好,要多给钱;卖的人说自己东西不好,要少要钱。我们是来到那个君子之国了吗?两个姑娘各买了一斤,格格笑着走到小巷深处去了。
在小巷深处,我看见隔巷并立着两户人家的房子,一户的墙面是暗红色,而另一户的墙面为灰黄色,并立在一起别有一种趣味。灰黄的一幢,山墙上开了一个小窗户,石框木扉,石窗台上垂下长长的藤蔓,也许不是栽的,是小鸟播的种,垂丝上像绒球似的缀着土红色的小花。而对面红房子的墙边上,又砌出半堵石墙,可能是遮住大门的意思。墙垣上,用破旧的搪瓷脸盆,栽种了两盆花,一盆栽着菊,开着黄花;一盆种着葱,开着白花。而再往前走几步,与红房子毗邻的,是一幢更古旧的房子,它的墙面上生满绿苔。墙下面是五寸宽的一条阳沟,沟里流着清水。我掏出手机拍了几张照片,又独自在那里伫望了好一阵。我那时忽然产生了一个奢望:假如能在那木窗下读书写作,那是多么惬意的事啊!在这里不会遇到太隆先生数百年前所回避的扰攘,可以静下心来做一点事。倦了,可以放下书稿从窗口眺望一会儿;从这里刚好可以看到村口那一株柿子王树、村外的茂林修竹、青山和青山之上的天际。而且吃过晚饭,在楼下村里的小路上走走,或是到村中心那株柿子王树下的场地上,看村里的孩子们做那种他们老一辈传下来的游戏,也是令我向往的事情。完了,又坐到窗下去继续做自己的事。我同宁波的作家朋友说过这个想法,他说同村里联系一下,租一间小屋、包括吃饭,都是可以解决的问题。我当时很激动,可惜回到我所生活的城市,这个美好的想法却被种种现实否决了。可见即便是六百多年以后,要像沈太隆先生一样,离开城市到深山隐居,哪怕是短时间,都是不容易的。中国过去的士大夫阶层,大体是得意时安享繁华,失意时则隐居宁静的乡野。而现代的知识阶层则是居城市久了、腻了,不过是到乡下走走,消释一下工作或人事关系造成的压力,呼吸一点新鲜空气而已,很少像古人、比如太隆公那样,深刻反思甚而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所以我觉得同古人比较起来,现代人是生活得迷茫而混沌的。
有人概括柿林村的街巷,说是“二横二纵一古井”,只能说大体上是这样,因为村子里还有一些短促的小道没有计算在内;另外村子的边上,还有一些石板铺成的路径,有的路绕村而过,有的路通向后山,而沿着有的路径走去,在火红的枫树树丛中转一个弯,最后可以抵达掩映在竹林中的两三家人家。但是毕竟村庄不大,就算所有路径在内,如果不在某一处逗留,大约一个小时就走遍了。
那口古老的水井在村子中间,以它命名的小巷叫古井弄,一条稍宽一些的石板路,一直通达井边。古井不深,水清澈见底。同一般意义上的水井比较起来,它更像是一汪泉水,人们来取水时,是用瓢直接把水舀进桶里。井里的水不会满溢,也不会干涸,始终保持着一种深奥的平衡。井边上,作为护墙的石头上,长着绿色的、朦胧的苔藓,石缝里生长着小草。虽然这样,但是如果不经人介绍还是很难想象,这水井已经有六百多年的历史。传说太隆公当年在四明山中寻找隐居之地时,曾将装饭的袋子挂在一棵树上,等辗转半天回来,饭仍是热的,老先生可能以为这是神的一种暗示,一挖树脚,果然得一清泉,这就是今天古井的来历。柿林村沈氏现在是一个七百多人丁的大家族,正是这一口水井,哺育了这个家族,使之繁衍数十代而绵延不绝。据说现在村里早就通了自来水,但人们还是来井里挑水用。有游客掬水而饮,连声说清凉回甜,我因为身体的原因没有品尝。我想起明代文人沈明臣在他的《四明山游记》里曾经写到柿林村,说:“登一小岭,绕而南去,乃一旷土,宽数十亩者,有沈氏居焉。地曰柿岭,家户业纸,屋后山如屏。”业纸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经营纸张买卖,二是造纸;在偏僻的深山里操作纸张买卖不可想象,这里说的应该是在明代的时候,至少是沈明臣先生来考察的时候,柿林村家家户户在从事造纸的营生。造纸需要大量的水,水井虽然终年不涸,但水量有限,不可能供应“家户业纸”,所以我推测,当年柿林村造纸的地方应在村下面的赤水溪畔,用的是赤水溪的水资源。村子东边,在树竹的掩蔽中有一条石头铺成的、梯子一样的小道,通向下面的赤水溪,这是不是就是数百年前村民们的“业纸石道”呢?另外,柿林村周围满山遍野的竹子不正是造纸的资源吗?那么我们沿途见到的海洋一样的竹林,也应该是四明山中古老的种竹传统的一部分吧?
中午的时候太阳出来了,我看见有的老人开始坐在廊檐下的竹靠椅上烤太阳,一面聊着闲天,老太太手里则摘着菜叶,再过一会儿,下地干活的人要回来吃饭了。这天中午我们也在村子里的吃饭,是所谓农家乐。主人家朴实谦和,供应我们的饭菜,从肉到蔬菜都是最生态的。席间有人说起沈氏宗祠,朋友才知道我没有到那里去参观过。我说我知道沈氏宗祠也是柿林村的一处重要建筑,其中不仅有沈太隆的牌位,而且也有沈括的牌位。沈括是沈氏宗族的第二十四世祖,一生在宦海沉浮,死后被宋哲宗谥为文肃公;此外沈氏第二十九世孙沈绅也曾被谥为文肃公,所以沈氏祠堂里高悬着一块匾叫“文肃世家”,这件事是柿林村的一件美谈。但是我认为宗祠是人家氏族的私第,就没有去造访。此外,刚才说起的赤水溪,因为时间仓促也没有去,不过我认为那里已经不属于村庄的范围了。而且山水风景无非是大同小异,只有人文景观才各有各的妙处,从这个角度说,柿林村的确是一个美好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