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瑰的旅途
——司猗纹的出走之路
葛冉冉
(温州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
玫瑰的旅途
——司猗纹的出走之路
葛冉冉
(温州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
出走是妇女争取自我解放的一个重要路径,同时也是女权主义文学作品中常见的主题。铁凝在长篇力作《玫瑰门》中凭借其卓越的才华描写了司猗纹的灵肉出走历程,关注以司猗纹为代表的女性日常生命状态,对生活在“菲乐斯中心主义”社会中的女性命运进行思考,追问当女性取得经济独立后与男性以同一高度站在权力舞台上的可能性,探索隐藏在男权世界中女性出走背后的女性问题。
铁凝;《玫瑰门》;司猗纹;出走
女性出走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化原型。从早期神话嫦娥奔月、仙女下凡的故事,我们可以发现关于女子“出走”的原始意象早已储存在集体无意识之中。“出走”模式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经典母题,这既有对中国古典文学模式的借鉴,更受到西方文学模式的影响。事实上,它的快速发展最早得益于易卜生作品《玩偶之家》在中国的传播。“由男性大师易卜生所创造的娜拉,只是一个用来填充易卜生孤独的诗意与痛楚的激情的空洞能指;娜拉的出走只是一个在高潮戛然而止的戏剧动作。”[1]易卜生作为男性作家,他无法彻底摆脱男权思想对其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娜拉的出走并无女性主体意识的过多参与,也没有为女性出走后的生活添加些许希望色彩。鲁迅指出,“从事理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坠落,就是回来”[2]。因此鲁迅笔下的子君,为了实现形而上的“人”的完整性而出走,但是受生活现实所迫,依然逃脱不了“回来”的宿命。《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不堪夫家的凌辱逃回娘家;又因遭受嫌弃,再次出走香港,百般曲折后与阔少范柳原结婚。走来走去都脱离不了对男性及男性家族的经济依附。于是人们认为,女性出走受挫源于经济不独立。铁凝这位思维敏锐的女性作家,在她的《玫瑰门》中进行了一番新的思索,即当女性取得经济独立时,她的出走就会成功吗?就可以获得与男性分享同等权利的资格吗?本文从司猗纹灵肉出走的历程进行分析,以探寻铁凝所给予我们的答案。
一、为爱与自由而出走
“五四”时期是中国社会伟大的震动时期,对个性解放的追求成了时代的最强音。在这一时期,很多中国女性开始觉醒,大胆地追寻恋爱自由。虽然早在“五四”之前,女性作为大胆的爱情追求者与家庭反抗者的形象已出现在文学作品当中,如为追求爱情自由而离家出走的卓文君、李千金、王宝钏,为爱殉情的祝英台与刘兰芝等,但“五四”时期女性思想解放影响范围之广是前所未有的。生活于这一时期的司猗纹在进入圣心女中后,年轻的生命注入了全新的血液。在学潮运动中,她遇到了人生中第一份爱情。虽然这份爱情遭到了父母的强烈反对,但此时的她大胆前卫、不顾世俗,真诚而热烈地追寻爱情自由,在华致远将要远行的雨夜献出了少女的贞操。“交媾从来不在真空中进行;尽管它本身是一种生物的和肉体的行为,却根植于人类活动的大环境的最深处,从而是文化认可的各种态度和价值观的集中表现。”[3]“五四”蓬勃发展的女性解放运动唤醒了沉睡在象牙塔里的猗纹,开始从“无意识”的梦境中醒来,走上了寻求个性解放与发展的征途,与《终身大事》里的田亚梅一样,用出走来追求爱情与自由,决绝地反抗封建礼教。此阶段猗纹的生命轨迹是逐渐上升的,即思想不断地发展、进步,从而带来生命高度的提升。铁凝关于“雨夜”的描写很唯美,没有丝毫色情杂质。但梦幻、幸福、青涩而又凄凉的氛围,预示着她这次灵肉出走的失败。探其原因,首先是动荡的社会无法给这些进步青年一个能够获得幸福的环境;其次是在司猗纹表面觉醒的背后,其意识深处隐藏着对封建礼教的皈依与认同,她无法走出传统婚姻道德观的藩篱;最后,只有十几岁的他们,仅有青春的热血,缺乏成熟的思想,没有稳定的收入,如羽翼未满的鸟儿试图走出牢笼展翅飞翔,这一结果注定是消亡。
二、为履行血缘责任而出走
血缘意识与家族观念是中国人难以割舍的心理情结,处于血缘关系中的个体会受到其他成员的爱护,这种爱会成为一种族类自我意识。这种意识能使个体自觉承担在血缘关系中的道德责任,反之,罪恶感便会吞噬叛逆者的心。实际上,这是一种被传统异化了的带有极大虚假性的自我意识。铁凝为了揭露这种虚假性的自我意识,沿用了鲁迅“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的思想安排情节,出走后的猗纹带着忏悔回归了家庭。在五四“出走”光芒的照耀下,精神上闪现的火花稍纵即逝,历史的惰性、传统道德文化及家族观念的强度反弹,使稚嫩的猗纹又被迫退回到自我生命抑制的无奈之中,不能自拔,为自己曾经的“不贞”而忏悔。在男权制下,性被认为是女性的命运所在,男权制试图并且成功地使女性仅作为性的器皿。“舆论仍然指责那些在婚前失去贞操或者被怀疑乱交的女性。对女性贞洁的根深蒂固的观念是占支配地位的性道德的一种功能。”[4]婚前失贞,为世人所不耻。贞操被视为男权社会中的美德,代表着一件货物原封不动送到了买家手里。几千年的意识形态传递的是“男人往往以占有女人的身体来显示自己的权力”[5]。即使不喜欢这件货物,也要对它享有完整的所有权。男性通过对女性原欲的残忍禁锢,借以缓解本身的阉割焦虑。所以当庄少俭知道司猗纹的过往后便怨愤交加,却忽略了自己曾经的纸醉金迷。
司猗纹与叶圣陶长篇小说《倪焕之》中的金佩樟相似,婚后从站在时代浪尖上的新式女性进入了传统的贤妻良母角色。她不怨恨丈夫洞房花烛夜的侮辱和报复,对丈夫绝对地服从。当她向男权制度低头时,就注定了人格独立性的丧失,庄少俭对她的远离也在情理之中。司猗纹成为了被男性世界所认可的除“忠贞”之外,集“美貌、温驯、富于献身精神”于一体的天使型女性。此时她的生命轨迹是下沉的,即生命轨迹的一种竖直向下运动,是精神思想在向前向上发展过程中的后退。原因有三,最主要的是为了完成家族的血缘责任替自己赎罪;同时,少女懵懂的心在见到高大帅气的庄少俭后对爱情重新充满了期待;最后,传统的“妇德”不仅将女性囚禁于闺房和灶台,更是从精神上囚禁了女性的生存空间。这一阶段孤军奋战的司猗纹,无法突破这一狭窄的空间,只有默默承受。
三、为维护婚姻幸福而出走
出走叙事是对出走者从一个环境向另一个环境转移的表现。现实环境之间存在优劣差别,它作用于人的心理,引起心理失衡从而产生对更好环境的向往。猗纹在庄家受到了庄少俭持续一年之久的冷暴力,情感心理失衡进而主动出击追随丈夫去扬州,寻求更好的生活环境。这一出走行为涉及到了文学史上的“千里寻夫”模式,即丈夫外出后不归,妻子离家寻找。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孟姜女》因讲述了千里寻夫的故事而广为流传,《琵琶记》里的赵五娘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主动争取获得了千里寻夫的成功,这在人们的思想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司猗纹受这些传统文化的熏陶,忍受了丈夫在扬州生活的糜烂与一连串厌恶的质问。“我决定给你以宽容。因为我是你的妻子,何止是妻子,是贤妻。”[6]135千百年来,理想的女性是贤妻良母,她们被强制性安排在家的空间,在操持家务和照顾他人中实现自己的“第二性”地位,接受男人强加在自己身上诸如“贤妻”等的重重身份,在“菲勒斯中心主义”社会中陷入无路可走的“主体的困境”。司猗纹千里寻夫的故事与《孟姜女》相似,结局都是不完满的,一个是丈夫不爱,一个是丈夫已逝。此时司猗纹对庄少俭是坚贞不渝的“愚爱”,如同专制制度中臣民对君王的“愚忠”,不计对象的优劣,不着眼自身的尊严与人格。在这个“粉红色男人”面前,司猗纹连卑躬屈膝地做“贤妻”的资格都没有,想做婚姻中的“奴才”而不得。痛失儿子的猗纹,在一系列悲惨的打击后开始觉醒了。
四、为冲出无爱围城而出走
司猗纹为庄家的付出,只换来公公对她的憎恨与诅咒,她藐视着庄家男性统治者老太爷的虚伪与贪婪,并亲自买下北平东城的住所,从而成为了庄家的中心人物。她带着怜悯性质接受了从北平回来过年的庄绍俭,意想不到的是,这个整日流连于花丛的“嫖客”竟给她带来了灾难——梅毒。对于司猗纹这样一个倔强孤傲,初尝权欲快感的女人来说,这无疑是致命打击。不仅身体上的痒痛令其难以忍受,圣洁灵魂被玷污的创伤更是难以泯灭。然而她没有倒下,病毒重塑了她的肉体,改变了她的性格,一个获得新生的像罂粟一样妖艳邪恶的司猗纹出现了。“司猗纹以一种天塌下来也不怕的气概,带着一身月光和一身黏痰和姑爸的惊异回屋睡觉去了,她躺下就着。”[6]188她以极具冲击力的乱伦方式,实现了女性自我由客体到主体的完美转变,并在这一过程中释放了长久以来被压抑的原欲,成为男性世界所憎恶的具有主体性的恶女型女性形象。肉体的新生带来了精神的复苏,她改变了男人属于攻击型、女人属于被动型的这一两性气质特征。此刻的她是带刺进攻的玫瑰,打破了“阴茎崇拜”的光环,她体验了父权文化的味道是如此不堪。此时她完全取得了经济独立,虽然这份独立是来自于男性家族的剩余物,这是她人生中最光辉灿烂的时刻,生命轨迹几乎是垂直上升。可能这种表达方式太让人震撼,一时让人难以接受,但其实这种人物反抗方式在文学作品中并不少见。《水浒传》中的潘金莲不甘于自己如花的岁月葬送在矮矬穷的武大郎手中,因此通过与西门庆通奸的方式释放内心的苦楚。《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在长期性压抑的生活中,与小叔子暧昧又被其戏耍,无处释放的愤懑与压抑只能在对儿女的“毒杀”中得到宣泄。当平凡的女性怀着觉醒的心想要冲出无爱的婚姻围墙时,现实中的困难使她不得不采取一种非常规非理性的方式,在这个从不接纳她的空间里开辟自己的一席之地。
五、为在时代中生存而出走
文革开始时,这个每天吃维生素养生,做蔬菜面膜的具有资产阶级情调的女人明显不符合那个时代的要求。她不属于劳动阶级,虽然她竭力地想往这个阶级靠近,但却一次次地被排斥,不能取得相应的社会身份。然而她不甘心社会给自己所贴的“妇女”标签,不满于自己政治上“类”的划分,她要跻身主流意识形态。她放下身份去糊纸盒、锁扣眼、砸鞋帮。在革命运动如火如荼时,她主动搬离了高大的北屋,上交了家具。在白天,她谄媚地奉承迎合,半夜又通过偷吃廉价点心的方式来抚慰高傲的心在白天所受的创伤。此时的司猗纹通过人格分裂的方式,在这一压抑的社会中作着顽强的挣扎。白天她是时代的“奴才”,晚上她是自我的“主人”,这一“奴才”与“主人”的双重身份压得她气喘吁吁。司猗纹用一种社会舞台表演的方式,换得了在这个疯狂的时代里生存的资格。在荒谬的政治中,当人性都丧失时,女性要建造一个正常的合理的空间只能是徒劳。从司猗纹所受的教育及行为来看,她并没有对这个时代产生质疑与不满,也无法理解她丧失尊严的根源,甚至觉得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而她所有的经营与努力都只是让自己在貌似注定的命运中较为优越地生存下去。
六、为梦醒后的救赎而出走
文革结束后,司猗纹终于成功了,和罗大妈一样做了时代的主人。作为北屋的主人,“她希望罗大妈多坐会,看她怎么吃,再腾出眼神儿多看几眼她的梳妆台”[6]396。司猗纹被压抑的优越感以井喷的方式喷涌而出,一发不可收拾。她一直处在被压抑的状态,性压抑,“奴才”与“主子”双重身份的压抑,被压抑得太久,导致成为“主子”的她已不知道如何做“主子”。从紧张的生活空间中突然松弛下来,让她倍感不适,越发地心力交瘁。她渴望救赎,需要精神寄托,却无人与其亲近。于是她跟踪竹西,跟踪眉眉,给眉眉的丈夫写举报信,在这种自虐与虐人的过程中,宣泄婚姻的不幸,抚慰尊严被践踏的创伤。但是这种释放的冲击力过大,使她的人格偏离了正常的生命轨道而走向幻灭。司猗纹在一次疯狂的跟踪之后,再也没有能够站起来。追逐了一生的权欲使她即使瘫倒在床上也要尽最大的努力来维持自己的领导地位。然而她的自我救赎最终以失败告终,生命的起点与终点在胡同重叠,落于一片灰烬之中。
司猗纹坎坷的一生,对传统的家庭婚姻价值观、男权社会做出了有力的冲击。波伏娃说过:“女人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7]。在《玫瑰门》中,司猗纹一生的出走历程是这一观点的最好验证。她的一生由社会、家庭、自身共同造就。她的生活态度、生存方式、人性的扭曲、女性意识的畸变也是在现实生活与男性话语氛围中一步步形成的。从司猗纹的人生经历可以看出,女性想要出走成功,经济独立固然重要,合适的、开放的社会环境更是不能缺少。人们思想里根深蒂固的封建文化、男权思想必须得到清除,这样女人才有实现自我的可能。同时,女性自身由生理所限往往存在局限性,遇事缺乏冷静偏于情绪化,处事易剑走偏锋,在生活中会被一些表象所迷惑,在生命的迷宫里渐行渐远。女性出走的成功之路还很漫长并充满艰辛,因为控制着所有权利通道的男性,是不会接受一个为与自己分享同等权利而奋斗一生的异性,他们要永远站在金字塔的顶峰俯视卑微的女性。在“菲勒斯中心主义”社会中,女性出走之路刚刚起步,前途的美好风景我们共同期待。
[1]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37.
[2]鲁迅.娜拉走后怎样——1923年12月26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讲[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59.
[3]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36.
[4]艾华.中国的女性与性相——1949年以来的性别话语[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180.
[5]西蒙娜·德·波伏娃.女人是什么[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24.
[6]铁凝.玫瑰门[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
[7]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309.
【责任编校 朱云】
On the Reason why Ms Si Ran-away form Home
GE Ranr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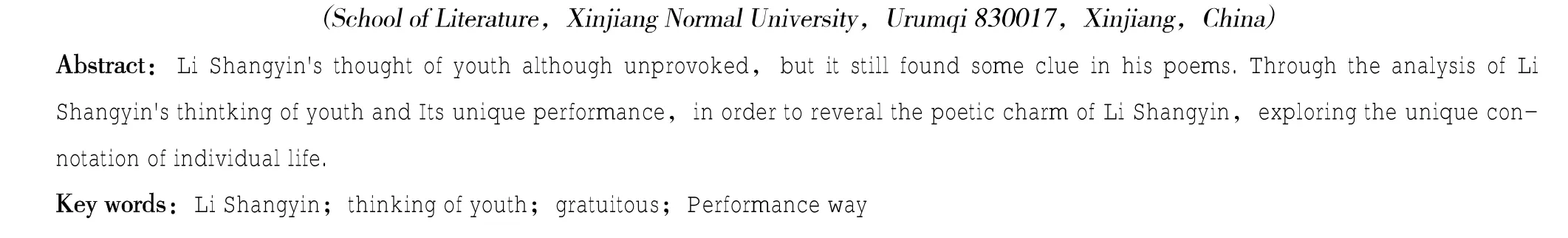
I206.7
A
1674-0092(2015)05-0076-04
2015-04-17
葛冉冉,女,安徽淮南人,温州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