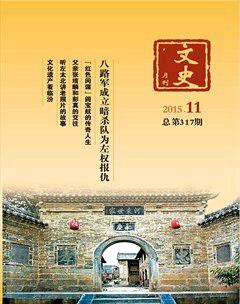中国社会学的奠基者
智效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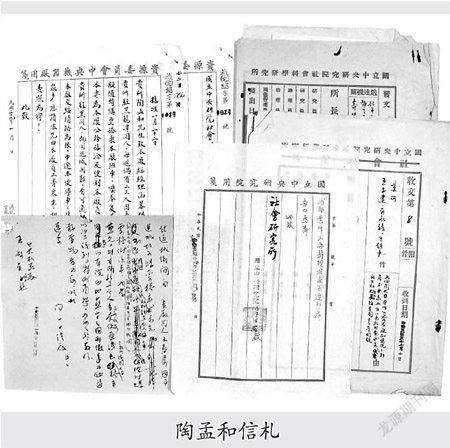
为《现代评论》撰稿
《努力周报》停刊后,《现代评论》于1924年年底在北京创刊。《现代评论》的性质与《努力周报》类似,也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刊物。所不同的是,它的作者范围更广,内容更丰富,存在时间更长,影响也更大。作为学术界的一个重阵,陶孟和自然是它的主要撰稿人之一,特别是在《现代评论》的前期,即1927年7月迁往上海之前,每隔几期就有他的一篇文章。这些文章涉及到教育改革、学生运动、经济独立、科学研究、土地人口、种族问题、政治宣传、国际评论等诸多领域,可见作者的通与博。读陶氏文章,可以看出两个特点:一是善于运用现代文明的基本原理评论现实的社会问题,二是喜欢以通俗易懂的文字阐明深刻的道理。比如1925年4月18日发表的《言论自由》就是很好的例证。文章开篇写道:“人有自认为全能全知的吗?我想除了最狂妄最无知的人以外,没有敢这样自认的。能力越大的人,越觉得自己能力微小。知识越高的人,越觉得自己的知识有限。但是也有人认为自己全能全知者,他们凭借特有的权力,无视他人存在,一意孤行,为所欲为,这就是言论不能自由的根本原因。”接着陶孟和举例说:“假如邻居在你的门前倾倒垃圾,你还可以与他理论;倘若那个倒垃圾的是政府官员,你要是批评他,就可能被扣上妨害公务的罪名。”对于这种异常的状况,陶孟和做了如下分析:第一,政府的职能是维护社会治安,但维护社会治安决不能成为强迫人民服从的借口。第二,政府首脑也是普通人,他们或许有特别的知识或高人一筹的本领,但他们并没有长着三头六臂,也不是无所不能的神仙。第三,当今社会已经进入一个分工越来越细的时代,这就更不是少数官员能包办的事情了。在这篇文章中陶孟和还反复强调:“政府是由人而不是由神组成的,所以政府犯错误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现代社会的政治结构和文化团体都是为人民发表意见而设置的。政府有过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有了过错不肯承认,不允许批评。不认错不仅会给人民带来危害,还使政府丧失改正错误的机会和长期存在的可能。”因此文章的结论是:“恶政府视言论自由为毒害,为仇敌,好政府视言论自由为兴奋剂,为滋养品。言论自由是每个好政府必不可少的要素。”(《现代评论》第1卷第19期)同年5月30日,陶孟和还发表了《我们为什么意见不同?》,继续讨论这个问题。文章说:“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不同的意见,当然非常美妙,但实际上这是永远也不可能的。人与人之间有不同意见,首先是由于‘人的禀质不同’,比如对于日落的景象,乐观者会有‘夕阳无限好’的感慨,悲观者却会有‘只是近黄昏’的哀叹。再加上所处的环境不同、所受的教育不同、每个人的利益不同,要想让大家意见一致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政府的作用,应该是为所有的人提供发表意见的机会,让每一个人都有实现其愿望的可能。这也是政府存在的理由。”(《现代评论》第1卷第25期)此外,徐志摩当年主持《晨报副刊》时,还约陶孟和写了《再论梁巨川先生的自杀》一文,试图引起争论。这是作者《论自杀》一文的续篇,可惜除了徐志摩的两篇文章和陈衡哲的一封来信外,这个话题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
主持社会调查所
1926年2月,美国一个社会宗教团体愿意捐赠三年专款,委托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增设一个社会调查部,并聘请陶孟和主其事。1929年,陶将它改为社会调查所,成为一个独立机构,开始对中国社会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从此,陶全力以赴地投入到这一事业之中。
关于陶孟和在这方面的贡献,曾在社会调查所工作过的巫宝山在其文章中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在这里,我只想补充两条材料。一是千家驹的一篇题为《怀念陶孟和先生》的文章(《怀师友》,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年版)。1932年,千家驹从北大经济系毕业,因一篇发表在小报上的文章深受胡适赏识,被推荐到陶孟和那里。千家驹进调查所后,最大的感受就是陶的宽容和信任。千说:“陶先生是知道我的政治立场的,但他颇有蔡元培兼容并包的风范。他从不干涉我们的研究自由,他评判一个人的研究成绩,是看他的成果,而不是其他。”此外,陶认为研究工作应该以自愿为原则,有研究兴趣的人会日以继夜地工作,没有兴趣的人让他整天坐在办公室也没用。
另一条材料是费正清的回忆。抗日战争期间,费正清与陶孟和相约,由重庆出发,沿长江到达宜宾附近的李庄。在路上,费正清被中国内地千奇百怪的现象所吸引。当他看到一个呼吸困难的男子躺在地上,想上前帮助时,陶孟和却不让他多管闲事。陶说:“这也许是个圈套,你一旦碰了他,就很可能被缠住,迫使你花一笔冤枉钱。”可见陶孟和对下层社会是非常了解的。李庄是中央研究院所在地,在这里费正清目睹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后,颇有感慨地说:“依我设想,如果美国人处在此种境遇,也许早就抛弃书本,另谋门道,改善生活去了。但是这个曾经接受过高度训练的中国知识界,一面接受了原始纯朴的农民生活,一面继续致力于他们的学术研究事业。学者所承担的社会职责,已根深蒂固地渗透在社会结构和对个人前途的期望中间”了。(《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269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当时,陶孟和的妻子沈性仁患有严重的肺结核病,这对他来说不啻于雪上加霜。沈女士也是一位学者,早年在《新青年》上就有译作发表,1920年与陶孟和合译凯恩斯的《欧洲和议后的经济》,被纳入《新青年丛书》出版。沈是1943年病故的,费正清说“她是我们朋友中最早去世的一个”。据巫宝山介绍,沈去世之后,陶孟和的生活非常孤寂,但是他对研究事业的热忱仍一如往昔。在陶孟和的感召下,社会调查所于战争时期完成了一大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培养了严中平、梁方仲、汪敬虞等一批很有才华的研究人员。值得一提的是,陶孟和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损失估计和谈判情况非常了解,所以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就着手抗战损失的研究,为战后的赔偿作准备。巫宝山说:“在中日复交的谈判中,周恩来还派人了解过这方面的情况,但不知为什么中国政府又主动放弃了索赔要求。”
政治立场左倾
抗日战争胜利后,陶孟和率领社会调查所迁回南京。1948年,中央研究院奉命迁往台湾,陶对所里的人说:“朱家骅(时任中研院院长)是我的学生,我可以顶他,他不会把我怎么样。”(《近代中国》第5辑第390页)与此同时,他还反对文物图书南迁计划。陶孟和立场左倾,可能与他的连襟钱昌照有关。钱是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主任,他虽然与宋子文关系密切,却一直是中共的统战对象。据《竺可桢日记》记载,1949年5月,竺由杭州潜往上海,听任鸿隽陈衡哲夫妇说:“陶孟和颇赞成共产,近来大发议论,于首都陷落前三日赴京……”(《竺可桢日记》第1246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虽然任、陶二人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曾经在使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的问题上有过矛盾,但是陶孟和的左倾立场却与《新青年》时代形成鲜明对照。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社会学所的所长。不久,陶、竺二人又返回南京、上海,以他们的声望和影响,动员旧日同事共赴北京。
然而从五十年代开始,陶孟和的处境却不容乐观。据当年中国科学院的真正负责人张稼夫回忆:“1930年我在河北搞农村调查时,认识了北平社会调查所的韩德章等人。韩德章等知道我到了北平,就和我取得联系。这时我才知道他们在天津《益世报》编副刊,每星期出一至二期。韩德章知道我在西北安村当过村长(按:张稼夫是山西省文水县西北安村人),对农村情况比较了解,就约我为《益世报》副刊写文章。我刚到北平,生活无着落,当下也难找到北方局,就答应了。把我在山西农村了解到的情况写了一篇文章,以张稼夫的名字,发表在《益世报》的副刊上。我用张稼夫的名字公开发表文章,意在找党,其实也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庚申忆逝》第39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天津《益世报》委托社会调查所办副刊一事,千家驹在回忆中也谈到了。他说:“是陶先生答应下来之后,让他编这个副刊的。”而且那是千家驹从广西调查回来之后即1933年的事。我不知道张、千二人说的是不是一回事,但是从张的叙述来看,他在学问上是不如千家驹的,更不要说陶孟和了。当时张是以副院长兼党组书记的身份成了中国科学院“掌院大臣”的。有意思的是,上任伊始,张要“整顿”科学院,曾组团去前苏联取经。为了有个像样的名分,代表团给他“报了个历史学家的头衔”。(同上,第122页)
专业不保 晚年遗憾
当时,年过六旬的陶孟和虽然是科学院的副院长,却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这一点,从张稼夫回忆中可以看出。张说:“在科学院工作时期,我们相处得十分融洽,科学院的重大事项,郭老、李老、竺老、范老(范文澜)和我都事先交换意见,统一思想,然后再交院务会议通过。”(同上,第127页)按说陶孟和也是个副院长,但是却不在“事先交换意见”的行列。1951年土改结束时,陶孟和寄希望把科研工作尽快提上议事日程,但由于当时科学院“有三分之二以上的研究所没有党员副所长”,有的研究所甚至连一个党员也没有,所以任何工作都无法开展。(《庚申忆逝》第132页,《近代中国》第5辑第393页)这与当年千家驹进所时的遭遇迥然不同。没过多久,社会学所就被改为经济所了,整个社会学专业也被取消。
1957年反右运动进入高潮的时候,科学院曾散发关于陶孟和某些言论的材料。据说他不顾个人安危,曾在一次大会上讲:“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们相互间的关系和社会的进步,依靠的是友爱,而不是仇恨,知识分子应发挥他们的作用,而不应当受到敌视(大意如此)。”(《近代中国》第5辑第394页)据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回忆,当时陶孟和还讲了许多“过头”的话,他甚至说当时的反右斗争对知识分子是一场浩劫。有人说,“浩劫”一词,是陶孟和第一次使用。因此在总结时大会主席曾对陶提出警告,所幸最终没有把他定为批判对象。
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陶孟和曾写过一篇题目是《我们小民的希望》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向当权者提出三个要求:一是尊重生命,二是尊重财产,三是尊重人格。这三个要求条件不高,很容易做到,但当时却很难实现。因此他希望“在最近的将来”能有一个这样的地方。
(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