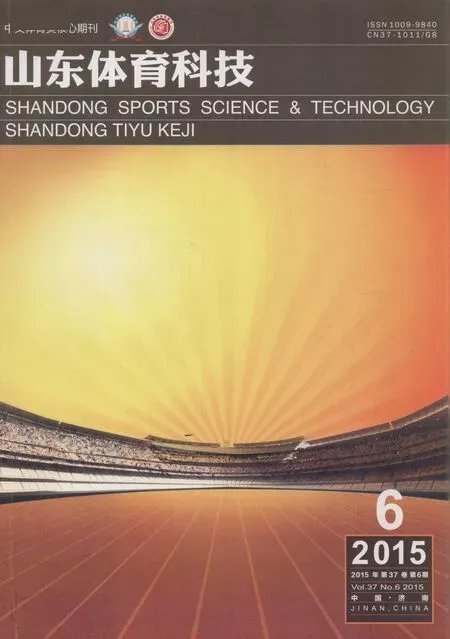从传统到现代:武术人社会生存论析
吕思泓
(齐鲁工业大学 体育学院,山东 济南 250353)
从传统到现代:武术人社会生存论析
吕思泓
(齐鲁工业大学 体育学院,山东 济南250353)
摘要:通过文献梳理和逻辑分析,从传统到现代纵向考察了武术人的社会生存状况,反思当下武术人的群体特征及其历史使命。研究认为:1)传统社会武术人在体制内、外两大场域内生存,但因江湖社会与国家权力的抵牾、文武之争、社会的“文学化”等而深陷困境。2)冷兵时代的完结,为武术发展换来了宽松的政治环境,武术人通过武术教育化、竞技化和经济功能的发掘,获得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和更高的发展平台。3)当今武术人以“技术派”和“文化派”的区分呈现,并伴随着群体内的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二者共生互补地担负着武术发展的历史使命。
关键词:武术人;传统;现代;生存;资本
社会在变迁中发展,武术人及其事业也在社会变迁中发生着变化,武术人的历史是适应社会变迁的历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武术是武术人的武术,也是发展的武术”[1]。一项事业的发展由从事这项事业的人所推动,研究武术及其发展,必须基于其主体角色变迁反思当今,意义在于:第一,只有回溯武术人的社会生存,才能更好地认识武术人的时代担当。第二,国家以独立学科的形式赋予武术极高的地位,学科的重要性需要我们重新审视武术人的历史使命。第三,认识武术人也是认识武术人所从事的武术事业的过程。探讨武术人社会生存的历史和当今,利于武术人理性认识自身的“遗传基因”,找到恰当的人生定位,做出应有的时代贡献。
1江湖与功名中的困境
江湖,从自然的空间概念演变为一个泛指的生存场域,上有游侠世界,下有勾栏瓦舍的“街角社会”、恩仇交错的帮会、“绿林”。不可否认,身体暴力是江湖空间处世立足的重要手段,因此,武术人自然也成为江湖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侠成为第一批游走于江湖中的武术人,并获得了“纯而无私,公而不偏”[2]的至高褒奖。然而侠的历史并未持续太久,原因正如梁启超所言,“我民族武德之折丧,则自统一专制政体之行始矣。”[2]从秦始皇“杀豪俊,收天下之兵”,到汉高祖时代“功臣武士,皆载敢摄伏,汗下不敢仰”,尚武精神消灭殆尽。此后,武术人的生存空间转入街头、镖局、帮会等场域。从宋代兴起的勾栏瓦舍一直到北京街头天桥,是武艺表演者的江湖;崇山密林、关隘要口是镖师的江湖;地下社会是帮会成员的江湖,等等。但随着社会的变迁,江湖不断退格以至消失。一者,大众娱乐形式的多样化直接导致了武术表演形式的消弭;二者,现代运输技术的飞速发展取代了保镖行业;最重要的是,江湖社会因其行为准则与国家权力的法治要求格格不入而成为“法治外社会”,江湖社会的这种特征决定了它日渐萎缩的命运。
隋唐以降,国家为武术人开辟了一条重要的社会通道——武举。尽管武举使部分武术人成功进入仕途,同时也使其面临诸多无奈。第一,真正进入官方获得高级官阶的武术人实为少数。如孟二冬教授生前所著《登科记考补正》新增“武举22人,其中编年者3人,入附考者19人”[3],唐代的著名将领几乎没有一个是通过武举考试产生,著名将领郭子仪也只是出身唐代制举武科。《清代七百名人传》“军事编”所收一百七十三人中,武科出身者只有十一人,仅占6.4%[4]。第二,武举的推行,直接危及文人的生存,以至于文武之争恶化,武官地位卑贱,甚至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如明代中期以后,武官与兵部、兵科的文官打交道,稍讲自尊者自称“门下小的”;动辄自称“门下走狗”者亦不在少数[5]。第三,武举与我国传统社会的变迁趋势不符。台湾学者龚鹏[3]程指出,从唐宋至明清,中国逐步进入一种极端的“文学化”社会,人人以尚文或取得功名为荣,所谓“士有不由文学而进,谈者所耻”[7]。在这种社会风气下,武艺成了下等的勾当,以至唐代有“不肖子弟为武官者,父兄摈之不齿”(《唐会要》卷七二《军杂录》)之说。
可见,无论在体制内为官还是在体制外行走江湖,武术人文化资本的先天缺失和社会网络的层级低下,造成了武术人的生存困境。这种困境源于传统冷兵社会紧张的军政关系,也源于政治体制内文武之间对生存资本的争夺。
2武术人的生存转机
冷兵时代的完结,为武术换来了政治上宽松的发展环境。武术人正是在这一时代变迁前提下,通过武术教育化、竞技化和经济功能的发掘,获得了更加体面、广阔的生存空间。
2.1“流动的现代性”中的转折
有人将现代社会开端定位在哥伦布地理大发现之时,因为从那时起人类真正开启了世界范围内的流动过程。因此,现代社会的特征也被鲍曼等人概括为“流动性”,武术人的生存境遇正是在现代社会流动性中发生转折。
西方为近代中国带来了两件事物:西方文化和国人失败的自卑感。后者源于西方列强的侵略,直接导致了晚清以来精英对于国家颓弱的反思。他们认为“身体不如人”是导致国运颓败遭受外侮的主要原因,于是基于强种强国、富国强兵理想以及保存中国传统文化的初衷,将武术作为实现强国梦的首选。于是,在朝野合作之下,从强国必先强身的理念出发,中国在20世纪初期以中央国术馆、精武会等组织为主要推动者,意图通过建构“科学与理性的中国固有体育”这样一个正式与条理清晰的意识形态来发扬国术[8]。从改良传统武术重构新时代国术价值,到推行各类国术训练与教育,打破了传统武术狭小、封闭的教育和传播模式[9]。西学东渐,西方体育也随之而来,学校中开始设“体操科”,也就是现在所说的体操、田径之类。体育教学发轫的同时,本土精英从抗衡西方体育出发,一方面展开“土洋体育之争”,论证武术教育化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将我国的武术作为“土体育”的代表搬进各级学校的课堂。从1910年代始,武术便与西方体育在学校中平起平坐,一直至今。
在“流动的现代性”带来的中西碰撞中,武术第一次以新的功能被世人所发现和重视,在教育化、竞技化和社会化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全面启动了武术现代化的进程,实现了武术人角色从镖师、艺人、帮会成员等向教师、教练等的转换,为其以新的面貌融入国家社会发展打开了突破口。
2.2新中国武术的“体育”新平台
上世纪百年中,国家行政权力对体育不断强化,武术形式实现了从传统到竞技的转化,武术人的角色和处境也因之发生转变。
传统武术人的崇高志向在于“上马定乾坤”,但如今保障民族国家安全既无需上马,也无须左突右杀的一身武艺。时至今日,人类历史不可逆转的现代化进程在方方面面影响着武术,城镇化的侵蚀、多样化健身和娱乐方式的冲击等[10],这一过程在过去的一百年内从未停止。现代化使得武术与其孕育生发的时代(农耕社会)渐行渐远,使这一以格斗为本质特征的身体技艺成为“传统”。但幸运地是,一方面武术摆脱了民国时期裹挟于政治的困境,另一方面又因其负载着优秀传统文化而与国家行政体制更加紧密地关联。从这个意义上讲,武术被纳入国家行政体制内进行的竞技化发展就有着不容抹杀的积极意义。尽管学者对武术以西方体育为模式的竞技化多有苛责,强调武术与西方体育“异中之异”[11],走自己的发展道路。但无论如何,从民国到新中国,武术人最大的成就就是把武术从草莽民间托举到国家体育行列,在改变习武人卑贱身份的同时,使武术获得了更大更高的发展平台。
2.3市场经济中的受益者
武术作为商品出售古已有之,从宋代将“套子”搬入勾栏瓦舍之时,那些武术表演者就以之获益。此后武术人大多以“门户”为载体,通过“以徒养师”的方式获取生存资本。市场经济的出现则完全改变了武术传统的生存模式。
市场经济的运行逻辑起点是“出于个人私利而产生公共利益”[12],作为社会个体的武术人同样可以,也已经成为市场网络中的无数节点,在以武术为社会服务的同时满足了自身的利益需求。如今,武术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资源宝库,包含舞台表演、商业赛事、武校教育、影视作品等多种形式。武术经济功能的开发已经发展到产业化的程度,从个人到团体,从国内到国际,从核心产业到附属产业。在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的操控下,武术不再是保镖护院、好勇斗狠的手段,而是武术人获取经济资本的有机网络。在现代社会将传统武术人的“江湖”推出历史舞台之后,市场经济以公平和自由为原则,以外在法治和内在武德为约束,重构了一个新的“武林”,其中的“豪杰”可以是擂台之上拼搏的猛士,亦可是动作明星、武术教师、运动员,甚至是从中获益的经纪人。武术人从单一的以武谋生者深入到社会的多个行业和阶层,在使武术价值最大化的同时,也极大地扩展了武术传播的空间。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市场经济细化了以武术为核心的行业领域,使武术人从中受益,形成了推动武术多元发展的良性循环。
3各负使命的当代武术人
武术在新中国成立后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技术派”和“文化派”两类武术人,分别扮演者传承者和反思者的角色,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共同推动着武术事业的发展。
3.1技术派:技术传承与产业发展
一方面,技术派形成了当代竞技武术的生力军,促进了竞技武术的发展和传播;另一方面,他们为武术开疆拓土,成为武术发展形式从传统向现代转换的推动力量。
武校、体工队内的武术教练和学员是技术派的第一类。这些人经过多年的训练,大多具有丰富的经验和全面、过硬的专业技术,在武术方面有一技之长,因此,技术上的精英多出于此列。第二类是真正实现武术当代转化的生力军。清末至民国,武者从民间流向大城市,以开武馆、当保镖、当教员等各种形式尽可能地获取生存资本[13]。当下,他们从事与武术本体相关的多个领域,如官方运动队教练、俱乐部教练、域外武术传播者,影视演员等,有时兼具多重身份。尽管这一群体在武术各种形式的传播过程中或多或少地加深了“中国武术的负面形象”[14],但从长远来看,正是这批武术人为其以之谋生的武术实现了“产业升级”,换言之,他们在先前武术基本限于师徒之间形成的生产与消费关系之外,拓展了武术的生产形式,扩大了武术的消费群体和地域,成为现代武术产业化发展的先行者。
技术派的时代使命在于保存、创新武术本体。从武术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对武术的保存和继承是延续武术这一民族运动形式命脉的必然选择,而创新是适应社会变迁的根本之法。
3.2文化派:文化传承与发展反思
所谓文化派武术人,即以研究、思考武术及其发展为主业,以理论思辨见长者。高级者,不仅谙熟技术,同时具有较高的研究能力且醉心武术研究,致力于探求武术历史文化、关注武术现实发展。当前文化派武术人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似乎摆脱了传统武术人武而不文、知识匮乏的局限,但却遭遇知识结构不合理的滞碍。高等教育序列中的武术人较少学习理科知识,导致文化派武术人在其后的发展中长于质性探讨,短于量化研究。虽然已有不少学者通过吸收跨专业学生、组建多学科团队等法来弥补自身缺陷,但至少目前仍难以摆脱上述局限而真正实现学术研究的独立和强大。文化派武术人尽管有其客观局限,但其存在不无意义。民国武术人即通过著书立说力图证明武者亦能文[15],武术圈的“文人化”延续至今,成为一个突出现象。一方面是人才选拔制度使然,另一方面也是武术人占据高等教育这一高平台一席之地后壮大自身群体的必然选择。
文化派武术人的当代使命在于重建武术的文化谱系,也是其贡献所在。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从研究方法、范式等多方面积极借鉴多学科经验,将研究触角深入到社会学、人类学、西方中国学等当代显学领域并大有细化研究的趋势。武术研究取向的这一变化,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到今天论著的对比中显而易见。多学科研究呈现了武术文化棱镜的多个面向,在前人纵向观察的基础上,将武术文化研究进行了充分的横向剖解。从历史学的视角看,当下文化派武术人所从事的是以微观、中观的笔触对宏观武术史“概论式的判断”[16]的修正,是对武术历史文化分析的细化和完善。不可否认,文化派武术人在某些领域比较成功地实现了对人文社科研究者的僭越,拓展了武术人的生存空间。
3.3两派关系与社会分层
“文化派”与“技术派”的关系是一种特殊的文武关系。总体看,二者是依存共生的关系,有着服务武术发展的共同目标。技术派为文化派提供了思考研究的素材:传承、习练武术的人们构建的武术界种种社会关系,以及他们所习练、创新的技术动作,成为文化派研究的“田野”和进行各种力学分析、生理生化研究的样本。文化派的研究则反过来指导技术派的技术实践和生存认知。
武术界文武关系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阶层区分和阶层流动,尤其是在技术派仍存在官方与民间区分之时。民间习武者为自由武术人,进入官方体制则意味着“铁饭碗”,因此就产生了技术派由民间向官方的流动。另外,如英国人麦高温所观察,“在中国,当家中有男孩子出生的时候。几乎每个父亲都希望自己的儿子将来能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因为在中国,财富与荣誉的获得并不限于某一个特定的阶级,任何身份、地位的人都可以成为一名书生。……任何人都有可能获得国家授子的最高荣誉。因为在理论上——至少在理论上——通向荣誉最正当的途径就是教育。”[17]在国人这种传统认知下,民办武校向普通高校流动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也进一步加剧了武术人的文人化。技术优秀者致力于从单纯习武者到大学生的身份转变,以武术精专为旨归的习武目标,被通过进一步地深造获取更好生存条件的目标所弱化。因为学历的高低决定生存资本的多寡,因此产生高校以技术见长的本科生极力争取进入硕博行列的现象。社会学家郑也夫[18]对我国教育中存在的这种病症开出了药方:分流。但前提是被分流出高等教育行列者收入不能与受高等教育者差距过大。郑也夫的药方对中国教育一时难以奏效,但在武术界已有成功之例,技术派“出界跨行”之举就起到了明显的分流作用。不少技术派的武术人从运动员成功转型为动作明星(如:李连杰等),施展才华的同时获得比接受高等教育更多的财富、威望和社会地位,以一技之长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倘若有更多的分流途径和更大的成功可能,武术界的“文化派”与“技术派”则会形成真正和谐共存的局面。
4结论
“现时孕育、造就未来,从过去的遗产中经由当前创新而打造出来。”[19]为此,我们对武术人的社会生存做了纵向的梳理,尽管传统社会武术人生存状况不容乐观,江湖退却,但武术却没有消亡,反而因进入官方教育、竞赛体制,加之市场经济的引入而重获生机。武术人在进入现当代国家体制之后,获得充分的发展机遇,在武术的健身功能、文化名片功能、产业经济功能等被高度重视的今天,武术人也在自身“技术派”与“文化派”分化中担负着不同的历史使命。
武术的现代化归根结底是武术人的现代化,武术现代化过程中竞技化、产业化等种种现象是社会变迁的必然。作为武术人,一方面要以武术为本,保证武术本体的传承和创新,深入探究武术文化,反哺武术发展;另一方面,应吸取历史经验,避免武术界内部的文武相轻,为争取武术人更大的生存、发展空间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戴国斌.文化自觉语境中武术研究的探索与思考[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4,(5):67。
[2]张品兴.梁启超全集·第五卷[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1377,1385.
[3]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
[4]许友根.武举制度史略[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7:86.
[5]宋应星.野议·练兵议[A].收入氏.宋应星佚著四种[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27.
[6]龚鹏程.中国文人阶层史论·序[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1-35.
[7](宋)李昉.文苑英华·卷944·侍御史摄御史中丞赠尚书户部侍郎李公墓志铭[M].北京:中华书局,1966.
[8]Andrew D. Morris.Mirror of the Nation:A History of Sport and Physical Culture in Republican China[M].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133-147, 214-225.
[9]易剑东.民国时期武术社会化探析[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1995,(4):42.
[10]李文鸿.现代冲击与传统生存:一项高校体育教学的对比研究[J].中国成人教育,2014,(16):189.
[11]王岗,吴松.中国武术发展的当代抉择:“求同”乎?“求异”乎?[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2010, 24(2):35-39.
[12]詹姆斯·L·多蒂.市场经济读本[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1.
[13]林伯原.中国近代前期武术家向城市的移动以及对武术流派分化的影响[J].体育文史,1996,(3):16.
[14]李源,王岗,朱瑞琪.中国武术负面形象的形成原因及反思[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3, 36(9):33.
[15]李文鸿.民国时期武术的科学化变革[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4):138.
[16]杨念群.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自序[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7:5.
[17](英)麦高温.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M].朱涛,倪静,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45.
[18]郑也夫.吾国教育病理[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19]Archer, Margaret S.Taking time to link structure and agency[M].New Delhi:Ⅺth 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 (mimeo),1986.
From tradition to modernity: the social survival of martial artists
LV Si-hong
(SchoolofSportsandCulturalIndustry,QiluUniversityofTechnology,Jinan250353,Shandong,China)
Abstract: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nd logical analysis, we longitudinally examine the era character and status change in history development of martial arts people from the angle of civil-military contrast, and reflect on the present martial arts group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historical mission. Studies suggest that: 1) the martial arts group has experienced the state from being unified to split, from "outside the system" to "system". Transgression of martial arts people on the literati was an important feature in this process. 2) Social changes since the late Qing Dynasty made martial arts people out of the weak role in the ancient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and committed to making nation strong, and then got the new higher sports development platform. 3) Today, the differentiation of martial arts people are divided into 2 schools: the "technology school" and the "culture school". Both of the schools undertake historical mission of martial arts development together.
Key words:martial artists; tradition; modernity; survival; capital
作者简介:吕思泓(1969-),女,山东青岛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武术历史文化与社会变迁。
收稿日期:2015-09-14
中图分类号:G80-0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840(2015)06-001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