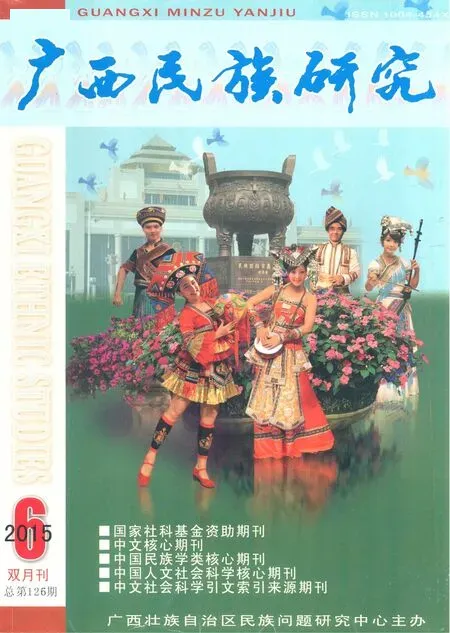中间权力网络与边疆多民族地区的治理现代化*
张 燚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边疆多民族地区的治理现代化,一直是中国国家秩序得以建立和维系的重要一环。相较于以往的历史阶段,当代中国边疆多民族地区的治理状况是最好的,但相较于边疆社会发展的需要而言,其又略显不足,“从纵向比较来看,我国的边疆治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好,但从横向比较的角度来看,边疆治理在国家整体发展格局中的地位却有所下降”[2],且不同边疆多民族地区的治理绩效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本文将围绕着“边疆治理差异”而展开,尝试着从“中间权力网络”的角度来探寻治理差异生成的原因,以及消弭治理差异的路径和方法。
一、中间权力网络: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组织基础
英语中的“治理”(governance)可以追溯到古典拉丁语和古希腊语中的“操舵”一词,原意主要是指控制、指导或操纵,与government 的含义互有重叠。“治理”的概念在20 世纪90年代以前并没有被学术界广泛重视,但自从世界银行在1989年发布题为“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的研究报告之后,有关“治理”概念和理论的探讨开始流行,而有关“治理现代化”的研究则尤为热门。然而,学者们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解却不尽相同,例如,俞可平教授认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公共权力运行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民主化”“法治”“效率”与“协调”;[3]何增科教授认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实现治理“民主化”“法治化”“文明化”和“科学化”的过程;[4]李景鹏教授认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要使“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适应现代社会发展对“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法治、自身成长和现代文化发展”的要求;[5]虞崇胜教授认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应具有“民主化”“法治化”“制度化”“科学化”“效能化”和“公平化”等六个特征。[6]
综上所述,已有的研究成果具有以下两个共同点:一是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包括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两个部分,二是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具有有效性与合法性两大特征,前者包括治理的“科学化”“效能化”和“公平化”,后者则包括治理的“制度化”“法治化”“民主化”。因此,笔者认为,所谓“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为满足现代社会的治理需求,进而实现有效治理的过程。从内容上来讲,“国家治理现代化”主要包括两部分,即国家治理体系——“国家制度”的现代化和国家治理能力——“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的现代化;从过程来看,“国家治理现代化”意味着公共权力的行使,有赖于国家与社会通过“协商”而实现的“分工与协作”,国家或者社会包揽一切的做法都将不利于治理现代化的实现;从结果来看,“国家治理现代化”意味着“有效治理”(或称“善治”)的实现和“无效治理”(或称“恶治”)的规避,前者与后者的不同在于是否能够同时获取治理的有效性与合法性。
从组织的角度来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有赖于现代化中间权力网络的建立和发展。众所周知,治理理论的兴起是以“治理空间的多样化”“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问题的复杂化”和“治理问题的风险化”为背景的,目的是为了借助国家与社会的分工与合作,来突破国家“治理能力的局限性”和“治理技术的单一化”。[7]因而,既不同于“依靠强制性力量,或者以强制为后盾来维护公共秩序”的国家统治,也不同于以“提供公共福利服务”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国家管理,国家治理强调通过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合作管理”来同时实现“维护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最大化”。[8]这意味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有赖于国家与社会的分工与合作,单纯地依靠国家公权力或者社会自组织,都无法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治理的有效性与合法性。在已有的相关研究中,大多数学者将注意力集中于国家公权力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例如,辛向阳教授提出的“以定型和强体为主线、以统筹和协调重大关系为前提、以法治和核心价值观为依托”[9]的治理现代化策略,而本文则主要从“中间权力网络”这一社会自组织的角度来分析和研究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所谓“中间权力网络”,是指介于国家与私人之间、具有“经纪”和“非正式政治”属性的组织体系,其目的是为了通过维护国家权威或保护社会权利而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根据其利益实现方式的不同,“中间权力网络”可以分为以下三类:一是权利型中间权力网络,即主要通过“法律”来维护自身权益,这主要包括政党、群众团体、企业和社会自组织等;二是权力型中间权力网络,即通过“暴力”来实现自身利益,这主要包括土匪、暴恐组织、黑社会、军阀等;三是传统型中间权力网络,即通过“习俗”或“文化”来实现自身利益,这主要包括宗教、宗族和同乡会等。不同的中间权力网络应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方式也不同,其中,依赖于“国家公权力”的权利型中间权力网络采取“积极参与”的方式,与“国家公权力”具有竞争性的权力型中间权力网络采取“对抗参与”的方式,独立于“国家公权力”传统型中间权力网络则采取“消极参与”的方式。换言之,传统型中间权力网络与“无政府主义”相契合,权力型中间权力网络与“国家统治”“国家管理”的理念相匹配,而权利型中间权力网络则与“国家治理”的理论相适应,因而,对于强调通过“协商”来实现国家与社会之间分工与合作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而言,其组织基础只能是权利型中间权力网络。
二、有效与相对有效:差异化的边疆治理绩效
如何对治理绩效进行客观、准确和公正的评价,是所有研究治理现代化的学者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不少学者和国际组织提出了诸如“元治理”“健全的治理”“有效的治理”和“善治”等概念,并围绕着这些概念提出了不同的评估标准,这对本文的研究将提供必要的帮助。例如,联合国就曾提出评价治理绩效的8 个标准,即同意、负责、透明、回应、有效、高效、平等包容和守法,①同意(consensus oriented)、负责(accountable)、透明(transparent)、回应(responsive)、有效(effective)、高效(efficient)、平等包容(equitable and inclusive)和守法(follows the rule of law)。参见联合国亚太经济与社会委员会(UNESCAP):What is Good Governance?。而有国内学者也提出了治理评估的6 大标准,即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和有效。[10]9-10国内外学者所提出的具体标准虽不尽相同,但却都围绕着治理的“有效性”和“合法性”而展开,这也将成为本文治理评估标准的核心。治理的有效性和合法性的不同组合,将会产生三种不同的治理效果:其一是有效治理,即同时实现有效性和合法性,建立起获得社会成员普遍认同的公共秩序;其二是相对有效治理,即实现有效性或合法性,要么建立起没有公众认同的公共秩序,要么获取没有公共秩序的公众认同;其三是无效治理,即有效性和合法性都没有实现,既不能建立起公共秩序,也无法获得社会成员的基本认可。由此不难发现,治理绩效的好坏取决于有效性与合法性的强弱,而治理的有效性反映在国家治理所涉及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治理的合法性则反映在社会成员的政治认同和政治行为。
当代中国的边疆多民族地区,主要包括东部边疆的黑龙江省、吉林省和辽宁省,北部的内蒙古自治区,西部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和甘肃省,以及南部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和云南省,而各边疆多民族地区的治理绩效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差异,基本上呈现为“东部和北部边疆强于西部和南部边疆”的格局。
一方面,从治理的有效性来看,东部和北部边疆要强于西部和南部边疆。所谓有效性,是指“实际的政绩”和“作用”,即“该制度在大多数人民及势力集团如大商业或军队眼中能满足政府基本功能的程度”,[11]53能够通过行政效率和社会经济发展表现出来。因此,要准确反映治理的有效性,就必须对行政效率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进行评估,其中,行政效率的状况可以通过一般公共服务支出②一般公共服务支出,主要是指保障机关事业单位正常运转,支持各机关单位履行职能,保障各机关部门的项目支出需要,以及支持地方落实自主择业军转干部退役金等。与公共财政收入、公共财政支出的比值来测量,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则可以通过国民生产总值的多少来衡量。
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来看(见表1),一般公共服务占各地方公共财政收入的比例,分别为内蒙古19.65%、辽宁14.99%、吉林23.10%、黑龙江21.83%、广西31.36%、云南24.50%、西藏189.99%、甘肃45.88%、新疆29.90%,北部和东部边疆4 省(区)的比值低于西部和南部边疆5 省(区);一般公共服务占各地方公共财政支出的比例,分别为内蒙古9.17%、辽宁9.65%、吉林9.74%、黑龙江8.28%、广西12.88%、云南9.64%、西藏17.80%、甘肃12.06%、新疆11.00%,北部和东部边疆4 省(区)的比值低于除云南省之外的西部和南部边疆4省(区)。一般公共服务占地方公共财政收入和支出的比值,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各地的治理成本,其比值越高则意味着治理成本越高,反之亦然,由此不难发现,东部和北部边疆4 省(区)的行政效率要低于西部和南部边疆5 省(区)的行政效率。此外,从各地近5年的生产总值来看(见表1),东部和北部边疆4 省(区)一直稳居边疆9 省(区)的前5 名,而西部和南部边疆5 省(区)中仅有广西的生产总值进入前5 名(2014年位列第3,其余年份位列第4),其余4 省(区)的排名则一直靠后。一般而言,较高的生产总值意味着较好的社会经济发展,而较低的生产总值则意味着较差的社会经济发展,由此不难发现,生产总值较高的东部和北部边疆要比生产总值较低的西部和南部边疆,具有更好的社会经济发展表现。

表1
另一方面,从治理的合法性来看,东部和北部边疆也强于西部和南部边疆。所谓合法性,主要是指一种“价值”或“信仰”,即“该制度产生并保持现存政治机构最符合社会需要的这种信念的能力”[11]53,并通过政治行为表现出来。在当代中国边疆多民族地区,治理的合法性可以通过社会成员国家认同的强弱来衡量,较强的国家认同意味着较高的治理合法性,较弱的国家认同则意味着较低的治理合法性。所谓国家认同,主要是指公民对于政治共同体的制度、价值和政治过程的认可,“是一个民族确认自己的国族身份,将自己的民族自觉归属于国家,形成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主体意识”[12]。从西方近代民族国家成长的历史来看,国家认同的出现是以国家参与社会资源的再分配为背景,并随着其对社会资源再分配能力的提高而增强,而当国家制度取代血缘和信仰成为社会资源再分配的主角时,社会成员对国家的认同也将超越其对家庭、民族和宗教的认同。
在当代中国边疆多民族地区,国家对社会资源再分配的能力不同,也使各地的国家认同呈现出差异化的格局。众所周知,政治心理影响政治行为,而政治行为则反映政治心理,“外部世界对人的影响表现在人的头脑中,反映在人的头脑中,成为感觉、思想、动机、意志,总之,形成‘理想的意图’,并且通过这种形态变成‘理想的力量’。”[13]324公民的政治行为大致可以分为积极与消极两种,其中,积极的政治行为包括参与选举、投票、纳税和协商等,其反映了公民对于国家治理的较高认同,而消极的政治行为则包括群体性事件、暴乱、恐怖袭击和种族屠杀等,其反映了公民对于国家治理的较低认同。相较于东部和北部边疆省份的平静,西部和南部边疆省份自20 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了一系列暴力恐怖事件,其中,具有代表性有新疆的“巴仁乡暴乱”和乌鲁木齐“7·5”暴力恐怖事件、西藏拉萨“3·14”打砸抢烧严重暴力事件、北京“10·28”暴力恐怖袭击事件①从地域的角度来看,北京“10·28”暴力恐怖袭击事并没有发生在中国的西部和南部边疆多民族地区,但却与之有密切的联系。和云南昆明火车站“3·1”暴力恐怖事件等。“暴力恐怖事件”的频发意味着,西部和南部边疆的“国家认同度”要低于东部和北部边疆,换言之,西部和南部边疆的“治理合法性”要弱于东部和北部边疆。
综上所述,较高的行政效率和较好的社会经济发展意味着,东部和北部边疆比西部和南部边疆拥有更强的治理有效性,较高的国家认同意味着,东部和北部边疆比西部和南部边疆拥有更高的治理合法性,而较强的治理有效性与较高的治理合法性表明东部和北部边疆比西部和南部边疆拥有更好的治理绩效。为什么边疆多民族的治理绩效会有差异?是什么帮助东部和北部边疆拥有更好的治理效果呢?又是什么导致西部和南部边疆形成较差的治理效果呢?这些问题的背后暗含着实现边疆治理现代化的“密码”,因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现存的治理差异,而且能够帮助我们找到边疆治理现代化的路径。
三、边疆治理差异形成的组织分析
面对边疆多民族地区治理绩效的差异,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从制度、经济和文化的角度予以解释。1.制度的解释。金炳镐教授、马大正教授、周平教授和陈霖教授等认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组织形式、实现形式、自治机关民族化和自治机关设置、民族区域自治法律制度及政策”等方面的创新不足,是形成边疆多民族地区治理差异的原因,[14]因而,部分学者主张在维护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国家根本制度的前提下,对以“族际主义”为特征的传统边疆治理政策进行调整,构建以“区域主义”为导向的边疆治理模式。①参见周平:《中国的边疆治理:族际主义还是区域主义?》,《思想战线》,2008年第3 期;陈霖:《我国边疆问题与边疆治理探讨》,《社会主义研究》,2009年第6 期。2.经济的解释。贺金瑞教授和李育全教授等认为,经济发展水平低是制约部分边疆多民族地区治理的关键因素,因此,要改善部分边疆多民族地区的治理状况,国家就必须通过政策扶持、资金投入和发展援助等手段加快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使少数民族地区及其少数民族群体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受益者”[15]。3.文化的解释。马戎教授、周平教授和王越平教授等认为,治理差异的形成源于边疆多民族地区不同的国家认同,较好的治理效果往往与较强的国家认同密切相关,因而,“政治民族意识的强化”或“多元民族文化的调试”将有助于国家认同的增强,进而提高部分边疆多民族地区的治理绩效。②参见马戎:《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1 期;周平:《边疆治理视野中的认同问题》,《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 期;王越平:《边疆治理与多元民族文化调适》,《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09年第5 期。
综上所述,“制度”“经济”和“文化”是国内学者研究边疆多民族地区治理差异的视角,其在边疆治理研究中具有各自的优势和劣势,这既为本文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基础,也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空间。一方面,政治制度的不同将会造成治理绩效的不同,但在各边疆多民族地区所推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自治制度并没有明显的差异,这意味着,通过制度来解释边疆多民族地区的治理差异是不妥的;另一方面,经济和文化的解释是最具迷惑性的方法,但其对治理绩效的影响并没有学者们所预期的强,萨缪尔·亨廷顿就曾发现,“暴力、动乱和极端主义行为”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比在经济较落后的地区更容易发生。[16]41这意味着,经济文化与治理绩效的相关性并不强。概而言之,“制度、经济和文化”的作用,是为边疆多民族地区的治理提供必要的外部条件,但其对治理绩效的影响是通过对治理主体的影响来实现的,这表明,制度、经济和文化对治理绩效的影响存在着滞后性和不确定性,而治理主体对治理绩效的影响则更直接、更确定。
本文认为,在当代中国边疆多民族地区,治理差异的形成主要源于各地区中间权力网络的不同。正如迈克尔·曼所说,社会并不是一个“匀整”和“单一”的整体,而是以“混杂性”为特点的互动网络,包含“意识形态权力组织”“政治权力组织”“军事权力组织”和“经济权力组织”之间的互动,影响着社会治理的效果。[17]3由前文可知,根据其利益和利益实现方式的不同,中间权力网络可以分为“权利型中间权力网络”“权力型中间权力网络”和“传统型中间权力网络”,三者在各边疆多民族地区的不同分布,是形成东部、北部边疆与西部、南部边疆治理差异的重要原因。诚然,不同类型的中间权力网络在边疆多民族地区都有存在,但不同类型的中间权力网络在不同地区的分布并不相同,这形成了中间权力网络在不同地区的组织生态,也造成了不同地区的治理差异。
从中间权力网络的角度来看,东部和北部边疆多民族地区比西部和南部边疆多民族地区拥有更好的治理绩效,是因为前者比后者拥有相对强大的权利型中间权力网络,以及相对弱小的传统型和权力型中间权力网络。1.从组成权利型中间权力网络的各种组织来看,政党组织和群众团体在各边疆多民族地区的分布是“均质化”的,但企业在各边疆多民族地区的分布却呈现“差异化”(见表2)。由表2 中不难发现,无论是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总数来看,还是从国有及国有控股、私营、外资和港澳台资工业企业的数量来看,东部和北部边疆的各省区都比西部和南部边疆的各省区要多,这意味着,权利型中间权力网络在东部和北部边疆要比西部和南部边疆的力量强大一些。

表2
2.从组成传统型中间权力网络的各种组织来看,民族和宗教组织在东部和北部边疆的影响要弱些,而在西部和南部边疆的影响要强些。在1950年7月21日上报的《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中,邓小平就曾指出,“西南的国境线从西藏到云南、广西,有几千公里,在这么长的边境上,居住的绝大多数是少数民族”,就其数量而言,“恐怕西南比西北还多,而且情况也比较复杂”,因此,“少数民族问题,在西南来说是很重要的”。[18]361以云南省为例,在1953年民族自报登记过程中,云南省上报260 多种民族名称,在1954年的民族识别工作中共确定21 个少数民族①分别为彝族、白族、哈尼族、傣族、壮族、苗族、傈僳族、回族、拉祜族、佤族、纳西族、景颇族、瑶族、藏族、布朗族、阿昌族、怒族、普米族、崩龙族(后改为德昂族)、独龙族、蒙古族。参见马曜主编:《云南民族工作40年》,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年,第51 页。和104 个未识别的群体②经过1958年和1960年的进一步识别工作,104 个群体中的56 个被归并到其他民族,其余的48 个无法确定具体归属。参见云南省民族识别综合调查组主编:《云南民族识别综合调査报告(1960)》,云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印,1979年,第1 页。,在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又识别出水族和布依族,[19]606至此,仅云南一省的少数民族数量就已达23 个。云南省的民族状况展现了西部和南部边疆民族问题的复杂性,也凸显了“民族”等传统型中间权力网络在西部和南部边疆多民族地区治理中的影响和地位。与之相反的是,历史上多次出现的民族融合,已经让分布于东部和北部边疆的少数民族与汉族没有太多差别,例如,周恩来总理在1957年发表的《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中就曾以“满族”为例指出过这种相似性,“满族采纳了汉族的文化,首先是文字,以后又逐渐采用了汉族的语言,把自己的语言文字丢了,好像跟汉族没有区别了,实际上还是两个民族”[18]503,这意味着,“民族”作为一种组织来参与东部和北部边疆治理的可能性已经不大。
3.从权力型中间权力网络的分布来看,其在东部和北部边疆的影响,要弱于在西部和南部边疆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分别在2003年、2008年和2012年认定了三批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其中,被认定的“恐怖组织”主要包括“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东突厥斯坦”解放组织、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和“东突厥斯坦”新闻信息中心等四个组织,被认定的“恐怖分子”主要包括第一批的11 名、第二批的8 名和第三批的6 名,而这些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全都来自中国的西部边疆多民族地区。此外,1959年流亡印度的第十四世达赖组建了以“分裂祖国、主张‘西藏独立’”为目的的“西藏流亡政府”,并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办事处”,不断策划和实施分裂国家的骚乱和暴乱,例如,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在1989年3月5日蓄意制造了“拉萨骚乱”,于2008年3月14日在拉萨又制造了“3·14”打砸抢烧事件。由此不难发现,来自于西部和南部边疆的恐怖组织和分裂组织,对该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都产生了消极影响;相比而言,来自东部和北部边疆的同类组织的影响就非常小,例如,“蒙独”组织的分裂活动仅局限于网络宣传和海外活动,并未能够升级为影响地方稳定的暴乱。
四、中间权力网络的重塑:边疆治理现代化的组织路径
在当代中国边疆多民族地区的治理现代化过程中,不同中间权力网络的应对方式截然不同,其中,传统型中间权力网络的“消极”和权力型中间权力网络的“对抗”都使其无法满足现代化治理的需要,而权利型中间权力网络的“积极”则使其能够成为现代化治理的组织基础。由此不难得出以下结论,即相对于传统型和权力型中间权力网络而言,权利型中间权力网络的相对优势越大,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程度就越高,相反,权利型中间权力网络的相对优势越小或丧失,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程度就越低,因此,边疆多民族地区治理现代化的实现有赖于建立并强化权利型中间权力网络的组织优势。而要在边疆多民族地区实现上述目标,就必须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一是促进“传统型”中间权力网络的转型和重构。宗教的世俗化和民族的现代化是传统型中间权力网络转型和重构的重要体现,也代表着未来传统型中间权力网络的发展趋势。正如南京政治学院汪维钧教授所讲,世俗化就是“非神圣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将涉及“社会”和“宗教”两个方面的变化,其中,社会的世俗化是指“人类社会各个领域逐渐摆脱宗教之羁绊”,宗教的世俗化是指“宗教不断调节自身以适应社会向‘世俗’变化的过程”。[20]所谓现代化,就是指“从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使农业社会所具有的典型特征转变为工业社会所具有的典型特征”,这主要包括,自然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社会固态转向社会流动、信息封闭转向信息传播,习俗惯例转向规章制度、乡村文明转向都市文明等等。[6]因而,宗教世俗化和民族现代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消除宗教和民族对于社会生活的支配,而是为了“以另一种形式来取代原来的支配形式”,以便能够更有效地适应和促进现代经济和社会的发展。[21]11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国家必须不断强化对传统型中间权力网络进行“政策引导”,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对合乎现代化治理要求的方面进行保护和对违背现代化治理要求的方面进行限制,其目的是为了使其能够更好地适应边疆治理现代化的发展和需要。
二是引导“权力型”中间权力网络走向分化和瓦解。随着边疆多民族地区治理的现代化发展,以恐怖组织、黑社会、邪教组织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权力型中间权力网络,将逐渐被社会所边缘化,这是由其自身特点与现代社会的内在冲突所决定的。所谓权力型中间权力网络,是指以“暴力手段”作为获取“政治权力”或维护“组织利益”的政治组织,其与作为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组织——“国家”具有内在的冲突,与渴望文明和法治的现代社会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权力型中间权力网络在未来的发展方向主要有两个:一是分化与转型,即权力型中间权力网络摒弃非法、暴力的手段,转而通过合法途径与合法手段来表达和维护自身权益,这意味着,权力型中间权力网络将转型为权利型中间权力网络或传统型中间权力网络;二是瓦解与式微,即权力型中间权力网络拒绝通过合法方式来实现自身利益,在国家机关的打击和社会成员的反对下走向衰弱,这意味着,权力型中间权力网络将逐渐被“边缘化”。权力型中间权力网络的内在特点——对暴力手段的依赖和对政治权力的觊觎,使其在任何历史阶段、任何地方都无法成为边疆治理的组织基础,其在某一时间或者某一地域的兴起并不意味着自身的强大,而仅仅是因为权利型和传统型中间权力网络的弱化。
三是鼓励“权利型”中间权力网络进一步发展。借助于国家权力的支持和帮助,权利型中间权力网络在边疆多民族地区占有数量上的优势,但由于缺少明确的功能定位而在质量上略显不足,因而,提高“组织质量”将是权利型中间权力网络进一步发展的方向,本文以“党的组织建设”为例予以说明。对于边疆多民族地区的基层党建来讲,“竞争意识”的增强和“双向耦合”的功能导向将是其进一步发展的方向。1.在边疆多民族地区,基层党组织应增强“竞争意识”。在实行改革开放之后,边疆多民族地区的基层社会生态发生了重要变化,原有的一元化社会被多元化社会所取代,包括宗教、民族、黑社会、暴恐组织、社团、民主党派等在内的组织与中国共产党在边疆基层治理中并存,这在客观上形成了“组织竞争”的局面。“组织竞争”的出现意味着,任何组织的壮大不再单纯地取决于政治权力的强制,而是取决于组织对社会成员的内在吸引力,任何缺少竞争优势的组织都将被其他组织所取代或弱化。因而,“竞争意识”将能使基层组织建设时刻保持清醒,使其能够不断适应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2.在边疆多民族地区,基层党组织应以实现“双向耦合”为目标。基层组织的外部环境大致分为“政权组织”和“基层群众”,这意味着,基层组织建设应同时处理好与政权、群众的关系,即“双向耦合”,否则,基层组织建设要么出现脱离群众的危险,要么出现弱化执政地位的危险。要处理好与群众的关系,基层组织需要平衡针对群众的“政治引领”和“社会服务”两大功能;要处理好与政权的关系,基层组织需要强化针对政权的“执政意识和能力”。要实现“双向耦合”的目标,基层组织建设应做出相应的调整,例如,基层组织队伍不仅要吸收具有政治觉悟的先进分子,也要吸收具有专业知识的先进分子,以满足对执掌政权和服务群众的功能。
[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R/OL].(2013-11-15)[2015-06-20].http://news.xinhuanet.com/2013-11/15/c_ 118164235.htm.
[2]周平.我国的边疆治理研究[J].学术探索,2008(2).
[3]俞可平.衡量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标准——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思考[N].南京日报,2013-12-10.
[4]何增科.理解国家治理及其现代化[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1).
[5]李景鹏.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四个现代化”之后的第五个“现代化”[J].天津社会科学,2014(2).
[6]虞崇胜.科学确立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衡量标准[J].中州学刊,2014(10).
[7]杨雪冬.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球背景与中国路径[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4).
[8]何增科.国家治理及其现代化探微[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4).
[9]辛向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三大路径[J].江西社会科学,2014(2).
[10]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11]西摩·马丁·利普塞特.政治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12]贺金瑞,燕继荣.论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
[1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14]金炳镐,龚志祥.论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的创新与发展的几个问题[J].黑龙江民族丛刊,2005(2).
[15]贺金瑞.民族发展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6).
[16]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17]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一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19]郭净,等.云南少数民族概况[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
[20]汪维钧.论现代化条件下的宗教世俗化问题[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4(4).
[21]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