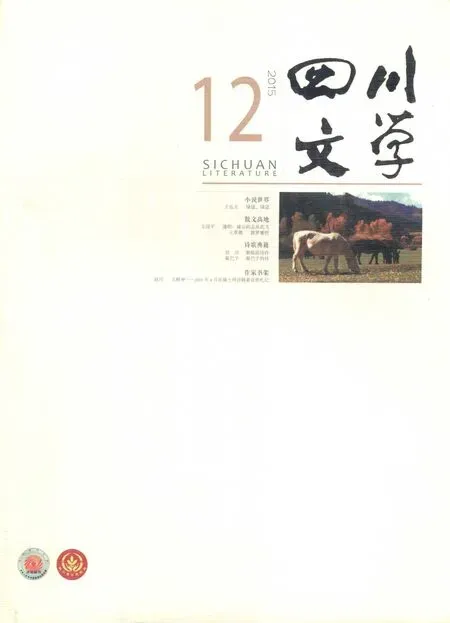家国往事
○ 尉克冰
一
我的曾祖父叫尉迟章。在我记忆里,他是个会唱戏、会糊纸人、会写一手漂亮毛笔字,习惯穿粗布衣裤的农村白胡子老头。他的胡须又长又密,如同老树发达的根须。
在他那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里,墙上挂的,地上摆的,全都是花花绿绿的纸人、纸马和纸楼,那是专门糊给亡者享用的,为了使他们在阴间的生活更加丰足。送葬那天,亡者的家属会把它们——烧在坟头。曾祖父心灵手巧,是个远近闻名的糊纸人能手,四里八乡的人只要是家里有了白事,都来找他糊纸人。他是有求必应,而且分文不取。
在小小孩童的眼里,曾祖父那双长满硬茧的大手好像会变戏法一样,秫秸秆儿、电光纸、毛头纸经过他的画、裁、剪、搭、粘、连一系列麻利娴熟的动作很快就能变成一个个栩栩如生、形象饱满的纸人,那些纸人全是穿着鲜艳的童男童女,脸上挂着甜甜的笑容,或许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将要被燃烧的命运。
那时候,我只有五六岁,只要一回老家,就会钻进曾祖父的小屋,趴在那斑驳的磨掉了油漆的八仙桌的一角,瞪大眼睛欣赏琳琅满目的艺术品和曾祖父制作纸人的过程。望着那可爱精巧的小纸人,有一次,我吵着曾祖父要拿来玩,可没想到的是,一向疼我爱我的曾祖父脸上立刻阴云密布,“这个不能玩儿,不吉利!”他的吼声如雷,吓得我顿时号啕大哭。自知失口的曾祖父又很快将我抱在怀里,用他那双带着硬茧的手替我把眼泪擦干,“乖孩子,纸人真的不能玩儿,老爷爷给你做个花风车好不好?”我立刻就会破涕为笑,全然不会注意到他老人家那昏花的眼睛里噙满的泪水。
儿时的我,真的不懂那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一提到要纸人的时候曾祖父会那样大动肝火,甚至还会伤心。只是自此后,就再也不敢吵闹着要纸人了,默默地惋惜着那逼真可爱的纸人刚来到世上就会遭遇被大火吞噬掉的命运。这或许是善良孩子最天真的想法。
直到后来,才知道其中缘由。
曾祖父还有个儿子,叫尉新泉,是爷爷的弟弟,我该称他二爷。1947年10月,二爷参了军,当时他只有16岁。17岁时,就凋落了年轻的生命,牺牲在解放山西临汾的战役中。
因为曾祖母总是固执地认为,二爷的死跟他小时候偷偷玩过纸人有关。这种观点或多或少影响到曾祖父。
“泉儿最聪明,最伶俐,可他咋就恁命短呢?这打仗的也有活下来的,他咋就一去不回了呢?该不会是因为小时候偷玩儿了纸人不吉利?这是给死人做的东西呀,你一个小孩子咋能玩?多好的孩子啊,说没就没了……”这是二爷刚牺牲的时候,曾祖母站在村西口,边张望边念叨的最多的几句话。
自那以后,曾祖父依旧热心地为乡亲们糊纸人,可他会把那间小屋牢牢锁住,不给任何孩子去触碰那些纸人的机会。
二
1947年,曾祖父把二爷送上了战场。
入冬了,夜来得很早。天上飘着细碎的雪粒,卷在北风中乱舞,洒落在街道上、房屋上和院落里。从邻居家的厩棚里不时传出骡子的嘶鸣声,或许是它饿了,或许是它感觉到冬的寒冷了。
北屋的煤油灯散发出淡淡的微弱的光,透过窗格上泛黄的毛纸,使得小小的院落并不显得那么黢黑。
曾祖父和曾祖母,盘坐在北屋的土炕上。屋内静得甚至能听得到豆大的火苗扑簌簌跳动的声响。他们相对无语,连呼吸似乎都是凝滞的,沉寂之外还是沉寂。
许久,曾祖父先开了口,“孩儿他娘,这次征兵征的是咱家老大,可我想好了,咱得让老二去。”他把声音压得很低。
“泉儿虽然娶了媳妇,可他毕竟还小,他才16岁,还是个孩子。”曾祖母眼里顿时淌出了泪水,她开始哽咽着,啜泣着。
“16岁,不小啦,咱泉儿是个好孩子,我刚问过他,这也是他的意思,他决定啦,要替他哥去从军。”
“可这兵荒马乱的,战场上枪炮不长眼,泉儿要是有个好歹……”她哽咽住了,“他可是你唯一的亲骨肉,是咱的独根呀……”曾祖母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早就泣不成声了。
“可是,咱从你姐手里把孩子接过来,就得让这孩子好好活着。海儿去了,要是有个好歹,咱咋跟姐交代?做人要对得起良心。”尽管他依然将声音压得很低,却显得很激动,说话的时候声音是颤抖的。
曾祖母默默无语了,只是流着泪。
“手心手背都是肉啊,俩孩子都是咱养大的,咱都疼。海儿憨厚,打仗斗的是智和勇,泉儿机灵,杀敌肯定是把好手,活着回来的希望也会大些……”曾祖父的眼圈红了,他使劲儿控制着眼眶里的泪水,尽可能不让它流淌出来。
这一切被恰好走到屋门口的爷爷听得清清楚楚,真真切切。泪水早就扑簌地往下落。
二十年来,他从来没有觉察出他是爹娘的养子。他时时刻刻都能体会到这个虽然贫穷但却充满幸福的家庭给予他的关怀和温暖。小时候,和弟弟拌嘴,爹总是责怪弟弟不懂事;发烧的时候,娘总是把热乎乎的汤端到自己跟前,一勺一勺地喂到嘴里;一次,到镇上去赶集,突然下起了大雨,爹打着油纸伞,深一脚浅一脚地趟着泥水走了八里路,到处喊着海儿,海儿。
这一幕又一幕,他怎能忘记?整整一夜,他难以入眠。尽管他憨厚木讷,对战争有着难以言说的恐惧,但他知道,他该怎么做。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他就跪在爹娘面前,坚决要求自己去应征。
可几天以后,穿上军装的依然是他弟弟。弟弟死活坚持,况且父命如山,他拗不过。
那是个月白风清的夜晚。一轮皓月高悬于夜幕之中,天空是那样的深邃,几颗暗淡的星星显得有些寂寥。
西厢房里,一对新婚的青年就要天各一方。
她依偎在他宽厚的胸膛前,静静享受着分别前最后的温存。他轻轻抚弄着她的发丝,她的脸颊,将她紧紧抱在怀里,仿佛一放手,就再也抓不回自己的爱了。
这一别,何时才能团聚?这一别,是否就会阴阳两隔?想到这些,她就心如刀绞,浑身战栗,泪水便如断线的珠子滚落下来。
他将她抱得更紧了。他是那样爱她,怜惜她。在他眼里,她是最完美的爱人,她娇美,温柔,善良,多情。她就像一只翩然的蝴蝶飞进他的世界,融入他的生命,化进他的骨髓。
此刻,他的心在滴血,可他不能落泪,他知道他的泪水会让她变得更加脆弱。
他将一面崭新的小镜子从怀里掏出来,在袖口上蹭了蹭,在她的眼前晃动着。于是,镜子中出现了一张面若桃花、清丽可人的脸和一张有棱有角、英俊帅气的脸。
“喜欢呗?”他轻轻拉住她,将镜子放在她纤细嫩白的手中。
旋即,两行晶透的泪水又从她明若秋水的眸子里淌出,弯弯曲曲在她白皙的脸上。
“妮儿,不能再哭了,哭红了眼睛可就变成丑丫头喽。等打完仗,太平了,俺就回家跟你好好地过日子。”他强装笑颜,轻轻抹去挂在她面颊上的泪花,又调皮地贴在她耳边轻声说,“俺得好好活着回来,爹娘还盼着咱给他们多生几个孙子呢。”
她终于又露出了笑脸,美得让人怜爱。
一阵鸡鸣声划破了拂晓的沉寂,他真的要走了。临行前,他给爹娘磕了三个响头。
村西口。曾祖父手双手捧着一朵大红花,那朵花在他手里微微跳跃着,在夕阳的映衬下,红得分外耀眼。他走到儿子跟前,将红花佩戴在儿子的胸前,像是为儿子佩戴了一团光鲜的圣火。他把目光移到儿子年轻俊朗的脸上,将儿子的眼睛、鼻子、眉毛、嘴巴仔仔细细端详了一番,目光里充满了无限的慈爱。他张了张嘴,想跟儿子说些什么,可什么都没说,千言万语都融在那对视交流着的目光里了。他捏了捏儿子的肩膀,使劲拍了两把,又把目光迅速从儿子脸上挪开。
那是一匹大个头的棕红马,曾祖父将二爷扶上了马背。
“好好干,不要想家。”
“放心吧,爹。”
曾祖母和二奶奶抱在一起,早就哭成了泪人。
一家人挤在送行的队伍中,敲锣打鼓声、嘈杂的说话声、妇女的哭泣声交织在一起。人群中,一双双的手紧紧扣在一起,难割难舍。他们都清楚,这是一场生离死别。
出发的号角吹响了,二爷已颠簸在马背上。
“照顾好爹娘和哥嫂,等我回家。”二爷扭过头,冲着二奶奶使劲喊着,泪水到底是流了出来。
马蹄声声,土路上扬起一阵狼烟,几乎吞没了血红的残阳。
远了,远了,任凭哭肿了眼睛的曾祖母和二奶奶踮起小脚,也看不到二爷消逝的背影了。
三
1948年,曾祖父拿着他亲手糊的穿军装的纸人,和曾祖母一起在村口迎接我二爷回乡。
盼星星,盼月亮,半年过去了,终于把儿子给盼回来了!可盼回来的是却是儿子冰冷的遗体,他再也无法叫声爹娘。
1948年4月,曾祖父接到二爷阵亡的通知。爷爷便从家乡赶着牛车到临汾去接二爷回乡。为了找到二爷,爷爷在新坟林立的山岭间找了三天三夜。挖开那堆黄土,二爷依旧安然地睡着。可他的身体,早已是千疮百孔。黑紫色的血,凝固在他的军装上。爷爷抚摸着二爷冰冷的身体,大声呼唤着他的名字,痛哭着。爷爷知道,是他可爱的弟弟用死换取了自己的生。
从山西临汾到河北老家,沿路村庄的乡亲们得知车上躺的是烈士的遗体,便自发为爷爷提供食宿。一程送到下一程,一村接过另一村,跟爷爷共同把二爷护送了回去。
遗体回乡了,热血留在了战场。
他还没留下后代,战争的火焰就吞噬掉他年仅17岁的鲜活生命。
一个人的苦难,或许容易改变。而一个时代的灾难,似乎注定了无法逃避。它需要无数生命为之作殉葬,作代价。在战争面前,生命向来脆弱得如同蝼蚁,不堪一击。
一个鲜活的生命从此凋零,换取了一张薄薄的革命军人牺牲证明书。
烈字第0018486号
尉新泉同志于一九四七年十月参加革命工作,在十三纵队卅八旅任战士。不幸于一九四八年四月十日在临汾战役光荣牺牲。除由我军奠祭英灵外,特怀哀悼之情报贵家属,并望引荣节哀,持此证明书向河北内丘县人民政府领取抚恤金及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其家属得享受烈属优待为荷。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第二野战军
司令员 贺龙
政治委员 邓小平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卅一日
通知书的背面,是表格,登记着二爷的基本情况。几十年过去了,那张由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政治部下发的牺牲证明书,已经被岁月侵蚀得破旧斑驳,躺在老家的一方旧匣子里,由我叔叔保存着。
从1951年开始,曾祖父每月向政府领取6元钱的抚恤金,直到1984年,曾祖父去世。
四
1960年,在曾祖父和曾祖母的反复劝说下,苦守二爷12年之久的二奶奶终于答应改嫁了。
自从踏进这个家门,二奶奶就没打算离开过,她深爱着二爷,深爱着这个家。当二爷牺牲的噩耗传来时,她根本无法相信那是事实。她身上还残留着二爷的体温,她脑子里印满了二爷的音容笑貌,她耳边回荡的全是离别时深情的悄悄话,她手里还握着那面锃亮的曾经同时照过两个人的小镜子。
二爷的遗体回乡时,她没有去接。她不敢面对二爷那千疮百孔的躯体,她无法承受失去爱人的剧痛,她害怕看到那个鲜活的生命从此变得冰冷无语。
她病倒了,粉嫩白皙的脸变得黯然失色,深陷的面颊和眼窝烘托出一双失神的大眼睛。她一天到晚反复念叨着我二爷的名字,重复着同一句话,“他说过要好好活着回家的,还说要多生几个宝宝。”泪便如泉水般从她的眼睛里溢出,打湿枕巾。
一年过去了,二奶奶整个人依然失魂落魄。
曾祖父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他已经失去了唯一的亲生儿子,再也不能让这个贤淑孝顺的儿媳有个好歹了。
“孩儿他娘,你再去劝劝泉儿他媳妇吧,人没了,可日子总归还是要好好过。”曾祖父长长地叹了口气,“打听着哪里有了合适的人家就劝她改嫁,咱家不说这个,泉儿如果在天有灵,也会答应的。”
曾祖母含着泪不住地点头。
二奶奶的床前,曾祖母坐了下来。
她一只手拉住儿媳的手,一只手怜爱地抚摸着儿媳凌乱的头发。
“菊子啊,娘知道你是个好孩子,怪只怪泉儿没这个福分。人死不能复生,咱活着的人都要好好的,泉儿在那边才能放心呀!”曾祖母一把搂住早已泣不成声的二奶奶,“不哭了,不哭了,邻村今天有庙会,咱赶会去。”
庙会上,曾祖母给二奶奶扯了好几块做衣服用的花布。
“喜欢呗?爹和娘已经托人给你打听了个婆家,那人家不错,孩子又能干又懂事!”
二奶奶放下那些花布,只是摇头。
这头一摇就摇了12年。12年来,她不允许任何人跟她谈改嫁的事情,一心孝敬侍候着爹娘。而曾祖父和曾祖母也早就把她当成亲生闺女一样疼爱着。
1960年,在那个极度饥荒的年代,曾祖父找到了一个最具说服力的理由,使二奶奶终于答应了改嫁。
那时,我爷爷和奶奶已经有了四个儿女。全家老少共九个人,一个个面黄肌瘦,皮包骨头。
村子里,不断传出哪家的孩子哪家的大人被饿死的消息。整个中国都处于物资奇缺、极度窘困的状态。
“闺女啊,咱家孩子多,摊上这年月,养活不了这么多口人了。”曾祖父狠狠地吸了口旱烟,“你娘给你打听了户人家,家里人少,条件还不错,你就听你娘的吧!”
“咱家会把你当成亲闺女打发出门,瞧,娘把蒙头红和花鞋都绣好了。”曾祖母边说边将包袱打开。
这一次,二奶奶终于点了头。她知道爹娘的良苦用心。
曾祖父为二奶奶置办嫁妆,打点着婚事,忙得不亦乐乎。
没过几天,在一片鼓乐声和鞭炮声中,大花轿抬走了我的二奶奶。她终于在曾祖父和曾祖母的关爱中,又一次找到了幸福。
我想,二爷在九泉之下,也一定是含笑的吧。
改嫁后,二奶奶每年回几次家看望我曾祖父和曾祖母。清明时,她也从不会忘记往二爷的坟头烧一把纸钱,添一抔黄土,放一束野花。
曾祖父和曾祖母也经常去城里看她,临出门时还会偷偷地往床单下压一点钱,那是他们从牙缝里省出来的。
如今,二奶奶已经80岁了,儿孙满堂,家庭和睦。提起那段往事,她依然刻骨铭心。
五
1984年,曾祖父永远离开了我们。
弥留之际,他突然睁大了眼睛,像是想起了一桩很重要的事情,他颤颤巍巍地伸出五个手指,翕动苍白的嘴唇。爷爷将耳朵贴在他的唇边,听着他竭尽全力从喉咙发出的最后声响,“五,五毛钱……还给邻居……韩家……”
痛哭声从小院上空盘旋而出,湮没了村庄冬日的沉寂。
那是一场感天动地的葬礼,几乎全村的男女老少都自发地为这位可敬的老人送行。
灵棚里,亲人们披麻戴孝,抚摩大红的棺材,哭得昏天黑地。灵棚外,悲怆的哀乐和凄凉的唱腔交织在一起,曾祖父的徒子徒孙们戴着重孝为他们的恩师唱了整整五天的戏。
没有统一的号令,没有事先的安排, 随着“起灵了”那声高亢的呼喊,全村几百名送葬的人竟不约而同下跪,呜呜的恸哭声顿时汇聚成一条悲痛的河流淹没了整个村庄。妇女们用手帕蒙住脸,长一声短一声地哭泣;有泪不轻弹的壮年男人张大嘴巴,失声痛哭;即使身子骨不硬朗的年近古稀之人也是捶胸顿足,老泪纵横。
曾祖父的一生,时时处处都散发出人格魅力的光辉,正因为如此,他才受到了全村百姓的缅怀和敬重。
他睿智广博,豁达诚信,宽厚仁爱。他只上过一两年私塾,却博古通今,才华横溢,成为乡亲们心目中的一部“大辞典”;他没有受过专门的戏曲培训,只通过看戏听戏就能掌握其表演技巧,做到融会贯通,游刃有余,在县内外组织成立了戏班子,带出了一大帮徒弟;他没有写作老师,却能创作出唱河北梆子用的剧本,《珍珠塔》、《红风传》、《忠孝节义》等等,在我们当地民间广为传唱;他生活并不富足,可“文革”期间,他能在节衣缩食养活全家老小的情况下,给需要接济的下乡知青送去珍贵的粮食;他没任何头衔,可乡亲们有了矛盾,却都乐意去找他,他三下五除二就能把事情处理得公平公正,令人心服口服;他失去了唯一的亲生骨肉,承受着中年丧子的巨大悲痛,从没有表现出过度的哀伤,他说儿子是为国捐躯,死得值!
在我家人和乡亲们的心目中,曾祖父就是一棵参天大树,有了这棵老树的庇护,心里才会更温暖,更踏实。因此,当这棵饱经沧桑的老树倒下后,整个村庄都会陷入悲痛中。
刺骨的北风,裹着白色的灵幡,飘在灰色的天空里。二百多人擎起放置棺材的巨大木架,像是擎起一座巍峨的高山,在哀乐声中缓缓前行。棺材顶部和四周堆放着素洁的花圈和用金银锡箔糊成的纸人纸马,还有一座精巧玲珑的纸房子。长长的送葬队伍像是一条游龙蜿蜒在去往墓地的路上。
六
我常假设,如果没有曾祖父和二爷当年的义举,或许就没有了父亲和我的生命延续,我们就不能享受到今天的幸福生活。
我怀着崇敬之情,从《内丘县志》里找到了二爷。他当年的铁血之躯,早已化成了一行细小的文字,静静地躺在书中。默默的,没有几个人知道。他太年轻了,参军还不到半年,实在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壮举,也没有成为众人皆知的英雄人物。甚至,就连他的相貌,我都不清楚。和他一起躺在烈士英名录中的还有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牺牲的将近一万名战士。这才仅仅是一个县,那么一个市、一个省有多少?整个国家有多少?我甚至不敢再去想那触目惊心的数字。我们今天所走的阳光大道正是铺设在他们的血肉之躯和累累白骨上!
我知道,千百年来,像曾祖父和二爷那样忠诚仁义的普通人有许许多多。时光的火焰和灾难的火焰可以吞噬掉他们的生命,但无法吞噬的是他们高尚的灵魂!
生活在安逸中的我们,要时刻让那灵魂成为照亮生命的一盏灯。唯有如此,才不至于迷失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