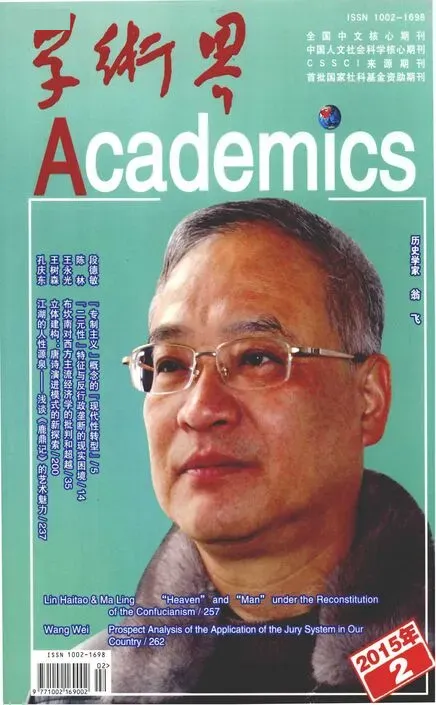翻译中可变之“门”〔*〕——《荒人手记》及其英译本的伴生文本〔1〕
○ 朱玉彬,陈晓倩
(1.上海外国语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上海 200083;2.安徽大学 外语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荒人手记》(以下简称《荒》)为台湾著名女作家朱天文的长篇小说代表作。1994年,朱天文创作了长篇小说《荒》,并一举夺得台湾地区第一届“《时报文学》百万小说大奖”的首奖。这部小说凭借其独特的同性恋视角、包罗万象的内容和优美的文字等文学特色吸引了众多读者与研究者的目光。小说出版后不久,便相继被译成了日文和英文。其中,英文版是由美国著名翻译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与妻子林丽君(Sylvia Li-chun Lin)于1999年合译完成,书名为Notes of a Desolate Man(以下简称Notes)。此译本印行当年,就获得了《纽约时报》和《洛杉矶时报》评选的年度好书奖,第二年又获得了美国的年度国家翻译奖(National Translation Award)。Notes之所以能够在美国得到众多英语读者的喜爱,除了原作本身的强大魅力之外,当然与译者高水平的翻译、出版商独特的设计、赞助商成功的宣传及推广是分不开的。本文旨在通过对《荒》及其英译本Notes两个文本各自的伴生文本成分进行系统性地比较研究——包括对内生文本(封面、宣传页、序言、注释、封底评价)和外生文本(原作者的演讲和译者的采访、书评、读者的评价)的异同进行比较,分析翻译活动参与人(如译者、出版商和赞助商等)是如何来设定具体的伴生文本成分的,从而探讨译作在获得广大目标语读者的喜爱之余,是否真实准确地传达出原作的思想内容及原作者的意图。
一、伴生文本与翻译研究
伴生文本(paratext)最初由法国文学评论家热奈特(Genette)在其1987年的法文著作Seuils(《门》)〔2〕中提出,此书于1997年被译为英文,英文书名为Paratexts: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伴生文本:阐释之门》)。热奈特将“伴生文本”比作一扇“门”、一个“不确定的区域”,〔3〕“它能够让文本在读者大众那里成为一本书”。〔4〕它“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其本质都是一种受制于外部的辅助性话语,专门为文本服务……”。〔5〕但是,伴生文本有时也会僭越自己的功能,玩起自己的“游戏”而损害文本的“游戏”,从而成为读者获取作者意图的一种障碍。〔6〕热奈特根据伴生文本与文本之间的空间关系将其分为内生文本(peritext)和外生文本(epitext)两类:前者与文本同时出现在书籍中,包括书名、封面、出版信息、序言和注释等;而后者并不直接出现在书籍中,主要包括对作者的采访、日记、访谈、书信、出版社的广告和海报等。〔7〕
近年来,国内外的专家和学者开始运用“伴生文本”这一文学理论研究翻译,并取得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其中,芬兰学者Kovala是研究译作伴生文本的先行者。他通过研究发现,芬兰1890-1939年五十年间出版的英美文学作品的伴生文本体现出“意识形态聚拢”(ideological closure)现象,即渗透在文化习俗中意识形态的统一过程,这些伴生文本都趋向“宗教—传统意识形态”(religious-conservative ideology),强调作品的思想内容及其对读者的化育(有时也有娱乐)功用。〔8〕后来,土耳其学者 Tahir Gürça gˇlar探讨了“伴生文本”对于翻译史的研究价值,指出通过研究诸如著译者身份和匿名等伴生文本成分,能够为译文的生成与接受提供更多有价值的观点。〔9〕英国学者Harvey对热奈特将外生文本限定为作者对自己作品的讨论、评价和宣传这一看法提出质疑,认为有必要将其他评论家和同时代作者发表的评论、编读来信(包括网站论坛上的讨论)甚至那些同类主题的其他评论都囊括进来,并提出用“粘连(binding)”这一术语代替“伴生文本”,然后他通过对三部同性恋题材小说原作和译作(英译法)中的“粘连”成分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在源语和目标语文化的意识形态处于相互竞争时,这些成分能够帮助读者了解翻译是如何与具体的文化语境联系起来的。〔10〕2012年,德国Peter Lang出版社出版了论文集《翻译的外围领域——翻译中的伴生文本成分》(Translation Peripheries:Paratextual Elements in Translation)。这本论文集共收录11篇论文,均来自巴塞罗那自治大学口笔译系2010年组织的国际翻译专题研讨会“翻译中的伴生文本成分(Paratextual Elements in Translation)”。这些论文大都借助个案研究的方法,探讨诗歌、歌曲和小说等体裁翻译中的伴生文本问题,发现与伴生文本有关的问题经常会成为翻译的核心问题。〔11〕
国内翻译研究者近来也逐渐开始将目光投向伴生文本的研究。在理论研究层面上,孙昌坤注意到译作序跋是评价译者、译作以及重构某一时期翻译规范的重要资料,只是他当时并没有在“伴生文本”的理论框架基础上开展研究。〔12〕肖丽指出,对伴生文本的研究能够揭示出单纯的译文研究未能完全说明的东西。〔13〕在伴生文本理论的应用研究方面,杨振和许钧从注释这一具体的伴生文本成分着手,以《傅雷译文集》第三卷为例,说明了译者直接阐释的重要性。〔14〕张美芳(2011)对影响新闻翻译中的超文本成分(即伴生文本成分)进行了基于实例的分析。〔15〕贺赛波和申丹(2013)通过女性成长小说的文类视角,对史沫特莱的小说《大地的女儿》汉译本的伴生文本成分(包括序、献词、插图和出版者等)进行分析,发现这些成分都直接或者间接与小说主题有关,强化了译作与社会语境的联系。〔16〕
在过去的研究中,“伴生文本”这一概念出现了泛化的趋势,不再以客观具体的话语为依托。本文则将伴生文本看成一个含有多种成分的“域”。换句话说,内生文本和外生文本的成分都须是客观存在的实体,而不是一些抽象的影响因素。在翻译研究中,研究者通过对伴生文本成分的综合分析,找寻出那些影响伴生文本生成的(潜在)因素,进而分析出一些有可能导致“伴生文本”这扇“门”变形的动因,从而能够更为全面地了解跨文化传播中作品的译介情况,拓展翻译研究的视角。下文将以《荒人手记》及其英译本的伴生文本为研究对象,分析其所传达的信息是否与原作的思想内容和原作者的意图相一致,进而探讨影响译文“伴生文本”的深层次因素。
二、《荒人手记》及其英译本的内生文本比较
(一)封面
《荒》的封面(图1)主要包括:图画、原作者手写的“荒人手记”书名和原作者签名。朱天文曾于1999年在英译本Notes出版的新书发布会上做了演讲《废墟里的新天使》,其中提到了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关于“新天使”的描绘:
眼睛注视着,嘴巴张开着,翅膀伸展着,他的脸朝向过去,看到灾难,灾难把残骸一个压一个堆起来,猛摔在他脚前。新天使好想停下来,唤醒死者,将打碎的东西变成一个整体。但风暴从天刮下,把他推往他背对的未来。他面前的碎片越积越大,高入云霄。〔17〕

图1 《荒》的封面

图2 Notes的封面

图3 耶稣受难图
本文认为该书封面图画设计的灵感正是来源于此,俨然一副“新天使”的面容。虽然男主人公自命为“荒人”,但通读全书,读者能够发现他并不是处于一种荒芜或荒凉的状态,小说主人公在经历了同性恋身份的自我承认、初恋、热恋、失恋和颓废之后,并没有一蹶不振,而是继续相信爱情,从沉沦于色欲到追寻“受贞之美”,再到学会“与寂寞共处”,来进行自我救赎。可见,整部小说虽然是以“荒”为书名,却走向一种“充实感”,彰显出整本小说的独特视角与核心内容。
葛浩文和林丽君合译的Notes封面(图2)也包括图画、书名、作者及译者姓名这些伴生文本成分,它们同样标新立异,较原著有过之而无不及。Notes封面上的图画类似于耶稣受难的形象(图3)。与原作封面上的图画相比,它具有如下一些明显的不同之处:(1)图画上的人物没有现出头部;(2)人物倒置;(3)人物身上插着七支箭(我们认为这七支箭象征着西方基督教中的七大罪〔18〕);(4)人物没有翅膀,体格显得非常健壮结实;(5)图画基本占据了书的整个封面。“倒置的人物形象”很好地展现出原作异于常人的视角,这一伴生文本成分很好地传达出原作的精髓,而图画上人物健壮的体格更符合西方人的审美观念。另外,原文将男同性恋者对爱情和人生的领悟过程比作是宗教上的得道和救赎,其中既有借助西方耶稣进行领悟——“我同类们的最伟大的原型,耶稣基督与一行十二门徒。”〔19〕也有借助佛教进行领悟——“……却怎么都变成了感情淬光之后的糟粕,一如唐僧抵达灵山渡河时骇见水面溜下死尸,是他脱掉的凡身俗骨。”〔20〕而译作显然是选择了前者中所描绘的宗教形象为原型来设计封面的图画,这是目标语译文读者更为熟悉的情景。我们认为图中人物身上的“七支箭”象征着西方基督教的教义,这里的处理主要从译文接受者熟悉的西方文化角度出发,使译作更加符合译文读者的期待视野。在书名方面,Notes的封面玩起了文字游戏,其形式是“notes of a desolate man”,与通常的英语书名不同,单词的首字母都没有大写,且字母的排列也是上下参差不齐,这种非常规的排版方式,暗示着与正常人不同的视角。
通过上述比较分析可见,出版社对译作的封面设计毫不逊色于中文原作的封面设计。它巧妙地利用了同性恋这一话题,以译文读者的文化背景和期待视野为导向进行设计,发人深省,吸引目标语译文读者的注意。
(二)宣传页
《荒》的宣传页上主要是对作者相关信息的介绍,包括作者肖像、家世与教育背景,她与胡兰成的师生关系,作者创作风格与著名作家张爱玲的相似性,作者的创作历程及主要代表作、所取得的文学成就及荣誉。宣传页特别指出作者师从胡兰成,在写作风格上与张爱玲相似,这反映出该书主要定位在华语文学圈发行,同时还强调这本小说作为台湾地区文学的代表,而这些都是为了吸引更多来自其他华语区的读者。
Notes的宣传页由于内容丰富,分列在书的前后,成为前宣传页和后宣传页。前宣传页从内容上看,并非出自译者本人之手。它一方面肯定了原作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对小说的主要内容也做了概括,旨在帮助读者理解该书。但英文前宣传页中有一句话:
Impressive in scope and detail,Notes of a Desolate Man employsthe motif of its characters’marginalized sexuality to highlight Taiwan’s vivid and fragile existence on the periphery of mainland China.〔21〕
(《荒》这部小说涉及面广,描述内容丰富细致,利用主人公边缘化的性取向来突显处于中国大陆边缘的台湾形象及其脆弱不堪的存在状态。)〔笔者自译〕
则明显表现出特定的意识形态倾向。朱天文本人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东亚系的演讲中说:“《荒人手记》里荒人的身份—— gay的角色,他既是一个隐喻的形象,整个也是一个寓言(allegory)。至于他隐喻了什么,寓言了什么,应是开放给所有的阅读者。我若对作品再多说什么,充其量都是后见之明,跟我创作的当时其实风马牛不相及”。〔22〕正像作者本人所说的那样,这部小说传达了什么,应当留给读者自己去领悟、去感受,而英文宣传页将原作的同性恋视角、文学价值和政治现状这些敏感的话题信息高度凝练,旨在吸引更多的欧美读者将目光投向这部来自台湾地区的小说,而违背了原作者的意图。
英文后宣传页在介绍作者时,列举她共有十五部作品出版,其中《世纪末的华丽》和《荒人手记》最为著名;她共获得五个重要的文学奖项,还在威尼斯和东京的电影节上获得了最佳剧本奖。此外,后宣传页也对两位译者作了详尽的介绍,以凸现他们在中文上的造诣和超卓的翻译技艺,从而向读者保证译文的质量。可见,前后宣传页中这些信息的设定都受到了译语文本所在的目标语文化语境中诸如主流意识形态和出版社促销需求的影响。
(三)序言
朱天文曾为2009年新版的《荒》写序。她在序中主要表达了三层意思:(1)是感慨简体字版《荒》出版的艰难;(2)是对老版及新版中内容调整的一些说明,认为编辑的用意是希望此作品能够脱离当时的语境,吸引更多的读者,但是她相信读者能够理解《荒》;(3)是对王德威教授将包括《荒》在内的一系列台湾优秀文学作品向西方宣传推广表示感激之情,并因此在Notes出版后去纽约作演讲,进而将她所看到的美国和书中描绘的台湾作了对比,认为两者都处在政治经济大变革的时期。整篇序有一半都在描绘美国,分析美国和台湾的异同,可见原作者还是希望西方读者能够认同自己的这部作品,看到台湾独特风情的同时,了解政治、经济、文化变迁是人类共通的经历。
译作的序言由译者撰写,旨在向译文读者传达他们在翻译过程中所采取的翻译策略。两位译者在序言中表示,他们在翻译过程中最关注的是可读性,〔23〕为了迎合译文读者的阅读习惯,适应目标语文化的意识形态,他们甚至不惜牺牲原作的语言特征,将标准的中文译为地道的英文,这样就在某种程度上不可避免地弱化了原作文字和句法的特色。例如,原作中有这样一段关于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黄巢的预言:“三七二十一,由字不出头,脚踏八方地,果头三屈律。”〔24〕译作直接将此句省略不译,只在注释中说明了原因,即中文独特句法的不可译性。此外,译文中的地名采用了台湾本地的拼法,这样则凸显出这部小说的台湾地域特色。可见,译者向读者展现出一个负责任的译者形象——尽量贴近原文,但为了方便读者阅读,以通顺的译法为主导,以适应英文读者的阅读期待。
(四)注释
中文原作没有注释,因此英译本的注释都是译者添加的。译者在序言中就对自己注释的方式做了简要介绍:凡是需要详细说明的地方,无论是原作叙述中的文化和历史的细致微妙之处,还是作者故意留下的空白,译者都在小说最后提供了尾注。〔25〕但是究竟在何处加注,译者并没有给出明确的标准,因此译者加注仍带有一定的随意性。
经过细读全书之后,我们发现全书共有28个注释〔26〕:7个是关于中国大陆及台湾的一些政治现象,7个是与中国文化相关,2个是关于日本电影和漫画的解说,剩下的都是关于西方宗教文献和文化的解说,注释的简况如表1所示:

表1 Notes中的注释简况表
虽然《荒》中有不少对西方的描写,但涉及到的传统神话、佛教和道教思想等诸类的中国文化元素的描述要远远超过西方文化元素,因此书中很多地方都需要加注说明。但对于原作中某些具有中国文化内涵的词语,译者采取了简单的直译方式,并没有加注给予任何说明,如“我只有诵着自己的经,经曰,西湖水干,江潮不起,雷峰塔倒,白蛇复出”,〔27〕译者只将其译为“I could only recite my own sautra,which went:The West Lake dried up,and there were no more waves.The Leifeng Pagoda fell,and the White Snake reemerged.”,〔28〕并没有对《白蛇和许仙》这一经典的中国神话故事做任何解说。译者如此处理,虽然没有给读者带来太多的阅读负担,确保了译文的可读性和连续性,但我们还是认为这一做法不免会削弱原作可能传达的信息。中国人都知道,白蛇和许仙一个是妖、一个是人,二者的结合是不为世俗所接受的,这在某种程度上与同性恋者之间的爱恋有一定的相似性,而译文这样处理就失去了这层意义。可见,译者确有为了译文的可读性而弱化中国文化元素的对外传播之嫌。
(五)封底评价
由于原作封底没有任何内容,因此本文只讨论Notes封底的评价。从Notes的封底可知,以国立台湾大学外文系副教授、哈佛大学讲座教授、哥伦比亚大学语言文明系教授王德威为理事的出版社编辑部(编辑成员还有台湾大学外文系著名教授齐邦媛等)将朱天文的《荒》、王祯和的《玫瑰、玫瑰,我爱你》(英文版为Rose,Rose,I love You,译者同为葛浩文)和郑清文的《三脚马》视为中国台湾地区现代文学的杰出代表并积极向外推介,这一评价彰显出这些作品的重要文学价值,出版社希望通过这些评价吸引更多的英文读者。
三、《荒人手记》及其英译本的外生文本比较研究
(一)作者的演讲和译者的采访
朱天文在题为《来自远方的眼光》〔29〕的演讲中表达了对文学“创作者”的独特见解:
……创作者是做什么呢?创作者是一群带有异样眼光的人。他看见了某些东西,把它截取出来,呈现在我们前面。他是把我们习以为常的眼前熟悉事物,予以“陌生化”(alienate)的一种人。
是的,陌生化。
陌生化提供了不同的眼光,不同看世界的方式……〔30〕
从此上述界定,可见朱天文担当起了创作者的责任,她希望用《荒》中独特的视角向读者展现一些他们早已习以为然的事情,就是要写给那些愿意去思考、有鉴赏目光的人看,强调了该作品所呈现的“不同”视角。
而译者在力求展现原作内容的同时,并没有原作者那么大的野心,主动去左右读者“看世界的方式”,反而有附和读者原有视角的倾向。正如葛浩文在接受采访时所指出的那样:国外出版商和编辑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英美读者的阅读期待和阅读习惯,“译者交付译稿之后,编辑最关心的是怎么让作品变得更好”。〔31〕因此,要想让《荒》这本以一位同性恋为主人公,描绘台湾当下人民和社会的一本富有哲理的小说成功地进入西方世界,就必须要让英语读者好之,呈现出他们所乐见的内容,而这些无疑都与原作者的意图有些差异。
(二)书评
外生文本的书评,主要是指文学评论家撰写的作品评论,特别是指用学术化的语言撰写的专门针对特定文本的评论。在有关《荒》的书评中,台湾著名文学评论家施淑的《〈荒人手记〉决审意见:文化工业下的个性店》一文颇有影响。〔32〕而关于Notes的书评,最有代表性当为美国汉学家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2000年在美国《今日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 Today)杂志上发表的书评。〔33〕通过比较这两篇有代表性的书评,本研究发现在关于作品的解读方面,两位学者在诸如生命诠释、官能书写和精神孤独等方面达成了共识,但就是否仅仅为同性恋题材的作品却产生了分歧。施淑认为《荒》中的同性恋叙述者代表的是被边缘化的女性官能写作,具有一定的女性主义含义,同时叙述者虽然是生命的一个个体,但他却揭示了整个人类的性和权力这一普遍关系,总之她并没有将《荒》完全看成一部同性恋题材的作品。而金介甫却恰恰相反,他将Notes看成是一部专门以同性恋为主题的作品,并将其与白先勇的《孽子》以及俄国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进行对比,指出《荒》在创作中的不足之处。这两篇20世纪写作的书评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撰写者身处的文化语境:由于美国社会对同性恋现象的认识已经比较成熟,所以他们可以直言不讳地畅谈这一话题,而当时的华语圈对同性恋现象的认识程度并没有欧美那样深入,所以还有所保留。但是不论如何,这两篇书评作为外生文本对读者的阅读心理有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三)读者的评价
现代社会已进入了互联网的大数据时代,我们很容易通过互联网搜集到读者大众的反应和评价。其中,网络书商的网站是普通读者评价最为集中的地方之一。在中文语境下,本研究从当当网上〔34〕搜集到1539条中文读者关于《荒》的评价,其中不少人表示这是一本比较难懂的著作,但是绝大多数读者都为朱天文的文字造诣所折服,认为她传承了张爱玲的写作风格,甚至有人大呼,张爱玲离开了我们,幸好朱天文还在。而关于同性恋这一话题,大多数读者认为朱天文把这种情感写到了极致,发出了同性恋的情感和异性恋的情感没有丝毫不同的感叹,同时呼吁人们应当理解和包容他们。可见,在中文语境中,《荒》所刻画的同性恋形象得到了读者的正面评价,而其情感也引起了读者的共鸣。在美国的亚马逊购物网站,〔35〕本研究共搜到9条读者评论。这些评论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情况:(1)两位读者高度评价了原作者的写作技巧和美学造诣;(2)四位读者谈到了小说的“同性恋”描写,其中一位予以肯定,另外三位都觉得描写不够真实;(3)三位读者做了较为全面的评价:三人都觉得Notes叙事宏大,贯穿东西,涉及文学、哲学、文化和台湾生活等众多话题,其中两人还联想到自己已经读过的文学作品,但由于觉得译文有不少地方有误解、粗糙和乏味之处,两人遗憾未能阅读原作。
从评论的数量上看,Notes在美国远没有达到轰动读者的效应。从评论的内容上看,无论是原作读者,还是译作读者,他们主要都是从“同性恋”、文化和文学的角度去阅读朱天文的这部作品,并没有太多地去关注国外出版社刻意强调的“社会政治”视角(当然这可能与只有9条海外读者评论有关)。此外,一些海外读者所谓译作“难读、粗糙和乏味”的原因,一方面可能与原作的内容涉及范围之广和汉语语言的独特性有关,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译者注重“可读性”的翻译策略,导致汉语文字和句法特色的弱化及注释的匮乏,从而导致读者阅读时产生的遗憾。
四、结 语
一部翻译作品的完整话语空间是由伴生文本和译文共同建构,从历时的角度看,因为译文产生于原作之后,是原作的再次传播,因此译文的伴生文本成分大多会比原文的更为丰富一些。这些丰富的伴生文本成分,构成了一张复杂而隐秘的网络,需要研究者条分缕析地去探究这些成分与文本之间的关系。美国翻译理论家韦努蒂在论述文化身份形成时指出:一部译作的效果除了依靠译者采取的翻译策略之外,还受到其在接受语境中遇到的各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页面布局、封面设计、广告样本、评论家观点、译本用途、读者的阅读方式与教师的教学等。〔36〕韦努蒂提到的这些因素都可以看成是伴生文本成分,它们与文本相互作用,共同对译作的接受和传播起作用。
伴生文本通常是读者接触文本之“门”,这扇“门”在翻译过程中无疑会受到目的语文化语境的影响,从而可能会发生“变形”,进而可能对目标语读者的阅读产生影响。本文通过对《荒》及其英译本Notes中伴生文本成分进行系统性地比较分析,发现翻译活动参与人在设定目标语文化语境中伴生文本的相关信息时,主要以译文读者的期待视野和主流意识形态为导向,而这种做法有可能会影响译文读者对原作思想内容和原作者意图的理解。从本研究可见,我国今后推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时,都需要重视对出版文本的伴生文本相关信息的设定,从而让这些伴生文本成分更好地发挥对读者阅读文本的预期影响作用。
注释:
〔1〕对法国文学理论家热奈特(Gérard Genette)提出的“paratext”这一术语,国内研究者有诸如“副文本”、“准文本”、“超文本”和“衍生文本”等多种译法,我们在本文中将其译为“伴生文本”,因“伴生”指“一种事物伴随着另一种事物一起存在(多指次要的伴随着主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39页〕,所以这种译法比较贴合“paratext”这一概念本身的意义,具体见本文第一部分“伴生文本与翻译研究”的阐述。同时,我们还将热奈特提出的“paratext”的下位范畴“peritext”和“epitext”分别翻译为“内生文本”和“外生文本”,因为它们都是从文本衍生出来的一些伴随文本。
〔2〕Genette,G.Seuils.Paris:Edition du Seuil,1987.
〔3〕〔4〕〔5〕〔6〕〔7〕Genette,G.Paratexts: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Translated by J.E.Lewin).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p.2,5,12,410,5,405.
〔8〕Kovala,U.Translations,paratextual mediation,and ideological closure.Target,1996,(1),pp.119-147.
〔10〕Harvey,K.Intercultural movement:“American Gay”in French Translation.Manchester,UK:St.Jerome Publishing,2003,pp.177-221.
〔11〕Gil-Bardají,A.,Orero,P.& S.Rovira-Esteva(Eds.).Translation Peripheries:Paratextual Elements in Translation.Bern,Germany:Peter Lang,2012.
〔12〕孙昌坤:《译作序言跋语与翻译研究》,《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
〔13〕肖丽:《副文本之于翻译研究的意义》,《上海翻译》2012年第4期。
〔14〕杨振、许钧:《从傅雷译作中的注释看译者直接阐释的必要性——以〈傅雷译文集〉第三卷为例》,《外语教学》2009年第3期。
〔15〕张美芳:《翻译中的超文本成分:以新闻翻译为例》,《中国翻译》2011年第2期。
〔16〕贺赛波、申丹:《翻译副文本、译文与社会语境——女性成长小说视角下〈大地的女儿〉中译考察》,《外国语文》2013年第1期。
〔17〕〔19〕〔20〕〔22〕〔24〕〔27〕〔30〕朱天文:《荒人手记》,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第232、31、67、226、192、111、219-220页,着重号强调为笔者所加。
〔18〕在西方中世纪和后来的基督教神学中,骄傲(Pride)、贪婪(Covetousness)、淫欲(Lust)、嫉妒(Envy)、贪食(Gluttony)、愤怒(Anger)和懒惰(Sloth)被视为人类的七大罪(Seven Deadly Sins)。凡是流露出这些罪孽的人们都要被打入地狱,他们唯有真心诚意地忏悔,才能获得救赎。对这些罪孽的描绘常出现在西方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艺术作品中,具体参见艾布拉姆斯(Abrams,M.H.):《文学术语词典(中英对照)》(第七版),吴松江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70-571页。
〔21〕〔23〕〔25〕〔26〕〔28〕Chu,T.Notes of a Desolate Man(Translated by H.Goldblatt& S.L.Li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9,inside front cover,preface,annotations,pp.167-169,88.
〔29〕《来自远方的眼光》系1999年《荒》英文版出版时,朱天文在科罗拉多大学东亚系的讲稿。《荒》的初版并未收录,在本文中将其归入外生文本的范畴。
〔31〕李文静:《中国文学英译的合作、协商与文化传播——汉英翻译家葛浩文与林丽君访谈录》,《中国翻译》2012年第11期,第59页。
〔32〕本文将《荒》参评台湾地区首届“《时报文学》百万小说大奖”获得的评审意见作为广义上的书评,全文参见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2788944/。关于《荒》的两篇评审意见,在1994年的版本有收录,后出的新版删除了这两篇评审意见。
〔33〕Kinkley,J.C.Review of Notes of a Desolate Man by Chu T’ien-wen.World Literature Today,2000,74,(1),pp.234-235.
〔34〕http://product.dangdang.com/20573203.html(2014年3月14日)。
〔35〕http://www.amazon.com/Notes-Desolate-Man-Chu-Tien-wen/product-reviews/0231116098/ref=sr_1_1_cm_cr_acr_txt?ie=UTF8&showViewpoints=1(2014年3月14日)。
〔36〕Venuti,L.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Towards an ethics of difference.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1998,p.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