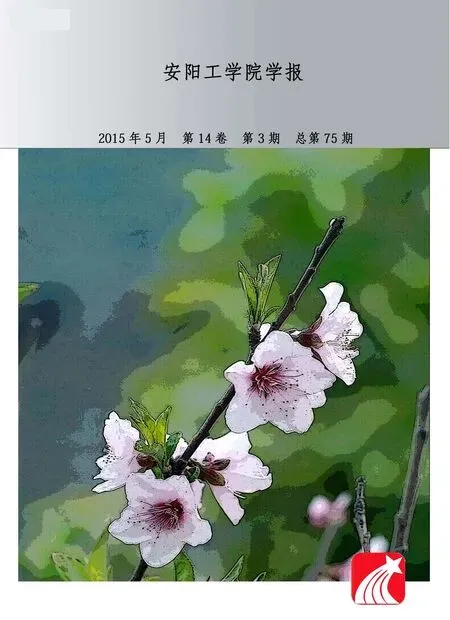女性视域下的乡土经验书写
——萧红《呼兰河传》与聂华苓《失去的金铃子》的比较研究
欧阳蒙(郑州大学文学院,郑州450001)
女性视域下的乡土经验书写
——萧红《呼兰河传》与聂华苓《失去的金铃子》的比较研究
欧阳蒙
(郑州大学文学院,郑州450001)
萧红《呼兰河传》与聂华苓《失去的金铃子》这两部乡土抒情小说以女性不同阶段的情感、心理体验,深刻地观照了乡土女性的苦难命运,但是写作语境的不同又使她们的情感书写具有明显差异。本文从两部小说的言说策略、生命形态、女性境遇等角度来分析其乡土经验的书写异质,并总结其乡土抒情小说的美学意义。
女性视域;乡土经验;《呼兰河传》;《失去的金铃子》;创作比较
东北作家萧红和台湾作家聂华苓虽属于不同年代、不同地域的女作家,但其笔下的乡土书写却有着相似的美学特征。1940年12月,萧红由重庆去往香港逃难,生活的贫瘠、战争的恐惧、肺结核的病痛、再遭遗弃的绝望使她轸怀儿时生活的呼兰河小镇。她深情回望沉滞的故乡,写出了颇具地域色彩的《呼兰河传》,以此来慰藉漂泊的灵魂。《失去的金铃子》写作同样具有类似的经历,1960年聂华苓遭受到台湾政局的“白色恐怖”专制:《自由中国》被查封,雷震等杂志部同志以“涉嫌叛乱罪”身陷囹圄。聂华苓遭受跟踪并失去维持生计的来源,与丈夫情感不合等坎坷使她濒临崩溃,“我成了一个小孤岛,和外界完全隔离了。那是我一生中最黯淡的时期:恐惧,寂寞,穷困。我埋头写作。《失去的金铃子》就是在那个时期写出来的。”(《失去的金铃子·写在前面》)
萧红和聂华苓是喧嚣时代中颇具个性的边缘作家。她们虽然身处政治社会变革的特殊时代,在主流文艺观念的教化下并未泯灭个人经验(一个是20世纪40年代大陆主流文艺倡导的“革命、抗日、反帝”等主题的战时文学,另一个是20世纪50、60年代台湾“战斗文艺”运动、“国家文艺体制”所倡导的具有政治情结和复仇情绪的“反共文艺”),萧红与聂华苓自觉疏离于主流意识形态之外,在国家民族话语的书写夹缝中,以女性化的原乡体验和美学追求,来观照乡村女性的命运悲剧,对她们的情感体验与心理状态进行了细致的刻画,并揭示了其深受父权制传统观念奴役的历史宿命。但是写作语境的差异又使她们情感书写略有区分,本文从两部小说的言说策略、生命形态、女性境遇等角度来分析其乡土经验的书写异质。
一、性别化的情感言说策略
女性作家往往凭借独特的性别体验,书写出女性不同年龄段的情感特质。她们以童趣、叛逆等情绪规避现实生活的残酷,使作品荡漾着温馨的诗意与别致的情怀。《呼兰河传》记录了萧红贪玩搞怪的童年时光:秋冬时节储藏室寻宝的惊喜好奇,春夏时节后花园的瞎闹折腾。她随性无忧,吃黄瓜、追蜻蜓、采倭瓜、绑蚂蚱,“把韭菜当作野草一起地割掉,把狗尾巴当作谷穗留着”[1]118,播种时踢飞祖父下菜种的土窝;浇菜时用水瓢往天空上撒雨;学诗文时震耳欲聋地喊叫;祖父训导时当耳边风地无畏;赶鸭子时贪馋好吃的窘态……萧红不仅刻画孩童顽皮、可爱、执拗的性情,还描写了贪馋天真与逗趣慈爱的祖孙俩。这一老一少稚拙憨直的陪伴,表达了萧红对祖孙间温馨情谊的真挚缅怀。在俏皮野趣的回忆里,又有着女性特有的敏锐洞察力。未经世事的顽童看到了成人世界中蒙昧卑琐的生命:敦厚愚直的有二伯、尴尬幸福的磨倌、马虎麻木的漏粉条的人、被折磨惨死的小团圆媳妇……成人世界的荒谬让年幼的主人公真切体验到成长的孤寂。长大后,萧红为追求自由爱情遭受命运的巨大打击,疾病、贫穷与漂泊几乎贯穿了她的一生,成人世界的疼痛使她怀着深沉理性来回顾童年,盎然的童趣掩盖不住女性由女孩到女人的寂寞创伤。“我家的院子是荒凉的”,后花园疯狂肆虐地生长背后是寂寞而苍凉的人生体验,渗透着辛酸的身世感与世态炎凉的绝望感,也有着萧红无法摆脱女性“他者”从属地位的荒芜感。
与《呼兰河传》天真的童年视角不同,《失去的金铃子》以十八岁少女青春期的细腻、躁动、惆怅的内心感怀,讲述了女孩子成长的经历。“成长是一段庄严而痛苦的过程,是一场无可奈何的挣扎。”[2]207青春期的苓子桀骜不驯,有着少女攀比爱美的天性,偷偷兜着红花围巾与假想敌比美,对滑稽丑陋的自己懊恼自卑。十八岁的她懵懂地憧憬爱情,一方面挖空心思地讨取尹之舅舅的信任与赞赏,“那滋味并不好受,人忽忽悠悠,还得打起精神作懂事的样子,懂人生,懂文学,懂每一个人,懂一切他感兴趣的事物。那确是一场费力的挣扎”[2]45,另一方面反感于其老气横秋、自作聪明。当别人说破她心中情愫时,又有女性特有的做作矜持,装模作样对尹之舅舅做出怒嗔与奚落。身处青春期的苓子,随着性意识的逐渐苏醒,渴望着尹之舅舅的身体。日渐成熟的她表现出对情欲、婚姻、生育的冲动、反感与羞涩等复杂态度。
“自从来到三星寨以后,我好像就由单纯中分裂,在个性的裂纹中挣扎——挣扎着成长,那不是我在一群啁啁啾啾的女孩子之中所能感受到的。”[2]63单纯少女经由暗恋而蜕变,这种成长并不是喜悦而是落寞。女性本能的敏感使苓子无缘无故地苦闷、心神不宁地猜测。当苓子发现尹之舅舅与巧姨的秘密时,因嫉妒引起的报复行为令她得意、痛快。虽有对攻击巧姨的负疚,但女性的矜持与骄傲仍拒绝帮助尹之舅舅。最终,尹之舅舅身陷冤狱,巧姨的宽容理解使苓子清醒,“我经过了一场战争,不论胜败,战争已经过去了,我真正自由了,不为任何情绪所苦了,只是为自己而活着,根据我内心的真理,沉默而严肃地活着。”[2]188苓子在成长中窥探出成人世界的人性本相——善于矫饰阴暗面的小姿态,尤其是女性在恋爱时猜忌、怨恨、自私、虚伪等复杂人性。单纯快乐的少女因爱经历了忧郁、浮躁、嫉妒、悔恨、稳重的情感蜕变。阅历成长之痛的苓子日渐成熟,她毅然告别过去,追寻踏实的生存意义,对女性身份的认同就是苓子求证存在意义的精神历程。
二、边缘化的生命存在形态
萧红与聂华苓或以启蒙视角或以文化视角来自觉疏离政治主流话语,在碎片化的情节、缓慢的叙述节奏中,蕴藉着她们对生命的边缘性思索。《呼兰河传》中呼兰河镇人因对生死无知而得过且过地苟活,“一年四季,春暖花开,秋雨,冬雪,也不过是随着季节穿起棉衣来,脱下单衣去地过着。生老病死也都是一声不响的默默地办理。”[1]92他们狭隘闭塞,如贴药膏一样,随意马虎应对安于现状。他们痛骂新学堂冲撞龙王爷,恐惧拔牙洋医生的广告,宁愿拆墙、种树就是无人愿意填平带来灾难的泥坑。他们平静中愚昧,迟缓中麻木,“风霜雨雪,受得住的就过去了,受不住的,就寻求着自然的结果。那自然的结果不大好,把人默默地一声不响的就拉着离开了这人间的世界了。”[1]104呼兰河镇人以“人间这样的人多着哩!”的冷漠来对待疯子、傻子,恻隐之心在“活着是一文不值”的观念中消磨丧失,他们无视丧子的王寡妇、染坊学徒的杀人案、造纸房饿死的私生子等悲痛,仍旧苍白、单调地匍匐于大地上。
萧红以启蒙理性来审视国民精神痼疾,但饱尝战争辗转流亡之苦的她,又感怀于百姓那命如草芥的挣扎意志。这些糊涂的生存群相尽管可笑可鄙,但仍能发掘他们以生命为基点的生存价值。《呼兰河传》呈现了底层百姓碎屑庸常的柴米油盐生活:野台子戏、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等庙会节场上,百姓之间谩骂调情、说媒骂俏、闲聊家常;接姑娘唤女婿的热闹;姐妹妯娌间礼节的周到;绅士明目张胆的偷窥;男女私订终身的反抗;孩童贪玩耍赖的倔强;集市上琳琅满目的小货摊;火烧云下的老人喂猪唠嗑、祖母驱蝇抚孙、孩童叫嚷民谣等都真实触摸到淳朴与污垢并存的民间风貌以及原汁原味的日常生活。他们夏夜闲聊、秋忙收割,为活着本身而生存,他们在混沌的生命轮回中有着近似麻木的坚韧。特别是朴质到有些迟钝的冯歪嘴子,他淳朴诚挚,慷慨热情,心疼爱怜妻儿,含泪哀求祖父施舍住处。他受人奚落又坦然为儿子包走食物。当王大姑娘产后而死,他恪尽抚育幼子的责任,以自己羸弱的肩膀承担起卑微但实在的生活,这正是萧红对“地之子”本分地承担生存职责的肯定。
与萧红笔下庸常、混沌的生命形态不同,聂华苓则肯定于生命所体现的顽强与生机,尤其崇拜女性庄严的生育经历。《失去金铃子》中苓子旁观新姨临盆,“我没想到年轻的小母亲,除了青草、月亮、星子、蓝天之外,还会与死亡有过这么凶险的搏斗,还会与油布、脚盆、污血、汗水有关系。”[2]114她歌颂女性在肉体刑罚中孕育新生命的奉献精神。苓子感叹于女性承担生育痛苦的愤怒与顽强,“一个生命挣扎着活下去,另一个生命挣扎着要出来”[2]118,母爱不论贵贱,“贵妇也好,娼妓也好,只要她生过孩子,她就应该和圣母一样受人供奉和赞美。”[2]120母亲承担着繁衍生命的神圣使命,这也是女性最崇高的生存价值。聂华苓对生命感悟还体现在对三星寨人原始的山野活力,以及普通百姓“人就是为了好好活着而活下去,一分一秒都不放过”[2]84执拗的生存信念的还原。“山呀,风呀,树木呀,流泻的蓝光呀,都还是原样儿,而我经过了世世代代的生与死,突然才记起原来我也是它们的同类。”[2]126在历史更迭、世事无常中生命表现出经久不衰的力量,日军轰炸的残垣断壁上存在着形形色色的生命:他们仍旧玩猴把戏、斗蚱蜢、赤膊捧酒、裸脚背柴,像往常一样庸常繁劳地过日子,“那就是生活,简单扎实的生活!流汗,拼命,喝酒,女人,调情,睡觉……死后躺在破祠堂外,苍蝇停在枯黄的头发梢上”[2]82,平实的生活中波动着混沌、自然的生命韵律。同样,面对死亡,苓子也没有悲戚感伤,“我望着那只死人的手,感到生命在身子里汹涌着,像一道喷泉。”[2]201她更加感恩短暂的生命,也更坚定了积极进取的决心。
三、荒谬性的女性生存境遇
女性天生处于懦弱压抑的地位,是男性随意施暴的对象。她们是礼教枷锁的主人和奴隶,她们极力维护男权社会模式,以父权社会所建构的文化秩序来塑造、扭曲自我。萧红笔下的女性是柔弱卑贱的,即使有女性以死来抗争不公平地位,也逃脱不了礼教所规范的妇道标准即“温文尔雅、孝顺公婆”的节烈颂名。就连祭拜娘娘庙前也要先去老爷庙“报道”,“可见男人打女人是天理应该,神鬼齐一。怪不得那娘娘庙里的娘娘特别温顺,原来是常常挨打的缘故。可见温顺也不是怎么优良的天性,而是被打的结果。甚或是招打的缘由。”[1]116神明信仰也要遵循于“男尊女卑”的等级伦理观念。萧红把婆媳矛盾置于无聊麻木的社会氛围中,来抨击社会制度和家庭制度的不合理。处世未深的十二岁小团圆媳妇倍受乡村伦理、家规妇道、社会积弊的钳制。她笑呵呵的天真活泼被众人诬陷为不懂羞耻、伤风败俗。当她赤身裸体被热水烫晕,围观的看客却没有怜悯心,而是咀嚼着小团圆媳妇遭毒打的痛快,“到底是开了眼界,见了世面,总算是不无所得的”[1]165。女性身为受害者并没有结盟,而是相互指责、控制,尤其体现在传统婆媳关系上。当“小媳妇熬成婆”,受虐者就会变成施虐者,颐指气使处处维护自己的权威。小团圆媳妇的执拗天真成为婆婆调教毒打的理由。“打猫,她怕把猫打丢了。打狗,她怕把狗打跑了。打猪,怕猪掉了斤两。打鸡,怕鸡不下蛋。惟独打这小团圆媳妇是一点毛病没有……她又不会下蛋,反正也不是猪,打掉了一些斤两也不要紧,反正也不过秤。”[1]161女性生命卑贱连动物都不如。当小团圆媳妇疯掉时,婆婆不惜花掉攒省的钱寻求秘方、跳神赶鬼、抽贴画符、下厨焙肉,对媳妇荒唐地百般关爱,只因媳妇是花很多钱买来的,不能赔本。她扪心自问并不谴责自己的暴虐,而是“她一生没有做过恶事,面软、心慈,凡事都是自己吃亏,让着别人”[1]161,理直气壮地怨恨老天爷的不公,最后只能以“前生没有做了好事,今生才找到了”[1]162聊以自慰,迷信且愚蠢。萧红通过描写女性的困窘生存状态,真实地挖掘出女性深受男权话语灌输而浑然不觉的悲剧宿命。
聂华苓也同样塑造了以封建男权话语戕害同类的女性形象,如黎姨妈整天埋怨咒骂,为了男人与新姨勾心斗角,并利用女儿的青春让其嫁给哮喘病人来赚取钱财。还有挑拨是非的玉兰姐,软弱的庄家婆婆等等。但聂华苓更关注的是封建法理对女性独立意识的窒息——她们自觉以无形精神枷锁压抑自我,养成循规蹈矩的守旧惯性。漫长父权制对女性精神的奴役,消磨了她们反抗的锐气。因此,在新旧夹缝中,她们左右失据于纲常名教与个性解放。《失去的金铃子》中聂华苓塑造了无法彻底逃离封建心狱的女性——巧姨。她犹豫纤弱,渴望自由和幸福,但没有勇气彻底挣脱封建枷锁的牵制。在宜昌读了几年书,受现代文明熏陶的她,却奉从父母之命嫁给了一个鸦片鬼。她年轻守寡,孝顺公婆,忙碌操劳,寂寞单调的生活吞噬了巧姨的青春,“又是那副专心、满足的神态,捶着那条细瘦的腿,一下下的,单调,有节奏;是的,单调,有节奏,在出殡的旧马车里,在昏暗的暮色中——那就是她的生活!”[2]27她反感枯燥守寡地生活,偷偷染指甲、带野花,与尹之舅舅遮遮掩掩传递情愫。但巧姨并没有与传统伦理秩序决绝的勇气。她恐惧死后丈夫鬼魂报复,摆脱不了内心的谴责与战栗。当巧姨与杨尹之的私情被发觉,她吞金自杀未遂而遭软禁,对自由人性的渴求变得万念俱灰。最后,她服膺于自己的命运,“不过你明白自己你就是生在那间黑屋子里的人,要跑也跑不出去的。我不要跑了。……现在我比那和尚的道行还高,不用门,不用锁,我也不会跑出去了。”[2]185她奋力挣脱最终主动退回。巧姨的爱情悲剧展现了新旧时代女性困顿于家庭、不能爱、不敢爱的精神状态,以及女性在挣扎道路上遇到的传统积习、社会现实等阻力因素。
萧红与聂华苓痛恨女性依附地位,她们以清醒的女性主义立场塑造了敢于追求自我的女性形象,以女性主体的独立、觉醒意识完成了对男权话语的批判与超越。呼兰河镇的王大姐虽着墨不多,但颇具反抗意识——她大胆追求婚姻自主,淡漠传统世俗观念。其可贵的自主意识,正是女性要求独立、追求自我的先决条件。王大姐不受封建伦理礼教桎梏的约束,没有扭捏造作的虚假,充满了朴野清爽的活力。她热情豪爽,能说能笑,风火响亮,“那声音才大呢,好像房顶上落了鹊雀似的。”[1]192;她健壮能干,提筐摘蔬菜,打水种地都比男人有力气。她爱美讲究,“她那辫子梳的才光呢。红辫子,绿辫梢,干干净净,又加上一朵马蛇菜花戴在鬓角上”[1]192。王大姐为追求自我幸福,敢于反叛旧礼教,与冯歪嘴子同居。大胆叛逆的举动使她倍受旧社会奚落,当她与冯歪嘴子自由结合,邻人便由“兴家立业的好手”、“膀大腰圆的带点福相”、“一棵大葵花”的夸赞变成败坏道德,有伤风化、蛮横泼辣、懒惰暴力、“没见过一个姑娘长得和一个扛大个的似的”、“说话声音那么大,一定不是什么好东西”[1]194的讥笑嘲讽,甚至编造冯歪嘴子上吊自刎引发了滑稽可笑的观闹。生活贫困与环境冷漠使得王大姐更加坚韧坦荡。她和冯歪嘴子相亲相爱,相濡以沫。不管旁人如何立传鼓吹,造谣生事,她并没有因传统伦理指责而有所顾忌退缩,而是在众人指指点点里释然自在地过活。“冯歪嘴子还是照旧的拉磨,王大姐就剪裁着洋花布做成小小的衣裳”[1]198,两人平稳安宁地过着柴米油盐的生活,平静地承担着生活给予的苦闷与欢欣。王大姐的幸福婚姻生活表达了萧红对女性自我意识苏醒肯定,以及对和谐真挚男女婚姻关系的向往。
《失去的金玲子》中的丫丫和苓子,是给陈腐的三星寨带来光明的敢爱敢恨的女性。天真野性的苓子,“我就是这么一个执拗的人——执拗地爱,执拗地活着,执拗地追寻。”[2]127她有桀骜不驯的反叛性格,敢于向传统秩序挑战。她潇洒随性、放荡不羁,穿着阴丹士林衫子,搭在眼睛的头发呼的向后甩,像男生一样吹口哨,爬树偷吃枣子。直率的她悄悄爱上了善解人意的尹之舅舅,她大胆逞强屡次试探杨尹之对她的感情。当窥视到尹之舅舅与巧姨的私情,女性强烈的占有欲和醋意使她“告发”了庄家姨爷爷。巧姨对苓子的释怀与理解,女性之间的惺惺相惜使少女苓子不断成长为真正的女人。她目睹了三星寨女性荒谬的生存状态与不幸历史宿命,迫使她急切逃离异乡女性萎缩的生存现状,“啊,真好!浪、风、太阳,都好!我恨不得一脚就跳上那条船!”[2]203重新选择了超越自我的新征程。丫丫是另一位独立倔强的女性,她敢于反抗不合理的婚姻,厌恶母亲与新姨明争暗斗、争风吃醋的同性斗争,不顾一切与郑连长出逃封建旧家庭。私奔的她经历了生存与情感的磨砺,清醒地摆脱了附庸男性的柔弱地位,毅然拒绝郑连长并回到家乡。但她不能容忍封闭陈腐的三星寨,选择了再次出走——对女性个体空间与社会空间不懈地追求,去重庆求学掌握自己的命运。苓子、丫丫这些新型女性敢于挣脱传统的牢笼,挑战男权话语秩序,大胆追求爱情与幸福,彰显了女性独立的自我价值与主体意识。
萧红与聂华苓两部乡土抒情小说以细腻的抒情文笔和强烈的自传色彩,呈现了偏僻地域的情感生活。她们伤感于东北三省与长江三峡的烽火狼烟的凄惶状况,以自我关切情感来洞察乡野女性在民间传统与男权文化压抑下的生命情状。她们突破狭窄的女性视角,真实琐碎地展现了乡野大地的生死轮回、世态生相、岁时风俗、风土人情,淡化主流政治话语的宏大叙述,凸显了女性话语方式的性别化特征。她们对人文关怀和创作个性的坚守,丰富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文化内涵。
[1]萧红.萧红选集[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
[2]聂华苓.失去的金铃子[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责任编辑:王念选)
I06
A
1673-2928(2015)03-0018-04
2015-04-01
欧阳蒙(1990-),女,河南周口人,郑州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