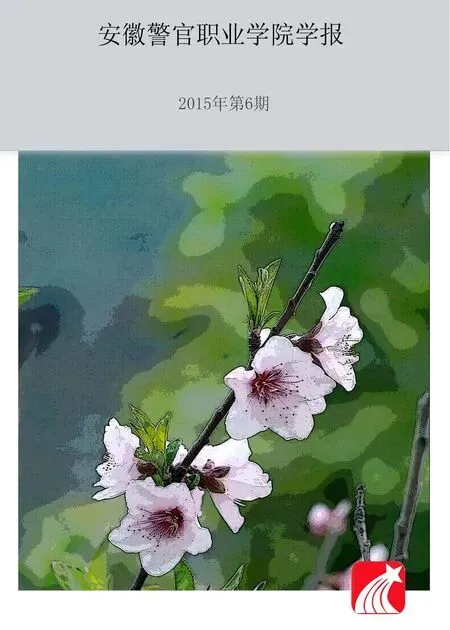民警在治安调解中的效力分析
申政伟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 100038)
民警在治安调解中的效力分析
申政伟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 100038)
治安调解作为警察行政管理中的一项重要职能,对维护社会治安、稳定公众情绪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基层公安民警愈来愈多地面临着在处理治安违法的同时需要附带解决由此产生的经济纠纷,具有化解群众矛盾、厘清经济纠纷作用的治安调解被广泛运用于治安执法过程中。然而,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治安调解与人民调解、诉讼调解的效力并未实现有机衔接,有必要厘清应对之策。
治安调解;司法效力;警察中立
警察职能的公共性,决定了警察处理民事纠纷引起的治安案件的重要性。随着我国公安队伍规模的扩大和执法环境的改善,民警通过治安调解化解民众日常生活纠纷以维持正常社会秩序的作用日显凸出。仅以治安案件的接警立案为例,民警在处理治安违法事件时因打架斗殴、债务纠纷、农民工讨薪等涉及财产分配、赔偿数额的纠纷最为普遍。依据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具备调解条件的治安案件同时也具备行政处罚的要件,而通过调解这种纠纷解决机制可以达到和平化解纠纷、迅速结案的目的。与治安处罚手段彰显的惩罚性不同,民警主持的治安调解具有增强民众满意度、节省办案资源、效率高等优势。因此,民警在办案过程中灵活运用民事调解来处理社会危险性较小的民事侵权、经济纠纷,不仅可减轻办案压力,这种在行使公权力中的附带性做法也贴合民意。
就治安调解的效力而言,其与一般民事调解的效力在法律上并未做明确的区分,而我国目前仅有对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后达成的调解协议允许司法确认产生司法效力的规定[1],至于治安调解后的调解协议能否参照 《人民调解法》的规定产生司法效力,法律并未予以明确,实践中的做法也不统一,常常出现调解后一方当事人反悔从而导致调解协议无法得到有效履行,直接造成治安调解制度的落空。
一、民警在治安调解中面临的问题
从民警日常接警情况来看,案源多为通过电话救助、受害人报案,民警要在第一时间做出询问后判断是否受理。在外来务工人员较多的地区,打架斗殴、债务纠纷引起的治安违法案件占了绝大比例。对涉及此类经济纠纷的案件怎样作出迅速处理、避免纠纷恶化以及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考验着办案民警的执法能力与办案效率。目前,民警在治安调解中面临的问题主要有:
(一)办案任务重
对治安案件的受理属于对此区域拥有行政管辖权的基层派出所,在部分管辖区域较广的地区,民警人均接警案件数量较大,而在治安案件处理过程中,以经济纠纷引起的治安案件多以社会危害性小,违法人员主观恶性不大而无需进行治安处罚,在此前提下,只要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民警通常会建议双方做调解结案,调解已成为一种对轻微违法案件的迅速处理机制。行政处罚由于涉及对公民私权利之干涉所需法律程序较为繁琐,以基层派出所的职能权限来看,超出权限范围需向其所属公安机关审查批准。①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派出所仅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作出警告或500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除此之外,不能以自己名义作出(应以设立该派出所的公安机关名义作出);拘留的行政处罚,派出所无权作出。治安案件要严格按照法律程序经历立案、笔录、审查、作出处罚决定。对于受理案件的民警,需要投入更多精力来完成整个案件处理的过程,以此保证处罚决定的法律正当性。作为受处罚的公民,如果认为公安机关对其所做的处罚决定有程序或实体上的违法时,有权对此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诉讼。然而,治安调解则免去了程序上的繁琐与规范性上的严格,虽然有作为公权力的公安民警的参与,但调解依然遵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民警在调解过程中更多的是扮演“中间人”的角色,公平公正的澄清案件事实,说服双方在各自立场上做适当让步以求达到双方意思一致的调解协议而顺利结案。可以看出,目前以经济纠纷为主要原因的治安案件呈上升趋势, 由此造成公安民警的工作量加大,办案压力可想而知。
(二)群众的支持
目前我国解决纠纷的方式与机制很多,公民可以私下和解,可借助社会第三方机构调解或者依法提起诉讼解决。在众多的调解机制中,私下和解的法律形式欠缺,第三方和诉讼造成的额外成本过高,民众在遭遇治安纠纷时更倾向于向公安民警求助以“主持公道”。以工业化的经济开发区为例,这里往往是外来务工人员的聚集区,他们的法律意识较为淡薄,在遭遇不公正对待或者民事纠纷时往往选择向其所属区域的公安机关求助。受侵害人寻求民警出面的目的是在于通过调解能够达成可行的经济赔偿,对于侵害人而言,其也不愿面临行政上的处罚因此“伤和气”而更倾向于调解。民警在权衡案件性质后也会尊重双方意思选择调解,以此处理违法性质较轻的民事侵权案件,提高执法效率,发挥节约司法资源稳定社会关系的作用。此外,纠纷当事人选择公安机关来处理此类案件往往隐含着对调解外诉讼结果的不确定性与诉累的心理障碍,希望有一个双方都能信服的主体站出来即由公安机关 “主持公道”。在这种环境下,公安机关作为“理”的支持者为说理一方提供权力形成的心理庇护,从而促成治安案件得到妥善合理解决。从治安案件的增多与民众对于调解的意愿来看,调解在缓解了民警办案压力的同时,也不失为纠纷的快速解决渠道。
(三)调解的风险
由公安主持达成的调解协议是否能够作为一份效力完整的合同在一方违约时向法院提起给付之诉产生强制执行力?[2]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对此存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治安调解应当与人民调解委员会做出的调解协议法律性质相当可以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从而要求一方当事人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义务;另一种观点认为,治安调解虽形式上类似于第三方调解但案件性质涉及行政法律管辖并欠缺第三方调解所具备的中立性特征,因此不宜作为一份有效的合同审理。[3]笔者认为,由公安机关主持达成的调解协议在具备合同生效所需条件情形下理应当作一份真实有效合同来对待,但从公安工作实际出发,多数情况下双方达成调解协议有赖于公安机关作为调解参与方形成的强制性心理约束,合同有效的重要条件之一在于双方的意思表示真实,公安机关参与调解是否对一方当事人做出民事行为产生行政权力压力或者负面心理作用无法通过证据得到有效认定。[4]此外,站在纠纷当事人立场,过错较大一方对公安机关的建议可能存在某种程度上的畏惧心态,面对行政处罚与调解的权衡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倾向于通过调解解决。但是,在此过程中,过错方对调解的支持具有妥协性,很难说明当事人对调解持有完全真实的意思表示,而调解过后认为不公平会造成自身利益受损因而出现不积极履行调解协议的情况。可见,公安机关参与调解却无权力执行调解,从而可能导致架空调解协议的履行。
二、民警参与调解与合同见证人概念辨析
民警参与治安调解的前提,是行使法律所欲赋予的行政职权。《治安管理处罚法》第9条明确规定,“对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的行为”,如果情节较轻可以通过调解达成协议作不予处罚决定,且在调解不成或者调解后反悔情形下可就先前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给予行政性质的惩罚。可见,公安参与调解的主要作用在于履行行政职能,对于违反调解协议的当事人只能发挥行政手段予以制裁,对于治安调解协议引起的法律纠纷公安机关并不做效力认定。调解的主要目的,在于化解矛盾引导双方解决问题,而调解协议的落空将给一方当事人增加额外的维权成本,这显然会违背当事人想通过公安调解的方式尽快解决纠纷的意愿,如果他们放弃诉讼主张选择“私了”,调解发挥的作用就难以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合同见证人与治安调解中公安机关扮演角色的内涵不同,合同中立方对合同的协商订立过程起到见证作用,而公安机关作为行政机构还承担着监督者的职能。就合同与调解协议的性质相比,引起合同订立与治安调解达成的前提不同。引起订立合同的事实并非以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为前提,作为合同成立的见证人对合同权利义务履行不产生任何影响,当然在一方违约或者不履行协议时第三方可辅助作证合同成立之有效性,而公安机关对不履行调解协议的当事人则依职权给予行政处罚。调解协议中对权利义务的分配虽基于法律但更多的是情理上的让步,事后当事人可能按照法律规定对调解协议内容提出异议。合同作为法律行为的标准文本,在权利义务分配时都有标准的格式化条文,因此法律规范性强于调解协议。
三、治安调解协议效力难题及其应对
(一)调解中立化
从《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立法初衷来看,公安机关运用调解手段解决治安纠纷案件一方面便于公安工作的顺利开展,另一方面对调解协议产生的效力虽然未有明确说明但从调解这一法律术语的运用来讲与民事调解中调解所包含的效力原则无异。[5]因此,治安调解的效力规则可以适当参考相关民事法律作为效力定性的依据,即符合条件的治安调解协议应当看作基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确立的合同,进而在诉讼中作为给付之诉的有利证据。
要让治安调解符合合同成立原则的有效做法,就是保证公安在调解过程中的中立,既要符合形式上的中立,又能保证实质上的中立。如前文所述,纠纷双方之所以选择治安调解解决矛盾,除考虑到调解具备的简易性外,还在于调解双方对公安机关能够秉公执法的信赖。在古代设立“衙门”这一机构来断案,纠纷双方各自陈词以示清白,对案件的判决结果由执政者做出很难保证中立,而当现代行政管理逐步走向亲民化,调解纠纷的公安机关对调解的结果不施加任何强制力,可从形式上保证调解结果的公平公正。
治安调解中公安所扮演的角色既是中立者又是监督者。[6]笔者认为,实现调解中立化的重点应当着眼于使警察调解的职能由监督者向中立者转化或倾斜,调解的前提在于纠纷引起的社会危害性小,在此基础上,发挥行政职能的主观能动性,将解决机制做适当调整,公安从行政执法人员演变为调解纠纷的中立方,摒弃自身凸显的“执法者”角色,形成类似发挥社会服务职能的角色担当,如此,纠纷双方可暂时消除行政执法的制裁性影响以求达到更好的调解效果。
(二)提升公安队伍的法律素养
公安系统的入警机制并未对从警人员是否具备专业法律知识做特殊限制,而在公安执法过程中,执法程序的规范与细节决定着受处罚人员对处罚结果的异议与否,而稍有法律瑕疵引起的舆论效应将对公安的整体形象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随着治安环境的日益改善,现代警察弱化保卫职能并由此向公共服务职能转变。[7]基层民警面对治安案件,不仅需要从行政执法角度熟悉法律操作规范,更需要具备民事法律知识来解决符合调解条件的民事纠纷,其调解的过程往往伴随着双方权利义务的让步,而让步所造成的法律后果当事人可能并不知晓,显然法律意识的薄弱势必影响调解一方当事人的公正。因此,民警在调解过程中理应对相关行为在法律上的后果做详细说明,在涉及双方权利义务的再分配时,应适当提醒当事人作出民事行为可能引发的法律后果。可见,治安调解更加具备法律上的严密性与规范性,提升公安民警的法律素养,是应对当下治安调解效力难题的必由之路。
1.促进治安调解的司法效力
治安调解不仅是公安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更是民众解决纠纷的重要机制。如果一份治安调解协议没有理清双方的权利义务,调解的结果不仅让人难以信服,更会产生无法预测的法律风险。调解注重程序的公开,利益的平等以及法律的公平对待等重要因素,而在调解过程中,公安民警对于违法行为人采取不予处罚的决定,容易给行政相对人在心理上形成对调解的利益牺牲,造成其在调解过程中的过分权力让步,致使调解协议沦为另外一种处罚的方式,最终让行政相对人产生对法律的错误认识。因此,要让调解更加符合一般的调解程序与原则规范,民警对调解的法律问题必须做出详细说明,从而让调解协议在真正意义上能成为具有执行效力的法律文书。
2.降低调解结果的不确定性
治安调解的目的,不在于将行政处罚演化为调解协议上的经济赔偿,而是采取平和的手段化解双方的矛盾并平息纠纷。民警在调解中的角色越中立,越能帮助纠纷双方更好的达成协议。对于侵害人而言,一份符合法律规定包含个人真实想法的调解书是符合其内心对于公正的要求的;对于受侵害人而言,调解达成后的经济赔偿比行政处罚更能弥补对其造成的财产损失。这种调解的优势,在于避免纠纷的再次发生,保证调解的法律可行性与行政执法的准确性,有效降低调解结果的不确定性,确保社会秩序的稳定。
四、结语
在强调警察执法程序正当化、服务人性化的当下,如何将民间纠纷隐藏的社会危害性通过调解降低到最小并避免纠纷的再次发生,是对公安执法能力和执法智慧的重大考验。规范治安调解的法律程序设计,加强民警的法律知识储备,无疑是公安机关摆脱目前治安调解困境的有效途径。
[1]张琳.试析司法确认对克服人民调解协议效力局限性的不足[J].传承(中旬刊),2011(1):80-81.
[2]何华珠.完善开发区文化建设策略的思考——以福清融侨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2:33.
[3]裴佳黛.农村治安调解问题与对策分析[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4.
[4]李克建.试论基层派出所在治安调解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J].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10(4):114-116.
[5]孟昭阳.治安调解的界定及适用范围与条件[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90-96.
[6]赵石麟.治安调解合理机制研究[J].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9(5):81-85.
[7]周章琪.中西警察职能比较[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05(3): 59-63.
Analysis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Police in Public Security Mediation
Shen Zhengwei
(Chinese People’s Public Security University,Beijing 100038)
As an important function of police administration,security medi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maintenance of social security and public mood.In the market economy system,China’s basic-level public security police now increasingly not only deal with public security crimes,but also need to solve economic disputes.In law enforcement,public security mediation is widely applied,for it can reduce mass conflicts and end economic disputes.However,in the legislative and judicial practice,the organic convergence among public security mediation,people’s mediation,and the litigation mediation has not been realized.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countermeasures.
public security mediation;judicial effect;police neutrality
DF34
A
1671-5101(2015)06-0051-04
2015-09-22
申政伟(1990-),男,山西晋城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2013级民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孙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