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生命的“大美”叙事
张慧萍
N多年前,梁文博先生就是画界名家了。行内有地位,行外有口碑,人生有故事,江湖有传奇。展会画廊、厅堂藏馆随处可见先生的妙笔神思,自成气象。
未识文博先生之前,先读过他的画,读他的画先识他的藤萝。藤萝是他绘画作品中的一个寓意和标签性符号一梁文博藤萝。
那是怎样的藤萝!有奔放,有内敛,有肆意,有娇羞,缠缠绕绕,低吟浅唱,柔柔软软地爬满了你的想象。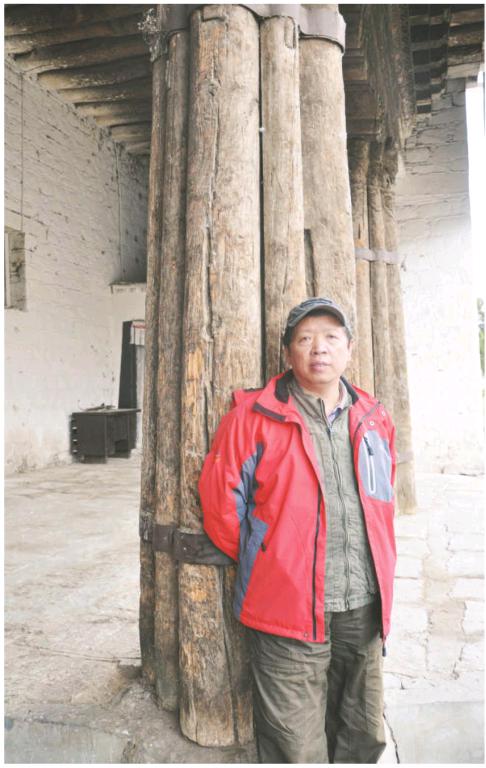
今年春天,在山东大厦气势恢宏的大厅里,不见文博,却见藤萝。这是一幅被收藏的巨幅画作《春雨初晴》,娓娓婉婉的藤萝好像一挂屏障,花繁叶盛,紫气东来。画面中,打伞的少女,肥硕的鸽子和喂鸽的少妇构成一幅美轮美奂的春光图。就像打开了一扇天窗,让人听到天籁之音,人间物语,天境对话。
一幅画,灿烂了一座大厦,迷醉了一个春天。
站在这里一转身,窗外就是另一番景象:街道开膛,车堵人燥,熙来攘往,滚滚红尘。突然想起那个贫穷潦倒的梵高和他笔下铁血般的麦浪,燃烧的向日葵,它们穿越了饥饿和冷漠,打通了古往今来。原来,人世间总有那么一些人,化腐朽为神奇,化丑恶为善意,在薄情的世界里深情的活着,即使一片绿叶。也灿烂成一座花园。
梁文博先生,他是怎样一个画家?怎样一个男人?
五十年前,梁文博先生出生在胶东一个文化世家,父亲是参加过抗战的老干部,曾担任一家工厂的党委书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被打成了右派;外祖父是胶东乡村一个有文化的地主,文化大革命被戴上高帽游街。梁文博小时候常住乡村外祖父家,他和许许多多的农家孩子一样,逮鱼捉虾,无比快乐。本是不谙世事的年纪,当他还不懂得父亲为什么丢了官帽。却又眼看着外祖父低下了高贵的头。
后来回到烟台上学。母亲是一个医生,医院相邻的桑园里有一座教堂,教堂里有一株很大的紫藤。这株紫藤就成了一个孩子的春天,并在他心里扎下来,一长就是几十年。
春天早晨上学,他会背着书包顺路去看漫延架子上的紫藤花,这时候,教堂里飘出了管风琴的旋律,赞美诗的颂唱。阳光打在脸上,春风扑在怀里,一个孩子最初的审美意识萌发了。放学后小文博常常会留连于紫藤下。就在去年,梁文博先生还专门回到烟台去寻找那座教堂,那株紫藤,教堂犹在,藤萝没了。就这样,紫藤和教堂蛰伏在早慧的少年心里,构成了梁文博精神原乡里最初的文化符号。
他说,他是个唯美主义的追求者,在创作的文化心理上,他不愿触动人类的丑恶,即使表现战争题材的作品,他也不喜欢血淋淋的场面。他更愿意发据人性之美,比如,前苏联电影《战地浪漫曲》《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都呈现出艺术家现代审美意识下的思考。在艺术创作的语境里,战争不仅残酷,也是养分。美学的本质在于审美而不是审丑,如同我们只愿意看到鲜花,而不愿意看到牛粪。
文博先生的画室,就是他自己的个展。墙上挂着画作,桌上堆着画册,案上铺着画稿。整个空间洋溢着暖暖的情调。读他的画,听他的童年故事,感受人间的美好,即使当他谈起打成右派的父亲,戴高帽子游街的外祖父这些一代人共同经历的苦难,也统统被他一带而过。在他的话语里,反复出现的是教堂,是紫藤,是童年的快乐,是沂蒙山老区的采风,是绘画的心得。多少年来,他心里一直有一座自己的教堂。从这飞出去的。是与生俱来的善意和美好。
作为艺术家,几十年来,他获过数次省级、国家级大奖,为社会呈现出大量的精美作品,如《赶场》《琴韵》《月上中天》《沂蒙小调》等画作,不仅获得了业内的高度赞誉,也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如果把他的《沂蒙山系列》《微山湖系列》《家园系列》《远离尘嚣系列》《童年系列》《母子系列》等等作品连接在一起,就是一部色彩斑斓,意味深长,关注当下,始于初心的人文情怀的生命叙事。
他给我看不久前新出的画作《高高的山岗》,一打开,就刷新了我的视觉,这幅作品虽然表现的是送郎参军的主题,但画面中的妻子没有悲伤,没有不舍,战士的娃娃脸上挂着微微笑意,挤在夫妻中间的娃娃也像在藏猫猫,这好像不是上战场,只是出一趟远门儿——这是梁文博先生笔下的抗战细节,他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概念化描述,将残酷的战争题材赋予了人性的温暖。
在创作此类作品期间,梁文博先生专门去老区采访,和老区人聊起他的画,聊起当年的情景,老人们说,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可见,人性之美原本就在一个民族的文化血脉中流淌着,你不过是换了一个思考的层面和审视的视角而已。
梁文博先生有着浓浓的沂蒙情节。在亲情上,他是沂蒙人的女婿,在文化上,他是沂蒙山的儿子。沂蒙老区在梁文博的精神世界里,不仅是一个文化地理,也是他绘画创作的一个宝库。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就爱上了沂蒙山。几乎每年他都跑到山里采风、写生。《沂蒙小调》《家园》《远离尘嚣》等系列作品都是沂蒙山对他的慷慨回报。如果说,这些作品在他绘画艺术和思想表达上已经达到一个高度的话,他近期创作的抗战系列作品《沂蒙六姐妹》《高高的山岗》等,让我们看到了梁文博先生对社会重大题材的创新和思考。
抗战胜利70年了,对于战争的思考我们本应该从浅表性的表达直指人性深处。我们打败了日本鬼子却过不了自己这道坎。社会转型期的价值观分裂。人性扭曲,导致了我们内心的彷徨和挣扎,如果再打一次战争我们能赢吗?我们还会送子参军吗?社会越发展,文化的审美功能就越强大,外化的视角,内化的审视是人类精神的最高境界。《高高的山岗》是昨天的山岗是今天的高度,是生命的赞美,活着的思考,画面上的妻子和丈夫不是别人,是你是我是我们。
纵观梁文博不同时期的绘画作品,整个的人物链条都洋溢着浓浓的人文情怀。无论是大山农夫还是市井小民。特别是他笔下的女人们,几乎个个丰乳肥臀,面若满月。他推崇少妇之美,尤其喜欢由女人变成母亲的女人。他说,中国绘画其实就是一种养生文化,追求生命的本质和美感,人类的生命和文明都需要阴性文化的滋养,男人对待女人的态度就是一个社会文明的坐标。他曾调侃自己的朋友,懂女人吗?还画女人?画不好还泛酸!去读读《金瓶梅》吧,读懂了《金瓶梅》就会画女人了。
梁文博说,不懂画面的人不懂生活。他有一个温暖的家。贤淑美丽的妻子和聪慧活泼的女儿,还有一只猫。这些可爱的家庭角色经常出现在他的画面里,如《有猫的人家》《雨后初晴》《晨妆》等。阴柔之美阳刚之气互为观照,生活创作融为一体,使梁文博的生命叙事在社会题材的广阔背景下显得更为生动,更为丰满。
朋友讲了这样一个笑话,说,一次梁文博和几个同学约好聚会,梁文博不会开车,同学电话里问他:你怎么走啊?梁文博答曰,你来接我呀!同学说,我是你的院领导,能接你吗?梁文博说,院领导又怎样?你是院领导也得来接我,我还是省领导呢!对了,忘了说,梁文博先生还是山东省的政协常委呢。此事一时传为段子。
几天前,和朋友聊天,又说起文博,她说,有一次,文博女儿回家,一本正经地对父亲说,爸爸,报告你一件高兴的事儿,我今天在马路上碰到一个男人,比你还丑,你不是最丑的!
读梁文博的写生日记,你看不到半点儿的“一本正经”,字里行间都是风趣幽默。你甚至不觉得他是一个画家,而是一个顽皮的大男孩。活的自然,活的简单,也是对待生命的另一种深情。
我们赞美自然,而恰恰忘记了我们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如同一棵树,一朵花。我们破坏了环境,破坏了文化,也弄脏了自己。任何艺术,对于美的创造和守望,最终就是创造和守望着人类自己。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相对于宇宙而言,所有的美都是短暂的,包括我们的生命。因此,对美的留恋和渴求在人类文化审美中是苛刻的,就像我们谈论生的美好而回避死亡一样。
梁文博先生说,追求完美是他的使命,也是他的宿命。在他的《家园》、《远离尘嚣》等系列作品中,无论是一介山民,一条小狗,一片山林,一丛野草都让我们读出了人和自然的和睦共存,相依为命,同时也读出了许多失去的忧伤和无奈。梁文博喜欢沂蒙山,他喜欢那里的红色符号,也喜欢那里的落后和平静,说起山里的石磨和毛驴,就像说起自家的宝贝一样。尤其说起山里的美食,文博就手舞足蹈,看人家招待我们吃饭吧,就从后院里摘根黄瓜,拔根萝卜,拿刀一切,吃吧。这情景,难道不是我们过往的生活?就艺术而言,距离产生美,就文化而言,落后也是生产力。但现实之下,所谓的“唯美”却无法抗衡生命本身的困惑。就如同我们打败了日本鬼子却解放不了自己一样。
有一次,梁文博先生约我去看他学生的毕业作品展,其中有一幅表现民工题材的画作,画面是高楼大厦倾压下的一排排脊背和头盔,这些脊背和头盔既像高山又像坟墓,这幅画的题目叫做《我们到哪里去》,看着这幅画,我和文博先生一时无语。
我想起那幅著名的十一世纪唯美主义画派的代表作《戈黛娃夫人》,戈黛娃夫人是一位美丽的贵族千金,嫁给了统治英国的考文垂伯爵,他认为丈夫征收的税负太高,让丈夫减税,丈夫说,可以啊,你只要裸身骑马穿过考文垂的街道。本是一句玩笑,戈黛娃夫人就真的裸骑穿过了考文垂。伯爵减少了税负,《戈黛娃夫人》成为了不朽。
其实,让我反复回味儿的不是这幅画,而是构成这幅画面的人物故事。画家描绘的岂止是戈黛娃夫人之美?是人类共同的文化价值观使她穿越了历史,耀眼了好几个世纪。
中国的先秦道家认为,自然无为的“道”是最高境界的“大美”,现实之美、艺术之美是“道”的外化。而西方美学的起源来自于哲学和宗教,可见,东西方美学在本质上就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初秋之夜,在写完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又一次打开梁文博先生的画册,紫藤、教堂,沂蒙山、微山湖,这些文博笔下的文化地理幻化出五彩缤纷的符号,洋洋洒洒,挥之不去。冥冥之中,飘来一首民谣:南山南,北海北,南山有谷堆,北海有墓碑……眼睛一阵潮湿,我看见了“自己”的轮回,一个新的“我们”从远古走来。
——大美伊木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