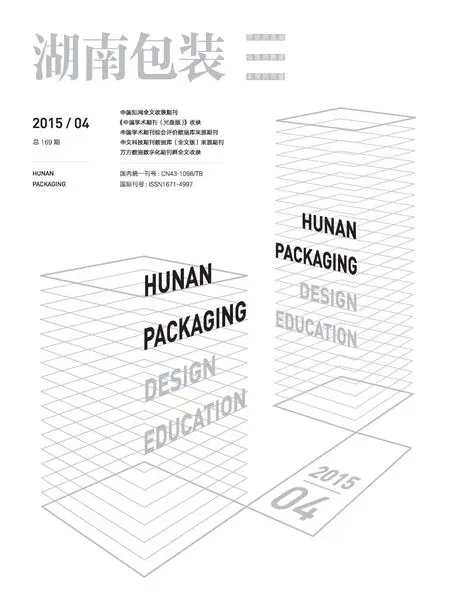中国传统装饰艺术的形成及其早期特征
陈 剑
(湖南师范大学,湖南 长沙 410000)
中国传统装饰艺术的形成及其早期特征
陈 剑
(湖南师范大学,湖南 长沙 410000)
中国传统装饰艺术的发生与艺术起源问题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结合史前彩陶纹饰的演变对中国传统装饰艺术的发生和形成过程进行理性推论,进而在此基础上概括性的指出中国传统装饰艺术所具有的象征意味和吉祥寓意。
装饰艺术,艺术起源,象征,吉祥
1 艺术起源与中国传统装饰艺术的形成
在艺术学的各相关研究领域里,艺术起源是一个关乎艺术史的起点、极其有趣而又难以解释清楚的课题,一直以来受到中外众多学者的亲睐,专著和文章屡见出版和发表。其中,较为中国学界所熟知的西方著作包括:格罗塞[1]的《艺术的起源》、普列汉诺夫[2]的《没有地址的信》、弗朗兹·博厄斯[3]的《原始艺术》、阿洛瓦·里格尔[4]的《风格问题:装饰艺术史的基础》;亦有部分中国学者涉足该领域[5][6]。另有一些诸如“艺术概论”、“艺术原理”的著作也涉及到了这一部分内容,但多为对上述理论的概要。综合来看,比较典型的观点包括模仿论、表现论、劳动论、游戏论、巫术论以及起源于季节变换的符号、起源于对动物亡灵的哀悼等[5]。然而,由于时间的远逝,史前社会包括音乐、舞蹈、祭祀等形态的艺术门类已经无法得以真实的再现,遗留下来的仅仅只有依附于固体物质材料的装饰纹样,装饰品和装饰艺术遗迹也因此成为考察人类艺术起源最为重要和直观的实物和史料之一。也就是说,无论论者从何种角度考探艺术的起源,装饰艺术都是必然不能绕过的一个关键。
近代以来,考古学的建立和不断进行的科学考古发掘一次次刷新了我们对中国远古文明的认识。考古资料显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发现最早的文明是在山西芮城西侯度发现的距今约180万年的32件石器,从广义的装饰范畴来讲,这些石器尽管粗糙,却也成为目前为止可知的我国旧石器时代造物艺术的基本形态。随着历史的发展,在开发其他材质工具的同时,原始石器在远古人类的手中得到不断的更精细地加工,形成了诸如圆球形、椭圆形、半圆形、长方形等几种规范的形制。到约1.9万年前山顶洞人时代骨角器和穿孔饰品的出现以及约1.3万年前的刻纹鹿骨的出土,标志着完全意义上的装饰品正式诞生。进入新石器时代之后,随着工具的更新,装饰艺术也得到迅猛发展,在公元前7000年左右出现了附着于陶器表面的几何纹装饰,使陶器装饰尤其是其后诞生的彩陶装饰与远古岩画和地画(图1)一道成为艺术起源的重要研究史料,同时前者也是中国传统装饰艺术正式诞生的标志[8]。然而,艺术起源和装饰艺术发生期的具体诱因依然是个杂乱的迷团,那些从数千年的睡梦里惊醒的史前彩陶能给出我们找寻答案的些微提示么?

图1 将军崖岩画稷种崇拜图(局部),新石器时代,石壁敲凿磨刻,原图纵280cm,横400cm[7]
自从1921年河南渑池仰韶村的考古发掘以来,彩陶便不断出现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中,除了引发考古学家围绕其地层关系、文化类型等考古学诸多问题展开的研究之外,陶器表面的彩绘也得到了艺术工作者和美学研究者的关注,将其纹饰视为纯形式意义上的装饰艺术,纷纷从抽象纹饰变形、构图形式法则等方面展开探讨,过于草率的得出一些或许与真实情况截然相反的结论。究其缘由,与研究者对器物的本原状态即彩陶在史前社会的历史语境的存在状态采取回避甚至漠视的态度不无关系。当然,也有部分学者注意到了这一问题,而将彩陶纹饰的研究纳入了诸如考古学、文化学、人类学等研究领域,发表了一些新的见解[9],使我们能“透过彩陶艺术,看到先民的思维和精神”。在对不同历史时期的艺术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尽可能的营造艺术品在其诞生的历史时空的文化语境,是我们能否得出正确结论的关键。所以我们不能单纯的将彩陶纹饰剥离原器物、作为纯粹的艺术品置于桌面上、纸上进行形式和平面的研究,而应该将其还原于当时的文化环境,与其时人类的物质生产条件和精神状态相结合,以得出尽可能接近真实或是“艺术真实”的结论[8]。
在史前人类的努力和探索下,工具特别是石制工具的诞生和演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近代以来史前考古学丰富的材料支撑使这一过程较为清晰的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天然石块经过击打成型,成为旧石器时代的典型器物;进入新石器时代后,石块的加工逐渐出现了磨制工艺,石器进一步定型,出现了诸如圆球形、椭圆形、饼形、梭形、菱形等几何形状。今天的我们根据科学原理得知,这样的加工使得工具更符合力学原理也更适合人的双手使用,进而这种工具的改进往往促进了诸如表现为命中率的提高、削割的锋利等现象的“生产力”的发展。然而,在史前人类那带有巫术的“神秘属性”的意识中,这是不可思议的,于是产生了对隐藏在工具背后的“神秘属性”近乎天然的崇拜。从工具演进的历史来说,这种崇拜可能更多的表现在工具的新式样——几何状的外形[8]。
基于这样的理论,我们再来探讨彩陶纹饰中各种图形出现顺序的缘由和含义,就比较清楚了。
按照时间顺序,几何纹、动物纹、人物纹先后出现在彩陶纹饰中。半坡遗址出土的早期彩陶中,纹饰多为宽带纹、三角纹、三角与斜带纹、波折纹、梭形纹和菱形纹等,而且这些几何纹中不少还与鱼纹、鹿纹、人面纹共存[10](图2)。半坡早期陶器几何纹不仅种类多,而且数量大,其中宽带纹在半坡整个彩陶纹饰中多达80%[12]。半坡类型彩陶纹饰中大量出现鱼纹、人面鱼纹、蛙纹等,庙底沟类型彩陶纹饰中则主要是鸟纹等,更晚些时候的马家窑文化彩陶纹饰中则多在仰韶文化晚期业已几何化的鱼、鸟结合纹样的基础上继续演变[11]……由此可见,彩陶纹饰从早期的几何纹到独立的动物、人物纹再到动物、人物结合纹的发展也如同其他艺术形式一样,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在史前人类的眼中也许并不存在我们今天所谓的抽象、具象的区别,而可能将其统一到纯“具象”的概念中,从这个意义来看,无论几何纹、动物纹、人物纹都与史前人类对自然界和当时人类所掌握的生产、生活经验息息相关。如果我们这些大胆的推测成立,则这些纹饰所丛生的最早产生的几何纹和之后具象纹样几何化的原型也就无所遁形了。也就是说,这些今天看来抽象无比的几何纹在史前人类的眼中可能“具象”至极。而在之后结合纹样的抽象化过程中,渔猎工具起到了较大的作用:捕鱼的工具往往是尖状物或网状物,故鱼纹逐渐演变为直线的带状图案和复杂的网状图案(图3);猎鸟的工具可能多为石球之类,由于这些工具在投掷过程中抛物线的发射路线及鸟类飞翔的流线形,史前人类在变形过程中将鸟纹演变成曲线纹(图4)……于是,这样的一种“抽象”在本质上很可能不是“简化”,而是一种恰恰相反的“复杂化”。从而使后期的几何形纹样不同于前期,而是经过了“具象”—“抽象”的演变过程,是一种绚烂之极的平淡,是一种“有意味”的几何形,又区别于最早的简单纹样的诞生的早期的几何纹。后者与史前人类对外形工整的磨制工具所具有的神秘力量的追捧密不可分。所以说,艺术的起源与人类对神秘未知世界的那种近乎迷信般的崇信有关。

图2 半坡人面鱼纹彩陶盆俯视图[11]

图3 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彩陶船形壶[13]
列维·布留尔认为,尽管史前人类和我们一样都在用眼睛看外界,但是他们用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意识来感知,没有任何东西是一样的,这就是我们在理解史前人类的表象方式时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的原因。“如果说原始人不像我们那样感知肖像,那是因为他们不像我们那样感知原型。我们在原型里面抓住的是一些客观的实在的特征……对于知觉趋向不同的原始人来说,这些客观特征(如果他也像我们那样抓住了它们)绝不是详尽无遗的或者最本质的特征,它们多半只是秘密力量、神秘属性——为任何存在物特别是有生命的存在物所固有的属性的标记或媒介。因此,对于原始人来说,存在物的图像自然是我们叫做客观特征的那些特征与神秘属性的混合。图像与被画的、和它相像的、被它代理了的存在物一样,也是有生命的,也能赐福或降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见到人所不知的存在物的图像,亦即能吓人的存在物的图像,常常引起一种异乎寻常的惊恐。”[14]也就是说,史前人类看待事物的眼睛中往往带有一种“神秘属性”,看待已经存在但是初次见识的事物尤其如此。史前人类以各种方法开始破解这种“神秘”,其中最普遍的方法我们今天称之为“巫术”。

图4 庙底沟类型彩陶侧面鸟纹演变图[11]
巫术论是西方社会关于艺术起源的“最有势力的一种理论”[5],并进而与图腾崇拜和自然崇拜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彩陶时代的史前人类来说,周围的世界莫不充斥着巨大的神秘气息,我们今天对客观事物的看法对史前人类来说可能具有另一套完全不同的意义,他们认为世间的一切都受到神秘力量的控制,这种力量的不可捉摸令他们好奇和害怕,于是产生了对它的虔诚崇敬,并通过各种他们认为可能的途径与之对话。也许几千年前遗留下的岩画、地画正是这种沟通的产物,基于这样的推测,彩陶纹饰的出现便自然携带来这种神秘的巫术属性,并进而发展成图腾。另外,图腾的产生一方面与巫术有关,一方面也来自于史前社会恶劣环境下个人生存的艰难,这种个人对自然的恐惧迫使史前人类凭借某些共同的信号结成同盟,半坡类型彩陶上的鱼纹、庙底沟类型的鸟纹、马家窑文化的鱼鸟结合纹在很大程度上便产生于这种图腾信仰,并反映了其时史前人类的共同生活场景与兼并活动。
祭祀是巫术活动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之一,在史前彩陶装饰纹样中也有相当的体现。其中最为显著的当属西安半坡出土的一批人面鱼纹陶盆。这些彩陶盆出土时大多覆盖在婴儿瓮棺的上面,在成人瓮棺葬和成人墓中从未发现,所以这类彩陶盆只可能是史前人类埋葬夭折儿童的一种葬具,其装饰纹样因而带有葬仪中巫术祭奠活动的文化属性。史前社会生活条件的恶劣造成婴幼儿童的高死亡率,而极低的生产力水平却需要补充大量人口,以至于人丁兴旺与否成为一个氏族或部落兴衰的标志。“氏族的全部力量、全部生活能力决定了它的成员的数目,因而每一个成员的死亡对于所有其余的人是一个重大的损失”[2]。于是,包括祭祀在内的生殖巫术应运而生。基于这样的逻辑,史前人类在彩陶上绘制的鱼纹、鸟纹、蛙纹等动物纹样的最初动机恐怕便是对这些动物强大的繁殖和生存能力的期望,而后期“几何化”的漩涡纹、波浪纹等纹样又有可能是出于对雌性生殖器官的刻绘或变形刻绘[15]。也正是这种“象征”,使得中国传统装饰纹样选择了走向“抽象”而又寓意深刻的非直白式的表现手法,从而也初步形成了早期中国传统装饰艺术的一个显著特征。
2 早期中国传统装饰艺术的基本特征及其流变
从彩陶纹饰的发生和演变过程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其作为史前装饰艺术诞生的大致背景和流变趋势,也让我们感受到彩陶纹饰的发生与史前人类的原始思维方式和观照方式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作为仿生学的模仿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种发生学的自觉性,如原始社会的捕猎活动中,人类为了接近猎物或是出于其他目的,以纹身、装饰的方法将自身打扮成动物的形态,不自觉之间亦完成了原始艺术的启蒙。另一方面,原始氏族对于动物的崇拜也促使人类开始有意识的模仿动物所具有的某些超越人力的能力。这种基于“模仿”之上的“超越”便构成了华夏民族传统思维方式和观照方式中某种征兆性的特征。
先秦典籍《周易》曾将这一特征在思想内蕴与思维轨迹上进行过充分的展开和展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李砚祖曾将这种视觉思维方式概括为“观物取象”[16]。史前人类的这种视觉思维方式,让我们不仅可以窥见古人创物的来源,也可得知古人造物之方法,并进而赋予这些被创造的物象以各种更深层次的内容,即“通过‘仰’、‘俯’、‘近’、‘远’以不同的角度和方位静观,而后以‘类万物’的方法再造物象于人间,进而付诸这些物象于‘德’、‘情’等文化内涵”[17]。彩陶纹饰发生期几何化的特征可以告诉我们,“象”作为后世造物的重要范式之一,其诞生的年代远比我们预知的要早,从目前可考的资料来看,最早的“象”字可在甲骨文中窥见其存在,本身就是通过突出其长鼻来描摹大象的外形(图5)。因此,象在其初始阶段,与前文所述“仿生学”类似,实指的仅仅是物之“形象”,尽管在随后的发展演绎中,它还将被不断的注入新的人文属性。但是,作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和观照方式,“象”在另一方面也是自成的符号形象,是介乎于形象本体与深层次哲理等不易理解的文化意义之间的具有征兆性的中介和工具,故而产生了新的意味——象征。

图5 甲骨文字“象”[18]
在《辞海》里,“象征”由两个层次的意义组成:“① 用具体事物表示某种抽象概念或思想感情;② 文艺创作的一种表现手法。指通过某一特定的具体形象来暗示另一事物或某种较为普遍的意义,利用象征物与被象征的内容在特定经验条件下的类似和联系,使后者得到具体直观的表现。”并进而指出,作为形象,象征可分一个民族文化中习用的公共象征或传统象征以及个人自创的私设象征或个人象征两大类。前者即传统象征自然是我们讨论的焦点和中心。
黑格尔曾从艺术的角度对象征进行过解析:第一个是意义,即事物象征的或暗示的含义;第二个是这意义的表现,即外在事物。他说:“意义就是一种观念或对象,不管它的内容是什么,表现是一种感性存在或一种形象。”[19]卡尔·荣格则从心理学的角度认为象征是人的潜意识的产物,梦是所有有关象征知识的源泉;象征既能在梦中出现,也在所有的心灵表象中显示。并进而给象征作了概念上的界定:“所谓象征,是指术语、名称,甚至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景象。但是,除了传统的明显的意义之外,象征还有着特殊的内涵。它意味着某种对我们来说是模糊、未知和遮蔽的东西”、“当一个字或一个意象所隐含的东西超过明显的和直接的意义时,就具有象征性”[20]。荣格的观点对后世符号学理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苏珊·朗格将其运用于美学的研究,认为艺术形式就是一种情感的符号象征。基于人类学的理论,米尔希·埃利亚德认为象征符号基本上指示的是一种宇宙结构的构成,原始人就是生活在一个被神圣化的宇宙之中,是通过宗教的象征将杂七杂八的现实世界统而合一。
在黑格尔的论述中,“象征”从出现到与“艺术”结合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分别是不能列入艺术的非完全意义的象征、真正象征的过渡、具备艺术特性的象征的艺术作品[21]。应该说,这与中国传统装饰艺术历史发展的阶段也是吻合的。在古中国人看来,偶然事件非征兆性的发生本身便带有某种神秘的色彩,若干次重复之后形成了尝试的行为,经验积累到最后终于形成了对这类事件的必然感应和联想。彩陶时代的纹饰便是其中典型的日积月累型的经验结晶。象征便自然的产生了对那种生生不息、日新不滞、奇妙莫测的生命本身的向往,因而与以生殖和图腾崇拜为主要内容的巫术也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与之一道形成了中国传统装饰艺术特征主要的表征和处理手法,并对作为中国传统装饰艺术中心主题的吉祥意识的产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吉祥”本意为美好的预兆。《周易》有“变化云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未来”之句,庄子也借孔夫子言道:“瞻彼阕者,虚室生白,吉祥止止”,唐成玄英疏曰“吉者,福善之事;祥者,嘉庆之征”。由此可见,吉祥是对未来的希望和祝福,具有理想的色彩。吉祥是人类对万事万物希冀祝福的心理意愿和生活追求,它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人性至善至美的本质。人类对于生活祝福的中心主题是“吉祥”,这是一个延绵千万年的永恒性主题。如前所述,原始彩陶纹饰已包含了一种广义的“吉祥”寓意在内,史前人类带着对吉祥虔诚的信任和希冀而精心刻画各式各样的纹饰,他们相信,这些装饰纹样本身或使器物也具有某种神性,能给自己带来力量。彩陶纹饰中的人面鱼纹、鱼纹、蛙纹、鸟纹、太阳纹以及其他一些纹样,无论是出于巫术、祭祀、图腾还是希求多子、生殖繁衍的目的,无不体现着期盼吉祥的意义,是史前人类渴求吉祥观念的古老形式。
根据我们对传统中国吉祥观念的考察,这种观念不仅表现为相应的图式,也与文字、语言、风俗、习惯等因素广泛关联,乃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大特色。对于中国传统思维的模糊性、非逻辑性和非理性的特征来说,“象征”的出现无疑是必然的,它使得中国人在面对未知世界时采用一种趋于感性的处理方式。而且,随着国家的逐步统一和“天下”这一文化概念的增扩,各种象征物也聚集一堂,充斥画面,成为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在汉画像作品中体会现实、阴间和仙境合而为一的图式的重要原因。事实上,这种画面的组合在如“人面鱼纹”的原始彩陶纹饰中便已经出现。除却原始彩陶纹饰,包括原始岩画图像、汉字、青铜器装饰、周易的符号象征世界、汉画像中的图像符号以及阴阳五行的哲学观念、原始诗歌舞的三位一体、赋比兴的艺术形式等在内的大部分中国文化符号也都具有象征性。可以说,象征性和于此基础上形成的吉祥意识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内核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刻的内涵,中国传统装饰艺术仅仅只是这种内核的一个表现。
[1][德]格罗塞.艺术的起源[M].蔡慕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2][俄]普列汉诺夫.没有地址的信[M].曹葆华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3][美]弗朗兹·博厄斯.原始艺术[M].金辉,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
[4][奥地利]阿洛瓦·里格尔.风格问题:装饰艺术史的基础[M].刘景联,李薇蔓,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
[5]朱狄.艺术的起源[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6]张晓凌.中国原始艺术精神[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
[7]中国古代岩画·彩绘纹饰选[J].北京:中国书法,2008,7:2.
[8]陈剑.马王堆装饰艺术源流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09.
[9]林少雄.人文晨曦:中国彩陶的文化读解[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
[10]严文明.半坡仰韶文化的分期与类型[J].北京:考古,1977,3:182-188.
[11]张朋川.中国彩陶图谱[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
[1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半坡[G].北京:文物出版社,1963:169.
[13]杨泓 李力.美源:中国古代艺术之旅[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14.
[14][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M].丁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40-41.
[15]户晓辉.中国彩陶纹饰的人类学破译[J].北京:文艺研究,2001,6:131.
[16]李砚祖.装饰之道[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17.
[17]陈剑.从马王堆《导引图》看中国传统体育与艺术精神[J].南京: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08,4:19.
[18]杨红卫 杜志强.甲骨文书法鉴真[G].合肥:黄山书社,2006.
[19][德]黑格尔.美学:第二卷[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0.
[20][瑞]卡尔·荣格.人类及其象征[M].张举文等,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1-2.
[21][德]黑格尔.美学:第二卷[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27-28.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11YBB271)
陈剑(1982-),男,湖南师范大学讲师、硕士研究生导师,苏州大学博士研究生。E-mail:chens1982@126.com。
2015-0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