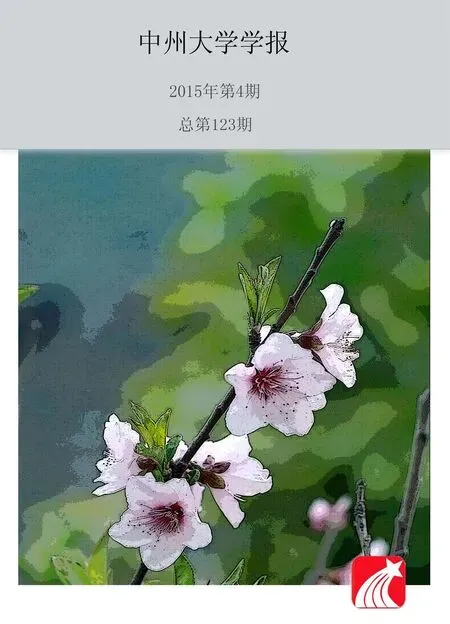“重写文学史”和《今天》的相遇与重叠
“重写文学史”和《今天》的相遇与重叠
刘忠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34)

摘要:提及“重写文学史”,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上海文论》1988年第4期至1989年第6期开设的“重写文学史”专栏,以及围绕“要不要”重写、“如何”重写、“价值”何在等问题展开的论争。其实,从1991至2001年间,远在海外的《今天》接过这个旗号,把“重写文学史”专栏薪火相传了十年。如果把《上海文论》时期的“重写”专栏称为“重写文学史”的上半场的话,那么《今天》时期的“重写”专栏则是它的下半场。毫无疑问,无论是精彩度还是影响力,下半场都不及上半场。这之中,除了《今天》的“民刊”性质为“重写”专栏罩上了一层非意识形态的神秘色彩之外,20世纪90年代以后文学史研究渐趋冷静、理性,现代性反思之声渐起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再就是《今天》与重写文学史定位的抵牾和错位。
关键词:重写文学史;《今天》;相遇;重叠
收稿日期:2015-07-1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1BZW101);上海市曙光计划项目(10SG43);上海高校一流学科(B)建设计划项目(12sg12)
作者简介:刘忠(1971—),男,河南固始人,文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5.04.001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5)04-0001-08
Abstract:Referring to “Rewriting Literary History”, people firstly think of the “Rewriting Literary History” column of Shanghai literary theory from No.4 1988 to No.6 1989, and the debates on such issues as “whether or not” rewriting, “how” to rewrite and its “value”. Actually, from 1991 to 2001, Today far away from overseas took the banner and had the “Rewriting Literary History” column for ten years. If the rewriting column during the period of Shanghai literary theory is called the first half of “Rewriting Literary History”, the rewriting column of Today is its second half. Undoubtedly, the wonderful degree or influential power of the second half can not be compared with the first half. In addition to the privately-possessed nature of Today which covers a layer of ideology of mystery to rewriting column, researches on literary history have gradually become calmer and more rational since 1990s, and the gradually rising of modern reflection is also an important reason. Moreover, the contradictions and dislocation between Today and “Rewriting Literary History” column is another important reason.
提及“重写文学史”,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上海文论》1988年第4期至1989年第6期开设的“重写文学史”专栏,以及围绕“要不要”重写、“如何”重写、“价值”何在等问题展开的论争。其实,从1991至2001年间,远在海外的《今天》接过这个旗号,把“重写文学史”专栏薪火相传了十年。
一、精彩不够——重写文学史的“下半场”
如果把《上海文论》时期的“重写”专栏称为重写文学史的上半场的话,那么《今天》时期的“重写”专栏则是它的下半场。毫无疑问,无论是精彩度还是影响力,下半场都不及上半场。何以如此?远在海外,读者和研究者很难及时知晓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今天》刊物的民间、同仁性质为“重写”专栏罩上了一层非意识形态的神秘色彩;还有一个原因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文学史研究渐趋沉静、理性,思潮、跟进式的“重写热”开始降温,影响力大大减弱。事实上,《今天》“重写文学史”专栏的尴尬从开设之初就显现了出来。
首先,相左的意识形态取向不可回避。创办于1978年12月的民刊《今天》,因为“告别过去、迎接未来”宣言的引领作用,在新时期思想史、文学史、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至今人们仍能如数家珍地列举那些与《今天》有关的作家与作品,食指、北岛、芒克、多多、舒婷、顾城、江河、杨炼、方含、严力……赵振开的小说《在废墟上》《归来的陌生人》,诗歌《回答》《一切》《宣告》《结局或开始》,食指的《相信未来》《命运》《疯狗》《四点零八分的北京》,芒克的《天空》《十月的献诗》,江河的《祖国啊,祖国》《星星变奏曲》,舒婷的《致橡树》《中秋夜》……一份油印同人的文学刊物,从最初的张贴式发布到后来的邮寄发行,从1980年9月因“刊物未经注册,不得出版”勒令停刊到1990年8月在挪威奥斯陆复刊,几经沉浮和变迁,不变的是对文学的热爱。
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左是《今天》不容回避的取向,它带给《今天》的不仅有“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评,还有延续至今的言说禁忌。这一点,从重写文学史口号提出者王晓明在其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的“前言”“后记”中绝口不提《今天》“重写文学史”专栏的隐秘做法中,似乎可以找到草蛇灰线。他说:“有心的读者可能还会注意到,本书较多地选收了一些在港台、海外的学者的论文,这不仅因为他们的研究成果展示了他们极富特色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而且还因为他们的著述不容易被一般的读者见到,他们的论文从选题到思想方法上都有其独到之处,应该得到重视。”[1]388巧妙地回避了《今天》与《上海文论》“重写文学史”专栏的续接关系,以及它在文学史研究领域的创新价值。
其次,传播不畅、受众面狭小是客观事实。《今天》创刊之时,正值新时期改革开放之初,经历“文革”的一代知识分子迫切需要一个表达自我的话语场,《今天》见证和言说了一代人的成长,他们在迷茫中寻找出路,在下沉中获得力量,在集体失语中呼喊。自由、平等、真理、正义、理想、未来,这些闪光的词汇曾经照亮了一代人的黑眼睛,影响波及文学、美术、电影、戏剧等多个领域,成为新时期先锋文艺的开端。其后,经历了停刊、自由化批判、同仁星散、远走去国等风波,进入90年代,《今天》的影像越来越模糊,国内同时期读者群的思索热情渐趋冷却,代表着叛逆、反抗的《今天》更多地留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中;文学热点也由之前的伤痕、朦胧、反思、改革、寻根、先锋、新写实、新历史、女性主义等“纯文学”话题转移至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现代性、网络文学等“泛文学”话题上,新成长起来的读者更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了。不要说“重写文学史”专栏,甚至《今天》复刊的消息也是知之甚少。何况从1990年夏季复刊至今,《今天》仅编辑部就几经移址,挪威的奥斯陆、瑞典的斯德哥尔摩、美国纽约、洛杉矶、中国的香港,每到一处常常面临严重的资金紧张和发行困境,国内市场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得到开发,客观上造成刊物传播不畅、受众面狭小,很多的研究者、专业人士都不知道《今天》有一个坚持十年之久的“重写文学史”专栏,自然也不会把《今天》和《上海文论》的“重写文学史”进行比较研究,寻绎它们的相同与相异。这既是对《今天》的不公,也给“重写文学史”的全面研究造成了盲视。
最后,时过境迁,《今天》的反抗、先锋姿态与国内文学史写作的学科化走向明显背离。经历了90年代初“重写文学史”的论争与实践,学者们发现仅仅在审美艺术和纯文学视阈中对抗革命文学和政治话语,藉此实现文学与生活、文学史与文学的分离无异于缘木求鱼,不仅不能很好地认识文学自身,而且容易滑向“审美—纯文学”的单一、偏执泥沼,成为一种架空思想、政治、道德、伦理的“单向度”文学,限制了“重写”的高度与深度,与既有文学史并无二致。于此,以“反思现代性”为突破口的文化研究恰逢其时地为文学史写作摆脱“启蒙与救亡”“政治与审美”“大众化与化大众”“官方与民间”的二元对立思维定势提供了契机。90年代中后期开始,重写文学史研究不再坚持异质化,而是在历史语境和全球化秩序中寻找同质的可能性,整合文学史的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审美、心理等质素,打通横亘在文学史写作中“审美主义”与“生活实践”(包括政治革命、社会运动)之间人为的界墙,进而实现从“对抗”走向“和解”。很显然,这种研究趋势与《今天》的“重写文学史”专栏貌合神离。“《今天》抗议和反抗的对象不仅是文学和艺术的体制,还包含着这些体制后面的制度安排和历史含义”,“《今天》代表的写作和学术性写作之间,天然有一种不和谐,或者说敌对”等的价值取向从一开始就为国内学者的研究制造了观念接受上的障碍。关于这一点,《今天》“重写文学史”专栏主持人李陀本人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如果把八十年代至今的‘重写’历史拿来做一番比照,我想文学史写作如何受制于体制,可以看得更为清楚。十多年前,为《今天》‘重写文学史’专栏撰稿的作者们今天还都很活跃,很多人都已经是自己学术领域中的权威人物。如果《今天》再一次开设‘重写’专栏,再一次热情邀请大家写文章,还会有人寄来文章吗?专栏还能再继续十年吗?我可以肯定,不会的。这不是因为这些人不再愿意为《今天》写作,我相信,只要有机会,大家都愿意以自己的写作支持《今天》。问题不在这儿,在别的地方。《今天》和‘重写’相逢,无论对《今天》,还是对文学史写作,都是一段插曲,这个插曲如今之所以不能再重复,更深刻的原因还在它们和体制的不同关系。”[2]8这里,李陀所说的“体制”是指经过十多年时间的和“国际接轨”,文学史写作愈加规范化、学术化,与主流意识非但没有远离,相反还在跨文化交流中,与体制更加密切了。
二、必然与偶然——重写文学史与《今天》的“重叠”
人们常说,世事难料,许多看似不可能的事情成为了现实。1991年夏,在挪威奥斯陆复刊刚满一年的《今天》在第3、4期合刊上接过来“重写文学史”专栏的接力棒,开启了重写文学史在海外的十年之旅。一个飘洋过海的民间刊物,一个争议不断的热门话题,两者的相逢偶然之中又有着必然。反抗、颠覆既有文学史写作体制,确认自己的存在价值,让两者相互倚重,走过一段“是盟友,是支持,是合作,但绝不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的艰难历程。
在专栏“编者按”中,主持人李陀说:“1988年,《上海文论》开辟了一个栏目——‘重写文学史’,由此引起了一场风波。在反对者看来,文学史是不准重写的,可恰恰是历史告诉我们:一切叫做历史的东西都在历史中不断地被重写。……‘重写文学史’的栏目早就被停掉了,十分可惜。本刊早就有意接过这个话题,使之继续。前不久正好收到王晓明先生的一篇来稿,与‘重写’有关,而王又恰是‘重写文学史’一事的始作俑者之一,这自然是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在本期郑重辟出‘重写文学史’专栏,希望这个栏目会得到读者的关心,也希望对这个题目有兴趣的各方人士踊跃来稿,使‘重写’的事再度热闹起来。”[2]2“编者按”表达了三层意思:其一、肯定文学史是可以而且能够重写的,为《上海文论》和《今天》架设重写观念的“相通”桥梁;其二、亮明重写主旨与重点,彰显与《上海文论》重写目标之不同;其三、叙述“重写”专栏开设的触发点,在《上海文论》和《今天》之间接通血缘纽带。
正是在“目标之不同”上,《今天》的刊物定位与“重写”专栏的初衷产生了罅隙和抵牾,这为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两者的“游离”和“不协调”留下了遗患。为“重写文学史”的两种不同叙述方式播下种子:放在“文学史”的学术传统和学术机制里进行分析和讨论;放在《今天》的历史和命运里予以审视和评判。很显然,前者是大陆学界的叙述,后者是《今天》的叙述。
《上海文论》时期,重写文学史的对象是官方的新民主主义话语,并未触及文学史写作背后的体制因素,也没有把评判的矛头对准“文学史写作”本身,只是把“启蒙”“审美—纯文学”作为标杆,期待文学史写作的多样化,而非彻底的去“官方”、去“政治”、架空“道德”,这在之后的重写文学史实践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无论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新文学整体观”,还是新中国文学、两岸三地文学,抑或是现代性文学、女性主义文学,打破的仅仅是文学史写作的种种束缚,以回到常识、回归文学本身的策略淡化政治与文学史写作的规训,寻找文学史写作的多种可能性,“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始终处在此消彼长的状态。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依然是主基调,对待革命文学、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十七年文学是“重读”“新解”;对待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人性文学是“肯定”“张扬”;对待通俗文学、大众文学是“认识”“默许”。总之,文学史写作走在一条多元化的整合道路上,兼容并蓄、互动共存是它最显著的特点。而在《今天》看来,这种写作尚处在修修补补的学科化、学术化初级阶段,实在是太落伍、太保守了。与《上海文论》的“重写”相比,《今天》的“重写”更加彻底、坚决,有它自己的知识谱系,有它特殊的烙印。反抗、先锋、解构、颠覆、异质、拒绝等标签可以轻而易举地贴到它的身上。“《今天》的挑战和质疑的矛头,并不是只指向文学写作,而且也直接指向文学史写作”;“《今天》生来就是一切体制,也包括文学体制的敌人——在‘我不相信’这面旗帜下,《今天》所追求的写作永远是拒绝和反抗的象征,是对现存世界的种种压迫关系,对现今一切统治秩序进行批评和反抗的不屈不挠的表达”。如此的《今天》,如此的“重写”专栏,与《上海文论》的差异何至道里?
《今天》视野中的“重写文学史”叙述存在两个悖论。
其一、“重写”使命与《今天》的视野难以匹配。作为一个专栏,放在《今天》的历史和命运中审视自有其道理,“可以扔掉一些包袱,澄清一些遮蔽,给文学史的重写一个新的方向,提出一些新的可能”。但是重写文学史毕竟是一个学科建设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历史语境、意识形态、社会风气、心理积淀、思想导向、阅读习惯、传播方式、文学史家的知识结构、价值标准等方方面面的因素。任何单向度的写作都会破坏文学史的丰富性、多样性,甚至造成“翻烙饼”式的内耗,无休止的颠覆和对抗,而没有建构和生成,滋生文学史写作的相对主义,陷入不可能论。共性的消失换来的是个性的膨胀。
其二、《今天》“重写”专栏的初衷与文本实践相左。从“专栏”开设初衷来看,是要把《今天》的反抗性、解构性进行到底,避免同质化,进而实现对文学史写作的“重写”。挑战体制、警惕体制、疏离体制、突破体制、解构体制等词语,屡屡为《今天》“重写文学史”专栏主持人李陀提及,而且每次提及似乎都充溢着自豪与兴奋,认为这才是《今天》与“重写文学史”相逢的深远意义。但是,事与愿违,实际的情形是,《今天》“重写”专栏发表的29篇论文中,没有一篇对《今天》与“重写文学史”之间相互“重叠”的意义与价值进行关注。很明显,论文的写作者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论文在《今天》上发表与在国内其他刊物上发表有什么不同。“《今天》的特殊历史和它的特殊意义,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也许,激励文章撰写者们的唯一念头,是被无情腰斩的‘重写’竟然死里逃生,大家终于又有一个空间可以思考和写作”。[2]4不仅思想观念上,“重写”专栏上的论文与《今天》的先锋品格不相协调,而且体例、写法上也迥然有别。“就拿在《今天》发表论文的这些作者来说,明显的,大家都想以自己的‘重写’,来对旧的文学史做出质疑和批判,但是,这样做的同时,每一位作者又都同时在努力保持写作的‘学术性’,使其符合学术体制所要求的规范。如果放在一本正常、普通的学术论文集里,这种做法是当然的,没有什么特别,只能如此。但是这些文字,还有这些文字所负载的学术性和学术规范出现在《今天》这本刊物里,就显得十分不协调,甚至怪异。”[2]5这种怪异甚至传染到主持人李陀本人,他说:“每当一辑‘重写’文章刊出时,不论这些文章写得多么出色,心里总有点别扭,觉得它们不过是混迹在《今天》里,这儿其实不是它们待着的地方。”姑且不论《今天》把“对抗”“解构”“颠覆”“先锋”作为唯一尺度的做法对错与否,单就它要求论文写作不拘泥于学术性的做法还是有可取之处的,至少在90年代中后期“学术与世界接轨”的大潮中葆有了论文写作的“文学性”和“主体性”。正是在这一点上,李陀说,“重写”专栏的文本实践与《今天》是“盟友”的关系,“合作、支持”的关系,而非“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因为“《今天》生来就是一切体制,也包括文学体制的敌人”。
在纠结和悖论的反向弱化作用下,2001年《今天》夏季号上“重写”专栏宣告终结,至此,“重写”与《今天》的“重叠”正好走过十个年头。如果把《上海文论》时期也算上的话,“重写”专栏前后持续了十二三年。在这个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时间里,文学创作、文学研究经历太多的变化,个性化、多元化、主体性、审美性已经成为常态,表达不同意见和看法的渠道更趋开放。作为“双百”方针之一部分,思想争鸣、观点论辩不再与立场身份挂钩,成为人身攻击和思想批判的工具。知识分子的精英角色在淡化,学术报刊的号召力在减弱,经济、网络、大众、移动互联在文学生产、研究、接受、流通环节中的地位大幅提升,不要说“重写文学史”,即便是“人文精神讨论”,抑或是新左翼、新自由主义、底层文学都很难在人们心目中激起群体性共鸣,人人争说“重写”的景象很难复现。如此,《今天》和“重写”分道扬镳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两者之间不仅“神离”太久,而且当初的“形似”也面目可憎,失去了相互倚重、“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如果我们把《今天》时期的“重写”称之为“后重写”的话,它的终结似乎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文学史写作再无“重写”一词,或者说很难再现“政治”与“审美”绝然对立、“社会”与“个体”互相敌视的叙述方式,当下乃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文学史写作都将在多元并存的轨道上行进。
三、美丽的误会——《今天》“重写文学史”专栏文本解读
自1991年设立“重写文学史”专栏至2001年停办,《今天》共发表“重写”论文33篇,记录了《今天》与“重写文学史”的十年重合历史。
《今天》“重写”专栏的“编者按”中有一段看似不经意的话,“‘重写文学史’的栏目早就停掉了,十分可惜。本刊早就有意接过这个话题,使之继续。前不久正好收到王晓明先生的一篇来稿,与‘重写’有关,而王又恰是‘重写文学史’一事的始作俑者之一,这自然是个很好的机会”。两个“早就”说明是有意为之,蓄谋已久,与“重写文学史”相逢乃历史的必然;“正好”“恰是”把接续“重写”专栏解释为偶然、意外之举。综合起来,就是“偶然中的必然”。以此观之,专栏第一篇文章《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当是有意组稿所得,而非自然来稿。
《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正是《今天》需要的文章,见解独到、另辟蹊径、质疑、批判,有“我注六经”式的生机和风采;不仅与杂志风格一致,而且可以起到样板、示范作用。当年的《新青年》何尝不是现在的《今天》,它们在做着同一件事——颠覆、打破、反抗,拥有相同的底色和主张——经由刊物促进思想、文化的活跃,进而达成社会政治的变革。《新青年》不是一个纯文学刊物,在它的周围,有同仁的意见分歧,有读者来信的不同反响,有发行收入的经济制约。《今天》虽然是一个文学刊物,但从它的生长轨迹来看,政治的、思想的、文学的“先锋”一以贯之,“《今天》有着丰富的先锋性内涵,无论这一运动和‘文革’的复杂渊源,还是这一运动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联系,以及它在全球化中获得的机遇和位置,都使得《今天》和它推动的先锋运动有着西方先锋派无法比拟的深刻的政治文化内涵”。显然,在这一点上,《今天》希望“重写”专栏上的文章能够远离学术,走出体制的规范和羁绊,把“重写”的种子播散到文本之外,一如既往地“反抗”与“颠覆”。与杂志风格如此之吻合,与专栏初衷如此之一致,这样的文章只能是有意约稿,而非自然来稿。
在《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一文中,王晓明认为,陈独秀之所以创办《新青年》,是因为他相信思想文化是继政治、军事之后的“第三种武器”,“批评时政,非其旨也”仅是表面之举,离开是为了更好地返回,不谈变幻莫测的时政,而是预谋民主、科学这样的宏大政治。胡适回忆,“在民国六年,大家办《新青年》的时候,本有一个理想,就是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离开政治,而在教育思想文化等非政治的因子上建设基础政治”。胡适把《新青年》那份深藏的政治动机表达得更加清楚。尽管在编辑理念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鲁迅等人之间有分歧,陈独秀难耐介入政治的冲动,“本志主旨,固不再批评时政,青年修养,亦不在讨论政治,然有关国家存亡之大政,安忍默不一言?”胡适强调思想学术对政治的间接作用,希望杂志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但是在“实效至上的功利主义”面前,在“国家民族存亡”面前,他们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一致。综合《新青年》产生的语境、编辑理念、文学主张等因素,王晓明认为《新青年》有四大个性特点:“实效至上的功利主义”“措辞激烈,不惜在论述上走极端的习气”“绝对主义的思路”“以救世自居的姿态”。
由于《新青年》是当时唯一倡导新思想的刊物,“它的个性逐渐扩散为整个新文化运动的个性,它所登载的文字,也就构成了一套独特的话语体系”;“《新青年》就像是一把钥匙,可以帮助你打开新文化大厦的许多暗门”[3]。 它的个性渗透到五四新思潮、新文化、新文学的方方面面,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人都不是致力于文学创作和研究的人,他们鼓吹“文学革命”的目的何在?无论是陈独秀的“今欲革新政治,势必革新盘踞于运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4],还是胡适的“我们提倡的文学革命,是要替中国创造一个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才可以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5],目的似乎只有一个:把文学革命作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重要渠道。在《新青年》同仁眼里,文学革命与思想启蒙其实是同一涵义,他们谈论文学、从事创作,无不出自宣传主张之虞,而非思索文学的意义与价值。如此,就可以解释当时的人们为什么热衷“规划”“建设”新文学路径了。王晓明说:“五四新文学的这种独特的诞生方式派生出三个观念:一、文学的进程是可以设计、倡导和指引的;二、文学史应该而且可以有一个主导倾向的;三、文学理论是非常重要的,它完全可以对创作发挥强大的指导和规范作用。”正是在这样三个观念的作用下,文学研究会才担负着组织文学、发展文学之责任,如同今日之“中国作协”;新文学才会在一个个或这样、或那样的主义影响下前行,文学革命、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抗战文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这种轻视、无视文学创作的个性差异,追求群体立场的做法在《新青年》和文学研究会中均可找到源头。
既有文学史让我们耳熟能详了反帝反封建文学、革命文学、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工农兵文学、《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等范畴,王晓明的《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一文让我们透过《新青年》和文学研究会的身影,看到了一段迥然不同的文学史图志。
1993年《今天》第4期“重写”专栏刊发李欧梵的文章《漫谈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颓废”》,以“漫谈”方式考察“颓废”在现代文学中的“出场”和“演出”,为文学史写作提供了一个新坐标。李欧梵指出:“自文艺复兴以来,随着科学、理性和人道主义信念的确立,人们逐渐发展出了一套关于历史是无限发展的乐观主义信念,但在这种乐观主义背后同样伴生出一种新的‘颓废’观念。高度技术的发展同一种深刻的颓废感显得极为融洽。进步的事实没有被否认,但越来越多的人怀着一种痛苦的失落和异化感觉来经验进步的后果。这种‘颓废’感从19世纪中后期法国象征派诗歌中逐步发展起来,并最终形成了一种‘现代性’自身的对立面——‘美学现代性’。”“五四”启蒙对人们最大的冲击是时间观念的改变,即“从古代的循环变成近代西方式的时间直接前进——从过去经由现在而走向未来,所以,着眼点不在过去而在未来,从而对未来产生乌托邦式的憧憬”。这种线性前进的时间想象“经过五四改头换面之后,变成了一种统治性的价值观,文艺必须服膺这种价值观”[6]。由于“颓废”从未作为“现代性”的另一面进入中国文学研究专家、学者的视野,因此,在一切求新的“五四”时代,“颓废”成为一个类同于堕落、衰败的“不道德的名词”。事实上,“颓废”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不仅是反抗资产阶级庸俗现代性的美学立场,而且“它注重艺术本身的现实距离,并进一步探究艺术世界的内在真谛”,为“重写文学史”提供了新路径。不过,洞见与盲区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那样,新的视域可能产生新的遮蔽,在救亡压力远胜于启蒙批判的时代,在一个工业化尚处在起步阶段的国家,颓废现代性的负面作用也就明显了。
1993年《今天》第4期“重写”专栏还发表了陈思和的文章《民间的浮沉——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解释》,题目明确亮出“重写文学史”的新思路,一种既迥异于“官方”又有别于“精英”的文学史阐释方式——民间。陈思和说,“民间”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概念,它和西方的民间社会、公众空间并非同一概念,吸收了其中自由、自为、自在之意。在官方与精英之外,在中心与边缘地带,“民间”以一种特有的隐形结构潜滋暗长,丰富着文学创作和文学史形态。文章从民间在文学史的地位、民间形态与官方形态的关系、民间隐形结构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三个方面探讨了民间的文学价值,认为文学史上的“民间”一直被意识形态的“官方”遮蔽,被处在官方与民间之间按照意识形态的要求创造新文化,献媚于官,愚弄于民,服从现实功利的“精英”漠视;“民间”以反改造、反渗透的姿态潜藏在主流文学之中,构成文本的复杂性、多义性悖论。陈思和认为,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中国文化的三大领域基本处于割裂状态,文化冲突主要发生在官方和精英之间,知识分子虽然提倡白话文,主张大众化,但这只是他们对抗官方文化的语言策略,并不是接纳民间文化,而是把民间视为充满了封建毒素而需要改造的对象。抗战的全面爆发使得官方、精英、民间的互动、融合成为可能,“民间文化形态”得以确立的标志是发生在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期间伴随着官方与民间的改造、反改造等一系列矛盾冲突。20世纪50、60年代的文学作品中经常存在两个文本——“显形文本”和“隐形文本”,前者通过外在故事内容表现主流意识形态的干预;后者受民间文化形态制约,内蕴为文本的娱乐情绪,展现自身的存在价值和魅力[7]。
面对既有文学史“主流与非主流”“左冀文化与非左冀文化”“反帝反封建传统与非五四传统”“进步文学与反动文学”之类的二元对立叙述模式,我们看到,《民间的浮沉》及其关键词“民间文化形态”“民间隐形结构”实现了对过去文学史理论框架的突破,把被遮蔽已久的文学史归还给了文学。相对于王瑶先生开创的“相信文学历史的不断进步,强调社会政治因素对于文学的决定性的影响”的研究范式和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开创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研究范式,陈思和的民间文化形态、民间隐形结构等范畴延续了《上海文论》的“重写文学史”观念:从新的理论视角提出对新文学史的个人创见,文学史研究应当多元化,突出文学史写作的主体性,强调文学史写作的当代性,从而“冲击那些似乎已成定论的文学史结论,激起人们重新思考昨天的兴趣和热情”[8]。
钟爱“不确定”“多元的”文学史阐释是《今天》“重写”专栏的一个重要特点,《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民间的浮沉》都是这样,一个开拓文学史研究空间,一个重建文学史写作范型,与《今天》的风格十分贴近。
《丁玲不简单——毛体制下知识分子在话语生产中的复杂角色》,是李陀亲自撰写的一篇“重写”文章,发表在《今天》1993年第3期上。李陀将丁玲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样本进行拆解,以回答千千万万知识分子“为毛文体感召,并且以毛文体参与话语实践”的深层次原因。对于习惯于“压迫/反抗”“启蒙/救亡”二元对立思维的人们来说,理解1940—1942年间在延安创作《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新的信念》《我们需要杂文》《“三八节”有感》等作品的丁玲轻而易举地放弃批判立场、心甘情愿地归顺到毛文体之中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流行的“救亡压倒启蒙说”“苦难说”只能解释局部,不仅不能令人信服,甚至有点勉强,“仅仅靠政治压力就能使千千万万个知识分子改变自己的语言而接受另一种语言?蒋介石当年施加给知识分子的政治压力并不小,其特务统治形成的恐怖一直延续到台湾,可三民主义话语为什么没有取得绝对霸权,反而大量的知识分子更加倾向革命,倾向马克思主义?问题显然不那么简单。一种话语在激烈的话语斗争中,为什么能排斥其他的话语而最终取得霸权地位,这是由许多具体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是多种社会实践和话语实践在互相冲突又互相制约中最终形成的结果。毛文体或毛话语形成支配性的、具有绝对权威的历史也只能是如此”。
“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深受西方现代性话语影响,毛文体何尝不是一种现代性话语,而且是“一种和西方现代话语有着密切关系,却被深刻地中国化了的中国现代性话语”。但是,在许多研究者看来,毛文体与现代性话语是对立、不相容的,而忽视了毛文体与现代性话语的同一性,“考虑到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历史环境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的种种复杂的压力,考虑到他们不得不在反帝、反列强的前提下追求‘现代化’,则在中国生产出这样一种具有双重性的、适应中国情况的现代性话语,并且用它来推动改造中国的社会实践,这实在是合情合理的。反过来,一旦这样的话语被生产出来,知识分子们为它所吸引,并且积极地参与这种话语的生产,也是毫不奇怪的。在这个意义上,‘启蒙’和‘救亡’的合奏正是中国式现代性话语的魅力所在”。李陀的毛文体的“现代性”观点跳出李泽厚“启蒙与救亡”二分法和人们习见的“压迫说”局限,为文学史写作拓展了解释空间。但他没有看到“革命”“救亡”“集体”对文化造成的巨大破坏,对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权力话语象征的“毛文本”缺少整体认识和反思,以偏概全,很容易走向“现代性”的反面。
在作家作品解读上,《今天》与《上海文论》“重写”专栏没有什么两样,或为曾经的边缘作家的作品“叫好”,发掘其笔下人性深邃、审美的特异;或为熟悉的作家作品进行一番“重写”,批评“革命”“阶级”“工农兵”“集体”“思想改造”如何阻碍了作家主体精神的实现、审美艺术的表现。一定程度上,以作家作品论为主要形式是重写文学史的基础工作,既可以避免整体性“颠覆”“解构”造成的强烈震动,又能够收到积少成多的效果。黄子平的《文学住院记——重读丁玲短篇小说〈在医院中〉》采用隐喻的方式,把《在医院中》置于20世纪的“话语—权力”网格中进行解读,考察小说与历史语境的互文关系,呈现以丁玲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如何在权力话语支配下放弃自我言说的过程。黄子平认为,主人公陆萍走的是一条与鲁迅“弃医从文”相反的“弃文从医”的道路,不是自我追求的启蒙国民的文学道路,而是受党指派到新建的医院做“产婆”的医生道路。在医院中,陆萍积极向上、认真负责、友好善良的工作态度与医院上下愚昧无知、偏狭保守、自私苟安的整体环境格格不入,她提意见、抱怨、抗争,相信“还是杂文时代”,但根据地的严酷现实是:不仅医院人浮于事、官僚主义作风一时难以改变,就是自由表达的“文学也要住院”,知识分子改造、整风运动的结果是——杂文时代夭折,秧歌剧时代来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脱胎换骨”等医学术语取代“科学民主”“个性解放”“批判现实”等文学术语,成为知识分子日常必修的科目。为此,黄子平说:“如果文学家能被‘治愈’,文学真的能被治愈吗?如果文学已被治愈,‘国民性的病根’又于今如何了呢?更重要的是:社会群体真的可以视作与人的身体一样的有机整体吗?文学真的是医治这个有机体的一种药物吗?文学家的道德承诺与他们实际承受的社会角色之间真的毫无扦格吗?”[9]黄子平的诘问是沉重的,意味悠长。
统计学告诉我们,如果选取的样板有足够的代表性,通过对一定数量样本的分析,得出的结论当是有说服力。在考察和梳理了一些“重写”专栏文章之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专栏文章多局限于文学史范畴,为典型的作家作品论,很少溢出文学场阈,更不要说对抗意识形态,与《今天》本身的“反抗”“解构”风格不相协调、不相融洽。这种不协调、不融洽堪称与生俱来,很难突破,特别是对于王晓明、陈思和等一批高校的中青年学者来说,论文写作已经与教学、科研工作不可分割地融在了一起。从文本实践来看,叙事学、语言学、接受美学、形式主义等批评方法不同程度地让“文学回到它自身”,韦勒克、沃伦所言的“内部结构”的不及物性更加不能把反抗、颠覆尤其是体制的批判落到实处。尽管黄子平、蔡翔、孟悦们最大可能地将丁玲、张爱玲、钱钟书等人的作品与外部的意识形态牵连起来,发上一通“迫害说”“从众说”指责,但似乎收效甚微,与《今天》的期望甚远。这也从一个侧面注解了主持人李陀的遗憾——“重写”专栏的许多作者没有考虑到在《今天》上发表文章有何特殊性。这是“重写”论者的尴尬,亦是《今天》的尴尬——在海外,失去了意识形态束缚,“重写文学史”不再是一个富有冲击性的话题,很难获得一种变相的话语权力。
除“论文体”文本与《今天》的先锋风格不协调、不默契之外,《今天》更大的尴尬来自“重写”论者星散,组织不起队伍,形成不了规模,这种个体化的自言自语式写作无法满足《今天》“反抗”体制的心理期待。与之前《上海文论》时期的“重写文学史”动议引发的群体热议、规模效应构成了极大反差,碍于国内1989年学运风波影响,“重写”论者仅仅把《今天》作为他们在海外的临时栖居地、《上海文论》的备胎。在学术范围内讨论文学史写作,“审美原则”“多样性”“学科建设”是陈思和、王晓明在“主持人的话”中反复提到的词汇,而非体制层面的对抗,更不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干预,这种意图、宗旨上的分歧注定两者的“重逢”有点阴差阳错,有始无终。难怪十多年后,专栏主持人李陀深有感触地说:“现在回头看看,当初开辟这样一个专栏,就《今天》的性质和特色来说,并不合适。”[2]2专栏还是那个专栏,加盟成员陈思和、王晓明们的热情依旧,但刊物风格不同了,当年以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作协的青年教师、学生为主体的“圈子”不在了,来自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中国作协的资深文学史家王瑶、严家炎、钱理群等人的声援没有了,时过境迁,留给《今天》“重写文学史”专栏的是大环境的文学边缘化、学术专业化,小环境的文学史写作已经进入到一个实践操作时期,而不再是理论层面的争鸣时期。2001年夏,《今天》“重写文学史”专栏黯然收场,终结了它与重写的十年之缘。
当然,这样说并非否定《今天》“重写”专栏十年的存在价值,更不是否认重写文学史行为的意义。如果把重写文学史的历史拉长来看,《今天》十年不仅意味着新的研究空间的开拓,也收获了文学史研究的新视角、新方法、新成果,比如能否从文学期刊的经纬、读者接受的理路编写一部期刊文学史?能否以跨语体交际的修辞变迁写作一部话语文学史?能否突破文学史写作的学术规范写作一部抒情文学史?能否以知识分子的结社交游活动写作一部编年文学史?……应当说,在这些方面,王晓明的文章《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陈思和的《民间的浮沉》等文章给了我们不少启示,刺激了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报刊、出版中介研究,丰富了文学史研究方法和实践,理当是重写文学史之一部分,与《上海文论》时期的重写文学史构成了时间上的前后序列,空间上的互文参照。
参考文献:
[1]王晓明,主编.批评空间的开创[C].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
[2]李陀,编选.昨天的故事:关于重写文学史[C].北京:三联书店,2011.
[3]王晓明.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J].今天,1991(3,4).
[4]陈独秀.文学革命论[J].新青年,1917,2(6).
[5]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J].新青年,1918,4(4).
[6]李欧梵.漫谈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颓废”[J].今天,1993(4).
[7]陈思和.民间的浮沉:从抗战到“文革”[J].今天,1993(4).
[8]陈思和,王晓明.主持人的话[J].上海文论,1988(4).
[9]黄子平.文学住院记:重读丁玲短篇小说《在医院中》[J].今天,1992(4).
(责任编辑刘海燕)
Meeting and Overlapping between
“Rewriting Literary History” andToday
LIU Zhong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Key words:Rewriting Literary History;Today; meeting; overlapp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