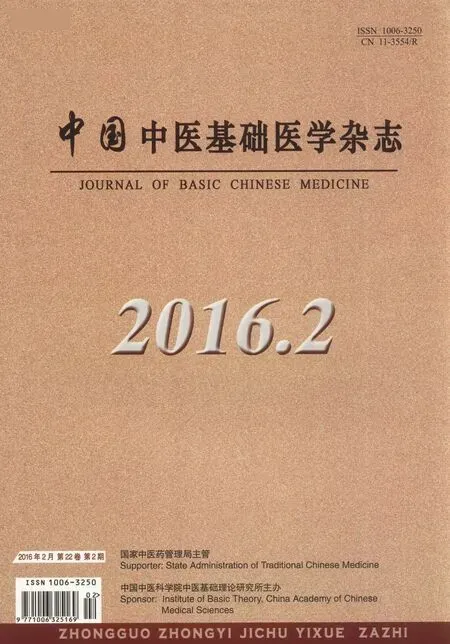论《黄帝内经》中肝与情志的多重关系
李永乐
(内蒙古医科大学中医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 010110)
论《黄帝内经》中肝与情志的多重关系
李永乐
(内蒙古医科大学中医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 010110)
情志与五脏的对应关系是中医学的固有命题,而《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对于五脏与情志的关系论述不仅存在着一一对应模式,而且存在着一对多的复杂模式。故重点结合《内经》原文对肝与怒、恐、忧、惊之间的关系分别加以分析,从脏腑生理功能、生理特性的角度阐述肝与各种情志形成的内在机制,指出肝与情志的一一对应模式多反映人体的生理情况,一对多模式反映的是人体病理情况,阐明肝与情志之间的多重复杂关系,为情志病证的临床治疗提供一定启示。
肝;情志;关系;内经
情志是中医学对情绪的特有称谓,是人对内外环境变化进行认知评价而产生的涉及心理、生理两大系统的复杂反应[1],在《内经》中已论及情志的产生、与人体脏腑的关系、情志致病等各种问题。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指出,肝“在志为怒”,心“在志为喜”,脾“在志为思”,肺“在志为忧”,肾“在志为恐”,认为情志与脏腑间存在着按照五行配属关系的一一相对应模式,这也是现代中医理论体系中关于脏腑与情志关系的基本观点。《灵枢·邪气脏腑病形》云:“愁忧恐惧则伤心。”《灵枢·本神》指出,怵惕思虑伤心、愁忧伤脾、悲哀伤肝、喜乐伤肺、大怒伤肾等,认为多种情志可伤及五脏。《灵枢·本神》云:“肝气虚则恐,实则怒”,“心气虚则悲,实则笑不休”。《素问·宣明五气》云:“并于肝则忧,并于脾则畏。”《素问·刺疟》云:“肺疟者,令人心寒,寒甚热,热间善惊,如有所见者。”又指出五脏病变可出现多重情志改变,表明脏腑与情志之间还存在多重复杂对应关系。其中,《内经》认为肝脏与怒、恐、忧、惊多种情志对应相关,本文重点对此深入阐述,以明经旨。
1 肝与怒
怒即愤怒、气愤,是由于愿望受阻、行为受挫而产生的情绪体验,是一种向外宣泄的情绪,通常是一种正常的情志活动,适度的发泄对维持人体正常的生理平衡有着重要作用。《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在志为怒”,指出怒是肝之志,究其原因主要与肝的生理功能和生理特性密不可分。一方面,肝在五行中属木,木曰曲直,性喜条达而恶抑郁,具有主疏泄的生理功能,能调畅气机,促使气血运行畅通。《素问·八正神明论》云:“血气者,人之神”,指出气血是人体精神情志活动的物质基础。因此,肝通过主疏泄的功能,调畅气血,调节人的情志活动,对保持情志活动正常有重要作用。另一面,肝为将军之官,性刚强,具有主升主动、刚强躁急的生理特性。《素问·四时刺逆从论》曰:“血气上逆,令人善怒”,故各种原因导致气机失调,令肝气升发、疏泄太过、气血上逆皆可出现“怒”。因此,《素问·藏气法时论》曰:“肝病者,两胁下痛引少腹,令人善怒。”《素问·调经论》曰:“血有余则怒。”指出,肝病时出现愤怒的异常情志表现。针对此类问题,临床中常用的龙胆泻肝汤、丹栀逍遥丸之类,皆是通过降泻上逆之肝气(火)来止病证中之愤怒症状。
2 肝与恐
恐即恐惧、害怕,是遇到危险又无力应付而出现的害怕不安的一种情绪,是人内心的一种感觉,人皆有之。恐作为七情之一,本与五脏的肾相对应,为肾之志。然而《内经》多篇文章指出,肝病时可出现恐惧的异常情志表现。如《灵枢·本神》曰:“肝气虚则恐,实则怒。”《素问·调经论》曰:“血有余则怒,不足则恐。”《素问·刺疟》曰:“足厥阴之疟……意恐惧气不足。”《素问·藏气法时论》曰:“肝病者……虚则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善恐如人将捕之。”,从原文中不难发现,“恐”在《内经》中多见于肝病之虚证中。《景岳全书》进一步明确指出:“气强者不易惊,而惊恐者必肝胆之不足也。”认为恐惧是由肝胆之不足所引起。张志聪对此阐释道:“肝者将军之官,故气虚则恐,实则怒。”认为肝为将军之官,体阴而用阳,虚则气血衰少不能濡养肝脏,肝之功能不足,邪气来犯,不能发挥其性刚强之性而心生恐惧,故肝虚时可出现恐惧之症。《素问·经脉别论》又云:“有所坠恐,喘出于肝”,指出恐惧亦可病及于肝脏,表明肝与恐之间有着密切联系。李中梓在《医宗必读》论及恐有肾肝心胃四脏之分中指出:“治肝胆者,宜养阴,枣仁、山茱萸、牡丹皮、白芍药、甘草、龙齿之属。”可采用养肝血、柔肝阴之剂以治肝虚之恐。
3 肝与忧
忧即担忧、忧愁,是一种心情低沉、兴趣减少甚至丧失为特征的情绪状态,也是一种抑郁性的情绪。《素问·宣明五气》云:“五精所并……并于肝则忧。”指出邪气侵扰肝脏时可出现“忧”之情绪异常。《灵枢·本神》曰:“忧愁者,气闭塞而不行。”认为忧愁的产生与气机郁滞闭塞不畅有关。秦伯未在《谦斋医学讲稿》中曾指出:“肝气郁结与一般肝证恰恰相反。肝气证是作用太强,疏泄太过,故其性横逆;肝气郁结是作用不及,疏泄无能,故性消沉。[2]”认为肝气逆易出现愤怒等亢奋情志,肝气郁易出现情感抑郁、表情淡漠、善太息、悲忧善虑等抑郁状态,故在肝病时,肝疏泄不及,气郁滞不得伸展,可出现抑郁、消沉的情绪“忧”。现代流行病学调查[3]亦支持此种观点,认为肝气逆证呈现个性的外向倾向,情绪易于失控,易产生愤怒攻击反应;肝气郁证呈现个性的内向倾向,情绪体验深而不易外显,易产生压抑反应。针对性类病证,《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曰:“木郁达之”,提出肝郁致忧愁之症的治疗法则。林佩琴在《类证治裁·郁症论治》曰:“肝胆郁,血燥结核,加味逍遥散”,指出柴胡疏肝散、逍遥散等疏肝解郁、调畅气机之剂均是缓解患者忧愁情绪的临床可选之方。
4 肝与惊
惊即惊惧、惊骇,是突然遭受意料之外的事件而引发的紧张惊骇的情绪,是一种由外界刺激引发的情志活动。《素问·金匮真言论》曰:“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其病发惊骇。”《素问·刺热》曰:“肝热病者,小便先黄,腹痛多卧,身热。热争则狂言及惊。”《素问·大奇论》曰:“肝雍,两满,卧则惊……肝脉鹜暴,有所惊骇。”认为肝病时可出现“惊”这一异常情绪。《灵枢·本神》曰:“肝藏血,血舍魂。”王肯堂《证治准绳》曰:“魂不安则神动,神动则惊。”指出“惊”这一异常情绪与肝藏血舍魂有关。魂即是人的思想意识、情志意识、知识技能等精神活动,喜静,动则出现精神活动异常。魂以血为物质基础,肝属木主藏血,故魂藏于肝。当邪气侵扰肝脏时影响肝的藏血功能,可使肝所藏之魂不安而出现精神情志异常,受到外界刺激易出现惊骇不安,故张景岳《类经》在注释《素问·痹论》“肝痹者,夜卧则惊”时说:“肝藏魂,肝气痹则魂不安,故主夜卧则惊骇。”《素问·至真要大论》云:“惊者平之”,指出针对惊惧之情绪异常可采用重镇敛摄之品进行治疗,故叶天士在《临证指南医案·肝风》中针对惊怖不寐“治以酸枣仁汤、补心丹、枕中丹加减,清营中之热,佐以敛摄神志”,并将该理论应用于临床实践。
综上所述,《内经》中脏腑与情志之间存在着多重复杂的对应关系,肝与“怒、恐、忧、惊”多种情绪变化相关仅是其中的重要体现之一,与肝的生理功能和生理特性密切不可分。从《内经》原文来看,肝与怒一一对应模式是人体生理情况下的重要表现,而怒、恐、忧、惊多种情绪异常变化是肝病时出现的重要症状。因此,肝与情志的一一对应模式更多反映的是人体生理情况,一对多的复杂模式是人体肝脏的病理情况的反映。《丹溪心法·六郁》云:“气血冲和,万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人体气血失调是导致多种疾病的重要原因,而肝不论主疏泄、藏血的生理功能,还是肝为刚脏、主升发的生理特性,均与人体之气血关系密切,因此肝之功能失调导致气血逆乱亦是引发多种疾病的内在机制。《内经》中肝病时出现多种情志异常即是很好体现。张山雷云:“肝气乃病理之一大法门,善调其肝,以治百病。胥有事半功倍之效。”故古今医家多从肝论治各种情志疾病,而肝与情志之间的多重复杂关系及内在机制是其重要理论基础。随着医学模式转变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的综合模式,精神心理因素成为影响人体健康的重要一环。由于近年来社会环境、工作环境等的变迁,情志疾病发病逐渐增多并日益受到重视,而肝与多种情志活动的多重关系必将为中医治疗情志疾病提供一定思路,使临证治疗亦不拘泥。
[1]孙广仁.中医基础理论[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 224.
[2]秦伯未.谦斋医学讲稿[M].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78: 98.
[3]乔明琦,张惠云,王文燕,等.肝气逆、肝气郁两证发病与个性特征和情绪的相关性研究[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7,13(5):349-352.
Multipl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iver and Emotions in the Inner Canon of Huangdi
LI Yong-le
(Schoo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Inner Mongolia Medical University,Hohhot 010110,China)
Correspondence between emotions and five viscera are inherent in Chinese medicine proposition.Five viscera and emotional relationship is not only the existence of corresponding model,and there are many complex models in the Inner Canon of Yellow Emperor.In order to reflect the multiple and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iver and the emotions and providing some inspiration in clinical treatment of emotional disease and syndrome,the paper focuses on the liver and anger,fear,grief,terror relations between them,and demonstrates the intrinsic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he liver with a variety of emotion in the physiological and pathological conditions.
Liver;Emotion;Relationship; Inner Canon of Yellow Emperor
R395
A
1006-3250(2016)02-0154-02
2015-06-15
李永乐(1982-),男,内蒙古包头人,在读博士,从事《黄帝内经》理论与中医药的临床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