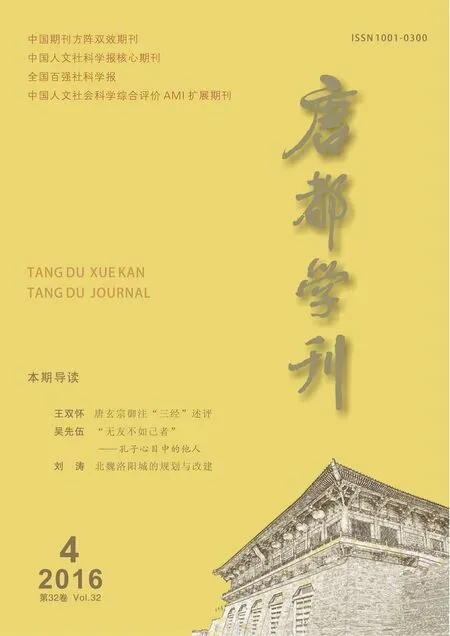王船山对张载“太虚即气”本体论议题的承续与开新
陈力祥, 王志华
(湖南大学 岳麓书院,长沙 410082)
【关学研究】
王船山对张载“太虚即气”本体论议题的承续与开新
陈力祥, 王志华
(湖南大学 岳麓书院,长沙410082)
王船山以张载为宗师,“希横渠之正学”,其哲学思想是张载哲学思想的延续与价值开新。以“太虚即气”为议题,由张载之“太虚即气”到船山之“太虚一实”,由张载之“气化”到船山“气之化也”,彰显出船山哲学本体论对张载哲学本体论的承续。由船山气之化的差异性导致宇宙万物的层级性,彰显出船山对张载之超越。
张载;王船山;气;本体;太虚即气
王志华,男,山西临汾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宋明理学研究。
船山哲学乃是张载哲学基础上的正学与开新,学术界已成定论。如嵇文甫先生认为船山“宗师横渠,修正程朱,反对陆王”[1];船山儿子王敔在其所作的《大行府君行述》中这样来概括他父亲船山的学术渊源:“至于守正道以屏邪说,则参伍于濂、洛、关、闽,以辟象山、阳明之谬,斥钱、王、罗、李之妄。”[2]73船山在自撰的墓志铭中也明确说道:“希张横渠之正学。”而且船山在晚年于67岁完成了《张子正蒙注》一书,又于72岁进行了修定[3]283,可见其对张载的推崇。清人邓显鹤评论船山说:“生平论学,以汉儒为门户,以宋五子为堂奥。而原本渊源,尤在《正蒙》一书,以为张子之学,上承孔孟之志,下捄来兹之失。”[2]410足以说明船山对张载之学的正学与开新。
一、由表入里:从张载之“太虚即气”到船山之“太虚一实”
船山对张载气本论思想的继承与发挥主要体现在他的《张子正蒙注》一书,此书由船山通过对张载《正蒙》做注而成。在张载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太虚”是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事实上,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张载之标举太虚,亦有独特之地位。”“张载之前,没有思想家以‘太虚’做为其思想体系的重要概念。所以,张载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位以太虚作为重要概念的思想家。”[4]59因为张载坚持气本论,所以“太虚”一词经常与“气”连用,比如在《正蒙·太和》中就提到:“虚空即气”[5]8。张载乃气本论者,与宋明理学的主流理学观或心学观不同,虽然这是学界的共识,但对张载气本论的解读却并不一致。出现这种分歧的关键在于对“即”字的理解:一种观点把“即”理解为“是”,那么“虚空即气”也就可以理解为“虚空是气”。“虚空”“太虚”虽然是气,但却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所说的气,而是“气的本来存在状态,他称这本然状态为本体”。我们一般意义所说的气“不过是这种清稀微细的太虚之气凝聚而成并可以看到象状的暂时形态”[6]。另一种观点把“即”理解为“不离”之意,牟宗三先生就坚持这种解读,他在《心体与性体》一书中说:“‘虚空即气’,顺横渠之词语,当言虚体即气,或清通之神即气。此‘即’字是圆融之‘即’,不离之‘即’,‘通一无二’之即,非等同之即,亦非谓词之即。”[7]牟先生之所以坚持如此解读,因为在他看来,只有把“即”理解为“不离”,才可以避免张载哲学的唯气论倾向[4]141。而如果一旦把张载哲学理解为唯气论的哲学,在牟先生看来,价值也就无法得到安顿。
对张载“虚空即气”之气本论的解读大体呈现为以上这两种观点,那么船山对张载“虚空即气”之气本论的解读又是如何呢?只有通过对比解读,才能进一步彰显船山对张载“虚空即气”之气本论解读的独特性。船山明确说道:“太虚,一实者也。”[8]402“人之所见为太虚者,气也,非虚也。虚涵气,气充虚,无有所谓无者。”[8]30首先,船山在这里用了“太虚,一实者也”、“太虚者,气也”的句式,这种句式在古代汉语中就是要明确表示一种主谓关系,说明“太虚”是一种实(在),这种实(在)不是别的,就是气。其次,“虚涵气,气充虚”并不是说“虚”作为空间包涵着“气”、“气”作为物质充满着“虚”,而是对张载原文“气之聚散于太虚,犹冰凝释于水”所作的注,所以应该理解为“虚”作为本体始终涵摄着“气”,“气”作为运动的物质(之用)不断扩充着“虚”(之体)。“散而归于太虚,复其缊之本体,非消灭也。聚而为庶物之生,自缊之常性,非幻成也。”[8]19因为这句话是对“气之为物,散入无形”原文的注,显然是说“气”返归于“太虚”,意味着又回到了它缊的本体状态,不是如道家所说的消失与灭无;而当“气”聚为万物时,也就必然会将其缊的性实实在在地赋予万物,不是如佛家所说的皆是幻象。从这一角度来讲,“太虚”或者“太虚之气”就是指“气之清虚至极的状态”[4]66,“太虚”终归还是“气”。
船山从“体—用”的角度说明了太虚与“气”的关系*此处的“气”包括由“太虚”而凝聚的气以及由气而凝聚的万物两部分,相对于“太虚”之“体”而言,无论是“气”还是万物,都是一种“用”。。“聚而成形,散而归于太虚,气犹是气也。神者,气之灵,不离乎气而相与为体,则神犹是神也。聚而可见,散而不可见尔,其体岂有不顺而妄者乎!”[8]23无论是“气”聚而成物,还是散而归于“太虚”,作为最根本的“气”始终没有发生改变。作为“气之灵”的“神”随着“气”的聚散也始终与气相为体用而时刻在起作用,对于可见的物是如此,对于不可见的虚气也是如此。所以船山才会接着在后一条注文中说:“凡虚空皆气也,聚则显,显则人谓之有;散则隐,隐则人谓之无。神化者,气之聚散不测之妙,然而有迹可见。”[8]23我们感官所能感觉到的一定是变化所留下的“痕迹”,“痕迹”的所以然也即是“气之聚散不测之妙”(“神化”),虽然不能为感官所捕捉到,但其同样也是“顺而不妄者”,因为体—用的一致性必然要求“虚气”不二。气聚成物为显,称其为“有”;物散归气为隐,称其为“无”。但船山一般不喜欢用“有—无”而是用“显—隐”来说明这种体—用关系,一方面固然是出于他反对道家“无中生有”与“有化为无”的考虑,另一方面则是他彻底坚持气本论的必然结果,“气”才是宇宙得以永恒的最终维系者,“其(引者按:指气)聚而出为人物之形,散而入于太虚则不形,抑必有所从来”[8]23。“抑必有所从来”说明了气化的根据,也就引出了颇为关键的一个问题:既然太虚是气,是否二者之间就不存在着区别呢?“太虚即气,缊之本体,阴阳合于太和,虽其实气也,而未可名之为气;其升降飞扬,莫之为而为万物之资始者,于此言之则谓之天。气化者,气之化也。阴阳具于太虚缊之中,其一阴一阳,或动或静,相与摩荡……”[8]32太虚虽然是气,但却是一种作为缊的本体之气。严格来讲,太虚还不可以被命名为气,因为只要言气就已经落到了物的层面。从狭义上来说,可以认为太虚只是气化(为万物)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也可被称之为“太和”。“太和”之中具有阴阳二气以及一阴一阳“或动或静,相与摩荡”的作用,这种二气交感的作用正体现了宋儒所说天道之生生不息的生命状态,不是有意为之于万物的蓬勃,但却又可以造就万物的生死轮回。“天生万物,所受虽不同,皆无须臾之不感,所谓性即天道也。”[5]63天不息地赋予万物以性,万物又无时地循当然之则相感。就此一层意义来讲,“太虚”又可名为“天”。毫无疑问,船山的这一思想正是对张载“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5]9之思想的继承与展开。“凡虚空皆气也,聚则显,显则人谓之有;散则隐,隐则人谓之无。”“其聚而出为人物之形,散而入于太虚则不形,抑必有所从来。”[8]23虚空、太虚既然作为本体的气,也就意味着必然要化生万物。船山称气聚为物为显,称物散为气为隐,隐显交替显示出太虚本身气化的复杂环节。“升降飞扬,乃二气和合之动几,虽阴阳未形,而已全具殊质矣。‘生物以息相吹’之说非也,此乃太虚之流动洋溢,非仅生物之息也。”[8]27气化一系列的复杂环节显示了太虚作为本体的巨大生命力与创造力。太虚之中蕴含着二气生化的微妙征兆(“二气和合之动几”),虽然还没有显露出明显的阴阳功能,但已经具备了造化的全部殊质。为了说明此种问题,船山还批评了庄子“生物以息相吹”的说法,认为这不仅仅只是局限于生物的相互吹息,同时也是整个太虚内部流动洋溢的状态。“太虚者,本动者也。动以入动,不息不滞。”[9]1044太虚本身是运动不息的,从无停滞。作为气的太虚,尤其又是作为宇宙本体的太虚,里面充满了浑沦的阴阳之气,“阴阳异撰,而其缊于太虚之中,合同而不相悖害,浑沦无间”[8]5。阴阳之气因为功能、性质的差异(“阴阳异撰”),二者缊于太虚之中,屈伸往来,相摩相荡,异质而同趣,归一而分殊,弥纶于太虚、万物之中,天地、宇宙之间(“合同而不相悖害,浑沦无间”),既是一种宇宙原初的和谐,也是万物最终所要达到的最高和谐。整个大秩序的顺理无妄有条不紊,一方面固然需要有湛然清通的本体太虚之气,一方面也需要有神妙精微的气化过程。船山的本体太虚之气,太虚之气犹如江河的源头,想要真正展示这一源头的活力与能量,就必须呈现江河的全幅景观,在这里也就是要把神化之气气化的整个过程揭示出来。
二、由浅入深:从张载之“气化”到船山“气之化也”
“船山把宇宙演化分为两个基本的阶段,即变合以前的气体阶段与变合以后的气化阶段,气体即气之体,亦即气之实体、气之本体。”“气化即气之用,在气化阶段阳变阴合,生成万物。”[3]189,189-190船山对张载“虚空即气”之气本论的解读其实就是在讨论变合以前的气之实体,明确了这一点,也就可以进一步讨论船山的“气化”思想,即气化过程中生成万物的问题。
船山首先指出:“气化者,气之化也。”[8]32“时行物生,不穷于生,化也。”[8]80时节运行万物产生而又不穷尽于生就是“化”。“万有之化,流行成用。”[9]979万有法象的生生不已,正是天道流行以成其妙用的体现。所谓的“气化”,归根到底就是“气”的一种作用表现,船山的这个思想显然是对张载“气化”思想的继承与展开。所以这里就有必要先讨论一下张载对“气化”的阐释:“天道四时行,百物生。”[5]13“道”对张载而言,就是“气化”,上面曾引述过他的一条表达:“由气化,有道之名。”“化”是与“变”相对而言的,“变,言其著;化,言其渐”[5]70。“变”揭示的是一种明显的改变,“化”则暗示着一种不明显的变化,二者之间的区别只在于显隐的不同,在于人是否可以用感官来把握。感官可以体会到四时的运行与百物的生生,但却不能察知到这种运行的不息之处与生生的流行之处。天道之“化”虽难以为人的感官所感知,但并不妨碍其本身作为“气”的功能形态而发生作用,因此张载说道:“天之化也运诸气。”[5]16太虚(“由太虚,有天之名”)之化的作用完全是气的运行与扩展而已。实际上,在张载看来,“气”—“化”的关系正是一种体用关系的呈现,“神,天德;化,天道。德,其体;道,其用,一于气而已”[5]15。单看这里的论述,似乎是在说德体道用,但只要将“德体道用”的思维往前推论,就会不难得出“神体化用”的结论。在张载的体系中,“神”始终是与“天”“不测”“一”相联系的,而这三者在根本上又是一而不二的,我们可以看一下他下面的几条论述:“鬼神,往来、屈伸之义,故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5]16“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5]9鬼神就是阴阳二气往来、屈伸之妙合变化的良能,这一功能就“天”的意义上来讲被称之为“神”。因为阴阳二气的作用总是精妙细微的,无法明显地捕捉,但其作用却是显而易见并且是遵循法则而有常,所以才说:“天之不测谓神,神而有常谓天。”[5]14但“神而有常”之所以可能的根本保证却在于“一”。“气有阴阳,推行有渐有化,合一不测谓神。”[5]16这里明确提到“合一不测谓神”,阴阳之气的渐化推行,只能说是不测的妙用,但这种妙用之所以显示出“神”的真正原因就在于“合一”,“合一”就是“一于气而已”。“神”“化”与“一”在张载的思想体系中是很重要的哲学范畴,关于它们之间的关系他的论述比较多,我们可以再看两则经典的表达:“一物两体,气也。一,故神(自注:两在故不测);两,故化(自注:推行于一)。此天之所以参也。”[5]10“若一则[有两],有两亦[一]在,无两亦一在,然无两则安用一?不以太极,空虚而已,非天参也。”[5]233此处的讨论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气(之体)”的层面,也就是终极本源的问题,除了气的存在之外,再没有其他的存在。一个层面是“气化(之用)”的层面,就在“两化(之用)”过程中始终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一(之体)”而言,即“神”;就“一(之体)”的作用必须展开为“两化(之用)”而言,即“化”。“一”(体)之“神”与“两”(用)之“化”合而言之就构成了天之“参”*“参”字既可读作“参加”之“参”(cān),也可读作数字之“参”(叁)(sān),行文此处读作数字之“参”,这样与“两”相互一致,比较符合张载思想的原意。。但实际上,天并不真的就显示出是“参”,而自始至终都是“气”而已。以上通过对张载气化思想的考察,大体可以得出船山“气化者,气之化也”的思想是对张载气化思想的继承。
以上述张载“气化”思想的理解作为基础,下文再来看船山本人对“气化”的承续。船山之“气化”有两大特点:一是侧重于论“气”的材质性,即作为构成万物的质料,注重一贯动态的整体呈现;一是侧重于“化”的类别性,即在万物之化中有物之化与人之化的区别,注重静态结构的细微分疏。先看他从“气”之材质性的角度对气化的论述。“天之所以为天而化生万物者,太和也,阴阳也,聚散之神也。”[8]369“而”字在此处不宜被理解为表示并列关系的连词,而是同《中庸》“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10]一句中“而”字的用法一致。天之所以为天就在于天能够化生万物,而天之化生万物的根据则是太和、阴阳与天之聚散的德性(张载原文:“神,天德。”)。三者之中,“太和”又是“阴阳”与“聚散之神”的根本。“天无体,太和缊之气,为万物所资始,屈伸变化,无迹而不可测,万物之神所资也。”[8]50“资”就是依靠,依据,主宰。“天”本身就是作为体而存在的,也就是“太和缊之气”,它是万物之存在所依靠的根据(“所资始”),也是万物之变化神妙的主宰(“所资”)。“阴阳者,二气缊,轻清不聚者为阳,虽含阴气亦阳也;其聚于地中与地为体者为阴,虽含阳气亦阴也。凡阴阳之名义不一,阴亦有阴阳,阳亦有阳阴,非判然二物,终不相杂之谓。”[8]57阴阳之作用的体现就是阴阳二气缊的结果。实际上,阴阳只是表示两种不同性质的力量,作为存在层面的“气”来讲,并不存在着阴阳两种不同性质的气(“非判然二物,终不相杂之谓”)。阴阳二气通常是浑沦无间的,否则就不可能发挥出太和缊的效果。“五行之化气合离融结,弥纶于地上,而与四时之气相为感通,以为万物之资,是亦天地阴阳相交之所成也。”[11]562太和缊的阴阳二气进一步聚为五行之气与四时之气,五行之气充满天地之间,又与四时之气相感通相生生,成为万物得以形成的直接质料。从太和缊之气、阴阳二气到五行之气、四时之气,再到万物的产生,这一过程就被称之为“气之化”。“化者,天地生物之事。”[8]355“天以神御气而时行物生。”[8]78“化”的过程既是天地生物的过程,同时也是“天以神御气”的过程,两者作为同一气化过程中的隐显两个层面,并行交错,相感通而生生不已。
以上是从一贯的动态过程来把握“气化”的生生流行,下面将从静态的层面来论述万物的“气化”结构。“天地之法象,人之血气表里、耳目手足,以至鱼鸟飞潜,草木华实,虽阴阳不相离,而抑各成乎阴阳之体。”[8]27-28张载在谈到“法象”时说:“凡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尔。”[5]9船山注言:“日月、雷风、水火、山泽固神化之所为,而亦气聚之客形,或久或暂,皆已用之余也。”[8]34“糟粕”原意为造酒之后所剩渣滓,引申为陈迹。日月、雷风、水火、山泽、人之血气表里、耳目手足,以至鱼鸟飞潜、草木华实在内的天地法象都属于“已用之余”,是经过神化作用之后所遗留下的可以把捉到的陈迹。尽管它们作为短暂的客形(相对于气化而言),但在维持其形质的阶段中,阴阳之气的两种功能一直在起着作用。“形之撰,气也。”“形无非气之凝”[8]407,408。“撰”为实在意。形体作为实在的承载者,无非是由气凝聚而成,气构成了形体的全部材质。“天地之产,皆精微茂美之气所成。”“气之所自盛,诚之所自凝,理之所自给,推其所自来,皆天地精微茂美之化,其酝酿变化,初不丧其至善之用。”[8]420*船山此处虽言“至善之用”,但此处的“至善”并不具有通常所说的与“恶”相对的伦理价值这一层意义,这里只是要说明万物本身的自然变化可以被归结为“气”之用。“诚”也是实在意,也就是形体。凡是由天地所产生的法象形体,要推究它们(在发生学意义上)最根本的来源,最终都可以归为一种“精微茂美之气”;而且其形体之结构性功能的发挥即理之作用的彰显也是来源于“精微茂美之气”最初的“至善之用”。“天之化生万物,人与禽兽并生焉。皆二气五行之所妙合而成形者也。”[12]511天地化生万物,不但要经历如前面所说的从太和缊之气、阴阳二气到五行之气、四时之气,再到万物之产生这一复杂的“气化”过程,而且万物形体本身也是由“二气五行之所妙合”而直接构成的。整个“气化”的过程不存在阶段性的中断,而是整体涵摄性地扩充并被赋予万物。“太虚之气,无同无异,妙合而为一,人之所受即此气也。”[8]123在万物禀赋“气化”的过程中,几乎无一例外,就连人的禀赋都是如此,因为本源的太虚缊之气并不存在差异性(“太虚之气,无同无异,妙合而为一”)。“人物之生,莫不受命于天。”[11]1115“天地人物之气,其原一也。”[8]328“人物同受太和之气以生,本一也。”[8]221人与物的现成生命形态归根到底都是天命的结果,作为本原所禀赋的气是一样的,因为本一的太和之气具有绝对的同一性。在这一点上,不仅人与物没有差异,就是圣人所禀赋的气也没有任何特殊之处。“人物之生,皆缊一气之伸聚,虽圣人不能有所损益于太和。”[8]44“日月之发敛,四时之推迁,百物之生死,于风雨露雷乘时而兴、乘时而息,一也,皆客形也。有去有来谓之客。”[8]18“唯万物之始,皆阴阳之撰。”[9]42万物生死轮回的不息,日月发光于外,收敛于内,四时循环推移,风雨露雷这些自然现象兴息有时,它们对于作为真正开端之实在的阴阳而言都是短暂的有去有来的客体呈现,唯有那缊之气的伸聚才是永恒的“主形”。
三、崇“本”开新:船山气化差异性层面彰显出对张载之超越
船山认为,虽然太虚之气作为万物的“本”与“原”是一,没有差异,但在气化为万物所禀赋的过程中却是有差异的,而且这种差异显得很悬殊,这样也就可以合理地解释天地世界的丰富性与人之性命的虚灵性。“一方面肯定气化流行这个自然宇宙的客观存在,另一方面则亦强调人是此气化流行而抟聚成之最优秀者,人实是天地之心,人能诠释宇宙,润化宇宙及缔造者,而且宇宙经由人之诠释、润化及创造之后方成其为人的宇宙。”[13]这是船山论气化独有的两个层面,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下文将重点讨论船山论气化的差异性,以彰显船山于气化过程中对张载的超越性。
气化的过程就是气之聚而成物,物又散而归气,这是一个客观的流行过程,没有一息的停滞。“气之聚散,物之死生,出而来,入而往,皆理势之自然,不能已止者也。”[8]20正是在基于气之聚散,造成了万物品类之间的差异。“植物根于地中,而受五行已成形之气以长。阳降而阴升,则聚而荣;阳升而阴降,则散而槁。以形而受气,故但有质而无性。”“动物皆出地上,而受五行未成形之气以生。气之往来在呼吸,自稚至壮,呼吸盛而日聚,自壮至老,呼吸衰而日散。形以神而成,故各其含其性。”[8]101植物的生命禀赋与成长来于五行之气,受阳气影响时,就呈现为欣欣向荣的状态;受阴气影响时,就表现为保藏含蓄的收敛状态。因为主要是(植物的)形体受气之作用的影响,所以植物只有气聚以成的质料,而没有气聚以凝的灵性。动物则不同,所禀赋的是比五行之气更为精微的还未成五行之形时的气,生命形态的盛与衰取决于所呼吸之气的聚与散,在呼吸之气的聚散过程中,一方面形体得以茁壮,另一方面在形体茁壮的同时,由形而来的神逐渐成为各自的性。“草木有气而无情,禽兽有情而无理,兼情与理合为一致,乃成乎人之生。”[12]218草木只有气而没有情,禽兽虽有情但缺乏理,二者都有偏颇,将情理合为一体,于是就有了人的产生。“人者,两间之精气也,取精于天,翕阴阳而发其冏明。”[14]与动植物都不同而又更为精微的是人所禀赋的精气,这种精气直接取自太虚湛一的清气(“取精于天”),妙合阴阳两种神化作用而显发出人的炯炯灵明。“人者,阴阳合德之神所聚,而相阴阳以协天地万物之居者也。”[8]369人既然作为阴阳神妙化合之聚的产物,当然也就可以配合天地成就万物。“天以神御气而时行物生,人以神感物而移风易俗。神者,所以感物之神而类应者也。”[8]78天地以气化之神造就了万物与四时的运行,人借气的神妙之用应运四时而感通万物以改变风尚而成一代良法美俗,这也正是船山所说的“感物之神而类应”。“阴阳之始本一也,而因动静分而为两,迨其成又合阴阳于一也。如男阳也而非无阴,女阴也而非无阳。以至于草木鱼鸟,无孤阳之物,无孤阴之物,唯深于格物者知之。时位相得,则为人,为上知;不相得,则为禽兽,为下愚;要其受气之游,合两端于一体,则无有不兼体者也。”[8]37与万物的禀赋一样,何以人的禀赋独特而茂美?这是船山需要回应的一个问题。为此他提出了“时位”的概念。人禽之别不在于阴阳之始的本一,因为二者都以太虚缊的和合之气为本源,同时也以太虚浑沦湛一的清纯之气为依归。所不同者就是时位相得与否,“相得,则为人,为上知;不相得,则为禽兽,为下愚”。“万物之生,莫不资于天地之大德与五行之化气,而物之生也,非天地合灵善之至,故于五行之端偏至而不均,唯人则继之者无不善,而五行之气以均而得其秀焉。”[11]564“时位相得”使人之所继者无不善,所禀赋的五行之气均匀而秀丽;禽兽则不然,不仅禀赋的五行之气有偏颇不均匀,而且本身也没有继承天地的欣和灵善的本性。“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为性,同得天地之气以为形,其不同者,独人于其间得形气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为少异耳。虽曰少异,然人物之所以分,实在于此。”[12]510“时位相得”还使人禀得了正气,气正使得形正,形气之正使人可以保全其固有的善性。尽管这种分别只是极为细微的差距,但却是人物之所以分的关键。尽管“时位”很重要,但也只是造就人之特殊的众多因素之一。“五行之气,用生万物,物莫不资之以生,人则皆具而得其最神者。”[11]561五行之气作为万物生生所必须要依据的质料,对人而言亦是如此,唯一的细微差异在于人还具备万物所没有的五行之气的神妙功能。“二气构形,形以成;二气辅形,形以养。能任其养,所给其养,终百年而无非取足于阴阳。是大造者即以生万物之理气为人成形质之撰,交用其实而资以不匮。”[9]892船山此处虽言“二气”,但实际上并不存在着真正的二气,这里只是就功能而言。对于万物生生所依据的质料是“五行之气”,对于人而言,不仅只有“五行之气”,还有阴阳二气。而且二者相比,阴阳二气对人的影响更为广大重要。阴阳二气不仅只是在初级阶段构成形体,更为重要的是还能辅养形体。无论是养气还是养体都是人所独有的,实际上养体的根本在于养性,养性又要落到养气上。
在船山本体论哲学中,船山对张载的超越之处在于其本体论哲学更为精细、深入。如果说张载哲学关于化生万物只是停留在重了悟、独断论层面,那么船山关于气化流行、化生万物则进入了重论证、重逻辑层面。
船山“希横渠之正学”,就张载“太虚即气”这一观点而言,船山对张载之学既有继承之处,亦有创先之处。从张载之“太虚即气”到船山之“太虚一实”,船山的继承更多地表现为由表入里的深入过程;从张载之“气化”到船山“气之化也”,船山更多表现出由浅入深的细化探究;船山气化差异性层面彰显出对张载之超越,崇“本”开新。
[1]嵇文甫.王船山学术论丛[M].北京:中华书局,1962:109.
[2]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6册[M].长沙:岳麓书社,2011.
[3]陈来.诠释与重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4]朱建民.张载思想研究[M].台北:文津出版社,1989.
[5]张载.张载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8.
[6]陈来.宋明理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47.
[7]牟宗三.心体与性体[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393.
[8]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2册[M].长沙:岳麓书社,2011.
[9]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册[M].长沙:岳麓书社,2011.
[10]朱熹.朱子全书:第6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53.
[11]王夫之.船山全书:第4册[M].长沙:岳麓书社,2011.
[12]王夫之.船山全书:第8册[M].长沙:岳麓书社,2011.
[13]林安梧.王船山人性史哲学之研究[M].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印行,1988:18.
[14]王夫之.船山全书:第3册[M].长沙:岳麓书社,2011:447.
[责任编辑王银娥贾马燕]
Wang Chuan-shan’s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Zhang Zai’s Ontological Issue That “Tai Xu is Qi”
CHEN Li-xiang, WANG Zhi-hua
(YueluAcademy,HunanUniversity,Changsha410082,China)
Wang Chuan-shan, one of Zhang zai’s disciples, inherited his master’s philosophical thought and expanded his own. The issue under discussion is that Tai Xu was Qi, proposed by Zhang Zai, and that Tai Xu was an entity, proposed by Wang Chuan-shan. All revealed the inheritance of Wang Chuan-shan’s ontology from Zhang Zai’s, as a result, Wang’s differentiation led to the gradability of the universe, showing that Wang Chuan-shan’s thought had really transcended Zhang Zai’s.
Zhang Zai; Wang chuan-shan; Qi; entity; Tai Xu is Qi
B249.2
A
1001-0300(2016)04-0057-06
2016-03-14
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王船山遵礼之道研究”(15YBA094)的阶段性成果
陈力祥,男,湖南邵阳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后,主要从事宋明理学和船山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