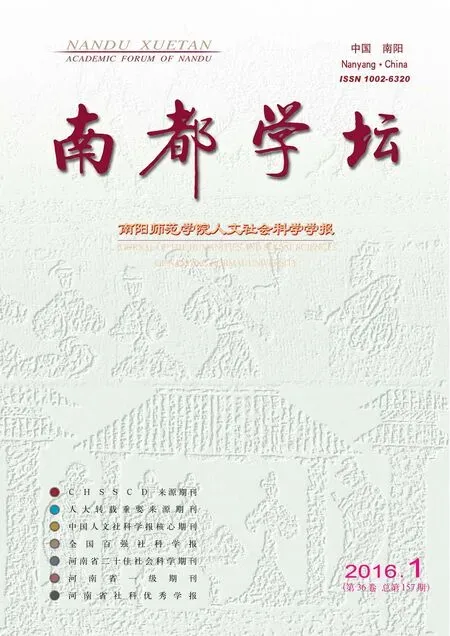复议机关做行政诉讼被告的制度变化及其理据分析——我国《行政诉讼法》首次修改中的一个争议点检讨
莫 于 川
(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 北京 100872)
复议机关做行政诉讼被告的制度变化及其理据分析——我国《行政诉讼法》首次修改中的一个争议点检讨
莫 于 川
(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行政复议是解决行政争议、促进依法行政的有效制度,但复议机关是否做被告,对于复议制度功能发挥的影响很大。我国行政诉讼法原有的“维持则不当被告”的不合理规定,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复议机关的“维持会”形象,首次修改、施行不久的行政诉讼法对复议机关做被告的问题做了根本性且平衡性的制度改变,但学界和实务界对此都有不同看法,故须对主要争议点及修法背景、修改理据加以深入分析,而且新司法解释也带来一些新问题,新法实施中应予注意的事项很多,只有形成必要的全社会共识才有助于新法有效实施。
关键词:行政复议;复议机关;被告;“维持会”;新法实施
一般认为,行政复议是立足于行政体系内部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既有行政性质又有司法色彩,其在整体上被视为行政争议的一种行政解决机制,但其准司法化已成国际趋势,在学界也取得较多共识[1]。即便这一观点成为通说,但是行政复议的准司法化,也须要理性地吸纳司法制度的长处,对复议权形成公正、公开、有力的程序约束,才能促使行政复议制度扮演依法解决行政争议、积极推动依法行政的一种主渠道角色。自《行政复议法》于1999年颁布实施以来,经2007年《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的补充细化,我国的行政复议制度在实践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其中的重要挑战之一就是如何改变长久以来形成的“复议机关是维持会”的负面形象①为人诟病的“维持会”现象的基本缘由是:1990年10月1日起施行的《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做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因此,在既往二十多年的行政法制实践中,许多行政复议机关及其公务人员从“趋利避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本性和从政心理出发,往往为了本机关不当被告而在复议实务中只是走走过场,简单地维持原行政行为的做法比较普遍,行政复议制度未能很好发挥出监督和救济功能,导致复议公信力严重下降的现实困境,这被人们批评为“维持会现象”。。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计划的《行政复议法》修法工作正在进行中,已形成的修法试拟稿针对此问题做出多项规定,但毕竟还只是修法构想。相比之下,与之同时开始进行的《行政诉讼法》修法工作则进展较快,已于2014年11月1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三审通过了修法方案,且于2015年5月1日起施行,其中就调整复议机关的被告资格制度做出了专项规定,旨在从根本上解决“复议机关是维持会”的老大难问题②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二、三款规定的基本含义可以概括为“维持必然当共同被告,不作为也可能当被告”。许多专家学者和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常委对此持肯定意见,认为“这一修改有利于发挥行政复议的缓冲作用”(列席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贾春梅语)。。但学术界和实务界对此也有不同看法,存在一些疑虑。如何认识此争议对于新法实施所产生的影响,本文就此略作分析、略陈管见,并求教于大方。
一、复议机关是否做被告的制度变化梳理
在我国,行政复议制度与行政诉讼制度相比较,从制度设计初衷而言,前者具有高效、便捷、专业等制度优势,还具有行政系统特有的资源配置和隶属关系优势,有助于简便快捷地实现案结事了,在特定案件中更有利于保护申请人利益,更有利于行政争议的彻底解决。因此,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二元并行的行政争议解决机制在我国目前及未来很长时期不仅有必要维持,还应将行政复议塑造为解决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但前提是必须对行政复议制度进行公正性改造,能够公正地解决行政争议。
由此观之,原有的复议机关的角色和责任问题,就成为绕不过去的一个疑难体制问题,必须勇于面对、妥善应对、合理解决。在由于多种原因致使拟议中的《行政复议法》修改工程滞后的情况下,利用《行政诉讼法》时隔25年首次修改的机会,对于复议机关是否做、如何做行政被告的长期争议难题加以根本性解决,彻底改变“维持会”现象,不失为明智的行政法制革新路向。
为给《行政诉讼法》修改工作提供参考,笔者曾在10年前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的要求,组织中青年学者完成了《关于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建议稿(中国人民大学方案)》,于2005年3月30日报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供该项修法工作参考。之后随着行政诉讼实践新进展,社会各方面对此已有更多共识,修改《行政诉讼法》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和工作安排,笔者再次组织《行政诉讼法》修改研究课题组,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修改专家建议稿(中国人民大学2012年方案)及其理由说明书和专题研究报告,于2012年2月报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而且将多次课题成果充实修改形成专著《建设法治政府需要司法更给力——行政诉讼法修改问题研究及专家建议稿》,由清华大学出版社于2014年9月出版,提供立法机关进行修法工作以及关心法治政府建设和司法改革进程的社会各界参考。
我们课题组在修法建议稿中明确提出:按照现行的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对于经过行政复议的案件,当事人不服仍然起诉的,被告按照如下规则确定:复议机关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以原来的行政机关作为被告;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的,以复议机关作为被告;复议机关不受理复议申请或者没有在法定期限之内做出复议决定的,当事人仍然不服原来的行政行为,以原行政机关为被告;不服复议机关不履行职责的行为,则以复议机关作为被告。由此产生的一个严重现实问题是,复议机关为了避免作被告,往往不分青红皂白地维持原行政行为。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促使其更为认真、负责地对待行政复议,我们提出了两种备选方案:方案一:复议机关应当与做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成为共同被告,在试点推行复议委员会的地区,还可以将复议委员会引入成为第三人;方案二:法院应当依职权将复议机关列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方案二主要是考虑到一步到位地推行方案一可能难度较大,因而该方案只是一个过渡性的备选方案。我们课题组所提方案的总体思路,是要加强对复议机关的监督,鞭策其认真做出行政复议决定。无论是方案一还是方案二,与原有制度相比,其优点是显而易见的:一是有利于鞭策复议机关认真对待行政复议工作,防止复议机关为了避免作被告而一概维持原行政行为;二是便于弄清案件事实,因为“如果是做共同被告,那么复议机关的责任也强化了,举证的问题也解决了”[2];三是有利于保护公民合法权益,复议机关为避免败诉后果,必然促使做出原行政机关在诉讼过程中改变原行政行为;四是法院可以通过复议机关更好地督促原行政机关履行生效裁判。简言之,我们所提方案旨在强化复议机关的审慎和责任意识,促使其依法行使复议权,合理动用行政资源,认真对待复议工作,妥善解决行政争议[3]。
不仅笔者带领研究团队,在多次呈报的修法方案中提出上述意见和建议,其他一些研究团队和实务部门同志也提出了类似意见和建议。例如,江苏省兴化市人民法院卞婧娴法官就曾在2014年4月提出,由于复议机关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复议机关与案件审理结果有利害关系,复议机关具有参加行政诉讼的权利和义务,因此需要在行政诉讼法中增加规定,让做出维持决定的复议机关作为行政诉讼的共同被告[4]。
能否实现重大的法律制度变迁,时下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以及高层的认识和决心也非常重要。限于篇幅,这里简要梳理引述影响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制度变化的两条重要政策依据:其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在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方面,要“改革行政复议体制,健全行政复议案件审理机制,纠正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建立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综合机制”。其二,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健全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完善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这就为推动重要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制度变迁提供了必要的基本方针和政策依据。
在此政策背景下,2014年11月1日三审通过了《行政诉讼法》修改方案,新法于2015年5月1日起施行。25年来首次修改的《行政诉讼法》,不仅对行政诉讼的角色定位有了更为正确清晰的认识,更对受案范围、管辖制度、主体资格、证据制度、诉讼程序、裁判执行等几乎所有重大制度进行了修改完善,还就涉及行政复议法的若干疑难问题做出了重大修改。当然,这些修改未必都能获得完全一致的肯定意见,很多问题有待学界和实务界同仁进一步研讨,有待司法实践加以破解,但可以相信,随着我国法制建设进入精细化、科学化发展阶段,行政诉讼制度定会更趋完善,同时也会促使行政复议制度加快完善步伐,从而促进实现良法善治,最终建成法治国家。
修改后、刚施行的《行政诉讼法》第26条第2款规定:“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做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第26条第3款(本次修改新增的)规定:“复议机关在法定期限内未做出复议决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原行政行为的,做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起诉复议机关不作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这两款规定具有非常重大、深刻的意义,须要全面认知、深入理解、严格实施。
上述规定明确了复议机关不作为之际原告起诉的标的和被告的确定问题,也即行政行为被复议机关维持的,由原来规定的原行政机关作被告,修改为原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同时吸纳司法解释的成熟经验,针对复议机关不作为的情形增加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既可以以原行政机关为被告起诉原行政行为,也可以以复议机关为被告起诉复议机关不作为。这样的规定显然更符合改变“维持会”现象的需要,也会形成更多共识,从而使上述条款更加合理、更易操作。
二、此次修法的有关争议点及修改理据分析
上述修改带来的变化是积极和可行的,但学术界和实务界也有争议和疑虑,甚至引起一些争议,批评者认为此项制度革新不符合行政复议的准司法化趋势*所谓准司法化趋势,是指行政复议的审理主体、各方关系、审理对象、审理程序、裁决依据、裁决形式、法律效果等要素和环节越来越趋似于行政诉讼,其中一个重大相似点在于行政复议机关作为司法型纠纷解决机制中的裁决者也不因做出该项裁决而当被告。,会增加行政争议解决成本,且加重复议机关的负担,特别是一些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也不赞同作此制度改变*例如在修法草案审议中,符跃兰委员认为,作此修改后下级行政机关对上级复议机关容易产生依赖性,也易于出现复议机关疲于应付行政诉讼的情形;艾斯海提·克里木拜委员进一步表示,作此修改后不利于上级对下级的监督,既耗费当事人的时间和精力,又浪费行政资源和司法资源,故建议复议机关维持与否都不当被告。。这样的担心和疑虑是正常的,应当认真对待。针对本次修法所作的重要修改和存在的争议点,可从如下四个方面做简要的理据分析*此部分的理据分析得到北京市一中院行政庭副庭长龙非法官的诸多指教和帮助,谨致谢忱!。
其一,关于复议机关与原行政机关的被告资格认定问题。该条修改的目的是希望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复议机关施加一定的压力,解决复议机关甘当“维持会”的弊端。之所以在复议机关维持原行政行为时,须要让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是因为复议机关维持原行政行为即可不当被告,也就没有撤销违法行政行为的动力;而且一般行政法理认为,复议机关作为原行政机关的上级行政机关,具有极大的行政权限,行政复议决定也是一种特殊的行政行为——行政司法行为,一旦复议机关全面审理案件后做出维持原行政行为的决定,可视之为实际上是复议机关随后也做出了一个行政决定,只不过该行政决定的实质内容和外观形式与原行政行为完全契合而已,因而被诉后将做出维持决定的行政复议机关作为被告接受司法审查也在情理之中。该处修改在修法过程中争议较大,而且如何修改也几经讨论。修法过程中,还有一种方案提出,复议机关维持的,以复议机关为被告,原行政机关(做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列为第三人,对此,另有意见认为被告和第三人的诉讼地位各自独立,而复议机关与原行政机关均作为行政执法机关,不应有各自不同的诉讼利益,不宜处于不同的诉讼地位。还有的方案主张只让复议机关作被告,对此,另有意见认为只让复议机关作被告可能不利于查明案件事实。还有一种温和方案提出,可以不让复议机关当被告,但如果诉讼结果是撤销原行政行为,则可在判决中一并撤销该复议决定,这对复议机关是一个否定评价,对此,另有意见认为这种方案对复议机关的监督力度不足,显得太过温情。
综上,经过各种方案的讨论和选择,立法机关最终采用了在上述情况下让复议机关和原行政机关作共同被告的方案,主要是考虑到复议机关作为上级行政机关的特殊资源、审查便利、解决力度和特殊效果等诸多因素,这也是包括中国人民大学行政诉讼法修改研究课题组等机构所提建议方案的基本意见。需要指出的是,复议机关维持原行政行为时,复议机关与原行政机关作共同被告这种立法模式并无域外的立法例,可以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次制度革新尝试,其实施效果尚待观察。至于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的情况,则仍由复议机关作被告。
其二,关于制度变化如何影响法院管辖权和诉讼标的问题。实际上,被告的变化还直接影响到关于法院管辖权和诉讼标的应当如何认知和处理。首先,关于法院管辖权,根据新《行政诉讼法》第18条和第21条的规定,经复议的案件,也可由复议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案件,原告可以选择其中一个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上述规定,复议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和原行政机关所在地法院均有管辖权。但是,上述规定并未解决级别管辖的问题,特别是在复议机关是区县以上人民政府的案件中,原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对应的法院级别分别是基层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如何确定级别管辖仍未明确,对此仍有待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予以明确(此问题在进行跨行政区划设置法院的行政审判体制改革试点的北京、上海两地已基本解决)。其次,关于诉讼标的,新《行政诉讼法》第79条专门增加规定:复议机关与原行政机关为共同被告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对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一并做出裁判,即表明诉讼标的包括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
其三,关于如何正确辨认何谓改变原行政行为的问题。尽管根据新《行政诉讼法》,无论复议机关维持原行政行为还是改变原行政行为,均会成为被告,但是关于“改变原行政行为”的界定依然很重要,因为涉及复议机关是作为共同被告还是单独被告的问题。关于复议决定改变原行政行为,于1999年11月24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088次会议通过、2000年3月10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98条”)第7条规定了三种情形,(1)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所认定的主要事实和证据的,(2)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所适用的规范依据且对定性产生影响的,(3)撤销、部分撤销或变更原具体行政行为处理结果的。其中第三种情形比较容易判断;第二种情形由于要求改变依据必须达到对定性产生影响的程度,故实践中判断难度也不是很大;判断难度最大的是第一种情形,因为何谓原行政行为认定的主要事实和证据,常常存在较大的主观裁量空间,比如原行政行为认定了较为笼统的事实,而复议决定将相关事实进一步具体化,应该不会被认定为改变主要事实和证据。
除了前述司法解释规定的三种情形外,《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规定了新的复议决定方式,也对何谓改变原行政行为提出了新的课题。例如,根据《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48条第1款第1项的规定,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的,由于没有改变原来的行政法律关系状态,因此其法律效果等同于维持原行政行为。对于此种情况,可否认为驳回的前提是复议机关已做出了一种确认,也即确认原行政行为是合法的,实际上这相当于复议机关做出了一个与原行政行为的实质内容相同但并无维持决定外观的行政判断呢?还有一种情况是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复议决定既没有撤销或改变原行政行为,但又从法律效果上否定了原行政行为。目前在行政审判实务中的倾向性意见认为,确认违法毕竟改变了原行政行为的法律关系状态,应当认为是改变了原行政行为的一种情形。
既往的行政审判实务中还有一种更具争议的情形:申请人针对A行为申请行政复议,而复议机关错误地认定了复议标的,维持了一个B行为,申请人对复议决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究竟应当如何审查起诉条件?一种意见认为,复议机关针对申请人的申请实质上并未做出复议决定,而做出的复议决定并未改变任何既定的法律关系,故不可诉;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复议机关未针对申请做出复议决定,这已经构成违法,理当以复议决定作为诉讼标的。实际上,这种情况即等同于行政复议不作为,但同时又存在一个复议决定作为载体,因此申请人无论是从复议机关不履行复议职责的角度,还是从复议决定未针对具体申请做出的角度,复议机关作为被告都是适当的。至于人民法院受理之后是审理复议决定还是审理复议机关不履责还是兼而有之,大致只是一个技术处理层面的问题。
其四,关于复议不作为的情形应当如何处置问题。新《行政诉讼法》第26条第3款实际上是借鉴了“98条”第22条的规定,虽然表述上与司法解释略有差异,但含义并无差别,因此尽管是增加的条款,对于司法实务工作者来说应当不会感到陌生。原《行政诉讼法》只是规定了复议机关维持或改变原行政行为时如何确定被告,但没有涉及复议不作为的情形①其实,一般行政法理倾向于认为,“不作为”实际上也是有关主体做出的一种行为选择,是对应于“作为”行为的一种“不作为”行为,也是不履行法定职责的一种行政违法行为,故应受到司法审查和评价。,因此司法解释对此予以了完善和明确,该司法解释有关规定也在此次修法的过程中得到了立法者的认可。对于复议机关不作为的选择性诉讼,体现了行政复议对于当事人而言是一种选择性的救济途径(法律规定必须复议前置除外)。准司法程序的复议程序也是一种行政程序,其性质上的双重性是当事人可选择不作为的复议机关或者原行政机关作被告的法理基础,也表明此次修法尊重了当事人的选择权利。
三、正确辨识和妥当处理新司法解释带来的新问题
《行政诉讼法》时隔25年进行的这次修改属于全面修改,从最终通过的修正案来看,共61项修改,法律文本由11章减为10章(删去原第九章侵权赔偿责任),新法第7章(审理和判决)由旧法的不分节改分为5节,原法律文本约四分之三的条文有修改,最重要的增、修内容涉及8个方面32处,采纳了学界和实务界多年来呼吁修法完善行政诉讼制度的许多建议,整体框架更趋合理,修改内容针对性强,制度设计趋向细致,推出若干制度创新,均值得肯定。但是,正因为改变较多、较大,新法实施中应予注意的问题也很多,这里择要作分析。
在新的《行政诉讼法》即将施行的前夕,2015年4月20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48次会议通过并于同月22日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9号,简称“27条”),自2015年5月1日起施行。“27条”中的第6条至第10条共5条涉及复议机关做被告如何认识和处理,也即“27条”使用了略占条文总数五分之一的篇幅回应新的《行政诉讼法》第26条的有关规定,可见最高人民法院对此制度变化的高度重视以及与行政机关积极互动的态度之一斑。这里先简单列举条文如下:
“二十七条”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包括复议机关驳回复议申请或者复议请求的情形,但以复议申请不符合受理条件为由驳回的除外。”第二款规定:“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是指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处理结果。”
“二十七条”第七条规定:“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做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原告只起诉做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或者复议机关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原告追加被告。原告不同意追加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另一机关列为共同被告。”
“二十七条”第八条规定:“做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为共同被告的,以做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确定案件的级别管辖。”
“二十七条”第九条第一款规定:“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审查原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同时,一并审查复议程序的合法性。”第二款规定:“做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对原行政行为合法性共同承担举证责任,可以由其中一个机关实施举证行为。复议机关对复议程序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
“二十七条”第十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对原行政行为做出判决的同时,应当对复议决定一并做出相应判决。”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判决撤销原行政行为和复议决定的,可以判决做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重新做出行政行为。”第三款规定:“人民法院判决做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的,应当同时判决。”
上述司法解释条文,总的看是细化了法律条文,多数都有利于新法的理解和执行。但是,有的条文似乎与新法的精神和规范似有距离,须再加斟酌、妥当执行。例如,“27条”第6条的两款规定,实际上限缩了纳入司法审查范围的复议机关所做行为。特别是,新法关于“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的表述,实际上具有非常丰富的实际意蕴和行为类型,但经过“27条”第6条第2款看似简单的一句话(“是指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处理结果”)的“执行性微调”,大大限缩了应当接受司法审查的复议行为范围,给新法出台后正承受巨大压力、正认真谋求如何建章立制来增加和培训应诉人员加以应对的无数个复议机关大大减压,全都长长地舒缓了一口气,但制度革新的良法追求恐怕也就难以带来善治效果,如此司法解释条文恐会让所谓“最高人民法院成了最高立法机关、最终立法机关”的调侃性批评旧话被重提,徒增无谓争议和疑虑。
再如,“27条”第8条的规定也不尽符合这次修改《行政诉讼法》的基本方针和原则。这是因为,新法有关规定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采取有效举措来防治行政机关对于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干涉,这也是我国宪法关于司法制度的基本精神和制度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而要防治行政机关对于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干涉,首先就要从源头上解决在受案环节的行政干涉,其次还要在尊重当事人选择权的基础上,实行“就高不就低”的管辖原则和制度。因此,新的《行政诉讼法》专门增加了一个条文(第3条第2款),特别规定了“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干预、阻碍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而新法对于此类共同被告案件的管辖办法未作具体规定,是有特殊的立法考量的。但“27条”第8条规定:“做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为共同被告的,以做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确定案件的级别管辖。”这实际上是做出了“就低不就高”的制度安排(也许有方便诉讼管辖的考量),是否符合立法原意,显然值得再加斟酌。鉴于做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其在行政审判场景中是诉讼利益共同体的关系,而且此类案件肯定案情较为复杂或者当事各方之间的矛盾冲突较大,对于作为原告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来说,而且对于审理机关来说,均可谓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如果改由更高级别的人民法院来审理,行政审判实务生态或许会改善许多,这对于提起诉讼的行政相对人,也即甘冒诉讼风险拿起法律武器捍卫合法权益、同时也在客观上发动了能够引入司法审查促使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法律监督程序、因而带来公益功效的行政原告来说,或许是更合法、更合理、更正当的制度安排。当然,从便民原则、便利原则、法律经济学原则来考量,也可为行政相对人提供一种自由选择,也即规定一个但书:“如果当事人起诉原行政行为的,由做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参考文献]
[1]周汉华,主编.行政复议司法化:理论、实践与改革[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杨小军.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朱新力.行政复议应向司法化逼近[J].法学研究,2004(2);方军.论中国行政复议的观念更新和制度重构[J].环球法律评论,2004(1);刘莘.行政复议的发展历程与未来展望[J].江苏社会科学,2008(5);应松年.行政复议应当成为解决行政争议的主渠道[J].行政管理改革,2010(12).
[2]莫于川,等.行政诉讼制度改革中的焦点问题——目标、方案与理由[J].重庆邮电学院学报,2006(2).
[3]莫于川,主编.建设法治政府需要司法更给力——行政诉讼法修改问题研究及专家建议稿[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66.
[4]卞婧娴.维持决定的复议机关应为共同被告[N].人民法院报,2014-03-26.
[责任编辑:谭笑珉]
The System Changes and Rationale Analysis of the Reconsideration Organization
as the Defendant in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A Review of the First Amendment of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al Law in China
MO Yu-chuan
(School of Law,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The administrative reconsideration is an effective system to resolve administrative disputes and to promote administration according to law. It is of great influence on the function of the administrative reconsideration system to clarify the issue whether the reconsideration organization should be the defendant. The invalidated version of China’s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Law specified that the reconsideration organization shall not be the defendant if reconsideration sustains the original act. This unreasonable provision labeled the reconsideration organization as “reconsideration-sustain organization” to a large extent. The newly revised and implemented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law has made a fundamental and balanced change on this issue. But the academics and practical circles hold some different views, thus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a deep analysis about the main points of controversy, the backgrounds and reasons of law revision. The new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has brought some fresh issues, and there are a lot of things to be considered in the implementation. Only with the consensus of the whole society can the new law be effectively implemented.
Key words:administrative reconsideration; reconsideration organization; defendant; “reconsideration-sustains organizat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law
中图分类号:D9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320(2016)01-0063-06
作者简介:莫于川(1956—),重庆市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行政法研究所所长,中国行政法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
收稿日期:2015-11-19
——兼议《行政复议法(修订)(征求意见稿)》第六十二条之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