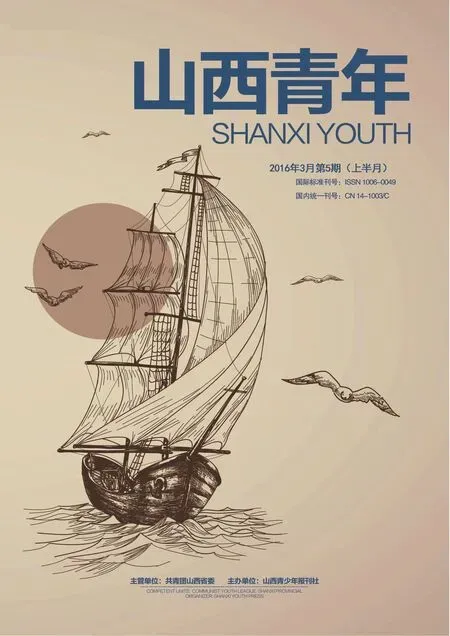农村污染问题背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逻辑初探*——以马鞍山M牛奶厂为例
汪 璇** 宋骅育 洪晶晶 储 颖 杨雪云**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 合肥230601
农村污染问题背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逻辑初探*——以马鞍山M牛奶厂为例
汪璇**宋骅育洪晶晶储颖杨雪云**
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合肥230601
摘要:农村环境问题涉及三大利益群体:村民、企业、政府,他们之间的互动逻辑及行为是农村环境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的深层次原因。马鞍山M牛奶厂在A村造成了严重的面源污染。通过田野调查发现该村的污染是由村民和牛奶厂、村民和政府、政府和牛奶厂之间的互动共同造成的。受益圈受害圈重叠程度高、农村社会的三大结构是纵横分析A村环境污染的框架。
关键词:农村环境;面源污染;利益相关;互动逻辑
*安徽大学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编号:201510357076)。
一、问题与文献综述
当前对于农村污染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下几点:1、具体存在的几大污染及其改善措施:水污染、空气污染、土壤污染、垃圾污染、牲畜污染等,如《中国畜牧业环境污染防治问题研究》[1]; 2、某地区存在的主要环境问题及解决途径或者防治对策《武威农村环境污染现状及改善措施》[2]; 3、涉及城乡关系的农村污染问题,如《城乡断裂下农村环境污染存在的问题及自治对策——以河南省舞阳县为例》[3]。
笔者认为,单纯地分析农村环境污染及解决措施是不够的,任何社会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人的问题,极少有学者将关注点放在人的身上。此外,以往的相关研究常常将关注点简单放在工厂唯利是图缺乏社会责任感、政府相关部门监管不力以及在两者的缺位下导致村民成为最大受害者而无处申诉的简单的静态的运作逻辑上。罗亚娟在《苏北“癌症村”》中提到村民在同企业的博弈中失败的原因:自上而下的行政体制和村民在话语权上的弱势地位;程鹏立在《富裕的“癌症村”》中提到村民对健康风险的应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环境抗争、避免接触污染物质、永久性地搬离污染源;程鹏立,李彩虹在《贫困与癌症共存》中发现,村民抗争的积极性中存在经济利益上的纠葛。这些研究都非常具有启发性,本文认为三大群体(村民、企业、政府)之间平衡的动态互动模式很有可能是农村环境污染难以解决的重要线索。
二、田野概况与问题缘起
本研究选取了安徽省马鞍山市D镇的A村为调查地。A村位于马鞍山市东面,介于南京、芜湖之间,属于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年平均降水量在1100毫米左右。该村地形平坦,河渠纵横,适宜种植水稻、油菜、小麦、山芋等作物。A村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村庄,村民靠土地吃饭,自给自足;土路高低不平,一旦下雨,就会泥泞不堪。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入城市,村民的生产方式和心态都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村民对土地的情感逐渐淡薄,另一方面,对致富和改善生活品质的需求愈加迫切,这些心理成为了招商引资的动力。在D镇镇政府的网站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段文字:“在‘十五’期间,D镇紧紧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目标,以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为主线,以市场为导向,大力发展‘三资’农业,全镇新办‘三资’农业企业5家,总投资2.7亿元,其中M牧场项目投资2.5亿元。”
M牛奶厂于2005年建成,拥有10000多头奶牛,每头奶牛大约每日产粪便50公斤左右,产生的牛粪用途有三:沼气发电,周边农户沼肥,剩余的沼渣做卧床。M牧场一度给了村民和政府以致富的希望:部分村民的就业问题得到了解决,村里也修起了水泥路。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牧场带来的负面效应也显现出来并严重影响了村民的日常生活:牛粪的气味从牧场向四周扩散,引来的苍蝇群成为村子里的常客,牛粪的抛洒带来严重的水土富营养化……
到了夏天,你在外面晒得衣服、被子,那苍蝇往上面一扒,不要你打的,你那衣服就不能用了,那苍蝇身上都带着污秽的东西,你洗的干干净净的东西,往上面一扒……而且那个苍蝇叮人,吸人血,跟蚊子咬人还不一样……洗衣服、洗菜都不在池塘里面洗……鱼虾全部都死掉了,有的塘甚至被用来储存牛尿了。(2015年12月31日,王某)
在招商引资的时候,村里领导和村民均没有充分考虑过该牧场是否会带来环境污染,只是单纯地“想把A村死气沉沉的气氛给带动起来”。后来,牧场带来的视觉和嗅觉上的冲击使得村民感到不安和焦虑。该问题从2005年一直持续到今天都未得到解决,并且越来越严重。
为了更加细致地了解A村的环境污染问题,于2015年12月至2016 年4月初,先后进行了多次田野调查,无结构访谈了多名村民、村干部和牧场内部员工,并获取了详尽的访谈资料。
三、利益相关者的互动逻辑分析
(一)村民对企业:爱恨两难
1.积极抗争者
M牛奶厂建在上游,A村建在下游,到了夏季,风向偏南,牛粪的臭味都吹到家里去了,很多村民反映“家里简直不能待”。除此之外,M牛奶厂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家门前原先可以养鱼的池塘如今已经荒废,村里通了自来水,村民也不会在塘边洗衣服、洗菜了;成群的苍蝇在空中飞舞,咬人和牲畜,污染食物和衣物;终年不散的臭气给村民带来不小的困扰。
“以前反映的人蛮多的,记者也来过,因为记者来,我们才拆迁的。三四年前有村民反映过,几个村都反映,村民一起去反映,每到下大雨,脏都往门口淌。村民去反映,牛奶厂送两个钱给政府(村里面的),不就算了嘛。”(2015年12月31日)
村民对以村干部为代表的政府表示很失望。但仍有部分村民以自己的微薄力量抵制牛奶厂。我们的一个访谈对象,郑某,他家世世代代居住在A村,祖房就在M牛奶厂旁边,是全村受牛奶厂危害较深的人,也是抵制情绪最强烈的人。一谈到M牛奶厂,他就特别激动,怨念颇深,但表示不会搬离这边。
“牛奶厂刚来的两年,大家吵……有了。现在我们村庄只有十几户人家了,哪个哄呢……江苏那边拆迁的标准是两千二百五十块钱一个平方,这边是七百五十块钱一个平方,我觉得钱太少了,不愿意拆。另外,我家祖宗八代都住在这里,我不愿意他们拆我家房子。”
郑某如今和自己的老伴坚持住在牛奶厂旁边,成为了该村拆迁的钉子户,在这场村民和企业之间的较量中,郑某的行为似乎并没有取得成效。
实地调查发现,大多数村民对周边的环境污染持消极态度,能够坚持抗争的仅仅两三户人家。M牛奶厂最初的时候会给周边的村民发放喷雾剂,后来就不再发放了,此外,还委托村领导劝村民搬迁。
2.消极躲避者
(1)搬离村庄。A村中的很多房子是闲置的,调查显示,有相当一部分村民在街上买了新房并且已经搬离。这种现象固然与农村拥有大批的剩余劳动力、村民的土地情结断裂等因素有关,但留下的村民更倾向于将该现象归结为M牛奶厂带来的环境污染,村民的言谈不免带有夸张的色彩,但从侧面还是可以看出M牛奶厂成为了村民搬离的一大推力。
“A村以前有三十几户人家,现在只有十几户。因为这个厂而搬走了一半的人家。其他几个村也是这样。这个厂影响五个村。”
成功搬离A村,在街上开小公司的陈某是村中的经济精英,他在A村还有一栋小洋楼,偶尔会回村里看一看老人。因为同M牛奶厂并没有利益上的牵扯,又不再受A村污染的影响,陈某表示对村中污染不是非常关心,也不了解现在的污染程度,但仍希望村中的环境能够好转。
(2)用常识规避风险。A村已经通了自来水,村民的饮用水都依赖于自来水。池塘闲置在那里,甚至用来储存牛粪、牛尿。田野调查显示,A村的青壮年劳动力带着他们的孩子流入了城市,常驻居民是老人和婴幼儿,从事农业耕作的村民已是寥寥。留守的村民有相当一部分会把田承包出去,并自留一块田,种自己吃的庄稼和蔬菜。村里的农作物长势越来越不好,池塘里的水越来越浑浊,这些都给村民带来了土壤和水质被严重破坏的信号。
3.相对支持者
调查显示,还有部分村民成为了M牛奶厂的相对支持者,虽然能切身体体会到M牛奶厂带来的环境污染,但牛奶厂带给他们经济上的利益亦是难以舍弃的。调查发现,A村的部分村民因为体力和经济收入上的不平衡而不再种田了,他们的经济来源是土地的租金、儿女的孝敬或者其他途径,比如用自己家闲置的田装牛粪换取微薄的利益。“牛奶厂会在这边继续存在下去,污染会越来越重。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牛粪牛尿啊,不停地扩散,污染只能越来越重。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好的处理方法,就是抛洒,它是有偿的。比如讲家里的田是荒在这个地方,然后他打个电话,有热线的,讲我家需要几车子牛粪,一车子牛粪是给20多块钱。农村现在好多人都是无业的,打牌打麻将,输了钱怎么搞呢,打个电话,让送10车子牛粪过来,他就又有钱了。他不管那样对地好不好……”(2015年12月,王某)
在M牛奶厂打工的村民亦是经济上的受益者。M牛奶厂招收的员工有52人,大部分都是周边的35到40岁村民。该厂的工资待遇在当地来说属于中上等,开出的住房补贴、五险一金、节日福利等也吸引着不少村民前往。离家近、待遇好等因素使这部分的村民对M牛奶厂“恨”不起来,表示“时间长了就习惯了”。
(二)村民与政府:靠不住的情分
1.村民与村干部:管辖与被管辖的熟人关系
中国传统农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A村也不例外,村民和村干部大多都是沾亲带故的,“人情、关系”使得村民在环境抗争过程中抹不开面子。A村的村干部基本上都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人,一方面,他们是村庄的管辖者,另一方面,他们又是村民的亲戚与晚辈。盘结交错的关系网像蜘蛛网一样,不仅束缚了村民的环境抗争,也束缚了村干部的管理行为。面对村民的抗争行为,村干部更愿意选择用情分私了的方式。
2.村民与监管部门:无奈与失落的信任关系
“污染天堂”理论认为污染密集产业会倾向于选择环境标准较低的地区,A村地处偏僻,环境污染在短期内很难显现,且类似情况较为普遍,所以A村的环境问题很难引起媒体和大众的重视。环保部门是一级单位,很难顾及到像A村这样的偏远农村,面对村民的上访,一开始是派人来A村视察了几次,发现情况并没有村民反映得那样严重,让牛奶厂给了周边村民一些补偿,后来下来的次数就少了。然而,实地调查中,积极抗争的村民表示并没有拿到什么补偿,或许实际情况就是如此,或许村民只是想夸张一番引起社会的注意。但从侧面可以看出,村民正由积极抗争转向消极避害,他们的心态正由对政府的信任依赖到不信任和麻木。
(三)企业与政府:看似暧昧
1.牧场与村干部:互惠的熟人关系
(1)政绩上的牵扯。随着新农村建设轰轰烈烈地开展,改善农村景观成为了一项衡量村干部和地方政府工作的重要指标。M牛奶厂作为引进的一大企业,D镇的“摇钱树”,对地方财政收入贡献颇大,只要不产生大范围的环境污染问题,那么就不是问题。
“省里面、市里面的领导给地方下了压力,土地方面我也不知道是有偿的还是无偿的。地原来就是种庄稼的……我们这边原来很落后的,村领导、镇领导非常渴望来引进一个企业……”
调查发现,村领导利用自己的人脉资源在镇上开了一家规格高档的饭店,他在镇上买了自己的房子,每天开车去村里上班。提及M牛奶厂,他也是非常无奈,作为村民,他对牛粪带来的污染感到“不能忍”,于是凭借着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的双重身份,他成功逃离了村庄。
(2)人情上的往来。提及M牛奶厂的厂主,村干部说他不是本地人,是一个特别会做人的人,“常在一起吃饭”,跟他们是很好的朋友。牛奶厂帮他们解决村民的就业问题、带来了A村景观的改善,他们帮厂主解决人脉和其他问题,双方合作非常愉快。这也造成了积极抗争者的不满。
“前有村民反映过,几个村都反映,村民一起去反映,每到下大雨,脏都往门口淌。村民去反映,牛奶厂送两个钱给政府(村里面的),不就算了嘛。”
2.牧场与上级监管部门:有效抵御与低效监督
“我们现在是循环经济,所有牧场都是可以循环的。我们会自己种植饲草,牛粪一部分会成为沼渣作为卧床,另一部分,会用做沼气发电。我们牧场……自给自足。有专门部门进行沼渣的物液分离,分离后进行卧床铺垫,用来保证牛只趴卧的舒适度。我们还会用牛粪来还田,跟周边的农户签订种植的协议,他们无偿的使用我们的沼肥,他们种植的青储玉米,又会作为我们的饲料我们来统一收集。所以这是一种很完善的循环。”
调查发现,M牛奶厂确实有自己的沼气发电设备,并且都价值不菲。用地下管道将牛粪还田的方式听起来十分环保,然而一辆一辆驶出的装满牛粪、一路滴滴洒洒、散发臭气的卡车也是不容忽略的。
“环境保护局这边的人来了也是摇头,污染企业都有应对措施,讲我们在建一个沼气发电,进行无害化处理(真的有那个设备,也用了,效果确实不明显,牛粪太多了,一天600多吨排泄物,供过于求了,只能处理一部分)。上面人来检查,一看,什么措施都有,只是效果不是很明显,厂方也讲了,我们正在想办法改进。我估计那里有一个技术问题,我觉得那个沼气发电不是很成功。他们觉得抛洒是最直接的方式。”
监管部门会定期下来检查,而M牛奶厂会让他们看到应该看到的东西,并表示,沼气发电的效用是长期的,需要时间。实地调查并没有找到M牛奶厂环保中心的员工,公关部门的员工小李说“他每天都不是在办公室里的,都会去农田看一下牛粪使用情况,监督一下”。
四、原因初探
(一)受益圈受害圈高度重叠
研究发现,受益圈受害圈的重叠程度对村民抗争的强度及策略选择、村民的内部分化有较大的影响。受益圈受害圈理论是日本环境社会学的经典理论,它源于日本社会学者对新干线造成的公海问题的实证研究。
污染的受益者从厂主、以村干部为代表的政府、在牛奶厂工作的村民、靠用自家地装载牛粪换取生活来源的村民再到普通村民,收益程度依次减弱。相反地,污染的受害者从村干部再到厂主、政府、村干部再到普通村民,受害程度依次增强。牛奶厂厂主拥有足够强硬的社会资本来有效规避污染给自己带来的损害,村干部也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搬离村庄。
村民选择忍受的一大原因就是,他们在环境污染的损害中获取了不忍舍弃的利益。大部分村民因为种田的成本太高而选择不种田了,经济来源微薄,加上A村赌博风气严重,用田地有偿装载M厂抛洒的牛粪似乎是最为便捷的挣钱方式。
(二)三大结构因素
1.亲缘-地缘关系结构
虽然A村已经步入现代化的轨道,社会结构发生的了较大的变化,但“熟人社会”的特质依然存在。村民之间存在复杂的血缘和地缘关系,碍于情面,村民往往不愿意为了作为公共产品的环境而破坏熟人社会的人际关系。
2.精英-大众结构
农村中的“精英-大众结构”影响着村民环境健康风险的规避,也影响着村民的环境抗争行为。精英是环境抗争的牵头人,是村民和政府、企业沟通的中介人物,环境抗争的意识也遵循着从精英到大众的逻辑。调查发现,A村青壮年人口流入城市,精英损失严重,政治精英又是政府的代言人,所以无论是经济精英、文化精英还是政治精英都没有起到牵头的作用。
3.代际结构
农村社区代际结构的分化日益突出,面对环境污染,年轻人群体受教育程度较高,更倾向于用网络媒体等现代方式维护权益或者逃离村庄,而中老年人群体倾向于逆来顺受、运用常识和智慧规避风险。然而,年轻人群体的乡土情节较为淡薄,对未来的期望值较高,争先恐后地涌入了城市,带走了村庄的活力与自保的屏障。
[参考文献]
[1]孟祥海.中国畜牧业环境污染防治问题研究[D].华中林业大学,2014.
[2]安冬梅.武威农村环境污染现状及改善措施[J].甘肃科技,2011(19).
[3]郝伟霞.城乡断裂下农村环境污染存在的问题及自治对策——以河南省舞阳县为例[J].安徽农业科学,2011(32).
作者简介:**汪璇(1994-),女,安徽马鞍山人,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本科在读,研究方向:环境社会学;指导老师:杨雪云(1969-),女,安徽合肥人,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女性学。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049-(2016)05-001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