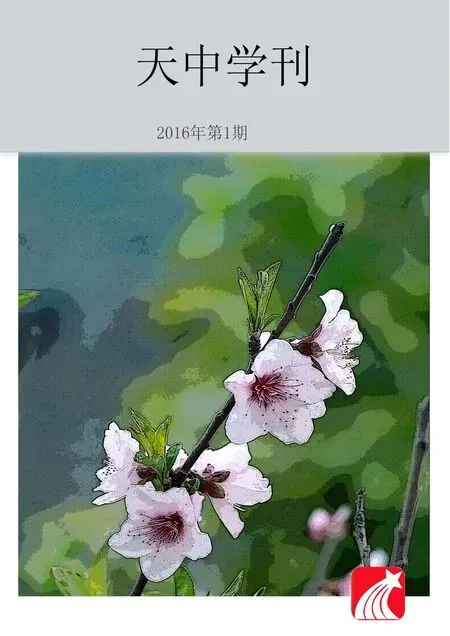对“竹林”文学传统的思考
许结(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对“竹林”文学传统的思考
许结
(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摘 要:唐人对竹林七贤人生品格与生活态度的向慕,是一段隔代的追寻与记忆;唐人对竹林文学传统的接受呈示一定的“现代性”。竹林文学传统的成立则与汉晋以来的名士文化传统密切相关,有一个不断被“经典化”的过程,包含着后人对竹林七贤的追忆与想象。七贤风雅与竹林逸韵在历史的升坠间被人们反复言说、不断影写,其蕴含的文化意义是多方面的,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关键词:竹林七贤;唐代士人;文学传统;经典化;文化意蕴
唐人朱湾《七贤庙》诗云:“常慕晋高士,放心日沈冥。湛然对一壶,土木为我形。下马访陈迹,披榛诣荒庭。相看两不言,犹谓醉未醒。长啸或可拟,幽琴难再听。同心不共世,空见藓门青。”①诗中的“长啸”“幽琴”等,是对魏晋之际竹林七贤人生品格与生活态度的向慕,也是一段隔代的追寻与记忆。而这种记忆构成的一种集体化相承、相续的联系,为“竹林”的经典化书写了丰富多彩的历史。值得强调的是,竹林作为特定的文化符号,当与七贤之群体兴起的特定时代有关,因为面对这一或称“高士”或称“名士”群体的兴起,切不可忘记其中“文学”的参与。换言之,正是处于个体化文人的大量出现而在某种程度上标明文学“自觉”之时,这一群体才以文学展示和记录了自己,后代又更多地以文学方式表达追慕情怀,于是成就了历史上罕与媲美的名士化的竹林文学传统。而这一文学传统在“异代不同时”的接受与彰显中,又呈示每一时段的“现代性”。
一、名士·文士:竹林文学之成立
“竹”作为意象在文学作品中的出现甚早,例如《诗经·小雅·斯干》“如竹笣矣,如松茂矣”,《楚辞·山鬼》“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路险难兮独后来”,都已写到竹与竹林。将竹与个体化的文人生活结合在一起,则在东汉时期,如仲长统《乐志论》描写的“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匝,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的情景,被称为“仲长园”,其中“竹木”也是怡情自然的重要因素。固然,如前引《楚辞》与仲长之说,竹的意象已具有了比德的成分,然与魏晋之际之七贤以“竹林”为充满诗意的符号,而呈示其人格与生活,并成就其一种集体化的文学形象相比,则尚有一段审美距离。因为在七贤时代,“竹林之游”在人们的记忆中,已与人生、与文学融为一体。这种最初的记忆首先呈示于作为七贤之一的向秀的文学作品《思旧赋》中,如其赋序谓“嵇志远而疏,吕心旷而放”“嵇博综技艺,于丝竹特妙”,“余逝将西迈,经其旧庐。于时日薄虞渊,寒冰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音寥亮。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这既是人生伤逝的感怀,也是“竹林”纪事的文学创造。再看《世说新语·伤逝》中,王戎有关“黄公酒垆”触景生情的记述:“王浚冲为尚书令,著公服,乘轺车,经黄公酒垆下过,顾谓后车客:‘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饮于此垆,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来,便为时所羁绁。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1]581−582这则故事之所以引起后世迭起赓续的共鸣,也不仅在时过情迁的伤怀,而是内涵了某种人同其情的感动,是文心与诗意的传递。
从这种记忆看竹林文学之成立,关键在于这一名士集团钟情于文学之转捩。试从三方面作些说明:
其一,从文学背景看竹林文士。考原中国古代文学之兴,《诗》三百篇肇始,然属采、献而来,诚无名氏之为,最早有名姓者为战国两汉辞赋作家,然在西汉之世赋家的群体兴起,先来自诸侯王战国养士遗风,如梁孝王之“菟园”文宴,后成之于武、宣之世宫廷“语言侍从”之设。对此,班固《两都赋序》云:“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2]311其时文学虽有追奉《诗》之风雅颂而与“三代同风”之盛,然均囿于献赋制度,而缺少文学创作的个性化色彩。迨至东汉,随着宫廷言语侍从地位的衰落,私有化庄园经济的兴起,才出现了诸如前引“仲长园”类的文学怡情现象。钱穆《读文选》认为:“文苑立传,事始东京,至是乃有所谓文人者出现。有文人,斯有文人之文。文人之文之特征,在其无意于施用。其至者,则仅以个人自我作中心,以日常生活为题材,抒写性灵,歌唱情感,不复以世用撄怀。”[3]可以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出现了汉末到魏晋之际诸如“建安七子”“竹林七贤”这样具有文人化创作的文学集团。相比之下,被誉之“邺水朱华”而围绕“三曹”的“七子”或更多世用,其创作尚有侯王养士遗风,后世追奉的“竹林之游”的“七贤”,则处于或依附,或游离政治权力中心的形态,而其人格的锤炼与文学的趋新,却更多的是“不复以世用撄怀”的志趣。这既是汉晋文学大背景的历史走向,也可印证于竹林七贤的文学创造。
其二,从文学创造看竹林情怀。唐人李涉《葺夷陵幽居》诗云:“负郭依山一径深,万竿如朿翠沉沉。从来爱物多成癖,辛苦移家为竹林。”这是唐人对竹林情怀的向慕,其中的“爱物”与“移家”颇中其心与怀之结穴。考查七贤中人,并非皆能超脱政事与俗务,如山涛之“仕”与王戎之“俗”,就曾引起当时及后世的异议,即如借“酒”避世的阮籍,其撰《乐论》也极重政治功用,所谓“宾飨之诗,称礼让之则;百姓化其善,异俗服其德”“达道之化者可与审乐,好音之声者不足与论律”[4]77。只是在仕隐雅俗之间,七贤中人多选择一种混冥与游离的心态,保持一种人格的相对独立性。而这种心态落实于文学创造,正是通过两条途径来实现:一则“爱物”以游离于政事,其钟情于物的背后,则是“玄风”独煽的人生。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云:“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5]421如果说汉人论物多以宏大书写来“比德”,则魏晋中人尤好寄目微细,探寻物性,诚如张华《鹪鹩赋序》云“类有微而可以喻大”,也就是郭象注《庄》所言“大小虽殊,逍遥一也”。《晋书·向秀传》记载:“(秀)清悟有远识……雅好老、庄之学……为之隐解,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谈之者超然心悟。”[6]1374读七贤诗文,如阮籍的《清思赋》“飘摇恍惚,则洞幽贯冥;冰心玉质,则皎洁思存;恬淡无欲,则泰志适情”;嵇康《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璠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游物寄玄,“癖”中自有深意。二则“移家”,即心灵的安顿,再由内而外,成就其“雅致”与“清远”的品格。再以嵇康诗为例,其《酒会诗》有云:“流咏兰池,和声激朗……倾昧修身,惠音遗响。钟期不存,我志谁赏。”“兰池”与“竹林”,只是不同物态或符号的同一旨趣,其流咏与赏志,才是竹林文学的真谛所在。
其三,从文学追忆看竹林风采。唐代史臣在《晋书》中有评七贤之语:“嵇、阮竹林之会,刘、毕芳樽之友,驰骋庄门,排登李室。若夫仪天布宪,百官从轨,经礼之外,弃而不存。是以帝尧纵许由于埃 之表,光武舍子陵于潺湲之濑,松萝低举,用以优贤,岩水澄华,兹焉赐隐;臣行厥志,主有嘉名。至于嵇康遗巨源之书,阮氏创先生之传,军谘散发,吏部盗樽,岂以世疾名流,兹焉自垢?临锻灶而不回,登广武而长叹,则嵇琴绝响,阮气徒存。通其旁径,必凋风俗;召以效官,居然尸素。轨躅之外,或有可观者焉。咸能符契情灵,各敦终始,怆神交于晚笛,或相思而动驾。”[6]1385其中所述“嵇、阮竹林之会”“嵇康遗巨源之书,阮氏创先生之传”、嵇康的“临锻灶而不回”、阮籍的“登广武而长叹”,以及“嵇琴绝响,阮气徒存”“怆神交于晚笛,或相思而动驾”,已不限于史家的话题,而成为后世文学创作不断摹写的故事原型和精神意趣。这一点又可通过后代摹写七贤的追忆与想象,在成就作为历史化的竹林文学的同时,也因其创造而构建其经典化意义。
二、追忆·想象:竹林经典之构建
如果说向秀、王戎的“思旧”与“酒垆”属于当朝的记忆,则后世异代之人对七贤的摹写已然为追记,是通过语言符号(有关七贤事迹与七贤的文学创作)来接受并表达的。继魏晋南北朝之后,唐代是最接近竹林七贤的历史阶段,也是最具有自由挥洒、个性狂谲的诗意的时代,所以竹林文学的经典化正是通过唐人文学的追忆与想象而完成的。先看李白《献从叔当涂宰阳冰》诗中所述:“顾惭青云器,谬奉玉樽倾。山阳五百年,绿竹忽再荣。高歌振林木,大笑喧雷霆。落笔洒篆文,崩云使人惊。吐辞又炳焕,五色罗华星。秀句满江国,高才掞天庭。宰邑艰难时,浮云空古城。居人若薙草,扫地无纤茎。惠泽及飞走,农夫尽归耕。广汉水万里,长流玉琴声。雅颂播吴越,还如泰阶平。小子别金陵,来时白下亭。群凤怜客鸟,差池相哀鸣。各拔五色毛,意重泰山轻。赠微所费广,斗水浇长鲸。弹剑歌苦寒,严风起前楹。月衔天门晓,霜落牛渚清。长叹即归路,临川空屏营。”[7]639其中“山阳五百年,绿竹忽再荣”是对“竹林之游”的追忆,而其后的自我发挥却充满了现实的甘苦与历史的想象。荷兰学者佛克马、蚁布思对经典形成的界定就包括了“反复被提及”这一要素②,李白诗中所说的“绿竹忽再荣”,既是诗人对历史上之“竹林之游”的现实参与,也较典型地反映了这种反复言说的心态。
李白等唐代诗人创作对“竹林”文学的反复言说,成为咏竹诗文中的“七贤想象”,且从诸多方面展开。如“林下之游”,岑参《潼关使院怀王七季友》诗云“不负林中期,终当出尘网”;如“山阳之竹”,刘长卿《同郭参谋咏崔仆射淮南节度使厅前竹》诗云“湘浦何年变,山阳几处残”;如“阮家之会”,李白《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三首》(其一)诗云“今日竹林宴,我家贤侍郎。三杯容小阮,醉后发清狂”;如“叔夜风采”,陈陶《竹十一首》(其一)诗云“须题内史琅玕坞,几醉山阳瑟瑟村。剩养万茎将扫俗,莫教凡鸟闹云门”;如“竹林啸歌”,包融《阮公啸台》诗云“荒台森荆杞,蒙笼无上路。传是古人迹,阮公长啸处。至今清风来,时时动林树”;如“琴酒之趣”,王绩《独酌》诗云“浮生知几日,无状逐空名。不如多酿酒,时向竹林倾”。正是这种群体的追忆与想象,在形成经典话语的同时也成就了文学史的经典。
经典的形成既是一种复制,也是一种重构,七贤的群体性经典也常在个体性经典影像中得以凸显。例如唐人诗文中的“嵇康形象”就是一个典型。其一,龙章凤姿的名士风度——这是唐人追慕嵇康的风神气度。刘义庆《世说新语·容止》载:“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刘孝标注引《康别传》曰:“康长七尺八寸,伟容色,土木形骸,不加饰厉,而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正尔在群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器。”[1]553有此天质,方有其器识。唐僖宗《授郑从谠河东节度使制》谓“嵇松磊落,长标构厦之姿;和璧温良,克表如虹之气”[8]902,可窥一斑。其二,唯乐琴樽的个体自适——这是唐人追慕嵇康的生存情态。这源自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的自叙:“今但欲守陋巷,教养子孙;时时与亲旧叙离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意毕矣。”王绩《田家三首》其一云:“阮籍生涯懒,嵇康意气疏。相逢一醉饱,独坐数行书。”以意气疏喻示琴樽乐,在历史的记忆中参融了文学的想象。其三,千里命驾的契翕交游——这是唐人追慕嵇康的挚情与魅力。据《晋书》本传,嵇康“胸怀所寄,以高契难期,每思郢质。所与神交者惟陈留阮籍、河内山涛,豫其流者河内向秀、沛国刘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为竹林之游,世所谓‘竹林七贤’也……东平吕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辄千里命驾,康友而善之。”这一“千里命驾”之空间距离的泯会,还引发了唐人“千年契翕”之时间距离的协同,使“道契神交”的典范不仅属于历史,也是现实情怀的再阐。如李白《赠饶阳张司户燧》诗云“慕蔺岂曩古,攀嵇是当年”;《酬坊州王司马与阎正字对雪见赠》诗云“访戴昔未偶,寻嵇此相得”;《赠崔侍郎》诗云“不取回舟兴,而来命驾寻”,心灵之投契,略无扞格。其四,目送归鸿的潇洒人生——这是唐人追慕嵇康的恬淡怀抱与象外之意。“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乃嵇康《赠兄秀才入军十八首》(其十四)中的诗句,对此,清人王士祯《古夫于亭杂录》谈“晋人佳句”时以为“嵇语妙在象外”,“读者当以神会,庶几遇之”,堪称妙评。《晋书·顾恺之传》有载:“恺之每重嵇康四言诗,因为之图,恒云:‘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正是这种难以复制或再现的意境神韵,唐人诗中为之反复咏叹,如司空曙《送曹同椅》诗云“中散诗传画,将军扇续书”;唐彦谦《秋晚高楼》诗云“高楼瞪目归鸿远,始信嵇康欲画难”,是在图像与语象间书写了一种想象的意境。
诚然,“嵇康记忆”只是后人承协而追奉的个案,但对竹林意义之追寻却不无启迪。
三、风雅·逸韵:竹林意义之追寻
如果回到历史的本真,竹林七贤并不是一个情致尽同的整体,而是在仕与隐、雅与俗、狂与狷之间呈示出不同的选择与不同的走向。然而在后人文学作品的追摹中,竹林又往往成为一特定的语言符号,寄托了特有的情蕴,且以风雅的气质、潇洒的人生与高逸的韵致,成就其对竹林意义的追寻。
仍以唐代为例,在其大量诗文吟赞七贤风雅、逸韵时,尚有一突出现象值得关注,那就是在对当朝人“盖棺论定”的墓志中常引七贤为范,其中尤以嵇康的“雅志”与阮籍的“清远”作为人生书写的高标,这或许是接续了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所云的“嵇志清峻,阮旨遥深”的评价[5]45。先观嵇“志”的风雅,如谓“有叔夜之风,长松肃肃”(《大唐故处士吴君墓志》)③;“慕嵇夜之孤凤,追许由之绝轨”(《大唐逸人焦君墓志铭并序》);“每以琴书取乐,用启荣期之欢;文酒自贻,方给嵇康之志”(《唐故归州兴山县丞皇甫君墓志铭并序》);“陶陶然有嵇君之雅志,偘偘然有颜回之独乐”(《大唐故右卫翊卫吏部常选宁府君墓志铭并序》);“罇酒不空,得文举之深置;鸣琴流引,叶叔夜之幽栖”(《唐故始州黄安县丞尚君墓志铭并序》);“嵇康逸士,方得志于烟霞”(《唐故怀州河内县丞李府君墓志铭并序》);“马融长笛,对竹径以吟龙;叔夜鸣琴,坐梧庭而下凤”(《唐故冀州南宫县尉邢君墓志铭并序》)等,其对墓主风神、气质的描绘,“嵇志”或可视为魏晋风度的代词。再看阮“旨”的清远,如谓“阮嗣宗之材器,参亚府僚;刘公幹之词锋,才堪比况”(《唐故游击将军信义府右果毅都尉韩公墓志铭》);“通阮籍优游于步兵,庄周放旷于园吏”(《唐故支君墓志铭并序》);“俪嗣宗之竹径”(《唐故右戎卫翊卫徐君墓志铭并序》);“皎皎犹白鹤之冠群飞,肃肃类青松之标灌木……虽复步兵去位,何以尚之”(《唐故邓州司仓张君墓志铭并序》)等,也同于“嵇志”,是对竹林人生的再现。正因如此,嵇、阮合璧,也成为唐代评人铭志的惯例,如谓“一丘一壑,素琴浊酒,庄惠之临濠上,嵇阮之封山阳”(《郑故处士王君墓志》);“志尚清虚,讬巢由之放旷;情敦淡泊,访嵇阮之招携”(《唐故公孙君墓志铭并序》);“追何石之高踪,慕嵇阮之雅致”(《大唐故张君墓志之铭并序》),“嵇琴阮啸”,正在素琴浊酒、情敦淡泊之间,而托情之际,又何尝没有现实的风华与志趣?七贤风雅,竹林逸韵,在历史的升坠间被人们反复地言说,不断地影写,其文学创造中的文化意义何在?这又牵涉到另一个问题,那就是经典的树立往往是一种“纠正”,构建高标是为拯救沉沦,文学的创造与文学的研究均当作如是观。
由此,我想就“竹林”意义提出三点思考:
思考之一,雅正情怀与雅文学传统。我国自《诗》“六义”的倡导,已彰显了雅颂的文学传统,迨至班固《两都赋序》称颂汉人献赋为“雅颂之亚”,可知其所言雅颂属于宫廷文学的歌功颂德。而被后世推尊的七贤之“雅致”则不相同,是东汉文人化文学崛起后的人生毓养,是文明气质与高逸品格的礼赞。这种雅正情怀,支撑起中国雅文学传统的精神。然而这种情怀被追寻的前提,却是来自双重的挑战:一则为宫廷御用文学(如唐以后仍占主导地位的“翰苑”文学)所挤压,谀媚文风的华美与空疏,在无形销蚀与戕害文学气质、风骨时,人们对“竹林”的追慕与想象甚至重构,自然隐蕴了这层在可言说和不可言说间的深意;二则为民间俗文学的冲击,这在宋代兴起的“瓦弄”讲唱以及元人曲词中的“嘲圣”与对名士“虚伪”的贬斥中,已多呈现,“清高”常常成为嘲弄的对象而非神圣的向往。尤其是19世纪到20世纪漫长的时段,中国文学的主题是“救亡”与“济贫”,不仅宫廷的雅颂文学失落,而且个性化的雅正文学也遭忽略。而当批判文学呈示暴力,民俗文学流于低俗,中国形象与中国文明的呼唤也不限于“政治”与“旅游”,竹林文学的意义与再阐宜为警醒。
思考之二,著我精神与个性化创造。中国是个制度化极强的国家,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个人极为渺小,正因如此,竹林诸贤以其棱角分明的个性化色彩,受到后世文人的极力推尊,其中的甘苦除了“士不遇”的情怀,更多的是对自由的向往。清代诗人袁枚倡导独抒“性灵”,其中最重要的是“著我”的精神,而文学创作与研究,失去自我就没有创造,更谈不上什么“原创”,结果只是文字的堆砌和历史的复制。先父允臧教授在1936年写《我我歌》有云:“我也我固我,我及我之同;人亦我其我,更我我之躬。混合分解无非我,独体之我互爱勿交冲……不使大我损毫末,健全小我大我自成功。”没有“小我”(个性),何来“大我”(共性),竹林之“我”与后人追寻之“我”,既是孤星独耀,也是传统链接;当文学(包括研究)成为制度化的产物或规定性(如工程、项目)的附庸,苍白的学术病容不能不引起现实中人对竹林“自我”的怀想、追寻。
思考之三,艺术人生与文学的研究。在人们反复地追忆与复述“嵇琴”“阮啸”以及“千里命驾”“目送归鸿”的影像中,彰显的无非是艺术化的人生。自唐宋以后科举考“文”以来,当今学子写作论文工具化、模式化的“时风”日甚,对七贤的向慕之情弥切或许正意味着某种“缺失”。宗白华在《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一文中划分人生为五种境界,分别是功利、伦理、政治、学术与宗教,而在学术(真)、宗教(神)之间,所谓“化实景而为虚境,创形象以为象征”的才是艺术境界(美)[9]59。没有艺术的人生,何来艺术的创造、艺术的研究、艺术的享受?当文学成为追名逐利的工具,文学研究“流为历史考据学的附庸”(拙编《桐城文选·前言》),对七贤雅正、竹林逸韵的赞美,自有其推陈出新的价值与意义。
注释:
① 见清代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三〇六(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3478-3479页)。下引唐人诗文,除特别注明外,均出自《全唐诗》,不再一一标注。
② 参见佛克马、蚁布思著《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俞国强译)第三章“经典:批评和教学工具”。
③ 下引唐人墓志均见于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以及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出处不再另注。
参考文献:
[1] 杨勇.世说新语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2006.
[2] 费振刚,胡双宝,宗明华.全汉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3] 钱穆.读文选[J].新亚学报,1958(2).
[4] 陈伯君.阮籍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7.
[5] 周明.文心雕龙校释译评[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
[6] [唐]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7] [清]王琦.李太白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7.
[8] [清]董诰,等.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9] 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责任编辑 刘小兵〕
Reflection on the Literary Tradition of “Bamboo Grove”
XU Jie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Tang people’s admire of the quality and the life attitude of the “Seven Sages of the bamboo grove” is a search or memory of another generation. Their acceptation shows the certain “modernity.”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literary tradition of Bamboo Grov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elebrity’s cultural tradition in the Han and Jin dynasties, which is a continuous process of classicization containing the memory and imagination of the descendants to the “Seven Sages of the bamboo grove”. These seven laterites’ ups and downs in the history embody rich cultural significance in many aspects, which is worthy of our deep thinking.
Key words:Seven Sages of the bamboo grove; scholar in the Tang Dynasty; literary tradition; classicization; cultural connotation
作者简介:许结(1957-),男,安徽桐城人,教授,博士生导师。
收稿日期:2015-03-27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5261(2016)01−007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