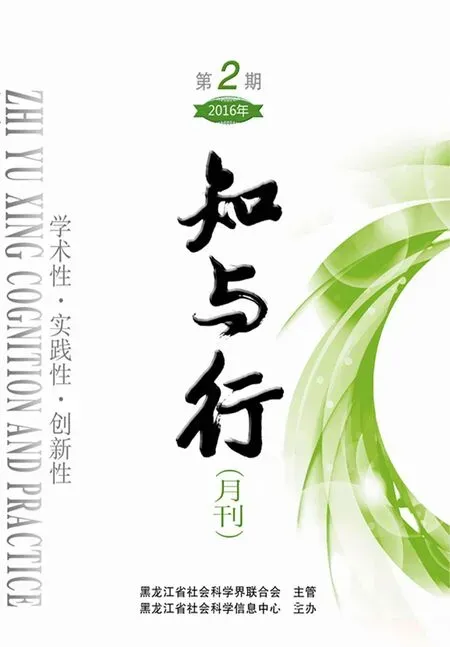文化自由、文化自律与文化他律之辨
马 健
(西南民族大学 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成都 610041)
文化创新研究
文化自由、文化自律与文化他律之辨
马健
(西南民族大学 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成都 610041)
[摘要]文化自由并非一个抽象而独立的概念,必须借助于其他概念方能准确得以理解。文化自由、文化自律和文化不自由(文化他律)这三个范畴共同构成了理解文化自由问题的整体性框架。文化自由度的大小取决于与之相对应的文化自律度和文化他律度。如果一个社会存在良好的文化自律机制,那么,每个人都能够相对充分地享受个人的文化自由,而根本无须第二方约束和第三方约束。如果一个社会缺乏良好的文化自律机制,那么,每个人虽然刚开始时或许确实能够比较充分地享受个人的文化自由,但迟早会因为社会运行成本过高而不得不诉诸第二方约束和第三方约束。如果一个社会完全缺乏文化自律机制,那么,每个人都根本无法充分享受个人的文化自由,而必须诉诸第二方约束和第三方约束。事实上,无论什么样的具体文化情境,总是存上述三种约束机制的某些组合,从而使社会运行总成本达到最小化。但问题是,每种文化约束机制都有自己的阈值。这意味着,当某种文化约束机制大大偏离其阈值之时,其他两种文化约束机制必须付出非常巨大的代价,才有可能产生接近于三种文化约束机制共同运行时所能实现的效果。所以,在充分考虑现实情况的背景下,最理想的文化约束模式是:三种文化约束机制都能够同时扮演分量相当的角色。总而言之,我们不可能抛开文化自律和文化不自由(文化他律)来抽象地单独讨论文化自由问题,因为实践中的文化自由往往是通过文化规制来界定的。当代中国正在发生深刻的社会变革,忽视文化自律,漠视文化他律,而只是单纯地追求和争取所谓文化自由的行为无益于中国的文化繁荣和社会稳定。无论哪种文化约束机制,只要大大偏离其阈值时,那么,中国社会的文化生态环境将付出非常巨大和沉重的代价。
[关键词]文化自由;文化自律;文化他律
一、文化自由:一个历久常新的话题
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并颁布的《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条内容就是“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作为一份旨在维护人类基本权利的重要文献,《世界人权宣言》开篇即将自由视为最重要和最基本的人权。就文化自由而言,《世界人权宣言》第十八条提道:“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教义、实践、礼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第十九条提道:“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第二十七条提道:“(一)人人有权自由参加社会的文化生活,享受艺术,并分享科学进步及其产生的福利。(二)人人对由于他所创作的任何科学、文学或美术作品而产生的精神的和物质的利益,有享受保护的权利。”[1]
纵观人类历史,正如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所说:“追求自由和反对自由这两者之间的斗争,构成了一条贯穿人类社会古代历史和现代历史的主线。作为一个共同的主题,自由的进程贯穿于古雅典、古罗马以及美洲移民的政体形态之中;贯穿于哲学和教会的宗旨之中;贯穿于教会和国家的斗争以及教会与教会的斗争当中;贯穿于基督教的基本原则之中,包括从中演化出去的各种教派及其敌人的教义之中。”[2]313就近现代而言,则如埃里希·弗罗姆(Erich Fromm)所言:“近现代欧美历史的中心便是人谋求自由,摆脱政治、经济、精神的羁绊。发起争取自由斗争的是那些渴望自由的被压迫者,反对的是那些维护特权的人。欲摆脱统治、谋求自身解放的阶级在斗争时坚信它在为人类的自由而战,因而可以以某种理想,吸引所有受压迫者,唤醒其内心深处隐藏的对自由的渴望。”[3]7事实上,岂止近现代的欧美历史如此,近现代的中国历史同样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时至今日,关于自由和文化自由的上述共识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公共知识。遗憾的是,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想要真正享受《世界人权宣言》所提到的那些文化自由,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那么,文化自由的实现究竟难在何处呢?
二、文化自由、文化自律与文化不自由
坦率地讲,“自由”本身就是一个不容易被准确定义的概念。阿克顿勋爵研究发现:“人们给自由所下的定义多种多样——这表明:在对自由的认识上,无论是在热爱自由的人们当中,还是在厌恶自由的人们之中,持有相同理念的人微乎其微。”[2]307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甚至认为:“同幸福与善、自然与实在一样,自由是一个意义漏洞百出以至于没有任何解释能够站得住脚的词。”[4]189布鲁诺·莱奥尼(Bruno Leoni)在回顾“自由”一词在历史上的诸多含义后总结道:“在过去的一个世纪,‘自由’一词的含义就开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同地方的不同人随心所欲地改变其含义。很多新含义是由哲学家赋予的,而这些含义是跟西方人日常语言中所普遍接受的含义大相径庭的。那些精明过人的人士一直在利用这个词比较吸引人的意思来说服他人改造行为方式,以造就一种全新的、甚至是相反的行为方式。‘自由’一词在哲学、经济学、政治学、伦理等等领域被越来越多的人按自己的方式使用,结果,该词用法上的混乱也就日趋严重。”[5]40
在布鲁诺·莱奥尼看来,从实在论(realistic)的角度来对“自由”下定义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某种独立于具体语境的所谓“自由”之物。相比之下,为“自由”下一个规定性(descriptive)和词典式(lexicographic)的定义似乎更为可行。他认为:“‘自由’一词之所以是个褒义词,是因为人们用它来指他们对自己所说的‘自由状态’(being free)的肯定性态度。”因此,无论是“自由”(freedom)一词,还是与之相关的“自由的”(free)一词,它们所蕴含的其实都是否定性内涵,都是对于“强制”(constraint)的否定性态度[5]52。就我所知,无论学者们对自由的理解有多么大的分歧,但在自由即是“免于……强制”这一点上还是相当一致的。问题在于,人们对“强制”一词内涵的理解很有可能大相径庭,因此,人们对何为“免于强制的自由”(freedom from constraint)的理解自然也就相去甚远了。作为自由的子集,文化自由所面临的问题显然非常类似。
当我们讨论自由问题时,往往会联想到一些相关的概念,例如,自由与责任,自由与强制,自由与纪律,等等。这些概念当然非常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理解自由问题。但如果我们想要真正理解文化自由问题,另外两对范畴恐怕更为重要,即:文化自由和文化自律,以及文化自由和文化不自由(文化他律)。事实上,文化自由和文化自律是天然地具有内在关联性或者互补性从而必须共同讨论的一对范畴。同样,文化自由和文化不自由,以及文化自律和文化他律(即文化不自由)也都构成了具有类似逻辑关系从而以成对面貌出现的范畴。这意味着,对文化自由的主张显然不能抛开文化自律,也不能忽视文化他律。于是,当我们讨论文化自由问题时,就不可避免地必须涉及文化自律和文化不自由(文化他律)这两个逻辑关系紧密的重要范畴。事实上,文化自由、文化自律和文化不自由(文化他律)这三个范畴共同构成了我们理解文化自由问题的整体性框架。但遗憾的是,关于文化自由问题的绝大多数探讨,要么只涉及文化自由和文化自律这一对范畴,要么只涉及文化自由和文化不自由(文化他律)这一对范畴。如此一来,显然很难全面地理解文化自由问题。只有同时观照文化自由、文化自律和文化不自由(文化他律)三者,才能真正认识到文化自由问题的关键所在。
如果我们按照“免于……强制”的传统思路来理解文化自由问题,即使不将文化自由置于“文化自由——文化自律——文化不自由(文化他律)”的这个整体性框架之下,同样会发现,文化自由并不是一个抽象而独立的概念,而必须借助于其他概念方能准确得以理解。因为文化自由从来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正如阿克顿勋爵所说:“任何自由都是有条件的、有限的,因而是不均等的。”[2]331“只有当人们学会遵守和服从某些法则之后,自由才开始真正出现。”[2]315因为“自由要求具有牺牲精神。它假定事物存在着众多的可能性状态——这就要求在相互竞争的众多利益之间要相互做出妥协和牺牲部分利益”[2]311。所以,文化自由不仅意味着一个人拥有进行自由选择的文化权利,而且意味着他必须随之承担起这一选择的各种社会后果,例如,尊重或者侮辱,褒扬或者批评。有文化自由,就自然而然会有文化自律和文化他律。
尽管我们也可以按照托马斯·格林(Thomas Green)和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等人的思路,将文化自由分为“积极的文化自由”(做……的文化自由)和“消极的文化自由”(免于做……的文化自由)。但如果我们抛开理解文化自由的上述整体性框架,会发现这种分类方式对于我们理解文化自由的帮助并不大。这是因为,从内涵来看,积极的文化自由(肯定性的文化自由)就是自己做主的文化自由。消极的文化自由(否定性的文化自由)就是非我做主的文化自由,即因为他人不干涉我从而赋予我的文化自由。就本质而言,积极的文化自由和消极的文化自由都是一种摆脱外在强制,没有外在障碍的文化自由。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积极的文化自由所面对的外在强制和外在障碍是由自己给自己的,而消极的文化自由所面对的外在强制和外在障碍则是由他人给自己的。只有当我们将这种分类方式置于理解文化自由的上述整体性框架中,才会发现其价值所在。因为积极的文化自由直接对应于文化自律,而消极的文化自由则直接对应于文化他律。但这种分类依然无助于我们从数量上认识文化自由、文化自律和文化不自由(文化他律)的关系。因为这还涉及另外三个与之一一对应的概念:文化自由度、文化自律度和文化他律度。
三、文化自由度、文化自律度与文化他律度
事实上,文化自由度的大小,正是取决于与之相对应的文化自律度和文化他律度。如果一个社会的文化自律度很高,那么,根本无须借助于文化他律,个人就可以享有足够的文化自由。但遗憾的是,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很难找到这样的现实状况。因为人是非常复杂的动物,不同人对文化自由的认知也不尽相同,他们对他人言行的容忍度也不一样,这些人的文化自由实践更是各具特色。从时间维度来看,即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年龄段对文化自由的认知和对其他人言行的容忍度,以及他的个人文化偏好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从空间维度来看,即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情境下,他所表现出来的对文化自由的看法,他对其他人言行的容忍度,以及他的文化偏好也都可能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时候甚至根本分不清人们的行为到底是因为文化自律还是出于可预期的文化他律。
举例来说,由于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等原因,巫术与魔法在沙特阿拉伯是被明令禁止的重罪。据报道:“在沙特,搞巫术是与强奸、谋杀、武装抢劫及走私毒品等并列的重罪,巫师更是政府明令禁止的职业,抓到通常要被砍头示众。因此,即便是风靡全球的小说《哈利·波特》,也因为‘谈论巫术与魔法’而在沙特禁止发行。”例如,2011年12月12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市中心广场,一名主要在沙特北部朱夫一带活动,被认定为“巫师”的女子就被当众砍头处决。在沙特因此而获罪的人绝非个例。在她之前,同年9月,还有一名苏丹人因在沙特涉嫌“巫术诈骗罪”而被沙特政府砍掉了脑袋。即使如此,“在沙特,不少人相信巫术,对巫术的态度非常认真。特别是乡村和偏远地区,人们受教育程度低,文盲比例高,再加上生活环境封闭,这里的人很容易相信冥冥之中精灵鬼怪的存在,相信其神奇无比的力量”[6]。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看起来远离巫术的沙特人,到底是因为自己信仰坚定、严守教规(文化自律),还是他预料到了接触巫术的严重后果(可预期的文化他律),抑或是两种因素兼而有之(文化自律和可预期的文化他律),对于外人而言,确实很难判断。
另一方面,由于每个人都有追求文化自由的天性,因此,文化自律度很高的社会确实不多见,尤其是在那些缺乏信仰和道德失范之地。但这绝不意味着文化自律就不重要。事实上,如果没有文化自律的话,文化自由最终势必沦为文化不自由。但非常不幸的是,这种情况极其常见。当社会的文化自律度很小的时候,就不得不诉诸其他文化约束机制。概而言之,在日常文化生活中,存在三种文化约束机制:一是来自自我的约束,即第一方约束(文化自律);二是来自直接利害关系人的约束,即第二方约束(文化他律);三是来自非直接利害关系人的约束,即第三方约束(文化他律)。在人类历史上,就有很多并无直接利害冲突但具有所谓“文化正义感”和“文化责任感”的“强互惠主义者”(strong reciprocator),他们之所以挺身而出维护文化秩序,主动扮演文化规制者的角色,对违规者实施利他惩罚(altruistic punishment),很可能仅仅因为“看不惯”和“不舒服”,他们仅仅依靠来自大脑尾状核(caudate nucleus)的自我激励机制就能够拥有足够的动力去做那些具有“替天行道”色彩的利他惩罚和很多看似“非理性”之事。
四、结语
如果一个社会存在良好的文化自律机制,那么,每个人都能够相对充分地享受个人的文化自由,而根本无须第二方约束和第三方约束。如果一个社会缺乏良好的文化自律机制,那么,每个人虽然刚开始时或许确实能够比较充分地享受个人的文化自由,但迟早会因为社会运行成本过高而不得不诉诸第二方约束和第三方约束。如果一个社会完全缺乏文化自律机制,那么,每个人都根本无法充分享受个人的文化自由,而必须诉诸第二方约束和第三方约束。事实上,无论是哪种具体的文化情境,总是存在上述三种约束机制的某些组合,从而使社会运行总成本达到最小化。但问题是,每种文化约束机制都有自己的阈值。这意味着,当某种文化约束机制大大偏离其阈值之时,那么,其他两种文化约束机制必须付出非常巨大的代价,才有可能产生接近于三种文化约束机制共同运行时所能实现的效果。所以,在充分考虑现实情况的背景下,最理想的文化约束模式是:三种文化约束机制都能够同时扮演分量相当的角色。总而言之,我们不可能抛开文化自律和文化不自由(文化他律)来抽象地单独讨论文化自由问题,因为实践中的文化自由往往是通过文化规制来界定的。当代中国正在发生深刻的社会变革,忽视文化自律,漠视文化他律,而只是单纯地追求和争取所谓文化自由的行为无益于中国的文化繁荣和社会稳定。无论哪种文化约束机制,只要大大偏离其阈值时,那么,中国社会的文化生态环境将付出非常巨大和沉重的代价。
[参考文献]
[1]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EB/OL].http://www.un.org/chinese/hr/issue/udhr.htm.
[2][英]阿克顿.自由与权力[M].侯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3][美]埃里希·弗罗姆.逃避自由[M].刘林海,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
[4][英]以赛亚·伯林.自由论[M].胡传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5][意]布鲁诺·莱奥尼.自由与法律[M].秋风,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6]黄培昭.违背宗教信仰,被指欺骗民众,沙特政府把巫师送上断头台[J].环球人物,2011,(34).
〔责任编辑:屈海燕〕
[中图分类号]G1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6)02-0061-04
[作者简介]马健(1981—),男,四川雅安人,副教授,博士,从事文化政策与管理研究。
[收稿日期]2015-1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