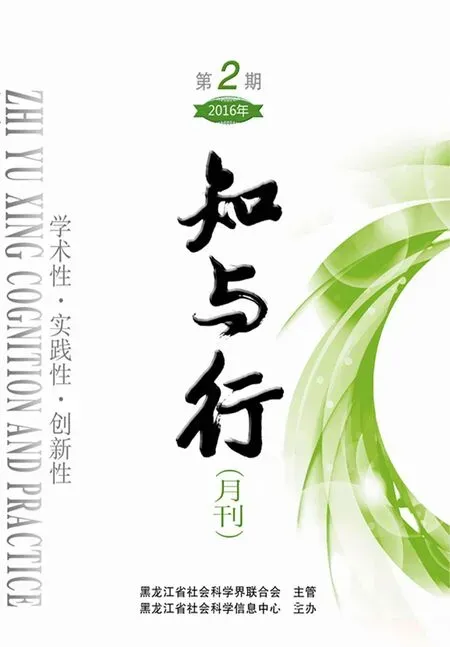浅谈巴赫金狂欢化理论对流散文学的影响
王华伟
(西北大学 文学院,西安 710127)
文化创新研究
浅谈巴赫金狂欢化理论对流散文学的影响
王华伟
(西北大学 文学院,西安 710127)
[摘要]莫欣·哈米德的《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是近年来在美国这一异质化文化土壤上生成的流散文学的代表作品之一,作品通过讲述一个因家道中落而生活在纽约的巴基斯坦裔流散者昌盖兹“美国梦”的努力构建与急速破灭,刻画了主人公因游离于故国文化和他国文化之间所不得不承受的孤独感、陌生感和漂泊感,在美国怪诞现实和异质文化的排挤与压迫下无奈地选择回归本土编织属于自己的“巴基斯坦梦”。作品暗示出“后9·11”时代美国对自我强势价值和文化的迷恋,对异质弱势文化和群体的强行同化。通过运用巴赫金狂欢化理论深入分析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加冕脱冕、降格升格、狂欢人物形象和复调因素等狂欢化特征,可以看出,作者莫欣·哈米德作为一名流散作家,站在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世界的双重视角,独特地审视 “后9·11”时代美国社会的病态心理、文化缺陷和怪诞现实,揭露“美国梦”的衰败之势,亦流露出流散者对母国的空间依恋和对原乡的精神渴求。
[关键词]狂欢;流散;美国梦
一、流散与梦想
流散(Diaspora)源自希腊语,意思是远离本土与本族而散居于他者异质文化的边缘地带和夹缝当中,亦可译为飞散、流亡、离散等。流散现象,作为历史文化范畴的概念,源于犹太人被迫逃离故土而散居世界的历史事实。但伴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蔓延与深入,尤其是在后殖民时代背景下,流散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各族裔大规模移民所形成的一种流散态势和普遍现象。流散文学即是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应运而生并呈蓬勃发展之势,流散文学又被称为流亡小说、边缘写作、少数族裔文学、夹缝文学和流浪汉小说等,流散作家代表及其作品有:奈保尔的《幽暗国度》,拉什迪的《午夜之子》,谭恩美的《喜福会》,莎塔碧的《我在伊朗长大》,等等。
《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The Reluctant Fundamentalist)是旅居英国伦敦的巴基斯坦裔流散作家莫欣·哈米德(Mohsin Hamid)入围英国布克奖决选的代表作品。作品一经问世便在伊斯兰世界和西方社会引起巨大反响,且评议不断、批评四起。小说主要讲述了一个巴基斯坦青年背井离乡远赴美国追寻以自由、平等和成功为主要内容的“美国梦”的故事。主人公昌盖兹(Changez)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美国顶尖名校普林斯顿大学,供职于纽约顶级评估行恩德伍德·山姆森公司。在外人看来,昌盖兹工作稳定、收入丰厚、地位颇高,作为一名流散于美国土地的异乡人离梦想渐行渐近,甚或已经得到梦寐以求的像美国人一样的生活。但实际上,他的外在肤色、容貌,失败的爱情,基督教的强权意识,以及边缘化的穆斯林异族和流散者身份,使昌盖兹承受了巨大的孤独感、陌生感和漂泊感,也使他认识到自己与“后9·11”时代的美国渐行渐远。在美国怪诞现实和异质文化的排挤与压迫下,昌盖兹最终选择回归遥远的祖国,找回“行将失去”的拉合尔,编织属于自己的“巴基斯坦梦”。小说作者莫欣·哈米德本人出生在巴基斯坦拉合尔市,具有多年美国名校教育背景与高级财务管理工作经验,并亲历“9·11”事件,这一切决定了其作品客观的态度、独特的视角、多维的关注和深刻的思考。
国外对莫欣·哈米德及其作品《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的研究较热且多侧重文化视角。国内学者则在其被译成中文之后,从文化和语言学的角度对其展开研究。从巴赫金狂欢化理论的角度来探讨和阐释《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的狂欢化特征,可以以全新的视角揭示流散少数族裔在异国他乡追寻梦想跌宕起伏的心路历程。
二、梦想的狂欢化
狂欢是大众的、全民的,是充满欢乐的,也是超常规的,它通过狂欢歌舞、纵情畅饮、疯狂派对,甚至是某些狂欢的日常活动得以实现。巴赫金狂欢化理论具有鲜明的民间立场,挖掘了民间文化中的原初性和全民性潜质,点燃了人类共有的狂欢化精神之火。这种潜质与精神不仅存在于古希腊罗马年代,同样存在于当今高度发达的多元化的美国社会。现实社会里的狂欢节以及狂欢节上上演的五花八门的狂欢化活动,通过文学作品来再现现实世界的狂欢化表现。在狂欢化的现实社会里,人们之间建立了一种有别于真实世界的、非官方的、无等级差别的新型交往前提与关系,这是一次自下而上、由内而外的彻彻底底的颠覆,可以说“狂欢节是一种全民性的演出,他打破了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以及与之相关的恐惧、敬畏、虔诚和礼节。在狂欢节中,人们可以尽情地放纵自我、欢歌笑语、自由自在”[1]85。因此,狂欢节俨然就是与现实世界形成鲜明对照的“第二个世界”,日常生活之外的“第二种生活”。 在《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中,对主人公昌盖兹而言,纽约便是其存在空间中的第二个梦想世界,而追寻“美国梦”的狂欢之旅自然而然成为他的第二种生活体验。
(一)多变的命运
狂欢仪式的高潮迭起是国王或小丑加冕和脱冕的戏剧性变化过程,充斥着加冕、脱冕的变化更替,具有非官方性、全民性、不确定性、包罗万象性和双重性等特征。巴赫金捕捉到了狂欢节深邃的象征意义,无论是加冕还是脱冕都不会是独立存在或不可转换的,准确来讲,“加冕与脱冕仪式的基础是狂欢节世界感受的核心所在,这个核心就是交替与变更的精神、死亡与新生的精神”[2]76。换句话说,狂欢节当中的形象都是“合二为一的”,具有显著两面性的,同时也是辩证统一的。加冕孕育着脱冕,脱冕预示着新的加冕,两者互为联系、此消彼长。
加冕、脱冕在作品《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中不断上演。主人公昌盖兹离开家道中落的巴基斯坦老家就读于美国名校普林斯顿大学并顺利毕业,完成了第一次自我加冕;大学毕业后,昌盖兹从众多求职者中脱颖而出获得纽约恩德伍德·山姆森(Underwood Samson)评估行分析师的职位,志得意满的昌盖兹通过工作顺利地融入纽约、融入美国上流社会,完成了第二次自我加冕;昌盖兹在大学毕业旅行中认识了美国富家小姐艾丽卡(Erica),回到纽约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两人之间的感情逐步升温,交往日益深入,完成了第三次自我加冕;昌盖兹因工作成绩突出、业绩考评优异,获得公司执行董事吉姆的青睐,经常被公司委以重任,至此昌盖兹完成了第四次自我加冕。昌盖兹的自我加冕让他看起来越来越像“纽约人”,也让他自以为已经实现了“美国梦”。
加冕和脱冕的交替变更精神决定了主人公昌盖兹的自我加冕只是暂时的。四次自我加冕并非永久不变的加冕,实际上预示着更为彻底、更深一层的脱冕。“9·11”事件的突然发生,不仅从肉体和心灵上伤害了美国人,也彻底改变了流散在美国的穆斯林异族的境遇、命运和梦想,同时也宣告了美国社会彻底告别过去的自己撕掉“自由民主宽容理性”的虚伪面纱。拥有着典型大胡子、深皮肤穆斯林形象的昌盖兹难逃例外,在现实中一次一次完成脱冕,尽管其脱冕有被动的也有主动的。“9·11”事件之后,不论因公出差还是因私回乡返程的入境,昌盖兹均被迫接受美国机场安检的严格而特别的搜身,公然受到美国人的怀疑和敌视,“后9·11”时代的美国社会对其进行了一次被动的脱冕;公司同事的冷眼相对,智利老人胡安·巴蒂斯塔催化剂般的谈话,最终让昌盖兹选择了辞职、选择了离开美国,昌盖兹离职时眼眶中的些许眼泪与同事们目光中透露的冷漠、不安和恐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昌盖兹脸上被贴上的“fundamentalist”(宗教激进分子)标签帮助其完成了一次主动的脱冕;“9·11”事件让气质典雅、魅力非凡的,最接近狂欢节女王形象的女主人公艾丽卡再次受到创伤,从冷漠到拒接电话,从抑郁到入住疗养院,从失踪到跳崖自杀,艾丽卡与朝思暮想的患病死去的前男友克里斯在天国继续相爱,完成了自我的彻底脱冕和再度加冕。至此,昌盖兹在异质文化中的流散趋于失败,在异国搭建的梦想最终破灭。
一次性的脱冕,或者一次又一次的多次脱冕,并非终身的、彻底的脱冕,而是“透过脱冕仪式,预示着又一次的加冕”[3]161。 昌盖兹结束身体和精神上的流散,回归巴基斯坦老家,在巴基斯坦大学从事自己喜欢的事业,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亦是另一个梦想的开始,也是再一次的自我加冕。正如主人公昌盖兹名字的英文拼写Changez一样,昌盖兹在流散纽约与回归故乡过程中所寻找的身份与文化认同一直充满着变化(changes),家庭的变化,文化的变化,梦想的变化,身份的变化和爱情的变化,却在变化中不断寻找自我。
(二)现实的怪诞
尽管按照现行法律规定了可以适用以及不得适用继续盘问的情形,但在实际工作中,仍然还存在着任意扩大继续盘问对象范围的问题。对于流浪者、乞讨者、已经被确定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仍然还存在着适用继续盘问的现象。对于流浪者、乞讨者,如果其行为不涉嫌违法犯罪,不能够适用继续盘问。
狂欢化的另外一种表现就是怪诞现实主义。怪诞现实主义的主要特点是世俗化、向下化和肉体化,重要的表现途径为降格,也就是“把一切高级的、精神性的、理想的和抽象的东西转移到整个不可分割的物质-肉体层面、大地和身体的层面”[4]24。降格就是通过对高尚事物的贬低甚至是毁灭来达到狂欢化的效果,具有否定和肯定的双重含义。逆向思考一下,基于巴赫金对狂欢化的阐述,文学作品亦可通过对丑陋的、低俗的和下贱的事物的正面描写与渲染,或者通过提升其地位,帮助物质的和肉体的形象实现升格,达到同样的狂欢化效果。
美国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就是因为在众多non-Americans(非美国人)的眼里,美国科技发达、社会开放、文化多元,是铸就个人梦想、实现人生价值的机会之所和理想圣地。作品主人公昌盖兹曾工作的美国公司的名字英文拼写为Underwood Samson,英文缩写是U.S.,无独有偶美国的英文缩写也是U.S.。文学作品中纽约的恩德伍德﹒山姆森(Underwood Samson)评估行只关心效益不关心被评估公司员工生计和死活的公司理念,象征着现实世界中的美国处处扮演世界警察、时时进行经济掠夺的强权蛮横形象,作品通过运用特殊的降格实现了对美国传统形象的丑化和世界地位的贬低。作品中的女主人公艾丽卡(Erica),其实是作者对美国另外一个英文名字(America)的拆分,暗指“I am Erica”。 实际上,作品通过大肆渲染美国富家小姐艾丽卡和巴基斯坦人昌盖兹之间从吸引、甜蜜到幻想、挣扎、失踪直至死亡的爱情故事,描绘出了一个现实的、真正的美国:社会不那么开放,文化不那么包容,梦想不那么容易,生活不那么美好,甚至是虚伪的、有缺陷的。艾丽卡的精神失常、失踪和死亡同样是对美国的又一次降格和贬低。借此,小说表达了主人公昌盖兹对美国社会现实的无奈和批判,流露出了对母国的回望之意和对原乡的思念之情。
(三)模糊的身份
狂欢的实现绝不可少的是狂欢广场上的焦点狂欢人物,他们多为狡猾的骗子、滑稽的小丑、忠实的傻瓜和夸张的巨人等形象。作为特殊群体的他们能够站在自己别样的视角,用自己狂欢的眼光看到他人看不到的现实世界与真实生活,揭穿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总之,“这些多种多样的诙谐形式和表现-狂欢节类型的广场节庆活动、某些诙谐仪式和祭祀活动、小丑和傻瓜、巨人、侏儒和残疾人、各种各样的江湖艺人、种类和数量繁多的戏仿体文学,等等,它们都具有一种共同的风格,都是统一而完整的民间诙谐文化、狂欢节文化的一部分和一分子”[5]4。狂欢广场上常见的小丑、傻瓜和骗子等狂欢化人物,通常来自社会底层,生活在边缘地带,基本或完全丧失话语权,成为狂欢广场上反面的而又不可缺少的存在元素。作为一幕幕狂欢化表演的狂欢广场随处可见,“只要能成为形形色色人们相聚和交际的地方,例如大街、小酒馆、道路、澡堂、船上甲板等等,都会增添一种狂欢广场的意味”[3]169。
昌盖兹不远万里来到美国追寻自己的“美国梦”,把纽约当作心灵的港湾和未来的归宿。衣食无忧的白领生活,美丽富有的女朋友,公司董事眼中的宠儿,上流社会的常客,如此等等。此时的纽约俨然已经成为昌盖兹的第二故乡,此刻的昌盖兹已经成为地地道道的美国人。所以,现实生活中的昌盖兹可以自由平等、毫无忌惮地与美国佬交流、交往甚至亲昵。但“9·11”事件让昌盖兹的工作无法再继续,与同事无法再相处,爱情无法再相守,生活无法再面对,梦想无法再实现,瞬间跌落至美国社会的底层,开始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流浪。凌建侯认为“狂欢人物经常是小丑、傻瓜和骗子三种人物,我认为还应加上流浪者。仪式、演出和广场言语只是狂欢化最表层的特点,而其核心是突出边缘视角”[5]107。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昌盖兹就是美国社会中典型的街头流浪汉。
狂欢人物在狂欢广场上的表演通常不受具体空间的局限,只受时间的限制,而且一切形式的狂欢化表演皆有可能,一直处在正在进行中的和未完成的状态。对《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中的主人公昌盖兹而言,海滩、咖啡馆、公司、纽约的大街小巷就是象征意义上的狂欢广场。虽然昌盖兹的流散经历在表现形式上看似缺乏足够的狂欢化因素(仅仅是巴基斯坦裔流散者,美国人心中的“小丑”和“流浪者”等),但它的基础却是狂欢节的世界感受,所以昌盖兹就是狂欢广场上的焦点和主角。所有的这一切,让昌盖兹最终幡然醒悟自己自始至终都没有真正融入美国社会,一直是游走在美国社会边缘地带的“异类”,是美国主流社会之外的“他者”。
(四)渐失的对话
狂欢打破了生活中的常规习俗、等级秩序和权威统治,使得具有不同文化与身份背景的人们可以自由、平等而亲密地交往,进而就为平等对话的实现和新型人际关系的确立提供了可能性。小说中各种声音所体现的自由度和独立性,构成了小说人物进行平等对话的场域,而正是“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3]29。也就是说,各种文学作品中的多种声音和意识各自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并作为独立个体交织于整体之中。在小说《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中就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声音,有公司执行董事的声音,有公司副总的声音,有公司同事的声音,有女朋友的声音,有具有穆斯林背景的人的声音,有来自第三世界智利老者的声音,等等。所有的这些声音相互冲击、碰撞和交融,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对话,具备了一定的复调因素,平等的或不平等的。
《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中主人公相对独立的个性特征和较为清晰的自我意识,为小说的复调打下基础,为人物的对话铺平道路,作品凸显出复调小说“不是主人公是怎样出现于世界,而首先是世界对他来说是什么,和他自身对自己来说是什么”[6]31的特点。主人公昌盖兹作为一名流散于美国世界的巴基斯坦追梦人,他的声音和意识都是通过生活、工作和爱情来自然表现和流露的,因为美国就是他心目中开放、包容、多元的天堂,而自己可以自由、自信、自得地行走其中,这种对话表面上看起来是中心的、独立的和平等的,事实上也曾经如此。“9·11”事件却让这种对话瞬间土崩瓦解,昌盖兹很快被打回到“他者”和边缘人的原点位置,声音被掩埋、话语被剥夺、爱情被扼杀,这就意味着具有穆斯林背景的流散者和美国人之间并不能真正平等亲密地对话,复调对话也就无从谈起。因此,美国社会有限的开放、虚假的包容和强势的文化,让深处其中的昌盖兹无法真正平等地与美国人对话。
三、结语:没落的“美国梦”
《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是一部充满狂欢化色彩的流散小说,作品通过描绘家道中落的巴基斯坦裔流散者昌盖兹起起伏伏的梦想经历和爱情故事,巧妙运用加冕脱冕、降格升格、狂欢人物形象和复调因素等狂欢化表现形式,暗示了“后9·11”时代美国对自我强势价值和文化的迷恋,和对异质弱势文化和群体的强行同化。作为一名流散作家,作者莫欣·哈米德能够站在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世界的双重视角,独特而客观地审视美国社会的病态心理和文化缺陷,揭露“美国梦”在“后9·11”时代的衰败之势,同时流露出流散者对母国的空间依恋和对原乡的精神渴求。
[参考文献]
[1][苏]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3卷)[M].白春仁,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2]夏忠宪.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理论[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5):74—82.
[3][苏]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5卷)[M].白春仁,顾亚铃,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4][苏]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6卷)[M].李兆林,夏忠宪,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5]凌建侯.从狂欢理论视角看疯癫形象[J].国外文学,2007,(3):105—112.
[6]钱中文.复调小说:主人公与作者——巴赫金的叙述理论[J].外国文学评论,1987,(1):30—40.
〔责任编辑:屈海燕〕
[中图分类号]I10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6)02-0068-04
[作者简介]王华伟(1979—),男,河南南阳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从事文艺美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收稿日期]2015-1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