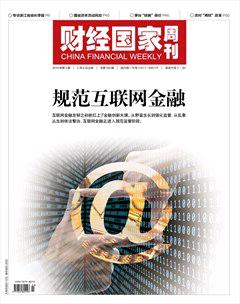国民政府官员眼中的日据台湾
唐博
1936年12月13日,台湾基隆。
“香港丸”号轮船缓缓离港。一群西服革履的男士在船舷边凭栏挥手,向岸上的送行者告别。码头上的建筑物渐渐依稀,而他们谈论的话题依旧是刚刚离开的宝岛——台湾,而不是前日发生在西安的爆炸性新闻——张学良、杨虎城“兵谏”。
国民政府厦门市市长李时霖就在这群人里,此次奉命率团一行11人赴台半月,足迹遍布基隆、台北、台中、台南。这一年,正是中日交恶、战祸临头的当口。选择此时参访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不免要冒政治风险。那么,他为什么要执意此行呢?故事还要从一年前的台北说起。
赶超梦想
1935年10月,日本殖民当局举办了一场“台湾博览会”,旨在纪念台湾“总督府”成立40周年,凸显台湾在“南进政策”中的枢纽地位。日本、朝鲜、“伪满”、华南、南洋等地纷纷参展,展品超过30万件。盛况令应邀参观的国民政府福建省主席陈仪深受触动。

厦门与小金门隔海相望,一衣带水,文化同源。
福建和台湾一衣带水,气候相似,环境相近,语言相通,文化同源。然而,1930年代的福建,交通闭塞,教育落后,粮食无法自给,社会秩序混乱,茶叶出口受到印度冲击,对外贸易一落千丈,导致财政羸弱。相比之下,“台湾之幅员只为福建四分之一强……而其生产能力竟超吾闽六倍以上,只米糖二项,一年所产值……足抵吾闽全省三年生产而有余。”
不过,陈仪在“台湾博览会”上推销福建特产,一月间卖了1.8亿元货值。要知道,这年全国出口总额也只有6亿元左右。这样的成绩让他相信,福建诚落后一时,但有能力赶超。为了让赶超的愿望尽快落实,李时霖领命率团赴台。考察团里,就有4名来自基层的县长。
“去中国化”
在李时霖的考察团里,中南银行厦门分行行长章叔淳眼光独到。在他的记述里,1935年的台湾,总人口500万,其中日侨30多万,祖籍福建厦漳泉的超80%。不过,“谈到台湾与福建的关系,他们与福建的关系,他们都茫然了,甚至于有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厦门与台湾是同方言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皇民化”教育和同化政策显然很突出。不过,章叔淳另辟蹊径,提到了两种“去中国化”的现象:
当时全台只有一所大学,主要开设农林医学专业。这就使台湾民众就地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少、专业选择面和就业面狭窄。导致陈仪所言的现象:“所有地位较高的工作,台湾人向来没有插足的机会。据闻台湾政府里面,仅有两个课长以及几个课员若干技士是台湾籍,其余都是日本人。”多数台湾民众失去了增长见识、了解外部的机会,随着时间推移和代际转换,不得不转入对殖民统治现状的接受和适应。
在台湾,“医生”从事中医,“医师”从事西医。甲午战争前,“医生”遍及城乡,“然彼辈诊疗方法,但凭经验而不重科学,故台湾政府决意淘汰之”。殖民当局一面“积极添设新式医院,开办医学专门学校培养(西医)人才”,一面制订规则,要求“医生”从业须到当局登记,领取执业许可证。后来,许可证停发,“医生”的执业空间压缩,从业人数锐减,到1935年仅剩256人,且后继无人。相反,在当局扶植下,“医师”从无到有,发展迅速。到1935年已达230多人。
明治维新倡导“全盘西化”,在“西医”和“中医”的定位上自然厚此薄彼。中医代表中华文化,对其逐步消除,成为殖民当局对台湾民众去除民族记忆的一种手段。西医借助政策扶植,不但在台湾落地生根,还在政治上有亲日倾向。这一现象至今仍有影响。
农业“统制”
随团赴台的永定县县长钟干丞,对台湾农业的进步赞赏有加:“举凡农田水利、生产、交通、咸与维新,荒陬孤岛,其物质建设之日就休明,真有出人意表者。”他将这一切归功于殖民当局的“统制政策”。
出于攫取农产品资源,支撑侵略战争的需要,殖民当局重视农业发展。其农业统制政策,包括扶植农会、改良技术、奖励耕种、减免租税、兴修水利等,近乎大包大揽。
根据1908年公布的规则,农会作为法人实体,由各地向总督申请报批,强制设立。日常工作由地方当局掌控,甚至会长和副会长分别由地方主官和地方劝业课课长兼任,官方色彩浓厚。殖民当局以农会为先导,举办农事讲习会、品评会、恳亲会、竞进会等,宣讲新技术,推动品种改良和疾病预防。农会成为官方贯彻农业政策和扶助农业经济的主渠道。
殖民当局还在农具改进、深耕堆肥、采种组合、除虫拔稗、施用绿肥等方面斥资奖励。农民购买特别种子苗木价值百元以上补助30元。开设农业传习所,向青年农民开展农业科普教育,学制一年,免收学费和伙食费。1930年代,台湾农民要交6种赋税,但名目固定,总体税率低于大陆同期水平。殖民当局出资修建嘉南大圳、日月潭水电站等大型水利工程,以及一批打通村落之间联络的公路,便利了台湾西部平地的农业生产。采取专人分区承包管理的模式,保护台湾中南部的原始森林免遭乱砍滥伐。
李时霖考察团目光所及,是日本殖民当局通过农业统制政策,对台湾农业和农村经济提供保护和扶助的表象,客观上推动了1930年代台湾农业的发展。然而,在表象的背后,还潜藏着哪些问题?这些所谓“经验”,对于振兴福建经济是否管用呢?
模仿效果
李时霖回闽之后,以“统制政策”为代表的台湾经验逐渐在福建落地。省府统一对外行文,实现政出一门,省主席说了算。这一强悍作风振刷了官场积弊,推动了当地的政治进步、经济发展和闽台交流。
强悍背后,隐忧频现。政府过多干预微观经济,配套措施脱节,导致民间经济活力衰退,民众未蒙其利,反受其害,抗议不断。1941年福州沦陷,陈仪失地有责,自请处分,调离福建。而李时霖早已奉命到香港募捐抗战善款,从此告别政坛,专注于翻译、书画和学术。
1937年,李时霖主编的《台湾考察报告》出版问世,汇集了考察团成员撰写的12篇专论和1篇日记。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的卫生事业、行政机构、鸦片制度、农村经济、交通电气、地租价格等情况跃然纸上,成为今人了解1930年代台湾经济社会面貌的重要文献。其收集的数据资料丰富,使陈仪团队成为名副其实的“台湾通”,为1945年接收台湾做了准备。
需要注意的是,李时霖等人警觉地发现,当时台湾与大陆的关系,由于隔绝日久而更加疏远。只有加强两岸交流,重塑台湾民众的中华民族认同,才能逐步破解由于国土分离造成的陌生感。然而,1945年台湾光复后,这一隐忧依旧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