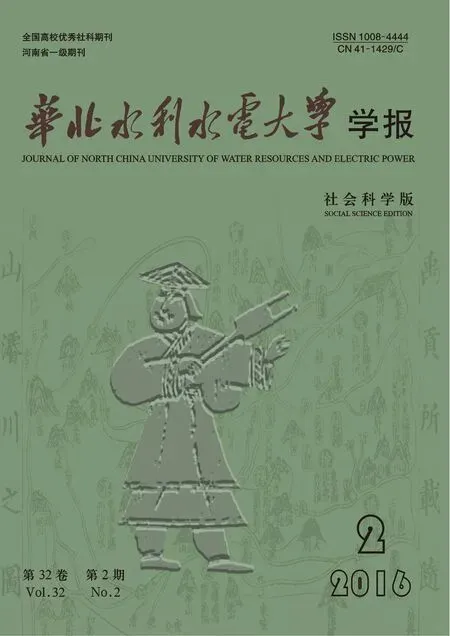视觉文化语境下文学经典的现代重构
——以《赵氏孤儿》改编为例
杨华轲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人文艺术教育中心,河南 郑州 450046)
视觉文化语境下文学经典的现代重构
——以《赵氏孤儿》改编为例
杨华轲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人文艺术教育中心,河南 郑州 450046)
摘要:在视觉文化语境下,大量的文学经典被改变成影视作品或其他的视觉艺术样式。这种改编既有经典的传承,也有现代性的重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具有通俗化倾向。《赵氏孤儿》在新世纪的改编有话剧版本、电影版本,还有其他电视剧、戏剧版本等。其中话剧版本和电影版本的改编既具有典型性,也具有创新性。这些改编通过改写矛盾冲突、淡化忠奸善恶、丰富人物形象,使之更趋于人性化、复杂化;通过改变故事主题,启发人们进行多元化思考。文学经典的现代重构既是文学创作规律使然,同时也是时代文化的深刻反映。
关键词:视觉文化;《赵氏孤儿》;现代重构;人性
视觉文化以影像叙事的形象性和直接性将人类从文字语言抽象概念的范畴中解放出来,以图像符号为构成元素,以视觉知觉可以感知的样式为外在表现形态,强调在表现方式上要脱离以语言为中心的理性主义形态,逐渐转向以形象(尤其是影像)为中心的感性主义形态[1]。当今时代,越来越被称之为一个“读图时代”,影像和各种视像成为现代文化的主要承载方式,审美文化正在日益变成一种视觉文化。在此语境下,文学影响力逐渐消弱,影视艺术强势崛起,这已成为令人瞩目的世界性文化现象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视觉文化的冲击下,文学创作及文学阅读走向衰落,而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和舞台艺术却异常火热。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了解一部文学经典,最便捷的方式就是通过影视或网络。“文学名著不断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越来越多的人乐于通过看电视剧而不是阅读来了解这些名著,影视镜像不断地驾驭、凌越乃至征服文字。”[2]
赵氏孤儿的故事在我国家喻户晓,在古典叙事文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这个故事最早见于《左传》的简略记载,后经《史记》进一步丰富发挥,到元杂剧时期,纪君祥创作的《赵氏孤儿》情节紧凑、矛盾突出、形象鲜明、感情饱满,成为舞台表演的经典作品。继元杂剧《赵氏孤儿》之后,这个故事更是不断被改编成各种戏剧形式在民间广泛传唱。至今,赵氏孤儿的故事承载着中国人对于忠奸、善恶、真假的文化评判,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一部分。进入新世纪以来,赵氏孤儿的故事除在戏剧舞台上被改编并继续上演之外,在话剧舞台和影视作品中也有了新的改编。2003年,林兆华和田沁鑫的同名话剧《赵氏孤儿》同时上演,引起剧作家和文学评论家的广泛关注。2010年,陈凯歌的电影《赵氏孤儿》公映,引起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和评价,有关赵氏孤儿的道德评价、文化评价、政治评价等再次引起广泛争议。
在今天视觉文化的背景下,赵氏孤儿的故事被改编是必然的,引起争议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话剧版和电影版的改编对于原著来讲,具有颠覆式的现代重构。它打破了传统文学经典中的情感意蕴、矛盾冲突、价值取向,对于经典重读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一、改写矛盾冲突:淡化忠奸善恶
众所周知,赵氏孤儿的故事在以元杂剧为代表的传统文学中,矛盾冲突在于赵氏与屠岸贾之间的血海深仇,他们之间是正义与邪恶的对立和斗争。围绕着托孤、救孤、抚孤的故事线索,赵氏一方如赵盾、程婴、公孙杵臼、韩厥、提弥明、灵辄等舍生取义,视死如归,忍辱负重,铁骨铮铮,是正义的典型代表;屠岸贾为个人私欲,残害忠良,杀害无辜,祸国殃民,是奸佞的典型代表。赵氏复仇是为正义讨一个说法,为众生求一个光明,是世俗意义上“正义战胜邪恶”“公道自在人心”的胜利。这既符合传统中国的审美价值,也符合中国人的文化情感,具有中国悲剧的典型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讲,《赵氏孤儿》这部剧体现了在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下道德伦理图解政治的典型特点,并且也承载了传统文化中民众对于忠奸善恶的基本评价。
将复杂问题二元对立,将人性问题道德伦理化,以善恶、正邪为评价标准,这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古代作家设置戏剧冲突、解决戏剧矛盾的常见模式。但在今天的视觉文化背景下,观众对于此段历史有着丰富的视觉经验,对于人物、故事的评价也不再标准统一化、单一化、唯一化。因此,不管是话剧的改编还是电影的改编,都力求在经典改编的基础上能够传达时代的思考,并在今天的文化视野下对经典作出新的评价。由此,我们看到《赵氏孤儿》最根本的改变在于矛盾冲突的设置,它已不再是单纯的忠奸善恶的强烈冲突,而是有着复杂的政治因素。
林兆华版本的编剧金海曙在论述这一冲突设置时说: “旧时代的轰轰烈烈、复仇屠戮均有其内在合理性及英雄主义光彩……”[3]在这一版本中,屠岸贾灭赵氏,事出有因。20年前赵氏曾逼死屠妻、逼走屠岸贾,而赵盾三朝元老,功高盖主,难以驾驭。因此,赵氏的覆灭是因为皇权对能臣的猜忌,屠岸贾不过是皇帝杀臣的工具,乃至平衡各方力量的新势力。而16年后赵氏的复仇,不过是屠岸贾也成气候,朝中各方势力的再次洗牌。在田沁鑫话剧版本中,赵氏的覆灭是因为庄姬的淫荡,为泄私愤,诬告赵氏谋反,屠岸贾借机屠杀。在陈氏电影版的《赵氏孤儿》中,赵盾和屠岸贾同朝为官,彼此之间有着明显的政治权力、地位高低的较量,你死我活、成王败寇残酷的权利斗争,忠奸善恶并不是矛盾冲突的唯一。在观影者的体验中,无论是赵盾父子还是屠岸贾,都是权力游戏的参与者,今天是赵盾一家被杀,明天也许就是屠岸贾满门尽戮,杀人是这场游戏的规则,被杀是这场游戏所应付出的筹码,并无任何道德优势可言。
显然,《赵氏孤儿》的改编版本在矛盾冲突的设置上,已不单是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更多地带有现代文化的思考。元杂剧《赵氏孤儿》的经典在于它真实地代表了当时的民心所向及价值取向,但对于今天的观众来说,重新审视这段远去的历史,超越封建伦理对忠奸的评价,政治斗争中本就无所谓忠奸、善恶,只不过是利益和权力的再分配与平衡。因此,看待这段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的往事时,在今天的编剧者手里,庄姬可以是识大体有勇气的母亲,也可以是荒淫无知的妖孽;屠岸贾可以在夺权之后成为治国能臣,也可以在抚孤过程中成为一个慈父。这样的设置根本原因就在于文化背景的差异。我国文化现代化的过程必然伴随着传统文化日益退出历史舞台,尤其是在强大的视觉文化的冲击下,各种文化思潮、异质文化越来越影响人们的生活,改变我们的文化认知。处于另一种评价体系中,古代经典中所谓的忠臣良将、士为知己者死都失去了存在的文化土壤。为满足今天的视觉文化的需求,也满足视觉受众的需求,从现代文化的角度重写经典也成了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赵氏孤儿》如此,《西游记》如此,更多的文学经典改编都如此。
对于叙事文学来说,矛盾冲突是戏剧性最高、最集中、最尖锐的形式,是情节最基本的单元。它的设置会直接影响故事情节发展、人物关系和主题意义。因此,《赵氏孤儿》的现代改编因冲突设置的变化,在人物形象和主题意义上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二、丰富人物形象:人性角度解构
一部戏剧能否成功,要看它的冲突,而能否经典永垂,则要看它的人物。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提出了扁平人物的理论,认为在17世纪的戏剧中存在着类型人物或者叫漫画人物,他们出现在戏剧里,只是为了表现一个简单的意志或特征,甚至就是为了某一个固定念头而生活在种种的矛盾冲突之中。 作家在创作这种人物时,赋予他们鲜明的固定的性格特征,并成为他们的标签贯彻全剧始终。这种人物具有高度典型化的特点,并使观者过目不忘,由此及彼,联想起这一类人。元杂剧版《赵氏孤儿》中的人物就具有这样的典型特征、符号化特点。程婴忍辱负重、公孙杵臼老成持重、提弥明英武忠诚、韩厥明辨是非,他们执着而纯粹,生动地诠释了仁、忠、义的伦理道德要求。屠岸贾则阴险狡诈、残忍暴虐,是人人恨之的伤天害理、残害忠良的典型人物。在这部剧里,他们之间的斗争彰显了传统伦理的道德力量,给观者以悲剧的精神洗礼。几百年来,他们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的典型人物。
重写经典是需要勇气的,也是需要智慧的。在现代改编中,这些人物形象在保留原有性格特征的基础上,创作者还赋予了他们一些时代的理解,进而重构。纵观《赵氏孤儿》各种版本的现代改编,人物形象更加丰富饱满,甚至在原著中一略而过的庄姬和程婴妻在话剧版和电影版中都从幕后走向前台。在这些被改写的丰富形象中,电影版中的屠岸贾、话剧版中的赵孤是比较典型和有价值的。
(一)屠岸贾形象更加多面化、复杂化
电影版本使屠岸贾的形象更加复杂和人性化。他不再是一个千夫所指的奸臣,残害忠良的刽子手,在观者心中,他甚至成了一个悲剧的英雄。电影前半段对赵盾与屠岸贾之间的矛盾斗争进行了铺陈。有网络评论说,屠岸贾的“悲剧色彩并不比程婴逊色,高层斗争波谲云诡,稍不注意就身败名裂,晋王的轻慢挑衅和赵家的羞辱迫使他不得不做出这样的选择。赵家之所以遭受屠戮,并非因为宅心仁厚,而是因为过于轻敌傲慢,如再假以时日,遭受灭门惨祸的可能就是屠岸贾了。屠岸贾的悲剧根源就在于为了自保,而不得不先做恶人,却又偏偏赵氏孤儿命不该绝,最终还是只得端起这杯陈年苦酒一饮而尽”[4]。尤其是电影后半段,孤儿成长的过程中,屠岸贾是培养孤儿各种生存能力的严父,他将孤儿带入一个自由、丰富的世界,培养他的文才武略、勇气胆魄。在某种程度上,因为无子,孤儿几乎成为他年轻的记忆和未来荣光的继承。如果说阴险暴戾、睚眦必报是屠岸贾性格中的一面,那么,舐犊之情的慈爱、世事洞明的睿智就是他生命的另一种状态。这两者在电影中看似矛盾,却统一地展现了人性的复杂。在矛盾冲突的铺垫中,在演员个人魅力的演绎下,有意无意地化解了民众集体无意识对他的恨,而与他达成了共鸣和理解。虽然陈凯歌一直说他并没有改编什么,但是屠岸贾的形象却被成功解构,获得了现代人的理解。在今天私欲横流的文化背景下,在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人性认识中,屠岸贾超越了传统的道德评价而成为一个真实的、充满了人性意味的悲剧人物。
(二)孤儿形象突出命运抉择之痛
孤儿在原著中是个被忽略的人,公孙杵臼们将死亡的接力棒义无反顾地接力下去,程婴16年的忍辱偷生,只为换来孤儿的生和复仇,如此方能为死去的人正名,死和生才都有价值。因此,孤儿不需要思考,不能犹豫,复仇是他命运的唯一选择。但是,出于对现代人性的理解和把握,不管是电影版本还是话剧版本,孤儿的成长过程、命运选择之痛被浓墨重彩地加以渲染。
田沁鑫的话剧版本和陈氏电影版本都添加了孤儿的成长过程,程婴和屠岸贾都给了孤儿父爱,尤其是在田版话剧中,孤儿深受屠岸贾的影响,生活方式已与当时的贵族子弟无疑,追求安逸和享受。当身世被揭开,赵孤对于复仇茫然并疑惑。认为“养父程婴那一辈的血雨腥风、恩恩怨怨,已经成为一个遥远陌生的故事”,他“尤其不能认同自己是一个复仇的使者”,认为“所谓的身世只不过是命运强加给他的一个多余的东西。他不能接受这个历史包袱”[3]。他痛苦地呐喊:“血光穿越苍穹,刺灼我的双眼。不敢看父亲的伤口,不敢望义父的目光,我迷路了,父亲,义父……我该朝哪个方向走……”[5]163在这里,孤儿选择的两难与金庸小说中的杨康、萧峰有了异曲同工之妙。父仇和养恩交织在一起,民族大义和人生情感纠缠在一起,伦理选择和人性复杂缠绕在一起,何去何从,成为孤儿的命运选择之痛。最终,田版话剧在痛苦的呐喊中闭幕,杀与不杀成为一个悬念。而陈凯歌华丽地铺陈了前半段,但在孤儿复仇这个问题上却陷入了选择困境。站在人性情感的角度,赵孤复仇失去合理性;站在道德和审美的角度,不复仇又不符合观众的期待,打破了悲剧审美的情感意蕴。最后,只好以莫名其妙的一剑草草收场。
中国传统伦理认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有道德感、有羞耻心。杂剧版围绕道德论述了人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肯定和提倡“为他”的道德取向,视舍生取义为道德的最高境界。因此,赵孤的血腥复仇必然是对善有善报的程婴们的一种报答和价值肯定。而现代人性则超越了传统道德,并拥有更加广泛和丰富的内涵:肯定个人生命存在的价值,提倡对生命的关爱与珍惜,并强调对个人尊严与权利的尊重。孤儿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并不能因为历史使命而放弃个人人生的选择,如果仅作为复仇的工具也是对他生命价值的不尊重。但是,人性论是个复杂的体系,不光有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尊重,更有人性的良知和基本的道德底线。如果孤儿的痛苦可以理解,那么孤儿认为“不管有多少人命,他跟我也没有关系”就显得无情和冷漠。在中国观众的眼中,这泯灭了良知,也是对那些为他而牺牲的人的极大的不尊重。因此有研究者称他为“软体孤儿”,认为“当代人的精神萎缩状态就折射在这出戏中”[6]。所以,话剧版的“不杀”与电影版的“巧合杀”都没有足够的说服力,引起了人们的争议。
所有的艺术创作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我们自身:表达人的情感、描写人的处境、思考人的存在、升华人的精神。一方面,在这一时代主旋律的影响下,艺术创作围绕人的发现,不断丰富创作的内容。另一方面,文学作品要研究、刻画人的情感,更要研究人建立在普遍情感之上的特殊情感方式。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和情感走向,人物的身份和性格决定了他的行为和语言。作家对人物的塑造,不能主观臆断。只有建立在对笔下的人物充分尊重、理解的基础上,站在人物的立场、处境来想问题、做事情,才能把人物写好。在今天视觉文化的背景下,原剧中的每一个人如果剔除他们身上的标签,还原他们客观的生活逻辑,想必这其中也肯定会有丰富的情感冲突和复杂的人性选择。话剧版和电影版的改编就是在试图进行这样一种还原。这些人物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人物关系中扮演不同的角色,他们除了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性格轴心之外,还有着丰富多样的性格变化,角色的多面性和人性的复杂性处于动态的变化中。因此,我们会发现,不管是话剧版本还是电影版本,《赵氏孤儿》中每一个出场人物都有更为丰富的多样性,他们都不再是伦理评价中的那一类,而成为活生生的一个人。因此,从人性化表现的角度上显然改编是具有一定价值性的。
三、改变故事主题: 多元化思考
对于一部叙事文学作品来说,矛盾冲突与人物形象发生了变化,故事的主题必然也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原著通过忠义之士为存赵孤舍生取义、前赴后继的故事,弘扬忠义精神,而改编之后的《赵氏孤儿》在复仇故事的主题上更加地多元化、多层次化,并赋予它相应的时代意义。
对于话剧来说,孤儿放弃复仇彻底颠覆了故事的根本走向,这也是观者热议的焦点。作为经典改编,故事的基本叙事过程与原剧无异,杀赵、托孤、救孤、抚孤,但矛盾冲突的改变,使救孤、抚孤的英雄行为不具有道德意义上的优势,牺牲不过是出于私谊,而这些在赵孤茫然的“与我有什么关系”的疑问前变得无足轻重。显然这是对传统文化中的愚忠进行了无情的嘲讽,两代人在生死取舍面前表现出的价值观冲突成为话剧版主题的重点。林兆华说:“在该剧主题的呈现上,也可以理解为新旧两个时代价值观念变迁所带来的无可解释的困惑。”[3]田版话剧《赵氏孤儿》则从人生体验与情感冲突出发,表现孤儿如何从困境和焦虑中成长起来,当孤儿放弃复仇也就意味着放弃他的工具使命,进一步获得个体生命存在的意义和尊严,进而表现出新一代的人在多元文化中成长与独立的需求。
对于这样一个宣扬传统道德观念的古典名剧,电影更多地是从现代人性的角度出发进行了重新演绎。传统道德中的忠与义意味着因等级、亲疏等伦理关系而确定的无条件的服从与牺牲,而现代文化观念则认为人人平等,每个生命都是有价值并值得尊重的,人的价值和欲望被不断释放。基于此,在电影中,程婴救孤不再是意志坚定的“为他”的主动选择,而是迫不得己的人生偶遇;不再是坚决和无畏的牺牲,而是“为己”无奈与不甘的随波逐流。程婴在不自觉、不主动的情况下完成了彪炳史册的义举。他不是顶天立地的英雄,而是在命运间挣扎浮沉的小人物。陈凯歌充分肯定人性中的懦弱、摇摆、自利等并不那么英雄和高尚的品质,认为舍生取义也只不过是小人物在无意间完成的壮举,而历史也恰恰就是这些懦弱、摇摆、自利却不时闪光的“人”的历史。也因此,电影少了英雄的壮烈,多了凡人的无奈;少了选择的纯粹,多了取舍的算计。电影的主题在复仇之外,生生地多出了许多命运的感慨。不管是程婴,还是赵孤,甚至是屠岸贾的灭赵,都多了些无奈的生死抉择。
当然,无论是哪位改编者,改写的目的都不是为了简单地还原历史,而是要对历史进行重新思考,对主要人物的行为重新定位,以此传达出不同时期在艺术创作规范、审美情趣、价值导向等方面的差异,从中也体现出艺术上的大胆创新。
而今,视觉文化大行其道,各种信息与资源铺天盖地、包罗万相,精英文化不再具有主流性和引导性,大众文化中的世俗性、娱乐性、消费性被不断扩大。利益的考量、人心的算计、取舍的两难是大众生存的常态,当“扶不扶”“救人该不该要钱”等都成为社会争议的话题时,传统社会价值观中的伦理与道德早就变得不堪一击。因此,即便是经典,《赵氏孤儿》荡气回肠的悲剧虽引人唏嘘,但大众对单一、平面的道德英雄心存疑虑,他们嘲讽大于欣赏。毕竟现代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使大众具有了对传统批判的能力和勇气。但是,社会发展中所暴露出的种种问题又使人们感到困惑与无助。新时期以来,不断兴起的国学热和新儒学,使人们意识到传统文化中的精髓也是疗救现实的一剂良药。因此,大众又渴望从传统文化中寻求解决问题的思想武器。具体到赵氏孤儿这一特定故事,表现为既“不相信程婴能用亲生儿子的生命换取‘诚信’的真实性,却又纠结于当今社会缺少‘诚信’”[7]。既不认同赵孤成为复仇的工具,又希望赵孤手刃仇敌。这样的矛盾,既存在于民众心理中,在改编文本中也就成为不尽人意的核心所在。林氏话剧表现出的绝望、田氏话剧表现出的回避、陈氏电影表现出的犹疑其实都是时代文化的折射,也是精英知识分子对时代文化的困惑、担忧和矛盾。不管是林兆华、田沁鑫还是陈凯歌,都已经感觉到当今人性与道德所构成的悖反,他们都想二者兼顾,但又不希望在任何一个方向走得太远,担心顾此失彼。患得患失、瞻前顾后的结果,便是拆解了传统经典之后却没有建构起堪称现代经典的艺术范型。
综上所述,《赵氏孤儿》作为一本戏剧经典在民间广泛传承,它的经久不衰与整个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中的价值观、道德观、审美观紧密相连。但随着视觉文化发展的需要,经典通俗化是必然的时代需求。当代的艺术家们在自身文化思考的基础上,结合当代人的心理特征,对原主题进行了全新的、大胆的处理,赋予了这个历史故事新的时代意义。虽然这样的思考和创作尚不成熟,存在一定的瑕疵,但我们相信,伴随着改编而引发的时代思考和讨论必然会对文化的整合、创新产生一定的作用。而文学的改编也绝不会止步于此,在民族精神的重塑和传承上,我们也期待文学经典能有新的作为和力量。
参考文献:
[1] 姚文放.媒介变化与视觉文化的崛起[J].文艺争鸣,2003(9):14.
[2] 周宪.视觉文化语境中的电影[J].中国电影,2001 (2):33-39.
[3] 金海曙.赵氏孤儿[J].剧本,2003(9):2-33 .
[4] 白胖饺子.《赵氏孤儿》: 已无是非对错然我欲罢不能[EB/OL].[ 2010-12-09]. http://ent.sina.com.cn/r/i/2010-12-09/15203172474.shtml.
[5] 田沁鑫.田沁鑫的戏剧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6] 华岩.2003中国话剧舞台纵论会议综述[J].剧本,2004(3):46-49.
[7] 解玺璋.《赵氏孤儿》: 道德与人性的二律悖反[N]. 中国青年报,2010-12-07( 9).
(责任编辑:王菊芹)
收稿日期:2016-01-01
基金项目:2014年度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视觉文化语境下影视媒介对文学形象的建构”(2014-qn-465)
作者简介:杨华轲(1979—),女,河南内乡人,华北水利水电大学人文艺术教育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44(2016)02—0130—05
Modern Reconstruction of Literary Classics in the Context of Visual Culture— Taking the Adaption oftheOrphanofZhaoas an Example
YANG Huake
(Humanities and Arts Education Center,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Water Resources and Electric Power, Zhengzhou 450046, China)
Abstract:In the context of visual culture, a large number of literary classics are transformed into films and TV series or other visual art styles. Not only with the feature of classical inheritance and modernity reconstruction, this kind of adaptation inevitably has the popularization tendency simultaneously. In the new century, the Orphan of Zhao has been adapted for stage play, film and TV series, drama etc. The adaptation of the play and film versions is typical and innovative. Conflicts are rewritten to dilute the good and evil. Characters are more humanized and complicated. The theme of the story has also been changed to inspire people to think diversely. The modern reconstruction of literary classics is not only the result of the law of literary creation, but also the profound reflection of the culture of the age.
Key words:visual culture; the Orphan of Zhao; modern reconstruction; human na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