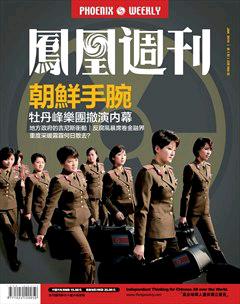缺少色彩的朝鲜二线城市
王强+吴如加
金正恩上台之后,很多从平壤回来的人告诉我,朝鲜出现了些许开放迹象。比如,现在可以携带手机等电子设备入境了,并且能走出羊角岛酒店所在的那座孤岛随意观光,甚至能用手机拍照了。
然而,这样的宽松待遇,我在2015年10月末的朝鲜之行中并未感受到。我选择的咸镜北道与中国接壤,从入境时起,接待方的警惕之心便显露无遗——入境检查时在机器扫描后,朝鲜海关人员还盘查了所有随身物品,甚至连衣角都细细捏过一遍。接着我被明确告知,绝对不允许拍摄除规定景点之外的地方。所有拍下的照片需经朝方人员检查,并需要删掉他们认为不合适的照片。
回想起五年前去平壤时,因为盯防不严,还是偷拍到不少朝鲜普通民众及军人真实劳动的场景,并幸运地将影像带出境。这次的朝鲜之旅在被“严格”审查后,相机里只剩下空无一人的景点、整洁的广场和高耸的领袖铜像。
或许政治中心的“改革新风”还没吹到偏远的咸镜北道,这里与五年前的那个朝鲜相比,没有丝毫变化,仍是封闭落后、没有色彩的城市与乡村。
罕见的机动车
此行中的会宁、清津、镜城、明川四地均位于咸镜北道,其中会宁与对岸的吉林省龙井市隔江相望,是我们入朝的第一站。从会宁到清津,从清津到镜城,再由镜城前往明川,四天的行程中,感觉到了诡异的寂寥。
大多数时间,我们的旅游大巴是路上唯一的机动车。每当经过盘山公路的弯道时,司机执著的鸣笛总显得多此一举——因为从没有其他车辆与我们相向而行。我猜测,鸣笛或许是为了警示行人,而不是为了会车需要。
作为外国人,要适应的第一件事是无止境的颠簸。这里的基建设施极差,各个城市之间由砂石路连接,但由于公路缺乏必要养护,以至于从会宁到清津短短91公里的路程耗费了两个多小时。
公共交通的缺位,导致普通朝鲜民众出行的方式非常原始。无论是国道或盘山公路,沿途随处可见骑着自行车,或背着沉重包袱的当地人艰难行路。
相比于中国东北人迹罕至的乡村公路,朝鲜的城际公路反倒显得热闹。清津与镜城之间的国道上,几乎全是骑车和步行的朝鲜人,想找到一个无人之处停车颇为不易。公路两旁是贫瘠的农田,水稻田和玉米地里没有任何农业机械,无论是耕种、收割还是运输全部由人力完成,连畜力车都寥寥无几。
在朝鲜,那些承担有限农业运输任务的牛车和手推车处境尴尬。由于橡胶的缺乏,它们往往无法配备充气轮胎。我曾无数次地将目光停留在那些不幸的轮子上,通常只有光秃秃的轮毂和钢圈,至多在外面贴着薄薄一层胶皮。
城市中的公共交通同样缺乏,这与如今的平壤截然不同。作为咸镜北道首府的清津,虽说是朝鲜的第三大城市,中俄两国在此分别设有领事馆,但正常运行的公交车辆同样罕见。清津市区内双向四车道的主干道鲜有车辆经过,没有任何交通指示灯——因为根本不需要,人们出行依赖自行车或步行。

清津是朝鲜国内除平壤外唯一有轻轨的城市,“轻轨”指的是老式有轨电车。清津人颇以此为傲,导游特地介绍,这是清津市的标志之一,欧洲来的游客会乘坐有轨电车游览市区。很可惜,我在行程中并未遇见有轨电车,只有老旧的铁轨和沿街的电缆证明着它的存在。
油料的短缺在这个国家显而易见。朝鲜路上为数不多的“机动车”中,不少是在他国已成历史的木炭汽车。我对其运作的原理不甚明了,只见其后箱的一端装着一个直径50厘米左右的大桶,应是特制的炉子,上面的烟囱一直吐着浓浓的炭灰。这种古老的机动车除了需要司机之外,还得有另一人在旁不时加炭、点火,若动力不足,还需其卖力鼓风。
从会宁到清津的路上,我们的大巴停在古茂山矿泉水厂旁休整。我注意到路边停着一辆抛锚的木炭汽车,车后箱的炉子里喷出滚滚黑烟,遮天蔽日。或许是害怕引来导游的不快,同行的朝鲜族朋友劝我“最好别盯着看”。
精挑细选的窗口
在朝鲜地图上,咸镜北道位于东北方位,以图们江为界,与中、俄隔江相望,东临日本海,被称为关北地方。迄今为止,朝鲜的三次核试验均在此进行。
如果说平壤是朝鲜的政治中心,距其最远的咸镜北道则是名副其实的苦寒之地。李氏王朝时期,触怒君王的臣子往往被流放至此,类似于沙俄的西伯利亚和清朝的宁古塔。古老的流放传统延续至今,据韩国专门报道朝鲜新闻的DailyNK网站披露,朝鲜人民军前总参谋长李英浩在2012年被解除一切职务后,就软禁在咸镜北道的一所将军疗养院里。
由于环境恶劣,咸镜北道的人多是金字塔底的庶民阶层,最无权力,饱受支配。直到现在,出生在咸镜北道的朝鲜人仍被认为是民族中意志最坚者。
美国《洛杉矶时报》记者芭芭拉·德米克在《我们最幸福》一书中曾记载,上世纪90年代的大饥荒中,咸镜北道比朝鲜其他地区更早地断绝了粮食供应。韩国民主劳动党对2003年抵达韩国的1281名朝鲜人的调查显示,在朝鲜12个道和直辖市中,来自咸镜北道的“脱北者”占了71.9%。
20世纪初,咸镜北道人烟稀少,日本人的到来改变了一切。日据时期,大型炼钢厂在首府清津港兴建,直至金氏主政后,它仍是朝鲜境内最大的工厂。日本人还开发了清津南部的罗南地区,那里棋盘式的街道与大型现代建筑多是日据时期的遗产。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清津市人口持续增长,在上世纪70年代达到90万,成为朝鲜第二大城市;但在经历了90年代的“苦难行军”之后,这座城市的人口据信已下降到50万,排名被咸兴超过。

时光在清津倒流,日本人遗留下的炼钢厂近20年来处于彻底停工状态。高耸的烟囱大多沉寂了,使得一度是朝鲜污染最严重的清津,伴随着荒凉,再次回归到天朗气清的田园时代。当我下车时,这里的空气好得完全不像是工业城市。当然,对清津而言这绝非幸运之事。芭芭拉在书中提到,饥荒时期工厂的管理者曾组织工人拆卸机器,然后运到边境贩售,用卖掉设备得到的现金为工人购买食物。这或许可以间接地说明清津是一座富有进取心的城市。
据信早在2005年,清津的水南市场就成为朝鲜最大的市场,商品种类之丰富远超过分拘谨的平壤;2008年,商贩甚至敢于公开抗议政府对市场的限制性政策,以至于这座城市一度被比作旧日的美国西部。

只可惜,市场绝不可能被列入我们的行程之中,我在车窗内看到的,只是一座黯淡之城。
咸镜北道的城市,无论会宁或者清津,都分享着同样灰色的气氛与景致——空旷的街道、单调的建筑、衣着黯旧的行人。城市里唯一鲜艳的色彩来自歌颂领袖的标语,数量之多,足以让不谙韩语的人能分辨出歌颂的对象究竟是金家的哪一位领袖。
相比起沿途破旧简陋的民居,会宁口岸可算得上富丽堂皇。其海关室内装修考究,配有大屏幕的液晶电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卫生间,堪称豪华,质地精良的卫生洁具不亚于国内大城市的酒店。即便是专门招待外宾的平壤羊角岛特级酒店,其设施在会宁口岸面前也只能相形见绌。此后我在朝鲜所见的卫生间都十分简陋,甚至没有自动冲水的马桶。这不是马桶的罪过,而是没有持续的自来水供应。
在前往明川郡民俗村的路上,车窗外掠过一座村庄,那里的房屋低矮、简陋,似乎随时有倒塌的危险,与美丽的海滨格格不入。但当我们的车跨过一座小桥到达民俗村时,俨然来到另一个世界。二三十栋朝鲜民居错落有致、建筑精良、宽敞明亮,每座民居就像是海滨别墅。这是朝鲜官方乐于向外界展示的幸福朝鲜,那个玻璃橱窗里的乌托邦。每个家庭都是一座旅馆,他们的生活也是他们的工作——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展现朝鲜民众的幸福生活。
驶过那座小桥时,我们被告知,这里是民俗村的边界,绝对不允许跨过这座桥。接着导游专门提醒,此前看到的那座破落村庄名为“狗村”,因为村里的狗特别多。似乎借机暗示我们不要试图跨越地界,走近那个村庄。
居住在这里的人显然被精心挑选过,无论男女都衣着入时,营养良好。青少年也和国内普通中学生别无二致。或许对于一桥之隔的“狗村”里的人,这里便像月亮一样遥不可及。
在这样一个封闭的社区,我们获得了唯一自由活动的机会。既能随意转转,也可以去村前的海滩散步。不过导游再次提醒我,拍摄街道可以,但不允许拍人,即使是村子里的人。
然而,即便在这样一个窗口,依旧免不了停电和断水。在咸镜北道,停电是稀松平常的事,接待外国人的旅馆也无法幸免。在民俗村,每家必备一种节能型LED灯和手电筒,夜间城市路灯照明根本不存在,许多公共场所也没有照明系统。我们抵达镜城的温泉澡堂时,天色渐晚,澡堂内一片漆黑。我在墙上摸索了许久电源开关,一抬头,发现天花板上空空如也——根本就没有灯泡。而由于没有持续的自来水供应,无论是旅馆或民俗村,人们都习惯用水槽或水桶储水。
我住在民俗村的一户人家中。一日起来,这家人正用影碟机播放韩语字幕的《功夫熊猫》,两位大人和孩子看得津津有味,不时哈哈大笑。意外的是,他们并不知道这部动画片来自美国,而很自然地认为是“中国制造”。

不变的领袖崇拜
如果说,平壤与平壤之外的朝鲜有什么地方完全一致,那就是对领袖的崇拜与敬仰。当我们通过图们江上那座公路桥、踏上朝鲜土地的那一刻,便无法回避领袖们的印记。
在会宁口岸的院子里,竖立着一座画有金正淑英雄形象的纪念碑,色彩鲜艳,画工精美。会宁的特殊之处也在于此——这里是朝鲜“国母”金正淑的故乡。作为金正日的生母,她的形象和对她的赞颂处处可见。
和平壤金日成万景台故居一样,会宁的金正淑故居也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虽然那只是间草屋,却一尘不染。我刚踏上门口石阶想看看房内的情形,却被告知石阶是不允许踩踏的。一切细节都营造出圣地的氛围,所有和领袖及其家庭相关的事物都显得无比神圣。故居后面的山上伫立着巨大的标语:“向抗日女英雄金正淑同志学习!”
每路过一个稍具规模的城镇,都能看见高高伫立的永生塔,上面刻着“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永远和我们在一起”。导游说,这是金正日将军下令修建的。为了表达对领袖的热爱,这样的永生塔遍布朝鲜全境,每年金日成的祭日与生日,朝鲜民众都要向永生塔献花。
同样遍布的还有领袖的铜像。根据最常被引用的一份数据显示,朝鲜境内的领袖铜像共计有34000余座,它们耸立在每个城镇的广场。活着时,他们权柄独操,死去后,他们就成了这个国家的神灵。
清津市中心的广场上,同样伫立着金日成和金正日父子的巨大铜像。铜像建于2014年,目测连带底座有十几米高。这两座铜像是青岩幼儿园之外,我们在这座城市参观的唯一景点。作为游客,下车之后被告知必须向领袖的铜像献花,每束花要价20元人民币。
领袖们慈祥的目光下,是空荡的街道和老旧的建筑。当地青年男女正在铜像前举行婚礼仪式,他们穿上最别致的衣服,在高大的铜像前拍照纪念。

如今掌权的年轻领袖金正恩,虽不似祖父与父亲那样拥有自己的铜像,却也在街头巷尾的标语中被歌颂着。许多巨大的横幅被挂在建筑物顶端或刷在外墙上,上面写着:“为了敬爱的最高司令官金正恩同志豁出性命战斗吧!”
我们一行共有六人,随行的朝方人员却多达三位,一位司机、一位专职导游,还有一位被称为服务监督员。朝鲜导游对游客的监视之严格,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但五年前去平壤时,除了导游之外并没有专事盯梢的监督员。当年那位导游曾经骄傲地告诉我,朝鲜是个自由开放的国家,早就取消了盯梢制度。
导游和监督员的首要职责,是防止我们走到不该走的地方,看到不该看的东西,拍下不该拍的照片,除此之外才是对景点的介绍。即便一路上,窗外的朝鲜人多是衣着灰黄,面有菜色。在导游的口中,不断创造高度和体积纪录的铜像和纪念碑成为朝鲜渴望成为强盛国家的注脚。他不允许我拍摄窗外那些低矮的房屋,却指着山上赞颂金正淑事迹的巨大标语自豪地说:“你知道吗,那些字每个都有三层楼那么高!”
平心而论,这位导游是一位真挚而热情的年轻人,面庞棱角分明,显得生气勃勃。攀谈中得知他受过良好的教育,与沿途赶路的黑瘦朝鲜人显然属于不同阶层。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对中国文化亦多有涉猎,聊起三国人物如数家珍,说话时总爱在句末加上一句“难道不是吗”,以此渴望获得积极回应。一路上他对我多有关照,服务亦十分敬业,若以导游的职业标准去考量,实在不应受到任何诟病。尽管他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删掉了相机中那些在他看来有损祖国形象的照片。

在会宁,我们的大巴路过一处名为“饮食一条街”的地方。据导游介绍,在领袖的亲自关怀下,新建的饮食一条街别具特色,汇聚了冷饮店、杂碎汤馆、兔肉专馆、豆腐脑馆、玉米食品专馆、炸酱面馆等各种餐馆。
一眼望去,街道干净整洁,两侧亦不乏精美的建筑,唯独缺少行人。车窗内的朝鲜年轻人接着说:“现在经济发展了,我们才能尽情地享受生活,难道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