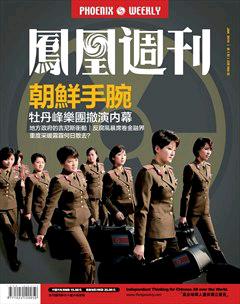中日恶性互动的前车之鉴
萧功秦
如何处理中日关系,是百年来中国绕不开的话题,也是百年来数代中国人面临的大难题。今日,中日两国在各个领域的较量角力,出现了诸多恶性互动,只有从历史视野考察,才有可能对这一问题形成比较清晰的认识。
中国人对日本的态度具有复杂的两重性。一方面,一百多年来,日本发动了两次对华战争,两次中断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给中国人留下了深重的苦难记忆。虽然战争结束已经70年,但中国人对中日战争的痛苦记忆仍然存在,对日本人有一种长期的不信任感,有时甚至是过度的敏感,宛如“惊弓之鸟”。这是一种出于生存本能的、应激性的民族主义反应,已经扎根为民族生存经验中的潜意识。这种应激性民族主义,只有经历过深重战争灾难的民族,才会特别强烈而持久。一般情况下,这种潜意识处于隐性状态,但一旦有特别的刺激,就会被重新激活,它需要漫长的岁月才能逐渐消解。
另一方面,中国人又受惠于日本现代化的成果,中国近百年来的改革家与革命家都得到日本人的支持与赞助。中国人对日本在现代化方面的成就由衷钦佩,比起英美等国,日本作为东方民族,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更值得中国借鉴。长期以来,中国人对日本是充满兴趣的,日益增多的旅日游客,对日本国民的教育水准与文明素质之高,都留下深刻的印象。正因为中日关系的复杂性,在不同的情景与环境下,中日关系就有可能出现不同的发展趋势。
中日关系的可能趋势
多年来,我们的历史教育有诸多值得反思之处,比如,对日本的介绍沿袭了过去的很多看法,造成国人对现代日本发生的变化知之甚少,甚至把过去的刻板印象继承了下来。以前,我们只泛泛知道日本教科书否认南京大屠杀,却很少有人知道,这样的教科书在日本各中学的采用率,只占日本全部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千分之几,而现行的绝大部分教科书都并不否认南京大屠杀。这一情况,甚至大多数专业的历史研究者都未必了然,更不用说普通中国人。
正如前文所说,一方面,我们对日本长期不了解,对它的怀疑和不信任感潜伏于心;另一方面,又对其现代化建设成果很是钦佩,这种二元态度就造成了中日关系完全有可能在不同的条件下向两种截然相反的方向发展:
一种方向是,随着两国交往加深,通过良性互动和相互了解,历史上形成的疑虑逐渐化解,双方在良性互动中走向和平友好的新时代——这是我们应该共同努力争取的。
另一种方向是,由于双方之间的不信任感,或者日本某些右翼人士主导的突发事件,把中国人心灵深处潜在的对日本的疑虑与不安全感重新激活,形成了应激性的紧张反应,中国的民族主义走向激进与亢奋。而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天生对外部环境有一种高度的不安全感,在这种不安全感的支配下,日本大众可能转而形成对右翼势力的支持。于是,日本民族主义与中国应激性民族主义之间,就会形成恶性的互动,如果矛盾不能化解,就有可能从双方的高度不信任走向冲突,甚至经由持续冲突走向战争。
这种双方的恶性互动趋势,在上世纪30年代就出现过。不幸的是,近年来这种可能性再次出现。中日关系将向何处去?当下正处于关键时刻。
近30年来发展回顾
为了寻求正确的解决之道,回顾一下中日关系的恶性互动趋势是如何发展起来的,是很有必要的。
改革开放初期,中日关系相对稳定,时任中共总书记的胡耀邦邀请3000名日本青年到华访问。日本青年受到中国方面的热情接待,许多人临别时还流下眼泪。当时日本与中国对彼此的观感都相对良好,从民意调查结果来看,双方对对方的好感率均高达80%以上。日本右翼是极少数,没有多少影响力。日本和平宪法的基础也很牢固。

90年代以后,虽然由于历史问题、教科书问题、日本首相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影响了中国人对日本人的看法,但随着中日经济与文化交往的不断加深,两国关系还是稳定地向良性发展。
在2005年到2012年中期,双方关系进入一个稳定的发展期。虽然安倍是日本右派,但2006年他作为日本首相访问的第一个国家就是中国,那次访问被称为“破冰之旅”;2007年时任中国总理的温家宝访问日本,被称为“融冰之旅”;此后,日本的新任首相福田在同年又对中国进行访问,被称之为“迎春之旅”。2008年的奥运会、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中日关系都表现得相对友好而平稳。虽然彼此有分歧,但都在可控范围内,中国民间街头自发的反日游行也受到中国政府的控制。
然而,风云突变,2012年下半年,日本右翼人士引发的钓鱼岛国有化事件,是双方关系从良性互动转向恶性互动的转折点。其实,右翼势力在日本的实际影响,远不如国人原先想象的那样大,它与日本和平主义的主流价值观相比,只是处于边缘状态。右翼人士的宣传车在东京市区呼啸而过,但并没有多少市民对它感兴趣。
七八年前,我去日本旅游也有过直接的感受。在参观靖国神社中的游就馆时,放映厅里,日本右翼人士拍摄的纪录片中,出现日本军队在南京入城时的镜头,偌大的剧院里,只出现几声稀疏无力的掌声,给人一种孤掌难鸣的感觉。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靖国神社外面的广场上,却是成千上万日本青年男女在纵情享受阳光。我当时就有强烈的感觉,日本右翼势力真是如同汪洋中的孤舟。
恶性互动如何形成
在日本,许多学者都指出,右翼势力在日本社会并没有多大影响力,然而,却在最近几年起到影响中日关系正常发展的强大作用。这是因为以石原慎太郎为代表的极端右翼势力的失落感与焦虑感,使他们终于找到了中日关系中的一个“软肋”,并且作出了超常发挥,从而改变了中日关系的走向。
石原利用其作为东京都知事的权力地位,提出了由东京收购钓鱼岛的计划。不幸的是,这又进一步引起了野田佳彦内阁错误的处理,野田从“土地权所有者”手中将钓鱼岛“国有化”。他似乎想用“政府购岛”这样的举动,让钓鱼岛继续荒废,从而减轻该问题对中国的敏感性。但是中国人却倾向于认为,两者是一种“唱双簧”的行为,侵犯了中国的民族利益。可以说,正是右翼人士石原慎太郎的一个意想不到的动作,引发了中日关系的“蝴蝶效应”。
日本右翼的极端态度,激发了中国人的强烈不安全感,沉重的不幸历史记忆由此而被重新激活,中国进入反应性民族主义的应激期。2012年,中国国内街头民族主义运动,在许多大中城市出现。这一应激性反应在网络上及部分中国人的行动中表现得相当激烈。有人提出“宁愿中国不长草,也要收回钓鱼岛”,反日游行抗议中砸日本车致使司机重伤等事件引起国内外的关注。一年多以后的2013年11月,中国政府宣布东海防空识别区,将钓鱼岛包括在内,中国政府对日本不得不表现出强硬的态度。
日本方面对中国反日游行中的某些过火行动的不满,对中国公布“东海防空识别区”的不满,再加上此前朝鲜导弹飞越日本领土等问题,让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出于不安全感与逆反心理,转向对右翼政策表示支持,右翼势力得到民粹支持而变本加厉。从历史上看,日本右翼一旦有了民粹基础,在与中国民族主义的互动过程中就会形成膨胀的势头。2014年2月,东京选举中极右翼大胜,从前一年的30万票上升到60万票。这一成果连他们自己也没有想到。
中国人觉得,右翼与民间力量的结合,是日本右翼势力进一步崛起的信号。中国反应性的民族主义也因此水涨船高。中国2015年9月进行抗战胜利日的大阅兵。日本方面对此作出回应,国会轻松顺利地通过了“新安保法”,意味着在法律层面正式解禁“集体自卫权”,这是自中曾根康弘担任首相以来的30多年间,历届日本首相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这样一种恶性互动已经在形成。
近年来,随着两国关系的紧张,有人说,“中国与日本之间,什么都不缺,就缺流血了。”一旦流血,百年来的旧仇新恨,不知要哪年哪月才能再消解。
在中国,有些“名嘴”不负责地说,中国可以“在半小时里把日本灭掉”;在日本,也有人说,他们的核废料也足以造两千枚核弹头。随着中日关系的紧张,这样的“硬硬互动”,使擦枪走火而引发战争的可能性仍然存在。这让人们不由得回忆起历史上双方互动的历史阴影。
两次惨痛的前车之鉴
从历史上看,中日双方的恶性互动是有前车之鉴的。重温这段历史,对两国人民都十分重要。
甲午战争后不久,中日曾出现过双方关系向好的局面,中国的变法人士与革命派都不断得到日本方面善意的支持,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取得胜利,客观上有利于中国东北避免成为俄国殖民地。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死伤达数十万人,仅战死就达10万人,耗费了20亿日元。由于各种原因,战后日本并没有取得中国的东北作为殖民地。1905年以后的十年里,中国向日本学习达到高潮。
然而,这样的良好关系,却由于少数日本右翼势力而发生逆转。1915年的日本右翼内阁向袁世凯政府秘密递交“二十一条”要求,逼迫中国同意日本方面提出的极为苛刻的条件,以此来逼迫中国对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损失作出“补偿”。当时连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也惊呼,日本直接把中国当作战败国来对待。中国作为弱国,不得不接受了其中大部分条款。从此以后,中国人对日本产生极大的警觉,抵制日货的反日民族主义浪潮越来越强大,“二十一条”也成为几代中国人无法挥去的痛楚与屈辱。此后上台的日本文官政府中的温和派,也曾为缓和这一局势作出各种努力,其中包括以优惠的西原贷款博得中国方面的好感,但两国之间的恶化过程不幸已经形成。
受“二十一条”的刺激,1928年的国民政府采取了强烈的民族主义“革命外交”政策作为回应,在自身国力尚不足的情况下,中国外长王正廷高调提出,要在短期内单方面地取消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得的各种东北权益(例如南满铁路24年的租借权),中国民间也出现对日本商人的过火行动。北伐军进入南京时,也有少数军人对日本侨民有杀害行为,这又引起日本民间的仇华心理。于是,日本民族主义的右翼势力、军国主义者与民族沙文主义者,得到了日本民众的支持而如虎添翼地嚣张起来。这一恶性互动趋势,是“九一八”事件的深层原因,此后,日本军国主义者不断得寸进尺,而中国民族主义则不断强化对抗,直至1937年第二次中日战争爆发。
可以说,在中国和日本已经有了两次恶性互动的经历后,我们有必要考虑内部一些结构性问题。这些结构性问题,就是双方的高度误解以及双方的高度不安全感。中国作为一个受害国,对日本是高度敏感的,而日本岛国的孤独状态,也使日本人的民族性格对外部世界具有高度敏感。日本右翼势力对中国发动的事件,激起了中国反应性民族主义,日本中间民众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反应,引起他们对右翼势力的进一步支持,从而使双方的恶性互动得以形成。
警惕“蝴蝶效应”
从长远来看,中日关系走向健康的“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是完全有希望的。要避免中日关系陷入恶性的互动,双方都应该努力,也需要两个民族共同发挥自己的智慧。
日本方面应该看到,要防止右翼人士通过挑战中国人的民族心理,来刺激中国的不安全感,从而激起应激性反应。中国对日本的高度敏感是历史上形成的,只有在比较漫长的时间里才会脱敏,在这一漫长过程中,极端右翼人士有可能利用中日关系上的“软肋”。虽然极右翼势力是少数,但这个边缘化的政治势力,却往往具有很大的活动能量,他们有可能借助日本人的岛国不安全感,成为“蝴蝶效应”的起点,而这种“蝴蝶效应”所产生的后果,却要由两国人民来共同承担,所以应该要警惕这种力量。
而中国人也应该看到,日本战后70年来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温和、理性的中产阶级已经成为社会主流。全球化使得日本可以通过国际经济贸易和高科技,满足本国各方面的需要,战争扩张主义已经失去了在民众中的影响力。日本是一个法治国家,日本人可以说是世界上对战争痛苦理解与体验最深的民族之一,日本民族性格的变化之大,恐怕只有13世纪的蒙古民族接受黄教后所发生的变化可以与之相比。
日本和平主义的力量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得多,这种和平主义是随着与中国人一起抵制日本极右翼保守势力而兴起的,如果两国人民在良性互动中加深理解,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可能性很小。当然,最根本的一点是,中国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不再像以前那样软弱可欺。我们不怕日本右翼分子兴风作浪,但也不必杯弓蛇影,有人说日本的军国主义正在复活,这样的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
不管怎么说,中国与日本就在一条船上,船上存放着汽油,有极少数人就是要让汽油着火。一旦着火,将成为船上所有人的共同灾难,在彼此相邻的船舱里生活的中国人与日本人更是首当其冲。我们要警惕这样的人,阻止这样的人破坏难得的幸福与安宁。正如无数历史所告诫的,如果我们不能从中获得警示,人类注定要重犯历史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