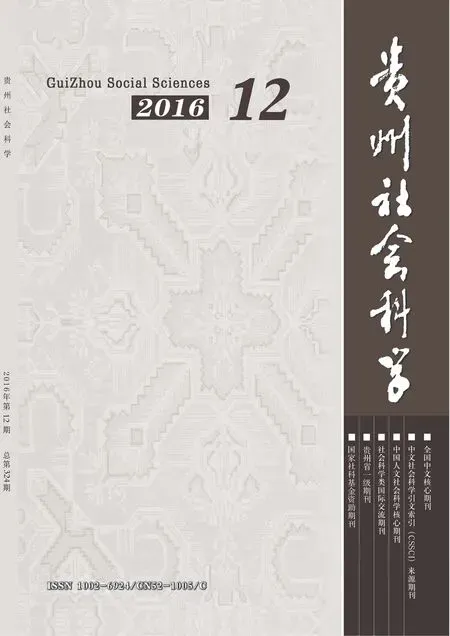卢卡奇《小说理论》哲学思想探析
李怀涛
(首都师范大学,北京 100089)
卢卡奇《小说理论》哲学思想探析
李怀涛*
(首都师范大学,北京 100089)
《小说理论》体现着卢卡奇早期的哲学思想及其发展变化,直接地对《历史与阶级意识》文本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小说理论》有着复杂的理论来源,卢卡奇从总体性视角说明古希腊社会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差异而造成的古代史诗与现代小说的对立,并且为自己构建的小说的类型学赋予了历史性因素。小说理论标志卢卡奇从新康德主义转向黑格尔主义,包含着他不久即转向马克思主义的端倪。
《小说理论》;总体性;小说形式与历史;小说类型学
卢卡奇的《小说理论》初稿写于1914-1915年,首次发表于1916年的《美学与一般艺术科学》杂志(马克斯·德索尔主编),1920年汇编成书在柏林出版。当时,卢卡奇在写《海德堡美学》时就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新史诗的吸引,这种新史诗力图描写现代大都市的内部世界;同时,黑格尔的总体性思想尤其是他对史诗的分析也对卢卡奇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匈牙利国内的社会矛盾以及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矛盾的尖锐化,世界大战中各国彼此的战争屠杀,使卢卡奇不断陷入绝望,《小说理论》就是这个危机时代的普遍弥漫的绝望情绪的集中表达。近年,西方左派正在重新发掘卢卡奇的思想资源,对于研究较少的卢卡奇早期思想应该引起更多的关注。
一
卢卡奇优越的家庭条件使他很早就受到良好的关于艺术、自由的教育和熏陶,中学时期更是认真阅读了莎士比亚、易卜生及托尔斯泰等的作品,大学期间作为戏剧青年的卢卡奇还同别人一起创立塔利亚剧场。在他看来,戏剧不仅仅是语言和动作的艺术,而是融合了视觉和听觉、观众和作者交织的复杂的时空的在场,能够更好地承载对于社会现实的批判。不过他很快转向了更具理论性的领域中,尤其是对形式问题的关注。形式并不是跟内容相对的范畴,而是具有康德先验哲学的特点,是心灵的现实性和表现。只有形式化以后,才能进一步进行社会学研究。
卢卡奇的上述思想其实是继承发展了狄尔泰的精神科学。卢卡奇还在上大学时,“正是在这个时候,我最初研究了康德,然后在当代德国哲学中研究了狄尔泰和西美尔的著作。”[1]60而到写作《小说理论》时期,“当时我正处于从康德转向黑格尔的过程中,然而我同所谓‘精神科学’方法的关系并没有什么改变,这种关系主要是基于我青年时代从狄尔泰、席美尔、马克斯·韦伯著作中得到的印象。《小说理论》事实上就是这种精神科学倾向的一种典型产物。”[2]3他还专门例举并分析了狄尔泰《体验与诗》的方法论。狄尔泰把文化当做生命的客观化和表现,他的哲学强调直觉,认为精神科学不必以事实为基础,以纯直观的方式从少数特征综合出普遍概念,然后再回到个别现象中,就得到所谓宏大的总体性。卢卡奇《小说理论》的方法,并没有超越精神科学方法的局限。
卢卡奇还受到了西美尔哲学的很大影响。他的著名的《戏剧发展史》就是在西美尔的直接指导下完成的“完整的作品”。西美尔提出的关于艺术的社会性问题成为卢卡奇的思想基石。而韦伯的影响虽然来得较晚,但是更深刻。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用“客观化”表述社会的“合理化”,这拓展了卢卡奇的思路,让他在西美尔异化论思想基础上更深入思考。更重要的是,在卢卡奇看来,韦伯不同于西美尔比较浅薄的方面,是想要创立一种全面的文学理论。相比西美尔“印象主义”的风格,卢卡奇受韦伯影响而更加专注于思想体系的构建,更加倾向于学术化和扎实的学术实践,这对于《小说理论》的创作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对卢卡奇的《小说理论》影响最大的是黑格尔的哲学思想。他说:“《小说理论》的作者已成为一位黑格尔主义者。……《小说理论》是将黑格尔哲学的成果具体运用于美学问题的第一部精神科学著作”。[2]5黑格尔的总体观认为世界统一于绝对(精神),实体就是主体,一切皆包容于总体之中。“总体主要不是一般的‘部分之和’,而是一种走向绝对的能动的创化力量。它驱使观念发展的每一个环节(部分)走向总体,扬弃观念的对象化和异化以回归主体,总体是一元的圣灵之大全。”[3]在这个意义上,总体性是黑格尔哲学的方法论。卢卡奇学生时期就非常熟悉黑格尔著作,卢卡奇希冀小说这种形式指向人的内在心灵本质的整体性,“他从永恒形式走向了美学范畴的历史化理解”[4]。卢卡奇用总体性范畴指代荷马史诗的世界,世界自身是完满的,一切都在它内部发生着,个别以总体作为存在依据。他在书中认为小说世界的结构展现了总体性,但这个总体性还是一种朦胧的期盼,是对过去史诗时代的怀念,只能在艺术形式中实现。而要真正实现总体性,要在主客体统一中来实现具体的总体,这是后来《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思想了。因此,“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具有决定性的区别。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5]当然,在后来卢卡奇的眼里,即便是《历史与阶级意识》也是过渡性作品,混杂着马克思主义与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
二
卢卡奇从总体性视角说明古希腊社会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差异而造成的古代史诗与现代小说的对立,并且为自己构建的小说的类型学赋予了历史性因素。
卢卡奇通过总体性范畴阐明古典史诗和现代小说之间的明显差异或对立。他按照黑格尔的观点,也把古希腊精神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史诗、悲剧和哲学,认为它们代表着“世界文学中伟大而永恒的典范形式的三个阶段”。《小说理论》用优美的词句描述了古希腊的荷马史诗时代人和世界和谐相处于总体当中,自我(心灵)不像后来那样疏离于世界。这个时代对内在世界、即主体性还没有形成任何观念,“存在与命运、冒险与完成、生命与本质是同一个概念”;“希腊人只知回答而不知提问,只知谜底(尽管是神秘的)而不知谜面,只知形式而不知混乱”。[2]2概括地讲,古希腊人的生活的意义在于它的总体性。卢卡奇说,这个时代的伟大史诗“刻画了广博的总体”。 所谓“总体”,狭义地讲,是指史诗描写的是一个时代生活的全面,它具有比抒情诗和戏剧更加广阔的世界,兼顾环境和个人的内心世界与行动,并且展示它们之间的互动。在他看来,史诗是表达以人为一方和以共同体和世界为另一方之间绝对一致的形式,是理想时代的艺术,是“史诗的世界时代”。在史诗时代,行动的意义是内在的,是当下业已完满自足的,所以人对其行动的意义不会感到怀疑,诸如“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生怎样才会有意义”之类的问题在当时的心灵中根本就没有提出来过。但是,在希腊的悲剧时代,人生的意义已不再内在于生命及其行动之中,而是需要悲剧英雄在自我创造中重新发掘出来,而这种创造活动与日常生活却是对立的。在哲学出现之时,内在与外在、内心与世界、心灵与行动的分裂已经比较严重,所以,人们需要将它们当作一个问题来反思,以寻求思想上的解答。毋宁说,哲学的出现就是这种严重分裂的预兆。可以看到,从史诗、悲剧直到哲学的过渡,在卢卡奇那里就是一个不断沉沦和异化的过程。
中世纪就某方面来说是希腊史诗时代的重复,因为超验的意义与现世之间是由耶稣沟通起来的,他使分裂的世界恢复成总体,使美学与形而上学再度结合。但丁的《神曲》就是中世纪的伟大史诗。当然,中世纪与荷马时代毕竟是不同的,因为中世纪是分后求合的表现,而在荷马时代,意义与生活在根本上处于尚未分离的原始统一状态。而且,但丁的《神曲》虽然有一个总体,但意义与形式的根源却是完全来自独一无二的上帝。
受黑格尔和席勒的影响,卢卡奇也把现代文化与古希腊文化作了对比,称前者是有问题的,而后者是总体性的。古希腊人没有形成主体性的概念,而始于笛卡尔的近代哲学却走向了不断强调主体的道路。上帝逐渐隐退,剩下人自己成为形式或意义的赋予者。文艺复兴之后的现代世界已经变成一个彻底疏离的时代,变成一个无限的、开放的世界,人丧失了总体感。这样,史诗的世界就与现代世界,即人与社会、宇宙彼此分裂的世界,与小说的世界对立起来。现代社会使得自我与世界之间横亘着难以跨越的鸿沟。
小说正是这样一个时代的产物和反映。卢卡奇认为小说之所以成为取代史诗的文学形式是因为现时代不再有史诗时代广博的总体性。《小说理论》把小说这种文学形式与社会历史、政治以及哲学相关联,把小说看作是时代和历史发展的产物,主张小说要与资本主义时代的关系来加以定义。在卢卡奇看来,小说刻画了孤独的个人的漂泊感,小说的英雄是“探寻者”,但这种探寻必定失败,它既无目的也无途径,“只能是犯罪或胡闹”,“因为犯罪和胡闹是超验的无家可归的客体化”,这是社会关系的人类秩序中一种行动的无家可归和超个人的价值体系应有秩序中一种心灵的无家可归,小说的形式就是“先验无家可归的一种表达”。[2]32卢卡奇指出,不仅在现代世界中我们与我们自身、与第一自然之间有一道难以理解的鸿沟,而且我们与第二自然或社会之间也是疏离的,人在其中找不到安身立命的意义。就像人们在第一自然中发现自然规律一样,人们也在社会中发现一些毫无意义的必然规律,却又无法了解这些规律的真正实质。
在此基础上,卢卡奇进一步阐述了小说所具有的不同于史诗的三个基本特点:
首先,在他看来,小说是在总体性失落后仍然执着于构建一种生活的总体。不同于史诗的主人公是社会这个有机的总体,小说的主人公则是一个自我封闭的有问题的个人。这个人所有的努力只能理解现实的某个侧面或者是留下一些模糊的印记,不可能把握全部现实。但卢卡奇也在多处强调:通过探寻,还是或多或少地存在自我实现的希望。
其次,卢卡奇像黑格尔一样,主张小说是由史诗演变而来的。然而,小说的主人公与史诗的主人公又是明显不同的。严格地说,史诗的主人公并非单独的个人,而是代表一个民族或共同体的个人。小说产生于有问题的时代,其主人公也是有问题的个人,因为他是孤独的,他的生活缺乏意义,他处在追求意义和寻找自我的过程中。所以,小说的内容是描述探险的主人公内心的冒险历程。卢卡奇说:“小说是内心自身价值的冒险活动形式;小说的内容是由此出发去认识自己的心灵故事,这种心灵去寻找冒险活动,借助冒险活动去经受考验,借此证明自己找到了自己的全部本质。”[2]80-81。卢卡奇主张,小说所对应的总体性已经不再遭到摧毁,生活的意义变成一个问题和一种向往,尽管它仍以总体方式得到思考。因此,小说成为孤独的人在疏离世界中寻找或追求人生意义的过程,当然,这种愿望在现实的社会结构中是注定不能完全成功的。
最后,卢卡奇关于小说的形式问题的理论中阐述了反讽的写作手法。他认为反讽是“小说形式的成分之一”,是“在没有上帝的世界中所能达到的最高自由”。这是因为反讽表达的是主观愿望、理想与客观现实的不一致。而小说中的道德意向就需要不停地自我否定。小说的“规范心态”就是反讽。反讽虽然表示主体在追求意义方面的失败,但由于它认识到现实的真相和失败的必然性,因而也显现出主体的自由。这种自由不在于积极地完成主体理想,而在于消极地否定任何业已完成的形式或呈现出来的意义。个人渴望的意义无法真正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反讽因而成了自我所能达到的一种超验自由的表现。反讽的作用是“对弱点进行自我校正”。作为形式的原则,反讽虽然不能消除小说形式的弱点,但它却能够使人预感到统一性。“所以,它不只是创造总体的真正客观性的惟一可能先天条件,而且也由于小说的结构类型与世界的状况基本一致,就把这种总体即小说提升为这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形式。”[2]84
卢卡奇构建出小说的类型学赋予了历史性因素。他在《小说理论》的第二部分阐述了个人与社会的分歧以及主人公与世界的无法逾越的裂隙。由于小说主人公的心灵与世界是疏离的,卢卡奇从小说主人公的心灵与外部世界的不同关系出发而构建了两种主要的小说类型。第一种类型是以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为代表的长于细致描写行为、但短于描写心理的小说,此类作品把“诗与反讽、崇高与怪诞、神性与偏执狂”都融合在一起,而且与历史环境联系在一起。其中主人公的心灵明显要比外界更为狭隘,这其实暗示了人的孤独的存在。即便是现实与某人对它的想法根本不一致,他也不会因此绝望或者去怀疑现实,他把头脑中的想法当成了现实本身。就像唐吉诃德一样,他眼中的世界显然不是真实的,他的所作所为已经没有价值,他的孤独已然成为可笑而荒唐的存在。即便他内心深处有坚定的信念,也没有任何意义。卢卡奇借这个作品想说明,在一个道德沦丧的世界,对于内心比外面世界还要狭隘的人,即便有英雄气概坚持理想也是可笑的。第二种类型则是以古斯塔夫·福楼拜的《情感教育》为代表的长于描写心理活动短于描写行动的小说,此类作品中主人公的心灵比外部世界广阔,这意味着心灵没有力量在现实世界中付诸实现,因而只有逃遁到幻梦中去。这种对待外部世界的态度不是选择主动的改造,而是选择被动的逃避,倾向于由心灵内部处理所有与外部世界相关的事情。所以,这类小说主要致力于对主人公的心理分析。这类小说之所以被称为“幻灭的浪漫主义”,是因为浪漫主义型的小说主人公在表面上虽然可在内心中造成一个自足的世界,把生活变得像是艺术品一样,但外在世界实际上并不会因此就消失,它迟早仍会强迫他面对现实,强迫他努力把理想在现实中加以实现。但由于他受制于那种消极被动的沉思态度,所以失败是注定的。而两种创作类型的综合的代表作品就是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这一类型小说的主人公既不像唐吉诃德那样坚定,只去努力实现理想而不顾现实的真相,也不像莫罗那样只在内心幻想而不真正去实现理想。特点是主人公既有理想,也顾及现实,既有内心生活,也努力将理想付诸实现,他对社会的关系既非完全否定,也非完全肯定,而是在互动的过程中达到“和解”。他虽是一个有问题的人物,追求意义与自我了解,但他并不是一个孤独的人,而是一个生活在共同体中的人。他与共同体中的其他分子有相同的目标,彼此互相切磋砥砺,这样就可以消除个人的孤独与获得某种意义。
三
卢卡奇《小说理论》到他晚期视为自己最重要的著作《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的思想发展历程非常复杂,既有断裂也有内在的连贯性。卢卡奇的思想创作与现实遭遇中,多次做过自我批评,有时甚至是违心的,既迫于压力的权宜之计也有真实的思想转变。
总的说,《小说理论》被公认为卢卡奇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的重要作品,问世以来受到了韦伯、布洛赫、阿多诺等思想家的一致肯定。布尔写道:“卢卡奇的《小说理论》(1920)所产生的影响(这里我们只举出他对H·马尔库塞和Th·W·阿多诺的影响),是巨大的。”[6]他甚至指出法兰克福学派及其批判理论如果离开了《小说理论》,将难以想象是什么样子。作为法兰克福学派重要代表的阿多诺确实肯定《小说理论》的思想深刻性,认为是哲学的美学经典作品。然而,1938年,卢卡奇在苏联对该书作了过分严厉的自我批判。他认为《小说理论》充满着神秘的唯心主义成分,对历史的发展做了完全错误的分析。1962年,他在《小说理论》的序言中,仍强调该书在方法上犯的严重错误,而使他对许多小说的分析都歪曲失实。他认为,这种方法的要点是以直觉所掌握的一些特征为基础去建构关于一个学派或一个时代的一般性概念,然后再由其演绎出对个别现象的分析,并借此达成一个全面的综观。虽然这种方法的应用产生了一套小说类型学,但是它由于太抽象和一般化而无法对《唐吉诃德》这样的小说做出充分的分析。此外,这种方法忽略了作品的具体历史社会环境,从而在许多地方产生任意和武断的判断。卢卡奇由此得出结论,虽然《小说理论》的部分细节(如对小说中时间性的讨论)有预见性的价值,但在整体上只有历史价值,即帮助我们了解20世纪20-30年代的意识形态,除此之外并无理论价值。卢卡奇晚年(1971年)对这部著作做了比较中肯的批判性分析,指出“这本书无疑包含有一些正确的看法。然而作为整体,它是建立在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世界文学中革命小说的顶峰这样一个前提之上的,而这自然是错误的。无论如何,即使这本书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文学的框框内,它还是探索了革命小说的理论。在当时,这种东西是从未有过的。……我的理论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上不是革命的,但是如果用当时的文学批评来衡量则是革命的。”[1]80-81他还认为《小说理论》仅仅是过渡时代的过度作品而已;虽然指出了这个罪孽时代,但缺乏列宁要彻底改变整个社会的积极性。卢卡奇对《小说理论》的三次批判性评价,从全盘否定到较为客观的分析,这种差别显然与他当时所处的不利环境及其变化是密切相关的。仅凭卢卡奇本人的这种隐情复杂的自我检讨,尤其是前两次检讨,来看待他的《小说理论》无疑是有失公允的。
《小说理论》标志着卢卡奇思想从新康德主义转向黑格尔主义,它既是对卢卡奇早期文学和美学创作的一次总结,也是开启卢卡奇哲学思想、尤其是催生《历史与阶级意识》的重要契机。我们知道,影响更大的作品《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清晰体现出卢卡奇深受黑格尔思想方法的影响,但是总体性、历史等概念早在《小说理论》中初步得到展现了。首先,在《小说理论》第一部分,卢卡奇对史诗、小说等艺术形式的分析遵从了历史的方法,主张古希腊、现当代的不同特征的生活面貌相应地产生了这些不同的艺术类型。在第二部分,卢卡奇从总体性、历史性思想出发探讨了小说形式的几种类型学。现代性与总体性的背离造就了理性的、浪漫的以及教养类等作为时代产物的不同的小说类型。其次,总体性的思想充分体现在卢卡奇对于艺术形式和小说类型的分析之中。像席勒和黑格尔一样,卢卡奇强调不同于古希腊史诗中直接对应的希腊人所属的世界总体性,小说中主人公要从被遮蔽的总体性中去发现世界的总体性。这种总体性是不同的艺术类型的分野的前提,也是艺术家创作的目的和归宿。最后,《小说理论》从人类历史和精神发展的观点出发深刻地阐明,在充满战祸的帝国主义时代人类正处在“恶贯满盈的阶段”,它以一战为背景深刻反思西方文化及社会的危机,希冀寻求一个“新世界”。尽管他心目中的“新世界”还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但他对当时社会的无情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执着追求,可以说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性分析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见解。《小说理论》较早地提出现代人的“无家可归”概念和现代性问题,已经论及日益严重的异化现象。虽然卢卡奇在大学期间就读到了马克思的一些著作包括《资本论》等,但据他自己回忆由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立场使得这些作品对他的影响还仅仅限于经济学特别是社会学。而此时卢卡奇用社会历史环境和时代特点来解释小说的性质,无疑包含着他不久世界观即转向马克思主义的端倪。
[1] (匈)卢卡奇.卢卡奇自传[M].杜章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
[2] (匈)卢卡奇.小说理论[M].燕宏远,李怀涛,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3] 张一兵,胡大平.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70.
[4] 仰海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7.
[5]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杜章智,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77.
[6] M·布尔.评卢卡奇[J].哲学译丛,1986(1):12.
[责任编辑:黄 昇]
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喀什大学南疆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重大项目(XJEDU070113A02)。
李怀涛,博士后,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国外马克思主义。
B5
A
1002-6924(2016)12-025-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