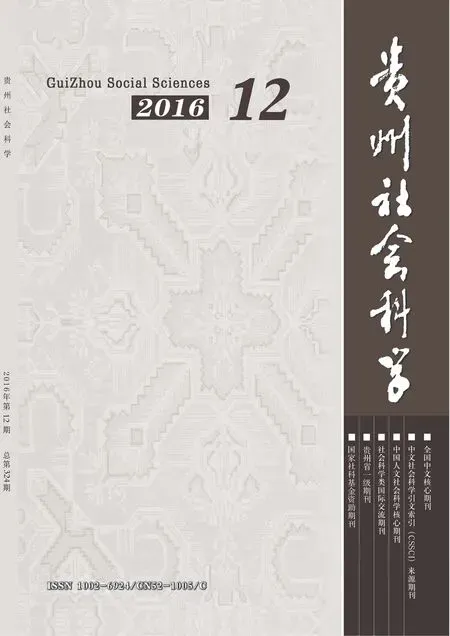体貌与文相
党圣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732)
体貌与文相
党圣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732)
在传统诗文评论的话语体系中,“体”有一种义项是指文章或者文学的整体性存在或整体风貌。“体”本指人之“身体”,“体”概念进入文论,与魏晋以降的人物品藻相关,而以人体由外而内的肉、骨、气、神等构成之整体结构,来比附文章及书画诸艺术的由表及里的“体貌”、“体性”等结构层次,则体现了“近取诸身”的致思范式与“远取诸物”的“象喻”批评特质。文章等人文制作与天地万物、人之身体等皆一气化成,故而一气贯通,异质同构,而品文之法与相人之术及对天地万物的仰观俯察之法,也道通为一,体现了中华文化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人文观、生命观、价值观等,对于中华美学精神的当代建设具有积极意义,理应加以重视。
体;体貌;文相;人物品藻;象喻
“体”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古代文献中有以“体”为词根的一系列文论概念群。在传统诗文评论的语境中,“体”有一种义项是指文章或者文学的整体性存在或整体风貌,双音节词“体貌”等与这一义项相关。魏晋以降的关乎相人之法的人物品藻开启了以“体”论“文”的中国特有之批评方式,而以“体”论“文”也是《文心雕龙》的重要内容。这就需要从“体”的原始意义和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说起。
一、“体”之历史语义学阐释
“体”字的繁体为“體”,从骨,豊声,是个形声字。“骨”是形旁,表意;“豊”是声旁,表音。《说文》:“体,总十二属也。”段注:“十二属,许未详言。今以人体及许书核之。首之属有三:曰顶,曰面,曰颐;身之属有三:曰肩,曰脊,曰尻:手之属有三:曰肱,曰臂,曰手:足之属有三:曰股,曰胫,曰足。他禮切。”*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四篇下,上海书店1992年影印清嘉庆二十年经韵楼刻本,第166页上。所谓“十二属”,皆承之于骨,故从骨;豊为禮器,凡祭祀,禮器必望厚,豊因之有望厚意。體“总十二属”,體有豊意。故體从豊声,亦从豊意。说明“体”最初是指由“十二属”构成的人的整体,“体”的本义是指身体,是指人的全身。所以“体”是一个整体性的称谓,是指一个生气灌注的有机整体,也可以理解为将各部分合成一个有机整体。从这一原始用义可以看出,“整体”义项构成了“体”在古典汉语语境中的基本内涵。但“体”有时也指身体的一部分,比如“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五体投地”之“体”,就是指身体的某些部分,但是这种“体”的用法更多的是代指身体的全部。
“体”的本义是指人的身体,所谓“体,身也”*王念孙:《广雅疏证》卷六下“释亲”,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清嘉庆王氏家刻本,第203页上。。后来引申为泛指事物之存在的实在性、基础和本根,比如“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周易·系辞下》,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 ,第89页上。、“天之与地,皆体也”*黄晖:《论衡校释》卷七《道虚篇》,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19页。等句中的“体”便是;亦可训释为“物质存在的形态”,诸如“液体”、“固体”、“气体”等等,总之,凡实在之物皆有“体”,故我们也把物叫做“物体”。此外还指相对抽象的制度性、体制性存在,如我们还说“政体”、“国体”等。“体”即物的实在的显现、是完全的完整的显现,因此我们有“整体”、“总体”的说法。“体”的本义与“形”密不可分,《庄子·天地》:“物成生理,谓之形;形体保神。”*郭庆藩:《庄子集释》卷五上《天地第十二》,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430页。“形”在庄子那里是一个生理学的范畴。在中国古人看来,无论人的肢体、物之形体、事之大体主体,都有一定的形态,都有一定的“体”,天地万物如此,文章也应该如此,而“体”正是文章由内容到形式的枢纽。没有这一枢纽,文章就难以成形,而凡文章必有体。因此,古代文论中的“体”在很多情况之下是指文章的存在形态,是指汇通形式、风格、内容等的文章的整体形态。古人以“体”称文的用意之一,正是为了突出“文章整体”和主次条理井然有序的有机性这层涵义。
基于“天人合一”的大传统,“体”论包含了古人身体观的独特认知。它强调身体的整体性,认为“形与神俱”,“形神合一”,同时认为天人同构,身体是一小宇宙,宇宙是一大身体,即人体作为小宇宙,与大宇宙是相通互融的。尤其汉儒讲天地人合以成体,是把人作为自然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的不可缺少的要素看待,甚至将之上升到“天人相副”的高度。董仲舒认为:“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天之副在乎人”*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十一《为人者天第四十一》,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18—319页。。体,本义是人的身体,引伸为宇宙整体,这个命题形象地表现了董仲舒把整个宇宙看作为一个普遍联系的有机整体的思想。当然在此之前,中国人在观察世界时,总是将宇宙看成一个有生命的、有机的整体,总是习惯于以人自身来加以拟附。《周易·系辞下》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周易·系辞下》,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第86页中。所谓“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便是这种思维方式的最好概括。
为什么人类社会的早期总是将对外物的认识和自身联系起来,尤其要和自己身体联系起来呢?从认识论角度看,“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的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古希腊智者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普罗泰戈拉提出的关于人的著名的哲学命题,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38页。,人类并非对所有成为直观对象的事物或现象都形成认识,只是和主体相关的事物或现象才成为现实的认识对象,也就是说,认识客体是为了满足主体的需要。而主体的需要最为迫切的是对自身的认识,所以,为了认识客体就须首先回到认识主体上来,然后再以对主体的认识结果作为参照系去加深对客体的认识。因此人可以以自身为对象,去把握宇宙。西谚说:“认识你自己吧。”人体是上帝的杰作。哲人说:“人啊!请正视你的身体。”所以在古希腊艺术中,对人体美的欣赏比对自然美的欣赏还要早。中国人虽然没有像希腊人那样在艺术中充分表现身体,但是从身体出发认识事物,比附对象,却有着久远的传统。
二、以“体”论文与“象喻”批评
中国固有文学批评在批评思维和用语上擅用比拟,往往以自然植物为喻、以人为喻、以生命为喻来论文。天人同构,人的身体与天地万物同构,作为人文制作的文章既与人的身体也与天地万物同构,而“一气贯通”,贯穿这一切的是生生不息之气。
以自然物象比喻文章的“象喻”批评,体现了古人“远取诸物”而认为文章与天地万物同构的基本思想。关于以自然、植物为喻,我们在此举例说明:
唐白居易说:“《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白居易撰,谢思炜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卷八《与元九书》,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22页。视诗如植物。
明代胡应麟将动植物联喻以言诗:“诗之筋骨,犹木之根干也;肌肉犹之叶也;色泽神韵,犹花蕊也。筋骨立于中,肤肉荣于外,色泽神韵充溢其间,而后诗之美善备,犹木根干苍然,枝叶蔚然,花蕊烂然,而后木之生意完。”*胡应麟:《诗薮》外篇卷五,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04页。视诗歌如同树木和动物,两者兼之,可见其比拟具有相通之处。
清叶燮说:“夫天有四时,四时有春秋,春气滋生,秋气肃杀。滋生则敷荣,肃杀则衰飒。气之候不同,非气之有优劣也。使气有优劣,春与秋亦有优劣乎?故衰飒以为气,秋气也。衰杀以为声,商声也。俱天地之出于自然者,不可以为贬也。又盛唐之诗,春花也。桃李之华,牡丹芍药之妍艳,其品华美贵重,略无寒瘦俭薄之态,固足美也。晚唐之诗,秋花也。江上之芙蓉,篱边之丛菊,极幽艳晚香之韵,可不为美乎?”*叶燮:《原诗》外篇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66—67页。视迭代诗风如同四季气候转换。
以自然之物作为比拟的例子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可谓俯拾即是。至于以人、以人体为比拟来论文论艺,更是中国固有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特点,体现的是我们古人“近取诸身”而认为文章结构与人的身体结构同构的基本思想。这里我们首先从表象入手,来看看中国固有文学批评的这个特点:
(一)以“体”论“文”。借助人的身体概念来论文,乃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屡见不鲜的事
齐梁刘勰说:“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肤肌,宫商为声气。”*刘勰:《文心雕龙》卷四三《附会》,陆侃如、牟世金译注:《文心雕龙译注》,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511页。以下所引《文心雕龙》皆同此版本。由里而外,由“情志”“事义”“辞采”“宫商”构成的文章整体,就活脱脱地是一个由“神明”“骨髓”“肌肤”“声气”构成的活人。
北齐颜之推说:“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卷四《文章第九》,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24页。
唐贾岛:“诗体若人之有身。人生世间,禀一元相而成体,中间或风姿峭拔,盖人伦之难。”*贾岛:《二南密旨》“论裁体升降”条,《丛书集成初编》第2546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7页。(《二南密旨》)“一元”者,气也,人之“体”乃一气化成,诗之“体”亦复如此。“风姿峭拔”者,人之“体貌”也,也可用来描述诗之“体貌”。
唐徐夤说:“体者,诗之象,如人之体象,须使形神丰被,不露风骨,斯为妙手。”*徐夤:《雅道机要》,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6页。“体象”犹“体貌”。
宋李廌说:“凡文之不可无者有四:一曰体,二曰志,三曰气,四曰韵。……文章之无体,譬之无耳目口鼻,求能成人;文章之无志,譬之虽有耳目口鼻,而不知视听臭味之所能,若土木偶人,形质皆具而无所用之;文章之无气,虽知视臭味,而血气不充于内,手足求卫于外,若奄奄病人,支离憔悴,生意消削;文章之无韵,譬之壮者,其躯干枵然,骨强气盛,而神气昏懵,言动凡浊,则庸俗鄙人而已。有体、有志、有气、有韵,夫是谓成全。”*李廌:《济南集》卷八《答赵士舞德茂宣义论宏词书》,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宋集珍本丛刊》第30册,线装书局2004年版,第727页上、下。“全”文当如“全”人,无“志”“气”“韵”之文如断气无神之人(行尸走肉),但无“体”之文则如无所依托的游魂,古人重志气、神韵而不轻体貌。
宋吴沆说:“诗有肌肤、有血脉、有骨格、有精神。无肌肤则不全,无血脉则不通,无骨格则不健,无精神则不美。四者备,然后成诗。”*吴沆:《环溪诗话》卷中,惠洪、朱弁、吴沆:《冷斋夜话 风月堂诗话 环溪诗话》,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30页。
南宋姜夔说:“大凡诗,自有气象、体面、血脉、韵度。气象欲其浑厚,其失也露;韵度欲其飘逸,其失也轻。”*姜夔:《白石道人诗说》,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80页。
元杨维桢说:“评诗之品无异人品也。人有面目骨体,有情性神气,诗之丑好高下亦然。”他还说:“面目未识,而谓得骨骸,妄矣;骨骸未得,而谓得情性,妄矣;情性未得,而谓得其神气,益妄矣。”*杨维桢:《东维子文集》卷七《赵氏诗录序》,四部丛刊本。
明归庄说:“余尝论诗,气、格、声、华,四者缺一不可。譬之于人,气犹人之气,人所赖以生者也,一肢不贯,则成死肌,全体不贯,形神离矣;格如人五官四体,有定位,不可易,易位则非人矣;声如人之音吐及珩璜琚瑀之节;华如人之威仪及衣裳冠履之饰。”*归庄:《归庄集》卷三《玉山诗集序》,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06页。“格”类陶明濬所谓“体制(体式”),“华”之“威仪”类若“体貌”。
清孙联奎说:“人无精神,便如槁木;文无精神,便如死灰。”*孙联奎:《诗品臆说》“精神”条,孙联奎、杨廷芝:《司空图〈诗品〉解说二种》,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29页。(《诗品臆说》)
清方东树说:“观于人身及万物动植,皆全是气所鼓荡。气才绝,即腐败臭恶不可近:诗文亦然。”*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25页。(《昭昧詹言》卷一)诗文与人身及万物动植,皆一气化成,故而同构,而品文之法与相人之术通。
清姚鼐在《古文辞类纂·序目》中将文章的要素分成八种,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学者之于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终则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姚鼐编选,吴孟复等评注:《古文辞类纂评注》,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页。“粗”与“精”或“形”与“神”之论,也关乎文之“体”构成的层次性。
近人陶明濬《诗说杂记》疏解严羽“兴趣”说:“此盖以诗章与人身体相比拟……体制如人之体干,必须佼壮;格力如人之筋骨,必须劲健;气象如人之仪容,必须庄重;兴趣如人之精神,必须活泼;音节如人之言语,必须清朗。五者既备,然后可以为人;亦为备五者之长,而后可以为诗。”文章之“体制(体式)”“格力”如人之“体干”“筋骨”,而文章之“气象”则如人之“体貌(仪容)”,文之“体”的构成也是有由内而外的层次性的。
以上列举的言说,都是将人体的结构和文体的结构进行比附、联想和判断、推衍,所谓“盖以诗章与人身体相比拟”,从而表达自己对文学艺术的认识的。不过以上列举的只是中国固代文学批评以体论文的冰山一角*钱钟书除了在《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一文中有举例外,还在《管锥编》和《谈艺录》两书中列举了众多的例证。,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诸如单音节词“气”“力”“形”“体”“神”“貌”“肥”“瘦”“壮”“弱”“病”“健”“首”“腹”“尾”“筋”“骨”“皮”“脉”“髓”“魄”,双音节词“精神”“神韵”“气骨”“风骨”“血脉”“皮毛”“文心”“诗眼”“主脑”“肌理”等术语,中国传统的诗文评将会是什么样子。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这样一些人化的理论术语或者喻象,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尤其是诗文评甚至是书画理论,都将会陷入“失语”的尴尬之中。可见借体论文已经成了中国固有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时至今日,有学者还认为文体结构与人体结构相同,并运用这种方式来论文:“一种文体的基本结构,犹如人体结构,应包括从外至内依次递进的四个层次,即:(1)体制,指文体外在的形状、面貌、构架,犹如人的外表体形;(2)语体,指文体的语言系统、语言修辞和语言风格,犹如人的语言谈吐;(3)体式,指文体的表现方式,犹如人的体态动作;(4)体性,指文体的表现对象和审美精神,犹如人的心灵、性格。”*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而刘勰《文心雕龙》实际上也暗含此类分层法(详论见后)。
(二)借“体”论“艺”如书画等。首先是以身体比附描写对象。在传统山水画论中的评论和对画理的比拟中,往往现“身”说法,总是不离身体
譬如宋郭熙认为:
石者,天地之骨也,骨贵坚深而不浅露;水者,大地之血也,血贵周流而不凝滞。*郭熙:《林泉高致》,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版,第50页。
山以水为血脉,以草为毛发,以云烟为神彩。故山得水而活,得草木而华,得烟云而秀媚。水以山为面,以亭榭为眉目,以渔樵为精神。故水得山而媚,得亭榭而明快,得渔樵而旷落。此山水之布置也。*郭熙:《林泉高致》,第49页。
把石头和水比作天地的骨血,从而引起画者在将自然“迹化”为作品的同时,融入对自己身体的联想,则画必如活人之体而血脉流动、神采焕发。又譬如:
石有面有肩,有足有腹,一如人之俯仰坐卧。*龚贤:《画诀》,鲍廷博辑:《知不足斋丛书》第四册,中华书局1999年影印本,第695页下。
山以林木为衣,以草为毛发,以烟霞为神采,以景物为装饰。以水为血脉,以岚雾为气象。*韩拙:《山水纯全集·论山》,《丛书集成初编》第1641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页。
以身体演示画理,有些画论简直就可以为你描绘出一个活生生的人体来。这在中国画论和绘画术语中屡见不鲜。它们把画中最精彩最传神的细部叫做“画眼”,把关键性的画面处理叫做“点睛”,把拘泥于细节而失去整体效果叫做“谨毛失貌”等等,这背后无不藏着身体及整体的尺度。就连画论中最为推重的“气”“力”“势”“态”之类的概念也无不从“体”观念中来。南齐谢赫的“六法”,其中核心的、纲领性的内容就借助于身体的联想。“气韵生动”、“骨法用笔”,都出于对身体状态和身体部件的联想。气与韵以及气韵,都是从人的肉体和生命现象中引申出来的感觉,转而投射于艺术作品,并进而成为品鉴标准,相人之术已成品画之法。“骨法”是更为典型的以身体为蓝本而衍生出的审美标准,这种审美标准从本根上来说是抽象的,其言说方式是比喻、比拟性的,因而给人以生动质感,并能触动人的联想。
在书法理论之中,这种情况更是普遍。概举如下:
五代荆浩说:“凡笔有四势,谓筋、骨、肉、气。笔绝而断谓之筋,起伏成文谓之肉,生死刚正谓之骨,迹画不败谓之气。故知墨大质者失其体,色微者败正气,筋列者无肉,迹断者无筋,苟媚者无骨。”*荆浩:《记异》,秦祖永辑:《画学心印》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第1085册,子部艺术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24页上。
刘宋王僧虔说:“骨丰肉润,入妙通灵。”“骨骼丰满,肌肉润泽,那就可以自接进入无穷妙境,与神灵相通。”*王僧虔:《笔意赞》,冯武:《书法正传》纂言上,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版,第134页。
北宋朱长文说:“(沈传师之书)爽快骞举,如许迈学仙,(骨)轻神健,飘飘然欲腾霄云。”“骨骼轻盈,精神健全,飘飘然好像要腾飞一样。”*朱长文纂辑:《墨池编》卷三《续书断上》“妙品十六人”,《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北宋苏轼说:“书必有神、气、骨、血、肉,五者缺一,不为书也。”*苏轼:《论书》,王原祁等纂辑:《佩文斋书画谱》卷六,中国书店1984年版,第156页上。
北宋米芾说:“字要骨格,肉须裹筋,筋须藏肉。”*米芾:《海岳名言》,《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1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明丰坊说:“书有筋骨血肉。”*丰坊:《书诀》,《丛书集成续编》第99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6页下。
清康有为说:“书若人然,须备筋、骨、血、肉。血浓骨老,筋藏肉莹,加之姿态奇逆,可谓美矣。”*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余论第十九,中国书店1983年版,第46页。
“肉”“血”“骨”“气”“神”也可显见画之结构如人之身体结构在构成上由表及里的层次性。古代的书法家总是视书法为一种生命的艺术,总是力求要在字里行间表现出生命体的筋骨血肉的感觉来,因此在批评书法和描绘书法性状时表现出明显的“体”观念,那就是艺术鉴赏中的拟人化倾向,以人论艺,以体论艺。如前所述,基于人类认识“近取诸身”的思维特点,从身体出发,并向人的综合素质延伸,论述艺术如同人的身体的有机性和整体性,这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所以,当中国人说“画如其人”的时候,就已经从人的身体散发出了许多东西,衍生出了许多尺度,内中也隐含了中国古人的致思方式,对此今人如钱钟书、朱光潜等先生多有所论。
这说明,传统谈艺论文,特别偏向于将文章、已作视为人之形体、生命,从而体现出重视感性生命,以生命呈现在人体自然中的力量、气质、姿容为美的审美观念和理论思维。中国学者对此进行的理论概括,应该从钱钟书先生对中西文学批评的比较说起。在钱钟书先生看来,中国文论中既具普遍性、独特性,又具有世界性的特点就是:
把文章通盘的人化或生命化(animism)。《易·系辞》云:“近取诸身……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可以移作解释:我们把文章看成我们自己同类的活人。《文心雕龙·风骨篇》云:“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瘠养肥词”(笔者按:“瘠养肥词”应为“瘠义肥词”,钱文此处错‘义’为养”。);又《附会篇》云:“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这种例子哪里举得尽呢?我们自己喜欢乱谈诗文的人,做到批评,还会用什么“气”,“骨”,“力”,“魄”,“神”,“脉”,“髓”,“文心”,“句眼”等名词。翁方纲精思卓识,正式拈出“肌理”,为我们的文评,更添一个新颖的生命化名词。*钱钟书:《钱钟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391页。
钱钟书先生的这一见解见于其1937年5月23日写成的长文《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刊载于《文学杂志》1卷4期(1937年8月1日)。其中核心的认识就是“把文章通盘的人化或生命化”,亦即所谓的“人化”或者“生命化”。此后钱先生陆续对此说进行补充,使之对中国固有文学批评特点的概括更加完善,论证更加充分。比如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曾说,中国古代文评的一个重要特色是:“谓其能近取诸身,以文拟人;以文拟人,斯形神一贯,文质相宣矣。”*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0页。钱钟书先生还从中国人认识思维的角度指出:“盖吾人观物,有二结习:一、以无生者作有生看(animism),二、以非人作人看(anthromorphism)。鉴书衡文,道一以贯。图画得其筋骨气韵,诗文何独不可。”*钱钟书:《管锥编》第四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357页。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的这种特征,必然会深深地影响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并孕育出相应的富于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美学理论,其特色就是以人拟文,以人拟艺。这一特色的形成,从哲学上讲是与中国古代哲学—美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有关的;从文艺传统上讲,又不能不说它在一定程度上受了魏晋以来将人物品藻与诗文评论结合传统的影响(详论见后)。
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对此也很认同并作了补充。朱光潜在《文学杂志》1卷4期“编辑后记”中说:“钱钟书先生拿中国文学批评和西方文学批评相比较,指出它的特色在‘人化’,繁征博引,头头是道。儒家论诗,以‘温柔敦厚’为理想,《乐记》论声音,举和柔直廉粗厉发散啴缓噍杀六种差别,《易·系辞》称‘精义入神’都是最早的‘人化’批评。汉以后道家思想盛行,‘气’,‘神’等观念遂成为文艺理论中的重要台柱。魏晋人论诗文,很少没有受道家思想影响的。应用‘人化’观念者不仅有文学批评家,论书画者尤为显著。同时‘人化’之外,‘物化’或‘托物’也是中国文艺批评的一个特色……司空图《诗品》是‘人化’与‘物化’杂糅,最足以代表‘中国固有文学批评’的一部杰作。看过钱先生的论文以后,我们想到如果用他的看法去看中国的文艺思想,可说的话还很多,希望他将来对于这问题能写一部专书。”*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八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2月第1版,第563页。可惜除了看见钱先生的专论之外,我们并未看到专书的诞生。可见这一问题也正如中国文学批评的特色,只可通过喻象来形象把握和体会,而不可以充分的理论化。
“近取诸身”,中国人习惯以人体结构来看待客体,中国古代文论、美学思想中的许多范畴和命题,如气脉、气象、体面、血脉、韵度、神韵、风骨、形神等等,都来自这一观念。古代文论十分关注文之“体”生气充溢的性质,如风骨、诗眼、气韵生动、活、肌理这些文论概念术语都应该是“体”的范畴延伸与衍生。同时,中国文学批评家喜欢把艺术与人体视为“异质同构”,喜欢用人体结构来比拟艺术结构。这可以视作是与中国文论喜欢以“道”“气”等浑朴性概念把握对象相并行的体认方法,如果说用“道”“气”是以难以具象把握的概念来体悟难以把握的对象的话,那么,用身体概念就是以可以具象化的概念来把握不具确定性的认知对象,体现出由实及虚、由粗而精、由表及里、由具象到抽象的认识倾向。这种“象喻”式的理论表述,不是将理论论域封闭起来,而是通过比拟使得表述更形象化、生动化,构筑起一个可以感知和体悟的理论体系,从而将读者也纳入理论的生成过程中,形成开放的理论论域,增强理论的感悟性与亲合力。
三、体貌与文相:“体”论与人物品藻
魏晋以降的“人物品藻”,是中国即“体”论“文”趋于成熟的一大关节点。在中国的认知模式中,合而观之,宇宙万物本为一“体”,人是一“体”,文章也是一“体”;分而论之,古人又用两两相对的词或范畴来描述这一“体”:比如人之体有“体性(体气等)”与“体形(形体)”之分,或“神”与“形”之别等等,但两者“不即”,也“不离”——文章亦复如此。因为“不离”,所以古人观察、鉴别人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相面”:由人外在之“面相”“体貌”察人内在之性格等等,相面之法,观人术也。这本是始于汉代的人物品藻的做法,而如果说汉人“相”人是为了政治上选拔人才的话,那么更重视风神、神韵的魏晋人则使人物品藻成为了一种审美上的品鉴,而且魏晋人还开始逐步把这种“相”人之术转化为“品”文之法,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这方面的详细分析,参见张法《中国美学史》第三章“魏晋南北朝美学”相关内容,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3—87页。,使以体貌记文相成为古人衡文谈艺的一般家数。
《文心雕龙》大量以“体”论“文”的做法,应受到其时人物品藻的影响,如《练字》篇有云:“夫文象列而结绳移,鸟迹明而书契作,斯乃言语之体貌,而文章之宅宇也”(《文心雕龙译注》,第470页),字为言语之“体貌”,而积字成句、积句成篇,则“文章”本身自然也有由文字构成的“体貌”,这种整体的体貌也可称之为“文象(文相)”。“体貌”一词在汉魏六朝时,使用极广,如《文心雕龙·时序》篇有云:“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文心雕龙译注》,第537页),《汉书·贾谊传》:“所以体貌大臣,而励其节也。”颜注:“体貌,谓加礼容而敬之。”“体貌”虽可解作“尊敬”,而“加礼容”云云则表明“体貌”也需用外在的仪式加以表现。又,《文心雕龙·书记》篇:“状者,貌也。体貌本原,取其事实”(《文心雕龙译注》,第348页),“体貌”虽也解作尊敬、尊重,但也有使“本原”由内而外、由隐而显之意。又,《文心雕龙·练字》篇:“状貌山川,古今咸用”(《文心雕龙译注》,第476页);《文心雕龙·夸饰》:“至如气貌山海,体势宫殿;嵯峨揭业,熠耀焜煌之状,光采炜炜而欲然,声貌岌岌其将动矣:莫不因夸以成状,沿饰而得奇也。”(《文心雕龙译注》,第454—455页)作为动词的“状貌”、“气貌”与“体貌”义近。推而广之,文章制作之法也需“体貌”之,而文章品鉴之法则需“相”之。
当然,《文心雕龙》中提到更多的是山水景物之貌,《神思》篇有“物以貌求”之语,而以“貌”求“物”乃是山水景物文章(诗赋等)的基本套路,如“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文心雕龙译注·辨骚》,第134页)“巧言切状,如印之印泥,……故能瞻言而见貌,即字而知时。”及“体物为妙,功在密附。”以及“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文心雕龙译注·物色》,第552、550、352页)更有:“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及“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文心雕龙译注·明诗》,第143,144页)“赋自《诗》出,分歧异派。写物图貌,蔚似雕画。”(《文心雕龙译注·诠赋》,第168页。)“延寿继志,瑰颖独标;其善图物写貌,岂枚乘之遗术欤!”(《文心雕龙译注·才略》,第561页)
当文章家能“体物”“密附”而用语言成功表现出景物之体貌(写物图貌)时,景物之体貌也就成为文章之体貌。后世唐僧皎然《诗议》即直接以“体貌”论诗:“论人,则康乐公秉独善之姿,振颓靡之俗。沈建昌评:‘自灵均已来,一人而已。’此后,江宁侯温而朗,鲍参军丽而气多,《杂体》、《从军》,殆凌前古。恨其纵舍盘薄,‘体貌’犹少。”*皎然:《诗议》,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南卷“论文意”,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142页。又,《文心雕龙·辨骚》篇云:“《离骚》之文,依经立义;驷虬、乘翳,则时乘六龙;昆仑、流沙,则《禹贡》敷土;名儒辞赋,莫不拟其仪表;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者也。”(《文心雕龙译注》,第126—127页)及“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惊才风逸,壮志烟高。山川无极,情理实劳。金相玉式,艳溢锱毫。”(《文心雕龙译注》,第136页)“金相”论也可谓“文相”论。
除了“物”之“貌”外,《文心雕龙》中还多有“声貌”之论,如:“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遂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子渊《洞箫》穷变于声貌”(《文心雕龙译注·诠赋》,第160、165页)“夫夸张声貌,则汉初已极。”(《文心雕龙译注·通变》,第388页)“王褒构采,以密巧为致,附声测貌,泠然可观。”(《文心雕龙译注·才略》,第561页)
今人一般认为“声貌”可作两解:或作“声音与状貌”,或作“声音的状貌”,而“子渊《洞箫》,穷变于声貌”之“声貌”当作“声音的状貌”解,汉代尤其魏晋以降大量音乐题材的大赋,往往通过繁复的景物描写来状声音之“貌”:形貌是诉诸视觉的,大量音乐赋表明,“不可见的”声音特性是可以通过“可见的”景物表现出来的,可谓“体貌(或状貌、气貌)声音”;而“不可见的”情感等也是可以通过景物之“貌”表现出来的,比如:“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沈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出日之容,‘瀌瀌’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皎日’、‘嘒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穷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虽复思经千载,将何易夺?及《离骚》代兴,触类而长。物貌难尽,故重沓舒状,于是‘嵯峨’之类聚,‘葳蕤’之群积矣……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吟咏所发,志惟深远;体物为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状,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写毫芥。故能瞻言而见貌,印字而知时也。”(《文心雕龙译注·物色》,第552页)又如:“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赞曰:神用象通,情变所孕。物以貌求,心以理应。刻镂声律,萌芽比兴。结虑司契,垂帷制胜。”(《文心雕龙译注·神思》,第359—366页)物、万象、貌、采、声、形、物貌、风景、草木等为一端,感、气、心、情、志、神、志气等为一端,今人囿于西人分析性二分思维法,将这两端割裂开来理解,视前一端为所谓“形式”,后一端为“内容”,即使再怎么强调两端统一,也未得彦和之理。即使从文章法的角度来看,《文心雕龙》以骈体表述,也当互文见义。《物色》篇还说:“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沈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文心雕龙译注》,第548页)“情”既然随物之“容”“貌”而迁并以辞而发,则由辞所描画的物之体貌,可察人之情。上引数语后来多为诗话中的意象、情景论所征引,若云象、景为文之体貌,则由此体貌、文相而察、观其中之意、情,方是“相”文、“品”文、“评”文之正道。
又,《文心雕龙·比兴》篇云:“夫‘比’之为义,取类不常: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文心雕龙译注》,第448页)“诗人比兴,触物圆览;物虽胡越,合则肝胆;拟容取心,断辞必敢。攒杂咏歌,如川之涣。”(《文心雕龙译注》,第450页)“拟容取心”亦可谓“体貌”法。《颂赞》又云:“‘四始’之至,颂居其极。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文心雕龙译注》,第169页)传统的礼乐(诗、舞)交融的活动与身体有直接的关联,特别重视其中的“声”与“容(表情、肢体动作等)”之正,可以说,以音乐、舞蹈艺术结构来“正”人的身体动作进而使“心”正,而这正是古人即“体”言“文”的思想渊源之一。
古人品藻人物、相人之术是有层次性的,一般来说,“貌”或“色”是最外在的层次,所“相”者,“面相”,再进一层则还当观“骨相”。“相”文之法亦复如此,前引陶明濬语即云:“此盖以诗章与人身体相比拟……体制如人之体干,必须佼壮;格力如人之筋骨,必须劲健;气象如人之仪容,必须庄重。”若云观文之“体貌(仪容)”是第一层,则更进一层当相文之“体制”“体式”“体格(类人之‘体干’‘筋骨’)”,对此《文心雕龙》亦有分析:
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故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若总其归涂,则数穷八体。(《文心雕龙译注·体性》,第368页)
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然绠短者衔渴,足疲者辍涂;非文理之数尽,乃通变之术疏耳。故论文之方,譬诸草木:根干丽土而同性,臭味晞阳而异品矣。( 《文心雕龙译注·通变》,第384页。)
今人视以上为西人所谓“风格”论,并以“风格”为所谓“形式特性”,而与所谓“内容”无关。其实,这种支离的理解是不得彦和之要领的。以上也提到了“情性”、“气力”等,“内容”乎?“形式”乎?其实,对应于人之体,相关问题就豁然开朗了:文之“体貌”(犹人之肉、容、色等)对应的是一般所谓的感情、情绪等,对应于文之“体式”(体格,犹人之体格、骨骼等)的则往往被表述为性情、情性、风趣等,而骨肉相连,文之“体貌”与“体式”岂可支离而割肉剔骨乎?以西人之语来表述,我们古人的形式、风格、内容三者是“一气贯通”的,而西人之弊正在支离。明乎此,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前已引《文心雕龙·附会》之语“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有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文心雕龙译注》,第511页),其层次性就昭然可见了:若以“情志”“事义”为“内容”,以“辞采”“宫商”为“形式”,则难免支离;若作层次观,则四者可环环相扣而成一整体。总之,理解古人文体“结构”论,结合人体“结构”来看至关重要。“体式雅郑”也是古代文论重要话题,而这其实与相人之术也是相通的,语云:体貌不端,则心术不正;而文章家欲得性情、心术之正,则当重视文之体式之正,当然,“正”不弃“变”,“通变”之谓也,兹不多论。
前引彦和“貌”论,既有“物貌”之说,也有“情貌”“气貌”之语,非惟人有“情”“气”,物亦有之,天地万物、人文制作等皆一气化成。人之情、气不可见,物之情、气乃至“道”亦不可见,也需“体貌”以见。《文心雕龙·原道》赞曰:“道心惟微,神理设教。光采玄圣,炳耀仁孝。龙图献体,龟书呈貌;天文斯观,民胥以效。”(《文心雕龙译注》,第102页。)若云“道”为文之“体”,则“文”者,“道”之“貌”也。《夸饰》云:“夫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神道难摹,精言不能追其极;形器易写,壮辞可得喻其真。才非短长,理自难易耳。故自天地以降,豫入声貌,文辞所被,夸饰恒存。虽《诗》、《书》雅言,风格训世,事必宜广,文亦过焉”(《文心雕龙译注》,第452页)。辞若得喻形器、万物之真,则近乎“道”。《诠赋》云:“拟诸形容,则言务纤密;象其物宜,则理贵侧附。斯又小制之区畛,奇巧之机要也”(《文心雕龙译注》,第163页),用词多化用《易》语,文章若能“象其物宜”则也可以物貌见道。
不管怎么诠释,大致说来,体之貌、文之相(象),首先是感性而非知性把握的对象,而人把握体貌、文相的主要感官是耳目,《文心雕龙》《情采》篇有“声文”“形文”“情文”之“三文”说,前两“文”就是诉诸耳目的体貌、文相的两个方面,而统领《文心雕龙》全书的首篇《原道》其实也贯穿着这三“文”之思路: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锽。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文心雕龙译注》,第96页。)
“形立则章成”者,“形文”也;“声发则文生”者,“声文”也;天地万物皆以“形文”“声文”显现其貌;万物之形文、声文又皆是“道之文”,或曰“道”以万物之形文、声文而见;而作为“天地之心”的人,又以“言”之形文、声文表现天地万物之“文”,而“道”在其中;而仰观、俯察之法,同样也是“相”文之法。刘勰在统领《文心雕龙》全书的末篇《序志》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思路:
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岂取驺奭之群言“雕龙”也?夫宇宙绵邈,黎献纷杂;拔萃出类,智术而已。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夫有肖貌天地,禀性五才,拟耳目于日月,方声气乎风雷;其超出万物,亦已灵矣。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文心雕龙译注》,第602页。)
人以耳目“肖貌”万物,也主要以耳目把握天地万物,并以语言形文、声文之“制作”表现天地万物——此即文章也,而“道”在其中,“性”在其中,“情”在其中。人以文章制作而参天地之化育,并因而不朽——这也是刘勰的基本文章价值观。
总之,“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文章等人文制作参天地之化育,与天地万物、人之身体等皆一气化成,故而一气贯通,异质同构,而品文之法与相人之术及对天地万物的仰观俯察之法,也道通为一。中国古代的以“体”论文及“象喻”批评等,体现了中华文化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人文观、生命观、价值观等,对于中华美学精神的当代建设具有积极意义,我们理应加以重视。
[责任编辑:郑迦文]
党圣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论、文艺学、传统思想文化。
I206.2
A
1002-6924(2016)12-041-0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