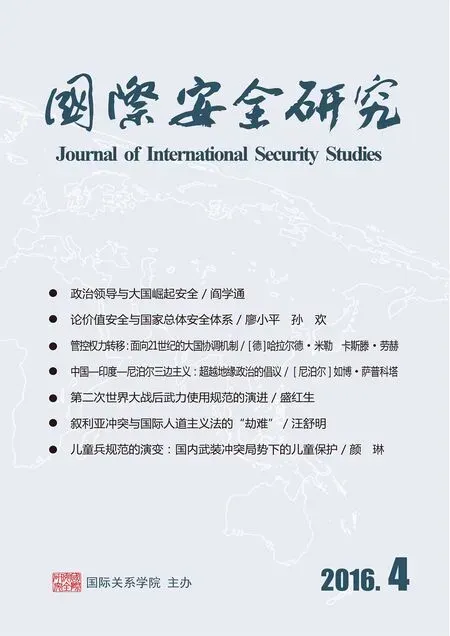论价值安全与国家总体安全体系*
廖小平 孙 欢
论价值安全与国家总体安全体系*
廖小平孙欢
【内容提要】 人的普遍性决定了价值的普遍性,人的特殊性决定了价值的差异性和多元性。价值的多元性和差异性正是引发不同价值体系安全问题的本质因素。狭义的价值安全是指一个国家、地区或民族、阶层的价值观念没有危险、不受威胁,即观念化价值体系安全。广义的价值安全是实在性价值体系安全与观念化价值体系安全(价值观安全)的统一。国家价值安全由国家内的价值安全和国家价值的安全构成,前者以多元价值主体的价值认同为重要表征,后者以国家的价值主权为重要表征。就其对国家总体安全体系的意义而言,价值体系是元文化,且观念化价值体系安全是文化安全的一部分,因而价值安全是文化安全的核心,也是元文化安全,必然地成为国家总体安全体系的重要构成要素;价值安全又意味着国家总体安全体系所有构成要素的价值目标、价值规范的安全,因而又是国家总体安全不可或缺的柔性支撑。
价值安全;国家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国家总体安全体系
一 价值安全释义
在我们讨论“价值安全”“国家安全”等安全概念之前,首先必须明确“安全”具有何种含义。对于安全的词义,中文里最基本的含义就是“没有危险,不受威胁”,而英文“security”的意思包括“没有危险、焦虑”和“提供安全保障,使其免除危险或焦虑”两层含义。尽管英文关于“安全”的解释相比中文多了“提供安全保障”“免除危险或焦虑”之义,但是在这两种文化背景中安全的基本含义是一致的,即没有危险,不受威胁。因此,安全反映的是一种客观状态,即安全主体的生存状态没有危险,不受威胁。美国学者戴维·鲍德温(David Baldwin)认为,安全是指这样一种状态:已经获得的价值被损坏的可能处在较低的水平。*David A. Baldwin, “The Concept of Security,”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3, No.1 (January 1997), pp. 5-26.但是,英文中安全的“免除焦虑”之意实际上已经超然于客观状态,而是一种来自主体的主观感受。这种感受我们不能笼统地称之为“安全”,而是“安全感”。
要从哲学上来研究安全问题,就十分有必要对客观上存在的安全与主观感受的安全加以区分。主观感受的安全是主体对自身安全状态的非理性的自我体验与经验性自我判断,也即“安全感”。或者说,安全感是这样一种主观的心理反应——主体免除了对受到威胁或危险的担忧和焦虑。安全感不同于安全,它们的区别在于:一是安全感是一种主观体验,而安全是一种客观状态;二是安全感是仅针对安全主体自身、而非针对其他主体而存在的;三是安全感以非理性的自我体验为主要内容,以经验性自我判断为次要内容;四是安全感与安全不存在固定的正比或反比关系。*刘跃进:《从哲学层次上研究安全》,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第59-64页。“安全”与“安全感”的关系,就如同哲学上“客观”与“主观”的关系,不能混为一谈。安全感可以是安全主体对自身安全状态的真实反应,即主客统一;也可以是对自身安全状态的错误反应,甚至是主观臆断或情感偏见,即主客分离。因此,安全是安全主体在客观上没有危险、不受威胁的状态。而这里所说的主体,是指具体的社会主体,包括个体、集体以及国家。
而在厘清什么是“价值安全”之前,我们还必须明确“价值”的含义。“价值”这一词语,可以说在人类现存的各种语种中都是一个高频词汇,也是一个涉及多学科、多领域的概念。从历史上看,“价值”起初等同于有用物,常常和商品、财富联系在一起,也因此受到了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亚当·斯密(Adam Smith)、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和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等古典经济学家的青睐。“价值”概念成为哲学式的抽象,要归功于德国哲学家赫尔曼·洛采(Rudolf Hermann Lotze)、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以及新康德主义哲学家厄恩斯特·卡西勒(Ernst Cassirer)将“价值”引入哲学领域。随着价值问题在现代社会的凸显以及哲学价值论或价值哲学研究的发展,哲学领域也出现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关于价值的各种界定。迄今为止,有代表性的关于价值本质的观点有这样五种:实体说、属性说、关系说、意义说和存在论。*廖小平:《价值观变迁与核心价值体系的解构和建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13页。实体说和属性说脱离人去界定价值的本质,其不足是显而易见的;意义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归结为关系说,它们虽然较好地解决了主体需要与客体属性相统一的问题,但对价值冲突和价值变迁缺乏解释力。只有存在论从作为目的的人存在本身解释“价值”,才能更加贴切、合理地抓住了价值的属人本质。存在论主张的是“在价值与存在的关系中把握价值”,在哲学意义上“价值就不是一种固定存在着的某种抽象实体,甚至也不仅仅是关系,而是人的存在(生存)以及对人的存在(生存)所具有的意义。”*吴向东:《重构现代性——现代社会主义价值观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26页。不难看出,价值是一个以人为本的哲学范畴,它意味着一种以主体——人作为尺度的主客体统一状态。人是具体的、历史的,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价值不同于真理,真理总是一元的,价值既是一定社会的共同指向,具有一元性,同时又是受社会历史环境的影响且因人而异,具有多元性。
由于“价值”本身就是一个颇具争议的理论范畴,学界对价值的内涵以及价值的“一元性”和“多元性”的看法也就不尽一致。从价值学的角度来看,价值的内在规定性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在个体层面,价值是具体个人所形成的特有的人生理想与其在现实生活中所获得的人生意义。第二,在社会层面,价值是特定社会(国家或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共同指向的一种社会价值目标。而这两个层面的内容又包含着三种基本关系:一是价值的理想形式和现实内容的关系,前者是一般的、绝对的、本质性的,后者则是特殊的、具体的;二是价值内容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前者代表了个人对社会趋同化的价值期待,后者表现为社会的外在化价值在具体个人身上的内在化和个体化;三是目的性价值和工具性价值的关系,前者是根本性的,决定工具性价值的内在性质,后者则是目的性价值得以确立和实现的基本条件。按照这一逻辑,价值的一元性指的就是个体或社会在终极价值目标上的统一性或一致性以及以共相形式表现出来的价值普遍性;价值的多元性则是个体或社会在价值目标追求的具体过程中的多层次性,实现价值的具体途径、方式与手段的多样性以及基于对共相价值的认可基础之上的各特殊价值表现形式的差异性。*万俊人:《论价值一元论与价值多元论》,载《哲学研究》,1990年第2期,第33-40页。由此可见,对价值内在规定性的认识,仅仅在一元性和多元性之间做某种机械的片面性选择,很容易陷入机械目的论或狭隘经验主义的认识误区。抽象地强调价值一元论和片面地强调实用主义价值多元论,都是不审慎的。
既然已经明确:价值的一元性与价值的多元性并不矛盾,价值的普遍性和价值的特殊性自然也可并存。前文指出,价值是以主体——人作为尺度,而人是具有普遍性和共同性的,这是人超越动物的核心特性之一。马克思曾说:“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人比动物越有普遍性,人赖以生活的无机界的范围就越广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5页。还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普遍性和共同性不仅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之中,更重要的是它还作为社会实践关系存在于人的现实当中。然而,现实的人也是具体的、历史的,具有社会性和阶级性,是具有特殊性的人。因此,毛泽东在谈及人性问题时十分肯定地指出,“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0页。因为人是价值的尺度,人的这种特殊性也就决定了现实的人在价值客体、价值目标、价值规范和规则上具有差异性。总的来说,人作为类的普遍性和共同性,决定了价值的普遍性和共同性;现实的人的特殊性和差异性,决定了价值的异质性和多元性。
尽管也有人提出人类确实存在某些普遍共享的客体、普遍追求的目标和结果以及普遍遵守的规则和规范,但是普遍共享的价值客体并不意味着多元价值主体必然会形成共同的目标和结果,普遍追求的价值目标和结果也并不意味着多元价值主体必然会遵守一致的行为规则,且即使存在普遍的行为规则和规范,也极有可能因为多元价值主体之间权利和责任的不平等而失效。*李德顺:《怎样看“普世价值”?》,载《哲学研究》,2011年第1期,第3-10页。在这个意义上,即使我们承认和肯定普世价值的存在,多元价值主体在价值目标、价值规则以及制定规则的权力和标准上仍是可以存在矛盾和冲突的。再加上价值本身具有的异质性和多元性特点——在阶级社会甚至是以阶级对立的方式表现出来,在现实社会中,尤其是在不同阶级、不同民族国家之间,价值冲突、价值矛盾、价值对立的存在是必然的、现实的。换言之,如果价值是绝对一元性的,即只存在绝对终极意义上的价值目标指向的统一性、目的论意义上的一致性和普遍表现形式上的共同性,不同价值主体之间便不会存在价值冲突、价值矛盾、价值对立。然而,现实是价值的一元性是相对的,价值还具有多元性,即其实现过程具有层次性、实践手段具有多样性、特殊内容结构具有差异性,这些特性使价值冲突、价值矛盾、价值对立的存在成为可能。
结合前文对“安全”的界定和对“价值”问题的讨论,价值安全就是特定价值主体所追求和实现的价值体系没有危险、不受威胁。价值安全问题起因于价值的多元性,正是不同价值主体在价值的实现过程上的层次性、实践手段上的多样性、特殊内容结构上的差异性使得对价值安全问题的讨论更有意义。从价值的一元性来看,人类社会具有普遍性和共同性的价值体系,呈现出同质性的特点;但从价值的多元性来看,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地区或民族在价值的实现过程上具有层次性、实践手段上具有多样性、特殊内容结构上具有差异性,这些特点使得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地区或民族、阶层的价值体系出现了分化,甚至是冲突和对立,因而呈现出异质性的特点。价值安全问题因此就有两种表现形式:
第一,在同一个历史时期,一个国家、地区或民族的价值体系受到来自另一个在价值实现过程、实践手段和特殊内容结构上相异的国家、地区或民族、阶层的价值体系的危险和威胁。如从现代社会政治的发展进程来看,“民主”确实是人类社会一种具有普遍性和共同性的价值。然而,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在中国是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主要的实践方式;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是资产阶级民主,在西方国家是以选举制度为主要的实践方式。因此,美国将所谓的“美国式民主”一厢情愿地向全世界推销,实际上是意图通过“民主输出”实现异己价值体系的美国化。
第二,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同一个国家、地区或民族的新生价值体系对旧有价值体系的危险和威胁。在中世纪的欧洲,上帝是绝对价值,其他一切价值都是上帝价值的衍生品;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则提倡和推崇人的价值,用理性取代了上帝。从教会对启蒙思想家的打压和迫害来看,他们确实意识到了,以“人”为核心的新生价值体系对以“上帝”为核心的价值体系是致命威胁。
不难推断,“价值安全”问题的成立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即存在着两个或两个以上在价值实现过程、实践手段和特殊内容结构上相异且能彼此交流的价值体系。如果人类社会只存在一个绝对的、不变的价值体系,甚至是只存在一个终极的一元价值,或者是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彼此孤立的价值体系,那么价值冲突、价值矛盾将是难以存在的,至多能产生单一性的、偶发性的价值冲突、价值矛盾。但实际情况是,在当代社会,价值主体已从传统的一元走向多元。*江畅:《论价值冲突》,载《人文杂志》,1994年第2期,第24-29页。价值主体的多元化是激发价值实现过程的层次性、实践手段的多样性、特殊内容结构的差异性的根本性因素,或者说价值主体的多元化是引发价值安全问题的根源性因素。以中国社会为例,传统的中国社会价值主体便是社会整体(通常就是国家),价值客体只有在符合社会整体的需要时才是有价值的,这种情况几乎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之前。而且,传统社会的国家通常处在一种封闭的状态,这个唯一的价值主体坚守着自己鲜有变动的价值体系。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价值主体开始出现分化,除了国家这一价值主体,企业、社会组织、家庭以及个人也成为了价值主体,且在全球化浪潮中,人类整体也成为一种价值主体。多元价值主体自然便有了多元价值体系,在不同的利益和需要的背后也自然产生了价值体系的冲突、矛盾和对立,价值安全问题才会成为显性问题并引起价值主体的重视。
若从国家安全的层面来审视的话,没有危险和不受威胁的价值体系只能是整个国家的价值体系,而不能仅仅指个体、家庭、企业和社会组织所追求的价值体系。国家价值体系的危险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国家总体的价值体系和作为社会原子的个体、家庭、企业、社会组织的价值体系之间存在较大分歧,即国家主导价值体系与社会其他价值体系不一致,甚至是存在冲突、矛盾和对立。这种情况较为典型的是出现在社会大变革或转型阶段。在中世纪之前,许多欧洲国家尤其是西欧国家受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滋养,以“德性”为中心的道德价值体系占国家价值体系的主导地位。然而,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由于失去了强有力政权的统治,封建割据带来的频繁战争使西欧进入了所谓的“黑暗时代”——中世纪,罗马教皇在西欧渐渐取得了帝国般的统治地位,“上帝”也逐渐成为各国价值体系的中心,甚至成为了绝对的、终极的一元价值。而随着文艺复兴和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人文价值和科学价值获得了生长空间,“上帝”作为绝对价值被赶下神坛。第二,一个国家的价值体系与其他国家的价值体系之间存在差异、冲突或矛盾,前提是国家间彼此存在交流,不管这种交流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实施的民主输出,即“文化帝国主义”。
因此,国家层面的价值安全就是指一个国家的价值体系在价值实现过程、实践手段和特殊内容结构上没有受到国内其他非主导价值体系以及其他国家的价值体系的威胁。国内其他非主导价值体系带来的威胁通常有两种类型:一是个体或社会群体基于非正当需要或受异端学说、邪教影响产生的价值体系对国家主导价值体系的挑战;二是社会变迁或转型产生的新价值体系对国家原有价值体系的冲击。其他国家的价值体系带来的威胁也有两种类型:一是一个国家的价值体系受到另一个或几个国家的强制价值输出的侵蚀;二是基于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一个国家或国家的精英阶层有意识地引入别国的价值体系,这种引入自然会成为原有价值体系的威胁。价值安全的威胁通常情况下分别是指国内威胁和国外威胁的第一种类型的威胁。至于后两种来自新价值体系和引入别国的价值体系产生的威胁,只有国家层面的主导价值体系认为其是危险的、错误的,并拒不接受,才能形成对主导价值体系的威胁;如果主导价值体系能基于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理解并接受新价值体系和别国的价值体系,那这种情况只能视为主导价值体系的自我更新、自我完善,因而它们不构成一般意义上的价值安全威胁。
二 国家总体安全体系构成
安全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要,也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关于国家安全,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国家安全就是国家处于没有危险的客观状态,也就是国家既没有外部的威胁和侵害,又没有内部的混乱和失序的客观状态。*刘跃进:《论国家安全的基本含义及其产生和发展》,载《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第62-65页。从价值学的角度来看,对国家造成威胁和侵害或使国家陷入混乱和失序的危险因素,除了上文提到的与国家主导价值体系在价值实现过程、实践手段和特殊内容结构上具有异质性的其他价值体系之外,还包括信奉这些异质性价值体系的人们所持有的价值观。价值观通常是指人们基于生存、发展和享受的需要,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关于价值的总观点、总看法,是人们的价值信念、信仰、理想、标准和具体价值取向的综合体系。*李景源、孙伟平:《价值观和价值导向论要》,载《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第46-51页。这个以价值信念、信仰、理想、标准和取向为核心内容的综合体系,是人们对现实价值关系的评价性反映的总和,它一经形成便可以对人们的社会生活实践产生反作用——具体表现为对人们的价值活动发挥着目标选择、情感激发、评价标准以及行为导向的功能。社会价值观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核心,也是社会文化体系的灵魂,既可以成为一个社会的黏合剂,又可以演变成一个社会的离心力。因此,多元的且相互冲突、对立的价值观也是国家安全的重要隐患因素,价值观安全也就构成了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
由于价值观是人们对于价值的总观点、总看法,它具有明显的主体性,即由于所处社会历史条件、文化传统、生存状况、生活经历和实践方式的不同,尤其是利益、需要、能力和素质的不同,不同国家、地区或民族、阶层的价值观总是不尽相同的,不同个体的价值观也是各异的。这就必然使有些价值观是科学、合理、先进的,有些价值观则违背了自然和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有些价值观背离了基本的科学精神和科学原理,有些价值观在价值取向和价值标准上是非理性、自私自利的,还有些价值观甚至是反社会的、不文明的。价值观安全不仅是指科学、合理、先进的价值观没有受到背离科学精神、违背自然和社会历史规律的价值观的危险和威胁,也指特定价值主体(国家、地区或民族、阶层)的价值观不受其他价值主体的价值观的危险和威胁。
价值观是基于人们需要而形成的关于价值的总看法、总观点,也就是意识化、观念化的价值体系。价值观安全因而也就是意识化、观念化的价值体系的安全,是一个国家、地区或民族、阶层的价值信念、信仰、理想、标准和取向等的安全。有不少研究者在意识形态安全、文化安全中都提及了价值观念安全,实质上这是一种狭义的价值安全,即观念化价值体系安全——亦或价值观安全。作为总体国家安全重要内容的价值安全是一种广义的价值安全,既包括客观层面、实在层面的价值安全,也包括主观层面、意识层面的价值安全。
因此,广义的价值安全是实在性价值体系安全与观念化价值体系安全的统一。它包括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国家或民族的核心价值体系——包括实在性价值体系与观念化价值体系——不受其他国家或民族的价值体系的危险或威胁,始终保持其在该国家或民族价值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二是基于核心价值体系形成的社会主导价值观始终发挥对多元价值观的引领和导向作用;三是社会主导的观念化价值体系与实在性价值体系的关系是主客一致的关系。换言之,社会主导价值观是对实在性的国家核心价值体系科学、正确的反映,是一种符合自然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看法、观点。
不论是从狭义还是广义上的价值安全,安全都是国家最为根本的利益,国家安全的本质便是国家最根本利益的调适。人们关于国家安全的讨论基本是集中在国家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领域,这被学者们称之为传统的国家安全。近年来,随着国家安全外延的拓展,“非传统的国家安全”“新国家安全”等成为了新的国家安全形式。多数人已经接受这样一种分类——国家安全包括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前者强调军事安全,将军事力量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最主要手段;后者强调安全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信息、科技、环境以及人类安全等多个维度,重视除军事力量之外的其他手段对于国家安全的作用。
显然,国家安全不能特指某一安全领域,它是由涉及国家根本利益的多领域的安全构成的安全体系。传统国家安全由于过分强调军事手段,容易使国家间关系因为缺乏安全感而陷入“安全困局”,这也许是人们提出“非传统安全”的直接原因。从传统安全到非传统安全,安全出现了三种形态的转变:一是从主权安全到人权安全的转变;二是从国家安全到全球安全的转变;三是从军事安全到社会安全的转变。*刘胜湘:《国家安全观的终结?——新安全观质疑》,载《欧洲研究》,2004年第1期,第1-16页。这种转变确实具有时代必然性与合理性,其根源在于信息化、全球化的深入使得传统安全的高阶政治问题同非传统安全的经济、社会、文化等低阶政治问题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但在现实层面,任何国家都不会放弃军事安全。因此,非传统安全并不能从根本上取代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的意义是从客观上解决传统安全因其内在逻辑矛盾所致的“安全困局”,缓解信息化、全球化对传统安全的冲击;主观上满足人们用新思维对国家安全的理解和界定。
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有学者曾根据国家安全的史前内容、源生内容、伴生内容和派生内容,将国家安全概括为国民安全、领土安全、经济安全、主权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和信息安全10个要素。*刘跃进:《试论当代国家安全的10个方面》,载《国家安全通讯》,2001年第11期,第37-39页。后来,该学者又将社会安全与资源安全列入国家安全要素体系,并将领土安全改为国域安全,形成了包含12个要素的国家安全体系。*刘跃进:《为国家安全立学》,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这种学术上的探索,为国家安全战略的完善起到了一定的先导作用。在2014年4月召开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及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习近平:《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新华网,2014年4月15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4/15/c_1110253910.htm。也就是说,国家安全是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有机统一,而这里提到的“11个安全”则是构成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因素。
根据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讲话精神,从安全范围上看,国家安全包括内部安全和外部安全;从国家的构成要素上看,国家安全包括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从涉及国家根本利益的相关领域上看,国家安全包括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从国际关系上看,国家安全包括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尽管“人民安全”或“国民安全”被置于前列,但在中共中央对国家安全体系构成要素的首次集中论述中却未将其纳入进来。有学者指出,12个要素中的“国民安全”——也叫“人民安全”便没有被纳入国家安全体系之中。*刘跃进:《大安全时代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国家安全重要讲话中的哲学思想》,载《北京日报》,2014年5月19日,第17版。因此,国家安全体系应是指由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国民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及核安全等要素基于国家生存和发展的目的而形成的有机整体。从要素的性质上看,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及核安全是“物的要素”的安全,文化安全和国民安全是“人的要素”的安全。国家总体安全体系必然是“物的要素”的安全和“人的要素”的安全的统一。在这个意义上,价值安全也包括“物的价值”的安全和“人的价值”的安全。因此,价值安全不能简单地归纳为国家安全体系的一种构成要素,而是贯穿于国家总体安全的“12要素”中。
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目前中国国家安全的内涵与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国家安全的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也都要宽广,国家所面临的内外部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也都要复杂。从国内形势来看,中国目前已经进入了改革的深水区和攻坚期,社会矛盾多发频发;从国外形势来看,全球化浪潮使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策略更易实施,从而导致中国的国家安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险——一是改革发展的稳定大局被破坏的危险,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被突然打断的危险,三是人民民主专政国家被侵略、被颠覆、被分裂的危险。而来自军事方面的危险变得越来越不那么明显,来自经济、社会、文化——尤其是价值方面的危险却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入。以美国的“民主输出”为例,“民主”作为一种政治价值目前在全世界几乎已成为一种统一性的价值目标,也似乎具有共同性的普遍表现形式,但“美国式民主”绝非普世价值,因为它在实现过程、实践手段、特殊内容结构上都与社会主义民主有着明显区别。因而在面对美国的“民主输出”过程中,价值安全问题并非是别国与美国在民主的价值目标、普遍表现形式上存在分歧,而是美国将特定地理、历史、文化环境下形成的“美国式民主”的实现过程、实践手段和特殊内容结构强加给别国,也包括将其特定环境下形成的价值观念强加给别国。这是一种隐匿的“温水煮青蛙式”的侵略与颠覆,比粗暴的领土侵占、赤裸的政治干预更具危害性。
近些年来,学界和国际政治现实中流行着一些关于“世界主义”和“颜色革命”的论调,这便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价值输出漂洗中国文化,以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根基。起源于古希腊斯多葛学派的“世界主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曾一度成为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侵略和掠夺殖民地、反对第三世界国家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的工具,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殖民地国家的独立有所消沉。近来,又有人将“世界主义”抬出来,并将之等同于“全球治理”“世界大同”,宣扬“人权高于主权”“人类利益高于国家利益”。这种论调几乎就是古希腊和近代“世界主义”的现代翻版,它从一开始就是为满足世界帝国的需要。*吴兴唐:《“世界主义”与“颜色革命”》,载《红旗文稿》,2015年第8期,第38页。“颜色革命”实际上也是“世界主义”的一种表现,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高举“民主化”的旗号、颠覆别国政权的“和平手段”。以一些中东国家为例,如叙利亚、伊拉克等,西方国家通过“中东马歇尔计划”使这些国家逐步接受了美国的价值体系与政治原则,并在形式上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与选举制度,实现了军队的国家化,但实际上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很多都是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军人或政客,形式上的民主缺少内涵的民主精神。美国之所以在全球范围内开展所谓的“颜色革命”,实际上是通过价值输出来巩固自身的国家利益——在中东表现为掌控中东的石油资源和地缘政治意义。
不管是中东、非洲,还是在乌克兰发生的“颜色革命”,美国的价值输出似乎并没有真正开花结果,仅仅给这些国家带来了政府专制和堕落腐败,甚至是政权颠覆和民族分裂。美国曾经引以为豪的“颜色革命”终将褪色,它既无法彻底改变别国的颜色,也无法帮助美国实现既定的政策目标。*史澎海、彭凤玲:《美国和平演变战略与中东“颜色革命”》,载《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第113-118页。随着中国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美国似乎又开始抓紧了诱导中国开展“颜色革命”,将其标榜的以“美国式民主”“美国式人权”为主要内容的价值体系向中国输出,近年来网络更成为了美国输出观念化价值体系的重要手段。这种观念化价值体系输出可以称为“价值转基因”工程。美国所信奉的价值体系便是美国文化的遗传基因,价值输出的意图就是要将美国文化的基因注入中国文化,使中国文化具有美国特征,甚至成为美国文化的“衍生物”。这种“价值转基因”工程给中国国家安全造成的威胁是隐秘的、持续的、温和的,比直接的军事威胁、政治威胁更可怕。
国家总体安全的“12要素”均存在价值安全问题,也都有可能受到其他国家价值输出的威胁。物的价值(如政治价值、经济价值、国土价值和科技价值)层面的安全,人的价值(如文化价值、国民价值)层面的安全,或者自然价值(如生态价值、资源价值)层面的安全,社会价值(如国民价值、政治价值、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层面的安全,属于实在性价值体系的安全。观念化价值体系的安全则是围绕上述价值领域形成的价值观念的安全,如政治价值观、经济价值观、生态价值观、文化价值观的安全等。西方国家的价值输出既有实在性价值体系的输出,也有观念性价值体系的输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价值观变迁,其中愈演愈烈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正与社会主导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产生激烈的价值观冲突,其中便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价值观输出在推波助澜。
“12要素”层面的安全是具体领域的国家安全,而价值安全贯穿“12要素”之中,是抽象层面的国家安全。也正是这个原因,要素层面的国家安全威胁更容易被识别,从要素层面来构建国家安全体系也更精准、更有效;抽象层面的国家安全威胁更难被识别,从抽象层面来构架国家总体安全体系也更复杂、更困难。如果将要素层面的国家安全看作是一支军队拥有的坚船利炮,那么抽象层面的价值安全便是这支军队的“军魂”。也正是价值安全将“12要素”层面的安全串联成了一个紧密的有机整体。因此,中国必须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国家总体安全体系,具体来说就是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家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道路。只有构建出一个完善的国家安全体系,才能统筹应对多种安全威胁、系统谋划国家安全工作,实现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安全。
三 价值安全对国家总体安全体系的意义
价值安全在国家总体安全体系中到底居于何种地位,或对国家总体安全有何意义?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难免会让人产生这样的理解:价值安全是国家文化安全的一部分。如有学者提到,文化安全最主要包括语言文字安全、风俗习惯安全、价值观念安全和生活方式安全。*刘跃进:《解析国家文化安全的基本内容》,载《北方论丛》,2004年第5期,第88-91页。这里的价值观念安全指的就是观念化价值体系的安全,而不是价值安全的全部内容。在学术界和国际政治中,文化安全确实也在理论上、实践上都受到更广泛的关注,其系统的论述可以追溯到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的“文化多元性”理论和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学术界就文化安全的认识仍未形成一致,存在广义与狭义两种界定。国家文化安全的狭义解释即“国家文化的安全”(security of national culture),通常特指作为一种政治实体的主权国家的国家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基本政治制度、人民群众的政治认同以及国家形象等主要文化要素免于内部或外部敌对力量的侵蚀、破坏和扭曲,从而确保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在其主权范围内也包括在国际上享有比较高度和一致的合法性认同;国家文化安全的广义解释即“国家内的文化安全”(cultural security in a nation-state),指的是主权国家的主流文化价值体系以及建立于其上的意识形态、社会基本生活制度、语言符号系统、知识传统、宗教信仰等主要文化要素免于内部或外部敌对力量的侵蚀、破坏和颠覆,从而确保主权国家享有充分完整的文化主权,具备同国家政治、经济发展协调一致、良性互动与不断创新的文化系统,并在人民群众中间保持一种高度的民族文化认同。*石中英:《论国家文化安全》,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第5-14页。因此,作为国家总体安全体系构成之一的文化安全既是国家文化的安全,也是国家内的文化安全。
不论是实在性价值体系,还是观念化价值体系,价值体系本身都是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化系统的核心部分。因此,按照上文对国家文化安全的理解,国家价值安全也包括了国家价值的安全和国家内的价值安全,前者实际上指的就是观念化价值体系的安全,后者则包括了观念化价值体系的安全与实在性价值体系的安全。有研究者也提出,国家文化安全语境下的文化包含三个方面,即意识形态、民族文化、公共文化,与此对应,国家文化安全由意识形态安全、民族文化安全、公共文化安全构成。*韩源:《国家文化安全引论》,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6期,第90-94页。国家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符号系统、宗教信仰等文化要素都是建立在一定价值体系的基础之上,即有着统一性的价值目标。意识形态是围绕政治价值体系衍生而来,民族文化是围绕民族价值体系衍生而来,公共文化是围绕公共价值体系衍生而来。价值体系是元文化,意识形态、民族文化、公共文化是衍生文化——元文化的具体化、丰富化产物。因此,抛开文化的这些具体内容,文化安全的根本就是价值安全。*由于篇幅限制,对于价值安全与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等概念的区别和联系,笔者将另文讨论。
对价值安全乃至文化安全的强调,是对传统国家安全观的“唯物”情结——过分重视国家安全的“物的要素”——的一种弱化,而把作为国家主体的人民的安全强化,将国家的“物的要素”的安全和“人的要素”的安全结合起来,这个结合物便是国家总体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对“人的安全”的充分关注,不但体现了国际社会新的普遍诉求,更重要的是其站在时代高度对国民安全与国家安全的辩证联系进行了科学界定。*黎宏:《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变革性特征》,载《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第153-157页。虽然上文提到的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国家安全构成要素仍是属于“物的要素”的安全,但相比传统安全观只强调政治安全、军事安全而言,国家安全的外延有了较大的、合理的、顺应时代要求的扩展;更值得肯定的是文化安全、人民安全等“人的要素”的安全被纳入了国家总体安全体系。价值安全的提出本质上也是对“人的要素”的安全的肯定,是突出价值对人的存在及对人的存在的意义之重要地位。对既定价值体系的维护,本质上就是价值主体对自身存在和存在的意义的维护。从国家安全的层面来看,捍卫国家价值安全,本质上便是对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维护。
国家价值的安全有一个重要的表征,即国家内部的各价值主体——可以是构成国家的各民族,也可以是包括个人、家庭、企业、社会组织在内的各社会基本单元——具有高度一致的价值认同。而价值认同是一种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即一种价值选择能否被人民群众所认同,不能单凭抽象的理论说教,而是要看它是否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需要。*何隆德:《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几个问题》,载《湖湘论坛》,2012年第6期,第157-160页。这种高度一致的价值认同,在社会生活中就表现为各价值主体在价值观上的同一性。从现代民族国家模式的三个组成部分:国家观念、国家制度和物质基础来看,国家观念是否得到公民的广泛认同是涉及国家安全的中心问题。英国国际安全问题专家巴里·布赞(Barry Buzan)指出,除非国家观念已经深深地扎根于人民的思想中,否则,作为一个整体的民族国家就会丧失牢固的根基。*[英] 巴里·布赞:《人、国家与恐惧——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安全研究议程》,俞可平、闫健、李剑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82页。价值认同便是这种应该扎根于人民思想中的国家观念,“藏独”和“疆独”分子在国际反华势力的煽动下搞的暴力恐怖活动、民族分裂活动,在国家观念上的表现便是价值观对立。这种对立表现为,党和国家以及广大人民群众都高度珍视爱国主义传统,而“藏独”和“疆独”分子却数典忘祖地推崇受国际反华势力操控的分裂主义逆流。
国家内的价值安全也有一个重要的表征,即国家内部的各价值主体既具有普遍共享的价值客体、普遍追求的价值目标和结果以及普遍遵守的价值规则和规范,也具有高度一致的价值认同,而且这些价值客体、价值目标、价值规则、价值认同没有受到来自其他国家的威胁。以民族为例,中国有56个民族,各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但是在长期相互交流融合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凝聚产生了基于共同的民族利益的“多元一体”的价值体系。换言之,价值安全意味着各民族尽管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但就整个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机体而言,各民族却有着共同的遗传基因,这就是在历史长河中结成的共有价值体系。
国家内的价值安全也意味着国家具有充分且完整的价值主权。所谓价值主权,是国家对价值体系进行自主选择、自主安排的权力,是国家根据本国的文化传统和现实需要凝练和宣传国家的核心价值体系,并以此作为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改革和发展的价值指引。试想如果一个国家不能自主地凝练和宣传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再怎么高谈阔论价值安全也是徒劳,国家总体安全构成要素的国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及核安全等,也终将是盲目的、无方向的。在这个意义上,价值体系安全不仅仅是国家文化安全,更是国家总体安全构成各要素的价值目标、价值规范的安全。因此,相比传统安全观将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视为国家安全的全部内容来说,价值安全的提出丰富了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
前文已经强调,虽然作为类存在的人具有普遍性和共同性,也使不同国家的人有着共同的价值客体,但却因为现实的人同时具有特殊性和差异性,决定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人在价值实现过程的层次性、实践手段的多样性、特殊内容结构的差异性。社会主义中国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是“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尽管在语词上中国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价值目标、普遍表现形式上具有相似性,但其实质是有所区别的。就“民主”这一价值目标而言,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内容是人民当家做主,是人民主权;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内容是多党或一党,是资产阶级主权。人民民主专政与资产阶级民主政体不可同日而语,它们有着根本性区别。因此,各国在国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领域必然地在价值的实现过程、实践手段和特殊内容结构上存在冲突,甚至是不可调和的价值矛盾,最终可能升级为军事冲突,危及国家总体安全。从这个意义上讲,价值安全并不是什么新的安全,仍属于传统国家安全的范畴。
值得注意的是,价值认同作为国家价值的安全之表征与价值主权作为国家内的价值安全之表征,并不是绝对的、唯一的。价值认同也可以成为国家内的价值安全之表征,价值主权同样也可以成为国家价值的安全之表征。因为,获得各民族广泛认同的社会价值观,实际上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内在凝聚力、向心力和团结力,在国际交往中就代表着国家软实力,从而彰显国家的价值主权;而国家基于价值主权所凝练出来的核心价值体系,通过获得多元价值主体高度一致的价值认同,便可以真正成为国民的共同的价值观。正如有学者认为,文化安全乃是一种柔性安全,属于国家安全的软组织,为国家安全提供不可或缺的柔性支撑,为一个族群共同体建构认同基础和精神河床。*张涛甫:《文化安全:不可轻视的非常规安全》,载《社会科学报》,2015年5月15日,第4版。价值体系是元文化,价值安全也是元文化安全。因此,就价值安全是元文化安全而言,价值安全必然也就是国家总体安全体系的重要构成要素;而就价值安全是政治安全、人民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及核安全等的价值目标、价值规范的安全而言,价值安全属于国家安全体系的软组织,为国家总体安全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柔性支撑。
【修回日期:2016-05-31】
【责任编辑:谢磊】
廖小平,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校长、教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博士生导师;孙欢,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长沙邮编:410004)。
10.14093/j.cnki.cn10-1132/d.2016.04.002
D815.5
A
2095-574X(2016)04-0020-16
2016-04-23】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中国价值安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研究”(项目批准号:14AZX019)的阶段性成果。作者感谢《国际安全研究》匿名审稿人的评审意见,文责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