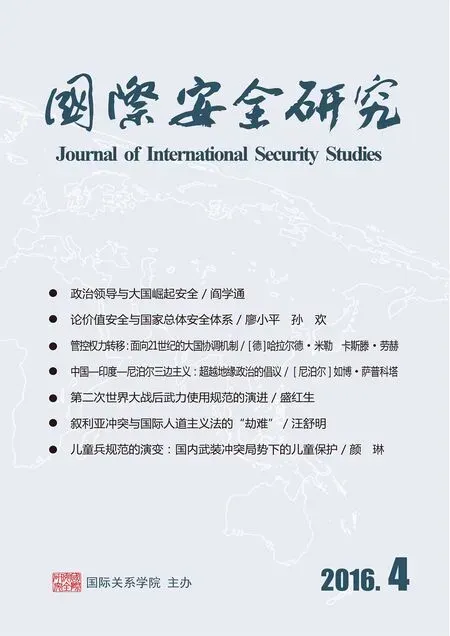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武力使用规范的演进*
盛红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武力使用规范的演进*
盛红生
【内容提要】 在国际法体系中,武装冲突法可谓编纂得最为完备的一个分支。经过数百年的积累和铺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武力使用规范逐渐发展成为完整的规范体系并呈现出四大特征:即为了适应国际关系的新变化武装冲突法扩大了适用范围; 使用核武器是否合法成为国际法的重要问题;出现了在武装冲突中“反向”使用武力以达到实现和平目的的新方式——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以及在武装冲突中出现了大量作为作战手段而使用的性暴力行为等。然而进入21世纪以后,武装冲突的形态与样式均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以无人机、自主作战机器人、纳米生物武器和网络战为代表的新型作战手段方法层出不穷;另一方面,非国家行为体在武装冲突中使用武力的情况有所增加,更出现了私人军事安保公司等法律地位在国际法上尚处于空白的交战主体。以朝核危机为标志,核武器对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巨大的潜在甚至是现实的威胁再次凸显,迅速成为国际政治和国际法中的热点核心议题。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武装冲突法的基本原则依然相对稳定,但是不断出现的新作战手段和方法,仍然给国际法和国际安全提出了一系列亟须应对的新挑战。
作战手段;作战方法;自主武器;法律规制
一 导言
作为人类社会一种极为常见的病态现象,战争(武装冲突)久已存在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仍会长期存在。在武装冲突被纳入法律规制的视野之后,需要解决的至少有两个主要问题,即诉诸武力的合法性(jus ad bellum)*jus ad bellum又被称为国家的“诉诸战争权”。也有学者将其称为“武力使用法”,参见俞正山主编:《武装冲突法概论》,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页。以及武装冲突中交战各方使用武力的手段与方法的合法性(jus in bello)。*jus in bello又称“战时法”。也有学者称之为“作战行为法”,参见俞正山主编:《武装冲突法概论》,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页。从二战结束时起,又逐渐形成了禁止非法使用武力和通过刑事司法惩治战争犯罪的一系列规范。长期以来,武装冲突一直都是从事世界历史、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研究学者的重要研究对象,迄今为止,中外学者在武装冲突特别是武装冲突中的武力使用规范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一大批成果。*比较突出的成果包括,张景恩:《国际法与战争》,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俞正山:《武装冲突法概论》,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宋新平:《武力使用法面临的困境与挑战》,载《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第50-56页;徐进:《暴力的限度:战争法的国际政治分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黄瑶:《从武力使用法看保护的责任理论》,载《法学研究》,2012年第3期,第195-208页;郭寒冰:《当代国际社会合法使用武力问题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2012年版;朱雁新:《数字空间的战争:战争法视域下的网络攻击》,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黄志雄:《论网络攻击在国际法上的归因》,载《环球法律评论》,2014年第5期,第157-168页;刘铁娃:《保护的责任:国际规范建构中的中国视角》,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美] 路易斯·亨金:《真理与强权:国际法与武力的使用》,胡炜、徐敏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Christine Gray,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Use of For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等等。英国学者克里斯蒂娜·格雷(Christine Gray)认为,二战之后,国际社会一直持续做出努力以限制国家单方面使用武力,改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独占”使用武力的权力,但是这种“独占”必须是出于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理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才可以使用武力。*Christine Gray,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Use of For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General Editors’ Preface.国外学者还主张,“支持民主的干涉”“经同意或受邀请的干涉”和“对内战的干涉”等行为都属于国际法上合法使用武力的情况。对此我们可以提出诘问的是,国家出于自卫或者为了民族解放的目的就不能单方面使用武力吗?*关于在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内使用武力问题,请参阅盛红生、汪玉:《国际法上的“使用武力”问题与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改革和完善》,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第5页。人类进入21世纪,国际法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其“弱法”性质有所变化,通过制裁等手段使国际法加强了实效。如果说国际法摆脱了以往原始和低级的状态转而趋向“成熟”的话,那么制裁规范的充分发展与完备就很可能是促使国际法成熟的重要因素。然而,在国家使用武力的条件特别是手段和方法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即使武装冲突法的基本原则依然稳定,但是不断出现新的作战手段和方法,给国际法提出了一系列新挑战。例如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中出现了一种值得注意的法律现象,即除了国家正式武装力量之外,还有私人军事安保公司和恐怖主义组织(如“伊斯兰国”)参与了战争或者武装冲突。对私人军事安保公司人员是否适用武装冲突法是个新问题,这种法律现象无疑对武装冲突法进而对一般国际法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在作战手段和方法方面,针对战场自主作战机器人问题,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于2013年5月27日在瑞士日内瓦开会,讨论议题之一为是否冻结研发“杀人机器人”,并成立联合国专门委员会讨论相关政策。此外,网络战也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另一个焦点。
在这个宏大的国际背景之下,对武装冲突中关于武力使用规范的历史沿革和嬗变过程进行研究,特别是对其未来发展走向做出初步判断,显然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又具有突出的实践意义。
二 武力使用规范在战后全面发展
在全面论述战后武力使用规范演变进路之前,对古代和近代武力使用规范进行简要梳理很有必要。在电影《斯巴达300勇士》中有一个情节,斯巴达将军对全体将士下达命令“不留活掳”(no quarters),将所有敌人官兵全部杀死,可见依照那时的交战规则,杀死敌方丧失作战能力的军人和俘虏并不违法,因为当时并不存在战俘制度。当然,值得注意的是那时的武力使用规则十分原始、分散和零散,其适用的对象也不是今天严格意义上的国际性武装冲突,充其量只能被看作是交战行为中的一些“规矩”,是武装冲突中武力使用规范的雏形。但是古代战争法遗迹对今天的国际法上武力使用的规则依然有重要影响,在很多战时法规则中,我们都能找到古代武力使用规范残存的某些痕迹。
及至近代,在如何看待战争性质和战争中使用武力能到何种程度的问题上,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并存:一方面是以普鲁士军事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为代表的一派,他们认为战争是政治以另一种形式的继续,而战争手段和方法应服从于政治目标,“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暴力的使用是没有限度的”,*参见[普]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删节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78年版,第5页。战争就是对暴力的无限制使用。古罗马西塞罗(Cicero)有云,“法律在使用武器的人面前保持缄默”。*“Laws are silent among [those who use] weapons.” Cf. Marco Sassoli and Antoine A. Bouvier, eds.,How Does Law Protect in War?: Cases, Documents and Teaching Materials on Contemporary Practice in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Geneva: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2006, p.83.另一方面,也有人开始反思在战争中是否应当无限使用或者是过度使用武力,认为“即使是战争也是受限制的”,*The People on War Report: ICRC Worldwide Consultation on the Rules of War, Report by Greenberg Research, Inc., Geneva: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1999, Front Cover.否则在战争这样一种极端特殊的社会关系领域,势必出现法律真空和“无法无天”的状态,这与人类的理性相悖。关于为何近代开始出现系统地限制作战手段和方法规则的历史原因,国内有学者认为是受人本主义的影响,所以近代以降出现了对战争中使用武力的强度和手段方法进行限制的主张和实践。*关于武力使用为何到了近代受到了有系统限制的问题,请参阅徐进:《暴力的限度:战争法的国际政治分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1页。
在国际法的整个大家庭中,武装冲突法也可以说是编纂得最为完备的一个分支。从最早的1856年《巴黎海战公约》到2013年《联合国武器贸易公约》,涉及武装冲突的各类国际法律文书共有103件。在国际习惯的积累方面,2005年3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发表了一项长达5 000页的研究报告,列出了161条习惯国际人道法规则,这些规则加强了向“受战争影响之人”所提供的法律保护。
经过国际社会多年的不懈努力,如今以《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及其两个1977年《附加议定书》*实际上2005年12月8日又通过了增加了没有任何宗教含义的红色水晶作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标志的《第三附加议定书》,但是相较于1977年6月8日第一和第二附加议定书,第三附加议定书的重要性稍低。为主体,形成了武装冲突法体系。*俄罗斯联邦政府的官方观点认为《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和《1977年两附加议定书》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备的战争法法典。可以参见[英] 鲁博特·迪斯赫斯特:《马尔顿条款与武装冲突法》,曹永刚译,载李兆杰主编:《国际人道主义法文选》,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7页。目前的武装冲突法主要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禁止或者限制使用某些作战手段和方法的原则规则,包括禁止使用具有过分杀伤力和滥杀滥伤作用的武器、禁止使用改变环境的作战手段和作战方法、对不分皂白的作战手段的限制和禁止背信弃义的作战方法。*此外,在武装冲突中严重破坏珍贵文物的行为能否构成战争罪问题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第二部分是战时保护战争受难者的原则规则,具体包括战时对平民的保护、伤病员待遇和对战俘的保护。此外还有海战与空战特殊规则。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武力使用规范体系的发展过程中至少呈现出了以下四个特征。
(一)为适应国际关系的新变化武装冲突法扩大了适用范围
受国际政治发展的影响,有三种使用武力的“情势”被提升到“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地位,在国际社会的大力推动下,逐渐产生了武装冲突法对内战也适用的情况,即反对殖民统治、外国占领和种族主义政权的武装冲突。如果对适用于国际性武装冲突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这两大类武装冲突的不同规则对比分析,我们就不难发现,国际人道法定义了一个“被保护之人”的范畴,它基本上由享受其完全保护的敌国公民组成。但是,不属于“被保护之人”的武装冲突受难者也并非完全不受保护。与国际人权法相一致,并在其影响下,这些人享有越来越多的保护性规则,但是,这些规则并未提供像给予“被保护之人”那样完全的保护。*参见[瑞士] 马尔科·萨索利、安托万·布维耶等:《战争中的法律保护》(第二版),第一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处组织翻译,北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处印行,2006年版,第110页。
《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第二附加议定书》将保护战争受难者的战争法规的适用范围扩大到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即内战), 发展和补充了《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共同第3条”关于适用范围的规定,但是同时对内战的范围进行了限制:“本议定书不应适用于非武装冲突的内部动乱和紧张局势,如暴动、孤立而不时发生的暴力行为和其他类似性质的行为”(第1条第2款)。它仅适用于“在缔约方境内发生的缔约方军队和反叛部队或有组织的武装集团之间的武装冲突,而反叛部队或有组织的武装集团应处于负责任的指挥官管辖之下,对部分领土实行控制以便实施持续和统一的军事行动并执行本议定书”。*《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第二议定书),第1条第1款。关于如何将国际人道法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在1974-1977年的外交会议上,各国重申了对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概念做出详细定义的必要性,并最终在《第二附加议定书》第1条中给出了这一定义。根据该条款,各国同意《第二议定书》“应适用于……《第一议定书》第1条所未包括、而在缔约一方领土内发生的该方武装部队和在负责统率下对该方一部分领土行使控制权,从而使其能进行持久而协调的军事行动并执行本议定书的持不同政见的武装部队或其他有组织的武装集团之间的一切武装冲突……”。但是,这个相当严格的定义仅适用于《第二议定书》,而并不适用于日内瓦四公约的共同第3条。 实际上,由于持反对立场的集团的组织规模还不足以使《第二议定书》得以适用,所以某些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仅能适用公约之共同第3条。另外,《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在适用问题上提供了一个中间的门槛。它不再要求武装冲突必须发生在政府军与占据一定领土或具有一定指挥体系的叛军之间。*Article 8 (2) (f) of Rome Statu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Paragraph 2 (e) applies to armed conflicts not of an international character and thus does not apply to situations of internal disturbances and tensions, such as riots, isolated and sporadic acts of violence or other acts of a similar nature. It applies to armed conflicts that take place in the territory of a State when there is protracted armed conflict between governmental authorities and organized armed groups or between such groups.”但是,武装冲突仍必须是持续性的,而且武装团体也必须具备组织性。
适用于这两类不同性质武装冲突的规则之所以存在差别,主要原因是将武装冲突法扩大到对非国际性武装冲突适用的理论与实践出现较晚,各国政府在内战问题上一般都不希望受到国际法的束缚。传统国际法上还有个“普遍参加条款”,即遵守和适用武装冲突法是以对方也遵守为条件的。与此同时,依照条约法中“条约对第三国无损益”的原则,条约对第三方既不创设权利,亦不创设义务,反叛武装可以借口自己不是武装冲突法条约的缔约方,因此他们可以不遵守。在国际人道法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了另外一面,即及至《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和《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第二附加议定书》签订时,旨在限制和禁止某些作战手段和方法的“海牙规则”与旨在保护武装冲突中的受难者的“日内瓦规则”逐步互相结合,并最终形成了一个国际法的重要新分支——国际人道法。*参见朱文奇:《国际刑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2页;王铁崖主编:《国际法》,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621页。
(二)使用核武器是否合法成为国际法上的重要问题
由于在武装冲突中使用核武器的巨大风险始终存在,核武器犹如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于人类头顶。与此同时,核武器产生异化并成为各方都希望拥有但却无法应用于实战的威慑手段。核武器问世后,除了仅有的由美国对日本实施的两次核袭击之外,作为武器的核武器已经逐步远离实战化的要求,因为它无法区分平民和战斗员,也无法区分军事目标和民用物体。由于一国使用核武器会导致对方有核国家也使用核武器进行报复,拥有核武器并未带来安全,恰恰相反,拥有核武器甚至威胁到有核国家的自身安全,使自己更容易受到攻击。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核武器的主要功能是起威慑作用,使对手不敢贸然发动武力攻击,或者在遭到核打击之后向对方进行报复性的第二次打击。然而,有人认为拥有核武器使自己更安全,例如有外国学者认为,“随着核武器的出现,尤其在冷战后,大国战争的可能性已经大为降低”。*参见Christoph Bluth, “The Security Dilemma Revisited: A Paradigm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ights, Vol.15, No.8 (December 2011), p.1363, 转引自袁莎:《言语习惯与安全困境:超越物质主义与理性主义的思考》,载《国际安全研究》,2016年第1期,第58页。这种观点不无道理,但是它却忽视了另一个问题,即已经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都在努力使核武器小型化,企图生产战术级核武器,使之可以用于实战。各国对这个问题必须予以高度重视。换言之,我们在防止无核国家成为有核国家这种所谓“横向扩散”的同时,也必须通过国际法限制甚至禁止有核国家借助于技术手段使核武器升级换代的所谓“纵向扩散”。更为关键的核心问题是,目前的五个核大国真正承担不扩散核武器核技术的特别义务,唯此才能使核武器不成为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消极因素。
在核武器问题上一个值得关注的动向是,南太平洋岛国马绍尔群岛共和国在二战后被美国当作核试验场、饱受核辐射之苦。马绍尔群岛共和国于2014年4月24日向国际法院提起了一项“史无前例”的诉讼,指称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中国、以色列、印度、巴基斯坦和朝鲜等世界上九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未能履行尽早停止核军备竞赛的义务,并要求九国削减核武器,*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Press Release, “The Republic of the Marshall Islands files Applications against nine States for their alleged failure to fulfill their obligations with respect to the cessation of the nuclear arms race at an early date and to nuclear disarmament,” http://www.icj-cij.org/presscom/files/0/18300.pdf.马绍尔群岛共和国请求国际法院对此做出判决。被起诉的九个有核国家又被分为接受国际法院管辖的国家和未接受国际法院管辖的国家,国际法院已经要求有关国家就诉状提出的问题提交口头和书面初步答辩意见。此外,马绍尔群岛共和国还在美国旧金山提起了一项诉讼,美国总统奥巴马、美国国防部、能源部和国家核安全部都成为其诉讼对象。
与在冷战时期人类长期处在“核恐怖平衡”之下的情况相比较,目前核武器对于世界和平和国际安全的消极影响有所减弱,公众一般并不太关注核领域里的问题。然而,近年来通过印巴核试验危机、伊核问题特别是朝鲜核问题表现出来的爆炸性和潜在的毁灭性,核武器问题依然是国际社会的热点问题。20世纪90年代围绕“国家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问题展开的大辩论和国际法院为此发表咨询意见,就充分说明核武器在国际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在一些联合国会员国和非政府组织的推动下,世界卫生组织在1993年5月14日通过第46/40号决议,请求国际法院对如下问题发表咨询意见:即“就对健康和环境产生的影响而言,一国在战争或其他武装冲突中使用核武器是否违反了该国的国际法义务包括世界卫生组织的章程”。在世界卫生组织向国际法院请求发表咨询意见之后,联合国大会也于1994年12月15日通过决议,请求国际法院就“国际法是否允许在任何情况下威胁和使用核武器”的问题发表咨询意见。根据国际法院的要求,三十多个国家向国际法院提交了书面陈述,一些国家还提交了书面评论。1995年10月30日至11月15日, 国际法院听取了世界卫生组织和22个国家代表的口头陈述, 其中很多国家都主张在国际上有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协定国际法和习惯国际法,在任何情况下威胁和使用核武器都是非法的,因为核武器的使用会伤害平民、对战斗员造成过分的伤害和痛苦、污染环境等。针对这一问题,国际法院认为,“使用核武器是否合法与世界卫生组织的职能无关。世界卫生组织向国际法院提出的问题不是关于核武器的使用对健康的影响,而是就对健康和环境而言,使用核武器是否合法”。国际法院认为,无论那些影响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处理它们的职能都不取决于造成那些影响的行为的合法性。因而国际法院认为,《世界卫生组织章程》第2条的规定不可被理解为赋予该组织处理核武器合法性的问题和向国际法院提出这一问题的权利。法院认为,无论核武器是否被合法使用,它们对健康产生的影响是相同的。
事实上,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上述请求的本来意图在于促使国际法院表明使用核武器和以核武器相威胁是非法的。然而,国际法院的法官们刻意回避了问题的实质部分,最终得出了使人不得要领的结论。*盛红生、肖凤城、杨泽伟:《21世纪前期武装冲突中的国际法问题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79页。虽然国际法院拒绝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请求,但是却接受了联合国大会提出的同样请求。就联合国大会起初的请求,国际法院发表的意见是:习惯国际法和协定国际法都未特别准许也未全面、普遍地禁止以核武器相威胁和使用核武器;违反《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4款的规定以及不符合第51条的所有要求用核武器来进行武力的威胁和使用核武器是非法的。*凌岩:《国际法院关于核武器的使用和威胁是否合法的咨询意见》,载《中国国际法年刊(1996)》,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13-315、317页;Marco Sassoli and Antoine A. Bouvier, eds.,How Does Law Protect in War?: Cases, Documents and Teaching Materials on Contemporary Practice in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Geneva: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1999, pp.556-570。有西方学者认为,“主张认定核武器违法的一方强调自然法的重要性,敦促国际法院要超越国际实在法规则。‘马尔顿条款’支持了这一立场,因为该条款暗示武装冲突法不仅提供了实在的法律规范,而且提供了道德规范。”*[英] 鲁博特·迪斯赫斯特:《马尔顿条款与武装冲突法》,曹永刚译,载李兆杰主编:《国际人道主义法文选》,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3-34页。
(三)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
一般说来,军队的主要职能是以暴力手段消灭敌人,而维持和平行动中的部队则有其特殊性,因此出现了在武装冲突中“反向”使用武力以达到实现和平目的的新方式——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The Blue Helmets (2nd edition),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Public Information, August 1990, p.19.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本身不是军人的职责,但是只能由军人来完成。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军人虽然身着军装,但是其身份和法律地位不同于国内法中的军人。例如,在1994年通过的《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第8条就认定,维和军人在被扣留时为平民身份,不是战俘。*《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第8条规定:“释放或交还被捕或被扣的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的义务”:除非在可适用的部队地位协定(Status of Forces Agreement)中另有规定,如果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在履行职务时被捕或被扣,而其身份已被证实,不应对其进行讯问,而应立即将其释放或交还给联合国或其他有关当局。在释放前,应遵照普遍公认的人权标准和1949年各项《日内瓦公约》的原则和精神对待这些人员”。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中的军人和东道国的交战各方之间无交战关系,即“无战斗之敌,无战胜之地,武器仅用于自卫,效率依靠自愿合作”。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中的军人不是在进行战争,而是通过军事手段维持和平。这对武装冲突法无疑是个发展与突破,但是同时也带来挑战,因为身份与权利义务密切相关。维持和平行动,不同于依据《联合国宪章》第43条所组建之联合国部队*Boutros Boutros-Ghali,An Agenda for Peace,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1992, p.24.或依《联合国宪章》第42条所采取的强制行动。*The Blue Helmets (2nd edition),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Public Information, August 1990, p.5.维持和平行动是警察行动,而不是军事行动,一般情况下不得使用武力,仅在严格意义上的自卫时才可以使用最低限度的武力。联合国认为,“面临军事行动即将恢复,而答应撤退的要求,亦足以说明紧急部队是一个保持和平(peace keeping)而不是强制执行和平(peace-enforcing)的工具”。*朱建民:《国际组织新论》,台北:正中书局1985年版,第630-631页。
(四)在武装冲突中存在大量作为作战手段而使用的性暴力行为*关于战争中性暴力问题研究的最新成果,请参阅郑佳然:《战争与性别权力:解读现代武装冲突中的性暴力》,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网站,http://www.icrc.org/zh/document/observation-and-opinion-sexual-violence-1。
自古以来,在战争中与敌对行动相伴一直存在大量的性暴力行为,在全世界的武装冲突中都有性暴力发生。在当代许多武装冲突中,这种情况依然十分普遍,例如在中非共和国、哥伦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马里、南苏丹和叙利亚等国的武装冲突中就有大量性暴力案件发生。2014年,来自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奥斯陆和平研究所和耶鲁大学的研究者们公布了“武装冲突中的性暴力数据集”,回顾了最近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参与武装冲突的武装分子针对平民(男人、女人、男孩和女孩)实施的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活动的报告。根据他们的报告,在所分析的各场冲突中,有57%的冲突存在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在14%的冲突中性暴力最为严重。*参见[瑞士] 格洛丽亚·加焦利:《武装冲突中的性暴力:对国际人道法和人权法的违反》(一),李强译,载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处微信公众号,2016年2月17日,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MjIzMDIwNw==&mid=401488522&idx=1&sn=9faf4f00c7c4875feab21412d5819e5d&scene =1&srcid=0306nr6fG5KnDsrwSuMIwrhB&pass_ticket=gHW04SplPHVPJZv3P%2FS9cTvtvkqZM6W3MVnYvp1W6WPdV9Y5KP4tJ0mROYvAZNXg#rd。在联合国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审理的“阿卡耶苏”案(Akayesu Case)中,审判庭认为性暴力是“在强迫的情况下对一个人实施的任何带有性色彩的行为”;“性暴力并不局限于对人身体的侵入,还可能包括不涉及插入甚或没有身体接触的行为”。从这个定义来看,很明显的是性暴力包括强奸,但比强奸更广泛,而且从对女性施暴发展到对男子施暴。如果从犯罪构成要件来分析,在犯罪主体、犯罪客体和犯罪的客观方面它和普通刑法上的强奸等性犯罪并无二致,但是在主观方面武装冲突中作为作战手段的强奸等性暴力犯罪主要是出于获取情报、摧毁被害人及其族群的自尊心和反抗意识、强迫敌对族群生下本族群的后代以实现种族清洗等超越了一般满足加害者性欲的要求。随着人权保护意识的增强,在武装冲突中使用性暴力的行为逐步成为国际法规制的对象,在国际刑法中出现了战争罪项下的强奸罪、反人类罪项下的强奸罪和灭绝种族罪项下的强奸罪。除了以往在武装冲突中常见的诸如强奸等性暴力行为,在南斯拉夫内战和卢旺达大屠杀中又出现了为了战争目的诉诸性暴力的新形式,比如性奴役、强迫卖淫、强迫绝育、强迫妊娠和当着被害人亲属的面实施强奸和猥亵行为等。在武装冲突中性犯罪的客观方面,也产生了很多新问题。*Kriangsak Kittichaisaree,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112.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一系列判决对战争法和国际刑法产生了深远影响,甚至出现向很多国家的国内法“溢出”的趋势。为了保护人权,有些国家修改刑法将强奸等性侵害行为的被害人也扩大到男性,而不是像以往那样将性侵害案件的被害人仅仅局限于女性。
武装冲突中武力使用规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特别是冷战终结后的系统演变呈现出三个突出特点。第一,与近代那种主张对武力的无限使用理论和军事学术相疏离,战后一些国家开始主动对战争中使用暴力的烈度进行限制和控制,“全面战争”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局部战争”和“有限战争”逐渐成为战后武装冲突的主要形态。第二,与“有限战争”理论相适应,军事技术发达的各国竞相研究开发“智能”和“灵巧”武器,“外科手术式打击”和“定点清除”的作战方法开始登场,以减少武装冲突中使用武力对平民人口和民用目标的附带伤害,降低战争残酷程度,从而使战争更加“人道”,在不违反战争法的情况下有助于有关交战方实现其政治目的。第三,武力使用的空间不断扩大,从传统的陆地和海上发展到空中、外层空间、海床洋底乃至网络空间与电磁空间。随着化学战、生物战和武装冲突中性暴力行为的出现,又进一步扩展到空气和人类的身体,这个现象使武力使用规范适用的空间、时间和事项的范围也随之扩展。
三 武力使用规范正面临全新挑战
冷战结束后,武装冲突法又经历了较快的发展阶段。*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swers to Your Questions, Geneva: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2002, p.21.经过国际社会中各国的共同努力,2003年11月28日签订了《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的《第五议定书》(《战争遗留爆炸物议定书》),该议定书也已经于2006年11月13日正式生效。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向2011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于日内瓦召开的“第31届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提交的一份报告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列举了为“加强对武装冲突受难者的法律保护”等亟待研究的四个问题,包括“保护被剥夺自由人员”“建立国际监督机制以确保遵守国际人道法和对暴力行为受害者进行赔偿”“保护自然环境”和“保护国内流离失所者”。除此之外,目前国际社会普遍较为关注的与武装冲突或者使用武力有关的热点问题包括但不限于网络战、遥控武器系统、自动和自主武器系统、新型生化武器(基因武器)和防空导弹预先内置敌我识别密码等问题。另外,由联合国牵头制定的《联合国武器贸易条约》是联合国为监管八类常规武器的国际贸易制定的共同国际标准,该条约于2013年4月2日在联合国大会上通过,2013年6月3日开放签署并于2014年12月24日生效。
武力使用规范在此阶段出现的新特点主要包括六个方面:
(一)进入21世纪以来不断出现新式武器和作战方法
实际上武装冲突法领域的其他进展都与作战手段有关。进入21世纪以来,武装冲突中武力使用规范进一步发生变化,具体表现为武器与人开始分离,武器智能化程度空前提高,新式武器如卫星武器(天基和地面发射攻击敌方卫星的武器)、自主作战机器人、无人机和网络战都给武装冲突法带来了严峻挑战,原先的规则已显得滞后,主要表现在交战各方的战斗员与平民无法区分。针对这个问题,有国内学者指出,“大多数网络攻击的私人性和隐秘性特点,使得这类攻击在国际法上的归因成为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黄志雄:《论网络攻击在国际法上的归因》,载《环球法律评论》,2014年第5期,第157页。此外,操作遥控无人机的战士或者技术员远在被袭目标数千公里之外,导致滥杀滥伤者的负罪感减弱甚至消失,而且对此类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人追责极为困难。有外国学者认为,“自古以来,在战争中使用毒药或病源性试剂就被视为背信弃义之举”。*[瑞典] 乔泽夫·高德布莱特:《论生物武器公约》,尹文娟译,载李兆杰主编:《国际人道主义法文选》,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8页。然而,有些国家近年来却加紧着手研制新型生物武器如纳米技术(Nanotechnology)炸弹。核武器无法识别人群,而基因武器却能够识别攻击某种特定基因结构的人群。种族或民族具有基因特征,据此,可以制造针对某一特定种族、民族甚至是个人的基因武器。*参见盛红生、肖凤城、杨泽伟:《21世纪前期武装冲突中的国际法问题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183页。研制和使用这种智能生物武器的国家可以声称这种做法能够实现“定点清除”和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以大大降低“附带伤害”,使自己始终处于战争伦理的高地。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即使具备一定的“智能”,智能武器毕竟还是武器,难以做到完全避免附带伤害,特别是将对平民造成死伤及财产损失。
关于战场自主作战机器人问题,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于2013年5月27日在日内瓦召开会议,讨论议题之一为是否冻结研发“杀人机器人”并成立专门委员会讨论相关政策。联合国“法外处决、即决处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克里斯托夫·海恩斯(Christof Heyns)在向人权理事会进行工作汇报时发言指出,“杀人机器人”的使用将对战争期间的生命保护带来影响深远的关切,因为它们一旦介入冲突,“机器而不是人类将决定谁死谁活……”。海恩斯呼吁各国在给予机器杀人的“权力”之前,必须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考量和探讨。特别报告员说,“没有国家目前正在使用这种可以被归类为‘杀人机器人’的、能够完全‘自主操控’的自动武器,但是相关技术已经存在,或者说很快就能成熟使用。尽管一些在该领域极为活跃的国家已经承诺不会在可预见的未来使用此类机器人,但非常强大的力量、包括科技和预算,却在朝着相反的方向有力推进”。如果出现了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如何追责,究竟是军队所属的国家、制造自主作战武器系统的公司还是具体使用自主作战机器人的士兵应当承担责任?在涉及自主作战机器人的刑事案件中,原来量刑过程中需要确定的“上级命令”“胁迫”等减轻情节究竟应当如何考量?海恩斯又指出,“杀人机器人还很有可能被强权政府所利用,拿来压制国内的反对派异己势力。因此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应呼吁所有国家制定出台并实施相关国家政策,以暂停生产、组装、转移、收购、部署和使用具有杀伤力的自主机器人,直到国际社会就相关问题协商出一个切实可行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框架。”
有学者指出,“在各种网络安全威胁不断增长的背景下,与‘网络战’有关的国际法问题日益受到重视”。*黄志雄:《国际法视角下的“网络战”及中国的对策——以诉诸武力权为中心》,载《现代法学》,2015年第5期,第145页。如果我们将网络战(信息战)看成一种作战方法或者是一种作战手段(武器),那么网络战给传统武装冲突法带来的冲击也十分巨大。按照武装冲突法的“区分原则”,应将战斗员与平民等不直接参与交战行动的人区分开,还应当将军事目标与民用物体相区分,但是网络战使以往在确定交战主体(战斗员)和打击目标(敌方战斗员与敌方军事目标)方面所坚持的“区分原则”基本失去意义。在网络战中平民可以参战,在未来的武装冲突中,军民两用物体或者民用物体(甚至是包含危险力量的工事,如电厂、水坝与核电站等的网络控制系统)也都可能成为网络攻击的目标。此外,网络战中的敌对行为还可能涉及第三国,因而传统的中立法也碰到了很多新问题。
(二)非国家行为体在武装冲突中使用武力的问题十分突出
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法律现象,即除了国家正式武装力量之外,还有反叛武装、恐怖组织和私人军事安保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参加战争或者武装冲突,即战争的私人化(privatization of war)问题,*Dino Kritsiotis, “Mercenaries and the Privatization of Warfare,”The Fletcher Forum of World Affairs, Vol.22, No.2 (Summer/Fall 1998), pp.11-26.或者说是升级版的“雇佣军”在21世纪借尸还魂,对国际法造成了严重挑战。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世界上大约有六百多家私人军事安保公司。私人军事安保公司不是国家的武装力量,但是它们的成员实际上却参加敌对行动。一些国家认为,私人军事安保公司的优势在于它们可以完成安全保卫和参加某些军事行动,即使出现违法犯罪的情况也可以用不是国家正规军队的名义加以开脱。这个现象带来了几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武装冲突中各方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都来自于身份,伤者病者遇船难者、战俘和平民之所以受到国际法保护是因为他们是不实际参与作战行动之人,否则他们便丧失了受保护之人的身份和法律地位。私人军事安保公司的成员具有平民身份,但是他们拥有武器并实际参加敌对行动。如果私人军事安保公司人员攻击杀害有关交战方的战斗员和平民,那么他们的行为应该如何认定?如果有关交战方的战斗员或者平民杀死私人军事安保公司的人员,那么他们的行为又应该如何确定?在这个国际大背景之下,2008年9月17日,包括中国、阿富汗、伊拉克、南非、瑞士和美国等国在内的17个国家在瑞士的蒙特勒共同签署了一份反映国际社会在私人军事安保公司问题上的意见和观点的规范性文件——《武装冲突期间各国关于私营军事和安保服务公司营业的相关国际法律义务和良好惯例》(又称《蒙特勒文件》)。该文件比较详尽地规定了私人军事安保公司及其雇员、东道国、母国等主体须遵守的国际法律义务,并在第二部分提出了有关私人军事安保公司的73条良好通例(做法)(good practices)。《蒙特勒文件》是第一份专门致力于解决私人军事安保公司问题的国际性文件,其问世对规制与规范私人军事安保公司的活动和私人军事安保公司雇员的行为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也为今后相关的国际立法提供了良好的示范。*王秀梅:《〈蒙特勒文件〉对私营军事和安保服务公司的规制评析》,载《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第103页。然而,这份文件不具有法律强制力,也不是在联合国主导之下签署的,能否被适用于实践还取决于各国自身的意愿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
(三)在反恐战争中出现了大量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的情况
例如,在反恐军事行动中对攻击目标不加区分,美国对在阿富汗反恐战争中抓获的人员强行带往古巴关塔那摩美国军事基地,不审不判,长期关押,并给这些人冠上国际法和国内法上都没有的一个特殊名称叫作“敌方交战者”(Enemy Combatant)。这些人受到长期关押,宗教信仰自由受到严重侵害,常常受到虐待和体罚。一些人在长期关押无法证实有罪后,又任意引渡和遣返至与这些人员缺乏法律联系的国家,而不是当事人的原国籍国。美国总统甚至签署总统政令允许对在审讯这些人员时发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开脱不予追究。这些行为既违反美国国内法,也严重违反了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联合国叙利亚问题调查委员会在发表的一份报告中表示,叙利亚政府部队和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均犯下危害人类罪,而由战斗人员犯下的战争罪极为普遍。报告指出,支持叙利亚政府的部队对不受政府控制的地区进行的空袭导致成百上千名平民的伤亡、大规模流离失所以及重要民用设施的破坏,但所有交战方,包括支持政府的军队、反政府武装组织和“伊斯兰国”以及努斯拉阵线都进行了不加区分的攻击,向对方控制的平民居住地区发射炮弹。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指出,暴力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继续使用自杀式炸弹袭击和简易爆炸装置对平民实施杀戮、致残、制造恐怖氛围,针对学校和医院的攻击导致医护人员、病人、教师和学生遭到杀害。*联合国新闻中心:《联合国叙利亚问题调查委员会再次确认:所有冲突方均犯下侵犯人权罪行》,2016年2月22日,http://www.un.org/chinese/News/story.asp?NewsID=25690。
(四)在武装冲突中有关交战方屡次违法使用国际法全面禁止的化学武器
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2013年6月4日向正在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23次会议提交报告。该报告称有合理理由相信叙利亚政府和反政府武装均在冲突中使用了化学武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国际在线:《联合国调查报告认为叙利亚冲突双方均使用化学武器》,2013年6月4日,http://gb.cri.cn/42071/2013/06/04/2625s4137226.htm。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伊斯兰国”和其他恐怖团体不断使用工业有毒化学品和化学武器战剂的事实显示了这个问题的极端紧迫性。此外,在利比亚和也门发生类似罪行的危险也在不断增加。来自中东地区的非国家行为体的这类行为造成的威胁还有可能扩散到区域之外。另有报告显示,恐怖主义团体正在获取生产化学武器的科技文件,攫取化学工厂及其设备,联络外国专家帮助合成化学武器战剂。 在2016年3月1日召开的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简称“裁谈会”)高级别会议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建议裁谈会就起草一项新的制止化学恐怖主义行为公约进行谈判,此举可以实现双重目的,一方面打击化学恐怖主义,同时打破裁谈会长期以来无所作为的僵局。*联合国新闻中心:《 俄外长提议拉夫罗夫就制定一项新的制止化学恐怖主义行为公约启动谈判》,2016年3月1日,http://www.un.org/chinese/News/story.asp?NewsID=25731&Kw1=%E5%8C%96%E5%AD%A6%E6%AD%A6%E5%99%A8。
(五)在武装冲突中严重破坏珍贵文物的行为能否构成战争罪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伊斯兰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恐怖组织,其资金主要来源于开采其所占领土的自然和经济资源,包括油田和炼油厂及农田,其他来源还包括抢劫银行、勒索、没收财产、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的捐赠以及掠夺和变卖古文物。据估计,2015年,“伊斯兰国”从石油和石油产品获得的收入在4亿至5亿美元之间。*联合国新闻中心:《秘书长报告:伊黎伊斯兰国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史无前例的威胁》,2016年2月9日,http://www.un.org/chinese/News/story.asp?NewsID=25623&Kw1=%E6%96%87%E7%89%A9。2015年3月6日,“伊斯兰国”继破坏伊拉克摩苏尔博物馆文物后,又对伊拉克北部尼姆鲁德的亚述古城遗址进行了大肆破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Irina Gueorguieva Bokova)为此发表声明对该事件予以严厉谴责,称毁坏尼姆鲁德遗址的事件是针对伊拉克人民的又一次袭击。博科娃在声明中指出,国际社会不能对“伊斯兰国”毁坏尼姆鲁德遗址的行为保持沉默,蓄意破坏文化遗址的行径可构成战争罪。*联合国新闻中心:《“伊斯兰国”大肆毁坏伊拉克古城 教科文组织称破坏文化遗产可构成战争罪》,2015年3月6日,http://www.un.org/chinese/News/story.asp?NewsID=23568。文化遗产与各族人民和他们的权利是不可分割的。对文化遗产的攻击就是对人民和基本人权的攻击。博科娃强调,由政府和非政府人员实施的毁坏文化遗产的行为亟待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同时她也向2015年在叙利亚古城帕尔米拉遭到“伊斯兰国”武装人员残酷杀害的叙利亚考古学家阿萨德(Khaled Assad)表达了敬意,并指出:“国际社会必须向这些勇于站出来保护文化遗产的普通民众致敬”。*联合国新闻网:《人权特别报告员:攻击文化遗产等同于剥夺人民的基本人权》,2016年3月4日,http://www.un.org/chinese/News/story.asp?NewsID=25764。2016年3月4日,联合国文化权利特别报告员卡里玛·贝农(Karima Bennoune)发表声明,对国际刑事法院首次以独立的战争罪罪名对马里文化古城廷巴克图的文化和宗教遗址以及历史性纪念碑的破坏行为提出起诉的决定表示欢迎。*联合国新闻网:《人权特别报告员:攻击文化遗产等同于剥夺人民的基本人权》,2016年3月4日,http://www.un.org/chinese/News/story.asp?NewsID=25764。
(六)国际刑法复苏和快速发展增强了国际法尤其是武装冲突法的实效
冷战结束后,从1993年起,国际社会陆续建立了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等七个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经过国际社会的长期努力,《国际刑事法院规约》于1998年7月17日在罗马通过,《国际刑事法院规约》是促使各国进一步尊重国际人道法的一个重要措施。新的国际刑事法院对战争罪等四种严重侵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核心罪行”享有管辖权,不论这种行为发生在国际性武装冲突还是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均应受到法律的制裁。由于国际刑法的复苏和快速发展,国际法中制裁机制的进一步强化,反过来使武装冲突法对交战行为的规制效果也更加明显。以往的国际法相对而言缺乏制裁机制,所以才会背上“弱法”的名字。但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为起点,作为国际法分支的国际刑法开始逐步形成。通过刑事审判并将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人绳之以法,国际法对武装冲突法进行补充和完善,加强了制裁机制,国际刑法大大地加强了武装冲突法甚至是国际法整体的效力,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弱法”所处的不利境地。
综上所述,目前武力使用规范正在遭遇历史上最为严峻的挑战。第一,进入21世纪以来不断出现新式武器和作战方法,非国家行为体如反叛武装、恐怖组织和私人军事安保公司等在武装冲突中使用武力问题使得法律相对滞后性的弱点显露无遗,造成国际社会关系中屡屡出现难以避免的法律空白现象。第二,国际社会平行、分散的特点都使国际法原则规则的遵守与实施变得困难。早在中国古代就有法谚云:“徒法不可以自行”,即使国际造法再完善,也必须依赖各国和国际组织的守法和司法,在反恐战争中出现了大量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的情况和在武装冲突中有关交战方屡次违法使用国际法全面禁止的化学武器的情况就是注脚。第三,由于作战手段和方法仍在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方式发展,与此相适应的是,武装冲突法对交战行为的规制空间和范围也在进一步扩大,围绕在武装冲突中严重破坏珍贵文物的行为能否构成战争罪引发国际社会广泛争议的现象就能够令人信服地证明这一点。
四 武力使用规范的未来走向预测
由于受到国际政治的严重掣肘,国际法发展的空间极为狭小。根据对近年来国际关系发展变化以及武装冲突法出现的新动向的观察,未来武力使用法的可能走向将会突破目前国际法的框架,在国际社会中使用武力的情况会大大增加。最近的案例是,2015年3月25日,也门外交部部长在埃及呼吁阿拉伯国家对也门实施军事干预,打击也门的胡塞反政府武装。沙特阿拉伯空军随即对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展开空袭。被迫逃亡国外的也门总统此前已向海湾国家请求军事干预,并且要求联合国设置禁飞区以关停叛军掌握的机场,因为叛军利用这些机场运输来自伊朗的武器。*《对IS空袭 阿萨德曾致信普京请求军援?》,新华网,2015年10月1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10/01/c_128285337.htm。本来受到各方保留的“受邀请的武装干涉”*《沙特联合10余国对也门展开轰炸 外媒:新中东战争爆发》,凤凰网,2015年3月26日,http://news.ifeng.com/a/20150326/43420613_0.shtml。行为或许将成为国际关系中的常态,当然其合法性问题仍会受到一些国家的强烈质疑。此外,国际社会通过使用武力落实“保护的责任”带来的问题,也会超越近代以来形成的主权国家“同意导向”的国际法实施机制,而逐步向国际社会“规制主导”的方向演化。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加以密切关注。
我们在充分肯定国际人道法的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应当注意到国际人道法对武装冲突的制约作用极为有限,例如它并不禁止武力的使用;它无法保护所有受武装冲突影响之人;它无法根据冲突目的做出区分;它无法禁止一方征服另一方;国际人道法预先假定武装冲突各方均具有合理目标。*Marco Sassoli and Antoine A. Bouvier, eds.,How Does Law Protect in War?: Cases, Documents and Teaching Materials on Contemporary Practice in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Geneva: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2006, p.82.此外,国际人道法也无法阻止将科学技术上的新突破应用到武装冲突中。但是,我们仍然应该对国际人道法保持相对乐观的态度,因为正如美国国际法专家路易斯·亨金(Louis Henkin)指出的那样,“绝大多数国家在绝大多数时间遵守绝大多数的国际法原则和绝大多数的义务”。*“...almost all nations observe almost all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almost all of their obligations almost all the time.” http://www.law.columbia.edu/louis-henkin/55703.如果说科学技术影响新式作战手段和方法太快而国际人道法相对滞后,那么作为人类理性在战争时期发挥作用的体现,同时也是作为人类良知的底线,“马尔顿条款”(The Martens Clause)*1907年的《海牙陆战法规公约》序言部分称:“在本议定书或其他国际协议所未包括的情形下,平民和战斗员仍受来源于既定习惯、人道原则和公众良心要求的国际法原则的保护和支配。”这就是国际法学者通常所说的“马尔顿条款”。的重要意义迄今仍然没有过时,还在起着“安全阀门”的作用,或者可以把该条款视为“兜底条款”,换言之,即使在所有其他规则都失效的情况下仍然能够保持着对人的基本保护。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指出:“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7页。转引自刘杨钺:《国际政治中的网络安全:理论视角与观点争鸣》,载《外交评论》,2015 年第5 期,第135页。这一著名观点被历史事实多次证实。就“交战行为法”的未来走向而言,毋庸讳言,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和军事装备的改进,在武装冲突中所使用的暴力手段和方法也将随之发生重大发展与变化,但是国际人道法的七项基本原则即“人道原则”“军事必要原则”“相称性原则”“区分原则”“限制原则”“条约无规定的情况不解除交战国尊重战争法的义务”和“将‘战时法’(jus in bello)与‘诉诸战争权’(jus ad bellum)相区分原则”*参见盛红生、肖凤城、杨泽伟:《21世纪前期武装冲突中的国际法问题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183页。将会保持相对稳定。武装冲突法仍然在引导和规制交战各方在战争中合法使用武力的手段和方法,将战争对平民等“战争受难者”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最低程度,并为限制甚至禁止使用某些作战手段和方法以保护战争受难者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
五 结论
纵观武力使用规范演变的历史沿革特别是其在战后至今的系统演进,我们不难发现其演进过程中呈现出两大规律:第一,科学技术进步迅速转化应用于军事,增强了国家的军事实力并提高了作战效能,而经济发达、科学技术先进的国家在这个方面总是占据优势。第二,国家总是在同时追求拥有军事优势和希望保持道德优越这两个目标。然而,技术进步应用于军事在促进作战效能和增强伦理优势的时候,仍然无法彻底解决武力使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因为即使是再“人道”的武器毕竟也是武器,政治对于法律的制约在此领域显露无遗。值得注意的是,法律毕竟对战争施加了一定的限制,这两种情形也同时存在并将延续下去,直至战争彻底退出人类社会生活。即使未来出现了更为先进和尖端的作战手段和方法,但是武力使用规范的整个嬗变过程依然会呈现出这两种规律,而这两大规律的交互作用,将共同推动武力使用规范向新的历史阶段发展。
【修回日期:2016-04-14】
【责任编辑:谢磊】
盛红生,上海政法学院国际法教授、最高人民法院“一带一路”司法研究基地(上海政法学院)主任(上海 邮编:201701)。
10.14093/j.cnki.cn10-1132/d.2016.04.005
D815.5
A
2095-574X(2016)04-0093-19
2016-03-25】
【编者按】武力冲突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几乎一样漫长。在人类社会不断的武力冲突实践中,也产生了形形色色的使用武力规范,特别是近代以来国际法的发展以及国际社会使用武力领域不断涌现的各类新议题,使武力使用的规范也呈现出了许多新变化。基于此,我们邀请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李开盛研究员主持,并由上海政法学院盛红生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汪舒明副研究员和湖南师范大学颜琳讲师共同参与了“武力冲突中的规范演进”专题讨论。在此向参与主持和讨论的几位学者表示诚挚的感谢!
*本文系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法律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5BFX187)的阶段性成果。作者感谢《国际安全研究》匿名审稿专家的修改建议,然而文中疏漏由作者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