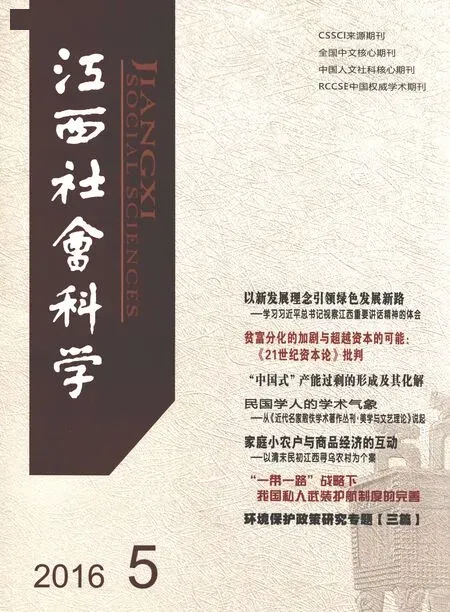民国学人的学术气象
——从《近代名家散佚学术著作丛刊·美学与文艺理论》说起
■赵 勇
民国学人的学术气象
——从《近代名家散佚学术著作丛刊·美学与文艺理论》说起
■赵 勇
《近代名家散佚学术著作丛刊·美学与文艺理论》收录吕澄、范寿康、张世禄、梁昆、宋寿昌、阴法鲁、齐如山、王钧初、林风眠、潘光旦出版的11册著作,其中既有美学理论,也有艺术学、文艺变迁史、音乐、绘画、戏曲等方面的专门论述。本文重在对这些著作逐一评点,以确认其学术价值;同时也指出,之所以能从这些学人的早期著述中看出大气象,是因为他们往往学贯中西,身兼数任,并未局限在某一专业领域,而是以学术为志业,以人间情怀和乌托邦精神为支撑,这些也是他们著书立说的动力所在。凡此种种,均可丰富当今学界的学术话语和治学理念,成为当下学人追模的榜样。
民国学人;《近代名家散佚学术著作丛刊·美学与文艺理论》;学术气象;人间情怀;乌托邦精神
赵 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艺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5)
《近代名家散佚学术著作丛刊》选取1949年前出版的学术著作120册,涉及文学、语言文献、美学与文艺理论、史学、政治与法律、民族风俗、宗教与哲学、经济等学科,可谓洋洋大观。作为编委会的成员之一,笔者所负责的“美学与文艺理论”系列共收录11册著作,分别是:吕澄(1896—1989)的《美学浅说》(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和《色彩学纲要》(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此二书合为一本,范寿康(1896—1983)的《艺术之本质》(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张世禄(1902—1991)的《中国文艺变迁论》(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梁昆(生卒年不详)的《宋诗派别论》(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宋寿昌(生卒年不详)的《中国音乐发达概况》(文心书业社1934年版),阴法鲁(1915—2002)的《唐宋大曲之来源及其组织》(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年版),齐如山(1875—1962)的《中国剧之组织》(北华印刷局1928年版),王钧初(1904—1986)的《中国美术的演变》(文心书业社1934年版),林风眠(1900—1991)的《艺术丛论》(正中书局1936年版),潘光旦(1899—1967)的《小青之分析》(新月书店1927年版)。仅浏览书名,便可见其五花八门,往往指涉着更专门的学科。而把它们统统归拢到“美学与文艺理论”名下,也不一定十分妥帖。之所以如此,大概是因为它们的理论味更浓一些吧。
只是,要为这些或中或西,或论诗或谈曲或说戏的著作写点文字,其难度很大。笔者并非音乐、美术、戏曲等方面的研究专家,只能说是对美学与文艺理论略知一二。于是便只好采用笨办法,先认真读书,再查阅相关资料,然后依次评点(吕澄的两本著作只评点其一),写出一点读后的感受来。
一
先从吕澄说起。吕澄虽说是以研究佛学著称于世,他早年对美学颇为用心。1915年留日归国后,他曾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职两年,此间结合教学,他便编撰了多种美学、美术著作,计有《美学概论》《美学浅说》《现代美学思潮》《西洋美术史》《色彩学纲要》等。[1]《美学浅说》就是他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
《美学浅说》共45页,可谓一本名符其实的小册子。作者从“现代的美学和从前的美学”谈起,梳理现代美学的源泉,思考现代美学的分歧点和统一点,进而确认何谓美感,何谓艺术品。而最终的落脚点则是“艺术与人生”。
从全书的架构看,作者显然更看重现代美学。而所谓现代美学,既是从斐赫那(Fechner,今译费希纳)开始注重经验事实的实验美学,也是栗泊士(Lipps,今译立普斯)等人所开创的心理美学。前者有感于“由上的美学”太悬空,便从基础的实验工作做起,重视 “黄金截”(Golden Section,今译“黄金分割”),从而形成了“由下的美学”[2](P10)。而后者则更看重美学的心理学依据——“感情移入”(empathy,今译“移情”)。可以看出,吕澄对于“感情移入”是极为重视的,因为这是他所确认的不同于单纯快感的美感之所以发生的基础所在。他指出:
我们当“感情移入”很纯粹的时候,自随着事物构成一种生命,发动那样的感情,临了就觉是事物自有那样的生命。这样一来,感情经过已自和别时不同,所觉得的感情也就不同。因为我们原有的“生命”不必恰和从事物所感得的符合,所以到了此时,两者间一定要构成或正或反的关系……所以美感只是对于生命这样开展的快感。再从反面说,因着“纯粹的反感”便觉我们的生命受着压迫,不容顺其自然的开展,同时起了一片的不快;从这里就辨别得“丑”。[2](P24-25)
由“感情移入”来区分美丑,进而确认美感和不快感生发的原因,这种思路既偏重心理美学,也让吕澄成了中国最早倡导“生命美学”的美学家之一。于是,他对艺术品的鉴定,强调的是个体生命的灌注。[2](P29)而他把“美的人生”看作审美的最终归宿,亦可看作“生命美学”奏出的强音:“艺术和人生只有一种关系,便是实现‘美的人生’。”[2](P45)如何实现这种 “美的人生”呢?最重要的方法有二:“第一,启迪一般人美的感受,发达创作的能力,使他们自觉‘美的人生’的必要,能逐渐实践出来。平常所说的‘美育’,便有这样的目的。第二,改革现代的产业组织,助成‘美的人生’的实现。”[2](P44)从这些论说看,他的思考与蔡元培的美育思想很接近,而细究下去,恐怕相异之处也不在少数,但这已是一个很专门的话题了。
有研究者指出:“吕澄的《美学浅说》和《现代美学思潮》是在德国哲学家、心理学家摩伊曼的‘美的态度’基础上编译的。”[3]《美学浅说》是不是编译之书,需要做专门的研究。笔者想指出的是,作为美学学说最早的介绍者和传播者,美学家们在其研究中大量借用西方学界的研究成果,可能也是当时的一个通例。而这种情况在《艺术之本质》一书中体现得尤其明显。
如果不读到最后一页,很容易认为《艺术之本质》就是一本专著,因为封面上有“范寿康著”的字样。但这本书的末尾却出现了如下文字:“这一部小书的材料是取诸伊势专一郎氏的著书。对于伊势氏特表谢意。十三年夏莫干山上编译者识。”[4](P113)伊势专一郎是日本的美术史研究专家,著有《支那山水画史:自顾恺之至荆浩》等书。而《艺术之本质》究竟是全部编译自伊势氏著作,还是也融入了范寿康本人的感悟理解,就不容易查考了。
由于是编译之作,《艺术之本质》一书颇显得体系完备。全书共八章,除绪论之外,还分别在崇高、优美、感觉美、精神美、悲壮、滑稽与谐谑、丑的名目下展开了专章论述。而每章之下,所论也非常详尽。以崇高为例,作者先是在第一节中从量的感情、深的感情、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和无形式雄大自由四个方面,论述“崇高之一般的形相”,又分别以两节内容展开“崇高之主要的种类”:恐怖的崇高、战栗的崇高、凄惨的崇高、沉郁的崇高和壮丽、严肃、壮静、庄严、激情。这种分法很是细腻,显示着日本学者做学问的特点。另一方面,作者又辅之于相关例证,夹叙夹议,把深奥的美学问题讲得通透有趣。比如,作者说:“美味与我们以一种快感。但是这种快感,我们决不以之当做由心底涌出的感情。换言之,就是美味未曾伴有‘深’的感情。所以对之只可说快,不能说美。美丑的体验本来如是,故除伴有深的感情以外,决无成立的余地。我们就美之高下上说,亦不可不求之于这‘深’字上面。而这‘深’的感情中的特深者与量的感情中的特大者互相结合的感情,就是崇高的感情。崇高不外是与某种特别的‘深’所结合之某种特别的人格的伟大之感情罢了。”[4](P20)这种叙说既呼应了绪论中所谓的“美的快”,又很自然地衔接到了崇高的感情,读起来颇感妥帖,顺畅。
吕澄主要是佛学家,而范寿康则主要是教育家。但他们早年又都介入美学领域,成为美学理论的译介者和传播者。同时他们还是美学教科书的最早编撰者 (范寿康也编写过《美学概论》,192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除此之外,他们两人都曾在日本留学。虽然他们的美学理论多取自西方,但对日本美学界的研究成果多有译介和借鉴。这也意味着,美学来到中国,除像朱光潜那样直接从西方引进外,其实还有一条途径,那便是绕道日本。
二
张世禄是语言学家、音韵学家,在介绍他的成就时,一般不会提到他早年的这本《中国文艺变迁论》。比如,复旦大学当年介绍张世禄时,在其官方说法《博士生导师张世禄教授》一文中讲道:“张世禄教授是海内外著名的现代语言学家,在古代汉语的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现代汉语的语音、语法、词汇、修辞方面以及普通语言学方面都有深的造诣,著有《广韵研究》《语言学概论》《中国音韵学史》《古代汉语》等十几种专著;《中国语与中国文》《汉语词类》等译作数种。”《中国文艺变迁论》却只字未提。然而,即便用今天的眼光看,这本著作的学术价值也是不言而喻的。
据张世禄自己讲,他写此书是想矫正二弊:一弊是,研究中国文艺往往偏重于文艺的体制形式,“而于其内容之变迁如何,其受于时代思潮之影响者如何,其关于文艺本身外之实事如何,则罕有论及。此则不为统体观察之过也”。二弊是,“诸述文艺史者,大都仅罗列文学家作品与身世,以实各代史料而已;至于其相互递嬗交替之关系,与受于时代变化之原因等等,则略而不讲。此则缺乏历史方法之过也”。[5](P1)职是之故,他借用法国学者泰纳(Taine)时代、民族、地理三要素,用35章的篇幅,直把《诗经》以来文艺变迁的脉络、路径、成因等论述得风生水起。其史料之翔实,思考之深入,灼见之迭出,令人过目难忘。比如,谈及中国古无史诗之原因,他指出,中国不像印度和希腊的地理环境,或土地肥沃,或海阔天空,而是“非勤于操作,不能有获”。“故其民族心理,常以发挥实践躬行为准的;虚无缥渺之思,殆为先民所罕有。”另一方面,印度希腊古代有多神观念,叙述史事亦带有神话色彩。“吾国偏于实际之人生,此种多神观念,几经洗炼蜕变;至有史时代,至高抽象之一神,所谓天道观念者,已渐确立。”这样一来,便“宁使文学之为历史化,而不容历史之文学化”。[5](P19-20)凡此种种,都限制了中国史诗的发生。像这种论说,就颇令人玩味。
纵观全书,张世禄对新旧文艺递嬗变迁的观察与思考应该是相当准确的,而他的如下论述,亦可视为此书最核心的观点:
凡一种文艺由生长而成熟而衰退,其形式必日趋于扩大而渐形固定;其格律必日趋于细密,其工力必日就于技巧……文艺亦然,当其生长力衰退时,形式必已固定。一般从事于斯者,既无以超越前人,惟向形迹中求之,于是格律日就细密,工力日趋技巧;而其文艺之气运,至是遂告终极。[5](P11)
顺着张世禄的思路,我们便看到一代之所以有一代之文艺,便是因为旧文艺走向了僵化,不得不让新文艺取而代之。古代赋、诗、词、曲、小说的演变更迭,各领风骚,就很能说明这一问题。
也需要指出的是,张世禄毕竟是语言学家,这样他看历朝历代文艺时,便或隐或显地带上了语言学家的眼光,打量出的东西也就不同寻常了。例如,谈及汉代词赋发达之原因,他在罗列“社会之富厚也,民族之强盛也,君主之好尚也,乡学之发达也”之外,还特意指出了汉赋之盛,与当时小学的发达关系甚密。他特引日本儿岛献吉《支那文学史纲》的话说:“支那文字,以象形为基础;而指事会意形声皆有一部分之象形。象形与图画,只有精粗之异耳,试观郭璞《江赋》,通篇文字中以水为偏旁者,占十之五六……故一篇文字,全体生动,善写高山绝峰,峻极于天之雄势;易使人想见鸟飞天鱼跃渊之活境。皆于文字之构造,含有图画性质之所致。”[5](P62)由此可见,汉大赋之所以铺张扬厉,雄伟壮观,文字的铺排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谈及宋词时,《中国文艺变迁论》曾用短短一章内容论述其渊源与派别,而宋诗却只字未提。这也难怪,因为宋诗并非宋朝文学之主潮。但梁昆却写出了厚厚的一本《宋诗派别论》,在他的笔下,宋诗的各门各派一下子显得条分缕析了。
梁昆开门见山地指出:“诗之有派别始于宋。欲论宋诗,不可不知其派别:盖一派有一派之方法,一派有一派之习尚,一派有一派之长短,一派有一派之宗主。凡派别同者,其诗之方法同,习尚同,长短同,宗主同;苟不知其派别之异,徒执其一,以概其余,曰宋诗云云,宋诗云乎哉?”[6](P1)正是意识到了派别在品评、鉴赏、分析、论说宋诗当中的重要性,梁昆便把宋诗各派做了详细的归类,区分出11种之多,计有香山派、晚唐派、西昆派、昌黎派、荆公派、东坡派、江西派、四灵派、江湖派、理学派和晚宋派。而每一派别,作者又大致遵循如下体例,分而述之:先是“小传”,把某派中诗人群体之简历一一列出,并附有当时或其后对其诗歌的评论;接着是 “宗主”,指出某派所法者何人,述其师承渊源关系;然后又是“习尚”,泛论某派诗歌的诗风、格调和艺术好尚;最后是“批评”,概括出某派诗歌的优劣、得失和短长。这样一来,各诗派的方方面面就呈现得眉目清晰了。
比如,论及东坡派时,作者先把苏轼、秦观、张耒、晃補之、文同、孔文仲、唐庚等诗人的情况详加叙述,然后考辨其宗主:“苏派固无所专主,然必各受东坡影响;东坡固亦无所专主,然必对古诗家有所宗仰。”[6](P72)而在梳理前人六说的基础上,他又特别指出:“窃忖度之:盖东坡高才大力,无所不举,无所不好,然早年在蜀,学白乐天,中年入洛,出入欧公之门,受其熏染甚深,……欧公诗体宗韩愈,故公中年诗亦学韩愈,晚年谪惠州,始喜陶渊明……”[6](P73)通过这一番辨析,苏轼之诗受何人影响才算是水落石出。言及习尚,作者认为欧派习尚即东坡派之习尚,于是,在“重意”、“好述事”的层面两派相同。但两派虽然都“主气”,“欧阳派是气格,含有力气而拘定一格之意,故极力欲其诗之为奇怪奔险雄豪,东坡派是才气,不含力气之意,故任人之才气求词达而已,不欲限使趋于一体或加力为之,以成奇怪奔险雄豪也”。[6](P74)这种辨析十分精细,道出了两派在“气”上的微妙之处。至于“批评”,作者认为东坡诗派有一长四短:长在于“解放诗格”,“四短者何?一曰以文为诗,二曰议论,三曰好尽,四曰粗率”。[6](P75)
实际上,这部书最有看头之处应该便是“批评”部分的文字,因为那里正是作者的用武之地,所褒所贬颇见功力。例如,论黄山谷诗,作者先是指出“寡味”和“不自然”二病,然后进一步指出了第三病:
此外尚有一病曰沿袭。原山谷倡导脱胎法换骨法,未尝不是,要在融化运用之善否;善者直可超越原作,有出蓝之妙,否则直成沿袭剽窃,若谓山谷剽窃古人,吾固未之敢信;惟考唐贾至诗云:“草色青青柳色黄,桃花历乱李花香,东风不为吹愁去,春日偏能惹恨长。”山谷仅改“历”字为“零”,“李”字为“杏”,“东”字为“春”,“为”字为“解”,便以为己作……此类不胜枚举,似难免剽窃之讥。《滹南诗话》:“鲁直论诗有脱胎换骨点铁成金之喻,世以为名言;以予观之,特剽窃之黠者耳。”[6](P89-90)
在这一问题上,钱钟书亦有评说,但他说得更直接,亦由此及彼,由点及面,上升到了一个高度。兹引数语,以便对照:“在宋代诗人里,偷窃变成师徒公开传授的专门科学。王若虚说黄庭坚所讲‘点铁成金’、‘脱胎换骨’等方法‘特剽窃之黠者耳’;冯班也说这是‘宋人谬说,只是向古人集中作贼耳’。反对宋诗的明代诗人看来同样的手脚不干不净:‘徒手入市而欲百物为我有,不得不出于窃,瞎盛唐之谓也’……偏重形式的古典主义有个流弊:把诗人变成领有营业执照的盗贼,不管是巧取还是豪夺,是江洋大盗还是偷鸡贼,是西昆体那样认准了一家去打劫还是像江西派那样挨门排户大大小小人家都去光顾。这可以说是宋诗——不妨还添上宋词——给我们的大教训,也可以说是整个旧诗词的演变里包含的大教训。”[7](P18-19)若“教训”之说成立,那么,诗歌剽窃的合法化应该是始于江西派。
正因为这部书对宋诗派别的评说颇下功夫,今天看来,其学术价值依然不容低估。有学者指出:“梁昆的《宋诗派别论》,是一部专门从流派入手研究宋诗的力作……虽有泛流派的倾向,流派划分的标准也不统一,甚至有些名目失当,但仍有借鉴意义。”[8]
三
宋寿昌的《中国音乐发达概况》实际上是一本科普读物,正如本书《卷头语》中所言:“本书编辑的目的,在供给爱好音乐者具有音乐史的普通知识,故所述清晰而揭要,极易得到系统的领悟。”[9](P1)大概正是出于这一目的,这本书写得提纲挈领,要言不烦,但又描摹出了中西音乐发展的线索。例如,关于音乐效果,作者首先在三方面加以总结:“其一、是把音乐当做一种娱乐,用以调节疲劳,慰娱精神;这活动在音乐的效果中为最普通。其二、以音乐作为教化的工具,用它来陶冶性情,转移人心,以收潜移默化的功效;由这活动所生的效果,便是所谓道德的效果。其三、音乐从生活中反映出来,进一步而作神的表现时,就成了音乐的宗教活动。”[9](P1)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我国的音乐,向来侧重于上述第二方面的道德效果,这事实我们证之于各时代的史实,历历可考。”[9](P1)“中国音乐因为以道德的效果为中心,所以处处和政治发生密切的关系。像历代国势的盛衰,天下的治乱,以及帝王的文德武功,都象征于音律中间。”[9](P2)有了这样一个中心思想,作者便历数各朝各代音乐与政治的关系,雅乐与俗乐的此消彼长,乐器的进化和演变。整个看来,此书的上半部分便成了一个中国音乐简史。
下半部分作者特别指出,这本书并非音乐的“乐谱史”、“器乐史”、“乐制史”与“乐曲史”,而无非是想介绍一些音乐常识,为欣赏名曲做些准备。[9](P40)职是之故,作者虽然以“原始时代的音乐”、“上古时期的音乐”、“中世纪的音乐”、“近世的音乐”和“现代音乐”五个部分展开论述,但音乐家的地位凸显出来了。如谈到德国的浪漫派音乐时,作者分别分析了修裴尔德(Franz Schubert,今译舒伯特)、韦白(Kerd Mairavon Weber, 今译韦伯)、 孟德尔仲(Felix Mendelssohn Bartholdy,今译门德尔松)和修茫(Robert Schumann,舒曼)的音乐特点,浪漫派音乐重内容感情、重个性表现的音乐风格也因此较详尽地呈现在了读者面前。通过这种写法,我们似也约略感受到了中西音乐的一点不同:中国的音乐源远流长,但音乐家却寥若晨星,而谈及西方的音乐,许许多多的音乐家及其作品便扑面而来,那么,究竟该如何解读这一现象呢?
看来,我们得琢磨一下阴法鲁的说法了。他曾指出:“孤立的音乐研究很难做好,研究音乐需要丰富的知识,尤其是历史社会知识。研究音乐应该加上文化二字,音乐文化内含丰富,除音乐本身之外,凡是与音乐有关的内容,都是音乐文化研究的范围。”[10]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应该把他的《唐宋大曲之来源及其组织》看作一本音乐文化研究著作,它所涉及的东西也远远大于一般的音乐研究。
据阴法鲁说,他进入这一研究领域与导师罗庸和杨振声的指导密不可分。民国二十八年秋,他入北京大学研究院,两位导师让他研究“词之起源及其演变”,并强调研究词史要从“乐曲之见地,溯其渊源,明其体变”。“此时我开始接触一些古代音乐,起初我不懂音乐,通过有关古代音乐的记载,越来越体会到罗先生所说‘古代韵文是由于唱才发展起来的,唱是普遍的’这话是对的,用这种观点可以解释很多文学史上的问题。”[10]而在本书中,作者也如此写道:
为统计及分析当时之词调,曾先后纂辑“词调长编”及“乐调长编”两种。前者著录词调八百余,后者著录乐调两千曲。从事既久,颇有所得。乃就各个词调归纳门类,如何者属于大曲,何者属于杂曲等,先辨识清晰,然后分别逆溯其源,而由源返顾,复顺推其流……共为唐代之梨园法部所用者,谓之“法曲”;如仅截取其后半部分,则称为“曲破”。故法曲与曲破皆可归属于大曲。大曲盛行于唐宋而为两代音乐最高之典制。其影响所及,不惟产生若干词调曲调,即宋之杂剧,金之院本,元之杂剧亦莫不沿承其余绪。其在文学史上所居地位之重要,可想而知。[11](P1-2)
这段文字既讲治学心得,亦谈路径方法,顺便也解释了“法曲”、“曲破”和“大曲”几个专有名词,很值得玩味。沿着这种思路,作者遍搜唐宋大曲史料,分析大曲产生之背景,考订大曲渊源及曲名,辨析大曲之结构,活儿做得是极为精细的。查阅研究唐宋大曲的相关论文,发现许多人依然把这本书作为重要的参考资料,可见其价值之大。而此书只是在1948年出过一个油印本,觅之不得。此次出版,实为音乐研究界和文学研究界的福音。
还有一本书也涉及“组织”,这便是齐如山的《中国剧之组织》。所谓“中国剧”,书中“凡例”处解释为 “大致以北京现风行皮黄为本位”。[12](P1)而所谓“皮黄”,即现在的京剧(台湾称“国剧”),因京剧的腔调以西皮、二黄为主,故有“皮黄”之称。关于此0书,有研究者曾指出:“他写《中国剧之组织》的初衷是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戏曲艺术,以便服务于梅兰芳访日、访美演出,此书几乎涉及作为综合性舞台表演艺术的戏曲的所有方面,齐如山后来的许多重要理论都萌芽于此书,所以此书是齐如山戏曲理论的一个总纲。”[13](P24)大概正是因为此书“备译为西文,俾外宾知中剧之途径”[12](P1),故作者分为八章,在唱白、动作、衣服、盔帽靴鞋、胡须、脸谱、切末物件、音乐等名目下分而述之,而每一名目,又进一步细分论述,或详或略,可以说是把京剧中所涉及的东西一网打尽了。如谈到动作,作者细分为上下场、暗上暗下、行走、进门出门、举动、饮茶、饮酒吃饭、睡、舞、交战、其他小举动等多种,而说到交战,又区分出会阵、起打、过合、亮住、追过场、耍下场、架住、几股当、结攒、连环、出手、走边、起霸、趟马等,把京剧中交战的动作解释得格外清晰。笔者以为,这种书实可称为京剧宝典,内行人可看出门道,外行人也看得热闹,因为它普及了京剧知识。兹举一例。
谈及“背供”时,作者先是解释:“背供者,背人供招也,系背人自道心事之意。两人或数人,说话之时,其中一人,心内偶有感触,便用神色表现,以便台下知晓 (在真人,亦一定有此情形)。若感触之情节复杂,全靠神色表现,不易充足,则用白或唱,暗行说出。故打背供时,须用袖遮隔,或往台旁走几步,都是表示不使台上他人知道的意思。但有时一人场上歌唱,或说白,亦是自述心事之义,与背供意义,大致相同,不得目为无故自言自语也。”[12](P11-12)这种解释,已把背供的意思解释得一清二楚,更重要的是,作者又加一按语,有了延伸思考:
按背供一事,亦为中国剧之特点,东西洋各国戏剧皆无之。亦为研究西剧者所不满。惟鄙人则以为当年研究发明出此种办法来,实为中国剧特优之点。何也?因戏剧一有背供,则省却无数笔墨,省却无数烘托,而添出许多情趣。再者,西洋剧亦有一人在场上,自言一二语之时,而真人亦互有自言自语之时。其背供之来源,大致即由于此。况西洋歌剧,往往一人在台上自歌自唱,试问此系对何人说话?不过背供之义耳。[12](P12-13)
这种思考在中西剧的对比中确认京剧背供之优,很有道理,也让笔者想起了《沙家浜》《智斗》一场戏中对背供的改动。据汪曾祺回忆,《智斗》原来只是阿庆嫂和刁德一两人的“背供”唱,江青提出要把胡传魁拉进矛盾中来,由两人“背供”唱改为三人“背供”唱,汪曾祺等人接受了修改意见,并认为这种改动很有道理。因为“这样不但可以展开三个人之间的心理活动,舞台调度也可以出点新意,——‘智斗’的舞台调度是创造性的。照原剧本那样,阿庆嫂和刁德一斗心眼,胡传奎就只能踱到舞台后面对着湖水抽烟,等于是‘挂’起来了”。[14](P240-241)这意味着即便是革命现代京剧,背供也是必不可少的。不仅此也,而且还要在背供上狠下功夫,由此可见背供在京剧中的重要地位。
齐如山1948年去了台湾,但他对京剧艺术的贡献已惠及海峡两岸。有人指出:“在实践上,他成就了一代京剧大师梅兰芳,将中国戏剧推向世界……对这位学人在戏曲研究方面的成就和贡献,学术界有着很高的评价,或将其与王国维、吴梅并列为‘近代三大戏剧学家’,或称其为‘中国的莎士比亚’。”[15]这种赞誉之词,齐如山应该是承受得起的,因为从这部早年论中国剧的书中,我们已见识了作者的上乘功夫。
四
王钧初后来以胡蛮为笔名行世,笔名的名气也就遮盖了本名(他原名王洪,字钧初)[16],但《中国美术的演变》却是以其本名面世的。据研究者统计,民国时期,不少学者都写有中国美术或绘画史之类的著作,计有近20部之多。[17]那么,在这些著作中,《中国美术的演变》究竟具有怎样的特色呢?应该是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首开了马克思主义美术史的先河。而之所以如此,又与他的特殊经历有关。有研究者梳理,王钧初1929年从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西画科毕业后,随即东渡日本考察艺术,接触过一些革命美术家,访问过日本左翼美术家联盟。1930年冬,他加入“美术家左翼联盟”,并以《艺术起源于劳动》为主题做过演讲。不久又阅读苏联伏里契的《艺术社会学》和马恩列斯的译本著作。[18]所有这些,都让他的美术著作打上了唯物史观和左翼的烙印。例如,他认为“线”的艺术和“色”的艺术的起源,是同时从劳动中生发而来的。前者是由于“尖骨器”的使用,后者则是因为“火”的启发和生理上感官的遗传。[19](P10)他谈“龙”为什么在中国艺术上能成为一种尊贵神圣的象征时特别解释道:《易经》上有“云从龙”之语,“龙”和“雨”便有了神秘联系。农民每遇旱灾,向“龙王爷”求雨便成惯例。“这主宰了中国人民的农业经济的背景的‘雨水’,简直是人民生命攸关的唯一信仰,因而,‘龙’在中国美术上,历代不绝的都有显现。正因为人民迷信它,皇家便顺便的利用它。‘龙’的图案成为‘御用’的和贵族的装饰,以及旗帜上和建筑上雕刻上的取材。”[19](P5-6)像这种论述和判断,没有唯物史观的原理做支撑,是断然写不出来的。而至20世纪40年代王钧初写《中国美术史》(1942)时,他更是依托延安《讲话》精神,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运用得更自觉也更娴熟了。有论者指出,王钧初的《中国美术的演变》与《中国美术史》联系紧密,后者可看作对前者的发展和深化。其研究特点概括有三:“一、在美术起源问题上,打破了传统的神话史观、英雄史观,提出了艺术(美术)起源于劳动说。二、在影响美术发展的各种外部因素上,强调了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三、在美术创造动力论上,坚持以人民为本位的思想。”[20]单单验之于《中国美术的演变》一书,这种概括也是可以成立的。
此书凡21章,每章标题一正一副。即便以今天的眼光看,这些题目也起得颇有新意,是很能吸引眼球的。如《艺术起源的烟幕——一些荒诞不经的传说》《从武器到食器——从狩猎生活到农业生活》《铁的火花与奴隶的血汗——伴着工具的发展而来的文明曙光》《漆,简,笔,纸,砖头,瓦片——自然条件,生产条件与社会生活之综合的形态》《艺术圣人与民间艺术——从鲁班,吴道子,说到样子雷,画丁,刘篮塑》等,即可一见端倪。而全书行文活泼,其语调则不时显露出革命美术家的一些霸气,亦可看作此书的文风特色。
从出版的年份上看,《艺术丛论》虽晚于《中国美术的演变》两年,但书中收录的文章,其写作年代却更早一些(多在1928年前后);而从年龄上看,林风眠虽大不了王钧初几岁,是一代人,但在资历却比他老,名气和影响力也比他大许多。1925年,王钧初才考入国立北平艺专,而留法归来年仅26岁的林风眠已是这所学校的校长了。1928年,林风眠又在蔡元培的赏识和提携下,出任中国第一所高等艺术学府——西湖国立艺术院的首任院长。《艺术丛论》收录文章9篇,首篇写于1926年,末篇写于1934年,实际上就是他从北平至杭州期间的代表性思考。而由于作者本人首先是画家,回国后看到艺术界一片乱象,同时他又身居要职,所以,这一时期他一直在“大声疾呼”[21](P1),其拯救艺术于萎靡、于混乱的拳拳之心溢于言表。
这大概得益于作者虽年纪轻轻,却对中西艺术(尤其是绘画)都有深切的体会。在他看来,中国旧有的艺术,自唐宋以降,一直在走下坡路,乃至走到了穷途末路:“元明清三代,六百年来绘画创作了什么?比起前代来实是一无所有;但因袭前人之传统与摹仿之观念而已。”[21](P122)及至现代,国画几乎已是山穷水尽,西画也不过是“摹得西人两张风景,盗得西人一点颜色,如此而已”[21](P90)。于是他力主“调和东西艺术”,发起所谓的“艺术运动”,大概唯其如此,才能找到真正的艺术复兴之路。而在他那篇“大声疾呼”之最——《致全国艺术界书》(1927)中,其艺术主张、拯救方案、实施措施等等可谓一应俱全,今天看来依然价值不菲。
这就不得不涉及林风眠与王钧初在艺术观上的重要区别。如前所述,王钧初是“艺术起源于劳动”的信奉者和阐释者,但林风眠却不吃这一套,他认为艺术起源于情绪或情感:
艺术为人类情绪的冲动,以一种相当的形式表现在外面,由此可见艺术实系人类情绪得到调和或舒畅的一种方法。人类对着自己的情绪,只有两种对付的方法:前一种在自身或自身之外,寻求相当的形式,表露自己的内的情绪,以求调和而产生艺术。后一种是在自身之内,设立一种假定,以信仰为达到满足的目的,强纳流动变化的情绪于固定的假定及信仰之中,以求安慰而产生宗教。[21](P5-6)
由此出发,林风眠就把一切社会问题都归结为感情问题,而“艺术是感情的产物,有艺术而后感情得以安慰”[21](P22)。艺术与宗教同根同源,相因相生,二者都能解决人的感情问题,但因为中国并无宗教,“以艺术代宗教”便成为可行之举。在这一层面,他受蔡元培影响之深亦可见一斑,因为他说过:“蔡元培先生所论以美育代宗教说,实是一种事实。”[21](P7)然而,若要艺术担此重任,首先必得对现行那种不死不活的艺术进行改造。因为中国社会在他看来:“一面是贪官污吏以及军阀走狗们的腰缠十万,厚搾民脂,以供其花天酒地,长大疮,养大疮,医大疮之用。一面是农工商人的汗流浃背,辛苦奔波,以其所有供给官吏兵匪之豪用,家则妻啼儿号,己则茹苦尝辛!”[21](P36)如此情势,艺术家们本应关注社会,体察民情,把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作用于艺术,但实际上,他们却完全是另一种样子:
中国画家们,不是自号为佯狂恣肆的流氓,便是深山密林中的隐士,非骂世玩俗,即超世离群,且孜孜以避世为高尚!
在这种趋势之下,中国的艺术,久已与世隔别。中国人众,早已视艺术不干我事。遂至艺术自艺术,人生自人生。艺术既不表现时代,亦不表现个人,既非“艺术的艺术”亦非“人生的艺术”
可以看出,林风眠对此现象是痛心疾首的。所以他要大声疾呼,既是在“为艺术战”,也是在“与庸俗战,与因袭保守战,与生搬西洋战”。[22]与此同时,他自己又身体力行,自创出一条中西融通的路子。陈醉指出,作为一代艺术大师,徐悲鸿与林风眠的贡献都在于改革:“徐悲鸿的功绩是用西洋画改革了中国画,使之得到更新的发展。而林风眠的功绩,则是用中国画改革了西洋画,使之得到更广的传播。”[23]而在笔者看来,林风眠之所以能改革成功,得益于他对中西艺术的熟稔和精研妙用。例如,《艺术丛论》中的《中国绘画新论》(1929)一文,洋洋洒洒,中国画之美处妙处,被他解析得入木三分。而西洋画,尤其是西方现代艺术,用其弟子吴冠中的话说,是“他自己钻进去认真学习过,研究过,他懂,懂了就不怕。电工不怕电,指挥电操作”[22]。而即便在今天看来,林风眠的艺术创新之路对于我们依然具有重要的启迪。因为在文学艺术领域,中西问题至今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于是常有“食洋不化”的警钟长鸣。食洋不化肯定是有问题的,但化的前提是你得像林风眠那样,有一个很强大的中国胃口。
五
最后,要谈一谈潘光旦的《小青之分析》了。书中所谓的小青即冯小青,是明朝末年的年轻女子,风姿绰约,才华出众。但下嫁冯生做妾后,大妇奇妒,便把小青打发到了孤山佛舍。小青遂郁郁寡欢,以泪洗面,“辄临池自照,好与影语,絮絮如问答,人见辄止”。后一病不起,死时年仅18岁。小青死后,为她立传者不少,其作品(古诗一首,七绝十首,《天仙子》词一首和《寄杨夫人书》一封)亦被人编辑成集,定名《焚余》。她的生平事迹也被改编成故事,写成剧本,搬上了舞台。1922年,时在清华读书的潘光旦修读梁启超的“中国五千年历史鸟瞰”之课程,课程结束时他提交《冯小青考》,以为作业。梁启超读后大为赞赏,遂写评语如下:“对于部分的善为精密观察,持此法以治百学,蔑不济矣!以吾弟头脑之莹澈,可以为科学家;以吾弟情绪之深刻,可以为文学家。望将趣味集中,务成就其一,勿如鄙人之泛滥无归耳!”《冯小青考》初发表于1924年的《妇女杂志》上,1927年,他又对《冯小青考》加工修订,易名为《小青之分析》,由新月书店出版。1929年再版时,复改书名为《冯小青——一件影恋之研究》。[24](P3)
潘光旦对冯小青现象穷尽各种资料,反复考查,其研究用意何在?其研究结果如何?应该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小青生平事迹甚离奇,亦甚哀艳。前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于是群疑其伪托,以为绝无其人”[25](P11)。而通过其考证,他认为小青实有其人,其事迹并非凭空虚构。二、更重要的是,他使用了新的研究方法,得出了与前人完全不同的结论:“小青适冯之年龄,性发育本未完全;及受重大之打击,而无以应付,欲性之流乃循发育之途径而倒退,其最大部分至自我恋之段落而中止;嗣后环境愈劣,排遣无方,闭窒日甚,卒成影恋之变态。”[25](P71)
把小青看作影恋病例之典型,可谓石破天惊之语。因为小青哀艳的身世,出众的才华,实在是很能获得人们的同情的。有研究者甚至指出:“传者的态度,表明了男性文人对于才女文化的欣赏和支持。”“通过小青与大妇的对比,寄托了晚明男性文人对于女性一种新的性别想象和位置期待。”[26]然而,潘光旦的研究却戳破了男性文人的那种幻觉,指出了一个严酷的事实。而他之所以能独辟蹊径,又是与其特殊的学术经历密不可分的。据他自己讲,20岁在清华读书时,他便读过霭理士六大本的《性心理学研究录》。很快他又接触到了弗洛伊德的学说。“同时,因为译者一向喜欢看稗官野史,于是又发现了明代末叶的一个奇女子,叫作冯小青,经与福氏的学说一度对照以后,立时觉察她是所谓影恋的绝妙例子。”[27](P2)由此看来,潘光旦的这项研究,实为西学东渐与中国古代例证碰撞之后结出的一枚果实。
进一步追问,为什么潘光旦会去做这项研究呢?从他书中的“余论”中我们已能看出许多眉目。他指出:
改造社会对于欲性及性发育之观念,实为目前当务之急。观念既趋正轨,然后性教育之推行得所指引,而适度之男女社交亦可实施而无危害。为父母者,去其溺爱,则母恋中滞之现象即可随之减杀。发育期内,女子之有自我恋之倾向者,大率因深居简出,又绝少闺中良伴,致欲力之流,日趋淤塞;其行动略较自由,交友范围略较扩大者,又多流入同性恋一途;是亦欲流之中滞为之。是以女子教育兴,而自我恋之机绝;男女同校与社交公开之制立,而同性恋之风衰。同一欲力活动,同一须有活动之对象,由自身而同性而异性,亦即由可能的变态而归于常态;是则社会之欲性观与性发育观革新后必然之效也。[25](P86-87)
潘光旦后来成了著名的教育家、优生学家,而从这段文字中亦可看出,他在青年时代即有了思考国计民生的大气象。于是,他虽分析的是晚明人物,其用心却在当今社会。而社会能正常发展,全赖人之身心能正常发展也。男女的身心能否进入常态,而不坠入变态,春机发陈阶段又非常重要。由此看来,无论是他研究冯小青,还是翻译霭理士,其价值都超出了本身的学术领域,而成为一件有益于世道人心的事情。
实际上,《小青之分析》已跨越了学科边界,它首先应该属于性心理学,却又波及社会学、文艺心理学等学科。有人甚至在文学批评学的层面释放其意义[28],笔者认为也是可以成立的。
六
逐一写完笔者对每本书的一点心得之后,笔者可以写几笔关于它们的总体印象了。
可以说,这些著作大都是他们早年的研究成果,有的甚至可算得上是其“少作”,但我读这类书,却丝毫没有青涩之感,而是觉得很老到,仿佛他们已是治学多年、功力深厚的长者。他们写出来的书也往往不厚,并非皇皇巨著,却很有干货,问题也谈得通透。而之所以能如此,大概是因为他们首先以学术为志业,心无旁骛,加之国学功底本来就好,年轻时又出洋留学,这样便能启获新知,激活古籍,“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林语堂语),最终形成自己的真知灼见。而更值得重视的是他们为学背后的“人间情怀”。吕澄谈论美学,落脚点是“艺术与人生”;潘光旦思考小青之影恋,落脚点又在女子教育和社会常态上;林风眠更是力推艺术教育,倡导“为人生而艺术”,而要想让艺术有益于世道人心,前提是它必须绝假纯真,成为真艺术:“艺术不比别种东西,它的入人之深,不分贤愚,只要是件真正的艺术作品,其力足以动一人者,也同样可以动千百人而不已。”[21](P95)凡此种种,都可看出他们并非为学术而学术,或仅仅把学术看成是“为稻粱谋”的工具,而是有着更大的抱负、更重的担当和更多的责任。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第一身份虽然是学者,是艺术家,但他们一方面发扬着中国古代的士人传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语),另一方面又接通了西方世界业已成型的知识分子传统——追求正义,守护理念,批判社会,谴责权势。
当然,这样一来,他们的学术就有了一种乌托邦精神。在汉语语境中,“乌托邦”常常被理解为“社会乌托邦”,其贬义的意味往往较浓。而在德国学者布洛赫(Ernst Bloch)看来,“乌托邦”与“希望”(hope)、“朝前的梦想”(forward dream)等概念的意思相近,“乌托邦的”则与 “希望的”(wishful)、“期盼的”(anticipating)等概念的意思相仿。他用“乌托邦的”来意指世界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精神倾向:趋向(尚未到来的)更好状态的意向(intention)。这一精神现象表现在各个方面。因此,乌托邦远远超出了“社会乌托邦”的范围。换言之,“社会乌托邦”只是乌托邦的一个侧面,除此之外,还有技术、地理、建筑、绘画、音乐以及宗教等等之类的乌托邦。[29](P18-19)在此语境中我们不妨说,这些民国学人普遍有一种“艺术乌托邦”或“学术乌托邦”的情怀。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情怀,他们的学术和艺术才了一种气象,有了一种我们已经久违的精气神。
徐复观曾经指出:“一切伟大艺术家所追求的,正是可以完全把自己安放进去的世界,因而使自己的人生、精神上的担负,得到解放。”[30](P194)而这一点,可以说林风眠做到了,他的追求和选择,或许也可以为这批学人的追求和选择做出一个意味深长的注解。
[1]李林.吕澄是谁?——汉语佛学界最严重的遗忘[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2006,(5).
[2]吕澄.美学浅说·色彩学纲要[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
[3]高海燕.吕澄美学思想的研究[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13,(5).
[4]范寿康.艺术之本质[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4.
[5]张世禄.中国文艺变迁论[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
[6]梁昆.宋诗派别论[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4.
[7]钱钟书.宋诗选注·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9.
[8]张远林,王兆鹏.宋诗分期问题研究述评[J].阴山学刊,2008,(4).
[9]宋寿昌.中国音乐发达概况[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
[10]曾贻芬.阴法鲁先生访谈录[J].史学史研究, 1997,(2).
[11]阴法鲁.唐宋大曲之来源及其组织[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
[12]齐如山.中国剧之组织[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
[13]李军.齐如山戏曲理论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 2008,(5).
[14]汪曾祺.汪曾祺全集(5)[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15]苗怀明.齐如山的戏曲研究与治学特色[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6).
[16]王留成,邢长顺.胡蛮传略[J].中州统战,1996,(6).
[17]林树中.近代中国美术史论著与上海美专[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1,(6).
[18]赵丹.时代思潮下的创获:胡蛮学术贡献概述[J].美术观察,2014,(1).
[19]王钧初.中国美术的演变[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
[20]李小汾.论民国时期胡蛮美术史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倾向[J].美术研究,2007,(2).
[21]林风眠.艺术丛论[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5.
[22]吴冠中.百花园里忆园丁——寄林风眠老师[EB/ OL].http://lz.book.sohu.com/fullscreen-chapter-226354.html.
[23]陈醉.思考林风眠[J].美术观察,2000,(1).
[24]潘光旦.冯小青性心理变态揭秘[M].祯祥,柏石,诠注.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
[25]潘光旦.小青之分析[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4.
[26]张春田.“影恋”,性心理与“病”——潘光旦写冯小青[J].书城,2008,(9).
[27](英)霭理士.性心理学·译序[M].潘光旦,译注.北京:三联书店,1987.
[28]赖力行.潘光旦《冯小青:一件影恋之研究》的文学批评学意义[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2).
[29]陈岸瑛,陆丁.新乌托邦主义[M].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
[30]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
【责任编辑:张 丽】
I206.5
A
1004-518X(2016)05-007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