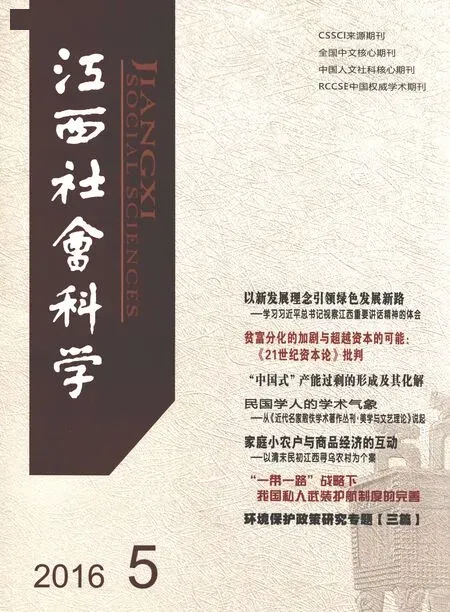新中国成立初期灾荒中的民众与地方政府互动
——以1953年河南省内乡县春荒为例
■李玉峰
新中国成立初期灾荒中的民众与地方政府互动
——以1953年河南省内乡县春荒为例
■李玉峰
在接连遭遇了水灾、旱灾以及虫灾等诸多灾害后,1953年4月,河南省内乡县境内再次遭受霜灾和旱灾,庄稼严重受损,粮荒问题严峻。时值新旧社会交替之际,面对一系列不同于过去的意识形态和治理方式,民众和地方政府对灾荒的解释和应对也势必受到影响。
新中国成立初期;灾荒;意识形态;民众;政府
李玉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生。(上海 200241)
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灾荒问题,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灾害情况和官方救灾政策及其实施过程的介绍和描述上,在其中却没有多少那些面临灾荒威胁的民众如何动作的身影和声音。这样叙述出来的灾荒史难免是跟事实或多或少有所隔膜的。
通过考察1953年春夏之交发生在河南内乡县境内的一场小灾荒,本文旨在探求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一系列不同于过去的意识形态和治理方式时,民众与地方政府在灾荒中如何互动,民众如何解释灾荒和应对其生存困境;地方政府又是如何理解民众的这些解释和应对,进而又采取怎样的措施来解决相应的问题。
一、对灾荒的解释和应对
1953年4月11和12两日,地处河南省西南部的内乡县境内天降酷霜,庄稼严重受损,夏季作物受灾面积达50万亩,占全县耕地面积83.23万亩的60%多。使情况变得更糟糕的是差不多同时还发生了旱灾。[1](P33-34)[2]1952年,由于水灾、旱灾以及虫灾等诸多灾害,内乡县委评估全县夏秋两季粮食收成都只有平常六成年景。全县受灾面很广,其中师岗、杨集、城关等三个区受灾最为严重。县委估计以勉强维持生活的最低限度来算,全县也平均欠粮两个月。到1953年1月时,根据官方调查统计,七个区已有1221户3611人出现断粮,甚至师岗区姚营乡发生了卖孩子度荒的现象。[3][4]故而到4月份的霜灾和旱灾发生时,势必有更多的人正面临粮食无以为继的局面,春荒未过,夏荒又要到来。
(一)民众的解释和政府的方针
传统社会有将自然灾害与天意和统治者的德行及治理质量联系在一起的习惯,这也影响到了内乡县底层民众对这种危及自身生存困境的解释。他们把灾害误解成是中共这个新 “朝廷”带来的,一些传闻时有可闻。[2][5]
与民间将灾荒与统治者是否顺应天意民心联系起来的解释不同,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来分析中国灾荒史的邓拓认为,封建剥削的加强导致了中国历代几乎所有的灾荒。[6](P2,P59-61)新中国成立初期,主管全国救济工作的董必武和谢觉哉先后表达过与之相似的看法。对于新中国刚成立时的灾荒,他们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日本的入侵和国民党的反动导致的长期战争的影响,严重削弱了人民抗灾的力量。[7][8]这直接体现在处理全国范围灾荒不断的问题时国家财力有限,能够提供给人们的救济也有限。因而,政府明确主张对灾荒应“生产自救、节约渡荒、社会互助、以工代赈,并辅之以必要的救济”,号召大家共同努力来加以克服和解决。[9]
内乡县委在处理1952年的歉收所可能带来的灾荒时,即按此方针强调要宣传教育群众自力更生,扭转其单纯依赖政府救济的思想。[3]与灾荒的天人感应宇宙论联系在一起的是,中国帝制时期的官府重视其自身作为灾民的救济者和保护者的角色,以维护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和社会秩序的稳定。皇帝和官员们对于受灾民众自认为负有家长式的“养民”责任[10](P518-519),民众遇到灾荒亦仰赖政府救济。中国共产党人视灾荒的天人感应说为封建迷信,但党和国家同样重视自己对民众的责任,我们党的意识形态要求党员干部“为人民服务”。内乡县委1953年初即要求其基层干部 “保证受灾农民不受冻饿之苦,不逃荒,更不能冻饿死一人,并加强一定的责任制”。但其目的不仅仅只是“为了使灾民不受冻饿死之苦,顺利渡过灾荒”,“同时也是为了保证1953年农业爱国丰产的任务完成,为大规模经济建设奠定良好基础”。[4]一方面限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财力有限,另一方面需要民众发展生产为国家经济建设做贡献,所以强调要破除民众依赖政府救济的思想,“要求每一个群众必须想出他自力更生的办法”[3],生产自救为主,辅以社会互济,政府救济作为最后手段。
(二)缺粮民众的个体应对
类似1953年4月份的这种灾害情况在内乡县历史上并不鲜见,一旦发生灾荒,政府又救济不力或无力救济,那么没钱没粮的普通民众就选择有限,为了生存往往被迫要么逃荒乞讨,要么做土匪。[11](P212)
此次,面对春夏作物即将减产甚或绝收的可能,本就正处于缺粮状态的人们也像过去一样面临有限的选择,他们也以其习惯采取实际的应对措施。缺少粮食又无钱购粮的人有些选择了出去逃荒要饭。新中国成立初期,有大量流民包括灾民在全国各地流动,尤其是流入谋生相对容易的城市。这势必不利于农村地区灾后的恢复和重建,且影响到流入地(尤其是城市)的社会秩序。1950年初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即在关于生产救灾的指示中要求各地劝止灾民“盲目逃荒”。[12]同年3月和4月份,内务部又接连发出《关于帮助外逃灾民回籍春耕的指示》和《关于帮助灾民外移和回乡生产的指示》,明确反对盲目逃荒,强调灾民应该就地生产自救。对于已经外逃的灾民,要及时劝导并在自愿原则下有组织地及时遣送还乡。[13](P161-163)1953年春,不少地区出现大量农民包括灾民流入城市的现象,针对此政务院在4月17日发布指示,要求制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为农民进城找工作开具介绍信的基层政府受到指责,政务院要求它们负责将由其开具介绍信到城市求职而找不到工作的农民动员还乡。[14](P2012-2013)
按照中央禁止农民盲目流动的指示,内乡县委也禁止干部 “不负责任的开路条介绍逃荒的作风”,要求对灾民要就地组织生产。[4]但在1952年就受灾严重的师岗区,部分家庭到此时已严重缺粮甚或出现断粮,受到1953年霜灾的新打击后,眼看夏粮也收不到了,有些人就到区政府去要求开证明到陕西逃荒。还有一人把老婆孩子打发出去要饭度荒,自己选择了上吊自杀。也有人不得已把小孩卖掉度荒。[2]
1948年5月内乡解放后,经过一年多对土匪的打击[1](P287-292),对投降登记的伪匪头目等的集训和管制,以及对民间残留武器的收缴等,民间像过去一样组织为匪的条件实际上已经丧失。所以,在1953年的这次灾荒中做土匪或暴动抢粮的情况倒是未再出现。但也出现了新形式的抢粮:有借无还的强迫“借贷”。如马山口区岳岗乡干部召集余粮户开会动员他们往外“借”粮,有52户被迫借出2005斤[15],对于那些他们怀疑有粮却不肯或少往外 “借”的10户还进行了搜查。[16]有一个代表区共有17户农民,其中16户联合起来向1户借粮。偷盗粮食的案件也在这一时期急剧增多。[2]
二、政府的售粮政策和民众的不满
自1941年起,由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的长期影响,内乡县的粮食市场一直处于紧张状态,粮价不断攀升。[17](P142-144)内乡解放后,这种状态并未好转,实际上由于战争仍在继续,新中国为了军粮需要在当地大量征收公粮,粮食市场更加紧张,供应紧缺,价格不断上涨。出于当时对私有经济的认识,政府认为是因为少数粮商囤积粮油,抬高粮价,牟取高利所致。为了“正确组织粮油贸易”,1950年6月内乡县根据上级命令成立了内乡粮店,负责管辖内乡县及临近的西峡县和淅川县的粮食市场。私人粮商受到抑制。[17](P80-81,P144-145)但直到1953年上半年国家尚允许私人粮商的存在,针对不少地方盲目排挤私商合法经营的情况,中共中央还于1952年11月指示要“保留20%-30%的粮食及主要经济作物,给私商经营”[18](P396)。因而粮食也有牌价(即由政府规定的国营粮店的价格)和市价两种价格。1953年春河南省的粮食市价高出牌价10%~20%。[19](P70)霜灾发生后内乡县附近的邓县罗庄市场上麦子和玉米的市价,分别比内乡县城关国营粮店牌价高出约25%和38%。[2]
内乡县农民自然愿意到价钱更低的国营粮店购粮,但这需要先到其所属的乡政府开具准许购粮的条子,然后才能凭条购粮。对于农民开具购粮证明条的请求,刚开始乡干部们一般都有求必应。内乡县委认为这种情况是乱开条,是乡干部们不负责任、怕得罪人的表现,于4月23日在下发的文件中对之予以严厉批评,并规定谁再乱开条子就给予严重处分,要求区干部要负起检查监督的责任,否则也要受到处理。[20]此后,民众再去乡政府开购粮条就遇到了困难,恼火之下也有人叫嚷要踢不给开条的乡政府的摊子。[2][21]
内乡县委这时之所以限制乡干部给农民开购粮条,是因为其手中粮食库存不多,没有那么多粮食可售,故而不得不实行限购办法:每人每次最多购买20斤小麦和10斤玉米。手中并不宽裕的农民在购粮时更愿意购买比小麦便宜的玉米,但政府粮仓储备中玉米较少,故而对玉米的限购更厉害。对此农民很不满。
政府开仓售粮的地点最初限定在县城、马山、赤眉和夏馆等四处。在县城、马山和赤眉三处,买粮的人很多,单在县城一处,4月21—24日每天少则有1000多人,多则近3000人购粮。位于北部山区的夏馆区缺粮并不严重,政府还能在当地收购玉米。反而缺粮严重的地区如师岗等地最初并未开仓售粮,师岗每逢赶集日想要购粮的人都有几百,议论纷纷等待开仓售粮。政府对粮食市场的限制以及粮食限购政策,使在灾荒阴影之下的群众更加焦虑不安,各种不满怨言、谩骂和谣言纷纷指向政府及干部。[2][5]
针对粮食问题引起的紧张局势,内乡县委一方面布置加强治安防范和护仓工作。县公安局4月20日即下了一个紧急指示到各区,要求严防敌人煽动群众暴动抢粮库,加强基干民兵对各区仓库所在地的看守。4月23日县委进一步要求各区把公安干部分配到粮库所在地进行工作,以搞好保卫仓库工作。同时要求干部要对群众普遍进行售粮政策教育,以消除农民的埋怨情绪。另一方面也根据情况不断地进行售粮上的调整,当部分地区开仓限售的政策不仅未能解决甚至加重了粮食的紧张局势时,县委决定从4月26日起暂停售粮,转而采取群众评议购粮的政策,由干部组织、领导群众开会讨论决定谁可以获得买粮食的资格和数量,评好后再售粮。为保证这个工作的顺利进行,县公安局于26日召开了各区公安员会议,27日上午公安人员分途下区,当天下午或晚上各区组织进行了购粮评议。公安局同时成立了两个重点侦查小组,负责侦破该时期的破坏活动。[20][2]
由于本县的粮食储藏不够供应,这时内乡县委也向上级请求了援助,5月4日确定获得外区援助的粮食并开始调运。在获得粮食援助后,内乡县委指示各区乡进行了第二次购粮评议,将购粮面扩大至各区人口的25%,购粮数限定为每人每天半斤,每人购粮数为7斤。同时规定将不超过各区购粮数15%的部分转变为贷粮,以帮助那些在购粮数内买不起粮的户。县里还给各区少量的救济粮,对于上次评议出的贷粮户中真正还不起的可转为救济粮发放对象,规定“每户救济可多可少,但面不要太宽”。县委指示中还提及区乡政府对有粮户可以号召其出卖或出借粮食,但不能强迫他们这么做。同时又提及可以 “揭发批判有粮囤粮发灾荒财的错误”。[22]这二者实际上是有矛盾的,揭发批判“有粮囤粮发灾荒财”必然会导致强迫。
群众评议购粮显然分化了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不满,许多缺粮农民得到了基本口粮的保障,因而不再抱怨。但也有部分在群众评议中未能评得购粮资格的人表达了更强烈的不满。地方政府对此次评议购粮中和此前一段时间内比较突出的不满分子采取了“扣押法办”的措施。[2][5]
三、集体应对:政府提倡的和禁止的
(一)政府提倡的:生产救灾、节约度荒
在想方设法解决粮食供应紧张问题的同时,内乡县委也根据中央既定的生产救灾方针采取了另外一些措施。一是号召大家节约,采集野菜等代食品。以野菜充饥历来是民间青黄不接时自救的手段之一。就内乡县来说,山区或靠近山区的地方可采集的野菜资源多一些,平原地区就差一些。但这次灾重的师岗、杨集和城关等地恰恰处于平原地区。二是号召农民种植早熟作物,并帮助部分地区解决缺种困难,贷给农民南瓜子154斤,玉米种50 000斤。三是号召“生产救灾”、浇水保麦。在有水利设施的地方,该项工作贯彻得较好,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是群众因为争水而冲突打架,如赤眉区就发生了十多起这样的事故;二是用水不当造成浪费。但全县有水利的土地毕竟是少数,一共也就浇了不到两万亩的地。在没有水利设施的地方,政府号召担水浇麦。这种方式效率很低,群众普遍对这种生产救灾方式没有信心,认为浇水无效。个别地方发生了强迫民众集体担水浇麦的现象。全县有四个区八个乡在4月19日到23日的五天时间里发动约9000担水浇麦,共浇地2528.7亩。[2][5][16]这对全县的受灾面积来说实在是杯水车薪。
(二)政府禁止的:求神祈雨和拜神求药
面对频发的旱灾[1](P1,P77-80,P108-9),内乡县民众更习惯的集体应对方式是祈雨。1953年春的旱灾在内乡县境内引发了普遍的祈雨事件,据内乡县委在6月3日给南阳地委报告中统计,4、5两月全县共发生44起求神祈雨事件。[16]4月底5月初内乡县境内下了一些小雨,灾情减轻,民众普遍认为这是祈雨灵验了,于是再组织向受益的各农户收钱或者粮食举行仪式还愿谢雨。组织和主持祈雨和谢雨(下统称祈雨)的历来都是地方社会的头面人物,1953年的内乡县则是转业军人、乡村干部等当时的新地方精英成为各地祈雨仪式的重要组织者和主持者。[21]
与传统政府从中央到地方都参与祈雨不同[6](P187-194)[23],新政权将祈雨视为封建迷信。内乡县政府对民间自发的祈雨加以了阻止。但官方的阻止是许多面临灾荒心急如焚的民众所不能理解的,阻止的行动往往激起民众的不满,甚或偶有激烈的人身冲突在祈雨群众和阻止的干部之间发生。地方政府将冲突视为是敌人的阴谋破坏导致,将组织祈雨的为首人员抓了起来。[5]
不知是否为了规避政府的打击锋芒,在祈雨活动中出现了众多由寡妇出面组织的情况,对此种现象,地方政府亦格外警惕其背后的煽动和主使之人。
拜神求药与求神祈雨同样被新政权视为封建迷信,这两者有时会相伴发生。典型的如1953年4月下旬发生在内乡县师岗区的永青山拜神求药事件,这一事件发生的契机就是祈雨并且在祈雨后不久碰巧下了雨。民众一致认为是永青山顶大王爷显灵,大王爷灵验和舍药的消息广泛传播开来,内乡县及临县淅川、邓县一些地区的民众听闻消息后纷纷前来永青山求药,达到每天数百人的规模。[24][25]
拜神求药契合了缺医少药的贫困民众治病消灾的实际生活和心理需求,长期以来在中国各地普遍存在。但当时地方政府不仅要担心这种落后迷信对农业生产的冲击、对部分参与者人身的危害、对政治秩序的影响,还要担心拜神求药事件是否是被会道门等反革命敌人制造和操纵的。所以,官方将关于拜神求药的言传信息界定为一种谣言,并且采取有力的措施试图全面消灭这种习俗。[26](P369-381)河南省公安厅和南阳地区公安处在内乡县此次春荒之前即分别向其下属的各公安机关发出过平息类似的迷信取药事件的通报。[24]
县公安局获知大量民众去永青山拜神求药的消息后,就组织了一个工作组于5月15日前往调查情况[24],21日开始采取措施打击和平息此次求药事件。首先组织乡公安员为主的干部,在前往永青山的各个要道口,对前来求药的人进行劝阻。其次以县卫生院的两个医生为首组织当地医生开展就地治疗,结合进行宣传。同时通过学校渠道教育学生规劝自己家庭及近邻不要再迷信上山取药。最重要的一个措施是逮捕和公开处理了跟这次求药事件的兴起和扩散有关的几个“坏分子”:王永柱和神婆等人。[25]
同一时期拜神求药的事件在内乡县发生多起。[27]政府采取的劝阻或制止群众再去求药,尤其是公开惩罚“事件主要造成者”的措施,可以暂时平息其正处理的求药事件,但并未能杜绝此类事件的持续发生。一个多月后,内乡县境内又不断出现群众性的拜神求药现象。[27]此后类似事件在内乡县也广泛存在。内乡县委也认识到这是因为 “当前我们的卫生工作赶不上群众的需要”,但还是将此类现象定性为“敌人抓住我们每个工作的缺点与群众的落后迷信思想,暗示煽动组织群众进行破坏活动”。[27]
从传统社会基层民众自我调适的角度看,祈雨之类的民间活动能为人们提供某种心理安慰,其焦虑不安的情绪通过集体仪式得以纾缓,在旱灾带来的社会危机中或可起到某种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拜神求药实际上也为无钱看病或当时的医疗水平一时无能为力的病人提供了一种安慰剂。但是,这样的民间习俗或传统毕竟迷信色彩居多,同时更因其属脱离政治控制的大规模集体活动,在敌我斗争形势下容易被敌对势力所利用,因而从地方政府的视角,只能加以抑制和平息。在这种情况下,如民众因为基于传统习惯表示不满或反抗,自然也就更容易被理解为是反革命分子或阶级敌人在主使或操纵,需要给予强力打击。
四、加强专政、发展生产
4月11日霜灾发生后的一个月间,围绕灾害和粮食等问题,内乡县发生“突出的群众性骚乱事件2起……其次是煽动群众威胁政府及干部2起,辱骂领袖及干部4起,组织群众祈雨3起(较为严重),打干部及积极分子2起,进行造谣的2起”,县公安局逮捕扣押了这些案件中的17人。[21][28]
有研究表明,中共华北抗日根据地政权考虑到灾荒时期的特殊性、为了避免严惩带来社会秩序的进一步紊乱,对于灾荒时期的买卖妇女和偷盗等违法行为给予较平时为轻的处理。[29]当然,买卖妇女和偷盗都不是直接对抗政府的行为,而内乡县此时逮捕扣押的基本都是因为粮食或祈雨问题而与地方政府直接对抗的人。至5月11日为止,15名被认定为属于应捕而捕的人中除了6人处于待审理处理状态外,教育后释放7人,找保释放1人,判有期徒刑1人。预言“中共的朝廷坐不下”的王文生审理后被认定为是可捕可不捕的,只是组织串联祈雨的李景田则在审理后被认定为是错捕,二人都获得了释放。他们之所以被界定为可捕可不捕和错捕,大概主要是因为其未与地方政府发生直接对抗,连语言上的反抗或违逆都没有的李景田更是被认定为错捕。从这个审理定性的过程和处理结果来看,或许可以说内乡县主政者在灾荒时期对违法问题的处理是谨慎的。但实际的抓捕扣押对于这17人来说却很可能是一个痛苦沉重的经历。
4月底5月初的降雨和政府在粮食销售上的供应增多缓解了霜灾和旱灾带给民众的恐慌,民众情绪和社会秩序都逐步稳定下来。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政府继续对霜灾、旱灾引起的问题进行处理。内乡县委认为虽然群众情绪稳定下来了,但是敌人的活动日趋明显,而不少干部和群众对此缺乏警惕性。要求各区重视专政治安工作,整建治安保卫机构,抽出专人负责搜集整理材料,对敌人发动群众性的政治攻势。并对在专政治安工作上不够重视的区委提出了批评。[30]
6月18日,内乡县委对治安工作进一步发出指示,要求将当年灾情前后所发生的案件进行大清理,并争取在7月20日前破案,以有力打击敌人。同时从县到区、乡重新组织和加强治安保卫委员会,区、乡每月各召开一次治安保卫会议。区每半月一个简报、每月一个综合报告报送设在公安局的县治保办公室。[31]
内乡县委此时强调的另一个重点是发展生产,从而根本解决救荒问题。强迫借贷成为其重点解决的一个问题,因为这种现象对个体农民生产的积极性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可能造成地方经济死滞,影响地方财政收入的实现。县委在4月底下雨、灾荒稍有缓解后召开了县区干部会议,要求各区乡学习贯彻上级关于保护私有产权、稳定农民发展生产信心的十项政策,纠正此前私有财产权受到侵犯的情况,把强迫借贷变成正式的借贷关系,订立手续,保证归还。[32]
受制于阶级理论,当时内乡县委对灾荒中出现的强迫借贷的处理只是将借贷关系坐实,并不惩罚任何实施了强迫借贷的人,虽然他们的行为实质上是破坏社会秩序的。强迫借贷的人们过去在遇到灾荒时可能会当土匪抢粮,此时失去了组织为匪的条件,则利用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以及自己在此之下的优势身份来强势获得粮食。虽然他们实际上危害了别人,在政府眼里也妨害了生产发展,但因为他们良好的阶级成分而未受惩罚,与过去做土匪抢粮求生的风险相比可谓相当于无。无疑,类似的“损失分摊”的行为将可能在后续的农村社会变革中一再上演,驱动着社会滑向一个更加受困扰的方向。
在后续的报告中,内乡县委以夏馆区栗园乡各阶层群众纷纷买牛和赤眉区有中农解除顾虑开始雇工种地为例,说明纠正强迫借贷收到良好反应。但也承认这一政策贯彻得不广泛,基层干部有抵触情绪,怕贯彻后检查出许多问题是自找麻烦。所以大部分地区做得不好。[15][16]
5月20日和6月6日内乡县境内下了两场雨,县委当即电话指示各区组织农民在春耕未播种的地和已经收了夏季作物的地上趁墒抢种、补种或移苗,以保证增加秋季作物收成。[16][33]在1953年夏征工作中,政府针对受灾地区进行了减征。[34]
五、余论
在既有的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灾荒史的研究著作中,往往都会提及新政权与过去的政府不同,也会比较新旧社会救灾政策的异同,但都未触及一个根本性的差异,那就是1949年成立的新政权,是以一种不同于过去的意识形态在指导着国家和社会基本制度架构的建立、改造和运行。这个意识形态的哲学基础是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有研究表明人们所抱持的意识形态影响着人们对灾荒成因的理解,也影响着人们采用什么样的灾荒解救措施。[10]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民众和地方政府面对灾荒时的应对,也势必要受到那些不同于过去的意识形态以及奠基其上的治理方式的影响。
与传统社会地方政府相比,1953年内乡地方政府在处理灾荒时最大的不同是其强烈的阶级敌情意识。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新旧社会更替,社会形势复杂,这种阶级敌情意识很容易使直接和灾民打交道的地方官员,将灾荒中的不满和异议言行视为来自敌人的破坏,也为那些在灾荒中可能负有一定责任并害怕承担责任的地方官员,自觉不自觉地推卸或掩盖自己的责任,提供了一个很容易行得通的借口,并为其以强力手段对待那些不满者或异议者打开了方便之门。这样做有可能导致两个不好的后果,一是民间真实的情况和声音被误解和遮蔽;二是地方政府自身的敌情意识不断地被证成和加深。
我们可以看到在1953年春夏之交的灾荒中内乡县民众惯有的对灾荒的解释和应对选择,与新政权的意识形态和治理方式存在着诸多矛盾和摩擦之处。地方政府一方面采取实际的措施解决农民的缺粮问题,另一方面也警觉地关注和处理着那些矛盾和摩擦之处。但是,地方政府对于那些矛盾和摩擦的理解和处理,却可能并没有让其更贴近实际地理解其治下的社会和民众,而是不断地加深了自己的敌情意识,导致当时的阶级斗争理论的不断自我证成和自我强化。
[1]内乡县志[M].北京:三联书店,1994.
[2]四月中下旬情况报告(1953年4月26日)[Z].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图书资料室,档号:W3/1/20/11-18.
[3]内乡县委生产备荒计划(1952年12月9日)[Z].内江:内乡县档案馆,档号:1/42/21-32.
[4]内乡县委生产备荒救灾工作方案(草案)(1953年1月10日)[Z].内江:内江县档案馆,档号:1/42/33-39.
[5]县公安局五天情况报告(26日—30日)(1953年4月30日)[Z].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图书资料室,档号:W3/1/20/23-28.
[6]邓拓.中国救荒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7]董必武.新中国的救济福利事业[N].人民日报,1950-05-05(1).
[8]谢觉哉.我们能够战胜灾荒[N].人民日报,1950-05-06(4).
[9]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生产救灾的指示[N].人民日报,1949-12-20(1).
[10]艾志端.晚清中国的灾荒与意识形态——1876—1879年“丁戊奇荒”期间关于灾荒成因和防荒问题的对立性阐释[A].李文海,夏明方.天有凶年:清代灾荒与中国社会[C].北京:三联书店,2007.
[11]王铎.民国内乡县县志[M].1932年石印本.
[12]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发出关于生产救灾补充的指示[J].江西政报,1950,(1).
[13]华东的生产救灾工作[M].上海:华东人民出版社,1951.
[14]于建嵘.中国农民问题研究资料汇编:第二卷(下册)[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
[15]内乡县委半年来生产工作总结(1953年6月29日)[Z].内江:内江县档案馆,档号:1/62/57-67.
[16]内乡县委四、五月份工作综合报告(1953年6月3日)[Z].内江:内江县档案馆,档号:1/59/28-40.
[17]内乡县粮食局.内乡县粮食志[Z].内江:内乡县粮食局,不详.
[18]中共中央关于调整商业的指示(节录)[A].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商业卷(1949~1952)[M].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5.
[19]赵发生.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20]内乡县委关于加强治安工作保卫社会秩序的紧急指示(1954年4月23日)[Z].内江:内江县档案馆,档号:1/ 65/27.
[21]内乡县公安局.霜灾后开展政攻发生重大案件及人犯情况报告(1953年5月11日)[Z].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图书资料室,档号:W3/1/20/166-168.
[22]县委对粮食问题的指示(1953年5月4日)[Z].内江:内江县档案馆,档号:1/64/4-7.
[23]郭宏珍.古代官方祈雨考述[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
[24]师岗区拜神求药的情况报告(1953年5月18日)[Z].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图书资料室,档号:W3/1/ 20/107-113.
[25]师岗区姚营乡永青山求神拜药事件总结(1953年6月2日)[Z].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图书资料室,档号:W4/1/23/60-65.
[26]史蒂夫·史密斯.地方干部面对超自然:中国的神水政治,1949—1966[A].董珗.走出区域研究:西方中国近代史论集粹[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27]内乡县委指示(1953年7月18日)[Z].内江:内江县档案馆,档号:1/65/55-57.
[28]霜灾后发生重大案件及逮捕人犯情况报告(1953年5月11日)[Z].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图书资料室,档号:W3/1/20/163-165.
[29]李红英,汪远忠.华北抗日根据地时期灾荒背景下的违法问题及法律应对研究[J].中国农史,2014,(2).
[30]内乡县委加强治安保卫工作的紧急指示(1953年5月9日)[Z].内江:内江县档案馆,档号:1/65/35-38.
[31]内乡县委清匪治安工作指示(1953年6月18日)[Z].内江:内江县档案馆,档号:1/65/30-34.
[32]县委对当前继续深入贯彻生产政策的重要指示(1953年5月21日)[Z].内江:内江县档案馆,档号:1/62/54-56.
[33]县委关于加强生产救灾与趁墒抢种的几点意见(1953年6月6日)[Z].内江:内江县档案馆,档号:1/62/23-25.
[34]对一个乡救灾工作初步意见(1953年6月17日)[Z].内江:内江县档案馆,档号:1/62/35-39.
【责任编辑:丁 一】
K27
A
1004-518X(2016)05-0146-07
广东省东方历史研究基金会资助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