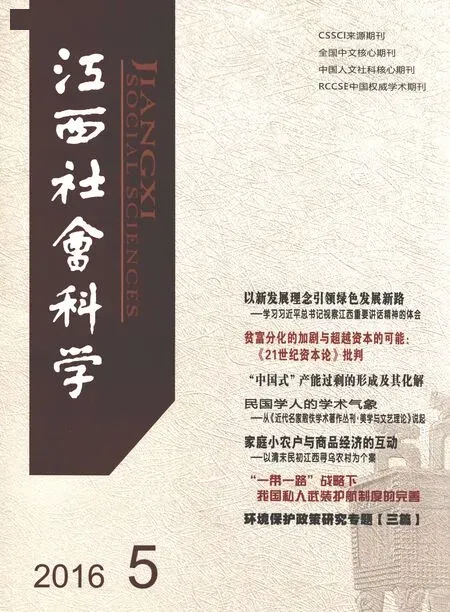不可译性:顾彬误译论之商榷
■胡 丹 刘毅青
不可译性:顾彬误译论之商榷
■胡 丹 刘毅青
中西语言与思想的差异使得中西之间的哲理思想翻译面临着不可译性,这样翻译必然包含着某种解释,翻译的局限也提醒我们重新认识翻译的意义。从不可译出发,德国汉学家顾彬强调了以目的语为目标的归化翻译,归化翻译强调了误译的合理性,但从将翻译作为更新自身文化的意义来说,顾彬的归化翻译立场就面临着困境。从汉学作为丰富西方思想资源的目的来看,异化翻译应该成为一种重要的翻译原则进入到汉学家的翻译中,以矫正目前汉学翻译中归化翻译占据主导地位的状况。
翻译;不可译性;异化翻译;归化翻译
胡 丹,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讲师,同济大学德语系博士生。(浙江绍兴 312000)
刘毅青,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浙江绍兴 312000)
西方汉学家是中国思想文化的传播者,对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功不可没,西方人尤其是不熟悉中国思想文化的西方学者对中国的认识与理解大多是通过汉学家对中国典籍的翻译。汉学家大多不是专门的翻译家,但翻译过程中遭遇的问题也迫使他们对翻译进行了思考,德国汉学家卜松山、顾彬就是如此。其中顾彬坚持一种归化翻译,并基于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对自身的翻译进行了理论辩护,他的翻译立场在当代的西方汉学家中有一定的代表性,比如以翻译莫言小说而著名的美国汉学家葛浩文就与顾彬的翻译立场相近。但在笔者看来,无论是从忠实于汉语思想的原意上来说,还是将翻译作为更新自身文化的意义上来说,顾彬所持的归化翻译立场都值得商榷。本文以不可译性作为切入点,对此进行讨论。
一
对于汉学家来说,对汉语文学与思想的翻译,首先遇到的就是文本可译性的考量,对中西之间的跨文化翻译而言,这种可译性的思考显得更为复杂,因为这里涉及的是两种不同思维方式的翻译,可译性的问题就显得尤为突出,正如德国汉学家卜松山所指出的:“所有对文学艺术的翻译都是在试图译不可译之事物。”[1](P88)
语言是人类赖以思考的工具,因而不同的语言是不同思维方式的体现,它并不能仅仅视为一种表达的符号或者中介,语言反映着深层的文化。语言的内在意味是一种生存方式,不同的语言对存在之本体论的预设存在着差异。按照法国汉学家朱利安的看法,汉语是真正有别于欧洲所从属的印欧语系的一种语系,这首先表现在,汉语没有西方的逻各斯中心的本体论。因此,德里达从汉语里发现了对西方语音中心主义——逻各斯中心的颠覆性,虽然德里达对汉语的理解本身或许存在不足,但他所指出的,汉语在逻辑思维上与西方的差异基本上是符合二者在思维范式上的特性的。
从汉学在欧洲的发展来看,最早的汉学家都来自传教士,他们在中西交流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从明代的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到清代的理雅各、卫礼贤,奠定了欧洲汉学的基础。故此,传教士大概是最早系统地将中国古典文献翻译与介绍给西方的人,但不容忽视的是,基于强烈的宗教信仰,欧洲传教士对中国古典的翻译与理解打上了深刻的基督教的烙印。从翻译理论来看,欧洲传教士的翻译主要采取归化翻译的范式,他们将不同于西方思想的中国思想诸如道、仁、礼等放在基督教的思想里进行理解,从而歪曲了中国思想的本来面目。这直接影响了借助他们翻译的中国思想来理解中国的欧洲哲学家们,从黑格尔到韦伯,他们理解的中国思想都笼罩在基督教的阴影下,他们对中国所作出的错误评价离不开其所接受的汉学翻译文献。
从翻译理论的角度来看,对传教士来说,中西的翻译在上帝的全能的保证下,不存在不可译性,上帝的话能够通过翻译传达给各个不同语言,不同民族与国家的人,同时,其他的文化也能够在上帝的思想指引下得到理解与翻译。但恰恰是在《圣经》中包含着关于翻译的不可译性的向度,在《圣经》的巴别塔的故事中,人类的语言本来是统一的,是上帝恐惧人类拥有一个共同的语言,从而妄图协作建造通向天国的通天塔。将人类的语言予以隔绝,正是为了让他们互相之间不能真正的互相理解,从而“变乱”(巴别塔在希伯来语中本来就有着这一层意思)人类世界。可见,语言的不可互通,难以互译,正是上帝所期望的。正因此,被冠之以解构主义的德里达在对《圣经》巴别塔故事的解释中,突出了翻译的不可能性。[2]不同于德里达从形而上学角度对不可译性所做的理论建构。作为汉学家,卜松山当然比德里达对汉语与欧洲之间的差异有着更深入的理解,在长期的汉学研究中他发现,与欧洲语言相比,汉语的特点使得它具有“很高程度的开放性或模糊性”[1](P88),这就是说汉语本身具有高度的诗性。
从文字的表达来看,古汉语没有系词,没有词性变化,词序灵活,词语在文本间能够自如活动,词意高度依赖上下文的语境,这种灵活性也就带来理解的多重性。古汉语在词汇与语法上的这些特征,使得中国古诗文在创造的时候,极容易形成一种对偶性,不同于西方诗歌依靠韵步来押韵,中国古典诗歌的韵律体现在对句中,一般是隔行押韵,而不是每句诗都押韵。中国古典诗文中存在大量骈句偶语,古诗的平仄与对仗等格律就来自对偶。而这深层来自中国传统的宇宙观:将事物看成是对立的两个方面,而两个对立面可以互相转换,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这就是安乐哲所说的关联性思维,在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中,对诗歌影响较大的首先在于其中的关联性思维。在这种思维里天与地、阴与阳、精神与物质都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这也形成了意义表达的复合性,词义往往具有明暗两重的“亦此亦彼”性。如卜松山所说:“在中国人的交流方式中,我们处处可以察觉到一种平衡与和谐的特性,例如,对并列形式或对仗的钟爱。这实际上传承了以下倾向:看待事物时不是依据非此即彼的二分法,而是采取亦此亦彼的模式(阴阳模式)。”[1](P92)
卜松山进一步指出,这种关联性思维在文字表达上就形成了一种互文性,在现代文论中,随着法国结构主义文论的流行,互文性成为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但正如卜松山所说:“在西方的文学研究中,互文性只是在最近才引起人们的重视。作为一种新方法,它往往在貌似不相关的文学作品之间发现相关联的东西。而长期以来,中国人有意识地运用互文性这一传统长期为人忽视。”[1](P90)具体来说,就是一方面,中国古典诗歌极具形式感,强调格律,从诗到文都严守一定的规则,但另一方面,中国诗歌又是极为含蓄的,这就构成了意义的开放式性。卜松山认为,这两者之间的张力构成了诗意的来源,从西方美学的角度来理解就是 “一种自由与规则的相互作用”。[1](P88)而这就给西方汉学家在翻译上带来极大的麻烦:欧洲语言无法像汉语一样,一一对应,严守数字与格律;如果按照翻译后的诗歌也按照某种格律,或者在形式上形成整齐的结构,则使得诗歌含义的表达严重失真,面临着诗意的丧失。
二
汉语语义的复杂性与生俱来,而古典诗歌尤喜用典,在根本上,中国文学的互文性特质很大程度上与其大量使用典故有关。典故的含义随语境而有变化,除字典的解释外,其背后隐藏着由历史文化心理所形成的意思,有时即便是中国人自己也难以理解,何况外国人。汉语里诗歌典故脱离了原有的语境,其故事的含义也发生了变化,有赖于它在新的语境中与其他文字意义发生的互动,从某种程度来看,典故在诗歌中充当了抽象的意义,其言外之意比其原本的意义要丰富许多。但古诗词中典故所包含的这些微妙用意,在翻译时被彻底瓦解,只剩下干瘪的词汇。中国古诗词的多义性对翻译是一种阻碍,它存在着不可译性,尤其是真正好的中国诗词,由于它的高度符合诗意蕴藉的汉语审美趣味,其美感更是只可意会无法言传。它存于读者的微妙理解,它所传达的往往是一种艺术气氛而并非具体的意思,这对翻译来说是一种挑战。
翻译的不可能性在汉学家那里就使诗歌的翻译也不得不成为基于原诗的二次创造,基本上以德国汉学家顾彬为代表的汉学家是主张归化翻译作为翻译的主要策略。在一次访谈中,顾彬以德国80多岁的汉学家兼诗人为例,对汉语德译的困境作了分析。这位汉学家用自己一辈子的时间翻译唐诗,作为诗人他的德文是一流的,他对汉语的理解也非常准确,总体上看他的翻译是非常成功的,但即便占据着双语上的能力与优势,他的唐诗翻译仍然不可能保持古典汉语诗歌原有的韵味和语言魅力。[3]正因此,顾彬认为,这种汉语诗歌中呈现的不可译性使得翻译只能采取归化翻译的立场,顾彬借用中国诗人杨炼的话提出了自己的翻译标准和追求:“如果我要翻译他的诗,就应该使他那些被我翻译成德文的诗作,在德国文学史上拥有一定地位。”[4](P224-225)他认为:“翻译成的德文的中国文学作品从语言来看,应该跟德国文学作品的语言水平一模一样。简单说就是,让读者看的时候最好不感觉到他在看译本。”[5](P225)在汉学家里,顾彬的特殊性在于,他本人也是诗人,他对诗歌翻译归化翻译的推崇,多少是因为他以为,他能够理解中国古典诗与诗人。但诗人作为翻译家,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他可能将自身的风格移植到译文中,忽视了所译之诗本身所具有的风格。汉语文学翻译成德语之后应该成为德语的经典,其实就是认为汉语要德语化,应该具有德语的语言风格,而不必保持其汉语自身的意境与风格,也就是说,汉语经过翻译后要尽量向德语靠拢,而不是相反。这就是他所说的:“我在翻译一个中国作家作品的时候,会用便于德国读者思考和阅读的词汇来替代一些只在中文中才能理解的词语。”[5]这种以西方固有的词代替中文词汇的做法,从翻译的理论来看,就是典型的归化翻译立场。而考察当今的西方对中国文学乃至文化的翻译,归化翻译占据了主流。
归化翻译由于是根据翻译目的语的语感与习惯来组织,在阅读上给读者的感觉是翻译得更为清晰。异化翻译则由于保留着原文的语序与语感习惯,让读者有着生涩不通的感觉。在意义的理解上,归化翻译经过了译者的理解,附加了译者自身的解释,而异化翻译则往往保留着原文的语句以及原文本身由于文化与思想的差异带来的隔阂,使得阅读的体验并不如归化翻译,一般来说归化翻译显得更为优美。但这种过于流畅与优美的译文或许掩盖了原作本身的意义与风格,而异化翻译则掩盖了译者对原作本身的理解程度。
顾彬对归化翻译立场的坚持基于他对伽达默尔解释学的理解。在《真理与方法》中,伽达默尔对理解的特质进行了分析,他在翻译这一活动中看到理解与解释之间的张力,对此做了深入的探讨,在伽达默尔看来,解释在翻译中是无可避免的,始终伴随着翻译的过程,翻译也就不可能是对等的,翻译的可能性只能基于译者的理解之中。这提示我们,翻译必须面对语言与文化存在的差异。中西文化存在的差异体现在翻译中就是,许多的语汇在中西文化中不存在完全对等的东西,在翻译和理解中,我们总是借助着自己已经有的东西来理解未知的东西,中西的互相翻译中,必然以解释的方式展开。而解释就离不开译者的前理解,译者的前见决定了翻译的限度,翻译以丧失原文的韵味为代价,译文体现的是译者的语言与文化特质。故此,在顾彬看来,不可译性使得翻译只能以“归化翻译”的方式存在,这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译文的表达深受译者自身的语言风格影响,同时附着了译者自身对原文所表达的意思之解释,译文展示译者的文笔。这种将汉语德语化的翻译,其实会让中国文学与思想中固有的意义与韵味在翻译中丧失殆尽。
三
伽达默尔对翻译的观点是其解释学的一部分,他的解释学强调交流与对话,在上面的引文中他就指出翻译启示着交谈所具有的可能性。为了解决翻译中存在的不可译性,顾彬受伽达默尔的启发,进而将翻译理解为摆渡,也就是一种交通,交流的手段,他说:“在德语中,翻译这个动词,是‘übersetzen’,它有两个义项。它的第二个意思是‘摆渡’,我们倒可以把翻译家看作船夫,这人把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人从此岸送达彼岸,从已知之域送达未知之域。不仅渡客和货物,连船夫自己也参与了这种变化。”[6](P623)摆渡意味着双方的对话,翻译应该成为一种对话,只有通过对话才能逐步消除不可译性。从根本上来讲,翻译理论是一种对话理论,翻译就是解释,而解释不是一次性,而是一个过程,是一个不断对话的过程,通过对话彼此达成共识。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对话始终需要建构一个共识性平台,平台的构建就决定了理解的方向。对跨文化的翻译与理解来说,如何构建对双方来说都是平等,从而能够获得共识的平台正是其所面临的巨大困难。人类在跨文化中面临着的种种问题,无不是围绕于此而来。
对顾彬来说,这个平台只能建立在归化翻译基础上。他建议将翻译理解为文化交流中一种无奈的方式,将翻译中的误译视为文化交流中无可避免的代价,这样来看,翻译的意义在于:“翻译总是一种向你自己的文化中的语义输入。翻译于是就不可能精确地保持一个原文文本的全部内容和丰富意义,就好像你不可能免得了在译文中添加新的细微意义一样。”[7](P623)这表明,翻译以归化为主(意译),只要将大致的意思表达到了,原文的风格与韵味是可以被牺牲的。从积极的方面来看,翻译使得汉语的诗歌能够被西方文化所接纳,经由翻译,古典诗歌文本就从文化的封闭性走向了开放性,从而具有了文学的普遍性,形成一种跨文化的世界文学,也就连通中国与世界,使得中国古典成为可以传达的文学,也就与当代西方有了某种关联。笔者也同意顾彬的看法,在翻译中译者完全放弃自身的前见是不可能的,译者的历史性存在于自身的语言、思想、经历之中,这都会带到译文中。但这并不意味着译者要代替作者,将自身的主观理解与自身的语言风格带到翻译中,原作作为一种目标限制着译者的过度僭越。
但问题在于,顾彬一味地强调翻译的解释性与对话性,过分强调译者的主体性地位,则会影响翻译的目的,翻译不能等同于创作,原著作为衡量译文可靠性的标准是无可动摇的,翻译之间仍然是存在着好坏之分的,并不是说,翻译是任意性创作。归化或归化翻译使得对话并不平等,从解释学的角度来看,一味地推崇归化或者说归化翻译就会导致一种过度解释,译者拥有对原作僭越的权利。真正平等的对话翻译应该是意大利符号学家埃科所说的,是 “一场谈判”,谈判的重点就在于协商,其实在一个译文中,异化翻译与归化翻译是可以互相容纳的,并不是一味地异化翻译或一味地归化翻译,异化翻译或归化翻译可以根据需要而发生变化。因此,一味地强调异化翻译或归化翻译都是错误的,基于平等对话的翻译应该是异化与归化之间的协商而达到平衡。翻译所面临的语言问题,究其竟是文化的差异问题,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从而是一种化合的过程,伴随着思维方式的转变。这就是另一种文明对于自己的意义,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翻译时面临的语言问题,其实质是文化问题,中西语言之间的张力实际上是中西文化之间的张力。事实上,即便我们承认翻译相对于原作是一种再次创作,但其创造性应该是以传达原作的自身风格与意义为目标,原作始终是译作的目标,它规定着译作的创作限度。
就诗歌翻译来说,其从根本上涉及的也是一种跨文化理解,对于翻译来说,如何克服由于文化差异,由于具体的历史语境而造成的隔阂,将古典诗歌本身难以言说的微妙情感传递出来,无异于一种二次创作。但这并不意味着,翻译可以僭越原作的意图,任意处置诗歌中的意义或意象。因此,虽然翻译中的不可译性使我们不得不承认,无论译者多么希望忠实于原著,但翻译终究还是离不开跨文化的理解,翻译在某种程度上需要“解释”,译作与原作之间难免会形成差异,不能等同起来。“绝对忠实”的翻译难以实现并不意味着翻译的无意义,而是指明翻译的限度。译作只是提供一个桥梁,让不同文化语境的人们可以互相认知,从而逐渐走向深入。翻译只是开启文化交流的钥匙,因而是必须的,它面临着不可译性的困难,因而是有限度的。
总之,归化翻译并不意味着从一开始就承认译者能够抛开文本来展开自己的创造,误译也应该是以重视原文为目的翻译活动。如果一开始以误译为目标,将正确的理解的目标搁置,则这种误译只能是出于对原文的利用,并不能促使文化间的对话。承认误译并非说明翻译本身就毫无意义,而是说,正确的翻译由误译开始。误译的创造性应该是基于原文,这样才能不至于完全背离原文,成为对原文的破坏。西方对中国文化的误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经典的翻译未能提供较为忠实的译本,因此,对更符合中国思想内涵的较好的翻译仍然是西方汉学研究中一项具有意义的事业,是对汉学家的挑战。
以不可译性为视角对顾彬翻译的思考是为了讨论西方汉学的翻译立场。如何用母语与自身语言之外的文化进行交流,绝不是词汇问题,更是文化问题。卜松山讨论不可译性的过程中,也最终面对的是文化问题,翻译不可避免的涉及文化,乃至成为文化理论问题的一个部分。从将翻译作为更新自身文化的意义来说,顾彬的归化翻译策略就面临着困境。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传播,但如果翻译未能真切的呈现异质文化的特性,就会将其脸谱化,如此,翻译究竟是增进了跨文化对话交流,还是增加了误解呢?
可以说,归化的翻译观,使得顾彬未能去设想德语其实可以通过引入汉语的诗性表达,丰富现代德语,弥补德语在意义呈现上的不足,这大概是他一贯以来的文学观念的体现,他对中国现代小说中的古典性就不以为然。比如,他曾对金庸的小说大加批判,认为其小说的古典性缺乏现代意义,不是现代小说,对莫言的评价亦是如此,认为莫言小说有太多的中国元素,影响了小说的现代性。[8]
由此看来,就当代汉学家来说,他们对中国古典的翻译还面临着一种古今的时间距离,而不仅仅是中西的跨文化隔阂。“由于译者对同一术语会有不同的译法,加之文化背景的差异以及‘编译’、‘译述’译法自身的不准确性等将导致译名的淆讹。”[9]比如说圣经的古奥语言翻译成现代德语,也会丧失其庄重感,用浅白的语言来表达神圣性的思想时,有时就会显得扎眼,丧失了在圣经整体上呈现出的精神之厚重。因此,当代德语本身也很难将中国古典文学所特有的言简义丰的特质表达出来。但更为重要的则是,在观念上,古今之间有着更深的隔阂,这种差异来自现代性本身所带来的思想与视野变化,现代人很难对古典有一种同情共感的认同。许多当代汉学家对中国古典的研究难以克服的正是这种现代性的立场,他们往往以现代性的立场来理解古典的中国,而忽视了中国古典对现代性所具有的批判性意义,对于诗歌而言,那就是我们可以引入中国古典诗歌的诗性以打破现代诗歌的僵化。
翻译是用本国的语言来接受异质性的文化思想,是在让异质性思想变成本国的语言。准确的理解被翻译作品的内涵是最重要的一步,但比之更重要的是如何将这种理解翻译为本国的语言。对汉语而言,汉学翻译里的异化翻译与归化翻译的矛盾显示的是,许多汉学家并未准备好充分吸收中国的文化,这或许与当代西方仍然占据着世界文化的中心有关。对任何一种文化、一个国家来说,其在吸收外来文学与文化的时候,始终面临着如何进行本土化的问题,文化间难免存在着冲突,这时翻译的重要性与中介性就体现出来。翻译是吸收外来文化的第一步,而异化翻译正是这第一步的基础。
从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其实就是通过翻译来更新自身的文化与思想的,现代的英法德意等欧洲人其实是身处于古希腊与古罗马的蛮族,他们并未享有共同的语言。对于当代西方人来说,他们视之为文化源头的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并不是其文明之始祖,这种对两希文明的追认其实是现代西方人自我的一种建构,而其基础就是大量的用现代的欧洲语言翻译古希腊语、古拉丁语的文献,至今这种翻译仍然是构成欧洲古典学的基础。对欧洲人来说,他们愿意或主动的吸收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并将其视为本国文化,但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却始终犹豫不决,我们更为清楚地看到顾彬的这种归化翻译或许就是这种文化心态的体现。
但笔者认为,无论西方是否准备吸收中国文化,汉学作为向西方引介中国文化的根本途径,理应尊重中国文化的特质,这种特质应该在翻译中体现出来。不可译性不能成为归化翻译立场的借口,它应该标示着翻译的理解深度——只有更深入的理解中国文化才能做到更好的翻译。因此异化翻译应该成为一种重要的翻译原则进入到汉学家的翻译中,以矫正目前汉学翻译中归化翻译占据主导地位的状况。
[1](德)卜松山.译不可译之文——研究中国文化的方法[J].世界哲学,2003,(2).
[2](法)德里达.巴别塔[A].陈永国,译.论瓦尔特·本雅明:现代性、寓言和语言的种子[C].吉林:吉林人民出版,2003.
[3]薛晓源.理解与阐释的张力——顾彬教授访谈录[J].文艺研究,2005,(9).
[4](德)顾彬,钱林森.作家的语言、声音及其他——顾彬访谈[J].跨文化对话,2010,(26).
[5](德)顾彬,袁剑.写作需要“休息”——顾彬访谈录[J].中国图书评论,2012,(4).
[6](德)顾彬.翻译好比摆渡[A].王哲祖,译.中西诗歌翻译百年论集[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7](意)翁贝托·埃科.巴黎评论·作家访谈Ⅰ[M].张芸,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8](德)顾彬.金庸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危机[J].杨青泉,译.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
[9]陆晓芳.晚清翻译的实学性——南洋公学译书院外籍汉译考论[J].东岳论丛,2014,(12).
【责任编辑:张 丽】
H0-0
A
1004-518X(2016)05-0242-06
绍兴市项目“绍兴20世纪文化名人在德国的影响力研究——以鲁迅为例”(12540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世纪下半叶西方汉学家的中国美学研究”(09CZW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