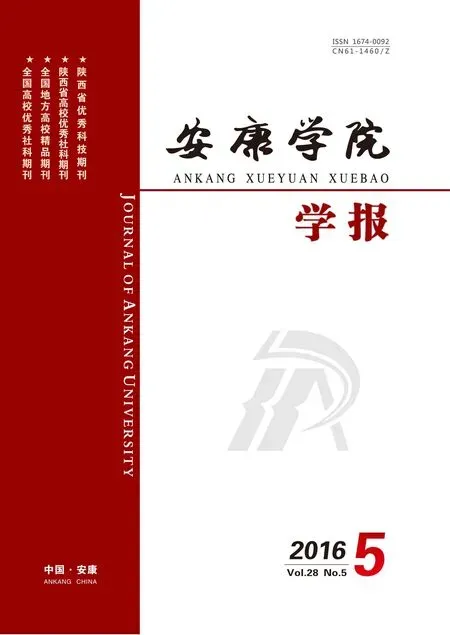事功追求与兵学研习——南宋永嘉学派薛季宣军事思想探微
刘春霞
(广东开放大学 文法系,广东 广州 510091)
事功追求与兵学研习——南宋永嘉学派薛季宣军事思想探微
刘春霞
(广东开放大学 文法系,广东 广州 510091)
薛季宣是南宋永嘉学派承前启后的代表人物。以事功为核心精神的永嘉学派十分重视学术的实用功能。从事功目的出发,薛季宣重视研讨兵学理论、关注朝廷军事问题,写下了一批以谈兵论战为主要内容的文章,包含了丰富的军事思想。
永嘉学派;薛季宣;事功;军事思想
薛季宣(1134—1173)字士龙,号艮斋,学者称常州先生,永嘉(今浙江温州)人,是永嘉学派的重要代表,亦是使永嘉学术转向事功之学的关键人物。《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季宣少师事袁溉,传河南程氏之学。晚复与朱子、吕祖谦等相往来,多所商榷。然朱子喜谈心性,而季宣则兼重事功,所见微异。其后陈傅良、叶适等递相祖述,永嘉之学遂别为一派也。”[1]625以薛季宣为核心的永嘉学派继承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重视对兵、农、财等实务的考察研究,其中对兵学的研究是事功之学的重要内容。学界对永嘉学派的政治、经济、哲学、史学思想都有深入讨论,但对其兵学军事思想少有人关注。本文拟以薛季宣为研究中心,探讨其军事思想,藉以一窥其事功之学的特征。
一
薛季宣性情淡泊霭如似儒者,但他具有深厚的兵学修养,其兵学军事之谈亦得到了时人的认可。南宋大儒吕祖谦在《宋右奉议郎新改差常州借紫薛公志铭》中评曰:“莅官随广狭,默寓之薄领期会之间,其僚或联曹,经时而不知公为儒者也。平生所际文武之职不同,未尝为町畦崖崖,而去就从违之际守义不可夺。言兵变化若神,而在朝每以不可轻试为主。”[1]621-622薛季宣校订了《阴符经》和《风后握奇经》,撰写了《八陈图赞并序》 《汉兵制》等兵学著作,并将其对兵学理论、军事历史的研究与朝廷战争形势、战守之策结合起来,对朝廷包括士林风尚、军事制度、战守之策等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写下了一批包含丰富军事思想的文章。
(一)论士风:战争取胜的舆论氛围
薛季宣认为,士风对战争取胜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上宣谕汪中丞书》一文专论振奋士气对于抗敌复国的意义。他称:“为待敌之计,所务乎盛气而已。”为政者必须激发士林之“气节”,方可望国之恢复,“强国以人,作人以气,士气振而众材用”“士气振者国必盛,士气索者人心亦从而衰”。薛季宣认为北宋嘉祐、元祐年间国家“涵养士气”,故而名士辈出,追配唐虞,国强民富;元祐党禁后,贤智放逐,趋时之士竞相阿颜附势,致北宋灭亡;南宋孝宗欲图恢复,士风振奋,江东遂兴;继而权臣柄朝,媢贤丑正,至岳飞披冤而死,士人方绝望功名,一时风尚索然,恢复愈加无期。至今则“天下滔滔,安于邪行,诬蒙苟且,上下相承,郡县朝堂,会为一律,论至于此,而求士气之振,邦家之兴,不戛乎难哉!”在这样的情况下,要使士人在战时捐躯效命以卫社稷是不可能的,“日为循缩之计,气不振,下将愒然而休”“以图恢复之功,固未知其或可也”。薛季宣认为,要取得战争的胜利,“不在乎敌之强大,而患吾气之犹索也”;朝廷当务之急在于振奋士气,“使气无有不振,人无有不备,则功何有不就”;要振奋士气,就需要朝廷明定国论,以恢复为务,明辨忠奸,赏罚分明,则“人人有向功之志,则贤者不敢隐其算,勇者不敢爱其力,太平可指日而俟”[1]249-250。
(二)论军事制度:战争取胜的制度保障
军事制度是薛季宣关注的重点,包括对民兵制度、将帅制度、屯田制度等多方面问题的探讨。
第一,关于民兵制度,薛季宣认为可以因地适变,建立民兵制度。由于宋廷有惩唐末世五代潘镇割剧之弊采取重文抑武的政策,造成将骄卒惰、战斗力下降的现状;由于宋朝采用募兵制,改变了前代寓兵于农的形式,庞大的军队完全仰食于民,造成军费冗巨、国困民贫的局面。据此,薛季宣提出在一定程度上恢复民兵制度,一则提高军队战斗力,一则可缓解军队冗费的问题。薛季宣认为,民兵不乏出于“窜名逃役”目的而出入行阵,“非教阅之兵,初与田夫不异”,如不对其进行训练,亦无济于事[1]215,但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古代郡县民兵合一的军事制度,教民战争是有积极意义的。他依据历史质证今事,称:“观历南国战守之计,未尝不保据城壁”,认为“南唐之弱当周之胜,犹能历岁坚守”,其原因正在于“郡县之兵盖与国兵为二,一专为守,一专为战,则事集矣”。进而针对宋廷以禁军为主、郡县兵制尽废,民各念家而无心守边的现实,建议朝廷可以利用江汉淮南之民,因其“敦实雄健,涉历世故,颇知用武”的特点,少其赋税,教之弓箭手法,“使之人自为战,制其勋赏一同正军”,既不废农桑,战时亦可自卫,不失为边防之一术[1]263。
第二,关于御将制度,薛季宣反对朝廷“将从中御”制。宋太祖立国之初,为惩五代藩镇祸乱之弊,采取枢密——三衙军事体制,以改变唐五代以来“尾大不掉”之势。“祖宗制兵之法,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总于三帅,有据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上下相维,不得专制,此所以百三十余年无兵变也。”[2]与三衙制一致,宋朝实行“将从中御”法以御诸将,每当部队出征,皇帝都预授将帅阵图,所谓“图阵形,规庙胜,尽授纪律,遥制便宜,主帅遵行,贵臣督视”[3]。将帅往往受令于朝不得临阵机变。薛季宣对此提出批评,“兵法:‘将能而群不御者胜。’故古之命将,筑坛推毂而必付之以阃外之寄。今诸道将帅,已有制置、招讨之除,而进取之计尚每听中旨,金字牌旁午于邮传,而一进一退,殆莫知适从矣”[1]232。
关于御将之术,薛季宣认为应赏罚分明。宋祖立国之初虽以“杯酒释兵权”的形式解除了大将兵权,但对前代将帅骄悍以致倾国的历史依然心有余悸,故而一方面削弱武将的权力,一方面又对将帅时时加优推恩而不敢严苛要求其权责。对此,薛季宣认为,朝廷转战十年而无尺寸之功,原因在于赏罚不明,致使将帅骄悍贪鄙而兵力孱弱,“转战十年不能成功者无它,以朝廷御将之术未尽其道耳。方诸将略有折馘之勋,则骄悍之气已傲视其上,以邀莫大之赏,而朝廷唯恐不满其意也。至于败军失守,则置而不问。有罪则阔略,行赏则从重,故张、韩之辈,卒不能复中原尺寸之土,而遂享三公之封。独一岳飞,颇有志于功名,然进退之机或戾中旨,卒罹其祸”[1]233。他认为朝廷应对将帅恩威并加,“将帅骄蹇,古今通患,人主务收其用,当结以恩,必有刚正之臣,绳之法。故诸将内有所感,外知所惮,用能指使如意,战辄有功”[1]234。
第三,关于屯田制度,薛季宣认为屯田不合时宜。“屯田”指军队在战争之余耕种田地,目的是为了避免从异地长途运输粮食,以解决边境军队之需,是一种兵农合一制。由于宋代实行募兵制,以国养兵,致使国家兵费冗巨,有识之士如李纲、曹勋、陈傅良、蔡戡等都纷纷提出实施屯田解决军事供给。薛季宣则认为古代屯田制虽确实收到了一定的成效,“散军就田,所耕足以赡众,军无惰卒,国无劳民,此历古屯田之利,赵充国、诸葛亮之所赖以成功者”,但“古之所以屯田,多缘宿兵塞上,馕馈不给,姑即弃地耕之,所求便事宽民,非以为利,不过自足军用,省馈运之劳。”“古之屯田,本缘捍御关隘”,而今天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自然扼塞,无田可耕,固非要害,散之则不可复众,聚之则奔命徒劳。一往于田,不可复教,积年阅习,一废之。流移之民,仅能复业,良田便于水利,固已耕耨于中”。如使兵耕种,无疑与民争利。“便民则军无可耕之地,扰之则民必流亡。”“今求辟地,利不两全。”[1]248
(三)论战守之策:战争取胜的宏观战略
薛季宣认为当时的形势并不适合战争,称:“兵力既弱,财力空匮,所恃以战者,不过三衙御前之众”。这种“兵交于前,人困于后”的现实,恐怕导致还未战争已祸起萧墙的后果。而在宋朝重文轻武的形势下,军事长官往往而临“寄任不专,孤立无助,小人不去”的处境,所以要想“成功立事”是不可能的[1]207。薛季宣认为当时朝廷“兵非素练,帅非旧职,边氓无所依怙”,发动战争必然败北[1]209,所以反对冒然兴兵,“至如用兵一事,起于喜事之臣。窃尝论以《孙子·始计》之书,盖未知其可也”[1]206,认为兴兵抗金应做长期打算,“至于用兵,则请留待十年之后,必以机会而举”[1]207。
薛季宣认为朝廷应坚持“守备”的战争策略,先加强守备、壮大国防,“恃吾之不可胜”,并“待敌之可胜”,然后一举战争而胜敌。薛季宣主张使敌人“不战而屈”[1]231“当为不可胜以待之”[1]278“惟当恃吾之不可胜”[1]237“以我之不可胜,待敌之可胜,而不恃敌之可胜”[1]245,只有加强守备、壮大自我才能在战争中取胜。他认为“不为先人制人之谋”,只会受敌牵引,疲于奔命,“奔走以救其弊,则虚实自见”[1]234。
薛季宣所强调的“守”并非消积被动,而是“以守为备”“以备为战”,其“守”的目的在于“战”,与其时苟安主和派有本质区别。薛季宣称“守”不是忘记祖宗恢复之计,而是“恢复之计在其中”[1]254。他分析了以“守”备“战”的必要性,“某闻待敌之计,和与战、攻与守而已也。四者交修,可以无敌于天下。又其次者,择一而固守之,然后事功可立”。而在当时用兵之弊已甚、国之兵力日弱的情况下,“为国家之计,和攻之事盖难言矣,惟战与守皆不得已而后动,是特不可废者”。因此他建议朝廷“料将帅之勇怯,察地形之险易,可守可战,豫为之谋,应敌之方,较若划一。使彼计无所出,则将送命于我,生之杀之,惟我所制,比之临事而动,其得失固未易以一二计也。”[1]279
薛季宣还认为“守”与“和”是辩证的关系,只有加强守备,才能真正与金人达成和议。他利用“揣摩”之策分析敌情,若我急于求和,“故敌人必有无厌之求;一辞其请,则和议不成;从其贪顽,必将倾尽国力亦不可使之满足;和议不成,则必有战争,如‘吾圉不固,其将何以拒之?’”在当前“边鄙则荡而无备,问其粮饷则匮而不给”的情况下,“不思自治之道,而论遂及于和,和固多端,然不自强则和不在我,则将靡事不为,而敌人得以制其命矣”。在这样的情况下,“求之人情,保国之计,和不若守。守御备具,则和议可成,和议可成,守之必固”,即在强国富兵之“守”的基础上与金人和议,才能掌握“和”的主动权;“和”则能够使国家长“守”久安[1]254。
薛季宣认为,加强“守备”关键在于“自治”,并对如何“自治”提出了自己的策略。他指出当务之急,“上策莫如自治”。又称:“某闻之兵法:‘勿恃敌之可胜,恃吾之不可胜。’是故先为不可胜,上策自治,此不可胜之略也。”[1]261“古求欲以胜人,以为莫如自治。”[1]243认为在当今“将骄卒惰,边障不修,备御之方,率多施之无所用功之地”的情况下,“为邦之道,自治为急,敌之强弱,非所当问”[1]264。只有加强自身军事防备,做好充分准备以待敌,才能最后胜敌。
薛季宣认为“自治”必须加强朝廷根本纲纪的变革,以仁义治国,选贤用能,赏罚分明,安抚边民、爱护人民,即其所谓的“丰本”之说。薛季宣引用古语“善治水者必涤其源,善呼卢者必丰其本。”“第丰吾本,无为兵先,机会之来,何容穷尽。”[1]209所谓“丰吾本”,是指通过一系列政策富民强兵,严备边防,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以仁义纲纪为本,备边之计,幸勿为浮议摇动!”[1]207“我能为自强之计,政事修,贤材用,名实不戾,刑赏有章,则夫机会之来,庸有穷尽。”[1]265“太平之基,骎骎方立,然而为治之根本,要在枢臣之正,众贤之多,此事之难,方劳庙算。”[1]276“朝廷待敌之计,莫若爱抚边民,使其民愿为我氓,安有不济!”“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为国劳民,未有能固其国者。”[1]252以仁义纲纪为国之大本,并以之为国家军事制度、战争策略的基础,这体现了以薛季宣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从儒家伦理角度立论的军事理论的根本特点。
二
薛季宣密切关注朝廷军事问题,与永嘉学派事功追求一致,是永嘉学派借经制言事功的学术理路的体现,与薛季宣受其师袁溉的影响而转向事功之学直接相关。
首先,薛季宣关注军事问题,与永嘉学派事功精神相一致。永嘉学派一改南宋理学家奢言性理、空谈性命的空疏习气,将形而上之“道”落实到具体之“事”上,体现出鲜明的现实功利性。《宋元学案·艮斋学案》称:“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4]1696薛季宣是永嘉之学转向功利之学的关键人物之一,永嘉之学又因薛季宣讲学及其师友切磋传承而大为发展。《宋元学案·止斋学案》中称道:“永嘉诸子,皆在艮斋师友之间,其学从之出,而又各有不同。”[4]1710薛季宣倡言事功,并广泛吸纳古代经典以求实用,陈傅良在《右奉议郎新改差常州借紫薛公行状》中称薛季宣“自六经之外,历代史、天官、地理、兵刑、农末,至于隐书小说,靡不搜研采获,不以百氏故废。尤邃于古封建、井田、乡遂、司马之制,务通于今”[1]615。正是出于事功目的需要,薛季宣才对前代学术广为涉猎、融汇贯通,其对古代兵法军制、朝廷军事问题的研究亦是出于其现实事功的根本目的。
其次,薛季宣关注军事问题,是其借经制以言事功的学术理路的体现。永嘉学派又被目为“经制之学”,所谓“经制之学”,指注重从历代典籍中研究制度之学,从经典中探求制度得失以资时用。永嘉学派不仅研究儒家经制,而且从史学、子书中探讨历代政治制度之得失,其中对兵制的探讨是其重要内容。永嘉学派众多学者都有军制研究专著。据明万历《温州府志》卷十七记载,薛季宣著有《汉兵制》一书,今佚。薛季宣门人陈傅良著有《历代兵制》八卷,与薛季宣《汉兵制》统绪相承,分别论述西周至北宋之兵制,探求历代兴亡与兵制得失之关系,其著书目的在于言古制以资时用,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评:“盖傅良当南宋之时,目睹主弱兵骄之害,故著为是书,追言致弊之本,可谓切于时务者矣”。永嘉学派另一学者钱文子著有《补汉兵志》一卷,将汉宋军制对比,指出宋朝军制之失,其撰书目亦在于以古制质证今事,“为宋事立议,非为汉书补亡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八十二《补汉兵志提要》)除了已佚的兵制研究专著《汉兵制》外,现在尚能窥见薛季宣军事思想的作品主要是其以谈兵论战为主要内容的各类上书、奏对、札子、书信等。这类谈兵文章最大的特点是以古代军事理论、军事制度为立论依据,借历史以言时事,并广泛引用古代兵学理论以质言宋廷军事制度、边防政策之得失。这都体现出永嘉学派借经制言事功的鲜明特征。
另外,薛季宣关注军事问题,与受其师袁溉的影响而转向事功之学直接相关。袁溉十分重视事功之学。《宋元学案·艮斋学案》称:“道洁(袁溉)之学,自《六经》百氏,下至博弈小数、方术兵书,无所不通。先生(薛季宣)得其所传,无不可措之用也。”“季宣既得道洁之传,加以考订千载,凡夫礼乐兵农莫不该通委曲,真可施之实用。”[4]1691《宋史·本传》称:“季宣既得溉学,于古封建、井田、乡遂、司马法之制,靡不研究讲画,皆可行于时。”[5]袁溉本师从程颐,但其学术理路已向考梳经制、发明义理、务求实用上转变。袁溉所学博杂,兵书就是其博杂学术中的重要内容。薛季宣正是在其师的影响下,在着力融会各种学术思想、并将之施于实用的基础上研习军事的。
薛季宣是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其兵学研究与军事理论都集中体现了永嘉学派的事功精神与经制之学的特点。薛季宣以其所谙熟的古代兵学理论为依据质证朝廷战争政策之得失,《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道:“其持论明晰,考古详核,不必依傍儒仙余绪,而立说精确,卓然自成一家”。薛季宣军事思想中所体现出来的卓识远见,与其躬身实践与务实精神分不开,所谓“其历官所至,调辑兵民、兴除利弊,皆灼有成绩。在讲学之家,可称有体有用者矣”[1]626;625。薛季宣军事思想的特点,突出体现了永嘉学派务求实利、不为空言的典型特征。
[1]薛季宣.薛季宣集[M].张良权,点校.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2]范祖禹.论曹诵札子[M]//曾枣庄.全宋文:第四十八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542.
[3]杨亿.李继隆墓志铭[M]//曾枣庄.全宋文:第八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68.
[4]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M].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
[5]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12883.
【责任编校杨明贵】
Studying on the M ilitary Concept of Xue Jixuan,a Scholar in South Song Dynasty
LIU Chunxia
(DepartmentofLiberal Artsand Law,Guangdong Opening University,Guangzhou 510091,Guangdong,China)
Xue Jixuan was themore important scholar of Yongjia School which was more desirous of achievement in South Song Dynasty. Xue Jixuan paid close attention tomilitary strategy and tactics,and wrote many articles about war and military issues,which contained plenty ofmilitary thinking.
YongjiaScool;Xue Jixuan;be desirousofachievement;military thinking.
I206.2
A
1674-0092(2016)05-0037-04
10.16858/j.issn.1674-0092.2016.05.008
2016-04-22
刘春霞,女,湖南澧县人,广东开放大学文法系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唐宋文学与文化方向研究。
——刘家文
——徐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