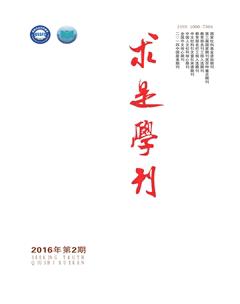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三重向度与文化微观视域的历史性介入
摘 要:挖掘并梳理散见于马克思诸经典论断中的意识形态理论,是马尔库什后期一项重要的学术任务。借此,他大致归纳出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范式的三重特质:其一,通过抨击先前各种思想幻象所彰显出的论战-揭露性;其二,凭借分析这些幻象由以产生的社会根源而突显出的解释-功能性;其三,立足更为广泛的文化视角进而生发出的批判-哲学性。由此可见,针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体系,马尔库什旨在建构一种“思想-日常生活-文化”三位一体的解读模式,从而真正实现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范式从宏观维度向微观视域的历史性转向。值得一提的是,该转向在完善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同时,又成为日后马尔库什进行现代文化批判的实践生长点。
关键词:意识形态;论战的-揭露性;解释的-功能性;批判的-哲学性;微观文化
作者简介:温权,男,哲学博士,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研究员、讲师,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从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
中图分类号:B5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6)02-0046-08
马尔库什发表于20世纪80—90年代的三篇重要论文:《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Concepts of Ideology in Marx)(1983年)、《隐喻的终结:基础与上层建筑》(The End of a Metaphor:The Base and the Superstructure)(1994年)以及《论批判性的意识形态批判》(On Ideology-Critique:Critically)(1995年),是其全面解读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代表作品。通过整合分散于不同文本中马克思对该议题的相关论述,他在建构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体系的同时,又归纳出后者所特有的理论向度。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马尔库什认为,马克思对先前各种意识形态的批判,旨在祛除隐含于其中的特殊阶级利益,揭露其所携带的普遍有效性幻象。与此同时,对它固有的历史局限性的揭露,又使马克思的理论天然具有鲜明的论战性质。对此,马克思自己也承认:“涉及这个内容的批判是搏斗式的批判;而在搏斗中……问题在于给敌人以打击。”[1](P4)故而,马尔库什指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范式具有论战的-揭露性特征。其次,在瓦解意识形态幻象之前,应先分析造成该状态的社会性根源。这就要求,批判的着眼点将逐渐转向更为深入的日常生活领域。而“正是马克思关于日常思维社会规定的理论,既为解答上述问题提供了基础,也为理解意识形态在社会中的功能作用提供了基础”[2](P126)。这说明,相对于具体的社会生活而言,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体系还具有解释的-功能性内涵。再次,既然马克思将批判的触角从纯粹的思想层面,延伸至现实的日常生活维度,与之相应,作为意识形态批判的客体,它必须涵盖更为广泛的社会文化领域。鉴于此,马尔库什进一步指出:“意识形态一方面在彼此分离的文化领域的元素之间……另一方面,在特殊的额外文化性(extra-culture)条件与过程之间建立联系。”[3](P85)换言之,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是一种广义上的文化-哲学性批判。因此,马尔库什将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这一特征,称之为批判的-哲学性。
不难看出,马尔库什对马克思意识形态体系的解读,实现了从抽象思想到宏观现实再到微观文化的理论嬗变。借助作为批判客体的“思想-日常生活-文化”的有机统一,马尔库什将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向度,逐渐深入到广袤的文化土壤中,从而真正诠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的批判性本质。此外,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微观文化定位,也为之后马尔库什进行现代性文化反思埋下了重要伏笔。
一、瓦解思想的幻象: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论战-揭露性向度
以论战的方式,揭露各种所谓“永恒真理”的阶级与历史局限性,是马克思进行意识形态批判的开端。其目的,旨在打破资产阶级诸学说自身的欺骗性,从而将之特殊的利益诉求公之于众。鉴于此,马尔库什指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在此意义上意味着‘揭露’历史上所有试图证明精神至高无上性的企图”[2](P123-124)。故而,它应被视作“直接反对所有历史唯心主义变体的论战工具”[2](P124)。
对此,马克思曾一再强调:“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地位的新阶级,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述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性的思想。”[1](P100)该论断包含两方面内容:其一,凭借逻辑普遍化手段,意识形态使特定的阶级利益在理论层面获得普遍的有效性;其二,按照排他性标准,它把统治阶级的历史局限性遮蔽起来,从而赋予其永恒的真理性。这意味着,意识形态体系试图在思想层面实现它对整个人类历史的钳制,并以欺骗的形式营造非批判的社会集体“无意识”状态。因此,马尔库什总结道:“作为意义的阐释体系,产生普遍性幻象并赋予特殊性以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倾向于无意识且在自身中消弭了普遍/特殊的区分,并破坏了反思性的意义。”[3](P75-76)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无意识”体现为它对反思性批判的消解。这是由于,“意识形态虽然属于‘意识’的范畴,但它实际上是无意识的,它们首先作为结构强加于绝大多数人”[4](P167)。由此可见,正是意识形态的先在结构所具有的排他性与封闭性,构成了消解反思性批判的内在根源。以此为基础,特殊的阶级利益才能掩藏其历史局限性,从而以普适性观念的样态投射到人类发展的进程当中。
鉴于此,马尔库什认为,“马克思使用了一种起源的意识形态批判方法”[2](P124),以揭露意识形态的幻像及其造成的社会集体无意识性。这就要求,把意识形态还原为特殊利益的同时,再将后者纳入历史环节中进行总体批判。其中包括两种视角:第一,从意识形态的起源来看,它毋宁是对人类历史现实的时段性(epoch)反映。虽然与特定历史阶段的交往方式相符,但马克思认为,随着人类历史的演进,“这种交往形式中的旧的传统观念……也就愈发下降为唯心的词句、有意识的幻想和有目的的虚伪”[5](P331)。也就是说,意识形态所谓的普遍有效性经不起历史的推敲。它充其量“不过是把人们引入歧途的镜子式的反映所俘虏的时代本身”[6](P163)。第二,从意识形态的作用方式来看,所有为掩盖其特殊的阶级利益,而进行的理论欺骗,都是针对受众的奴性“教育”。后者产生的理论“偏见”,不啻为意识形态达到自身排他性诉求的前提。对此,马尔库什指出,“那些既为它们中的合理对话建构可能性又为其设置限制的、非反思性的‘偏见’”[2](P136),是构成社会集体“无意识”的先决条件。正是在这样的立场上,马克思才反复强调,这种“资产者唯恐失去的那种教育,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把人训练成机器”[6](P289)。一旦受众成为特定历史阶段社会关系的无意识参与者,意识形态就把“这种思维封锁在一种既为自己的历史局限辩护又试图使之永恒化的范畴或表象体系之中”[2](P144)。
由此可见,马克思对意识形态幻象的揭露具有双重内涵。马尔库什通过分析指出:“一方面,在思想中,为其‘无意识的’,非反思的前判断(pre-judgement)所确证的这些意识形态形式的‘时代性’特征,并非一些过去的特殊利益的结构,而毋宁是给定社会形式的建构性特征与本质条件;……另一方面,它们具有这一意义,不仅是它们持续的(愤世嫉俗的)追随其预设的结果,更是由于从其理性的视角来看,它们希望解决这些社会生活的诸矛盾。”[3](P71)
反观意识形态的生成与作用机理,无论是最初的普适性谎言,还是之后的排他性特质,意识形态捏造所谓永恒真理的目的不过是试图从思想上最大限度的整合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如此一来,通过把特定的社会利益转变为人类理性的要求,这些思想体系促成了既定社会统治关系的稳定化:信念的固定变成一种合法化模式。”[2](P124)然而,遗憾的是,特殊利益终究不是人类的共同利益。马克思认为,纵然它披上了后者的外衣,但“这种共同利益是‘异己的’和‘不依赖’于他们的,即仍旧是一种特殊的独特的‘普遍’利益”[1](P85)。质言之,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在遭致种种质疑时积极编造的谎言,它本身就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现象,并“存在于作为一极的纯粹的谎言,和作为另一极的以某种被歪曲和有缺点的概念组织的结果形式存在的错误之间”[7](P66)。因此,意识形态幻象的瓦解,本身就是对虚假共同利益的祛魅。而这在马克思那里又带有强烈的论战意味。马克思指出:“对于这一对象,批判本身已经不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它的主要情感是愤怒,它的主要工作是揭露。”[1](P44)以论战式的批判为手段进而揭露意识形态自身的悖论,无疑为马尔库什所指认的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论战-揭露向度提供了充分的佐证。
另外,特别需要强调的是,马尔库什对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论战-揭露性向度进行阐释的根本目的在于,从思想维度划定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有效范围。马尔库什特意指出:“马克思针对构成和决定意识形态体系的隐藏利益所展开的论战,并不是在一种所谓能够克服所有历史局限的非历史的合理性名义下进行的,而是在由同样的社会利益产生和诱导的、历史和社会限定的、具体的、‘有限的’需要和遭遇的名义下进行的。”[2](P125)
既然马克思对意识形态幻象的揭露与抨击以现实的历史发展为准绳,那么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他的批判理论同样具有历史的阶段性。这主要是两方面原因造成的结果:第一,作为批判客体的各种思想体系本身就是特定时代的精神性代表;第二,对它们行批判时所采纳的各种背景支援,同样是具体历史环境下的产物。因此,马克思总结道,围绕意识形态批判体系的诸“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1](P142)。但是,意识形态批判自身的限度,并不意味着它从此就丧失了长远的有效性。作为一种方法,其批判特性会随着时代主题的流转历久弥新。
值得一提的是,在历史视域下,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这种有限性与无限性之间的关系,自身就隐藏着巨大的理论危机。针对该事实,卡尔·曼海姆不无疑虑地指出:“意识形态……就其运用范围而言过于广泛并且是一种过于重要的武器……任何事物都不能阻止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们拿起这种武器,并且把它运用于马克思主义本身。”[7](P81)由此可见,马克思在理论层面对意识形态幻象的批判确实是一把双刃剑。于是,如何在稳固自身立场的基础上,保证其范式的合法性,就成为马克思对意识形态体系进行更深入反思的理论要求。
二、打破社会的桎梏: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解释-功能性向度
从唯物主义的视角出发,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在思想层面产生的幻象,根源于日常生活自身的异化现状。他指出:“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呈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一样。”[1](P72)因此,马尔库什强调,从抽象理论切入到具体现实是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必然趋势。而唯有找到意识形态的社会性根源,才能准确定位其病灶所在。于是,马尔库什从意识形态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入手,展现了马克思批判范式的解释-功能性向度。
首先需要澄清的问题,毋宁是意识形态幻象由以生成的社会性机理。对此,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时曾尖锐地指出:“人们是怎样把这些幻想(意识形态——笔者注)‘塞进自己头脑’的?……这种世界观没有前提是绝对不行的,它根据经验去研究现实的物质前提,因而最先是真正批判的世界观。”[5](P261)显然,现实的社会经验是造成意识形态幻象的根源。至于它的物质性前提毋宁是为一种世界观所表征的日常生活交往方式。而后者的异化现状无疑是以上幻象产生的必要条件。对此,马尔库什将之称为“制度性的教条”,并指出:“个体对于生活和置身于其中的世界所形成的这种扭曲和被蒙蔽的理解方式……具体说来就是传递给被制度上固定了某些‘教条’的个体并被其占有的这一过程。”[2](P127)从中不难看出,当意识形态脱胎于异化的社会现实,并得到相应的制度性保障时,作为一种“教条”,它将成为人们日常交往所必须遵守的规范。这就意味着,“人们为了生活在一个既定的社会中,总得与该社会的意识形态认同,如果他完全不懂得这种意识形态,他就无法从事任何实践活动,建立任何社会联系”[4](P75)。也就是说,意识形态具有相应的社会有效性。它通过自身的再生产从日常生活维度决定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如此一来,异化的现实与思想的幻象就形成了合流,它们在彼此融合的过程中,完成了意识形态的现实化。从此,意识形态就“并非是对(社会)存在的‘虚假意识’,而是这种存在本身”[8](P28)。
发轫于异化社会的意识形态,现已成为能够进行自我再生产的物质力量。通过对日常生活的制度性规约,它“系统地排除了一种总体化反思的可能性,排除了既反思这个世界历史-实践的构成,也反思这种思维方式的社会规定性的可能性”[2](P129)。毫无疑问,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把握社会生活的态度,在功能上具有解读并整合日常生活的作用。它通过“使这些所谓的‘观念’变成了坚持这些‘观念’的人所具有的某种功能,就使这些观念变成了这种人在其社会性周围环境中的地位所具有的功能了”[7](P61)。但问题在于,倘若社会生活本身存在异化,意识形态的消极影响也就显而易见了。鉴于此,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就不能只停留在理论层面。否则,这种“仅仅是反对这个世界的词句”,而“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1](P66)的批判,只能流于空谈。
在马尔库什看来,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对于日常生活的解释-功能性向度,实则突显了后者尚需进行社会批判的要求。他指出:“在这种意义上的(马克思——笔者注)意识形态批判,是内在批判的传统方法由文本领域向社会领域转换的更迭(transposition)。通过使文本与其非文本的背景(社会-历史性背景)相适应,意识形态批判试图揭示,理性对话或相互表征的结构及合法性的非反思性的先验预设,从而揭露反映社会环境‘外部’矛盾的概念及想象的张力。”[3](P72)
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视角由纯粹思想到社会现实的转向,可视为它所具有的解释-功能性特质针对日常生活异化现状的反讽。其中,又蕴含着意识形态自身性质的双重悖论。一方面,作为一种解释性理论,它对日常生活的观念性构想愈加完善,其潜在的无意识性就愈发具有强制力。这突出地表现为,“意识形态机器规定了由物质的仪式所支配的物质的实践,实践则是存在于全心全意按照其信仰形式的主体的物质行动之中”[9](P652)。这表明,一旦实践主体被纳入意识形态的机器当中,他就成为后者生产自身的物质性媒介。如此一来,为物质实践所建构的整个人类社会,就成为意识形态现实化的产物。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意识形态最先是一种扭曲的社会意识。它对日常生活异化现状的默许乃至刻意遮掩,必然使实践本身及至人类社会整体处于异化的再生产当中。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才专门强调:“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抛开人类史。”[10](P423)可见,在人类社会被异化的大背景下,意识形态对日常生活的构想本身就形成上述异化现象的再生产。
另一方面,意识形态之于日常生活的异化关系突出反映了人类物质实践的有限性。这表明,人类自身就是一种不完善的存在。对此,马尔库什从艺术的角度谈道:“从社会-历史性到非历史的‘永恒的艺术’特征的回溯……毋宁是为布洛赫所代表的、立足于人作为一种缺陷性存在(being of lack)的观点,其中就充斥着乌托邦意识。”[3](P82)不难看出,将意识形态冠以非历史的永恒性特征,毋宁是人自身的有限性使然。至于它所蕴含的乌托邦诉求,可视为历史中的实践主体,对日常生活进行全面整合的必然结果。而后者则主要表现为,在“制度上散播的统治思想体系系统了日常思维混乱和无序的概念表述,把一定程度的逻辑黏附性赋予其零散的结构,为最常遇到的与拜物教范畴表面上的自明性相矛盾的经验而辩护”[2](P129)。显然,意识形态对日常生活的整合毋宁是逻辑对现实的统一。它“涉及到人类同人类世界的‘体验关系’”。但“这种关系只是在无意识的条件下才以‘意识’的形式而出现”[11](P203)。正是由于人类的有限性及其对日常生活的无意识构造,意识形态的乌托邦内涵才具有投射于现实社会并促使其进一步异化的可能性。
问题的关键在于,意识形态所具有的解释-功能性向度,“使我们注意到社会关系可以被象征构造的流行或扩散所支持,社会变革可以被它所制约。它使我们注意到我们可以在一个进行着空前社会变革的社会内描述为的一个社会保护过程”[12](P46)。换言之,意识形态对于社会变革而言具有相应的阻滞力。它与日常生活彼此黏附,共同构成异化社会之拜物教基础。因此,马尔库什认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或拜物教理论)“首先是一种日常意识的批判——主要是对它自己的主体和接受者、工人阶级意识的批判”,而对异化的“克服不是一个知识问题,而是集体实践选择的创造问题”[2](P129-130)。可见,意识形态的解释-功能性向度,与其说是对日常生活异化现状的批判,不如说是对后者的直接揭露。虽然“所有这些工作都极大促进和深刻影响着对于统治关系的批判性反思,但这些工作本身并不会证明这些统治关系是不公正的”[13](P160)。与之相反,在马尔库什看来,它更多是为批判异化的现实生活创造实践的契机。
至于意识形态自身携带的阻滞力,无疑从侧面印证了它亟待变革的理论要求,纵然“意识形态的功能并不在于为我们提供逃避现实的出口,而在于为我们提供了社会现实本身,这样的社会现实可以供我们逃避某些创伤性的、真实的内核”[8](P64)。但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具有极大的麻痹性与非真实性。因此,马克思特别强调,意识形态的“批判撕碎锁链上那些虚构的花朵,不是要人依旧戴上没有幻想没有慰藉的锁链,而是要人扔掉它,采摘新鲜的花朵”[1](P2)。这表明,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解释-功能性向度,意在从现实的社会-历史层面为后者的彻底变革埋下理论的伏笔。
三、超越文化的壁垒: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批判-哲学性向度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对思想幻象和异化社会的揭露与抨击,还不足以说明它自身所蕴含的广泛性与深刻性。这是由于,其内含的文化维度尚未得到充分的阐释。对此,马尔库什专门指出:“意识形态批判作为一种过程的解释学,坚持不满足于仅仅对文本‘内涵的阅读’,因为它要求对将文本置于自己的社会-历史背景中的,传承下来的文化传统作出理解的解释。”[2](P135-136)而意识形态批判的客体,从具体的社会-历史到更为宽泛的文化领域的嬗变,必然伴随其研究视角由宏观向微观的转向。换言之,在马尔库什看来,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应当是一种具有批判-哲学性向度的、彻底的文化批判。
马尔库什指出,作为联结整个人类社会的纽带,文化本身对马克思而言实则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性质。
一方面,它于特定时间段构成人们交往方式的一般规范。至于其本质毋宁是对人类社会的历史性意识。马克思曾指出:“思想和观念成为独立力量是个人之间的私人关系和联系独立化的结果……无论思想或语言都不能独自组成特殊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5](P525)虽然特定的文化具有相应的时效性,但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它显然是社会生活由以构建的基石。马尔库什正是以此为出发点,进而搭建意识形态之于文化的关系。他指出:“人类活动及其产物始终是被诠释的,带有一种意向性的意义、有责任的含义,被社会编纂成文体现在语言中,其基本要素被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所共享并使他们之间的交流成为可能。”[14](P187)而语言抑或交流的场域,正是为主体所共同拥有的文化框架。既然前者被视为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由它所彰显的文化指向自然就成为人类社会赖以依托的前提。
因此,在马尔库什看来,与社会的异化现状密切相关的意识形态,其产生的根源应当定位于相应的文化背景中。他讲道:“意识形态是异化社会的文化,在异化社会里目标实现和目标设定……根本上变成彼此分离的。因此人类无法……控制自身活动的一般结果以及其自身后果的发展方向。”[2](P138)可以肯定的是,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异化的文化,会对人类的社会关系造成极大扭曲。其后果,毋宁是目的与手段、应然和实然的尖锐对立。这就从根本上阉割了主体实践之自由自觉的本性。更为严重的是,它还与异化的社会制度形成“同谋”,从而“一方面确保‘文化’环境的再生产,另一方面确保满足由作为适当实践活动载体的个人组成群体的社会成文的需要”[14](P193)。如此一来,意识形态就在文化、文化的再生产以及需要之间的关系层面,对个体形成牢固的掌控力,从而削弱了后者的批判意识。
鉴于此,意识形态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可视为相应的文化传统对人们交往方式的规约。作为一种被体制化的习俗,它们“无限伸展到过去……具有一种难以打破的刚性。它们包罗在社会生活之中,它们的非历史性质被象征形式所再次确认,这些象征形式在建构和重复中使偶发事件永恒化了”[12](P74)。可见,将阶段性的偶然事件冠以永恒有效性的文化,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直接表现。
另一方面,与时段性的文化不同,在马尔库什看来,马克思还界定出一种超越历史阶段的“划时代”文化。他指出:“马克思始终在那些所谓‘历史片段的意识形态’与那些代表着划时代的文化价值的意识形态之间作出区分。”[2](P132)后者的典型代表毋宁是具有普适性的艺术。也就是说,真正的艺术具有非历史的永恒价值。其适用范围并不囿于某一特定的历史范畴。相反,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晶,它彰显了人类实践的所有魅力。针对这一问题马克思就古希腊艺术之于现代的意义曾作出过明确的论断:
成为希腊人幻象的基础、从而成为希腊“艺术”的基础的那种对自然的观点和对社会关系的观点,能够同走锭精纺机、铁道、机车和电报并存吗……希腊艺术的前提是希腊神话,也就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成人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儿童的真实再现出来吗?……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15](P52-53)
诚然,按照唯物主义的观点,文化的生成及其意义与具体的时代密不可分。作为物质实践的上层建筑,它无法超越相应的历史背景。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艺术创作蕴含着不同于一般生产性劳动的自律性。因此,马尔库什才强调:“准确来说,艺术的人类学基础使后者被设想成赋予‘真正的’艺术品以力量去超越它们生成的特定条件,并且去获得一种普遍的意义。”[3](P86)虽然之前时代的艺术作品,其幻想性内容为后世的物质实践所填充,但这并不影响它对当前时代的审美价值。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所有真正的艺术作品的永恒特征……都赋予艺术以超历史性(transhistorical)的功能与任务:使社会的现实生活去庸俗化与人道化”[3](P82)。不难看出,艺术或高级文化非但不会使人们陷入拜物教的泥潭,它还是个体清除异化的手段之一。正是这种纯粹的审美特质,才激发了人们不断扬弃现实的动力。换言之,艺术的普遍性正是它所彰显的超历史性。
但是,在历史性文化和超历史性文化之间,人们很容易对二者的含义产生曲解。而意识形态的产生毋宁是这种曲解的直接结果。马尔库什将其归结为两个主要方面:第一,将超历史文化的自律性当作文化具有非历史特质的依据并进一步予以夸张。这就导致,历史性文化的时代局限性以偷换概念的方式对超历史文化的普遍性进行歪曲。其结果正是制度化的意识形态所营造的非反思性社会前提。因此,“意识形态批判在这个意义上是一种对文化对象化的批判。……这种批判反对它们自身主张的自律性,并且反对对它们来说仍然是隐藏的和非反思的,外部强加给想象和思想的屏障”[2](P138-139)。与其说马克思批判的是高级文化的自律性,不如说他在祛除自律性当中夹杂的非反思性。马尔库什认为,通过甄别自律性与非反思性的本质区别,马克思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批判确立了最初的起点。
第二,将超历史性文化的普遍有效性简化为制度或传统的永恒真理性,并使后者与历史性文化相等同。这种做法无异于使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动态性特征庸俗化为静态的教条。对此,马尔库什尖锐地指出,一旦“把这种‘划时代的’意识形态视为与一定社会类型相关的某种历史观点的理论表达……并因此将其基本的生存条件转换成真实的思想约束”[14](P195),那么文化自身所蕴含的批判精神也就随之消亡了。实际上,历史性文化是超历史性文化精神在具体时代的现实投射。它的更迭恰好符合超历史性文化的本质诉求。将鲜活的文化精神庸俗化为僵死的文化教条正是意识形态产生的重要根源,也是马克思竭尽全力想要破除的对象。
由此可见,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批判-哲学性向度旨在从自律性与普遍性两个维度打破钳制人们思想与实践的文化幻象,从而真正确立人道的交往方式。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出发,马尔库什指出:“意识形态的‘解放’概念所确立和建构的‘物质生活条件’与它们的文化-意识形态的表达之间的关系,并非是因果性或功能性的独立,而毋宁是一种转换(transposition)。”[3](P73)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马克思还是马尔库什,他们都承认文化相对于一般的物质实践而言,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作为社会现实的建构者与诠释者,文化对日常生活的表达本应就“包罗在描述过去并把现在视为永恒宝贵传统一部分的叙事之中”[12](P69)。
至此,马尔库什对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向度的全面架构就得以完成。不难看出,马尔库什通过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分析,逐步建构出“思想-日常生活-文化”三位一体的解读模式。与此同时,其研究视角在实现宏观领域向微观层面转向的同时,文化作为独立的问题域也由幕后走到台前。这不啻为马尔库什日后专门进行文化研究与现代性反思的重要转折点。
参 考 文 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乔治·马尔库什:《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载《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李斌玉、孙建茵译,衣俊卿校,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
[3] György Markus. “On Ideology-Critique-Critically”, in Thesis Eleven, Nov 1,1995.
[4] 朱晓慧:《哲学是革命的武器》,上海:学林出版社,2007.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6] 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7] 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霍桂恒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8] 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9] 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载《外国电影理论文选》,李恒基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 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