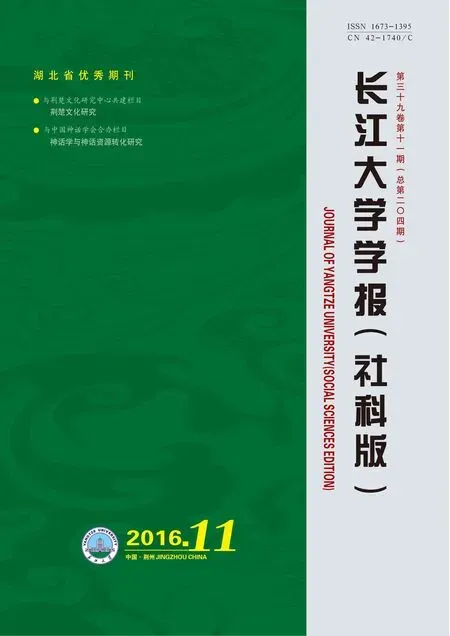《丹尼尔·德龙达》中格温多琳的权力悖论
徐颖
(国际关系学院 外语学院,北京 100091)
《丹尼尔·德龙达》中格温多琳的权力悖论
徐颖
(国际关系学院 外语学院,北京 100091)
《丹尼尔·德龙达》中渗透了权力关系,而这些权力的运作通过性别关系展示出来。小说的女主人公格温多琳身上凝聚着一种权力悖论。她自负地行使自己的女性权力来征服上层社会,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男权的凝视赋予了女性这种权力。而小说中父权社会的三位男性人物——格朗古借助阶级权力、克莱斯默借助职业权力、丹尼尔·德龙达借助道德权力,将格温多琳置于他们的男权凝视之下,消解了格温多琳的自我意志,剥夺了她的女性权力。
权力悖论;男权压迫;失权;无知;知识
《丹尼尔·德龙达》(DanielDeronda)是乔治·爱略特于1876年出版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该小说聚焦于英国19世纪60年代中期的社会问题,凸显道德主题。小说的英国情节和犹太情节分别以格温多琳·哈里斯和丹尼尔·德龙达作为叙事中心,既反映了受男权文化和霸权意识双重浸染的英国女性的精神困境,又探寻了犹太文化对基督教帝国的赎救可能性。
《丹尼尔·德龙达》出版后,并未像爱略特以往的小说那样好评如潮。小说的两分情节受到颇多诟病:里维斯(F.R.Leavis)在《伟大的传统》一书中对小说的犹太情节大加贬抑,称其为小说“坏的一半”,他分析了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小说《一位女士的画像》对《丹尼尔·德龙达》“好的一半”的借鉴[1](P80)。而詹姆斯本人却认为小说的犹太情节是个崇高的话题。萨义德(Edward Said)从后殖民主义的批评视角出发,分析了小说中的殖民话语[2](P22)。无论如何,将小说的英国情节和犹太情节割裂分析颇为不妥,有违作者本意。两部分情节相辅相成,渗透了人物间的性别、阶级和种族矛盾。格温多琳身上更是集结了种种权力斗争的痕迹,她本身也成为一个既有权又无权的悖论个体。
格温多琳这一角色复杂而生动。她美丽、聪明、自信,却又不乏自私自利的野心。她梦想驾驭自己的生活,自主进行婚姻选择,却因经济困境而嫁给格朗古,陷入不幸的婚姻。格温多琳身上集结了权力悖论:她既是男权文化和阶级观念的受害者,又下意识地抵抗奴役她的力量;她既表现出权力欲望,又时时被不安与自责所包围;她既享受着男性对她的朝拜,又透露出对男性的深深恐惧,“将性别关系同权力联系起来”[3](P166)。她所表现出来的权力意识,在男权文化、阶级意识形态和霸权话语下被逐渐消解。男权压迫造成了她的悲剧,而她的性格缺陷——无知,推动了性别压迫中渗透的阶级和种族等权力关系的运作。格温多琳的无知反映了英国狭隘、闭塞的国民性格缺陷:个人的无知带来了人生的错误选择,而英国社会的无知则是生成男权、阶级和种族偏见等种种社会弊病的根源。爱略特在小说中给出了一个理想主义的出路:她赋予德龙达救世主般的全知和泛爱,他的知识带给格温多琳走出精神困境、走向救赎的力量。
小说开始时,格温多琳表现出强烈的权力欲望。爱略特频繁使用“权力”、“统治”和“领导”一类的字眼来描述她,格温多琳的美貌被形容成驾驭男人的女性权力。小说还着力渲染了她的自由意志和对婚姻的自主态度。但是在这些权力的表象之下,隐藏着格温多琳的失权和失语。爱略特将格温多琳的非凡美貌称作征服男性的女性权力,又将她的美置于绅士们目光交错的凝视之下。男性的凝视不会带给格温多琳性别压迫感,反而满足了她的虚荣心,她陶醉于男性赌徒将她“当作幸运女神顶礼膜拜”[4](P6)。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还将这位主流基督教社会的淑女他者化为异教神话中的“塞勒芙”(Sylph)、“涅瑞伊德”(Nereid)和“拉弥亚”(Lamia)[4](P7),连格温多琳的母亲也称其为“女巫”[4](P62)。美貌是她征服男性的武器,同时也成为男性择选女性的工具。爱略特在文中提及斯潘塞和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论”——男性在婚姻选择中将女性美貌视为第一要素。可见,女性的美貌已不再是女性的权力,而变为男性的择选权力。女性在男性的凝视下被物化,在婚姻市场上成为待价而沽的商品。爱略特在第10章题词处将男性描摹为女性这种商品的消费者:“他们的品位检验了女人的价值”[4](P83),而女人要为迎合绅士在婚姻市场上的需求来改进自己的商品品质。
初入社交场时,格温多琳自信地标榜“自由意志”,幼稚地拒绝男性的追求,后来却也不得不承认“成为新娘是对女性权力的一种必要证明”,于是她又渴望在婚姻中“找寻比少女时代更大的自由”,未料终在婚后“陷入家庭的桎梏”[4](P30)。归根到底,格温多琳缺乏真正的女性独立意识,也无法超越英国上流社会设立的女性规范。格温多琳的名字(Gwendolen)谐音《仙后》(FairieQueene)中的王后“格温多琳”(Guendolene)。后者通过惩罚背叛她的国王来展现女性权力;而小说里自诩为“流亡女王”[4](P33)、“被罢黜的女王”[4](P245)的格温多琳,却只是在女性权力幻象里获得想象中的满足,逐渐失去对命运的掌控,成为婚姻中的奴隶。
《丹尼尔·德龙达》中渗透了权力关系,而“微妙的权力运作通过性别关系展示出来”[5](P123)。以格朗古为代表的恶魔力量、以克莱斯默为代表的艺术力量和以德龙达为代表的道德力量,全部将格温多琳置于他们的凝视之下。无论是格朗古的暴虐对格温多琳的精神压迫,还是克莱斯默的诚实对格温多琳职业理想的扼杀,还是格温多琳本人对德龙达救赎力量的渴望,都显现了女性在性别社会里的无力和无权。
一、格温多琳与格朗古阶级权力的博弈
占据英国主流社会显赫位置的格朗古是帝国和阶级霸权的化身,他贪得无厌地将权力的触角伸向广阔的领地。自诩有女性权力的格温多琳,在与他的婚姻博弈场上败下阵来,被牢牢掌控、无处可逃。小说多次将冷漠、残酷的格朗古描摹为冷血动物“蜥蜴”。他自诩为“领地之君”,可以随意发号施令,行使贬抑别人的至高无上的权力。
在和具有权力欲望的格温多琳的最初博弈中,格朗古的霸权意识即显现得淋漓尽致。阶级观念是他隐蔽的统治工具,而缄默和深不可测是他权力的外现。当这个单身贵族继承人莅临迪普洛社交圈时,众人对他趋之若鹜,而格温多琳对此却不屑一顾,天真地对这个贵族欲擒故纵。爱略特在二人的经典对话场景中隐没了格朗古的心理活动,对他的描写只是从格温多琳的视角出发。格朗古被格温多琳所吸引,是因为他的权力贪欲在驾驭这个可以驾驭别人的女性时得到了满足。就这样,爱情和婚姻变成了权力关系的角斗场。二人婚姻博弈的最初阶段,格温多琳仍能做出自主的道德选择,在得知格朗古同情人的关系后潇洒离去。但之后因其家族投资失败,格温多琳逐渐败下阵来。一贫如洗的她在焦急等待格朗古再次求婚时,依然自欺欺人地将自己打扮为“择选者”形象。求婚这几章频繁出现“权力”、“控制”等字眼,表明格温多琳和格朗古的恋爱关系自始至终都隐含着权力的运作。
爱略特在描述二人间的权力关系时用马作为隐喻。认识格朗古之前,格温多琳是个好骑手,经常与表兄一起纵马飞驰,但同格朗古交往时却顾虑重重,不敢策马狂奔。后来,格朗古送给她一匹漂亮的马。这马隐喻被征服的格温多琳。她曾下定决心决不会被格朗古所支配,也不会像其他女人那样牺牲自己的自由,她渴望“婚后彻底主宰这个男人”,想象着她“爬上马车,亲自驾驭飞奔的烈马,而她的丈夫只是在一旁抱着胳膊,静静看着她”[4](P115)。后来,她还为自己的婚姻选择沾沾自喜,认为那修饰一新的骏马象征着“掌控和奢侈”。然而,婚后不久,格温多琳的幻想破灭,这“奢侈”不过是格朗古对她的“掌控”。她被套上了“轭”,“像训练有素的赛马一样,尽管不那么情愿,也会在他面前跪下”[4](P269)。她那关于马车的比喻也被修正了,她痛苦地感到“自己的驾驭感被挫败……她已然坐上马车,而那个人握着缰绳,她本性又不允许自己在众目睽睽之下跳离马车”[4](P277)。她的美貌和聪明编织起来的女性权力彻底瓦解,格朗古才是真正的当权者,他将格温多琳变成了他马厩里的一匹“漂亮的被驯服的马”。
格朗古对她的男权暴政,主要通过其贵族地位实现。格温多琳强烈的阶级意识反映了她的权力悖论。她自诩为“流亡的公主”,因其生父“在西印度群岛门第显赫”,但她又担心“在太普通的环境中,不能彰显自己的社会身份”[4](P17~18)。她缺乏阶级地位的安全感,害怕从上等阶级的边缘地带跌落下来。小说开卷的赌场,各阶层的人混迹其中,有贵族、有商人、有平民……格温多琳对其中的中产阶级新富十分鄙夷,称其为“市侩”的“人类渣滓”[4](P4~6)。她觉得自家破败的房子有品位,适合“落魄的皇族”;她认为在庄园举行的射箭会也“很有品位”,因为“平民不得进入”[4](P84)。格温多琳将婚姻视作提升地位的通途,深知嫁给格朗古是稳固社会地位的上佳选择。在与格朗古交往之初,她就虚荣地感到全身裹挟在被格朗古选中的荣光之中,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格温多琳没有独立的女性意识,她标榜的“自由意志”不过是其“权力欲望”的变体。她的“自由意志”在生活困境中接连受到打击,被渐渐磨蚀。当她家财尽失,即将被上流社会放逐时,婚姻成为挽救其阶级地位的唯一方法。形容格温多琳和格朗古的关系时,爱略特有一个绝妙的比喻。格温多琳被比作令“奥德赛”忘归的海上仙女“卡吕普索”(Calypso),实际上,二人在婚姻博弈中互换了位置,“格朗古身上散发出的忘忧草(Lotos)气息占据了她全身心”[4](P114),而格温多琳成了食莲者(Lotos-eater),麻木地陷入贵族的温柔乡中无法自拔。这种权力关系不是赤裸裸的压迫关系,而是幻化成雾气,弥漫于她的生活中。
格温多琳始终被象征性地置于格朗古猎食者的凝视之下:初次相识,他就一直用“探索的目光”盯着她看;跳舞时,远处的他总是调整位置以便可以看到她;后来,格温多琳找机会同德龙达说话时,也总是难以逃脱格朗古的监视;直到格朗古溺水身亡时,他那“死人的脸”依然成为格温多琳的梦魇。格温多琳美貌的霸权,在格朗古暴君式的压迫中消解殆尽。小说第6章格温多琳饰演的活人造型(Tableau Vivant)——莎剧《冬天的故事》(TheWinter’sTale)暗合她与格朗古的婚姻悲剧。该剧女主人公赫耳弥俄涅被暴君丈夫折磨、囚禁,悲伤而亡;后其夫悔悟,哀悼妻子16年后,赫耳弥俄涅的塑像复活,一家人团聚。小说中格温多琳正是扮演最终复活场景中的塑像,而此时舞台一侧镶板掉下,露出了那张“死般面容”的画像,此时本该复活的格温多琳却“变成了一尊塑像,恐惧占据了她”[4](P49)。莎剧中的复活场景,表现了男性对爱人的忏悔和思念;而此处,男性对“女性的崇拜转化为暴力行为”。画像中的“死般面容”预示了后来格朗古溺水身亡后格温多琳梦魇中的那张“死人的脸”,他的凝视足以令血肉之躯石化为塑像。男权暴政此处尽显无遗。格温多琳的造型又暗合了勃朗宁戏剧独白诗《我的最后一位公爵夫人》(MyLastDuchess)。小说后文,德龙达好友汉斯在信中就将格朗古称作“阿方索公爵”,暗指勃朗宁诗中的公爵。格温多琳的命运与公爵夫人一致——被暴君丈夫戕害、物化为他的财产,成为“雕塑”和“画像”,成为性别压迫和男权目光的投射之物。
二、克莱斯默职业权力对格温多琳的碾压
在犹太艺术家克莱斯默挑剔的目光中,格温多琳的美依然展示得淋漓尽致,但是克莱斯默对艺术的尊奉,足以使他对抗格温多琳的女性权力,因为“他尊重女性的美,但他更敬仰音乐”[4](P39)。他以音乐家的职业精神,公允地评价格温多琳的演唱,令她膨胀的自我第一次受到遏制。格温多琳对自己受到批评感到出乎意料,她在克莱斯默身上看到了“高高在上的优越感”[4](P38)。
克莱斯默对格温多琳的凝视蕴含了权力关系。当格温多琳展现艺术才华、等待克莱斯默评判时,克莱斯默被描写成为“狮子”,而缺少职业能力的格温多琳变成了他爪子下面的“老鼠”[4](P49)。在克莱斯默的音乐才华的震慑下,格温多琳第一次意识到了自己的狂妄自大。她曾自诩为“圣塞西莉亚”——音乐艺术的守护神;她在公众面前演唱也相当自信,习惯听到一致的喝彩。但是克莱斯默“像塑像”一样凝视着她,在她自鸣得意的追问下,当众不留情面地贬抑她的音乐才华,称她的演唱不值一提。但格温多琳在痛苦之余,也感到克莱斯默“扩展了她的视野”,所以将克莱斯默称为“音乐魔法师”、“阿波罗神”。后来,格温多琳策划扮演活人造型时,特意邀请了克莱斯默,就是为了得到他的认可。她扮演赫耳弥俄涅时,克莱斯默成了“扛着十字架的基督,在爬满外行的世界踯躅”[4](P49)。得到了这个音乐家的好评之后,格温多琳觉得“她的才华像她的美貌一样打动了克莱斯默”,所以她受伤的自尊心再一次变得“洋洋自得”[4](P50)。
格温多琳落魄之时,自尊的她并不想依赖婚姻的解脱,而是最先想到咨询克莱斯默,渴望借助职业选择来走出困境。但是,克莱斯默诚实的分析使她最后的希望破灭。格温多琳和克莱斯默的对话充满张力。格温多琳维持着她即将丧失殆尽的自尊,而克莱斯默冷静地揭去她“成为艺术家之理想”的温柔面纱。之前的格温多琳丝毫没有意识到“艺术家”华丽外衣下包裹着无数的艰辛,克莱斯默“同情格温多琳的无知”,但他还是将成为艺术家所要经历磨难的“知识”灌输给了她,最终格温多琳依靠职业自立的愿望落空。
实际上,职业能力的缺失,部分造成了格温多琳这个阶级的妇女的无权地位。一方面,英国上等阶级妇女完全没有职业选择的机会,因为她们缺乏专业训练,不具备任何职业能力;另一方面,阶级地位也不允许她们纡尊降贵地去接受职业训练。英国上流社会蔑视职业和职业劳动,也并不尊重职业艺术家。如埃罗波恩特一家就是为了装点门面才请克莱斯默来当家教;后来克莱斯默力荐的米拉,到贵妇们的家中演出和任教,也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只被当作茶余饭后的消遣和彼此间的攀比工具。淑女们只是上流社会奢侈生活的点缀品,一旦身份降到中产阶级甚至下等阶级,就只能被平凡的生活所吞没。格温多琳从克莱斯默那里断绝了从艺的念头,也抗拒成为家庭教师,所以,当与格朗古结婚的机会出现时,她就抓住了这个重返上流社会的唯一的机会。相形之下,德龙达的生母“王妃”的女权主义选择,则有职业能力的支撑。她具有音乐才华,又受过职业训练,所以她有能力对抗父权并驾驭夫权。她的职业能力是其独立自主的后盾。米拉也是具备职业能力的女性,她在困境中可以选择独立但卑微的职业;收容她的梅耶克家也是个尊奉“工作和读书”的女性天堂。
爱略特利用倒叙的手法将格温多琳的困境和米拉的困境并置到连续的两章(实际上,米拉被救在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两个“困境中的少女”同时等待被救。克莱斯默同样对格温多琳和米拉两位女性给予艺术家的凝视,但是他对她们的评价迥异。一个原因是米拉具有非凡的音乐才华,而且受过专业的训练。克莱斯默高度赞誉米拉,将她视为与自己平起平坐的音乐家。当然,他对两位女性的凝视掺杂了民族自尊心。克莱斯默本人是具有民族良知的音乐家,他在同他的情敌、追求女继承人埃罗波恩特小姐的布尔特先生(Mr.Bult)对话时,自称为“永世流浪的犹太人”[4](P206),并无情地嘲弄了这位英国贵族的愚蠢和狭隘,称他为牛首人身怪物“米诺陶”。克莱斯默对米拉的欣赏也出于他们共通的民族感情。他对格温多琳音乐才能的贬抑,也影射着对她背后文化背景的讽刺,他认为她选的歌不过是那些“视野狭隘的人的所思所感。每一个乐句都充斥着一种自我满足的愚蠢;没有深邃的感情……没有普遍的特质”,只代表了“文化的初级发展阶段”[4](P39)。克莱斯默对格温多琳的批评,指向了英国狭隘的自恋情结。之前,埃罗波恩特小姐曾评说克莱斯默不太容忍英国人对音乐的态度。这位犹太艺术家对英国人霸权心理的嘲讽,渗透到他对格温多琳的凝视中。
三、德龙达对格温多琳的道德审视
格朗古的凝视代表了霸权话语对格温多琳的权力控制,克莱斯默的凝视使格温多琳意识到自己职业能力的缺失,而德龙达的凝视却给了格温多琳道德上的指引。格温多琳将德龙达看作牧师、圣人,在他的身上寻找一种宗教般的救赎力量。
德龙达对格温多琳的凝视也蕴含着一种权力的互动。小说开篇赌场一章中,格温多琳的美对德龙达预示着一种“权力”的存在,他感到将目光投向格温多琳不是一种“渴望”,而是一种“强迫”(coercion)。“强迫”一词常指权力关系,而此处却被用于审美范畴。格温多琳在男性的凝视中得到了接受朝拜的满足感,唯有德龙达的目光“审视”将她看作了“一个低等的人”[4](P5~6)。小说自始至终,德龙达虽然被格温多琳的女性魅力深深吸引,却一直将道德意识投射到她的美上。德龙达的道德力量也给予格温多琳一种“强迫力量”:格温多琳将这个稍长自己的绅士当成了“牧师”,她感到对他的敬畏和仰慕是“不由自主”(coercive)的[4](P368~369)。
爱略特塑造的德龙达形象带有浓重的理想化色彩。格温多琳把他当成牧师来倾诉自己的痛苦,忏悔自己的罪行。她甚至把德龙达当成了无所不知的上帝,希望他“不用听她的倾诉,就可以了解一切”[4](P368);她从未畏惧过上帝的震怒,却特别在意德龙达对自己的道德评判。深具同情心的德龙达更像是基督耶稣,他舍己救人,给予格温多琳的关爱和同情已然超出两性之爱。而且,他悲天悯人,是众多女性的“拯救天使”。德龙达的犹太身份更是为他耶稣般的博爱提供了注脚。他批判英国封闭的国民性格,拥抱开放的犹太文化。
在格温多琳的身上,体现了英国封闭的国民性格,她那无时无刻不渴望高高在上的心态,暗指了英国狂妄自大、不可一世的帝国扩张心理。这种对自我的盲目崇拜和对陌生事物的一味贬斥,都反映了无知和封闭的心态,必然会令其走入人生悲剧和文化困境。小说中描写格温多琳的感受时,多次提到“帝国”一词。格温多琳将获得男性的青睐看作“赢得帝国”[4](P52),她和瑞克斯讨论婚姻话题时,说她不愿在婚姻生活中受人摆布,宁可“去东方当个女王”[4](P57)。英国的帝国霸权话语投射到了这个不太关心时事的上流社会的淑女身上。格温多琳后来定居的迪普洛更是狭隘的英国阶级社会的缩影:迪普洛大多数家庭尤其是富有的家庭都自以为是,对外界漠不关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从上到下对“美国内战的结果毫不关心”,但格朗古莅临的消息却影响了“所有的社会阶层”[4](P75)。
他们对贵族阶级趋之若鹜,相反,对外来事物却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见。如在迪普洛绅士淑女的眼中,犹太音乐家克莱斯默的“异域性”被突出,被讽为“一个吉普赛人,犹太人,地球的一个气泡”[4](P210)。格温多琳位处英国主流社会,全身心被“优越感占据”,自以为是地“想象到别人的可笑”。对于世界上她不感兴趣的很多话题(可能是大多数话题),她都斥之为“愚蠢”[4](P31)。爱略特认为这种封闭自傲正是格温多琳的愚蠢之处。格温多琳的狭隘和高傲使她否定一切自己不了解、不感兴趣的东西。她也不会接受社会的先进思想,只会“不失时机地嘲讽那些致力于改革的女性,同她们划清界限”,她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把持至高无上的权力”[4](P31)。作为主流社会的一员,她歧视其他民族,在对待犹太人的问题上,更是显现出她的局限性。她去卖首饰时,觉得犹太商人乘人之危,肆无忌惮地占她的便宜。对于米拉,她也并不看在眼里,最后得知德龙达的犹太身份更是感到非常困惑。
而寄养在英国贵族家庭的德龙达,则代表了和其他民族文化融合的积极力量。他自始至终地表达着对边缘人群的同情和关爱。他怀揣着开放的心胸去探寻自己的身世之谜,主动接触中下层阶级的犹太人。他对英国人的狭隘有着自我审视,想要“除去英国人凡事惟我独尊的态度……想要捐弃国民偏见”[4](P152)。以格朗古为代表的顽固的帝国霸权和以德龙达为代表的融合其他民族文化的开放力量交战,战场就是格温多琳。她对非主流阶级民族的歧视,出于自大无知,而她的同情心也并未消失殆尽,对于母亲,对于她伤害过的瑞克斯,对于被格朗古抛弃的格莱舍夫人,甚至对于被溺死的格朗古,她都表现出同情和悔恨。性别和阶级的局限性使她无法受到开明的教育,无法认识到其悲剧的必然性,这是她权力悖论的根源。她只看到了自己的权力,却对自己的无权缺乏深刻的理解。在此,爱略特归结出小说的一个宏大的主题,就是知识和无知的交战。
格温多琳在男权的凝视下表现出了无知。小说第11章的主题即是无知,单纯冲动的格温多琳主观地臆断格朗古的心理,误将他视作“最有贵族气质的男人”,并盲目自信可以在婚后驾驭他,但是他对于她只可能是个“幽深的谜”。性别、阶级和生活环境的局限性使她远离客观的评价,只能无知地仰望或俯视不了解的人。格温多琳对艺术职业的无知,被克莱斯默一语道破。格温多琳对他人情感和生活的无知,最后又被德龙达所审视。爱略特认为格温多琳的无知是英国人共有的弱点,在第23章题记处,她将英国人的自我满足称作“疯狂的种子”,使他们“自信自己虽无支点,也可以撬动地球”[4](P213)。在第11章的结尾处,爱略特又进一步将格温多琳的无知和狭隘放大到对人类社会的隐喻[4](P102~103)。人类由于无知而造成了政治、宗教的派系纷争;英国人由于狭隘很难理解美国内战和废奴运动的正义。爱略特认为,知识足以对抗由无知所造成的霸权。在第21章题记中,爱略特论述了知识和无知的关系:
知识就是力量,但是谁又认真考虑过无知的力量呢?知识慢慢建构起来的东西,会被无知顷刻间摧毁……人类数千年用智慧筑就了高耸的神殿,而无知这个眼盲的巨人参孙会拽倒柱子,让神殿坍塌。这个曾经的欢乐之地,会如巴比伦古城般被掩埋在一片漆黑之中。[4](P194)
爱略特认为无知的可怕力量会摧毁人类的文明。的确,一个人的狭隘、无知会带给她个人的悲剧,而一个民族的狭隘、无知会给千千万万人带来绝望,而这个民族也会在自大的泥沼中无法自拔。而知识是唯一的拯救之道。爱略特借德龙达之口,给格温多琳指出的救赎之道是“追求更高的生活,那里爱与知识如影随形”。德龙达最后选择了米拉而不是格温多琳为伴,也符合这一主题。德龙达有着丰富的情感,而格温多琳只关注狭隘的个人空间。所以他给格温多琳的建议是“关注其他人的生活……不要只是关心小我的渴望,试着去关注广阔世界中的同胞”[4](P383)。
格温多琳的救赎始终维系在男性对她的理解和爱上,而缺乏同性之爱的支撑:她的母亲退到她的羽翼佑护之下;米拉将她视为争夺德龙达的竞争对手;同为暴虐受害者的情敌以复仇天使的面容出现;社交圈里的女性朋友都对格温多琳充满敌意。格温多琳一直都依赖男性的拯救,希望借贵族婚姻帮她摆脱困境,而后又渴望另一位男性来帮她走出婚姻囹圄。小说中其他女性依然无法摆脱男权的操控:犹太女孩米拉依然是“受难的少女”形象,德龙达对她的爱含有保护的成分。德龙达的生母“王妃”具有强烈的女权意识,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为了性别自由拒绝履行妻子和母亲的义务,并抛弃了民族信仰,甚至替德龙达选择了她认为高贵的英国贵族出身,她的女权建立在阶级和民族偏见之上。
在格温多琳的身上,男权对她的凝视分别瓦解了她以女性美和自我意志构筑起来的虚假权力:格朗古借助阶级权力、克莱斯默借助职业权力、德龙达借助道德权力对格温多琳进行了评判。格朗古和德龙达的凝视,是一恶一善的魔鬼与天使般的交锋,而克莱斯默的凝视是一种中性的审美凝视,远离道德评判。格温多琳陷入这些权力交织的目光之网,在男权的俯视下挣扎,她在格朗古身亡之后摆脱了他的暴政,却渴望着德龙达道德力量的控制。德龙达对她的道德指引令其看到了自己的无知与狭隘,小说结尾提到格温多琳的救赎是晦涩的,她最终依赖自我的力量摆脱无知、拥抱知识。在德龙达的婚礼上,格温多琳在送来的信中承诺做一个最好的女性,为别人带去幸福。这预示着她将更多地理解她不熟悉的和曾经漠视的人,突破无知的包围,走向更广阔的生活。
[1]Leavis,F.R.The Great Tradition:George Eliot,Henry James and Joseph Conrad[M].New York:New York UP,1963.
[2]Said,Edward.Zionism from the Standpoint of Its Victims[A].Dangerous Liasons Gender,Nation and Postcolonial Perspectives[C].Anne McClintock ed.Minneapolis:Minnesota UP,1977.
[3]Menon,Patricia.Austen,Eliot,Charlotte Bronte and the Mentor-Lover [M].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3.
[4]Eliot,George.Daniel Deronda (1876) [M].Oxford:Oxford UP,1998.
[5]Reilly,Jim.Shadowtime:History and Representation in Hardy,Conrad and George Eliot[M].London:Routledge,1993.
责任编辑 叶利荣 E-mail:yelirong@126.com
2016-07-01
2015年度国际关系学院“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科研项目(3262015T55)
徐颖(1977-),女,天津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19世纪英国文学研究。
I106.4
A
1673-1395 (2016)11-003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