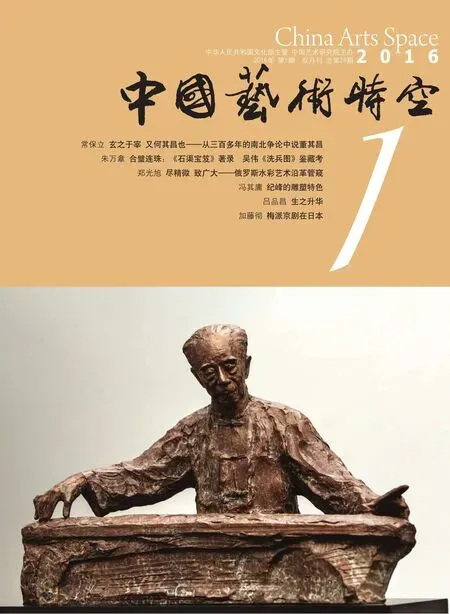联珠纹与宝相花、团花纹样文化内涵流变考
顾萍 王芳超 林泽洋
联珠纹与宝相花、团花纹样文化内涵流变考
顾萍 王芳超 林泽洋
【内容提要】联珠纹产生于中亚的萨珊王朝,在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时期经粟特人传入中国并风行一时,为中国装饰纹样带来了新的图案组织模式。联珠纹传入我国后就开始向着本土化方向发展,唐代完成了向一般团窠纹的转变。隋唐以后虽然其纹样骨架——联珠圈不存在了,但其团窠的图案形式却内化为各种形式内容的团花图案,对中国传统纹样的形态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联珠纹;宝相花;团花;团窠
一、引言
联珠纹是以大小相等的圆珠连续排列构成的一种图案纹样。成熟的、系统的联珠纹样产生于中亚的萨珊王朝,更早的一般追溯到公元前中亚、西亚等地钱币上围绕人物头像的联珠圈纹。但实际上,在萨珊王朝之前的北非、中亚、西亚一带均有联珠纹在不同载体上以各种形式出现,萨珊王朝的联珠纹在此基础上更加成熟,从形式内容到意义上都固定了下来,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南北朝到隋唐时期的中国一度广传并深刻影响了中国的装饰纹样形态。
对于联珠纹,我们应该认清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联珠纹是一种骨架纹样,由联珠带构成圆形或菱形空间,空间内添以动物、花卉等各种主体纹样进行图像装饰,并以此为基本单位组成二方或四方连续向周围循环排列。严格来讲,没有形成闭合空间以及主体纹样的单纯的联珠带也应属于联珠纹,但我们本文只讨论联珠团窠纹及其影响,联珠带不涉及,后文提到“联珠纹”时,均指联珠圈纹。其次,联珠纹存在的载体其实有很多,并非纺织品所独有,同时也存在于各种器物、和建筑装饰上。我们这里主要从服饰的角度进行分析。第三,联珠纹并非一时一地所独有,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均有可能自发的产生,如我国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商周青铜器以及汉代瓦当上就有联珠纹的存在。但这些都是零星的、不系统的,相互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对以后也没有较大的影响,风行于中国北朝以及隋唐时期的联珠纹的源头是中亚的萨珊王朝。
上面我们提到“团窠”,那么什么是团窠呢?一个相对独立和封闭的主题纹样单元谓之“窠”,有时也作“科”,唐代一般为圆形,故称为“团窠”。清代王琦在《李长吉歌诗汇解·梁公子》中解释:“所谓团窠者,即团花也。”我们本文所讲的联珠团窠,顾名思义,即由联珠为骨架构成的团形纹样单位。
目前对于联珠纹的研究是很多的,相关文章、著作举不胜举。但这些研究一般将重点放在联珠纹在中国的传播及随后的发展上,[1]部分地还指出了联珠团窠纹与唐代典型风格的宝相花之间的密切关系上,[2]对于唐代之后的影响并没有过多涉及。实际上,正是在联珠团窠纹的启发下,中国才演化出了团窠的图案样式。我们本文叙述联珠纹在中国传播的同时,也进一步论证它的这些影响。
[1] 如马东:《唐初官服“异文”与“陵阳公样”》, 尚刚:《风从西方来——初论北朝工艺美术中的西方因素》,王雪迪:《北朝隋唐时期墓葬中的联珠纹装饰研究》,陈彦姝:《六世纪中后期的中国联珠纹织物》,周菁葆:《日本正仓院所藏唐锦研究》等等。
[2] 如尚刚:《从联珠纹到写实花鸟——隋唐五代丝绸装饰主题的演变》,韩澄:《中国传统服饰中植物纹样的典型特征》,孙荪:《丝绸之路对中国染织图案的影响》,王静怡、包铭新:《宝相花纹样小考》,高山:《从唐联珠猪头纹锦看联珠纹样发展过程中的装饰演变》等等。
二、联珠纹传入中国后的本土演化
1.联珠纹传入前中国传统的织物纹样
前边我们说到,联珠纹的传入改变了中国传统的服饰纹样构成模式。那么中国本土的服饰图案是什么样的呢?商周时期的织物纹样主要以各种形式的几何纹(如云雷纹、菱形纹等)和各种变体动物纹(如饕餮纹、夔龙纹、窃曲纹等)为主,这和当时青铜器上的纹饰是相似的。春秋战国时期织物纹样在商周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几何骨架和对称手法仍然沿用,变化主要表现在内容题材的丰富以及风格的自由化,更加开放与写实。几何纹有矩形纹、菱形纹、十字纹、回纹等,动物纹有龙纹、凤纹、各种走兽纹样等等。在纹样的排列组合及构图上,则表现为二者的组合形式(图1)。汉代织物纹样主要有云气纹、动物纹、花卉纹、几何纹等,其中云气纹为主体纹样,往往混同其他纹样一同使用,人、物活跃在云气纹中间,线条流动飘逸。此外汉代还新出现了使用文字的做法,一般将其填充在纹样的间隙中,文字主要为“延年益寿”、“长乐明光”等吉祥语。总之,中国最本土的服饰纹样是以几何纹、动物纹、龙纹、云气纹等为主要题材,以横贯全幅、前后连续为主要构图布局的形态。曾经在中国广泛流行的、以联珠团窠为主要单位,呈现二方、四方连续循环排列的联珠团窠纹来自西域。

图1 湖北江陵马山砖厂出土风纹
2.联珠纹的传入
联珠纹的传入并风行中原实际上是从南北朝经隋至唐初这段时间,这和外来文化(胡风)大量影响中国的时间大致是相一致的。这一时期中原王朝对这些民族没有种族、文化上的偏见,同外来文化的交融也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时期。唐代称粟特人为“昭武九姓”,他们善于经商,经河西走廊进入内地,大量分布于中原内地,为中原王朝带来了外来的货物与文化,联珠纹就是这样进入中国的。东晋时期传入我国新疆地区,于阗地区的佛寺壁画就有联珠纹的出现;北朝时,西域高昌国(今吐鲁番)联珠纹丝织物已经流行。阿斯塔那纳墓葬出土有大量的、形式多样的联珠纹织锦,充分融汇了波斯萨珊王朝的图案方法,其中最著名的还要数联珠“胡王”织锦 (图2)。联珠纹传入中国后,成为中原图案体系的组成,丰富了织物的品种和图案,服装从纹样图案到服式都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图2 联珠“胡王”锦
3.传入后的联珠团窠纹的演变
在萨珊王朝,联珠纹图案除纯粹的审美意义以外,还是一种与宗教思想紧密结合的纹样。萨珊王朝以琐罗亚斯德教为国教,中国称之为拜火教或祆教。在装饰纹样上,连续的圆珠或圆圈象征着日月星辰的天空,即众神和光明的所在。同时联珠圈内存在多种多样的主体纹样,如带有双翼的天马、野猪猪头、鸾鸟、大角鹿等等,这些在祆教里也都是神明的象征,如带有双翼的天马是日神米特拉的化身,而野猪、骆驼、山羊则是军神维尔斯拉格纳的化身。1959年新疆阿斯塔那北区138号墓就出土有联珠猪头纹覆面。
隋唐时期政治环境开放、包容。联珠纹在东西文化交流过程中,风格面貌逐渐发生变化,被民族文化应用吸收。这时的联珠、联珠团窠更多地是作为一种富于异域风情的文化样式而存在,正如这一时期对其他外来文化的热衷一样。中原未必能够完全理解其纹样的本来意义,在对它从形式内容到意义的改造过程中都自觉不自觉地按照自身文化的审美喜好进行,其原有的社会意义也被淡化以致消失。联珠团窠纹的民族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产生了对称的纹样。纹样对称出现是中原文化的一个传统,在联珠纹传入后按照这一习惯对其进行了改造,表现为同一个联珠圈内纹样的对称出现。在纹样对称的联珠圈纹中,大多是左右对称出现,也有镜面对称(如我们上面所讲的联珠“胡王”锦)。左右对称的如1969年阿斯塔那北区134号墓出土联珠对鸡纹锦,1970年阿斯塔那北区92号墓出土联珠对鸭纹锦。
其次,是汉字的使用。在织锦上使用汉字是延续汉代以来中原文化的做法,通常在织锦纹饰的空隙中加入表示吉祥寓意的汉字。日本法隆寺收藏联珠四骑猎狮纹锦,图案的马腿上就有汉字“吉”和“山”。此外,例证还有阿斯塔纳出土596年、617年“贵”字联珠圈孔雀纹锦、620年“吉”字对年纹锦等等。
第三,是主纹图案的民族化。在东西文化的交流过程中,联珠纹主纹图案面貌逐渐本土化,唐代人们根据自身文化对联珠纹进行改造,用中原化题材代替外来形象,原来翼马、猪头、立鸟衔珠、狮子、骆驼等西域风格浓厚的题材纹样,变化为龙凤、虎豹、鸳鸯、鸡鸭这些本土纹样。如1959年阿斯塔那出土的联珠鹿纹锦,鹿体貌丰满,形态从容不迫,具有大唐王朝的风度(图3)。

图3 联珠对孔雀“贵”字纹锦覆面
第四,是纹样骨架的变化。对联珠圈本身的改造在很大程度上已失去它本来的含义而变为一种图案骨架,主要表现为改单层联珠圈为双层,或用卷草纹代替。1972年阿斯塔那出土景云元年(710)联珠龙纹锦(图4),主纹是中国传统图案的龙,联珠从原来的单层变为双层。日本正仓院藏联珠狩猎纹锦,联珠样式一层为联珠,一层为卷草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纹样骨架的变化是联珠团窠纹最大、并且最终影响中国服饰纹样走势的一种,它最终使团窠(花)图案进入中国的装饰领域。

图4 唐联珠对龙纹绫
我们要注意的是,虽然联珠纹风行一时并对本土纹样产生深远影响,但它并没有完全取代本土纹样,更不是唯一样式。同时我们不能因此认为联珠团窠纹完全内化为中原本土的纹样。《步辇图》描绘了一个对外场合,为标明身份,画家对画中人物的描绘是选取符合其身份的典型。其中吐方使者身着典型的联珠团窠纹,唐方衣着则没有团窠纹样,男性均是素色长袍,女性衣着虽有纹样,但也不是团窠。由此可见,当时人的意识里仍然将联珠纹视为外来的胡文化的标志,与中原是有区别的(图5)。

图5 《步辇图》(局部)
4.团窠纹样
联珠纹在中国风行一时,但也并非伴随唐朝的始终,到中唐时联珠纹就逐渐衰落了下来。“联珠纹在中国流行了大约一百五十年”、“7世纪50至80年代……后,迅速转入衰微”。[1]原因有两个:一、萨珊王朝公元651年灭亡之后,联珠纹的输出也就失去了源头,“在唐锦上表现出来的萨珊风格就愈来愈浅”,[2]已经传入中国境内者被中国渐渐同化。二、与唐代的禁锦令有关,武则天、玄宗、代宗均曾禁锦:长寿二年(693),武则天禁锦,随后的开元二年(714)玄宗又更加决绝地禁锦,禁锦令使联珠纹样失去了存在的重要的载体。我们认为第一个原因的因素更大一些:禁锦的出发点在于禁止奢华,纹样繁杂的联珠团窠纹也在其中,但除联珠纹以外的纹样依然存在,这就不是政府禁令所能解释的了。况且由于对外贸易的需要,禁锦也不可能彻底。
联珠纹衰落下去了,但它的影响却一直存在,经过中原民族审美取向的改造之后,与中国本土的装饰纹样融合,为中国传统纹样的题材领域注入了新的元素。唐代常见的一般团窠团花以及具有典型唐代风貌的宝相花的产生了就是与联珠团窠纹紧密相连系的。
(1)联珠团窠与宝相花的关系
宝相花是唐代一种代表性的装饰纹样,雍容华贵、端庄大气的风格充分契合了盛唐丰腴艳丽的美艺术思想。它集众多花卉形象为一身,整体呈放射状对称排列。“宝相”一词本有“佛像的庄严”之意,“宝相花”一词最早出现在宋代,《营造法式》中有“宝相花花心为如意形”的记载。宝相花首先以莲花为主要母体,这是与当时佛教的盛行是密切相关的。但实际上宝相花纹样构成是复杂的,组合了多花卉于一体,“将印度佛教的莲花形象、中亚的葡萄和石榴形象、地中海的忍冬和卷云形象、中国本土的植物图案组合出变化无穷的、富有独特中国韵味的丰满的宝相花形象”。[3]
宝相花不是联珠纹直接演化而来的,这得到了公认,但宝相花的产生与联珠团窠纹有密切的关系。宝相花纹出现于7世纪末,并在开元天宝年间广为流传,从时间上看是与联珠纹的衰退相互顺接的。从形式上看,二者也存在内在的联系,具体来说,就是宝相花纹借用了联珠团窠纹的团窠形式,并结合本民族的题材而成。因此它也是一种团窠纹,但它的静态、富丽和汉代云气纹的流动迥异,佛教背景使之与当时及后世的一般团窠的世俗化不同。
[1] 见尚刚:吸收与改造:六世纪至八世纪的中国联珠圈纹织物与其启示》,《创意设计源》,2009年第2期,第26页。
[2] 孙机:《中国古舆与服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451页。
[3] 孙荪:《丝绸之路对中国染织图案的影响》,《东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6月,第2卷第2期,第55页。
[4] (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第十卷·唐朝下》,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
[5] 赵丰:《中国丝绸艺术史》.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
(2)一般团窠纹
联珠纹团窠也是团窠纹样纹的一种,在传入中国后的演化已逐渐失去闭合联珠圈的外壳形式,却仍沿用团窠形的图案形式,此时的图案已不能够称其为联珠团窠,而是一种一般意义上的团窠,并且是相当民族化了的。从联珠团窠到一般团窠,这一过程的关键一步是在唐朝就完成了的。团窠图案以各种形式留存了下来,成为民族化的、影响长远的图案样式。
说到唐代的团窠纹样,就不能不提到“陵阳公样”。“陵阳公样”记载于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卷十中:“窦师纶……封陵阳公。性巧绝,草创之际,乘舆皆缺,敕兼益州大行台检校修造。凡创瑞锦、宫绫,章彩奇丽,蜀人至今谓之陵阳公样。官至太府卿,银、坊、邛三州刺史。高祖、太宗时,内库瑞锦对雉、斗羊、翔凤、游麟之状,创自师纶,至今传之。”[4]从这些文献,我们可知“陵阳公样”是一种以对称为主要构成特点的图案样式,并且被用作宫廷作坊的样式。对于“陵阳公样”的构成形态,“赵丰认为,花环团窠与动物纹样的联合很可能就是陵阳公样的模式”。[5]同联珠团窠纹相比,“陵阳公样”与之都采用了团窠的组织模式,不同点在于具体内容的民族化,花卉纹样、对称排列都是中原的。因此我们可以说,“陵阳公样”是对联珠团窠纹继承发展的结果。
但对于陵阳公样目前并无例证或者说确切的图像例证可见,仅限于后人对它的推测。目前可见唐代一般团窠纹样的图像资料却是相当多的,表现形态也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在流传至今的唐代卷轴画以及壁画等所描绘的人物服饰上都能看到团窠纹的存在。如在《簪花仕女图》中,左一、右二人物均身着团窠(团花)纹长裙。《挥扇仕女图》中则有较多表现:右一人物,身着大团窠长袍,手持团扇上也有对凤纹组成的团形图案;右五人物身着小团花袍,“窠”较为小和分散;右八人身着大团窠长袍,应与右一人物同款(图6)。

图6 《挥扇仕女图》(局部)
实际上,同古代社会的其他时期一样,唐代也利用服饰纹样来区别官阶。团窠纹样在官服中要求的基本规律是大团窠纹为贵,小窠次之。如《旧唐书·舆服制》记载,武德四年(621)颁布了一次官常服面料图纹制度:“三品已上,大科狾(细)绫及罗,其色紫,饰用玉。五品已上,小科狾(细)绫及罗,其色朱,饰用金。”[1]

图7 白沙宋墓壁画
三、联珠团窠纹样对中国服饰纹样形态发展的
在联珠团窠纹的影响下,各种形式的团窠、团花图案长远地存在于中国古代服饰上,直到明清仍然方兴未艾。对此,我们应有这样的认识:联珠团窠走向各种形式的团窠纹样,关键的一步是在唐朝就完成了的,在唐以后随后漫长的时期内没有本质的变化,只是具体风格会随各个时代服饰纹样风貌的发展而变化,具体表现在题材内容、造型方法,以及与整件服装其他部分的相互构图关系上。
宋、元时期服饰纹样构图与隋唐流行的联珠团窠的繁密形式不同,改为疏朗,图案之间有较大空隙。这更符合东亚尤其是汉族人的审美。在这一阶段人们对服饰纹饰的崇尚改繁密为简素、淡雅,宋代尤其如此。从目前所见宋代的服饰图像资料可知,这时有团窠的服装要比无团窠的服装少得多。
明清时期各种形式的团窠纹样更加丰富了起来,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使用团窠的服装多了起来;第二,被团窠采用的题材多了起来;第三,团窠纹样与周边纹样的组合形式多了起来。之所以有这些变化,究其原因,在于人们审美趣味的转变。宋代美学思想崇尚质朴含蓄,服饰上的纹样用得较少,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包括团窠纹样在内的各种服饰装饰图案被用于服装上,以突显富贵、吉祥的视觉感受和精神寓意。相比唐代宗教意义浓厚的宝相花,这一时期的团窠图案更接近于传达世俗的精神追求。明代纹样在宋元的基础上发展,吉祥纹样更多出现。如北京万历皇帝定陵出土明代十二团龙衮服,上有团龙十二个(图8)。清代服饰纹样风格细密繁缛,乃至矫饰造作,题材意必吉祥,除了动物、植物及其组合形式以外,有时甚至直接用文字如“喜”、“寿”等(图9)。同样在官服系统中,团花图案也有自己独特的表现,不再详述。

图8 明代十二团龙衮服

图9 清富贵一品瓜瓞绵绵团花纹绣
四、结语
以上就传自中亚萨珊王朝的联珠纹等问题进行了分析,进而论证了联珠团窠纹在中国的南北朝、隋唐时期由于当时人们对于外来文化的崇尚而风行一时。在联珠团窠纹传入中国以后,就不断地本土化,其主题纹样的题材及布排方式均向着本土审美方向发展,甚至原有的闭合联珠圈也逐渐消退,但它的基本图案形式——团窠内化为中国的一种传统样式,可以说它是失其形而存其神。联珠团窠纹的传入,改变了中国本土的服饰装饰纹样,从唐代直到明清各种形式的团窠图案一直存在于中国传统服饰纹样中,当然,各时代都随各时代的具体风格发生着变化,如题材内容的选择、构图造型方式,以及在整个服装中的位置安排等等。
(作者单位:西安美术学院。本文为2015年度西安美术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2015XK111)
[1] (后晋)刘昫:《后汉书》,中华书局,2000年,第1328页。
敦煌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