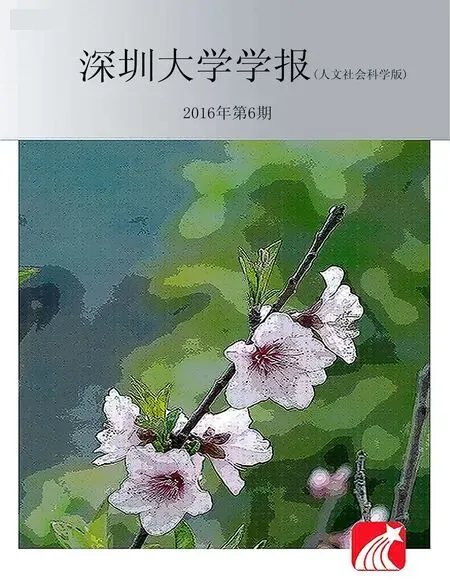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制度—文化约束
陶一桃
(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广东深圳518060)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制度—文化约束
陶一桃
(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广东深圳518060)
从根本上说,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无论对中国还是沿线国家来说都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文化大于资本、制度重于技术的非纯经济问题。相对于资本与技术而言,来自于制度—文化的约束,既是最软的约束,也是最坚硬的约束,从而也是最根本的约束。所谓制度—文化约束是指,由不同习俗、价值观等文化因素所形成的内在制度安排之间的相互认同障碍,以及这种具有不同文化特质的内在制度安排对更广泛区域或共同体内部、正式制度安排缔结和制度环境形成的影响。跨越制度—文化约束的关键是在共同繁荣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彼此尊重、相互包容的可操作的制度—文化认知共同体系。这对一带一路倡议掷地有声地实施,无论从逻辑还是现实意义上说,都是应该先行的策略与智慧考量。
一带一路;制度—文化约束;包容性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中国社会由政策开放走向制度开放,由外向型经济迈向开放型经济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中国社会改革开放38年来由经济迅猛发展所致的资本、技术、产能高度积累的自然选择;是中国社会经济转型、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趋势;更是今天的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所秉承的包容性发展、共同繁荣理念的具体体现。但是从根本上说,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无论对中国还是沿线国家来说都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文化大于资本,制度重于技术的非纯经济问题。相对于资本与技术而言,来自于制度—文化的约束,既是最软的约束,也是最坚硬的约束,从而也是最根本的约束。因为实际上,是共同的价值观和规则界定着一个社会和这个社会或共同体及其个人的选择行为。而在一个社会或共同体中发展起来的,并已经成形的非正式制度,不仅是制度这一系统的组成部分,也是文化这一系统的组成部分。因此,跨越制度—文化约束的关键在于构建一个彼此尊重、相互包容性的可操作的制度—文化认知共体。这对于一带一路倡议掷地有声地实施,无论从逻辑还是现实意义上来说,都是应该先行的策略与智慧考量。
一、关于制度—文化约束的制度经济学诠释
这里所说的制度—文化约束,不是简单的制度加文化的约束,而是一个制度经济学上的概念。它是指由不同习俗、价值观等文化因素所形成的内在制度安排之间的相互认同障碍,以及这种具有不同文化特质的内在制度安排对更广泛区域或共同体内部,在正式制度安排的缔结和制度环境形成方面的影响。我们知道,没有无文化特质的制度,也没有无制度功能的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即制度,制度即文化。不同的民族以不同的方式创造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又以不同的方式创造着不同的民族,在这一过程中,决定并形成一个民族或国家的规则、制度及其选择行为。正如美国当代杰出经济学家托马斯·索厄尔所说:“文化不是博物馆里的藏品。它们是日常生活中工作着的调节机制。具有决定意义的判断不是研究者和理论家们的判断,而是那些隐含在干百万单项决策中的判断。这些决策要保留或放弃各种持定的文化习惯。而做出这些决策的人要么从这种决策受益,要么独自承担这种决策可能造成的代价、无效率和遭废弃。那样的代价并不总体现为货币,它们可以有多种形式,从不方便到死亡。”[1]其实道理也很简单,如果在一些问题上达不成某种共识,尤其是文化—价值共识,一个人就很难与另一个人顺畅交往,国家与国家之间亦然。
人们通常把制度定义为一种由人制定的规则,它抑制着人际交往中可能出现的任意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增进着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秩序与信赖,从而降低着交往的不确定性与成本。德国制度经济学家柯武刚(Wolfgang Kasper)、史漫飞(Manfred E.Street)曾这样来阐述制度的功能:“所有人际交往都需要一定程度的可预见性。当人们受规则(我们将其称为制度)的约束时,个人的行为就较可预见。当然,人们也需要制度来促进经济生活,因为经济交易不可能在真空中发挥作用。事实上,在经济增长速度和共同体成员满足其经济目标的程度上,制度的类型和质量造成了巨大的差异。……对经济增长理论的简短考察证明,增长是一种复杂现象。新古典增长理论只能识别那些最直接的增长条件,如资本积累和技术变革,而要解释人们为什么要储蓄、投资、学习并收集有用的知识,我们就必须着眼于经济成败背后的各种制度体系和价值体系。”[2](P1)
制度作为一种引导人们行动的手段,根据其起源的不同被区分为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内在制度被定义为群体内随经验而演化的规则,如习惯、习俗、礼貌、道德观以及文化—价值观等;而外在制度则被定义为外在地设计出来,并靠政治行动自上而下强加于社会的规则。可以说在现实生活中,大量的内在制度根据经验不断演化并控制着人的相互交往,人们长期保存内在制度,因为有些人发现它们并觉得它们有益。内在制度在构建社会交往、沟通以自我中心的个人与实现社会整合上的重要性也早已被先哲和社会学家们所认识。如约翰·洛克(1632—1704年)、大卫·休莫(1711—1776年)和亚当·斯密(1723—1790年)都表达过类似的思想:一个社会的制度框架必须以演进的内在制度为基础。有意识制定的、立法通过的规则,以及由政治过程决定的制度的整个架构,都是必须以内在制度为基础的[2](P122)。对这一观点最强有力的支持者还有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3]。
根据对违规行为惩罚的方式或强制程度不同,制度还被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通常对违反内在制度的惩罚是分权的、自发的社会反馈,因为内在制度大多诉诸自愿协调。然而,对外在制度的违反的惩罚则是通过正式的、有组织的机制来强制实施的,所以相对于非正式制度,正式惩罚的强制性留给个人评估得失的空间和余地要小得多。内在制度大多属于非正式制度。但是在很多时候,内在制度安排不仅具有刚性,而且还在相当程度制约着正式制度安排,并经常在人们现实生活中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如作为内在制度重要内容的习俗、习惯、价值观就具有这样的力量和作用。
不仅构成内在制度的某些类型属于文化的范畴,从根本上说,规则系统也是文化的组成部分。英国社会学家爱德华·伯内特·泰勒把文化定义为:“一个人作为社会一员所获得的全部能力和秉性。”[4](P1)研究制度经济学的学者们认为,爱德华·伯内特·泰勒的文化定义,不仅恰如其分地指出了由文化沟通的个人与社会群体间的张力,而且还着重于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文化附着于习得制度和支持这些制度的价值。这种意义上的文化由语言、思想、价值、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构成,它甚至是一个大于制度内涵的概念。
文化包含有许多内在制度,诸如习俗与习惯等等。有学者认为,那些来自于深受不同文化影响,并打上特定文化烙印的习惯与习俗,不仅很难用语言予以清晰阐述,而且还很难孤立地传递给不属于该文化的人。所以,文化可以被看作是一套基本上不可言传的规则系统。由共同熟悉、认同的文化所形成的内在制度,减少着人们交往的风险和成本,所以人们更驾轻就熟于自己文化中的制度安排,并相对于其他文化规则体系也会更加如鱼得水。但是,随着国际化和文化的多元化,一个个人完全可以在从属于一个村庄文化的同时,又分享着一个行业中的世界性文化惯例。人们也会在分享世界分工的好处时意识到,异己的事物并非必然不好,也不必然有威胁性。尽管如此,在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里,人们也只能在检验其在实践上如何帮助人们实现诸如自由、和平和繁荣这样的共同基本价值方面来比较文化性制度的品质,而在协调人们的行为或应付变化上,并非所有的文化都能同样有效。所以,文化的开放与包容,并不是无批评地肯定所有文化都有价值,包括我们已经熟悉习惯了的,并节约着我们交易成本的那些规则[2](P196-198)。
文化通常是缓慢地演变,所谓的路径依赖往往源于文化的凝固力,尤其是文化性制度的作用①。但是,当新的思想在原有文化体系中产生,当外部因素冲击、影响既有文化体系时,人们要么会深切感觉到,如若不改变原有规则,就无法获得潜在的好处;要么会强烈意识到,外来文化制度比自身已具有的更具有优越性时,当新的文化特质得到模仿,并使社会中接受它们的人数超过一个临界点时,它们就变成了一个新的规范或者说制度了。从世界经济发展历程来看,“当商人和制造商们认为另一些国家有更受规则约束的政府和更可信赖的制度环境时,就会迁往那些国家。这不仅迫使统治者们放弃了任意的机会主义,提供了可信赖的规则,而且还鼓励了某些内在的文化性制度,如诚实、守时和节俭。”[2](P198)当内在文化性制度和建筑之上的外在制度被拥有不同文化的民族国家所普遍接受时,一种具有公共物品性质的制度——国际惯例也就由此形成。
可以说,突破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的制度—文化约束的过程,就是在更广泛区域共同体中,对构成内在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性制度(习俗、习惯、价值观、信仰等内在制度)的逐步包容、认同的过程。因为它们是区域共同体间正式制度得以缔结的最柔软然而又最坚硬的基础。
二、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制度—文化约束
应该说,经过38年的改革开放和国力增强,我国已经有相当的潜力可以通过输出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在发展中国家中的影响力。但是,由于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对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国家了解的匮乏;由于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把一带一路更多地只当作经济项目来做;由于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更多地关注我们自己一厢情愿的政绩目标的实现;由于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还没有彻底摆脱“运动心态”和急功近利的潜意识;所以在客观现实中,我们原本善意的愿望和“惠己悦人”的行为,又难免由于我们自身的原因而遭遇尴尬与挫折,缅甸的密松水坝就是最典型的案例。
2011年9月30日,缅甸总统吴登盛宣布,为“尊重人民的意愿”,由中方投资兴建的密松大坝项目暂停建设,直至他的五年任期结束。这个令人心痛的结局让我们很多人措手不及,包括中国电力投资集团的高层领导者。但是,这却是缅甸当地村民、社会活动人士、学者及科学家们携手战斗五年多的结果,而我们却失去了工程初期与当地居民和公民社会组织深入对话,相互了解,达成共识的极好机会。从密松水坝项目的流产中,我们起码应该意识到来自制度—文化障碍的三个方面问题。
其一,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最大瓶颈是知识的贫瘠,是我们自身对沿线国家相关知识的相对匮乏,尤其是对沿线国家包括习惯、习俗、宗教信仰、价值观等文化性制度,即内在制度的了解严重不足。目前能够帮助我们走出这种知识困境的重要并快捷的力量是专家学者们,而不是单纯的资本与技术。那些能够流利运用当地语言,熟悉相关对象国的历史与文化,并对其做过长时间研究,而且通过常年跟踪研究积累广泛人脉的地区研究专家学者们,是带动资本与技术流动的深层而又容易被各方接受的力量[5]。如前面提到的缅甸密松水坝,如果在项目启动前,有熟悉当地历史文化、习俗信仰的专家学者们对水坝周边社会文化环境进行深入考察,客观评估政府在项目所涉及到的拆迁、社会动员等诸多问题上的实际动员力,科学预见到缅甸既有的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以及无法摆脱西方的影响和干涉的现实,准确判断到在弱势的缅甸政府领导下,涉及公共选择的重大问题不可能以“中国式”的方法与速度整齐划一地得到解决等等,或许不会激发美英支持下的克钦民族在英、日、澳、美等地广泛组织的反对密松水坝修建的抗议,或许有可能会避免在国际舆论方面造成的不可逆转的影响,或许不会彻底导致缅甸领导人最终只能妥协的被动局面[5]。可以说,在许多问题上,在相当程度上,是构成内在制度的习惯、习俗、价值观等文化性制度的认同障碍,影响、制约了拥有不同文化历史的区域共同体之间的正式制度安排的缔结,而不完全是经济利益方面的选择与取舍。
其二,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最重要阻力不是来自于外在,而在于我们自身的认知能力。首先我们应该明白,在全球化的今天,跨越文化的区域共同体的发展进程中,情感的力量有时会大于资本的力量。如密松大坝附近的克钦独立组织是水坝建设的最为活跃、也最能发声的反对的力量。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克钦族人将美卡河与马里卡河的交汇点,即密松水坝坝址尊崇为自己文化的发源地,因为这里是宽广的伊洛瓦底江的源头。而我们的项目建设者则没有及时表达出对这一民族文化渊源与情结的高度尊重与敬畏,从而造成了不必要的,同时也难以一下子挽回的情感对立[6]。其次,要学会与对象国利益相关者的对话,而不能“中国式”的只与官员、政府部门、权力部门沟通,尤其要学会按照所在国的公共选择程序与路径行事。密松水坝的窘境告诉我们,从一开始就不重视,甚至拒绝同当地社区及公民组织打交道,会让我们自己付出沉重的代价。如随着项目的进行,其他舆论媒体告诉水坝住址的居民,这个项目只是为了满足中国对能源的需求,而不是为了缅甸的发展。密松水坝一旦建成,发电能力将达到600万千瓦,约为三峡大坝的三分之一。其发电量的90%将输往中国。与此同时,一个大小相当于新加坡国土面积,深达66层大楼的巨大水库将淹没缅甸文化的中心地带。12000名克钦族居民将被搬迁,20000多人将受到水库建设和运行的影响。虽然中方投资商也曾尝试规范做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估(EIA)(其实在环评研究远未完成之前,大坝施工就已经起步了),但环评报告是在反对声浪已成汹涌之势才姗姗而来的,无疑已经失去了当地人的信任感[7]。再次,要学会高度重视公民社会组织的力量,道理在于“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在仰光,活跃着勇敢而强大的环保NGO组织汇合而成的团队,他们花费了数月的时间动员、说服缅甸新政府的高层官员,使他们相信人民不可忽视,并且该项目的可能危害还会更大。之后,昂山素季发表拯救伊洛瓦底江的公开呼吁,将NGO的反坝斗争推上了国际舞台。缅甸境外的组织,如缅甸河流网络,也在不懈工作,以提高国际社会对水坝工程的了解和关注。终于国际河流组织向缅甸NGO组织提供技术分析,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并且为他们与中国电力保持接触提供支持,就水坝工程进行对话[7]。然而,我们自己面对陌生的社会决策程序和一直没有重视起来的如此强而有力的社会组织则处处被动,甚至一时束手无策。因为我们既不熟悉所在国的规则,又无法或不可能在所在国已成熟运作的社会规制中按我们熟悉的规则来办事。最后,我们要学会对不同文化和国度的发展观的了解,这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文化约束之“结”。我们知道,密松水坝是七个梯级水坝工程的一部分,我国为此投资近130亿人民币。但是,是否所有国家都乐意在自己的江河上拦河建坝,都愿意牺牲滔滔江河来满足对能源的需求,这是个应该探讨、磋商的问题。因为发展观的价值判断不同,将直接影响项目的落地和正式制度安排的顺利缔结。其实,人类所有的经济行为都不能不计代价。据《南华早报》报道,中国南方电网公司为凸显其社会责任感,退出了柬埔寨几座争议很多的水坝项目。中国水电集团在上海证交所公开发行股票前夕,潜在投资人、证券分析师以及中国媒体都对其环境政策草案进行了讨论,该政策草案是其应对海外经营风险的举措。根据媒体的报道,全球大坝的最大投资商中国进出口银行因考虑到下游国家的诸多关切,推迟了对埃塞俄比亚境内尼罗河上齐莫哥耶达水电站的投资。显然,许多中国水坝建造商与投资商正在尝试着面对所在国的公民社会组织的关切,而跨越制度—文化约束,或许也正是在以共同繁荣为前提的博弈与挫折过程中逐步完成的。
其三,一带一路倡议推进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自身观念与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改变。中国改革开放38年的经验证明,“举国体制”是有效且成功的。它在集中稀缺资源干大事方面,在快速动员民众参与重大建设项目方面,在整齐划一地高效解决群体问题方面都具有其他体制无法比拟的效率与优势。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以这样的思维习惯与方式去“中国式”地处理、落地一带一路项目,尤其是直接涉及当地居民利益甚至文化信仰的大工程。依法行动,按国际惯例办事,摒弃急功近利和“大运动”心态,用时间换共识,用了解换共赢,用法律保障效率与利益,这或许是我们可以考虑的理性选择。正如文化不能直接改变社会,但能够改变人,而人则能够改变社会一样,内在制度往往并不能直接改变规则,但会影响规则的制定者。而作为规则制定者的人,尤其是政府,则是制度这一公共物品的创造者或供给者。
三、包容性发展的意义与价值
谈到制度的重要性时,柯武刚(Wolfgang Kasper)、史漫飞(Manfred E.Street)曾指出:“民间的个人和企业只有在确信他们的预期能够兑现的情况下才可能购买、销售、雇佣劳动、投资和进行创新。个人和厂商间的大量交易都基于重复性运作。人类包括经济生活中的相互交往,都依赖于某种信任。信任以一种秩序为基础。而要维护这种秩序,就要依靠各种禁止不可预见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的规则。我们称这些规则为‘制度’。……因此,在正常情况下,防止这类情形出现的制度就构成了我们的生活水平、我们的安全感和共同体的真正基础。”[2](P14)
全球化是以某种价值认同为前提和基础的。价值认同是区域合作的潜在的制度性资产②。构建能够一致理解的价值共同体,有助于设法使共同体内在制度演化变得更加可预见并有序。所以,对于演化中的共同体内在制度而言,共同价值发挥着过滤器和凝聚剂的作用。然而,价值认同是共同体成员对内在制度的一种非正式认可,所以它不会被硬性地强制执行,而一定是文化互动包容的结果与收获。因为,任何一种文明与文化之间的传播都不可能是单向的,它应该呈现出双向交流、双向收获的势态。这样的交流才是健康的、可持续的。经济的交往也是如此。另外,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有时国与国之间合作缔结的偏差,往往并不简单是追求目标和发展路径选择上的偏差,而是基于情感认同、价值认同的信任关系方面的偏差。这种偏差的存在既是区域共同发展繁荣难以避免的问题,又是必须共同面对,并努力携手逾越的最柔软然而又是最坚硬的障碍。
包容性发展无论对国与国之间还是区域共同体之间,都不仅仅是一种境界、一种理念、一种价值观,更是真正实现合作,切实共谋繁荣的缔结盟约的思想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观念、价值、共识本身就是资源,就是创造财富的财富,是带来繁荣的无形资本与保障。
包容性发展的宗旨就是共同发展繁荣。然而人类共同发展繁荣的过程,绝不是用观念战胜观念的过程,而是在对人类普世价值观认同、敬畏的前提下,观念对观念的包容,价值对价值的尊重,文化对文化的兼容过程。
包容性发展的要旨是对成员国自身发展的肯定与支持,是对国别差异性的接纳与尊重,而不是此消彼长的竞技与厮杀,更不是用共性对国别性的限制与否定。经济全球化的现实,不仅在经济运行机制内部已经为个体在共同体中的生长、发展、繁荣提供了空间,也为共同体的共同发展繁荣提供了无限的可能。
包容性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对彼此核心利益的保护与尊重。市场是以公平交换为前提的。市场非战场,战场上要歼灭对手,而市场上则要培育对手,培育生意伙伴。没有健康的伙伴关系,就不可能有健康的市场秩序,更不可能有惠及彼此的持久发展与繁荣。区域经济的发展,总会伴随着正的外部效应,或者说“邻里效应”的创造与释放,如经济的相互拉动与趋动。尽管由于各个国家经济体量大小、开放程度高低和经济发展类型等因素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各自所创造、释放的正的“邻里效应”的辐射力有所不同,但是,正的外部性无疑对区域各国乃至共同体都是可以分享的“社会剩余”。这种“社会剩余”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分享之可谓“搭便车”,弃之将是“无谓的社会损耗”。
包容性发展还必须直面矛盾、分歧甚至冲突。在区域合作中,矛盾、分歧甚至冲突的存在都是在所难免的。因为各国有各国的利益、价值观和价值判断乃至政治倾向,但关键问题是如何化解、减少、弱化、解决上述问题。在这方面老庄哲学值得我们重温。道家所展示的是一种柔美的力量。柔美作为一种力量,具有超越刚毅的坚韧,高于勇敢的智慧和摆脱强大的征服力。“上善若水”的真谛在于“无为而无不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要旨在于“上兵伐谋”。我们可以用强大对抗强大,用暴力反击暴力,用武器消灭武器,但我们很难用强大、暴力、武器去消灭观念、智慧与境界。这,就是柔美的力量。有时,我们挫败不是由于缺少勇敢,而是因为只有勇敢;我们失误不是由于没有力量,而是因为只有力量;我们停滞不前不是由于没有坚守,而是因为只有坚守;我们输于他人不是由于没有努力,而是因为只有努力。智慧赋予柔美以力量,就像兵法赋予武器以智慧一样。我们敬仰古人不仅仅是由于对历史的敬重,更在于历史能给予我们无穷的滋养。
包容性发展的根本还是价值认同的培育与确立。“丝绸之路”自古以来就具有某些区域经济市场的初级特征,它既是一条贸易通道,也是一种原始的经济意义上的共同市场,通道只是维系这个事实存在的共同市场的交通体系,而价值认同则是未来更深、更广层次合作的这个共同市场的“交通”规则。对于一个多元文化的共同体,源于价值认同基础上的包容性发展,对其成员的福祉是十分重要的。这些非正式的内在制度元素,既能增强内在规则系统的日渐优化的演化能力,又有利于区域共同体正式制度的缔结。文化开放与包容是共同体应对外界变化的有益方式,它能使文化演化过程朝着化解冲突和降低交易成本的方向前行。
一带一路倡议绝不是一个短期工程,它将是足以改变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伟大行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最需要完成的任务是互信的确立。而国与国之间的互信,是可以通过文化与价值的包容、认同来实现的。文化与价值认同过程,不可能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简单趋同或否定,而应该是在彼此尊重中达到共赢的过程,是在包容发展中实现共同繁荣的过程,是在向人类先进文化学习中认知与文明共同提升的过程。应该说,没有什么比相互了解和情感建立更有利于国与国之间互信的确立。被区域共同体成员普遍认同并遵循的共同规则,也只能在这样的背景下才能成为资源和财富。
注:
①探讨经济增长中文化性制度的伟大先驱,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创造了“新教工作伦理”概念。他断言中国文化被过分锁定于它的“趋保守极”(pro-conservative pole),以至于不可能出现经济增长(Weber,1951)。而现在的学者们却在钦佩地谈论着“新儒家经济”,并将它们的成功归结于文化特性(参阅Kasper 1994b)。
②制度资本的概念是柯武刚、史漫飞基于对制度竞争的认识提出来的。他们认为:“制度能增强生产要素,如劳动——在满足人类需要上的效能。这种作用的方式类似于其他一些生产要素,如资本——资本使劳动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因此,我们可视共同体的制度为一种宝贵的生产性资产。我们可称其为‘制度资本’(institutional capital)。”(参阅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43-144)
[1]Sowell,T.,Conqest and Cuture:A world View[M].New York: Basic Books,1998
[2](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3](英)弗里徳里希·冯·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卷)[M].邓正来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52-78,152-190.
[4](英)爱德华·伯内特·泰勒.原始文化:神话、哲学、宗教、语言、艺术和习俗发展之研究(两卷)[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
[5]Thomas Fuller.Myanmar Backs Down,Suspending Dam Project[N].The New York Times,2011-9-30.
[6]David Steinberg and Hongwei Fan.Modern China-Myanmar Relations:Dilemmas of Mutual Dependence[M].Copenhagen: NIAS Press,2012.
[7]Su-Ann Oh and Philip Andrews-Speed.Chinese Invest-ment andMyanmar’sShiftingPoliticalLandscape[M].ISEAS Trends in Southeast Asia,Issue 2015,No.16.
【责任编辑:林莎】
The Institutional(Cultural)Constraints to
Implementation of“One Belt and One Road”Initiative
TAO Yi-tao
(Research Center of China’s Special Economic Zones,Shenzhen University,Shenzhen,Guangdong,518060)
Basically,the implementation of“One Belt and One Road”initiative is not only an economic issue for both China and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 but a non-pure economic issue in which culture outweighs capital and institution outweighs technology.In comparison to capital and technology,the constraints from institutions (cultures)are both the softest and the hardest.The so-called institutional(cultural)constraints refer to the barriers in mutual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rnal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caused by cultural elements such as different customs and values,and the impact of the internal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of different cultural traits upon the establishment of formal institu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in broader regions or within the community.The key to transcend the institutional(cultural)constraints is to establish an operable institution of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tolerance——a common cultural cognition system——on the basis of common prosperity. This should be the first strategy and consideration to ensure the implementation of“One Belt and One Road”initiative in both logical and real sense.
“One Belt and One Road”initiative;institutional-cultural constraints;inclusive development
125.5
A
1000-260X(2016)06-0019-06
2016-10-2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经济特区发展史(1978-2018)”(16ZDA003)
陶一桃,经济学博士,深圳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经济思想史、西方经济学、中外经济特区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