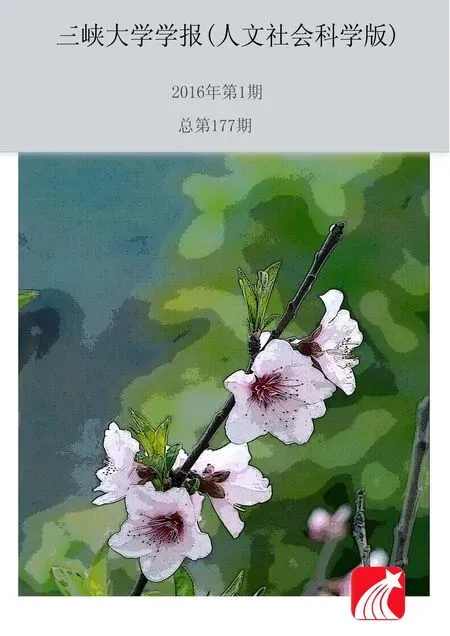当代中国村落民间故事讲述的基本特征——基于《都镇湾故事》的分析
王 丹
(中央民族大学 党委宣传部, 北京 100081)
当代中国村落民间故事讲述的基本特征——基于《都镇湾故事》的分析
王丹
(中央民族大学 党委宣传部, 北京100081)
摘要:都镇湾民间故事讲述现状成为中国村落社会中的重要文化表现,该村落的民间故事讲述呈现内容生活化、形态主干化、目的娱乐化、主体多样化等倾向,这些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当下中国村落民间故事讲述与传承的基本状态和特征。
关键词:《都镇湾故事》;民间故事讲述;民间故事特征
讲故事是中国民众重要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从目前我国政府命名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来看,涉及到民间故事保护的有11项,诸如湖北的伍家沟故事、下堡坪故事、都镇湾故事,重庆走马镇故事,河北耿村故事,西藏嘉黎故事等。对于这些民间故事的保护,均关涉到传承人讲述和民间故事流传的生态,它们主要依托的就是村落。民间故事村落具有讲述故事的历史传统和浓厚的社会风尚。伴随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民间故事的讲述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然而,民间故事讲述传统的淡化并不意味着这种传统就会消亡,讲故事仍是中华大地上许多村镇社区的生活内容与方式,但也呈现出新的特征与趋势。
一、从“都镇湾”到“都镇湾故事”
都镇湾是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的一个乡镇,位于长阳县的西南部,地处清江中下游。春秋时期,都镇湾属巴国之地。秦统一六国之后,隶黔中郡。汉唐置佷山县,属武陵郡。尔后,都镇湾又先后隶属于东汉南郡,三国、晋、刘宋的宜都郡,北周的亭州资田郡,隋代的巴山、盐水县,唐武德元年的长阳县。宋代属荆湖北路峡州,元代隶湖广行省峡州路,明代隶荆周府夷陵州。清初改属荆州,雍正六年又改属归州。自明代起,都镇湾属容美宣抚司管辖。
20世纪早期,贺龙率领红军第四军曾经三次到达都镇湾。1929年1月,中共长阳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都镇湾的庵坡召开。1929年10月,红四军在都镇湾十五溪的台子召开了军事会议。解放后,都镇湾一直设有区和人民公社级别的行政建制。1987年9月撤区建镇,都镇湾镇共辖5个办事处,44个村,353个村民小组,面积293.5平方公里,镇政府位于佷山。1989年4月,因清江隔河岩库区蓄水,都镇湾镇政府所在地从佷山迁到庄溪。2000年12月乡镇合并,都镇湾镇管辖9个办事处,70个村,206个村民小组,面积518.29平方公里。
从都镇湾的历史沿革来看,行政区划的改变主要是出于行政管理的需要,但它并未影响都镇湾文化传统区域的变化。在都镇湾的土地上,民间故事讲述氛围一直浓烈。都镇湾行政区划内的自然生态和政治生态影响着都镇湾人的故事讲述。都镇湾的“生态小生境”和传统知识体系孕育了都镇湾的文化类型和民间叙事资源的种类,而行政区划的每一次变化也为其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山的故事,水的神话,植物精怪信仰的表述和各类动物故事均源于都镇湾的自然环境,源于都镇湾人与自然的密切关系。”[1]
到了重视和保护民族民间文化的21世纪,“都镇湾故事”因其内容丰富,类型多样,旨趣各异,地方知识凸显,民族特色鲜明,于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都镇湾还被评为“宜昌市首批非物质文化保护之乡”和“长阳县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多重举措的落实为都镇湾故事的讲述、传承和创新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助力。
2014年出版的《都镇湾故事》一书一共采录、整理、刊出民间故事331则,并列出未收入书中的故事篇目249则,这些故事主要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传讲的故事,较为系统、全面地记录和呈现了当下都镇湾地区民间故事及其讲述面貌,它的面世是搜集、整理都镇湾故事,摸清、记录故事传承人现状,呈现中国村落社会中民间故事讲述基本状貌的典型案例,是不断充实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资源数据库的标志性成果之一。
二、故事讲述内容生活化
《都镇湾故事》按照广义民间故事的概念,分列出神话、传说和狭义的民间故事三大类。具有神圣叙事性质的神话仅有两篇——《神龙造天、造地、造人》和《洪水泡天》,分别讲述“天地形成、人类起源”和“洪水泡天、人类重生”的远古时期的事情。但从叙事的情节来看,生活气息浓郁。比如《神龙造天、造地、造人》中讲到“阳龙在天上游荡,常用双眼察看阴龙的活动,睁得又大又圆的那只眼睛就是太阳,半睁半闭的那只眼睛就是月亮”[2]2,神灵的举止行为颇具人的情态。《洪水泡天》开头便讲管束不住儿女的老婆婆病人,“儿女们问她想吃什么?老婆婆想请雷公老爷把那些横儿子制一下,就说:‘我想吃的东西,你们弄不来,听说世间只有雷公肉最好吃。’儿子们说:‘我们弄得来!’”[2]3这一情景就是民间普通百姓生活的写照。
《都镇湾故事》中的传说包括风物习俗传说和动植物传说两大类,故事包括地名故事、人物故事、嫁匠故事、幻想故事、生活故事、鬼狐精怪故事、笑话等类别。这些传说故事大多源于现实生活,即便带有神秘、神奇色彩的鬼狐精怪故事、嫁匠故事、风俗传说等,也褪去了些许诡秘与奇妙,更强调与民众实际生活的关联与互动。例如,与巫术密切相关的嫁匠故事一般讲述眼见耳闻的人、事、物,并不注重对嫁术的详尽描摹和解释,而是侧重对生活事实的描写和事件结果的陈述,增强了“故事生活”的真实性,制造了亦真亦幻的叙事美感。
老巴子(老虎)是土家族的图腾信仰物,在长期的传承和演化中,它早已进入都镇湾人的口头叙事中,形成多种类型的民间故事,象征着民族精神,标识着民族身份。《都镇湾故事》中的“老巴子精”“老巴子还情”“孕虎”和“老巴子报仇”等故事,均将神圣的信仰对象世俗化、人性化,它们善恶分明、知恩图报,极具人的性情,不再是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膜拜对象,而是就活跃在土家人的身边,与他们发生着亲密的关系。连土家人敬仰的“白虎星下凡”的向王天子都“屁股坐在羊角山顶上,脚能伸到清江河里,一双脚搅得河水哗哗啦啦,直打漩漩”[2]97,如同孩子般顽皮可爱,富有亲和力。
《都镇湾故事》中的故事是立足于都镇湾人的现实生活,一方面是都镇湾人对现实生活的记录,另一方面是对未来生活的期望。从这个角度上讲,《都镇湾故事》以讲故事的方式和都镇湾人特有的艺术想象建构了都镇湾人的生活世界。
三、故事讲述形态主干化
《都镇湾故事》一书中,短小精悍的故事占了很大比重,除了部分与历史有关的故事、带有幻想成分的故事以外,大部分故事的讲述篇幅不长,尤其是生活性强的故事。都镇湾人讲这些故事遵循该类型故事的基本结构框架,在叙事中情节推进极快,不作过多的描述和解释,重在说明事实,表述过程,在可以继续生长情节枝蔓的地方,在可以充分发挥想象的关节,并不“节外生枝”,多是按照事态的发展进程给予叙述,进而造就出故事精干明晰的特点。比如,“做好事延寿”[2]209讲到一个富人命中只有六十岁,他便出门游玩散心,途中他为人修桥、捐钱、解困,到了六十大寿时,他因做好事而躲过劫难,活了高寿。故事的讲述原本可以在许多情节上展开刻画和描写,如描述主人公的富有,但讲述人只用了“他有蛮大的家产”这样的短短数语来表达;主人公出游路上做的三件好事也可详尽的叙述和延展,不过讲述人却采取平铺直叙的手法,毫不“多费口舌”。又如,“勤俭”[2]203这则故事由五个情节单元构成:一户人家两个儿子,一个勤快,一个会持家;老人在的时候,两弟兄一个主外,一个主内,日子红红火火;老人去世,两弟兄相互指责,闹着分家;分开过的两弟兄很快败了家,结果发现“勤”与“俭”缺一不可;悔悟的两弟兄又一起过日子,发了家。讲述人的着重点是讲明勤俭的道理,因而对于故事情节的叙述并不强调事件过程的精细描述,只追求讲完故事的基本情节即可。整则“勤俭”故事的讲述仅用了328个字。这种故事讲述形态的主干化并非仅与讲述人个人的讲述风格相关,在《都镇湾故事》中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截取传统民间故事的某一片段或个别情节进行讲述,乃至夸大,是故事讲述形态主干化的极致表现,即碎片化。譬如,“孟姜女寻夫”[2]102故事开篇便从万喜良被征去修万里长城,孟姜女千里寻夫讲起,对传统经典的孟姜女故事前半部分的情节没有提及。“孟姜女寻夫”集中讲述孟姜女在长城滴血验亲以及与秦始皇斗争的情节。“甘罗赶考”[2]104是言简意赅,只讲他进京赶考,与考官对对子的情节,寥寥数语凸显他的机警聪慧。这类故事在都镇湾人那里并不鲜见,而且数量较多。这种主干化、碎片化的讲述倾向反映了当下都镇湾人对民间故事本身的认知和理解,以及他们在信息化时代对于叙事传统的选择性接受、传承与讲述。
四、故事讲述目的娱乐化
与其他许许多多中国大地上的村镇社区一样,都镇湾受到现代化浪潮的强烈冲击,都镇湾人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在思想意识领域,这必然影响着他们的民间故事讲述。在传统社会,民间口头叙事是都镇湾人接受教育、传播知识的重要渠道,如今这种功能逐渐削弱,人们更多地追求故事讲述的娱乐化。在《都镇湾故事》中,笑话一类就占有75篇,故事的主人公有丈夫与妻子、儿子与父亲、先生与学生、老板与顾客、县官与百姓、亲家、兄弟、书生、道士等,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关涉到日常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且讲述多描画细小之事与生活片段,如“喝酒”“吹灯”“写信”“学说话”“闹洞房”“信禁忌”等,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了都镇湾人讲述故事的类别取向。随着物质资料的丰富、交通条件的便利、文化水平的提高,都镇湾人能主动、有效地掌控自己的生活,对神灵鬼怪故事、奇异幻想故事、隐秘巫术故事等不再笃信不疑,讲述渐少,即使讲述,也常以轻松、幽默的口吻展开,他们更倾向于贴近真实生活的故事表述。
在快捷、单调和聚会时间相对减少的生活条件下,都镇湾人讲故事偏重于对故事整体的观照和故事核心的把握,愈加强调和寻求一份内心的愉悦与快感。所以,诙谐、调侃、幽默是诸多故事讲述的情感基调和叙事风格。比如,“三姨佬”系列故事是都镇湾人颇为钟爱的一类生活故事,它属于“三女婿”故事的范畴。都镇湾的“三姨佬”不但有“呆”、“傻”的特质,更具有自己的独特品格,这成为故事讲述喜剧效应的焦点。在当地,“姨佬”是一种他称,即出嫁的姊妹对彼此丈夫的称呼,因而故事中的人物角色是同辈的平等关系,故事讲述人又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和立场来叙述故事,因此,在都镇湾,不论是“三姨佬祝寿”的故事,还是“三姨佬纠葛”的故事,抑或“三姨妹助夫”的故事,其叙事重点都放在“赞四句”、比才华、嘲弄人的情节上,进而抖露笑料,令人捧腹。
五、故事讲述主体多样化
都镇湾不仅民间故事多,而且故事讲述人多。现今,都镇湾的民间故事讲述人显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格局,其中主要有两种结构性的状态:一是传统民间故事的讲述人逐渐减少,传统的讲述方式逐渐减少;二是以现代生活为中心来建构故事的讲述人依然众多,现代的讲述方式和传承方式依然旺盛。也就是说,在都镇湾,民间故事的讲述不仅包括传统的故事讲述人,而且包括具有当代生活特质的讲述人。2003年至2004年,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文化馆和都镇湾镇文化站联合调查走访了都镇湾十五溪村609户人家,2234人,登记能讲故事的有689人。初步统计,能够讲400则以上故事的有李国新、刘泽刚、刘维芬和彭绪贵四位老人,能够讲300个左右故事的有5人,有18人能讲200个左右的故事,现已搜集故事3000余则①。除了故事讲述人数量众多之外,都镇湾还有杰出的民间故事讲述家,他们是孙家香、李国新、刘泽刚、刘维芬等人,这些讲述家不仅故事讲述质量高,而且讲述的故事类型多,他们不仅在都镇湾享有较高的地位,而且在全国也是有影响的故事讲述家。“都镇湾故事”的国家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有2人、省级传承人4人、市级传承人6人。
《都镇湾故事》中收录了都镇湾主要的故事讲述人讲述的故事。从受教育程度来看,这些讲述人有的是文盲,有的只读过小学低年级,有人则读过高中,他们的文化层次有很大差异,讲故事的文采和风格自然迥然有别。从身份来源来看,都镇湾的故事讲述人有的是土生土长的都镇湾人,有的是从外地迁居而来的,也有的是在都镇湾工作的,不同的身份来源使得他们的故事讲述各有特点,这也从一个侧面展示出都镇湾故事的丰富性、包容性和适应性,以及本土化的表现。从年龄段来看,都镇湾的故事讲述人既有高龄健谈的“孙家香”们,也有富有生活经验的中青年人群,还有天真烂漫的少年儿童,不同年龄段的讲述人讲述的故事满足了不同年龄、不同层次人的需求。可以说,讲述人的多样性亦是当代都镇湾故事讲述的重要特征。
六、结语
《都镇湾故事》是当代都镇湾故事的集大成,是中国村落民间故事传统生存现状的缩影,尽管这个传统故事村落面临着当下社会的急剧变化和中国乡村的巨大变革。“讲述故事的口头文学活动急剧衰退,它所依存的社会文化生态已经残破,很难完全修复重建了。”[3]传统讲故事的环境发生了变化,尤其是讲述传统故事赖以生存的土壤不再如故,讲述传统故事就会越来越少。诚如德国哲学家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中断言:“千百年前在最古老的手工业生产氛围中编织起来的讲故事的艺术,到如今渐渐经散纬脱的原因就在这里。”[4]手工业是德国民间故事生存的土壤,对都镇湾来说,故事的生存土壤就是农村、农业和农民了。当代都镇湾的农民逐渐离开故土,农村空心化现象严重,因此,传统民间故事的讲述必然衰微。“曾经的生活方式为都镇湾故事创造了适宜的土壤,所以都镇湾故事得以世代流传。现在,这种土壤已经渐渐流失。”[5]但是,当我们从现代生活的立场和当今村落文化活动及其传播的视角出发便能发现,都镇湾人现实感强、生活气息浓、情节推进快、语言表达凝练的故事讲述,以及讲述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正鲜明而深刻地昭示了当代中国村落民间故事讲述的基本特征和存在方式,民间故事的转型和新生成为必然。多样化影视节目的引入,多样化传播媒体的介入,人员流动速度的加快,以及不同文化交流碰撞的频繁发生,促使人们对于故事讲述的诉求也更趋于生活化、信息化和娱乐化。只有正视这种趋势和倾向,才能更准确地理解当下民众对于民间故事的择取、传讲和创新,才能更真切地体悟故事讲述人及听众在口头叙事中享受的乐趣,才能将民间故事的保护和传承真正导向活跃着的生活世界。
参考文献:
①统计数据来自2006年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文化局申报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十五溪故事村”资料。
[1]林继富.民间叙事传统与村落文化共同体建构[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2:30.
[2]张颖辉,覃庆华.都镇湾故事[M].武汉:崇文书局,2014.
[3]刘守华.故事村与民间故事保护[J].民间文化论坛,2006(5).
[4]瓦尔特·本雅明.陈永国,马海良,编.本雅明文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299.
[5]谢国先.略论民间故事的文化生态——以都镇湾故事为例[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2).
[责任编辑:杨勇]

中图分类号:I 207.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219(2016)01-0050-04
作者简介:王丹,女,中央民族大学党委宣传部编辑,法学(人类学)博士,文学博士后。
基金项目:201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清江流域土家族‘打喜’仪式研究”(14FMZ004);“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与少数民族口头传统传承创新研究团队”(2015MDTD05A)。
收稿日期:2015-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