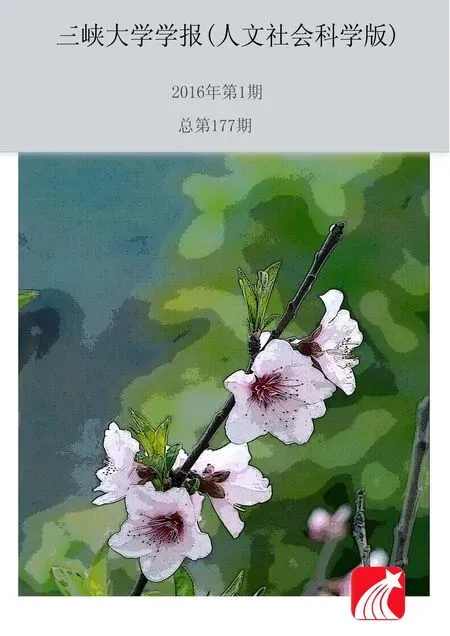论太宰治的自杀意识——以《维庸之妻》、《人间失格》、《维荣的妻子》为中心
孙 葳, 范静遐
(武汉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0)
论太宰治的自杀意识——以《维庸之妻》、《人间失格》、《维荣的妻子》为中心
孙葳, 范静遐
(武汉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北 武汉430070)
摘要:除了太宰治,再也没有哪个作家因为频繁自杀而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其实,在太宰治创作的很多文学作品中,也清晰地呈现着他对自我破坏与求死的倾向。本文以《维庸之妻》和《人间失格》为中心,借助电影《维荣的妻子》对太宰治的生平和文学思想的解读,探索太宰治的自杀意识和形成原因。
关键词:太宰治;亲身实践;文学作品;电影;自杀意识
奥野健男曾说:“太宰治只为自己写作的作品乃内在真实想法的自叙体。”①可以说,太宰治的每一部作品都或多或少融入了自身的经历和真实感受。尤其是在后期(1946-1948)作品中,太宰治把愈演愈烈的颓废、放任、自我毁灭、叛逆、信神等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是他生命的终结,却记录着他创作的巅峰。
《维庸之妻》和《人间失格》是太宰治后期的杰作,均采用自叙体。《人间失格》一直被认为是太宰治具有自传性质的小说;《维庸之妻》是以女性的身份自叙,讲述她颓废不羁、风流成性的丈夫大谷的故事。而电影《维荣的妻子》②在原著基础上增加和融入的“情死”情节大部分取自于太宰治的亲身经历③。
因此,本文将追溯太宰治生平,探索太宰治的自杀经历与真实原因;细读太宰治代表作《维庸之妻》和《人间失格》,寻觅太宰治作品中呈现的对人生与对死亡的态度;联系电影作品《维荣的妻子》中对“情死”主题的渲染,分析太宰治的自杀意识和其形成原因。
一、太宰治五次自杀经历
太宰治虽然只活了39岁,但是,他疏远于主流之外,以自虐与颓废抵抗社会的形象却是深刻而令人难忘的。
1909年6月19日,太宰治出生于津轻地区首屈一指的地主富豪之家,是家中幺子,上有五兄四姐。年幼时聪敏好学,成绩优秀,但生性敏感。
1923年3月,父亲去世。年仅14岁的太宰治转入青森县立青森中学就读,寄宿于远亲丰田家。中学期间,太宰治开始创作小说、戏剧和杂文,一度对泉镜花、芥川龙之介的文学作品相当倾倒。
1927年,就读弘前高等学校的太宰治听闻芥川龙之介去世的消息,倍受打击④。1928年10月,20岁的太宰治第一次自杀。或许是因为内心崇拜的作家芥川龙之介服药自尽,年轻的太宰治想追随偶像而去;亦或许是当时流行的无产阶级文学使他烦恼自身的阶级问题,太宰治选择和芥川同样的方式自尽。然而,由于吞服的安眠药剂量不到致死量的十分之一,太宰治活了下来。但这一次自杀,似乎开启了他后来频繁轻生的模式。
第二次自杀是在1930年11月。21岁的太宰治入读东京帝国大学法文系。他听不懂高水平的讲课,投身左翼运动,导致学业彻底荒废。在此期间,他接触了香烟、酒、陪酒女,并和认识仅三天的咖啡馆女侍者木津子同居,经常透支寄来的生活费。木津子本是有夫之妇,太宰治在生活的百般折磨下极度厌世。两人约定于镰仓七里滨海岸先服药,而后投水。这一次,太宰治吞服的安眠药依然未达到致死量而被救活过来,但年仅18岁的木津子却再也回不来了。太宰治因教唆自杀罪被法院起诉,但后来没有受到处分。
1935年,太宰治实施了第三次自杀。2月,太宰治的短篇《逆行》入围第一届“芥川奖”。太宰治万分渴望这个以偶像命名的奖项,也的确需要这笔奖金来偿还高额的医药费⑤。但担任评委之一的川端康成对《逆行》提出严厉批评,导致其落选。太宰治对川端康成恨之入骨,选择以自我破坏的方式泄愤——他奔上镰仓山,结绳上吊。但因为绳子脆弱崩断,他再次未能如愿。
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政治与生活多重矛盾压力下,太宰治再也不想在人间受折磨,于是要挟小山初代④一同去谷山温泉殉情。依然是服安眠药后投水,但两人都被救活了。返回东京后,两人因感情破裂而分手。
1939年,太宰治与石原美知子结婚,度过了较为安定的一段时期,写作上也取得累累硕果。1947年,太宰治与山崎富荣在一个乌龙面摊上相识,遂陷入爱河。1948年6月,太宰治和山崎富荣在雨中行走了200多米,最终双双跳入东京西郊的玉川上水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两人的腰部用红绳结绑,双手穿过彼此腋下,紧抱着对方的头……这是太宰治与世诀别的姿势。这次自杀的确切动机无人知晓。他在遗书中写到:“不要绝望,在此告辞!”这究竟是对生的鼓励,还是死的告别?至今也没有人读懂它的原意。
虽然,日本现代文人多有自戕之举,究其原因,除了文化之外,大多数的伤痕都是被历史生生割出来的。但是,毕竟没有谁像太宰治,因在短暂的39载生命里频繁自杀而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
在太宰治的遗体被找到的前一天,《朝日新闻》曾登载了一则题为《太宰治先生出走了吗?》的小新闻。而后,各大报刊跟风一般地大肆渲染太宰治的“情死”。可见,读不懂太宰治的人将其动辄轻生的态度仅仅归因于脆弱和绝望,或者是由于病态的心理所致[1]。
日本评论家平野谦曾说:“太宰的死,可说是这种历史的伤痕所造成的”。太宰治是大地主家庭的幺子,从小缺乏母亲关怀,生性敏感的他厌恶家庭却一生都在经济上难以脱离家庭支持。大学时代,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左翼运动,却眼睁睁地看着战前战后的变故摧毁了自己的生命信仰。作为战后崛起的作家,太宰治亲眼目睹了国家战败、战后左翼的妥协、国家被迫转型的全部过程。这些都促使他一步步走向更深刻的自我破坏和毁灭。
有评论家认为,太宰治把自杀作为展示自己叛逆精神的最好手段,以自虐的态度来抵抗战后日本的萧条和当代人精神与感官世界的双重萎靡[2-6]。而在笔者看来,对现实无力也无心调和,是他的懦弱;疏远于主流之外,以颓废抵抗社会,是他的叛逆。这是“无赖人”才能真正领会的无赖境地——无论身逢乱世还是太平年间,最大的兵荒马乱到底都是幻灭,鞭挞自己,甚至毁灭自己,得以改变自己的罪恶与自私;自我毁灭、自我否定就是对现有社会、现有道德的叛逆。理性思维与非理性行为拉锯自责,而太宰治本身在自我沉沦与放任自虐中跌入毁灭。然而,这种自暴自弃糅合出对自我存在的巨大怀疑,以及以彻底毁灭营造出辛辣绝望的不留余地的写作姿态,正是“无赖派”最显著的特征。
接下来,不妨细读太宰治晚期代表作《维庸之妻》和《人间失格》,并观看以其原著为基础改编的电影作品《维荣的妻子》,从中探寻:太宰治以自我破坏和自杀的方式来抵抗的普世价值到底是什么?
二、探索太宰治自我破坏的根源
1.太宰文学呈现出的生死观
奥野健男评价太宰治:“不断地毁灭自己,决不掩饰自己的不足之处,反而使之不断深化。这样一来,使得他叛逆于即成的社会、文学乃至一切的现实。”[5]
有评论解释说,太宰治的大多数小说中讲述的落魄主人公的颓废生活或毁灭之路都是对自我生活的反映,表现出一种懦弱的美学。
如其作品中所言,以“无知骄傲的无赖汉姿态活着,扮演白痴下等狡猾的好色男,伪装天才的欺诈师,过着奢华的生活,一缺钱就扬言自杀,惊吓乡下的亲人。像猫狗一样虐待贤淑的妻子,最后将她赶出。”[7]类似无赖汉的主人公形象正是太宰治的专利。然而,这仅仅是最初的颓废与邋遢,比这更可怕的莫过于求死。
“……自打我一出生我就总是考虑死的事情。就算是为了大家,我也是死了的好。”[8]171这是《维庸之妻》中颓废的男主人公大谷的自白。太宰治年轻时和大谷一样脆弱不堪、动辄受伤,“经常喝得烂醉如泥才回来……”[8]162他用酒精麻痹自己以消除恐惧,以放荡不羁的生活来填补内心的迷失和空虚。他认为活着总是在和恐惧搏斗,所以他一次又一次想要与恐怖的世界告别。那么,这世间令他恐惧的究竟是什么呢?
“其实,世界上被称为‘合法’的东西才更可怕。我不能死守在一个没有门窗的寒冷房间里,即便外面是一片不合法的大海,我也要纵身跳下去。哪怕是马上死去,我也心甘情愿。”[9]3
这个“合法”的东西正是让太宰治痛苦不堪的所谓“人”的世界,以及这世界中让他矛盾到精神分裂的“世间常态”。太宰治为何“怕人”?这还得从他童年的经历说起。
(1)“恐人症”与日后的人格崩盘。
《人间失格》中,主人公叶藏对“生活”和“人类”的恐惧感表现得尤为突出。这种恐惧伴随着叶藏也伴随着太宰治一生。
手记一描绘的阴森压抑的吃饭场面,“……吃午饭时,十几位家庭成员自顾自埋头吃饭,一言不发。这样的情形每每令我不寒而栗……我对开饭的时刻愈加恐惧。坐在那以南房间的末座,我不由得浑身战栗,木然地把米饭一小口一小口送到嘴边,勉强吞咽下去。”吃饭为何毛骨悚然?这显然来自太宰治的幼年体验[9]3。
在保守传统的大家族中,吃饭近乎一个机械的仪式。严谨刻板的家族氛围与父兄威严使天性敏感的叶藏对父权体制产生了强烈的抵触。然而这种抵触是大逆不道的,连他自己都无法接受。太宰治正如其笔下的主人公——既浸染着传统道德,但也恐惧刻板压抑的一切。自小弱不禁风的他不可能自立于外部由男性支配的世界,没有一个可以足够放心去亲近的人让童年时的太宰治像一个孩子发自内心地去赞美、欢笑、愤怒、哭泣……“恐人症”便从此开始。
于是,他故作愚蠢来取悦他人,在人们的笑声中寻求安全感。他没有自信,只能将独自一人的懊恼深藏在胸中的小盒子里,将精神上的忧郁和过敏密闭起来,伪装成天真无邪的乐天外表,使自己一步一步地彻底变成了一个滑稽逗笑的畸形人。
“欺骗”是现实给予叶藏本性第一次巨大冲击。在父亲的演讲会上,男佣们暗地里批评枯燥无味,一转身却为了讨好主人赞不绝口。目睹这一切,叶藏惊异于人类在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心口不一,但他也认同了这必是活下去的“妙谛”——阳奉阴违才是世间常态,而这绝非典籍中宣扬的仁义道德。所以“我对人类的恐怖仍在内心深处激烈的蠢动,且与以前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9]7。然而,并不是欺骗与堕落的行为让叶藏丧失为人资格,而是他没把这些行为认同为常态。
不认同,纠结,奔溃,直至成为完全脱离社会的精神病患者……皆因为价值观与社会常态激烈碰撞,彻底粉碎成末。主人公不禁向神灵发问:信赖也是一种罪吗?不抵抗也是一种罪吗?无限的绝望让太宰治从小便产生了自我认同上的矛盾分裂,成为日后人格崩盘的种子,以致于用自杀的方式来拷问这一直令他感到恐惧的“社会常态”。
(2)自我破坏意识和另类女性观的萌芽。
《人间失格》中的主人公叶藏是现实太宰治的演绎版——刚出生的太宰治没有喝过一滴母乳就被称病的母亲交给乳母喂养。母亲和大部分家庭的主妇不同,经常外出东京,担任众参议员父亲的贤内助,与尚在年幼时期的太宰治产生疏离,母子间的交流更是少之又少。因此,童年时期没有经过母亲的培育,没有学会与外界交流方法的太宰治产生自闭心理和“恐人症”是理所当然的。
不仅如此,母亲和祖母总是当着全家人的面悲叹太宰治相貌丑陋,这更加使得生性敏感的小太宰治背负了不必要的自卑意识和自我欠缺感。所以,他一直怀着如履薄冰的心情与女人打交道——“我对她们一无所知,如坠云雾,不时遭受惨痛的失败。这种失败与从男性那儿受到的鞭笞截然不同,恍若出血一般引人不快,其毒性攻心,难以治愈。”[9]7生在女人圈,却得不到母爱和其他女性的关爱,让他在对现实母爱的饥渴之中倍受煎熬。这反而使太宰治养成了敏感脆弱、动辄轻生的女性做派。
乳母走后,太宰治被交由姨妈抚养。当祖母和母亲感叹他丑陋时,只有姨妈会真正生气,反而夸太宰治是美男子。在太宰治心目中,姨妈是比亲生母亲更像母亲的存在。他曾一度怀疑自己是父亲与姨妈生下的“不义之子”。这种妄想或许是太宰治的自我破坏意识和另类女性观的萌芽,而这种意识一直持续到他成年之后。
2.电影渲染“情死”投射其女性观
剧作家田中阳造在编排电影《维荣的妻子》时,巧妙融入了原著中不曾含有的情节——殉情。很显然,该情节取材于现实中的太宰治。五次轻生,三次情死,每次都是红绳缠绕,紧紧相拥,世界上没有谁比太宰治更疯狂了。
剧作家这一天衣无缝的植入情节让观众一下子分不清戏里戏外——大谷就是太宰治,太宰治就是大谷。身出名门、才华横溢却放荡不羁;敏感、脆弱,如少年一般无所顾忌,引得几个女人为之倾倒,乃至和他殉情。但现实中的那些女人真的心甘情愿成为太宰治的轻生陪同者吗?在太宰治的意识中,她们是否包含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缺失母爱的太宰治一直在和其他女性交往时努力寻求着母爱。即便是与妓女交往,他依旧认为:“我没有一夜是为了享乐的,我是为了寻求母爱而去,是为了寻求母亲的乳房而去”[9]17。他“很快懂得了酒、烟、妓女都是可以消除‘恐人症’的灵丹妙药”[9]14。
太宰治和大谷一样是孤独的,所以很容易地因酒吧女招待员的一句“真寂寞啊”就产生了深深的共鸣,就连死都要和她纠缠在一起。女人虽然“时而如胶似漆,时而冷若冰霜……但与男人相比,女人更容易从滑稽的表演中体会到愉悦的感觉”[9]13,女人能够排遣内心的孤独和恐惧,哪怕是妓女,“我从她们身上体验到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亲和感,我常从妓女那里接受一种温馨的、自然的善意,那是一种没有利害打算的善意,一种毫不勉强的善意,一种对于萍水相逢的善意,我甚至在那些作为白痴或疯子的妓女那里,发现了玛利亚在现实世界漫漫黑夜中的神圣的光环”[9]17。
如果说太宰治的文学创作无传统伦理道德约束,也没有一般意义上的是非标准,那么现实生活中,他的风流放荡与对世俗的轻蔑反叛究竟是要给世人怎样的警醒?
从影片来看,女人的怀抱就是能慰藉“边缘人”恐惧的地方。大谷回来时烂醉如泥,脸色苍白,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一言不发地凝视着妻子,眼泪扑簌簌地落下来,他冷不丁地钻进妻子的被窝,紧紧地抱住,剧烈颤抖着说:“啊!不行啊!我好怕,好害怕啊!太恐怖了!快救救我!”可见,无论是哪个女人,无论在她身上发生过什么⑥,只要能让自己消除恐惧,大谷都会把她们妄想成自己的生母,扑向她们温柔的乳房。
然而,现实中的太宰治对女性的态度是复杂的。他可以趁妻子返乡时,与刚刚认识不久的咖啡馆女侍者同居,但却因为妻子与人通奸而遭受致命打击,从而胁迫妻子殉情。
太宰治的作品中少不了女性,她们都是能带来温暖,消除恐惧,忍辱负重的圣母形象,能和他一起殉情,逃离可怕世界的真正同伴;太宰治的生活少不了女人,她们是消除恐惧的怀抱,拯救失落灵魂的圣母,难以捉摸却易于取悦,善于背叛却令人欲罢不能的温柔窝。太宰治短暂的一生中,有关情死的自杀多达三次,而每一次,都是以紧紧相拥的姿势,或者用绳子绑在一起,以寻求对女性永恒的依赖。
三、结语
太宰治就如同一个混迹于成人世界的孩子,他依赖女人,选择自我破坏。自虐式的叛逆意向促使他一次又一次地自杀;孤独和恐惧让他选择殉情。太宰治因无力反抗阳奉阴违的社会从而厌倦自我,以不作为的颓废堕落来抵制普世价值。
自杀的确是为了求死,但太宰治的每一次自杀其实都是因为求生的破灭。或许真如太宰治所言:“女人无所谓幸福不幸福”,活着就行,而“男人只有不幸”[8]171。他深知时代需要破坏旧的秩序,重构新的未知;但他也纠结于自身的无能——无法理解人性的复杂与卑劣即是失败,向社会提出了种种质问却得不到解答即是愤懑。于是,他用鞭挞自己、破坏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对现有社会、现有道德的叛逆。也许,这种反省与行为的脱离就是对其遗言“不要绝望,在此告辞”的最好注解吧。
川端康成说:“死亡是最高的艺术。”那么,太宰治一生的颓废与自我毁灭就是创作的源泉,一次次的自杀,一次次寻找母爱的温暖都是杰出的行为艺术。
注释:
①奥野健男(1926-1997)是日本评论家,他解读太宰治作品《人间失格》时有此评论。奥野健男致力于解读太宰治的作品,他曾说:“以文学来说,坂口安吾为父,太宰治为母”。
②日本著名剧作家田中阳造以太宰治后期作品《维庸之妻》为蓝本,融入《回忆》、《樱桃》、《人间失格》等太宰治其他作品精髓,耗时五年,创作出《维荣的妻子》的电影剧本。田中阳造(1939-):日本编剧。其剧本《维荣的妻子:红樱桃与蒲公英》获第33届日本学院奖,本人获得最佳编剧提名奖。
③田中阳造指出:“男主人公大谷无论性格还是生活态度都与太宰本人极为相似,可以视为太宰的人生缩影。”
④小山初代是青森市滨町“玉屋”的艺妓红子,太宰治正在读高中时(1927年)和她(小山初代)相识。当地有土豪要为小山初代赎身,太宰治气急之下带着小山初代来到东京。家族听闻此事,觉得颜面扫地,提出:“和艺妓结婚,必分家除籍!”太宰治答应了。1928年,哥哥带小山初代回去办理相关手续期间,太宰治一个人留在东京,内心复杂难言,于是发生了和咖啡馆女侍者木津子同居并殉情的事情。1931年,太宰治回到家乡青森县,与初恋小山初代同居。然而同居期间,太宰治发现纯洁的女友竟然和别的男人有染,他的精神几近崩溃。从此,太宰治更加沉迷于酗酒和文学创作。
⑤由于过度饮酒、抽烟,太宰治患有严重的盲肠炎。为了止痛,他经常过度服用镇痛药,因而染上了毒瘾。在备受药物反应折磨的同时,也欠下一大笔医疗费。
⑥电影《维荣的妻子》保留了原著《维庸之妻》中妻子遭人强奸的情节。
参考文献:
[1]王健宜,吴燕,刘伟.日本近代文学史[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
[2]胡永红.追寻失落的精神家园:丧失为人的资格的主题探寻[J].世界文学评论,2006(1).
[3]陈希我.太宰治的“生”“罪”“死”[J].域外文苑,2010(10).
[4]陈潮涯.读太宰治的人间失格[J].文学教育,2010(8).
[5]谢卫平,解惠杰.一个自杀者的生存渴望[J].语文学刊,2010(12).
[6]于金凤.躲在角落里的生命真实:透过成长背景及作品对太宰治的性格研究[J].外语论坛,2009(13).
[7]太宰治.东京八景[M].东京:亚洲图书有限公司,2010:56-57.
[8]魏大海,侯为,邵成亮,译.维庸之妻[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171.
[9]太宰治.人间失格[M].东京:亚洲图书有限公司,2010。
[责任编辑:赵秀丽]

中图分类号:I 1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219(2016)01-0111-04
作者简介:范静遐,女,武汉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孙葳,武汉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5-0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