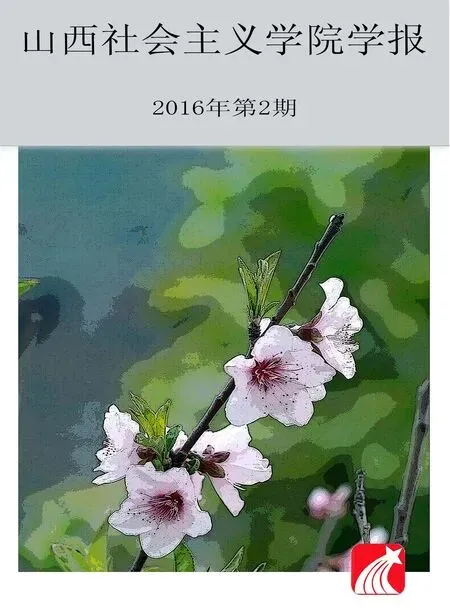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原因分析
李宽宽(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5)
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原因分析
李宽宽
(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875)
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与地方实力派建立统战关系的典型,也是各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国民党内部集团之间的冲突、群众运动、阎锡山本人的守土观念和爱国情怀等原因,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阎锡山最终选择中国共产党作为自己的合作伙伴,促进了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形成。
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
作为一个老牌反共专家,阎锡山却最早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区域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时正处于历史“夹缝”中的阎锡山面临生死存亡的抉择,在与日、蒋矛盾不断激化、中国共产党不断争取合作的情况下,阎锡山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作为自己的合作伙伴。
一、阎锡山浓重的守土观念和一定的爱国情怀奠定统一战线的主观基础
在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过程中,阎锡山的守土观念和爱国情怀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青年时期的阎锡山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在清政府全额资助其赴日求学且再三训诫他们严禁接触革命党人、参加革命活动的情况下,身处革命大熔炉中的阎锡山还是积极加入了孙中山建立的同盟会,并成为其核心组织“铁血丈夫团”的一员;1906年夏天,阎锡山冒着生命危险,利用回国机会为革命军带回了两颗炸弹;回到家乡后,阎锡山根据同盟会总部的指示,秘密考察实地情况,相机宣传革命,并于辛亥革命后在山西举起义旗,加速了清王朝的瓦解;阎锡山于1907年春向联队申请退学回国参加广东钦州三那地区民众发起的抗捐抗税运动,由于联队没有批准以及运动过早失败才没有成行……从他的这些举动中,可以看出他对革命的热衷。即使在后来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表,与其交好的日本帝国主义也一直努力制造阎锡山出面担当“华北自治运动”头面人物的形象,妄想借助其强大的军政实力、个人影响力以及与蒋介石之间的深刻矛盾来分裂中国、侵略中国的时候,阎锡山还是积极修筑防御工事,发表抗日演说以唤醒民众共同抵御日本的侵略。作为深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的割据军阀,阎锡山有浓重的守土观念,他想把山西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而非做日本的“儿皇帝”,他对蒋介石蚕食山西表现出极大的抵制性,对日本高官的叛国降日拉拢也予以婉拒。因此说,阎锡山的守土观念和爱国情怀为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提供了主观基础。
二、阎锡山集团面临的外部压力形成合作推力
1936年11月,阎锡山同意了薄一波提出的“约法三章”,标志着阎锡山与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合作正式形成。阎锡山的“爽快”与他所面临的险恶生存环境密不可分,日本的侵略、蒋介石的蚕食、群众运动的发展等外部原因为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提供了巨大的推力。
(一)日本占领山西的企图给阎锡山集团造成的危机感
对东北的控制基本巩固后,贪心不足的日本开始采取侵占华北的实际行动,继《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签订后,日本又策划了旨在控制整个华北地区的“华北五省(冀、鲁、晋、绥、察)自治运动”,并一直寄希望于阎锡山担当头面人物。对于控制山西、直辖绥远且以察哈尔作为重点发展区域的阎锡山集团而言,日本的这一举动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在加紧政治攻势的同时,日本又倚仗垄断资本和军事力量,逐渐控制了华北交通、金融、贸易和工商业的大部分,并利用猖獗的武装走私把日本廉价商品带到华北地区倾销,这对阎锡山刚刚建立的山西近代工业造成了致命打击。日本对察哈尔、绥远和蒙古的侵略也导致二者关系的恶化。1935年1月,日军直接出兵侵入察哈尔;1936年初,日本策划蒙古从中国分离,并支持建立了伪“蒙古军总司令部”、伪“蒙古军政府”和“西北蒙汉防共自卫军”等伪军政府和军队;1936年4月至5月,日军甚至唆使蒙古和察哈尔的日伪军进攻绥远……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日军的战略包围和军事进攻使阎锡山本能地产生了怀疑和警惕心理,本来甜蜜融洽的阎日关系变得空前紧张起来。
经济侵略和间接的军事威胁导致阎日关系紧张并不断恶化,日本直接侵占山西的企图触犯了阎锡山的禁忌,使二者彻底决裂。日本在1935年9月提出的“侵略华北之计划”中明确提出要大力开发山西的煤炭等资源。1936年1月,日本特务机关进驻太原、大同,加紧刺探山西经济和国防情报——日本准备侵略山西的战略布置已十分明显,其华北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甚至公开声称要“迫使山西阎锡山、绥远傅作义势力退到汾河以南”[1]256。在日军威胁到山西和阎锡山自身“存在”的情况下,一贯信奉“需要就是合法,存在就是真理”的阎锡山开始思考新的对策。
(二)“我不亡于共,也要亡于蒋”的哀叹
迫于红军东征的压力,阎锡山暂时违反自己坚持的“山西事山西办”的原则,急电蒋介石求援,至4月上旬,入晋作战的中央军已达12万之众。但是,在红军顾全大局主动回师陕北后,蒋介石并不打算撤回安插于山西的中央军,反而通过发展党组织、拉拢晋系军官、策动“河东道独立”等方式扩大中央在晋势力,其吞晋意图十分明显,正如中央军的一个士兵所说,“我们不是来和红军战斗的,我们来是为了赶出老阎”[1]262。蒋介石要求阎锡山从晋军中挑选15个团的兵力,附以骑兵、炮兵各一个团赴陕围剿红军,指定阎锡山集团中亲蒋的李生达作为总指挥,并以中央军监视其后,险恶用心不言自明。另一方面,二人的对日政策逐渐发生分歧。阎锡山认为,相比于共产党,日本对山西的侵略是直接的、致命的,他的当务之急是解决日本问题;蒋介石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不但不支持阎锡山对日作战,反而一再催促晋军赴陕剿共。前有丧地失家的东北军客居陕甘的沉痛教训,阎锡山绝不甘心成为“张学良第二”,要保住军队和地盘的阎锡山与对日妥协的蒋介石之间发生了尖锐冲突。正是在红军东征危机已经解除、蒋阎矛盾再度激化的情况下,阎锡山发出“我不亡于共,也要亡于蒋”[2]的哀叹。
(三)全国民众运动给阎锡山集团造成的恐惧感
“九一八”之后,东三省惨遭日本铁蹄蹂躏。1935年后,日本策划了华北事件,亡国灭种的危机不断加深,抗日救亡逐渐成为全中国普通民众的共同呼声。当日本要求南京政府成立所谓“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实现华北特殊化的时候,痛感“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北平学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一二·九”爱国运动。北平学生的行动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响应,天津、上海、南京、武汉、广州、开封、太原、重庆等城市的爱国学生通过请愿集会、示威游行、宣言、通电等形式声援北平学生;陕甘苏区学生联合会、苏区各界民众也集会声援各地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广州铁路工人、上海邮务、铁路工人举行集会,要求对日宣战;鲁迅、宋庆龄等知名爱国人士赞扬学生的英勇奋斗精神,捐款支持学生抗日救国运动;海外华侨也以各种方式支援爱国学生……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活动,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不得不延期成立。
“一二·九”运动中展示出来的群众力量使阎锡山不寒而栗,尤其令阎锡山感到压力的是,红军东征过程中广为宣传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红军的标语、减租减息的法令以及土地革命的实际行动已经在山西民众甚至是他的统治集团内部产生了深刻影响。虽然阎锡山通过“政治防共”、“思想防共”以及残酷屠杀等手段暂时维持了对山西民众的统治,但他十分清楚,共产党播撒的星星之火一旦燃烧起来,对自己而言就是灭顶之灾。在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情况下,阻止红军东渡黄河赴冀抗日的不明智之举使他成为蒋介石一样的“众矢之的”,为了不被群众运动的洪流所淹没,阎锡山开始考虑顺应时代潮流,联共抗日就成为他的重要选择。
三、共产党的不懈努力最终促成统一战线
外部矛盾激化固然推动了阎共合作的建立,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为了促进合作所作出的不懈努力。通过红军东征以及各种途径的劝说,中共中央使阎锡山认识到中共抗日的诚意,也向他展示了合作抗日必然胜利的光明前景。出于民族大义和自身利益的考虑,阎锡山最终同意了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一)红军东征展示的巨大力量
红军东征前,阎锡山曾两度派兵入陕围剿红军,非但没有达到“剿共”的目的,反而损兵折将。后来他转攻为守,沿黄河天险广筑碉堡,并在与陕北毗邻的晋西地区布置重兵,企图将红军挡在黄河以西。但是阎锡山的如意算盘落空了,1936年2月20日夜,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以摧枯拉朽之势突破了他苦心经营的千里河防,红军主力部队随后进入山西境内并实行战略展开。面对红军的凌厉攻势,慌了手脚的阎锡山紧急调整晋军部署,欲在中央军的配合下与红军主力决战。双方相持不下,红军出于“无论哪方牺牲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3]246的考虑,于4月底5月初主动陆续撤回陕北。红军东征虽然没有实现北上抗日的最初目标,但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消灭阎锡山军队约1.3万人;实行土地革命,使山西民众切身体会和了解了中共的政策;红军的工作队、宣传队通过标语、布告、群众大会等形式宣传了停战抗日、合作救国的主张,扩大了统一战线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中共的宣传使许多晋军士兵认识到国共内战属于同室操戈,获利者只能是日本帝国主义……除此之外,红军东征取得的巨大成就也使阎锡山陷入深深的困惑之中:红军在缺衣少食、枪炮落后的情况下,是如何仅凭共产主义的支撑走到今天的?经过苦苦思索,阎锡山逐渐认识到共产党代表了中国乃至世界潮流的发展方向,对于处在求“存在”十字路口的阎锡山而言,借助共产党来维持各方势力的平衡,甚至借此复兴山西并恢复自己绝对统治地位亦不失为正确选择。作为在矛盾中求存在的“专家”,阎锡山不再把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当作绝对的敌人了,这就为双方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二)共产党团结阎锡山集团的不懈努力
华北事变带来的民族危机促使国内各阶级和各利益团体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共中央适时调整政策,准备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以争取部分地方实力派建立区域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通过综合考量,中共中央决定把阎锡山作为突破口并迅速展开争取工作。早在红军东征之前,中共中央就向山西当局指出:幻想在不反蒋、不抗日的情况下摆脱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以及蒋介石的蚕食只能是一种空想,开展反蒋抗日运动才是山西的唯一出路。红军在东征过程中,分别于3月10日和4月5日发布布告——一切爱国志士,革命仁人,不分新旧、派别、出身,凡属同情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者,本军均愿与之联合,共同进行民族革命之伟大事业[4]101。一方面,再度向阎锡山表明自己的政策,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唤醒山西军民的抗日意识推动阎锡山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红军回师陕北后,毛泽东又托被红军释放的晋绥军第66师第392团团长郭登瀛带给阎锡山一封信,继续申述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心,向阎锡山表明中共愿与之建立统一战线的诚意——先生如能与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5]34。
除此之外,中国共产党还利用各种机会展开对阎锡山的统战工作。早在1932年2月,中共中央便邀请“中国民族革命大同盟华北联盟”主席朱蕴山通过老同盟会员的关系疏通阎锡山;5月,朱蕴山再次赴晋晤阎并谈到“反蒋抗日”之事;1932年底绥东抗战之后,朱蕴山应阎邀请第三次抵晋,并按照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向阎指出:当前情况下,只有联共抗日才是山西的唯一出路。1936年4月29日,已经与中共秘密达成西北抗日联盟的张学良抵达太原,张学良在秘密会谈中向阎锡山详细介绍了自己4月初与周恩来在延安的会面情况以及双方达成的互不侵犯协议,说明了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及红军东征的本意;5月27日,张学良又偕杨虎城赴太原会晤阎锡山,表明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决心,并积极建议阎锡山与共产党联络。为了尽快促成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还致函韩复榘、傅作义、宋哲元、赵戴文等阎锡山集团和其他地方实力派的重要人物,通过他们的劝说影响和争取阎锡山。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审时度势的阎锡山最终选择中国共产党为合作伙伴。
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敌我内外等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最终形成,作为形成时间最早、合作时间最长、战果最为丰硕的区域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它的形成和发展为山西、华北乃至全国的抗战起到了示范和鼓舞作用,也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和战斗经验。
[1]中共中央党校阎锡山评传编写组.阎锡山评传[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2]罗晓红.阎锡山缘何接收中共“约法三章”[J].党史文苑,2010(4).
[3]雒春普.阎锡山传[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
[4]苏飞.阎锡山[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
[5]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1984:1.
(责任编辑赵晓旷)
D613
A
1008-9012(2016)02-0052-04
2016-04-05 作者简介:李宽宽(1992—),男,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