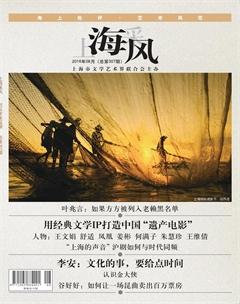徐庆华:心自由了,手就自由了
丁黎
历经遥远而漫长的路途来到松江,光地铁就坐了一个半小时,但一切的车劳马顿都止于推开徐庆华工作室的那两扇朱红大门——是的,就是那种装饰着“浮沤钉”的朱红宫门,配合着外围别有洞天的一整座庭院荷塘小桥流水锦鲤鹩哥,实在让人有种游园惊梦的不真实感:事实上一分钟前我从车里下来的时候看到的还是一处略破败的厂房门面,但一门之隔,却仿佛进入了另一个空间——而艺术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艺术,正是这样一扇隐秘却通向伟大的门,有的人终其一生都没能触碰到它,而有的人推开了它,就得到了另一个世界。
徐庆华显然是找到并推开了属于自己的艺术之门,在他那个朱门之内,老厂房改造的工作室裸露着水泥墙壁和屋顶房梁,显得粗犷而空旷,却又丰盛异常:因为两层楼的空间里堆满了他的书法、篆刻、油画、陶瓷作品,它们形式多样,却拥有同一根纤细的灵魂——那是一根属于徐庆华的“自由的线条”。还有主人网罗自世界各地的工艺品:半人高的非洲木雕,抽象而传神的铸铁鳄鱼母子,还有各式各样的小青蛙,瓷的铁的木头的珐琅的……“所以,你特别喜欢青蛙?”讲真这个有点出乎我的预料,因为眼前的这位留着寸发和艺术家小胡子的大学教授刚刚以一枚巨型印章和一幅巨幅草书成为上海交大120年盛大校庆上的焦点人物,艺术风格显然与这些可爱的小青蛙们格格不入。“啊,是啊,我很喜欢青蛙的神态,很放松,很自在,”没想到徐庆华笑眯眯地点头应了,“而且,我的名字,庆华,上海话念起来也和青蛙很像嘛,对不对?”
竟无言以对。于是我们的话题就被手动调回交大校庆的“一印一书”了。
一印一书,成就“最人文的交大校庆”
就在今年,走过三个世纪的上海交通大学迎来了建校120周年。在一连串声势浩大的庆典活动中,堪称压轴大戏的莫过于纪念大会上,全国五所交大的校领导共同在隶书长卷《交通大学赋》上钤盖“交通大学印”——用古雅的篆刻与书法向百廿岁学府传统致敬,这个仪式感十足又充满人文气质的形式深受师生和校友们的赞许,甚至有人开玩笑说,就因为这个,再也不说交大“只有技术,没有文化”了。而值得一提的是,这幅8米的隶书长卷《交通大学赋》,和这方古朴庄严的“交通大学印”,全都出自徐庆华之手。
“与其说这是交大交给我的一项任务,不如说是我的荣幸,能为学校这么重要的校庆活动贡献我自身的一些专业力量。”虽然被委以重任,但提起这件事情,徐庆华却谦逊地表示,能够以这样的方式成为“交大历史”的一部分,自己实在与有荣焉。事实上,徐庆华在交大从事艺术教育25年,不仅在自己的课堂上让数以万计的学子感受到了书法篆刻艺术的熏陶,他的作品更是多次被刻在校园景观石上、印在校徽里、当作珍贵礼品赠送给海内外友人。作为当今上海中青年书法篆刻界的领军人物,徐庆华当之无愧是为校庆刻制印章、书写长卷的最佳人选。
然而,说起这枚在校庆仪式上成为全场焦点的“交通大学印”,徐庆华半开玩笑地表示,为了这份人前的完美,自己在背后可是一路“见招拆招”费尽了心思。原来,最早版本的“交通大学印”是学校在1949年至1957年使用的印鉴,印面纵5厘米,横5厘米,边沿厚重,印文为老宋体,五字呈二三布局,其中“交通”较另三字略大。然而时隔半个多世纪,几经颠沛流离,原印早已无可寻觅,只有印花可供参考。而传留下来的印花亦是斑驳模糊,但这份“第二手资料”却是徐庆华刻制印章的唯一凭据——并且他还要在此基础上,把印文内容由5cm×5cm放大到18cm×18cm,刻到一方30多斤重的巨型青田石上。而这时候距离校庆的仪式,几乎只剩下一周的时间。
时间紧,任务重,但徐庆华决定要为校庆交出一份完美答卷。他先将印花打印在纸上,大小与石面相当,用毛笔把整方印重新描绘了一遍——从一方不太大的印章到巨印,放大后那些不起眼的设计缺陷也会暴露出来——因此这样的描字不是机械的复制,而是再创作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徐庆华基于对楷书印的理解,不仅把残损的笔画补全,还对文字布局加以调整,“大”字缩小,“学”字上移,所有横画加粗,使结构更加丰满稳妥,符合老宋体的审美要求。同时在印章细节上加以变通,如“学”底部的弯钩原本是平的,他重新设计后成为突变的转折。又如“交”、“通”、“大”右下角捺画的收尾处,他一改原印的混沌势态,使之折角分明。如此一来,新版的“交通大学印”既保留了原先印章的框架布局,又在文字细部融入新的创变,为后续的刻制打下了严谨而美观的底稿。
“那时候适逢清明三天假期,我一个人在工作室里几乎不眠不休地工作了三天,中途碰到各种问题,甚至凌晨把助手叫来调整方案,整个人都沉醉其中倒也忘了疲倦,最终总算不辱使命。”徐庆华寥寥数语说得不胜轻松,但过程的艰难其实不言而喻——虽然篆刻于他早已技熟于胸,但以往他大多刻的是10cm以内的作品,如此大到18cm的体量,对于他也是全新的尝试更是挑战。别的不说,单是这方30多斤的青田巨石,就已经移动不易,更何况它的顶上还是狮钮,形状不规则,普通印床根本无法夹持。“我尝试了各种方法去固定它——既要把这么个大家伙反着放平,又要确保整个篆刻的过程中纹丝不动,最后终于找到一个口径相当的古董花盆,将其中垫满泡沫,再用我的围巾把整个印身层层包裹起来,将它倒插进花盆,终于解决了第一步安置的问题。”但徐庆华因此就必须全程站立着刻印了,而且两个手都得用上,以防止刀口偏离方向。这既是技术活,更是体力活,三天下来,徐庆华的右手虎口被磨得一片通红,甚至起了血泡。
找到了印石的固定方法只是第一步。随后,徐庆华用一张透明的蜡纸坯蒙在底稿上,以双勾填墨法重新描绘印面,待复写纸干透后,再将有墨迹的一面覆在青田石上,用毛笔蘸清水涂匀,盖上宣纸轻压吸水,之后更换宣纸,用指甲刮压一次。接下来分别揭去宣纸和蜡纸坯,反相的印稿便呈现在石面上了。徐庆华又拿起毛笔,描画边框和个别笔画,对长短走势进行微调。待石面干透,就拿起钨钢刀开始刻制了。这刻的方式也有讲究。徐庆华平时长于雄放一路印风,刻印基本直接在印面写稿,大刀阔斧,干净利落,不喜复刀修琢。但这次他根据长久积累的经验,使用了二次成型法,力求万无一失。所谓“二次成型法”,即第一遍刻下去时,刀痕不是紧贴线条,而是保持约摸一毫米距离,刻出文字的大致轮廓——这一毫米起到缓冲保护作用,在突然滑刀、石质有裂、爆起石屑等特殊情况下不至于伤害线条;等铲完印底之后,再开始刻剩余的一毫米,露出线条的最后边界,充分体现线条的力度和质感。“在刻制这预留的一毫米时,有时候比直接贴线刻来得更加劲爽顺畅,”虽然过程艰难,但徐庆华显然很享受其中的挑战与乐趣:“在线条的交叉处,我又选择了完全不用焊接点的方式,宁肯刻得过一点,使文字更显力道和金石韵味。”
最终,徐庆华以娴熟的技巧、强健的体力和对艺术的虔敬,历时三天完成了“交通大学印”,最后一天的凌晨时分还在盖印调整效果,力求完美呈现。最后钤盖出来的印花大气庄重,炯炯有神,古意和新韵并存。细部处理匠心独运,用刀果敢大胆,让公章具备了艺术的表现力,更加富于纪念意义。如今,这方印章和徐庆华的书法作品《交通大学赋》一起被校方收藏,将在未来的校史博物馆中展示,成为交大历史发展的重要见证。“能以这样的形式在交大的历史上留下一笔,这对我意义重大。”对此,徐庆华如是说。
从草书到水墨抽象画,一根线条也有自由的魂
走进徐庆华的工作室里,从桌上到地上都堆满了各种笔、墨、字、画,不仅有如狂草般的写意水墨作品,亦有无序线条组合的抽象油画作品;不单是壁画和浮雕,甚至玻璃、陶瓷都可成为徐庆华书法艺术的载体。而站在这些繁杂而丰富的作品之中的徐庆华,也因此一直以来都难以被界定身份——篆刻家?书法家?陶瓷家?雕塑家?还是抽象画家?而其实他自己倒是对自己的艺术轨迹看得最清晰不过:“我最初师从韩天衡先生学习篆刻,楷书、篆书我都写过,然后草书写小草,后来发现能够吻合我心境的是大草,再后来到狂草,到现在逐渐消解可读性,朝抽象画发展。”
“我从小就对一切书画的东西都好奇,你可以说这是天分,但我更愿意说这是一种缘份——因为当时的我从未把那些当做艺术,只是觉得这些东西很好玩,很对我的脾性。”多年以后,已经成为上海市书协副主席的徐庆华回忆往昔,觉得自己在书法艺术上所走的这一条特别的轨迹,原来自小就初现端倪。小孩子大多爱看小人书连环画,但幼年的徐庆华只要有机会拿到这类书籍,阅完之后却总要照样子临摹书上的画面。当时条件有限,这一类书也不是时时能见,其中名作更少,很长一段时间里,年幼的他只能在艺术之门前徘徊。但也许天意如此,一次偶然的机会,少年徐庆华看到了韩天衡先生的印。“我当时看到韩先生的刻印,一下就迷上了。”徐庆华这样描述当时的心情。徐庆华为了观摩韩天衡先生的刻印,几乎走遍了上海的各大美术馆。“刘海粟、李可染、谢稚柳、程十发、黄胄、陆俨少等国画大师的画作上均有韩天衡先生的刻印,但他们的画作毕竟不是当时的我能随心看到的,于是我突发奇想,既然在美术馆里看不到太多的原作,不如买些画册回家品读?”这个灵机一动的想法让徐庆华获得了更多的资源。他几乎收集齐了当时能看到的所有钤有韩先生篆刻的画册,心追手摹,摹刻几可乱真。1983年,上海举办文革后“全国首届篆刻评比”,自学成才的徐庆华获得了优秀奖,那年他刚满19岁。次年,韩天衡便将他收入了门下。
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本就灵气逼人的徐庆华在韩天衡的悉心指导下技艺突飞猛进,深得韩式精髓,在书印领域大有盛名,以至于有坊间传说在“全国第二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家作品展”中,徐庆华以乱真的刀刻之法参赛,但被个别评委质疑韩师代刀而降格评为二等奖。但年轻的徐庆华并不满足这些成绩,1987年,他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了浙江美术学院国画系,对中国古代大家名帖进行系统深入的学习和研究。在这座堪称中国近现代书画重镇的学府中,徐庆华入古而出新,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博采众长,一步步拾级而上直到读出博士学位。提起这一段求学经历,徐庆华最不能忘记的就是王冬龄、陈振濂等当代书法名家独特而宽容的教学方式——这也许正是他如今淡泊名利却走上书法教育领域的心路历程之一。“王冬龄老师在我们上大一的时候,规定我们学习魏碑和唐碑各一种,为我们日后的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谓终身受益。还有他开放的教学理念和创作实践,深刻地影响了现代书法的进程和我的艺术道路,我有今天这样的艺术状态,与导师的引领和鼓励密不可分。另外,我记得上大三的时候,陈振濂老师为我们上现代书法课,要我们在课堂上完成一件现代书法作品并作说明,但当时我对现代书法毫无感觉,看其他同学都创作得十分投入,而我却无动于衷,最后就交了白卷。但陈老师并没有为此责怪于我,他看了我的说明后表示肯定。因为我觉得,对于艺术,如果没有真感觉,还不如不做。我以为对于艺术创作,真诚是第一位的。”看来,外表宁静儒雅的徐庆华,内心里却自有一番特立独行的锐气,而这正是他之后在书法领域破茧而出,开辟“水墨抽象画”之新天地的精神内核吧。
在科班的专业训练下,徐庆华掌握了楷书、隶书、篆书、行书等不同书体的要领,创作了不少作品,但他最喜欢的还数草书。“在所有的书体中,我最偏爱草书,而在草书中,我尤钟情于狂草。狂放不羁的线条,大起大落的节奏,摄人心魄的气势及变幻莫测的空间,观之常令人有一种莫名的感动。狂草的艺术表现力极其丰富,每每使我在超越技法的同时,能获得一种放浪形骸之外的快意和心灵无所挂碍的自由。这种自由是形式的,更是精神的。我一直以为,自由是艺术的最高境界,虽难以企及,却心向住之。”在徐庆华看来,草书集中了各种字体的优势,章草、大草、狂草,一种比一种表现性更强。通常,每种书体都有其内在的规律和要求,但徐庆华认为在符合法度的同时,更需注入艺术家个人的情绪和对书法的独到理解,这样的作品才会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徐庆华在丈二宣纸上完成的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看似只花了很短时间,实际却有着几十年书法创作的深厚积累,同时包含了彼时彼刻书法家才华的激发与外现。而徐庆华也用自己的作品践行了自己理念的正确性,他的草书作品曾参加2007年“海派书法晋京展”、2009年“全国草书名家上海邀请展”等一批重要展览,被中国美术馆、浙江省美术馆等权威艺术机构收藏,受到书法爱好者的青睐。
但“不安分”的徐庆华并未止步于此。以草书的“线条”为基础,徐庆华又开始实践起向抽象画甚至向雕塑的跨界转身——如果说传统草书对于书写的内容存在限定,要求作品为汉字并且可读,那么抽取了文字内容的线条就有着更为纯粹的表现力。徐庆华为现代书法而着迷,创作了“书非书”系列作品,剥离文字,把线条的形式当作独立的表现内容。这些作品乍看上去杂乱无章,纷纷攘攘,但又在线条的转折、浓淡、交叉等处体现出传统草书的特质,细品之下感受到舞蹈的狂喜。徐庆华认为,艺术的精魂在于自由,纯粹而质感丰富的线条最有利于表达自由的境界。“就我的‘书非书系列而言,内中包含了以形式为内容、强化线条之美的价值取向,可以说是当今多元化艺术中的一元。如果把它们当作以书法线条为基本构成的抽象画,那就容易看懂了。”在徐庆华看来,书法内容与线条形式的关系就像音乐里的歌词与旋律,歌唱你情我爱的陕北信天游可以打动听众,完全不要歌词的贝多芬交响乐同样可以让听众陶醉。“我相信,纯粹线条的表现力今后将得到艺术家更多的开掘。”
旺盛的创作力恰恰源于对生命本质的深刻颖悟,对自由的深沉追求,也是徐庆华对艺术创作规律的天才把握。“我也会像常人一样,在某些时候陷入创作上的瓶颈,但我跟其他人的区别在于,我能把这些事情暂时放下,先做其他事情。等过一段时间之后,再回来创作。一个人做事情,不能停滞不前,得让心灵自由。心灵不自由,手就放不开。我们经常说放下,不是真的把事情都放下,而是让事情在心里集聚一段时间,这样更容易把能量释放出来。”
把艺术楔入世俗生活
虽然科班出身,现在又是上海交通大学艺术系的教授,但很显然徐庆华并没有打算守着按部就班的“老师形象”和学院派的“传统规矩”过日子。在徐庆华看来,艺术分科的时代早已过去,现在强调的是融合,“以往我们强调书法是文化的核心,很多人忽略了书法作为艺术的本质,它的字型、线条、结构、墨色,都有独立的审美价值,是取之不尽的艺术源泉。”他认为不同的材料能够表现出不同的美感,艺术家应该不断为自己的艺术创作寻找新的突破点,“也就是我们现在流行的跨界,艺术边缘的模糊。”在徐庆华看来,正如韦伯、阿多诺等西方学者认为的那样,工业社会让人们陷入工具理性的主宰,而艺术承担着世俗拯救的功能,把人们从日常生活的刻板重复中解脱出来。他并不满足自己的作品停留在画册里、杂志上或展览厅中,而是致力于把自己的书法和抽象理念楔入日常生活,走向器物和实用空间,发挥艺术的审美救赎功用。
在这样的理念下,徐庆华几乎每年都拿出一段时间去江西景德镇,在瓷器生坯上创作,然后在当地上釉、烧制,得到成品。书写的内容既有传统书法文字,也有抽象的线条。他说,“自由”绝非胡涂乱抹,优秀的作品对于技艺有着极高的要求。在瓷坯上画线条,“墨”实际上是灰泥浆,涂上去之后很快就消失了颜色。泥浆很容易沉淀,隔一小段时间就要重新调和,这样“墨”的浓淡、用笔的轻重、不同线条的穿插全凭经验,稍有不慎,就会整个作废。在烧制之后,往往多有废品,但是“当艺术家熟练掌握瓷器特有的笔墨用法之后,就可以更加关注于结构布局、线条走向等,让瓷器承载艺术家的创造力。”虽然自己师出名门且一路科班地读到博士,但徐庆华的作品和思想上却几乎看不到“传统包袱”:“现在很多年轻人提到书法就认为是很迂腐的东西——为什么要那么辛苦把毛笔字写好看?我们这个时代甚至都不用笔了。但其实把字写得好、写得端正并不是书法,我认为书法艺术的这一面应该在现代生活中更为凸显。”他举例说,去年同时有一个现代书法和传统书法的展览,不少观众对于传统的东西已经没有兴奋点,而现代书法则非常有活力、观念开放、融合创新、其表现手法和材质充满想象力和艺术的感召力、震撼力。徐庆华认为,传统的东西在当今应该有一个形态的转换,若一味墨守陈规,会慢慢失去很多发展空间,“毕竟你是生活在当下,与当下总得有一种呼吸交流,书法不仅要继承,更要拓展。我一直在想书法怎样和当代人的生活结合起来,可以通过形式感、材质的独特性来加强。”
于是,在上海万航渡路上的某家大酒店内,店堂和包房里陈列着徐庆华的五十多件书法作品。在其中一个包房里,金色的宣纸上写着一列列金文,古拙遒劲,厚重雅致。每位来宾都知道是方块字,但大部分文字难以识别,只是可以感受到一种飞扬升腾的意象。凑近了去看,文字间零散地钤盖着一枚枚印章,如“平常心”、“了一”、佛像等,为画面增添了浓郁的现代感。宾客欢宴之余赏读书法,别有趣味。其他包房里还有甲骨文、篆书、草书作品,各显精彩,成为酒店环境装饰的点睛之笔。而在浙江电力大厦,数百平方米的外墙上贴着艺术浮雕,形式新颖,富于视觉冲击力,其文字正是出于徐庆华之手。他巧妙组合三角形、圆圈、长方形等块面,雕出富于美感的文字,兼具书法与篆刻要素,令古老的文字显现出现代的美感——综合材料的艺术作品融入一整座大楼,实用的建筑散发出浓烈的艺术气息。
在徐庆华看来,艺术上的跨界没有任何障碍。“障碍只在你心里,心一旦打开了,需要掌握的只是技能问题,因为你要表现的还是那些线条、那些精气神。”在这个能让线条听自己话的书法家眼中,世界万物都是由线条组成,“城市的交通命脉、人体的静脉动脉、甚至职场上的人脉关系,都是纵横交错在一起组成的线条,理解了这些你的心就自由了。”徐庆华认为,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自由的表达。“我创作一直保持一种激情,不会受固定技法的束缚,追求的是一种无法之法的境界。手的自由,首先是心的自由,艺术之路才会越走越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