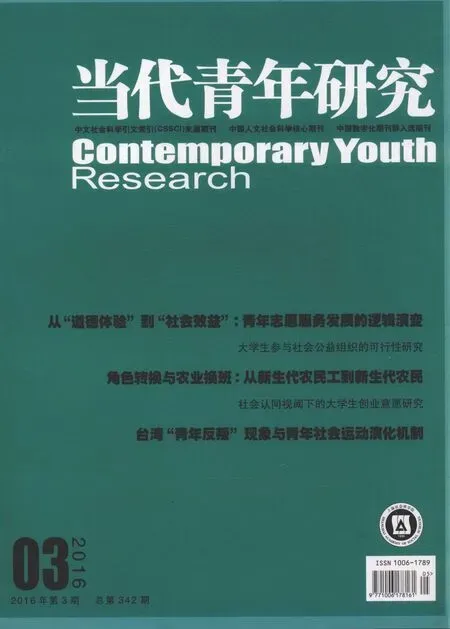大学生参与社会公益组织的可行性研究
——基于志愿服务媒介效应的调查
陆耀峰
(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大学生参与社会公益组织的可行性研究
——基于志愿服务媒介效应的调查
陆耀峰
(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大学生作为志愿者参与社会公益组织是实现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之一,对上海市高校与社会公益组织群体在志愿服务媒介效应上的调研发现,当前高校和社公益组织在媒介建设上都出现不同程度的缺失,而两者也更应注重发挥以“网络”和“人”为媒介的效应,为大学生参与社会公益组织提供可行性保障。
大学生;社会公益组织;志愿服务;媒介效应
一、背景
在党的十八大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要求下,大学生参与社会公益组织并担任志愿者实现社会治理的路径已成为必然趋势,就大学生参与社会公益组织的文化哲学研究路径而言,主要涉及精神文化、制度文化以及物质文化,高校与社会公益组织在这种文化上的建设情况,将直接影响双方实现对接与合作后的契合性、持续性以及创新性。
从志愿服务物质文化的具体呈现载体来看,主要包括书籍、报纸杂志、报告书、海报等传统制品;电视、电影、广播、网络等媒体制品;衣服、帽子、挂牌、徽章、证书等标示制品。从中不难发现,物质文化往往作为一种人与人、物与物以及人与物发生关系的媒介被人们所认知,也正如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认为的“媒介即是讯息”[1],这些物质文化的呈现载体无一不包括了志愿服务的讯息,从而,对志愿服务物质文化的研究就成了对其媒介的研究。就媒介的本质而言,媒介是一种工具而并非为目的,[2]探索高校大学生参与社会公益组织的可行性路径时,针对媒介的作用研究就要从其效应[3]进行评价。
志愿服务作为一项大众参与的事业,其所指的媒介可以等同为大众媒介,鲍德里亚认为,现代社会中最大的权力运作工具就是大众媒介,[4]发挥好大众媒介的积极效应必将推动社会治理体制的建设与创新。
二、研究过程
本研究选取高校与社会公益组织群体对招募、激励与总结三个环节是否开展相关媒介进行评价,以此来考察媒介效应。针对这三个环节中所产生的媒介就应当为:一是招募,主要体现在参与者获取信息的渠道;二是激励,主要体现在参与者所受到的物质类激励,比如衣帽、服务照片以及媒体宣传等能够激励志愿者的物质载体;三是总结,主要体现在参与者工作后的物质类反馈,比如总结会、证书以及感谢信等。
本研究以上海市的社会公益组织以及高校大学生的志愿者群体为研究对象,围绕以上媒介的具体内容,在高校层面选取了8所985和211高校、3所普通高校以及3所以专科见长的普通高校进行调研,共采集229份有效问卷;在社会公益组织层面选取了38家具有代表性的青年社会公益组织以及“邻里守望”组织进行调研,共采集153份有效问卷。同时,在以上社会公益组织中抽取了18家进行深入访谈。本研究数据的均值采取“二级评分制”,“选择该项”计1分,“未选择该项”计0分。卡方检验主要检测高校和社会公益组织的志愿者群体间对具体媒介的评价上是否出现显著性差异,以Sig值小于0.05为标准,若出现显著性差异,则表示双方合作时应当需要高度重视的内容。
三、结果与分析
高校和社会公益组织在媒介建设上都出现不同程度的缺失,两者在网络媒介的建设上都趋于完善,高度重视标示物和服务证书的媒介效应,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感谢信的媒介效应。
(一)高校和社会公益组织的招募媒介效应相一致,更多使用网络媒介
高校和社会公益组织在招募过程中,所运用到的传统媒介主要为海报、横幅以及传单等,而在数字化时代下,对于以网络为载体的媒介运用更为广泛,应当说,网络自身是一种“界面”(两种或多种信息源面对面交汇之处)[5],通过电子计算机、手机等终端来实现信息的传播与反馈,而正是具备了带有相关“讯息”的文字、声音、图片以及影像等媒介素材后,网络才能发挥其媒介效应。
但在招募过程中,无论是传统媒介还是网络媒介,都需要由志愿服务组织方进行建设,其建设情况是否良好往往表现在参与者获取志愿服务信息的渠道。进而,本研究围绕志愿服务信息获取渠道,对高校大学生以及社会公益组织群体进行调研后,形成的信息见表1。

表1 高校和社会公益组织群体获取志愿服务信息的渠道情况表(%)
高校大学生与社会公益组织群体在获取志愿服务的信息渠道上集中于组织方的自身媒体,并多为该组织的网站、微博、微信、腾讯平台等网络媒介。在“政府媒体”和“机构媒体”所显示的数据来看,高校大学生与社会公益组织群体在这两个渠道上的人群比例相近,一方面表现出政府媒体高度重视了志愿服务的招募媒介,另一方面也表明无论是高校还是社会公益组织都非常重视自身媒体的建设,并能够发挥该媒介的有效作用,才会使得两部分群体都会以此作为最为主要的信息获取渠道。当然,高校大学生与社会公益组织群体来源的根本性区别,也导致了其在“街道”和“朋友”的渠道比例不一致性。
当前,在不断形成居民自治良好氛围的时代背景下,政府部门的支持也加速了大众对志愿服务招募媒介的深入认知。以2010上海世博会志愿者为例,一是通过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介进行招募宣传,在宣扬世博会意义及功能时,进一步对志愿者、志愿精神与志愿文化进行了普及性宣传;二是通过建立志愿者报名网站,面向全球进行招募,并协同多家网站一同宣传世博志愿者信息;三是树立“标示物”到城市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世界在你眼前,我们在你身边”的标语、“心”形的志愿者标示以及城市服务站点等;四是形成志愿者招募的主题宣传片和歌曲等,并通过多种媒介载体进行传播。同时,部分高校还主动对接招募工作,开展校内的招募宣讲会、报名路演等。这些举措极大地激发了大众的参与热情,而其背后也体现了媒介的巨大力量。
在此种招募媒介的成功推动下,上海进一步加强市级层面的整体网络招募系统,形成“上海志愿者网”和“智慧公益平台”两大志愿者招募网站,其发布的项目具有类型多样、服务对象多种和参与群体丰富等特点,但从项目发布与实施单位来看:一是缺少高校组织;二是多为政府职能部门;三是社会公益组织相对较少。同时,于2014年12月启动的“智慧公益平台”当前正处于半停止状态,此种情况的出现,会降低志愿服务招募媒介的效应发挥,进而削弱大众参与志愿服务的热情,也就降低了高校大学生参与社会公益组织并担任志愿者实现社会治理的路径可行性。
针对以上情况,政府职能部门应当注重招募媒介的统一性,避免多元化平台带来的不稳定性,并降低网络媒介的“失真性”,为高校与社会公益组织自身网络媒介的建设树立标杆。
(二)高校和社会公益组织的激励媒介效应较一致,亟待加强建设
在志愿服务过程中,处处伴随着激励的措施,比如出征仪式、培训会、网络交流平台等,只要能促进志愿者激发服务热情与提升服务质量的措施,都应当认为是一种激励的手段。但综合这些手段来看,刨去“人”作为媒介并属于媒介范畴的手段,就主要表现为标示物、服务照片以及媒体宣传。本研究中,高校大学生以及社会公益组织群体对自身志愿服务组织激励媒介有无情况的评价不容乐观,见表2。大学生与社会公益组织群体自身志愿服务组织激励媒介有无情况的评价总均值为0.46,该均值趋近于0,这表明双方总体的激励媒介使用情况较差;其中,高校层面的均值为0.5,社会公益组织层面的均值为0.42,这表明高校的激励媒介使用率高于社会公益组织。

表2 高校和社会公益组织群体对激励媒介有无情况评价的卡方检验与均值表
1. 高校和社会公益组织应当加大对“标示物”的资金投入
从“标示物”使用情况来看,大学生与社会公益组织群体反映出的均值较为一致,以两个群体为自变量所得的卡方检验也表明,两个群体未出现显著性差异。对比其他两项均值来看,“标示物”的均值最高,也说明高校和社会公益组织都意识到“标示物”对志愿者以及自身志愿服务项目的积极意义。对志愿者而言,统一的“标示物”能明确其角色与身份,还能加快形成与融入团队的速度,更能让外界快速认识到该群体的存在并提升认同度。[6]从均值水平来看,仍有提升的空间,也值得高校和社会公益组织投入资金。
就“标示物”的媒介功能来看,一是其直观性与具象性不言而喻;二是其公益性原则,让人们看到“标示物”后产生天然的接受心理;三是其“讯息”的传播对象不仅只局限于志愿者和服务对象,更能覆盖到“旁观者”。志愿者在佩戴“标示物”后,首先会前往目的地,在这段旅程中就会产生大量的“旁观者”;其次在服务时,也会遇到一部分的“旁观者”;最后,佩戴“标示物”的志愿者也往往能够成为媒体宣传时的重要影像素材,能够覆盖更多、更广的“旁观者”,以上过程也是让“旁观者”接收“讯息”的过程,更是其成为志愿者的重要环节,而这也与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相一致。[7]
2. 社会公益组织应当重视服务照片的采集
从服务照片的采集情况来看,大学生与社会公益组织群体所反映出的均值差较大,高校层面的均值为0.52、社会公益组织层面的均值为0.35。同时,以两个群体为自变量所得的卡方检验Sig值为0.001也表明,两个群体出现显著性差异。综合均值与卡方检验表明,社会公益组织亟待加强对服务照片的采集。
志愿者服务照片的采集不仅体现了组织方对志愿者的重视,也是媒介效应体现的重要来源与保障。从服务照片本身而言,若不进行传播则不能称之为媒介,但现实情况是,只要进行照片采集,必定会将照片通过一定形式的载体进行传播。从而,服务照片的采集虽然不属于媒介范畴,但却是媒介的重要素材与来源。同时,照片自身也应当蕴含了大量“讯息”,比如“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又或者是快乐、幸福的表情等。这就要求高校和社会公益组织自采集服务照片时,应当注重图片的内涵性,并与自身组织倡导的价值观或理念相结合。
采集服务照片还有更为深层次的认知意义,在人的认知过程中,需要感觉器官提供相应的信息,感觉器官通过不同的体验方式来产生信号经由神经中枢系统达到大脑,综合所有感觉器官来看,“人类大脑从外界获取的信息有83%来自视觉”。[8]图片作为视觉的媒介对象,其呈现的画面内容与人的日常视觉内容较为一致,从而将被更为快速与深刻地让大众所认识与记忆。当然,录像所形成的视频内容与人的日常视觉内容更为一致,但其制作与观看的条件与成本相对较高,并非适用于所有志愿服务组织。
3. 高校和社会公益组织亟待加强媒体宣传的建设
从“媒体宣传”一词的组合结构来看,是通过媒体的手段实现宣传的目的。从“媒体”与“媒介”的含义来看,两者区别性不大,但在实际的志愿服务开展过程中,媒体宣传是一项具体的工作,更是作为一种重要手段来传播与志愿服务相关的“讯息”。从而,在本研究中将“媒体宣传”定义为一项特定的工作,并作为媒介的载体、传播的方式与手段。同时,志愿服务组织在激励环节对媒体宣传的建设,则是其媒介体现效应的重要表现形式。
激励环节中的媒体宣传,其实质则是发挥新闻报道的作用,其主要对象是参与志愿服务的志愿者,激励志愿者在参与过程中能够提升服务热情与质量。当然,媒体宣传的多样化载体也进一步影响到其他人群,使更多人能够关注到此项志愿者、服务项目以及志愿服务组织,并在关注的过程中接收了许多“讯息”,对志愿服务形成更为理性的认知,以此来发挥媒体宣传作为媒介的效应。本研究的数据显示,在激励环节中高校和社会公益组织均在媒体宣传上的建设力度不足,这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下志愿服务组织“重使用、轻培养”的志愿者管理态度。[9]志愿者若未能感受到自身受到足够的重视,则会降低对该志愿服务组织的认同度,也就有可能造成优秀志愿者的流失。
从激励环节媒体宣传的建设难度来看,主要受限于及时性因素。在志愿服务过程中,志愿服务组织首先就要进行及时的文字与影像记录,其次要将这些素材加以整合与编辑,最后通过媒体进行传播。而这些就需要志愿服务组织先要有此方面的建设意识,换言之,志愿服务组织的媒介素养层次直接决定其开展媒介建设的程度。然后,就需要有足够的人力、物力以及财力来完成以上的工作,这对许多面临“死亡边缘”的志愿服务组织提出了不小的挑战。
因此,高校与社会公益组织在自身加强媒介素养的同时,也可以适当招募一部分进行媒体宣传的志愿者来降低人力、物力以及财力的投入。通过形成一支“志愿者”队伍,也将有效提升其媒介的效应。
(三)高校和社会公益组织的总结媒介效应较一致,亟待加强建设
志愿服务的总结工作尤为重要,一方面是对现有成功经验与做法的有效归纳,另一方面也是对现有问题与困境的梳理与分析,还是志愿者对志愿服务产生并提升理性认知的重要环节。从总结环节所涉及的具体媒介,主要为总结交流会、服务证书、感谢信以及纪念品等,其媒介的效应对象主要为志愿者。围绕以上几种媒介,本研究对高校大学生以及社会公益组织群体进行调研得到的信息见表3。高校与社会公益组织总结媒介的总均值分别为0.34和0.36,表明双方在总结媒介上的使用水平趋于一致,同时,双方的总均值为0.35,趋近于0,则表明双方在总结媒介上的建设力度有待加强。

表3 高校和社会公益组织群体对总结媒介有无情况评价的卡方检验与均值表
1.高校和社会公益组织应重视总结交流会的媒介效应
总结交流会是发挥媒介效应的重要载体与手段,在此过程中,志愿服务组织一般会将文字或影像资料进行编辑,通过纸质报告、PPT等方式来向志愿者传递相关“讯息”,当然以“人”为媒介的方式也成为重要的呈现手段,会由该项志愿服务项目负责人、优秀志愿者代表以及服务对象等来讲述一些重要“讯息”。从调研对象所反映出的情况来看,高校与社会公益组织在总结交流会上的建设力度不足,殊不知总结交流会的媒介效应不仅只是“讯息”的传递,更是一种教育的形式。应当说,总结交流会是仪式教育的一种形式,从仪式产生的源头来看,往往是在具有纪念意义的时刻以群体性活动来呈现,而志愿服务工作的结束对每个志愿者而言都应有其纪念性意义,从而应当站在仪式教育的高度来看待总结交流会。
那么,此种仪式教育应当强调志愿者的体验与收获,通过互动的形式不仅能够让志愿者了解志愿服务以及志愿服务组织的历史,更能形成浓厚的文化氛围。而在高校与社会公益组织实现良好对接的过程中,也应避免仪式教育的“形式化”倾向,关注社会、文化与教育的发展,进一步实现个性化与社会化的融合。[10]
2.社会公益组织亟待注重服务证书的媒介效应
志愿服务证书承载的是对志愿者的行为和价值的认可,也是对志愿者崇高道德的最佳褒奖,志愿者获得证书后不仅会因为自己得到肯定并产生极大的自豪感,[11]而且在之后每每看到证书时,都会激发其志愿服务的热情。同时,服务证书相较于感谢信与纪念品而言更为正式,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一种履行“契约”后的证明,更是《关于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的意见》中对志愿服务记录工作的体现方式之一。
从志愿服务证书所蕴含的“讯息”来看,主要包括参加者姓名、项目名称、服务时间、服务次数以及机构名称等,这些“讯息”看似简单,但对志愿者而言,由于自己是亲身经历并获得成长与快乐,所以在看到证书时便能勾起满满的回忆,从中就可以看出,此种媒介的效应意义之重大。
表3显示,高校与社会公益组织的服务证书均值分别为0.54和0.44,两者的卡方检验Sig值为0.047,说明两者出现显著性差异,这表明,社会公益组织对服务证书的效应尚未形成更为理性与深入的认识。应当说,服务证书的制作成本相对更为低廉,社会公益组织应当努力完成此项工作。同时,社会公益组织也应将自身的服务理念与标示印制在服务证书上,加强此媒介的长效效应。当然,高校也应重视此项工作的建设力度,在体现“育人为本”工作理念的同时,更能迎合大学生希望受到重视与关注的心理。
3.高校与社会公益组织在感谢信与纪念品上的效应出现不一致
感谢信与纪念品从其媒介功能上来看,均具有纪念性功能,相较于服务证书更能体现志愿服务组织对志愿者的重视力度,而此种“以人为本”的“讯息”也能被志愿者所意识与接收到。在网络化倾向日益增强的今天,社会大众“沉浸”[12]在“虚拟世界”的同时,以感谢信与纪念品为物质载体的志愿服务衍生品,却焕发出更多的“人文关怀与精神”,也成为最不容易被遗忘的志愿服务记忆深深地烙在志愿者的心中。
从本研究所得数据来看,高校与社会公益组织的感谢均值分别为0. 1和0.39,两者的卡方检验Sig值为0.000,说明两者存在显著性差异,综合均值和卡方检验指,本研究认为高校在此项工作上存在一定缺失,亟待对此加强建设力度;同时,两者的纪念品均值分别为0.37和0.3,卡方检验值未表明两者出现显著性差异。根据以上对感谢信与纪念品的媒介效应分析,建议高校与社会公益组织均应加强此方面工作的建设力度,能够进一步发挥其媒介的长期效应。
三、研究反思
志愿服务过程中,时刻都发生着以“网络”和“人”为媒介的效应。从志愿服务工作的源头来看,人始终先于网络而产生,但人又“沉浸”于网络之中,而网络正如媒介作为一种“人的延伸”,为人提供着转换事物的新视野和新知觉。[13]这对刚诞生30多年的志愿服务工作而言,无疑是一种向大众普及志愿服务知识与理念的良好手段。同时,人沉浸其中后也必将以自己为媒介向他人传递“讯息”,以此形成良性循环使更多人参与到志愿服务之中。而高校与社会公益组织应当注重发挥以“网络”和“人”为媒介的效应,双方更应在媒介建设上加强力度并实现一致性,为大学生参与社会公益组织并担任志愿者实现社会治理提供了可行性保障。
(一)志愿服务应当发挥以“网络”为媒介的效应,秉持“真”的原则
在互联网时代,网络作为堪称“第一”的新媒介[14]逐渐改变着人的生存方式,原有的认知、交往、劳动以及休闲等生存方式,几乎都可以依托网络得以满足。[15]而志愿服务作为一种生存方式,也不能例外地可以通过网络来实现。
从认知角度来看,志愿服务的网络媒介已经形成并成熟,所有与志愿服务相关的信息都可以通过网络搜索进行获取。从国家到地方政府均建立了相应的志愿者门户网站以及微博或微信平台,以此网络平台发挥媒介效应,而各志愿服务组织也或多或少会进行效仿。若需获取更多相关信息,还可以在网络平台上进行提问,而相关组织也会及时予以回复,进而实现了认知的需求。
从交往角度来看,一是在政府、高校层面,举办相关大赛实现部分的交往需求的满足,比如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青年影响社会”上海十大青年公益项目评选、宝山区创建“文明城区”青年公益项目设计大赛以及高校志愿服务十佳团队等,以网络公告的方式提供了潜在的“线下”交往可能;二是志愿服务组织搭建的交流平台,比如QQ群体、微信群及飞信群等,直接满足了“线上”交往的需求。
从劳动与休闲角度来看,这似乎与志愿服务网络媒介没有直接关系,那就得从劳动与休闲的本质进行分析。一是劳动,一般指人通过付出智力与体力来完成某项工作并获取报酬,而志愿服务则是不以获得报酬为目的,自愿奉献时间和智力、体力、技能等,帮助他人、服务社会的公益行为,[16]但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是个人全面发展的自由自觉的活动[17],从一定程度上说,志愿服务更符合马克思对劳动的理解。二是休闲,一般指在空余时间通过一定的载体、手段与途径来获得身体与心理上的愉悦。志愿服务就是这么一种占用空余时间并付出智力、体力以及技能并获得快乐的方式。志愿服务的网络媒介则为人提供了实现劳动与休闲的可能。
正如网络新闻存有“失真”的情况[18],在志愿服务组织对网络媒介的建设上,也会出现“失真”的情况。此种“失真”往往表现为信息的不完整性甚至错误性而造成原因多样。一是多部门、多层次以及多载体在信息传递过程中,出现了信息遗漏或凭空增加的情况,一般是由于相互间的交流沟通不足以及信息完成后校对不严谨所导致;二是为博眼球采用更为具有吸引力的信息,这就容易造成志愿者在参与过程中实际获得的内容与宣传信息出现强烈反差,当此种反差超过了志愿者的容忍度后,就会爆发网络谴责甚至谣言等。三是能力不足,一些志愿服务组织存在资金、专业人员以及技术等方面的困境,就容易造成信息的延迟性与错误性。
应警惕的是,志愿服务的网络媒介可以将志愿者乃至志愿服务组织的真实属性进行遮蔽。比如,人原来的年龄、样貌、身份及谈吐等都可以通过网络进行重新构建,网络身份可以根据自身的喜好来设计,无论是高矮胖瘦还是英俊丑陋,抑或是性别都可以重新改变,个人依托不同的平台来完成个人信息的重构。志愿服务主体不再被自然特征所束缚,在网络世界中主体根据自身的喜好来建立虚拟主体,当然,也可以完全根据自身来打造相对应的属性。以上担忧成为了现实,某人在网络平台散布了自身虚假信息募捐得到15万元的非法资金,[19]也有志愿服务组织通过众筹的方式来获取资金,但其是否具有合法身份以及资金的使用情况等,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不确定性与非透明性。[20]从而,无论是高校还是社会公益组织都应当以“真”为原则建设网络媒介,以此获取公信力来进一步推动大学生参与社会公益组织并担任志愿者实现社会治理的目的。
(二)志愿服务应当发挥以“人”为媒介的效应,秉持“以人为本”的原则
人应当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体[21],人以自身为手段来实现自身的目的,那么这个手段可以被理解为媒介,而其目的的表现就应当是效应。从而,以“人”作为媒介发挥其效应与人的本质相一致。在此,本研究立足于志愿服务组织作为主导者,那么在志愿服务中的“人”就分为两部分主体,一是“自我”,二是“他人”。其中,“他人”的媒介效应不容乐观。
从志愿服务项目的发生过程来看,“自我”就是指志愿服务组织者,其通过“自我”为媒介向他人传递着大量“讯息”,于是就形成一大批认同其理念与工作的志愿者群体,而这批人群就可以被理解为志愿服务组织中的“他人”。那么,志愿服务组织就希望“他人”能够作为其媒介来发挥效应,一方面实现志愿服务组织的服务目的,另一方面实现志愿服务组织的宣传目的,让更多人支持该组织。但每个理性的人都应当自在地作为目的而存在,不是他人随意使用的工具[22],志愿者往往容易在志愿服务以“人”为媒介的过程中被淹没了“自我”的主体功能,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志愿服务组织相较于单一的志愿者个体而言,应当属于强势群体,若不能突破“上对下”意识的前提下,往往容易忽视志愿者作为“自我”的媒介效应。二是志愿者的“自觉能动性”[23]程度不足,未能意识到自身作为主体的功能与权利,进而导致其丧失作为“自我”的人的媒介效应。三是志愿服务的评价导向往往来源于服务对象的需求满足程度,这也会不同程度地降低或淹没志愿者作为自身媒介的效应评价。
在当前要求“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背景下,无论是高校还是社会公益组织都应当重视志愿者作为“人”的媒介效应,将“以人为本”作为其根本原则,也就是尊重志愿者的主体性地位,这也与志愿服务的目的相一致。当前志愿服务往往会聚焦于特定的服务对象,其工作的评价导向也是服务对象的需求是否满足,从而容易忽视对志愿者工作满意程度的评价,从而应当以原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2001国际志愿者年”启动仪式上的讲话来理解,即志愿精神的核心是服务、团结的理想和共同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信念。志愿者也应当是志愿服务的受益者,在服务他人的过程中也实现了服务自我的目的,并形成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念。同时,也只有具备了以上理念的志愿者,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媒介效应。
高校和社会公益组织应当在自身媒介建设过程中应充分融入志愿者的主体性因素,以鲜活的志愿者群体为媒介说好当代中国志愿者的故事。同时,应当充分发挥“人人都有麦克风”的自媒体优势,进一步强化网络媒介的互动功能,实现人人参与、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良好社会风尚。在“以人为本”的媒介建设原则下,不仅能够提升大学生参与社会公益组织的可行性,也能够体现高校“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教育理念,更能实现社会公益组织造福社会的根本宗旨。
[1][3][13]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33,56,96.
[2][4]徐琴.论鲍德里亚的大众媒介批判理论[J].东南学术,2009(02):27-33.
[5][12][15]迈克尔·海姆.从界面到网络空间——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M].金吾伦,刘刚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78、115.
[6][11]陶倩、董芳源、陆耀峰.社会治理视域下的志愿文化培育[N].文汇报,2015-12-25(008).
[7] Bandura, A.(1986). Social foundations of thought and action: A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Englewood Cliffs,NJ: Prentice-Hall.p.51.
[8]汪维丁、余雷.标志与企业形象设计[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1:37.
[9]张晓红.高校志愿服务教育课程化路径探索[J].思想教育研究,2011(05):85-88.
[10]张志坤.仪式教育审视:教育人类学仪式研究视角[J].中国教育学刊,2011(12):24-26.
[14]刘中望.媒介新技术:互联网与当代生活方式[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1):95-98.
[16]民政部.志愿服务记录办法[Z].民函[2012]340号.2012-10-23.
[17]唐正东.马克思与劳动崇拜——兼评当代西方学界关于马克思劳动概念的两种代表性观点[J].南京社会科学,2005(04):1-6.
[18]黄曼青.网络新闻传播失真原因探析[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5):183-186.
[19]谢宛霏.知乎大V童瑶事件风波[N].中国青年报,2016-01-21(04).
[20]钟智锦.社交媒体中的公益众筹:微公益的筹款能力和信息透明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08):68-83.
[21]邓翠华.人是目的与手段的有机统一[J].教学与研究,2007(08):88-93.
[22]陈旭东,汪行福.从德性义务理解“人是目的”的道德律令[J].山东社会科学,2008(07):49-55.
[23]凌厚锋.和谐社会与人的自觉能动性[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6):21-26.
A Feasibility Study on the College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Social Public Welfare Organization——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Media Effect of Voluntary Service
Lu Yaofeng
(School of Marxism, Shanghai University)
:College students as volunteers to participate in social public welfare organizat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ways to realize social governance. According to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Shanghai university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the volunteer service media effect, the curren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social public welfare organizations appeared different degree of lossin building a media. Therefore, the both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to play a “network” and “people” as the effect of the medium and provide a feasibility for college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social public welfare organizations.
dss:: College Students; Social Public Welfare Organization; Volunteer Service; Media Effects
G641
A
1006-1789(2016)03-0010-07
责任编辑 曾燕波
2016-01-26
本文系2015年度全国学校共青团立项课题“高校志愿文化培育的路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5LX101。
陆耀峰,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