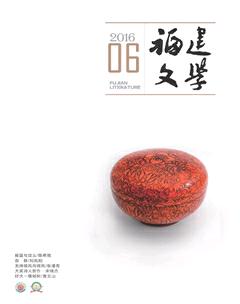回忆郭风先生
朱谷忠
在人群中转身,我看到
你越来越清晰的身影
先生,请允许我为你写一首诗吧
一半是回忆,一半是歌吟
——摘自拙作《我最爱的先生》
一
毫无疑问,作家都是以作品来吸引读者目光的。但当作家成名后,赢得读者目光的就不单是作品了。他们的身世、经历、喜好等等,有时竟也同他们的作品一样具有相似的或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吸引力。这一切,似乎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又是一件令作家无可奈何的事。
可见,读者喜欢一个作家,不仅在其作品,而且有时在其作家性情本身;不仅在其贡献,而且有时在其作家人格个性;等等。但事实上,许多作家往往不愿披露自己,而且愈有名望的作家愈是如此,这就不免让喜欢那些作家的读者感到有些“遗憾”了。
而郭风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
郭风,原名郭嘉桂,回族。中国现当代著名散文家、散文诗作家、儿童文学作家。
郭风1917年12月17日(农历)生于福建莆田城厢,福建师大中文系毕业后,历任莆田县凤山小学、中山中学、福州高级工业学校教师,《星闽日报》编辑,《福建文艺》《园地》《热风》《福建文学》杂志社副主编。之后相继担任福建省文联秘书长,福建省作家协会主席,福建省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和全委会名誉委员,中国散文诗学会会长,以及《福建文学》顾问、福建省文学院名誉院长等职务。诚如人们所知,郭风先生是在1933年创作了歌颂光明正义的短篇小说《配民夫》后,从此步入文学创作的人生旅程的。七十余年间,他辛勤耕耘,出版了五十多部作品,多次获全国奖项,1997年,《郭风散文集》获鲁迅文学奖荣誉奖。
记得从1973年到1999年,近二十多年期间,由于工作关系,加之同住在一幢楼,使我常常得以和郭风先生相处。但我发现,与他的创作相比,他的确更乐意让自己在生活里的一切都安于寂寞,安于平凡和清静。记得好几次他去北京参加数年一度的全国作家代表大会,夜间若有文艺演出招待会,他都会让我去向大会请假,说有早睡的习惯。还记得当时全国有不少地方邀请他前去讲授创作经历,但都被他一一婉谢了。再如我所知,与他认识并有书信往来的前辈著名作家就有茅盾、巴金、叶圣陶、冰心等人,但他从未请他们为他的作品集写过序跋,倒是满腔热情地为省内外许多尚未成名的作家写了数十篇序言,且分文不取。令我至今感念于心的是,1987年秋天,有一天傍晚,郭风从外面散步回宿舍见到我,忽然拉我到一个天井旁对我说:“你最近写了一些散文我都看到了,似乎有较好的苗头;这样吧,你能不能挑几篇给我,我来选一篇,向上海的《文汇月刊》推荐一下。”我一听大为惊喜,连忙点头称谢。要知道,当时的《文汇月刊》是全国著名的刊物,能在上面发表文章可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果然当年12月,郭风的评论和我的散文《妻子的困惑》,同期在《文汇月刊》上“我喜爱的散文”栏目里发表了。其实,郭风这种关心并奖掖后辈的热情,绝非仅仅只发生在我一个人身上,但却大都鲜为人知。难怪迄今为止,许多人总是常常提起:“有关郭风的作品我们十分熟悉,但有关先生其人,我们知道的似乎太少了。”
这里,就让我来说说郭风先生吧。
二
在我看来,郭风无疑是一个文雅但却充满着激情和智慧的著名作家。从他的作品不难看出,他是多么挚爱并欣赏故乡木兰溪畔的村庄、果林和美丽的谣俗;同时挚爱并欣赏祖国的大好山川,可谓几十年如一日,一直保持着对内心感受的忠诚。细读他的作品,还可发现,即便是理性的题材,他也从不说教,而总是在故事与诗境里拓展丰富的人性。而在生活中,他又是个放得下读书人架子的人,能与市井百姓亲切交流,互致问好。他尤其对同事和下属的苦乐极为敏感,好像其间的一切也是自己生命的一体,所有的冷暖都关乎自己的存在。难怪认识他的人都会说:“郭老是一个大好人!”
但从另一个角度说,不知是被一种什么样的使命感驱使着,郭风对待文学创作,几乎是怀着一种宗教式的献身精神的。住在他周围的人都知道他有个习惯,即每天清晨,他总是很早起身,洗漱毕,就坐在书桌前,在灯下,在窗外一线朦胧的曙色中,开始读、思、写……即使“文革”中被迫下放到深山,只要有一间蜗壳式的茅屋可居,他在内心中就不会放弃对文学的思考。
充满魅力的、变化的、又瞬息即逝的无数个早晨过去了,无数的亲历、亲见,也在他的心中、脑中一一刻录了下来。随之,散文、散文诗、评论、序跋,源源不断地从他的那支罄击奇妙的笔尖涌出。
也许人们提及《叶笛集》就会想起郭风,提及郭风就会想起《叶笛集》。无疑,《叶笛集》是郭风创作生涯的一个里程碑,是我国散文诗史上的一部具有开拓性的、表达非凡的作品。诚如人们所知,《叶笛集》于1959年初出版后,立即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冰心著文称自己“又发现了一个大诗人的喜悦。”许多评论家则称道:这部散文诗集是最富有音乐性的纯净的文字了。而熟悉他的人,仍感叹郭风是“一位勤劳俭朴的老农。一位爱吃地瓜稀饭的老乡。一位喜欢早起开窗的人。一位爱花、爱蝴蝶、也爱榕树的人。一位充满幻想的诗人……”其实,早在四十年代,黎烈文评价郭风的童话诗就说过:“郭风先生的童话诗,给中国新诗开拓一个新境界,成为新诗坛的一朵新花……”。五十年代以来,郭风突出的文学成就确在散文诗方面。这类作品多表现闽南乡间风光和具有乡土特色的生活情景,抒发作者对乡土和祖国的挚情。新时期以来,他的作品追求自然、本色、淳朴,具有更广阔的历史感和更深沉的哲理意蕴,体现了大家之风范。不过,我阅读了他从花甲之年步入古稀之年的绝大部分作品后,却惊喜地发现,《叶笛集》只是郭风创作生涯的一个纲要,一个里程碑,他的新时期的散文,则是他创作生涯中突破固有格局的最重要的高峰,这便是他作品中出现的对于时代和历史的沉思,对于时局、世情、世态的特有的关注、诤言及告诫,再现人世阅历的丰富和具有历史见证的性质,以及顿悟彻悟的大智慧。诚如八十年代期间,有一次他与我谈及冰心、巴金以及施蛰存等老人的散文作品时所说的那样:“当代一些老人作家所作的散文作品,可能出现某种新的文学景致。”许多人,包括我本人,以为把郭风的这一时期的散文列入这一真实的、具有强烈时代性格的“特殊的文学景致”中,是当之无愧的;由此,我在2004年8月4日的《福建日报》上发表的一篇关于郭风创作的文章中,就表达了这样的看法,但他看到后却笑道:“如果能与这种文学景致取得某种和谐,或者可得言:自己无负于学文五十余载。”
也许,正是他决心“无负”于五十余载的“学文”,数十年间,他一直惯于晨起作文,极少间断。但最令我不解的是,除了读书和写作,他基本不看电影不看戏,不参加娱乐活动。我陪同他走过不少地方,知道他有早睡的习惯,晚上看完电视新闻联播后的唯一节目就是上床。因此当地东道主要来请他晚间出去喝茶吃夜宵赏夜景一类的活动,都被我挡住了。我也只好如实用郭风的话对各地的来访者解释说:“这没什么,各人的习惯不同吧!”
三
事实上,人们都知道郭风是一个著名的散文家、诗人、儿童文学作家;但又有多少人知道,他还是一个资历久长、经验丰富、成绩斐然的编辑家呢。
他的编辑生涯应该从1938年主编文艺期刊《铁群之鸟》算起。之后,1945年又在福州改进出版社主编《现代儿童》;从1949至1978年,他还先后在福建省的文学期刊《园地》《热风》,以及《福建文艺》《福建文学》任职过。几十年来,他除了坚持创作大量的独具特色的散文、诗歌外,一直都在这甘苦不易为人所知的领域里,和普通编辑一样默默无闻地辛勤操劳着,既为许多作家提供宝贵的园地和养料,也为他们的前进拓宽了道路。
我是他的同乡。初出茅庐,便得以庆幸地在他手下工作,这使我有机会窥见到他身上的许多令人钦佩的编辑作风和工作热情。记得在他在《福建文学》工作期间,还为福建人民出版社主持《榕树》文学丛刊,我也成了其中一名兼职编辑。我看到,郭风从不用打印的约稿签,而是亲笔写信向外约稿。有时候一天要写十几封信。他向我说过,用约稿签让收信人看了不亲切。还说,“约稿当然要慎重,要想好了再约;还有,约来的稿,除非政治问题,都要尽快安排发表。”有一次,我正在编辑部处理来稿。他看到后便点点头走了过来,问了几句,他就说起他年轻时第一次给刊物投稿的事情。他记得十分清楚,他有一篇习作就是在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上发表的。茅盾先生的这一提挈,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他步入艰辛而又诱人的文学道路,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他告诫我说:“作为一个编辑,应当把主要精力用于发现和培养文学人才的、有着特殊意义的工作,而不能只是淡漠地、机械地像在履行某种公事,那样是极有可能使一些具备文学才能的年轻作者遭殃的!”说到这里,他笑了笑,又说:“所以,编辑一定要自觉地培养责任感,要锻炼眼力……”
还有一次,我和同事们正在编辑部讨论如何改进处理来稿的工作方法,大概是我们的话声被开会刚回的郭风听到了,他就从门外走了进来。他二话没说,一下就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几个“能不能”叫我们思考。
他说:稿件一旦被选中并决定采用,为了尽快让作者本人知道,能不能采取打电报通知的办法?
他说:文章打出清样后,能不能另寄一份给作者校阅或留存?
他说:一俟清样正式送厂付印,能不能就给作者汇寄稿费?
他在说话的时候,我发现他的眼睛特别静穆,声音里有着一种可以触摸的温厚。我甚至忘了他是什么时候又悄悄离去的。我奇怪地感觉他仍站在那里,如同他自己在一篇散文诗中写的那样,“只有站立得住的人,才站立在那里。”不知为何,这一天的情景我至今难忘!
那时候,作者常常来《福建文学》编辑部送稿,由于他的名声,许多作者都直接找他。在数不清的场合里,他总是十分真诚地接待他们。当时,编辑部的一间大房间排列着八九张桌子,我们就分坐着看稿编稿。我位置离郭风近,常常傍听他和作者的交谈。我发现,郭风看过他们的稿子后,通常他都不直接谈意见,而是放下稿子,先是询问他们的生活以及周围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随后才切入正题。如果他对作者的作品深有感触时,就会做出几分强调而又优雅的手势,并且点点头:“这稿件就先留在这里,我给其他人再看看”。 待送走了作者,他会立即坐下来开始编辑。事后,他也会把编好的稿件让其他人看一下,并亲自签发。许多作者可能都不知道,凡是他选留的稿件,或早或迟,他都会想办法用出去。我还发现,他似乎很少否定别人的作品,但又总是强调作者要切实接受生活经历、艺术修养和思想锻炼的磨砺,并常常用很有说服力的逻辑来表达他的观点。那些年,有时作者在写作中遇到困难,他总是想方设法与有关部门联系洽谈,尽力提供条件予以帮助;有时作者发表了较好的作品,他又总是不失时机地写信去鼓励他们,提出更高的要求……他对年轻人由衷的关切和奖掖,使人从心里更加充实了对这位仁者和长者的崇敬和仰慕。
他是在担任刊物领导工作期间戒了烟的。十几年后,依然绝口不抽。我记得他当时公开表明,他戒烟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为了谢绝作者难以推辞的敬烟。如果说那时他还有什么别的嗜好的话,那就是每天走路来上班。这时,他的气质中最富活力的散文感觉和童话感觉就会旁若无人地凸现出来。当时,我与他同住一幢公寓,离编辑部不过十几分钟的路程,便常常一同上下班。有时候,他一边走路,一边会注意经过的路旁桥边,在各个季节和不同气候里相继开放的小花。他曾对我说过,他实在是多么地喜欢它们。我至今还记得有一次他指着巷道小河沟旁的一簇小小的花卉说:“厉害!在这样的地方,它们居然能开出自己的花。”那一天我听他这样说时竟突然想到:这也许和他在工作中一如既往地密切注意到那些不知名的作者的作品,也有着某种联系吧?但他毕竟年纪大了,每天走路来上班,爬上四层楼,往往有点气喘吁吁,大汗淋漓。我真担心他会累倒,便利用一次在外组稿的机会,给他写了一封信,劝他注意身体,谁知他随即寄了回信来。信上说:“……年岁是大了,但我必须加紧工作,以有生之年,力争多做贡献吧!惜能力有限耳!”
即便后来,他已离开工作岗位,每天还总要抽出一些时间,亲自处理各地作者寄给他的信稿。甚至每月中至少要写二三篇作品读后感或序言。他认为多做这方面的工作,是责无旁贷的。难以置信的是,退休以后,他在全国报刊上不但时有佳作问世,而且陆续主编出版了《曙前散文诗集》《黎明散文诗集》《外国散文诗集》《外国百家散文诗选》《中国散文诗选》《中国百家散文诗选》以及《散文诗选》等诸多大型丛书,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
四
有人说,郭风在多年的散文、散文诗或诗歌创作中,描写爱情的篇章可谓“凤毛麟角”,更遑论把自己作为爱情的主人翁。纵观他的全部著作,事实的确如此,但又不尽如此。例如他在1945年至1949年之间,就写过十几篇散文、散文诗及读书随感和札记一类的作品,每篇题目下就明白无误地写上“致E.N”的字眼。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他把这些作品收进他的一本题为《开窗的人》的散文旧作集子中时,我读后就发觉这些作品无疑是一束情书,只是年轻的郭风对他钟情的那个“E.N”的反应和观察,常常仅只含蓄地、甚至有点羞涩地通过自然和气候的感触进行叙述和暗示罢了。也许那时的郭风就是试图以这种形式来叩问一位少女的芳心的,但无论如何他显得太彬彬有礼,而且“用心良苦”。其结局可想而知。又例如他直至老年,又通过他的散文《人生》,大胆庄重地假借作品中的友人道出他内心的一个从不告人的“秘密”:“我曾思念在我和亡妇结婚之前的那位恋人……”而这位恋人,正是当年的“E.N”。 有一回,他没有掩饰地向我讲述其实在他作品中早已是公开的秘密时,他的简短的、银白斑驳的头发下的那张细润中透出白皙的脸庞,不禁泛起些许淡淡的忧伤,但更多的,却是他眼中闪射的一种可亲的老人特有的达观精神。他向我解释说:当年的“E.N”确有其人。他写的那些文字,是用化名在若干期刊上发表的,但始终未发给这位他所倾慕的人。而郭风在散文中也曾借用第三人称这样写过:“他始终未曾向这位女子表达自己的心事。但情况又的确如此,他至今有时还会暗自念及曾经和她一起散步过的山间草茎,念及那座小山村,杉木林、小溪和小溪上的浮桥以及散步尽处出现的一座小小土地庙……
不用说,在同辈作家中,郭风对待爱情可说是极为谨慎的,甚至有一点守旧的影子。在这方面,他给我的印象是:他是个情愿克制自己对女人的情感的人。也许他有过爱的幻想,但那是永远不能实现的。以致他六旬失偶,有人赠他以诗,劝他续弦;有人向他提及:夜间,最好有人代你扭亮灯光等等,他都一概婉谢。
也许,这也是“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类型吧。
说到郭风的“爱情”,自然要说到郭风和他深深挚爱又深深怀念的已故的夫人。虽说,他和他的夫人的婚姻是当时难以摆脱的封建宗法观念束缚下的产物,但他们俩都有一颗金子般善良的心,从而使他们奇迹般地在屈从之后建立的家庭中,产生了相互了解、相互体贴的充满人性的爱情,并得以在一起相依相伴地生活了四十多年。
记得我到《福建文学》工作后,有一次,郭风曾请我到他家品尝他夫人亲手做的一些地道的莆田故乡的小吃。席间,他曾感叹地对我说:“我的家庭一切都是由我爱人料理的,买菜、做饭、洗衣。而我几乎不会做什么。”随后他还提起,大约是40年代初期,他到永安、南平就读,当时所得的稿费仅只勉强维持在学用费,因此家中一切由他的夫人和他的母亲支撑着,但他的夫人和母亲仍尽力省吃俭用,还不时托人携带肉品来,为他增加营养。正因如此,他才得以安心在外,进行研读、写作。记得郭风还曾说到他在“文革”中居于牛棚时,他夫人如何不畏艰辛,如何料理家庭和照顾儿女的事。说着说着,动了感情,连眼眶也有些发红了。
我还记得,在我和郭风一道工作的那些年间,若是下班前外面突然下起雨来,没多久门外定会响起郭夫人的声音:“阿桂(郭风的小名),伞放在这里了。”这是郭风夫人在下雨时必定要充当的角色。但她似乎从来没有走进办公室,从来只是把雨具放在门口后又匆匆冒雨赶回家去,而她可能也从来不知道她离去的背影上,投注过许多人崇敬和感动的目光。
郭风夫人的一生可算是真正默默无闻却又一直为家庭、丈夫和儿女默默奉献的一生。她是个有知识的女子,但与郭风结合后,便心甘情愿地变为一个贫寒的、恬淡的家庭妇女,数十年如一日,任劳任怨,毫不计较。这使郭风每每念及,往往内疚甚深。郭风夫人去世周年时,郭风曾交给我一篇散文《致亡妇》,在如泣如诉的文字中,他表达了他对夫人的深切悼念和动人心弦的情意。文章在《福建文学》发表后,曾传诵一时,至今仍有刊物加以转载。请允许我在这里照录这篇散文开头的一段:
“我常常觉得你仍然在我的身边;或者说,我仍然在你的身旁。我仍然觉得你时刻在勉励我,例如,此刻,当我自己在书案上整理文具时,我似乎感到仍然有一双温柔的手,一双为我所熟悉的手,一双因家务沉重而显得粗糙的手,在旁边帮助我;我以为这不只是帮个忙,这中间具有对我最亲切的勉励和体贴。……我常常觉得我们的心仍然在一切。我们互相信任的、真挚的心一起跳动。”
与其说这是散文,不如说这是一首诗。这是一个著名散文家和夫人彼此间深切的爱和不尽思念的交响诗!数年后我重新读这篇散文时,如同当初那样,似乎执著地相信并真切地看到了郭风在写下这段文字时泪水曾夺眶而出!
看来,郭风在家庭和爱情方面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未得到的东西,尽管他有个暗自思念,但他懂得如何克制;他已得到的东西,纵然绝非完美无缺,但他也会极力去珍惜和庇护。在这一情感生活中,他就是这样塑造着自己,并愉快地胜任着这个角色,也许,在他看来,这也是对人性了解的一种透彻?
五
乍见到郭风的人,都会发现他眼神的静穆,鼻梁的高挺,声音的宽厚,以及他身上的那种至可亲近的情趣。而他素来也确以亲切安详、平易近人著称。我有一个最深的印象是,我从来没有看到他发怒过。不管是在担任福建省文联领导期间或担任福建省作家协会主席以来,他从来没有对谁大声说过话。他的确没有一点架子,甚至不懂得什么叫架子,任是谁,也别想在他身上找到一丝半点知味辨色的味道。相反,他同许多人,特别是同他一道工作的作家、编辑和普通人员,却有一种宛如他同大自然那样物我两忘、平等交融的情谊。在这一点上,我情愿说,他是完全文雅的,并且是十分包容的。譬如他喜欢何为严谨认真的写作态度,喜欢蔡其矫浪漫的生活情调,喜欢我省中青年评论家的胆量和睿智见解,喜欢当时在散文诗歌创作方面涌现的一批男女作家和诗人。还譬如,私下里,他喜欢听袁和平以诙谐妙语谈论插队在内蒙的经历,也喜欢听我和其他人以不加掩饰的方式描述社会见闻,即使他听得想捧腹大笑,但最多只是撇撇嘴,耸动肩膀发出欢快的笑声。又譬如他和我们外出采访或下乡,不论有时吃住条件怎样不尽人意,他也总是说:“好,可以,可以。”他似乎天生具有不忧郁的随遇而安的高贵性情。
然而,不知是他文学气质中一种无邪的童心使然,还是像他这样年龄的老人特有的一种洒脱所致,在许多场合,他往往会随意地说出一些不失幽默的话语,作出一些令人忍俊不禁的举止。
有一次我陪他去闽北参加一个地方行业的文学笔会。开幕的那天,各方领导都在台上就座,他也在其中。当主持人宣布笔会开幕时,门外适时爆响了一串鞭炮,这使笔会顿时增添了几分庄重的气氛。接着领导就陆续开始念讲话稿。但说的无非都是那些坐在台下的人早已听得不耐烦的话。谁知轮到郭风时,他却出人意料地对着麦克风抒起情来:“各位,这个笔会开得好,因为我看见有两只蝴蝶从窗外飞了进来;我看见那是两只小小的、孱弱的,但又十分美丽的蝴蝶,我以为,它们就是被我们的笔会所吸引而飞来的,由此我也被深深地感动了……”话音未落,全场已响起一片由衷的掌声和笑声。
数十年前,我和郭风等一批福建作家去四川采风,路过奉节,在一个酷热难当的近午步行去白帝城。走到半路,人人都觉得口渴难忍,恰好看见有个老头坐在一棵树下,以为是卖茶水的,便不约而同地都涌到树荫下。结果不是,那老头也是在这里歇脚的。大概是口太干了,郭风开始注意老头身边有一个粗瓷罐。他问那老头,里边有茶水吗?老头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也不知说了些什么;这时,大家惊异地看见郭风毫不犹豫地端起罐子,仰脖喝尽了罐中仅有的一点汤水。待他放下罐子,这才发现罐里剩下的都是中药药渣。我惴惴不安地问他:“这是什么中药?你怎么喝了?”谁知郭风却满足地抹抹嘴笑道:“是中药就好,喝了还能治病。”
在现实生活里,郭风确实有不少入俗但又不俗的生活小节,一方面,表现了他一贯的泰然处世的作风,一方面,也袒露了他对生活从不计较的朴实本质。但正如他早年的寓言、杂文一样,这位看去温和的老人,有时也能从他的思维和言语中,流露出一些机智和讽喻的特质。记得有一次,我们碰到了一个很会纠缠的作者。他寄来一篇稿件发表后,立即又寄了第二篇来,接着就天天打电话来催问什么时候能发表,弄得大家很头疼,这一天他电话又来了。但找的是郭风。谁也没有想到,郭风在听了他的一通诉说后,却不动声色地回答:“我讲给你听呀,这刊物好比一碗饭,你已吃了一口,剩下的就让别人也吃吃好吗?”据说,对方听了,竟也立即被逗得笑了起来。
由于我和郭风有较多的接触,我注意到在饮食方面,似乎各种食物他都喜欢。且有一条与我相似,早餐时特别嗜爱喝稀饭。若是外出数天,吃不到稀饭时,便会生出一种情不自禁的思念。有一回在武汉,他和我下榻的旅馆早晨不供应稀饭。他便同我一起出去,走过两条街道,终于找到了一家专门卖稀饭的小店。吃完回来时,他还兴奋地告诉同行的舒婷和袁和平。结果他们俩都笑道:“跑了两条街道,吃一碗稀饭又跑回来,肚子不又空了?”郭风却认真地说:“你们不知道,重要的是吃到稀饭时的那种感觉,特别好!”接着又补了一句,“今天去三峡没问题了!”
大约是受先天遗传或童年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郭风特别喜欢走向自然,走向山水。年轻时如此,年老时更甚。他的心,似乎每时每刻都应着自然和山水的律动而跳跃。他走过无数的地方,依然向往未去过的地方。每次外出时,他好像都换了个人似的,一改平日的恬淡、平静,显得兴趣盎然、神采奕奕。即便在家,也如他自己在文章里写到的那样,他搁下笔后,“总喜欢在暝色夕霏中凭窗眺望苍穹和远山,观赏雾雷雨电,观赏花木虫鸟。”令人敬慕的是,他往往能从不同的环境中,以超然的慧眼窥见大自然的美。他常说过:“从来不曾重复的,这便是自然。”他还觉得,谈论自然,将是毕生的事。难怪,许多人都在他晚年的散文中,往往能读出他内心世界的剖析和审视,读出几分难以效仿的禅境。
1989年秋天我调到省作协工作后,同事们和我似乎都有一个毋须明言的约定:除非万不得已,一般都不去打搅他。因为,他毕竟已步入老年了,并且他坚持每天读书看报和写作,时间对他来说显得尤为宝贵。也许,在他的人生辞典里,早已抹去了“停止”两个字。有时我们遇到郭风家人,询问老人状况,得到的回答都是一样的:每天,他还是那样早起床,洗漱毕,坐到书桌前,还是那样专注地继续他的读、思、写……
2010年1月3日郭风先生在福州逝世,享年94岁。他把自己毕生的精力献给了散文、散文诗和儿童文学的创作事业。值得记载的是,2003年、2007年,福建省文学艺术界曾先后两次举办祝贺郭风文学创作70周年活动和祝贺著名作家郭风90华诞活动,郭风获得了福建省文学艺术界“德艺双馨”的崇高评价。
此刻,我的回忆,我的歌吟
都在时光的隧道里穿行
我想唱出你的洁,像叶笛上的露珠
我想唱出你的纯,像夜空里的星星……
责任编辑 陈美者